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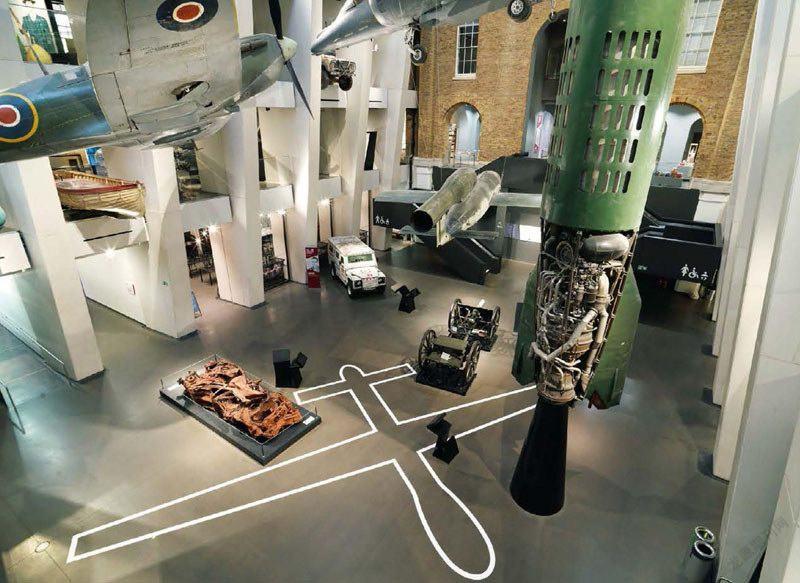

就地理空间而言,中国和巴西路途遥远,不过今天距离正被不断发展的信息与交通技术所缩短。即便如此,对中国来说,位处大洋彼岸,地球另一端的巴西,仍然属于陌生神秘叉魅力四射的国度。同样,在巴西人心目中,中国古老而富有吸引力。
中国和巴西之間的交流日益频繁,但显然不能局限在经济层面,文化艺术的交流也必然会随着经济互动而更多地开展起来。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举办的“对流——中巴当代艺术展”是中国和巴西在文化艺术方面深入对话的一次尝试,亦是中国观众了解巴西当代艺术的一个重要机会。中国和巴西各挑选了二十一位艺术家参展,其中不乏国际知名的艺术家,如隋建国、黄永砅、安东尼奥·迪亚斯等人。四十二位艺术家年龄各异,有已过花甲之年的重要作者,也有崭露头角的年轻艺术家,作品涵盖绘画、雕塑、影像、装置等不同媒介。
展览主题“对流”来自气象学术语“对流层”。对流层是大气层中最基础、最重要、最活跃的部分,也是与人类生活最为密切的部分。空气与水在对流层中循环,带来各种气象现象,也带来生命,所有的人类及生物几乎都生活在对流层中。人类共同生活的世界几乎就是对流层中的世界。在全球化进程正在走向多中心阶段的今天,世界各国之间的多维度交流依然相对欠缺。
“对流”很鲜明地体现出策展人的意愿:期待发生活跃的互动,甚至不可预测的猛烈碰撞。毫无疑问,对参展双方来说,这是一次相互展示水平、增进沟通的重要展览。艺术家们来自地球两端、横跨万里的两个国家,两个国家都是地域辽阔、文化丰富多彩的第三世界大国。作品既是使双方跨越距离彼此走近的纽带与桥梁,又是互为他者的参照物。我们能透过陌生国度的艺术家所呈现的作品,在视觉反差的基础上看清自己的位置和路径。因艺术相聚,相聚之后是彼此的再出发。
当代艺术经过全球化的撒播,已经成为某种意义上的世界语。“对流——中巴当代艺术展”跨越了中文和葡萄牙语的艰难互译,更多是在视觉图形和效果里便捷地言说与聆听。
当我们从一楼到三楼的展厅随意浏览时,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当我们把一些作品的展览标签摘除或互换,几乎谁也无法拥有十足的自信确切辨认出中巴艺术家及其作品。这个有趣的现象,似乎揭示出当代艺术的“视觉语法”极大地重叠其享。某些规整的几何图形,相似的物质材料,一时之间确实令人难分彼此。这种视觉语法的共通,无法与全球化时空的凝缩分开。现代技术驯化和改变我们的感官知觉,使相距万里的人也拥有类似的审美经验。这是当代艺术无法回避的共同背景。
但是,当代艺术拥有一种共同背禁,并不意味着彻底被它笼罩,以致放弃抵抗而主动呈现出无人称、无个性的风格。即便在相同的全球技术大背景下,当代艺术也因其所在地域而彰显出自身的特色。艺术家的个性,及各自地域的民族文化,虽被技术碾压,却并未粉碎。有智慧的艺术家仍能从中寻找到可能性和缝隙。
中国和巴西的不少艺术家,都善于利用深深根植于本土文化的元素与观念,这既是自身所熟稔的一种艺术资源,又是必须提取转化加以改造才能重新焕发生命力的事物。例如,巴西当代艺术的灵魂人物之一通加(新闻稿资料中叉译为汤加),他的《我、你和月亮》源自巴西多种族杂糅的文化,以玻璃和石英晶体等材料制作而成,这硕大高耸的雕塑装置立即就把人带到一个神秘的场域。印第安人、黑人等宗教的强烈萨满化氛围,于这件作品里得到了集中体现,传达出深邃而震撼人心的力量。卡通达的《冠军Ⅲ》是绘制于布面和织物上的丙烯作品,彩色的条纹与图案logo,像极了足球的球衣,充满着浓烈的巴西足球文化的符号与元素,展现出足球王国巴西植根于百姓心底的自豪感与荣誉感。
20世纪“文革”后首批留美的中国当代艺术家梁铨,他的《荷塘》一方面利用中国传统绘画的笔墨和宣纸等媒材,叉使用现代主义以来流行的拼贴技巧,最终成就了一种面貌独特的绘画。其中各种几何的图形,分明是西方抽象绘画的惯用语言,却因丰富的层次、大胆的留白,创造出一个具有中国传统美学意蕴的画面空间。他在创作中体现出来的中西方视觉文化的双重特色及互文性修辞成为其艺术风格形成的关键所在。余友涵既创作纯粹几何图形和色块的抽象画,也有借鉴中国水墨画的笔触构成的抽象作品,主要通过对视觉手法的探索并结合多重透视和对中国文化本体结构的研究,融合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社会主义时期的美术,以及西方现代及当代艺术的表达方式。傅中望受中国古代建筑的榫卯结构启发,一直将其作为重要的造型手段,《无边界》伸缩自如的层叠交接,造成繁复又单纯的效果。黄永砅的《桃花源记》更是对中国古代史上蕴含文人最向往之精神境界的篇章的再利用。
从视觉效果而言,中巴艺术家也各显身手。有艺术家延续着极简主义的逻辑,追求某种纯粹的简约;也有艺术家希望以强烈的力度打动观者。当今巴西最活跃的艺术家之一恩里克-奥利维拉,他的《冲淘》虽然是架上绘画,却因满溢的激情,看似凌乱到近乎疯狂的笔触,营造既抽象叉极其富有活力的生猛图像,一种动感的生命之流穿透空间,巴西人的热烈呼之欲出。帕拉特尼克的《W-H/1》是木板丙烯,表现出了大红色背景之下波浪般交织的线条,令人心潮涌动。圣克莱尔·切明的雕塑尽管体量极小,却因精湛的造型功力,传神地表现出神话人物的状态。
胡晓媛的《木/形》、王宁德的《有形之光/理想天空滤色镜》及王光乐的《水磨石》都专注于材料本身,而并不试图塑造出多么丰富的图形,只呈现一种看似贫乏的效果,给我们留下更丰饶的想象余地。隋建国的《盲人雕塑》放弃具体形象的塑造,只让手与材料自然相遇,展示手对材料的挤压、捏握,一种意想不到的力量由此产生。杨茂源的《得》系列则是将头像与陶器紧密融合,陶器嵌入人头,替换了人的面容,荒诞戏谑之余却带来了奇异的重力效果。
观念与视觉语言在当代艺术中极其容易重复,因此智慧和头脑对艺术家就不可或缺。宋冬的《双面镜子的界限》利用镜子之间的反射对映,使影像的效果变得错综复杂,荒诞夸张的动作不断重复,伴随着声音,仿佛一声一声地打在我们心里;无独有偶,安德烈·小松的《自动装置》因为镜子的加入,使空间切分得更像迷宫,人在其间穿行,压抑中又多了点趣味。路易斯·泽尔比尼的《无题(科尔梅亚酒店)》利用错视构图,使所绘酒店房间看似立体叉仍然隐藏。
巴西和中国同是以农业立国,劳动在社会生活里占有重要地位,如何处理劳动,成为当代艺术创作的一大问题。阿丰索·托斯特的《工作室系列》直接把农具作为现成品带进艺术创作里。他将农具的手柄雕刻成骨骼,以此哀悼数百年来曾在巴西种植园里被迫劳动的无数奴隶,并控诉罪恶滔天的奴隶贩子与种植园主。石青的《没什么不会改变》在方木上印上细腻的丝网图案,使实用的劳动材料自此一变,像一支支放大的铅笔,意味着之前的生产关系已彻底改变。
漫步在“对流”之中,中巴两国艺术家在作品之间构建起了直观的联系,在材料使用、图像风格、工作方法、问题意识、社会表征、历史叙述等不同的层面上相互发生连接,体现出两国艺术家在深处的共性,激发互相的共同体意识,呈现出了有意义的差异,促使我们更确切地回应当今全球化主题下的多中心议题。同时,展现了中国和巴西的艺术家在全球化境遇中探索自身艺术道路的努力:他们脚踩坚实肥沃的土地,精神却早已四处遨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