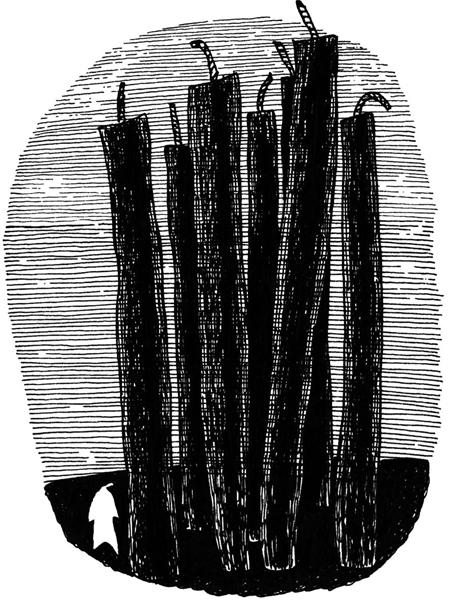
东汉末年,奸宦当道,社会动荡,400年大汉王朝大厦将倾。邦乱民危之际,汝南郡(今河南平舆县)名士许劭(字子将)、许靖(字文休)两兄弟发起的以评时论事、臧否人物为主要内容的谈论活动却成为污浊社会的一股清流涤荡人心,也成为了汉末社会生活中的一抹亮色。因为谈论活动固定在每月初一举行,时人称之为“月旦评”。“月旦评”问世之后,逐渐成为社会舆论的风向标。或人或物,一经品题即身价倍增。当时,士子官宦趋之若鹜,皆以入围“月旦评”为荣。“月旦评”俨然成为了东汉末期的“热搜”,也俨然成为了时人踏入社会名流门槛的“通行证”。宋人秦观诗曰:“月旦尝居第一评,立朝风采照公卿。门生故吏知多少,尽向碑阴刻姓名。”(《孙莘老挽词四首》其三)说的正是东汉末年,众多人物如“鲤鱼跃龙门”般通过“月旦评”名扬天下的事情。
那么,“月旦评”为什么会成为其时的“天下第一评”呢?
核心人物品格高峻,风姿超拔。据《后汉书·许劭传》记载,许劭“少峻名节,好人伦,多所赏识”,说许劭还在年轻的时候就自我要求严苛,注重名誉节操,讲究礼节,名声远播。许劭有个堂兄弟叫许相,靠荫袭祖业和谄媚权宦做了大官,曾经多次以封侯的优待去请许劭,但许劭不为所动,“恶其薄行,终不侯之”。另一位核心人物许靖,和其从弟许劭一样都是东汉末年有名的贤士,品德高尚,志趣高雅。董卓权势熏天时,曾慕许靖才名,将其招至麾下。可许靖很快就感觉到了董卓的暴虐和蛇蝎之心,不忍与乱臣贼子共事,干脆辞官不做,连夜逃出了洛阳,并因此得罪董卓。《三国志·蜀书》曾记载了许靖对这件事的自白:“党贼求生,情所不忍;守官自危,死不成义。窃念古人当难诡常,权以济其道。”正是有许劭、许靖这样出类拔萃的领军人物,“月旦评”才能够名满天下。
坚守准入底线,宁缺毋滥,宁少必精。“月旦评”不是什么都论,什么都评,也不是漫无目的,逮着什么论什么,而是有严格的预设和准入标准。大致来说就是,要么在当下具有重要影响,要么在未来具有重要影响,作为话题的人或物两者必居其一。而要做到后一点尤其不易,不但需要独到的慧眼,还需要高超的察人识物的功夫。就连后来大名鼎鼎的曹操,在还未发迹时都差点入不了许劭的法眼。许劭犹豫再三才将其作为品评对象,并给了评语:“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三国志·武帝本纪》)这样的评价可以说是有褒有贬,甚至是贬大于褒。但曹操仍然为上榜“月旦评”而喜不自胜,大笑而去。“月旦评”大获成功后,天下稍有名气或者还没有名气的人物纷至沓来,无论褒贬,皆以得到“月旦评”为荣。但许劭、许靖等核心人物不为所动,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月旦评”一直是叩门的多,进门的少。
评价结果客观公正、准确权威。“月旦评”评人论物坚持客观标准,不虚美、不隐恶。对袁术(字公路)的评价就是最好的例子。袁出身汝南望族,家门“四世三公”,身份可谓显赫。而“月旦评”论人不看家世,不看官位,只讲究“我口说我心”,是什么就说什么。给袁术的评价竟然是:“袁公路其人豺狼,不能久矣。”(晋·袁宏《后汉纪》)建安二年(197年),袁术称帝于寿春,建号仲氏。他骄奢淫逸,横征暴敛,导致江淮地区民多饥死、部众离心。后受到吕布和曹操攻击,元气大伤。没过多久,呕血而死。
能说明“月旦评”专业、公正,不为表象所惑的还有关于袁绍(字本初)的一件事。平时飞扬跋扈,连董卓、何进等权贵大臣都不放在眼里的袁绍,却非常忌惮许劭等人的评价。有一次,袁绍在前呼后拥回到汝南郡界时,竟然害怕在许劭那里得到不好的评价,就装作很俭朴、很低调的样子,轻车简从回家了。《后汉书·许劭传》说袁绍:“乃谢遣宾客,曰:‘吾舆服岂可使许子将见?遂以单车归家。”
对于东汉非常有故事的名士陈寔(别名陈太丘,成语陈寔遗盗、梁上君子即关于他的典故)、陈蕃(字仲举,“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即出自他口)二人,许劭同样给出了非常客观的评价:“太丘道广,广则难周;仲举性峻,峻则少通。”说陈寔交往太广,难免应付不周;陈蕃性情刚正,缺乏灵活性。
此外,“月旦评”评判人物还非常有前瞻性。比如前文说的曹操,在崭露头角时就被评价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一千多年过去了,这一预言已然家喻户晓,成为曹操这一历史人物的特定标签,被民间和史学界肯定。即便在徐州刺史陶谦(字恭祖)门下寄居时,许劭都能准确地作出预判:“陶恭祖外慕声名,内非真正。待吾虽厚,其势必薄。”(《后汉书·许劭传》)这一判断实际上也救了许劭的性命。在他离开徐州南避扬州后,陶谦果然凶相毕露,残害了许多曾经的宾客和幕僚。
东汉末年上层集团激烈的内部权斗,客观上给社会中下层民众带来了一定上升的社会空间,这也是“月旦评”能够生存的社会基础。然而,无论是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还是为世人乐道的竹林风流,天下士子们面对日渐腐朽的上层社会,都无力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月旦评”如流星般划过历史的天空,留下的却是天下士人“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精神。如果历代统治阶层都能像春秋时期郑国的子产那样,不但“不毁乡校”,而且能认识到民议、民声的可贵,历史或许将会是另外一番模样。
童玲/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