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所
我已经跨进门去,却赶紧又折返出来。我想再确认一下店牌。诊所!没错,是诊所。店牌上清清楚楚地写着:济玉路诊所。再次进来,在那个黄大褂的身后,仍然是一个个书架,上面各式各样的书码得整齐。
黄大褂说,你坐下。
我坐下了。
我发现黄大褂的两只眼睛很浑浊,像极了外面乌蒙蒙的天空。我于是盯着他的眼睛,使劲儿往里看,一直看到他眼睛里很深很深的地方时,才发现那最深的里面没有浑浊,全是清澈,像极了我常常梦见的一潭蓝蓝的湖水。
他说,你哪儿不舒服?
我开始说。我一边说他一边盯着我看,脸上慢慢呈现出惊诧。
他说,你怎么只张嘴不说话?
这回轮到我惊诧了。敢情是我说了半天,根本就没有发出一点声响?这我自己却并不知道。
他说,你张开嘴。
我张开嘴。
他反复看,然后陷入沉思。他抬头看着我说,很奇怪,你的嗓子绝对没有问题。
他起身,从后面书架上抽出一本书,很厚,递给我。我看了下书名:《百年孤独》。他说,你先翻翻,然后跟我做发声练习。
我的声音尽管很微弱,好在总算有了。
他说,注意不要太尖细。
我问,我是不是得了“伪娘”病?
他说,不像。
他问我,你是不是平常不怎么说话?
我说,我过去是一个很愿意说话的人。
那为什么后来不愿说了呢?
随便举个例子吧。有次,老板带我去参加一个应酬,到达酒店后,我看到一块古色古香的匾额,上书四个大字,我脱口而出:杜甫能动。老板看了我一眼,吃饭时老板说,你多吃点。过了一会儿,老板又说,这是我最后一次带你出来了。你知道吗,那四个从右往左的大字是:勤能补拙。
想不到现在的书法真是害人!
黄大褂说,这是网上的段子!
我纠正他说,你错了,这事是真实发生在我身上的。那网上的段子最初也是我发上去的。后来我不得不离开了那家单位。
就因为这事?
当然不会因为这事。是因为一单生意,要外包,大家都同意,可我却说,接手的那人不是老板家亲戚吗,这怎么行?我以为只有我知道接手的人是老板家亲戚,原来大家都知道,但大家都不说。就这么离开的。其实据说,我是可以提副总的。
为什么没提呢?
因为有次与老板和老板的一个朋友一起乘电梯,我不记得是男朋友还是女朋友了,老板不小心放了个屁,很臭,场面一度尴尬。老板看着我问,谁放的这是?我看了看老板,没吱声。后来,听说评价起我这个人时,老板很确定地说,他这人,缺少担当,不太能胜任领导角色。我哪里知道老板对人才的考察会如此严苛。
后来呢?
后来,我去了另一家单位。这家单位的大领导是刚从上面空降下来的,他在单位食堂搞了个小包间,职工在大厅吃,单位的几个领导躲在小包间吃,有专门的服务员,而且饭菜一分钱也不用花。不少职工调侃,从大厅到小房间,看似不远,但即使搭上一辈子的努力也未必能达到。我很看不惯,就跟一个同事交流起这事。有次,我这同事打了饭菜也去了那个小包间,没想到进去一会儿,饭菜就被扔了出来,而且在大厅里就餐的人都听到了一句让人很伤自尊的话:你也配进这个房间!后来,大领导追查责任,竟追到了我这儿,说是我鼓动的,就把我以不搞团结为由,给开除了。
我看到黄大褂听得认真,好像也是一直在琢磨,他先是从后面书架上抽下一本《历史的教训》,但犹豫了半天后,又放了回去。重新抽出了一本《呐喊》。他说,我觉得你需要喊一喊。同时,他问,如果不给你翅膀,你能不能飞翔?
没有翅膀怎么飞?但我想了想后,回答他说,能!
他点了点头,说,好。
他继续说,只要能飞,血压慢慢就降下来了,过去有点淤积也不要紧,会慢慢展开。只是你的气色……
我的气色很黄。
是,很黄,可怎么回事呢?
我失眠得厉害。
怎么会失眠呢?
不瞒您说,我的听力不知为什么这么好,这么强,只要有一点声音我听起来就跟打雷一样响。我靠山住,按说够僻静的了,可我总觉得山上有不知名的虫子在不断地叫。
黄大褂起身,拿过了一本书,说,你可以看看《三言》。
我问,什么是三言?
黄大褂说,就是喻世名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同时,你也要注意多听听你喜欢听的话,听自己喜欢听的话,时间久了,耳朵自然就钝了,不会再那么敏感。
我觉得黄大褂说得有理。
黄大褂像突然发现了什么似的,问我,你的眼睛怎么有点红,平常也这样吗?
我说,平常……也许……可能吧。总之是不时有些雾霾,有些风沙,有些烈日……
黄大褂说,我还是送你一副滤镜吧。
我接过来戴上,这一滤,我看到黄大褂身后是一排排的草药橱,每个橱上都写着名字:风化硝,六和曲,水安息,甘露子,古山龙,叶上珠,白头翁,白芥子,冬凌草,半枝莲……
我起身,走过去,取下滤镜,想看个真切,迎面却都变回了书架和书,我看到其中有一本叫《桃花源记》。我刚取下,就被黄大褂夺了过去。他说,这味药,并不治病。他又说,当然,几十年后,一百年后,你倒可以去那地方看看。但现在不行,现在去,会害了你。
黄大褂的话,很高深,好多我都听不懂。我出了诊所,来到大街上。我能清楚地听到大街上人声鼎沸,但仔细看时又觉得好像空无一人。
这座城市的所有街道都是以玉来命名的,各种各样的玉,五花八门,证明着这是一座与玉的质地完全相等的城市。
已经走出去好大一截了,但我好使的耳朵仍然听到一个女声在问,那人走了?走了。怎么感觉那人跟块石头似的。我没听到黄大褂再搭话,我想他应该是在沉思,也许在他从医的这些年里,他还没遇见过一个像我这样的病例。
其实也可以这么说,我天南海北走过那么多地方,还真没遇见一个敢把书本开成药方的医生,更不肖说弄几排书架放几排书就敢挂牌问诊的。
这世上不只我有病,医生也有病。我跟黄大褂的关系到底是医患关系还是病友关系,谁又能说得清!
不过,石头如果冥顽不化,也便接近了玉质。
那个谁
一
那个谁,我觉他有问题。请讲,什么问题?
他经常带女同事出差。
这有什么问题吗?
那女的是他老乡。
是吗?但,是老乡不能说一定就有问题吧?
那女的很年轻。
是吗?但,很年轻不能说就一定有问题吧?
而且很漂亮。
是吗?但,很漂亮不能说就一定有问题吧?
关键那女的很注意打扮。
是吗?但,很注意打扮不能说就一定有问题吧?
他们拍了好多照片。
是吗?但,拍很多照片不能说就一定有问题吧?他们拍的是两人的合照吗?
不是,是群照。但他跟她每次都挨在一起。
二
那个谁,可能有问题。请讲,什么问题?
他出差时常常带着两位女同事。
是吗?这有什么问题吗?
带两个,不太合适吧?
为什么要这么说?
因为从工作看,他带一个就够了。
上次,就你反映的情况,我们专门跟他谈了话。也许,他觉得带一个不好,他在改正。
三
那个谁,应该有问题。请讲,什么问题?
他最近经常带三个女同事出差。
是吗?这样是不太好。他为什么不带男同事呢?
他单位没有男同事。
噢,是这样。那么你觉得他跟三个女人都有问题吗?
这不好说。这事主要还不在他跟三个女人有没有问题,而是这么成群结队的外出,花枝招展的,哪像是工作,更像是旅游,而且无形中也增加了行政成本和基层负担。
上次,就你反映的情况,我们专门跟他谈了话。也许,他觉得带两个不好,他在改正。
四
那个谁,绝对有问题。请讲,什么问题?
他经常一个人出差。
是吗?这有什么问题吗?
如果单纯是工作,为什么把单位的人全抛到一边,一个人偷偷摸摸下去呢?恐怕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吧!
上次,就你反映的情况,我们专门跟他谈了话。也许,他觉得还是一个人出差更省心些,他在改正。
五
那个谁,问题不小。请讲,什么问题?
他作为主要负责人,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是吗?可能单位工作忙脱不开身吧。
即使再忙,也应该要多了解基层的情况。起码,每年要保证下基层搞调研的时间,这文件里可都是有规定的。不下基层,不搞调研,这是违反上级指示精神的。不出门,怎么决策?或者说怎么能保证决策的正确?
上次,就你反映的情况,我们专门跟他谈了话。他可能正在改正,但他不出门是不对的。
六
那个谁,问题绝不简单。请讲,是什么不简单的问题,是他跟那个年轻的,漂亮的女同事的问题吗?
是的。听说他跟那女的的父亲是同学。
是吗?这有什么问题吗?
怎么那么巧,她会在他的单位就职?
七
那个谁……绯闻
小城不大,真真假假有那么一帮所谓文人,整日里酸腐娇情,但真正纯粹者不多,冯君算一个。冯君原在政府部门工作,有着令人羡慕的职位,但为了文学,他选择离开机关,去了一家企业。某天,小城的文人们都收到了他的一封信,信中有他“长篇三部、中短篇多部、其他不可计数”的写作计划,要求文人们监督他执行。我猜想这一定是在他醉酒之后所写,亢奋激动,情之所至,豪言壮语,并不由人。我知道,他爱酒场,但却并不善酒,只要稍饮一点酒,就能让他产生无限幻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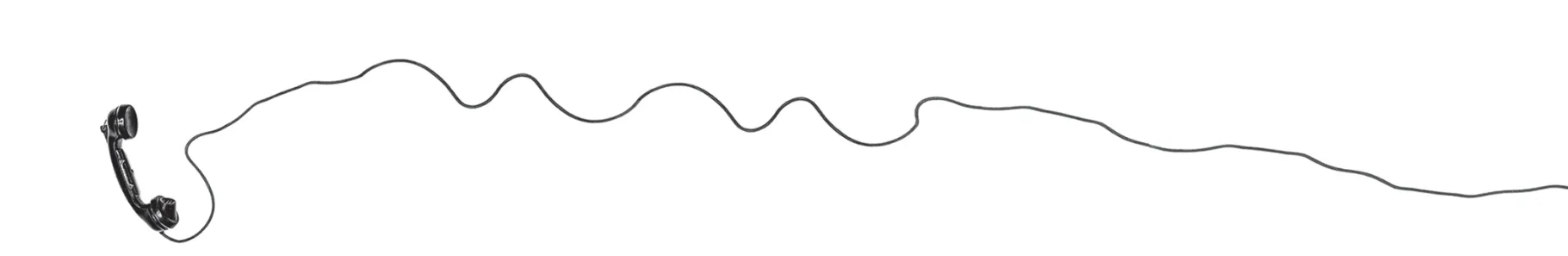
他所在的这家企业,宣传部门是一位女领导,人长得漂亮,思维清晰,行动泼辣,能力超群,独当一面。冯君虽然年长她一些,但在她手下却唯唯诺诺似小媳妇一般,两人仿佛置换了性别。本来,大家很想拿他们二人打打趣,搞点成人间的笑话,却不想正中了他的下怀。一待有酒场,寻着机会,他便很神秘地跟身边人交谈,并悄悄发问,我跟她的事你知道了吧?如果回答说不知道,他会惊讶,不会吧,外面传得这么凶,你不知道?于是,他会认真告诉你他们之间的事。我就被他这么问过好几回,看他那么神秘,我也很紧张,问他,谁呀?他说,还能是谁,她!我问怎么了?他对我表现出的啥也不知道,同样感到失望,说,这怎么可能呢,外面都在传。我说我确实没听说。他便举两至三例,细数他们之间的暧昧。
我印象最深的一例是,冯君说,她老公是公安,既精干,又帅气,身材高大,棱角分明,目光锐利。那天他去接她,她上车后,还专门回头看了我好几眼。我其实是很害怕的,但那一瞬间,我却有冲上去的冲动,感觉自己浑身是胆,很想对着她老公大吼一声。
我问他,你确准她回头了?确准。你确准她是在看你?确准。你确准……他打断我说,我见了她老公就害怕,你想想吧这说明了什么!
类似情境也发生在他和其他文友之间,但别的文友远不及我的友好和厚道,不仅表示不可能、不相信,还直接回赠他一些奚落。他便很急,急于举例,但文友们对他给出的事例,同样无情地举一件否一件。这让他很落寞,也很悲伤。
这段故事始终未能如他所愿风生水起,他便按下不提。
过了一段时间,当又一个酒场到来,我跟他又坐了邻座时,开场的前半段,一切正常,待酒过三巡,他扯了下我的衣角,我知道他有话要说。我侧低头,贴上他的肩,他悄悄说,你知道吗,有人要为我殉情。我一听,这不是小事,问他,谁啊?他说了一个名字。这名字不仅大家都熟,而且本人就坐在现场,在年轻的女作者中算得上是有姿色的一位了。他说,你听着就行,别看她。我问他,你怎么确定的她要为你殉情呢?其时,正是舞会正红火的时候,小城处处舞曲悠扬,冯君是各个舞场上的常客。冯君说,每次她都默默坐在一个角落里,有人请她,她大多会拒绝,而她不仅没拒绝过我一次,甚至期盼着我尽快邀请她。当我牵着她的手,走进舞池,我粗糙的大手轻轻从她的秀发和后背之间穿过去的时候,那一瞬间,她的脸微微泛红。有一次,跳累了,我们在舞池边上的窗前停下来,望着满城的灯火,我故意说,我真想从这儿跳下去。你猜她怎么说?她说,冯老师,如果您跳,我也会跟着跳下去。
关于这个桥段,冯君同样给许多人讲过,而且每次讲到“我粗糙的大手轻轻从她的秀发和后背之间穿过去”的时候,他的手都会立在那儿,讲完了,那只手也不会动,而是静静地等着你的表态,让你相信他。有位文友干脆把他立着的手扳倒,说,你说的这事我不信。
我们其实大都相信他们之间或许真有那么一场对话,但问题在于,在那个时间和环境里,这更多是一种会聊天的表现,不仅跟爱情扯不上关系,跟暧昧也仍然有着不小的距离。但到了他这里,事情的性质就不一样了,一切都会活色生香。
因此,殉情一说根本入不了小城故事。我能想象到他的遗憾和悲伤。
后来,有个女作者离婚了,自己在外面租房子住。一次酒场上,冯君神秘地跟我说,她离婚的事你肯定知道。我说,知道。他说,我怀疑这事与我有关。我表示惊讶,问,与你有关?他说,你看,城里这么多房子,她去哪儿不能租啊,可为什么偏偏要在我附近租呢?她都到了不怕别人说闲话的地步。我还想找个时间去看看她呢,你说我是去好还是不去好呢?
我已经懂得他的套路,问我去好还是不去好,显然并不是他要说的重点。重点是想让我知道,他跟那个女作者有不寻常的关系。我说,当然去看一下好。
那年的金秋时节,我在山上组织了一场诗会,小城文坛的前辈们都到了,冯君自然也到了。
冯君虽然始终没有写出几首像样的诗,但却从没有人怀疑过他诗人的身份。他浑身散发的诗人气质,会让人一目了然,也会让人过目难忘。也许正是因为他没把诗写好,所以他才比别人保持了更多对诗的虔诚。此时,秋风吹拂,层林尽染,金色的诗句俯拾便是。冯君立于一块巨大的山石之上,尽情张开双臂,接下来应该是一声长长的呐喊和一串群山之间的回荡,但他却对群山低声又低声地说了一句:我来了!声音轻得近乎无人听见。
夜的山,静谧,玄妙,充满禅意。
晚上注定是一场大酒。山上的人皆有醉意,个个张牙舞爪,狂放不知所云。醉酒后的冯君,歪歪斜斜攀山而去,直至不时从山腰间传回怪异的歌声。
早上,当一班文人还在沉睡之时,冯君便在房外的空地上,一遍遍喊:我的鞋子怎么不见了?我的鞋子呢?
冯君的鞋子确实丢了一只,但他并不可惜那只鞋子,而是心怀希望,这次能从某位女作者的房间里把他那只鞋子找出来,如此他便可以坐实一桩努力多年却一直未得的绯闻。这些年,他挖空心思,一直费心卖力地去制造一次次绯闻,期待大家去广泛传播,但每次的无疾而终都让他倍感失望。
他一直暗示我,可以写写他。而且暗示我,即使把我的绯闻按到他头上,算是借给他的也无妨。因为对他来说,他不是怕有,而是怕没有。不是怕多,而是怕不多。我说,问题是我也不“富裕”啊。他煞有介事地说,你让我怎么同情你好呢!
冯君后来养花、溜鸟、玩泥壶、做收藏,日子长了,偶尔也和我通个话,他那“长篇三部、中短篇多部、其他不可计数”的写作计划我肯定不会问,因为对他来说,这句话本身就是一部作品,已经千古。如果问,我也只能问问绯闻的事有没有新的进展。因为我越来越觉得,他配得上拥有一则像模像样的绯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