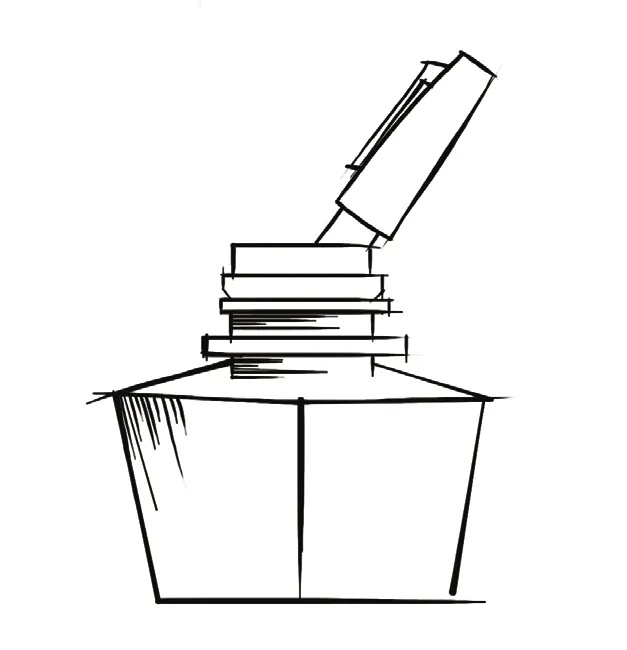
有一次阿巴斯说过,“每当我祖母要抱怨或表达她对某样东西的爱,她就用诗歌。”这位世界级的电影巨匠本人也热爱诗,不仅写诗,而且把他的电影拍得也像诗,譬如《橄榄树下》,还有《樱桃的滋味》。也许热爱诗,我们的生命就获得热情了,抑或充满了敏感和睿智。阅读袁东瑛的诗,在她看似平易平常又间或猝不及防的字里行间,仿佛跳跃着心灵的火苗,觉得那是词语在燃烧,变成了诗歌的烈焰,即使冷却之后成为孤寂的灰烬,却也已然灌注了一个人的全部生命热度。
《我一直在取悦我的歌喉》,是一组用絮语,娓语,轻歌和柔板协奏出的精神的咏叹调,这里没有急管繁弦,没有高声喧哗,只有款款流淌的低音区的生命乐章,然而也是带着落差和反差的个性触角的抵达和奏响。每一段每一节实则都镌刻着诗人自己对于大千世界的律动或者节拍的深深的依偎和眷恋。其心也诚,其情可感,其意味直抵肺腑深处,而我们对这些诗意的玩赏、掂量和捕捉,就如同一次山阴路上的漫步和游走,顾盼回眸之际,已经满足了爽心悦意的初衷。
袁东瑛的诗,是一位历练很深的阅世者的观感,描绘,勾勒及其窥探。这组诗的取材广泛,举凡整体局部,宏观微观,大事小情,幽微细节,可以说尽入法眼,不拘一格。然而无论她写什么,却都有着自己的法门,写属于自己的感知和见闻,写属于自己的情绪和烙印。
举例为证,在《乌镇:把时光弄旧》中,诗人的笔触闪展腾挪,将古典的心意和现代的流向做了恰到好处的焊接与处理。她写快节奏生活模式里凸显出来的乌镇的慢,写古风古韵里面藏着的人生襟怀和气象,写弄旧时光的氤氲的醉意,写忘了流年和归家的精神乡愁感。可谓笔笔皆如画,句句入声腔,也许诗人是把自己的身心魂魄都抵押给乌镇这隔世的古典写意和象征的乌托邦式的幻念。“把时光弄旧,便是乌有之乡/我迟迟不来,我有我的盘算/我一定是留宿过/吴越的正史和野史/不然我的心里/怎会留下乌墩与青墩的胎记……”,这样凝聚着中国古典风范和神韵的字句,某种程度上也是诗人自我精神世界的反光与折射,是在她个性中浸泡过的“词与生命的搭配和交接”。
在我眼里,真正的诗人是为时光留存精神物质颗粒的人,是贮存了灵魂养分和盐分的人。
诗人应该懂得生活的肌理构成,懂得方寸之间的情与趣,味与道。
袁东瑛的诗,已然走进了生活的腹地,融入了艺术的方圆,接洽了命运的召唤。这让她的作品呈现出某种包容性,开放性和普适性。当然,这会是稳中求胜的方便法门,却也是容易落入平庸的方便陷阱。你什么都可以写,却也什么都难以突破,难以博得头彩或者令人为之拍案。
我以为中国女性诗歌中,走险棋的人大概剑走偏锋,反而易于成名成腕儿,像翟永明,当年以“黑夜意识”为自己的荣耀奠定了基座,便是一例佐证。即便如李轻松,其诗凌厉高蹈,非凡人能够修炼达到。相比之下,袁东瑛走的是坦途,究竟也是难路。她的诗不追求奇险峻拔,但求在平常里冒出珍珠般的泉眼,写到佳境,就是令人连着惊呼三声,怎么可以这样!
我想说的是那首《皮影戏》,诗人写一个人在夜里,盘算着“木偶背后那一根根线索/机关与暗道”,她琢磨着人世间的一些道道,就从生活表层升华到了哲理的制高点,木偶是被表演者操纵的,关键是诗人写道自己也像木偶,得接受命运的摆布,听凭生活轨道赐予的爱恨情仇,更有意味的是她不甘心如此,她渴望来一次再生,“重新分裂一次自己”,哪怕抽干身体里的血,这是脱胎换骨吗?这是凤凰涅槃吗,这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吗?《皮影戏》写得不落俗套,尽管也有俗套的影儿,但写到最后,诗人翻身了,她在结尾处要“另选骨眼/用枢钉或细牛皮条/搓成一根结实的肋骨/给木偶按一个/真正的腰板”。我为之叫绝的是后面这些,有点女娲抟土捏人的意思。艺术家不都是创生者吗,不都是每一次会给自己笔下情境还魂和放生的人!
这样的写法,才是潜流激荡下的水花,才是柳暗花明后的写照。
看起来在袁东瑛的内心深处,始终游走着对风物人情理趣哲思的潜在打捞、探测和开掘。她的诗由表及里,由内到外,让人感到是在挥发着时间的香料,用以确证某种不可思议的悟性渗透到了词语的幽邃之处。读《干枯的芦苇》,你会觉得诗人是借助物象延伸触及到了对于生命本身的洞察与思索,她说,“它的哀伤,是囚徒似的/身体少了生鲜,哪怕瑟瑟发抖/我都想看见,那已旧的血/在周身沸腾一次”,由物到人,从品相到内心,作者将干枯的芦苇象征化了,隐喻化了,不知道因为什么,我读完全诗,就想起“哀莫大于心死”这句话的分量。《干枯的芦苇》折射着女性本体的抗争和诉求意识,她有恨,却已然恨过了,此刻一句真正的哭声都没有,哪怕连一句谎言都听不到了,爱退潮了,只剩下芦苇式的灵魂在干枯凝结憔悴。
诗人还写到一条狗,写到歇马山的杜鹃,写到卫河边上的风浪,写到登凤凰山的旅途观感……她笔端生发着与世间许许多多风景风情和风物的交接碰撞契合悖逆等等错综复杂的隐衷与幽情。她时而赞美,时而唾弃,时而惊悚不安,时而凝重安详,时而鼓噪而歌,时而静静俯视,时而徜徉其间,时而逃离其外……反正随着情感体味的不断历练,淬炼和摩挲,作者笔端遂挽起了精神的雷霆风暴,抑或细浪流沙。
其实,写诗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修心修行。那悟性不是总有的,那灵感不是常在的,那艺术的火花必经生活本身若干情境的触发,砥砺和助燃。
当年弘一法师曾有一句修道箴言:身居万物中,心在万物上。诗歌创作,其实也如修行,要有眼界和气魄,要有肝胆和心胸。
读袁东瑛的作品,觉得她已入道行,但距离理想的大化之境还存在一定距离。说心里话,中国当代诗人也都跋涉在半途上,修炼好一点的在半山腰,修炼差的还在山脚下。他们没有理由骄傲和自豪。难能可贵的是,有许多拥有自知之明的爱诗者,还像西绪弗斯一样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地推石上山,这其中袁东瑛是值得重视的一位心灵探索者。
读她的诗,感觉那里萦绕着一股盘旋的活力,活跃着一份挣扎的求索,涌动着坦然的贴近,逼视和裸露。诗人总是试图透过外表走到事物深处,越过外层空间进入心灵的腹地边缘,那是通往诗性精神的不归路。
她有一首《我珍藏疼》,写得简单纯净,明媚通透,将一个人的疼痛感与幸福感做了很有分寸的比照,“我珍藏疼,像珍藏着一笔财富/有人不敢炫富,我不敢喊疼/生怕/疼一旦走漏了风声/就会有那么多同情的手伸来/把我变成了乞丐/我更怕,此生还不起/那些善良的馈赠”。诗人是敏感的,也是敏锐的,是小心的,也是大度的。
袁东瑛处理笔下的生活素材,往往带着一丝觉察和反省,她不轻易地在单向度思维方式上模式化自己,而是力图寻找到另一种方向和方法上的表达和超越。在《致槐花》中,诗人移步换景,尺寸之间铺展开浓郁的情怀,她写道,“我走的很慢/生怕漏掉一丝的槐香/啊,满山谷的甜/需要和苦过的人交换”,这是生命意识的观照与聚焦,是人格物化的审美写照。
她写《春分》,也带着自我灵性的体味和打磨,说“南风带走最后一朵雪花/春天,才按原路返回/蝴蝶敢接近那些花蕊/燕子敢带来一些雷鸣/这一刻,我想起身/去向大地/讨要二分之一的人间”。这里以节令入诗,满口吻是美丽的戏谑,是款款幽情,接着诗中涌动着如下的曼妙说法,“这个黑与白的世界/我是它过去的时光胶片/春分过后/那些黑/覆盖过多少个白/那些白就会洗净多少个黑……”,融融笔致里,衬托着有底蕴的洞察与揭示,显露了袁东瑛的细腻和通达,舒缓和纡徐所在。
其实,真正的诗人无论如何表达,都是属于自己的一种姿态。读《在泰山》,我喜欢的就是作者看似卑微实则自尊自爱的那个姿态。意在笔先,心与物洽,从文化传统和诗学精神上,当然承接的是宋人的写法,或许作者就是潜意识里做到了这一点,她是从具体而微的物象开始,“一座山被云雾轻易地隐去时/鸟鸣正在试探它的底细/泰山,扑朔迷离”,她试图理解泰山之谜,毋宁说也是人生价值之谜,她想到司马迁,想到了鸿毛的轻与泰山的重,接着诗人笔触一转,以无限谦和冲淡的笔调写道,“我不敢做进一步的比较/我确信,鸿毛如我/在玉皇顶上/有扶不稳的轻/有不敢振臂高呼的恐惧”,继而,诗人淡定自若,找到了人生的正确而又自信的姿态,“很多人在‘五岳独尊’前/独尊/而我只在无字碑前/默立”。好一个默立,我觉得这也是诗性的魔力。想起鲁·布拉卡的说法,诗歌会在沉默中处处出现。一个默字当头,无限蕴含尽在其中。
或许,有什么样的人,就选什么样的词,就写什么样的诗。
这是词与生命的搭配和交接。
袁东瑛的诗歌命数里,有火,也有水,有金,也有木,水火既济,金木相克相生。主吉。
诗歌的命数体现在诗人的情感律动之间,显现于象,承载于道。通达于悟,成全于心。
曹雪芹通过林黛玉的口吻说,“事若求全何所乐”。用当代有大智慧的证严法师的说法叫做“凡事对机便是好”。人想通了,诗才成。人与诗互生互助互励互为。
我与东瑛素不相识,缘悭一面,为她的诗歌拉拉杂杂写下这些话。不是点拨,也不是一味赞许,而是有点在幽静小路上寻索心灵阳光的况味。
我的这些阅读观感,也许就是阳光下闪过的露珠,一颤即失,一念即逝,好在毕竟还留下了一缕心声,就权当留白的刻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