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我到木垒河上飘荡(外一篇)
○余 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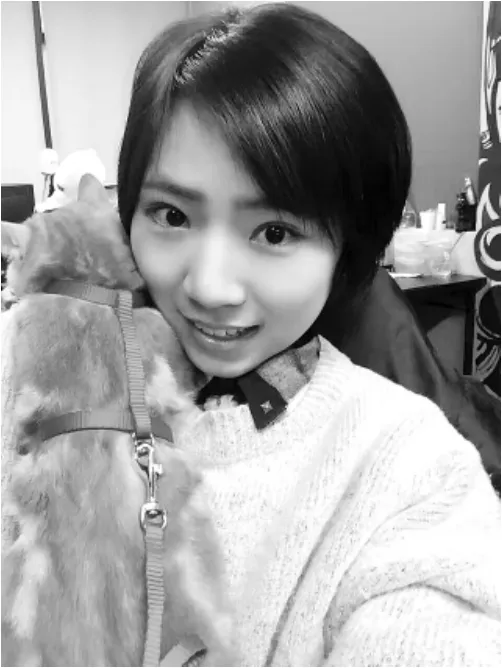
余玦,1995年生。无任何值得赘述的经历。写作于我是一场孤独的修行。惟愿我的笔坚实有力,冲破滥情、煽情的伊甸园,噙善恶之果,进入生命的浩瀚疆域,于书写中一寸寸贴近源头。
我总有种错觉,以为在大路的下个拐弯处会冲出一群蜜色的阿克哈·塔克马。它们在昼亮的烈风中疾奔,长鬃四下飞掷,穿过荒凉奇幻的红褐岩山,从积雪覆盖的冻土上驰骋而过,最后轰隆隆跃入洪流急涌的木垒河。巨大的漩涡翻滚声,像有雷阵正狂击着这片浊黄粗壮的水面,陷身其中的群马一齐仰头发出高亢嘶鸣……世上最古老高贵的马种,以及由千年积雪消融而汇流的木垒河。我仿佛看到冷寂树林后骤然强烈的太阳,在马的光裸脊背抽出利刃般的强光。看到路右侧的红褐岩山猛地晃动,看到我狂跳不止的心突然冲出胸腔,变成那条猛虎般的河流……
马群在我体内浩浩荡荡地奔窜,带动天上大风。我是那条河,我当真看见自己就是木垒河呀!我的眼睛里倒映出亘古苍茫的天和辽阔草场。阿克哈·塔克马的蹄子陷进我的头发和肚脐里,又迅速拔出来,我的身体里溅起一阵“咚咚”的响。当我站在大路的拐角,回头望向急吼奔腾的木垒河,眼泪都快流下来。我知道,我就是那条河呀。
我在三月底见到的木垒河,与从前所见的截然不同。冬天里,连续猛下半月的大雪攻陷了整个木垒。高楼、广场、街道乃至山冈,万亩麦地和牧场。从芦花大桥上往来无数回,每次我都凝神望向桥下的河滩。皑皑大片,无河流踪迹。后来好容易天气暖和起来,县城里的雪多数是化了,我急忙又跑到桥上往下看,消雪后的河床,露出灰暗肮脏的石砾泥沙,清浅慢淌的水,才刚漫过脚背。说不出的失望。那时候,我刚从上海到木垒不久,从那个终年不落雪、阴冷嘈杂的城市来到天山东麓的小县城,我一来便听说了木垒河的传说。樊梨花西征,遇河而不得过,因那河水湍急悍烈,犹如凶暴的巨龙。我见过浑浊喧哗的黄浦江,十几年南方生活中看过大小湖泊无数,但从未见过巨龙般的河流。我实在是满心期待。
拐向郊野尽头的连绵水湾,我在芦花大桥俯身看到的,当真是木垒河吗?有时我困在援疆楼房间里写稿,面前的纸张空无一字,我久久地呆坐,看着窗外枯瘦的老榆发愣。然后,像一道洁白的闪电,木垒河突然出现在脑海中。我会莫名地惊颤一下,那条巨龙般的河,樊梨花用利剑也砍不死的河。想到它,我内心淤塞的阴暗角落会松动一下,好受很多。有时无聊地走上街,街上全是陌生人,听不懂的方言、接孩子放学的家长和准备傍晚约会的年轻人。没有一个人是为我而来到这个世上,所有擦肩而过的眼睛转瞬会忘记我的容颜。我凄惶无助地停在半路,不消片刻,木垒河便会涌出……是怎样幽然决绝的孤独,使一条河变成巨龙。它在万籁沉寂中扭曲着,嘶吼着,那些纷纷而下的痛苦成了它力量的源头。愈是孑然无依,它愈汹涌。把尘世的千军万马,统统拦在了低矮贫瘠的泥岸上。我心底里认定的木垒河,正是那样的,只会是那样的。
木垒城太安静了。当我摊开一张白纸,这脆薄柔顺的纸面正如窗外沉默的冬日,大雪吞噬了一切起伏的动作和声音,它亦覆没了我内心所有鲜活的喧响。在最寒冷的季节,我跨越几千公里,远走家乡来到木垒,为了给这座小城写一本书。我人生中的第一本书。最开始的日子,没有对话,没有朋友,我就像个多余的人。我默默旁观着离我最近的援疆干部的生活,一群来自福建南平的人。他们每天上班下班,热闹大声地出门,然后又回来。仿佛隔了一层厚大的玻璃,我与他们之间截然分开两个世界。他们的世界里有煮沸的武夷茶,围坐茶炉的笑语欢声。而我,我只有一支干枯的笔,以及永远哽在喉头、吐露不出的尖锐搐动。
实际上干部们都好极了,待我就像大家庭中最小的孩子。但我该怎么告诉他们,告诉他们说木垒是这样安静,我走在路上都会胆战心惊,仿佛走在无声的悬崖边缘,稍不留意便会坠入更深的静寂中。我该向谁倾诉,说出每晚在我梦中飞来的那只黑色知更,它从不啼叫,连低声窃语都没有,只是隔着茫茫大雪,与我寂然对视。还有,还有那些衰败的黄昏,天突然黑透,我无处可去,却总想去街上乱转。因为木垒太安静了!是因为它太安静了,我才这样悲伤,就连身体最微小的褶皱里,都藏有一场恸哭。但,我始终没有哭出来。我可以听到冬日里哆嗦啜泣的寒风,在无人的街头彻夜地走,它像是个跟我一样敏感脆弱的孩子,寻找世间可供取暖的怀抱。所以风的叫声这样凄厉啊,它在每个亮灯的窗户前流浪辗转,它发了疯似的满世界跑。没有一个人愿意抱抱它。没有一个人愿意抱抱我。
最叫我伤心的是木垒河,我一刻也没有忘过的木垒河。它从漫长冬季里失踪,我走遍了木垒的清晨与夜晚,怎么也找不到它。于是我只有到纸上,到字里行间去找。我看到的每句话,无论它描述的是什么,但凡能使我为之怔忪失神,无言以对的,都是木垒河;我写下的每个字,晦暗不明、窸窣低响,那亦是木垒河。一个字一个字,在我体内液体般流转,撕扯着我隐忍的泪水。它把我的心磨得像斧头那样亮。从大地上消失的木垒河,它流进了我的肺腑之中。
一个人会不会爱上一条河?爱上她从未亲眼见过的河。世界多么空旷啊,而木垒又是这样的安静,如果不爱上一条河,我该怎么办呢。我压抑了太多感情,不跟人说话,不随便和人成为朋友,不哭,连躲在房间,蒙在被子里,也不哭。如果不去爱木垒河,我又该怎么办呢。
终于,终于我走进了平顶山,在三月末,在严寒逐渐败退,冰雪溃散的日子,我见到了木垒河。像从遥远黑暗的天地尽头一路奔涌而来,它裹挟着无数日夜的忍耐和苦痛,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我站在岸边,看它褐黄扭动的身躯,狠拍石岩,一头扎进落差十米的渠口中,继续狂暴直进,一往无前。因为离它太近,冰凉的水滴溅湿了我的裤摆。“往后站,小心点。”陪我同来的援疆干部郑老师不住地提醒我。小心?我要怎样地小心,这眼前渴望卷袭虚无的河流,就是我的心啊。从未有过的幸福注满我的血管,我牙关轻轻打战,是冷吗,是激动。且让河水代我一哭,那撕裂空气、号啕高声的水浪,是我数月以来体内积压的沉默,如今它决堤了。当寂静堆积成一座雪山,终有一天将有雪崩袭来。且让木垒河代我一哭,而我掏出肝胆,扔进河中,痛快淋漓地宣泄一场。
置身冰冻解固、泥土渐软的岸边,目睹河流深处的激烈冲击。狼狈生活中零碎的阴影,挫折,日复一日写作的折磨,恨不得抓住任意一只陌生的胳膊,却终究张不开口……那都过去了。听往复水声,时而迭起时而低落,听着听着,我忽然撞上了另种声音。难道仅仅是孤独吗?在远避众人,清醒独处的时刻,我不是从窗外的榆树的枯干枝条上,收获过感动吗?当大雪没膝的早晨,我游走县城内,那一张张迎面走来的脸孔虽然陌生,却火般通红,闪烁着快活笑意,他们也曾唤醒我认真生活的热情。还有纯粹的勇气,无边暗夜里我想象着激越暴烈的木垒河,它使我咬紧了牙关,不再沉浸自怨自艾中,去向文字的疆土采掘。是啊,木垒河哪里会是一条痛哭的河,它诞生自天山雪巅,经它流洗的地方,处处生命焕发。它是明亮至极的河啊。
卡里·纪伯伦的诗《我的心曾悲伤七次》,其中写道“第一次,当它本可进取时,却故作谦卑……第五次,它自由软弱,却把它认为是生命的坚韧……”来木垒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陷入了写作的困境。找不到准确的表达,一个词、一句话,每被写出,即刻凋零。因为它们并非出自真心。守在电脑前,我就像一只笼中的困兽。磕磕巴巴地写,写了又删,删完再改,但无论如何也不满意。我以为我枯竭了。在难以启齿的惊慌恐惧中,我为自己找到了一条河。它是残暴凶恶的,亦是坦荡绚烂的。它比我更强大,如此我便能够汲取它的力量。这便是我的写作的秘密。在想象中,与一条河流对话。
如同万物在春时的提问,到秋天终将得到应答。在木垒即将到来的春天里,我听到了木垒河的声音。那是一声悠远深长的回应,证明它确实真实存在,在那段疼痛的时光里。如今我向它走来,或者说冥冥中它召唤我前来,我们无言地相对,却又那样的默契和亲密。好像我的一部分早已抽身而去,投入水中。而唯有那与河流交融游荡的,才配称之为灵魂。
寄往苜蓿山坡的信
你带我,走进春天傍晚。阴凉空气中,一扇漆蓝的木门半歪着,遮住了青草秀美的小路,以及风低低吹过的那片山坡。就在木门旁,一棵杏树饱满明耀,颤颤地开出最艳的白。
书院后山里,有那么多榆树、桦树和杨树,枝干湿润银亮,在微弱光线里,睁大茸茸嫩叶,剧烈晃动。它们的快乐夹杂着一阵阵的喧闹声。唯独那棵杏树,驮着静寂的白花,一声不吭地美丽着。你走在我前面,率先跨过了那扇破旧的小蓝门,我看到几枚花瓣一闪而过,落在你身后。当时,我并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随你走进春暮的那个我,仍然太年轻,我以为那不过是世上一个普通的黄昏,你在前头引路,我跟着你。就像六年前,我在苍茫月光下,凭空伸出手,却突然抓住你陈旧的一角衣襟;就像六年来,以文字为凭,我凝睇你背影,如有所倚,内心安宁。
我欢喜难抑,因遭逢一棵光亮灿丽的花树。站在树下,我久久不肯离去。你愈走愈远,直至走到某个昏暗倾斜的高处,停住脚步,唤我。而我像所有置身青春当中的人那样,轻易被途中风景所蛊惑,一味痴想着当下的溢彩流光,而非遥远的目的地。真正让我迷失的,并不是盎然的繁花,却是炽烈茂盛的青春,我不可一世地年轻着,热切地张望世界,不断被新事物吸引,一次次起身,奔向远方。你,曾经亦是我的远方,而今抵达,见面熟识之后,我不耐久留,又生出跃然逃往他方之心。
但是,你又怎会不了解。过去六年里,你见证了我如何变化成长,甚至不必朝夕共处,透过一年几回的长途通讯,你便已知道我。因为,使我着迷的那株杏树,在你前半生中,你早已见过千百株啊。你了解那鲜润、洁净的白花在纵情绽放之前,如何以蓓蕾、以籽芽,甚而以种子的姿态在黑夜中挣扎。你见过她最初的瘦削模样。你知道一棵树是怎样在时光中忍耐着,强烈地愿望着,终于,用花朵的热焰溅湿了春天。同样,无须我多说,你清楚那些发生在青春里的故事,它们如何使一个像我这样的女孩跌撞着、汹涌着,最后,变成了今天的我。
时隔四年,再次回到你跟前,我眺望你眼中的我,我期盼她是美丽灼亮的,像旷野的灯盏,旺盛燃动着,使你惊讶,不禁发出赞叹。我太想得到你的赞赏及认可,哪怕只是一句,哪怕一句。
上次见你的时候我17岁。我依然记得离开你的那个炎热午后,我们站在路边的公交站台里,人群扰攘湍急地来去,我因不可遏制的悲伤,轻轻战栗。八月的风黏腻胶着,吹在我脸上却冷硬无比。与你分别后的四年里,我还是常常被卷入那团黑暗困重的冷风中,生活极不均等的掠夺与施予,使我变得敏感自卑,我慢慢习惯低头走路,双肩紧缩像是取暖。穿行在那座语调急促尖利的东北小城,我竭力吞咽着自己的南方口音,敛收一切锋芒,彻底沉寂下来。那一千多日夜里,我活得庸碌而无用,即便现在也是,我终究是个平凡人。
你看向我,你的眼神虽温热却波澜不起,我忽然有想哭的冲动。你或许想象不到,这些年来,你始终是我灵魂深处一道明澈珍贵的防线,你的存在提醒着我关乎纯粹本真的坚持。你曾说我是应该朝上飞的,而如今,我的翅膀日渐钝重粗糙。在那些屈从妥协之中,如果我有过一丝扯痛感,必定是因为那时想到了你这句话。你低头看我,父亲般安详宽容,而我知道我没有变得更好,你亦明白。
你召唤我走进那个谧静的黄昏,一如你在四年后的冬天召唤我回到你身边。我想过天山脚下大雪弥漫,四野旷瀚月明星稀;想过灯照亮一隅屋室角落,院内狗吠悠长。而我想得最多的,是如此天地间,有一个你。在上海去往新疆的飞机上,我心口仿佛云蒸霞蔚,一切壮丽景象于此齐并喧腾,我咬紧双唇生怕自己会忍不住失声叫出来,叫出那叶底的藏花,深海的潜浪,叫出暖烘烘的纷飞雪片,且要通通以你的名字为它们命名。
你是我在新疆唯一的地址。木垒小城,好像荒野中的一座陌生驿站,灯火寂然,照耀着那些棱角坚硬的面孔,而我坐进阴影中,等你。当我拥有了一间带窗的屋子,住进距你四十公里以外的援疆楼,漫长冬天里,我仍总是屏息凝听,朝着你的方向。那最初的日子里,我伤心不已。无边无际的积雪将地面抬高,天空晴朗辽远,光秃枝干空茫直指着,多少年的路程在雪中荒芜。你把我遗忘在一场大雪中,这冬天的尘世光芒刺眼,而我突然失去了你的消息。
尤其在天黑以后,我听人喧笑欢闹,明亮房间里热气涌动,他们相依作伴地度过长夜。而我却独自开着窗,长时间呆视着那雪地里白耀的路灯。渴望一寸寸地蔓延,继而又一寸寸地熄灭,无穷黑与白中间覆盖着微微轻颤的浓重的灰,我把整个身子埋了进去,热泪在眼眶里打转。你终究没有想起我,在那无数昏沉幽寂的冬夜。
我待在你身边的时间太过短暂,比起冬去春来的缓慢轮回,比起庞杂琐碎的每日的生活,我们每次的重逢都是那样的仓促迅疾。曾经隔开你我现实的距离已荡然无存,我径直地走向你,如同女儿走向父亲。你剥落了名气与光环,布衣上沁散着乡村午后般的温暖气息。在你跟前,我放肆性情,活得嚷闹而鲜明,而你一直纵容着我的恣意,从未认真与我生气。因为有你,我在新疆有了一个家。
只要你在的地方,我都无比的熟悉。木垒书院各个房间的细致轮廓,粗朴木头起伏错落的秩序,包括日常的饮食,生活其中的人获取快乐的途径……一切皆温柔地向我敞开,经你授意。它们自然地涌向我,毫无秘密可言,而正是这无所阻碍,无所不在的亲密,使我感受到你绵长深邃的温柔。
你是一个在情感表达上固守着农耕传统的人。我听你的母亲讲过,你从小就是那个最不让她操心的孩子,而你的妻子多次在我跟前抱怨你太过沉默与寡言。我们相识以来,常常是我莽撞激烈地反复讲述着自己,你低垂双眼,坐在椅子上静静地听我说,隔着三十多年的岁月,我对待生命的方式并不能给你带来新的惊喜,你却早在静寂中把语言淘洗得清澈无比。当你开口,语速轻缓,嗓音低沉,好像贮满宁静的黄昏,把世上仓皇赶路的脚步停住,把漂浮不定的灵魂喊住,而我在稠密广阔的暮色中蓦然回首,一眼看到你,端坐光明里。
是啊,你说出的每句话都直接避开乱麻般的真实,准确射中了事物古老的核心。在你看来,仿佛秋枯春荣,草灭岁生,皆是有情,而人间流转千般故事,滚油炙火、繁闹似锦也好,成灰成烬、滴水成冰也罢,桩桩件件里都有衷心。何苦推敲成败得失,你向来只是明心见性。你教我事过便忘,无事不可原谅。借由你的语言,我屡屡被引入另重天地。六年前,也正是你为我打开一扇门,使我窥见万物有灵,当时云垂海立,而后才有写作上的柳暗花明。你是我最为敬重的老师。
你带我亲历了许多风景。我记得和布克赛尔夜幕之前的马群,掠过漫野的石头,仰首朝向炊烟之际背后忽传来的嘶哑长鸣,你骑马从天边归来的黯淡身影;记得喀纳斯晨雾弥漫的黎明,野花辗转,空气中模糊的蜂舞,你指给我看那头嚼草的牛犊,带我悄悄跨过木栅栏……而今我再次跨越千山万水,来到木垒。又一次,我为你而来。
菜籽沟村落,牛拴在门前,羊散在院中,马在檐外梁下嚼草,屋脊背后露出大雪覆盖的成堆草料。太阳底下,并无新事,与你相伴的日子清白如一枚淡墨竹简。雪山、冻河与松林,乌鸫、野兔和雎鸠,漫长白天里我与这些事物比邻而居。偶尔坐在房内无事可做,便起身看你躬身写字,你俯首蘸墨,枯纸上遍地大风。到天色转暗,炉灶烧旺,坐在茶室,坐在你对面,开着一提马灯,听四壁响起的寒风动静。我看过你劈柴,扫雪,看你在晴朗傍晚出门散步。看天色渐晚,铁门轻响,大狗一身雪粒扑到你脚边,你身后的夜空淼远,星辰闪转。那是我此生从未见过的晶莹星空,每个深夜在我头顶,在松、杨、榆的呼喊之上,一片沸腾。我正度过一生中最接近魏晋、汉唐和北宋的日子,在二十岁,在你身边。
当我再次回忆那个傍晚,我的感官倏然复活,一切画面与声音都是如此地清晰。我看到那座朴素暖和的麦垛,你鼓励我爬上去,在我终于摇晃地在麦草上站起身时,斜阳将你的面孔映得通红发亮,你在笑,看着我笑。绵长麦田那样平阔,微黄如月光倾荡的海,我大叫着要你看那麦田之上的三棵榆树,它们在强烈光线中好像上帝精心手作的剪影……我们一前一后走着,走向那片飘荡苜蓿的山坡。我挎着竹篮子,脚踝上尽是草尖的露水。你弯腰,手指掐住那丛苜蓿嫩绿沁凉的部分,那在微风中轻曳如烛光的部分。你的手指温暖,停在苜蓿灿烂的内里,我从你身后慢慢走近,探头看。傍晚的光如此柔软透明,你采下一小株苜蓿,扔进我的竹篮里,刹那间世界如水浮荡不止,我的心头涌出大片露珠般的快乐。在那片苜蓿丛生的山坡上,你当时转过脸对我说了些什么,如何采摘,或是如何拣择。我认真地抬头凝视着你,是因为你,我才最后恍惚想起,那是春天。
下一个春天,我是否还在你身边?
但我向你许诺,时间永远不会将我打败。你是我在世上为数不多的亲人中的一个。无论人事怎样跌荡折转,当我望向你的眼睛,那片安谧澄澈的山坡始终还在,我为你摘下的两枚光嫩清新的苜蓿叶,永远地飘荡在你眼内,温柔无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