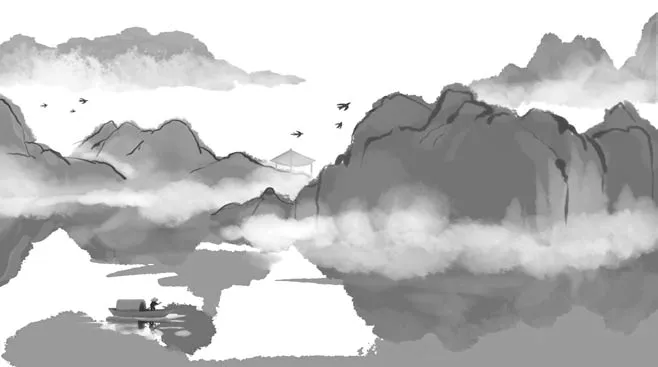
公子苏早已忘记了他,毕竟上一次见面是五十年前,而且那时他是个连法号都羞于告知他人的小沙弥,公子苏白得耀眼的袍服,令他深深自卑,想要藏住新打了补丁的芒鞋。公子苏当初多年轻啊,一双秋水般的眼眸,漫不经心掠过寺院上空的流云和绿树,轻轻叹出一口气。他虽是方丈指派来打打杂的小沙弥,也懂得公子苏高雅如天人,不敢怠慢的。
五十年前那个山雨空濛的清晨,公子苏是陪母亲到山寺还愿的。论起位份,母亲只是宰相家的如夫人,但宰相的三公子苏才学、品貌皆是出挑,庶出的儿子,倒在城内比两位哥哥更有名。小沙弥慧空,实在不知完美无瑕的公子苏为何要叹气。公子苏将母亲送到寺庙,随即不见了人影,当然,他很快就听到闲话,宰相府两个下人在准备茶饮时嚼舌头,说夫人也管束不住公子苏呀,他夜里都是留宿“红罗阁”吧。
五十年了,时间太漫长,清洗了沿途细沙。如今的公子苏,一身瘦骨,老眼浑浊,除了早年富贵生活留下的一点儿斯文影子,已和村野老人无异,但慧空不会看错公子苏花白发丛迸出的两道目光。公子苏饶有趣味地给一个老和尚讲起遥远的“红罗阁”,一丝苦笑爬上腮边皱纹。空山新雨,可那毕竟不是五十年前的雨滴了,公子苏眨了眨眼皮上的雨珠,他愿用自己半生的故事,感谢老和尚慧空今晚的收留之恩。
是的,红罗阁,当时城中最负盛名的酒肆歌坊,红罗阁拔了头筹,而阁中的燕姬姑娘,又是牡丹丛中最娇俏的一朵。母亲以为佛祖能替她管束儿子的心,但二十岁的我,岂肯与母亲一道留在这清寂禅寺,打坐、早课、茹素,将如丝欲望都在诵经声中洗涤干净呢?我当天就冒雨下山了。
如果说,之前我与燕姬的交往是人们眼中的“如胶似漆”,那夜因雨越下越大,遂滞留红罗阁,我们才真正地跨过壁垒,享鱼水欢情。红烛摇摇,罗帐昏昏,燕姬低了嗓音,轻轻为我唱歌,每唱一句,她脱下一件衣服,后来我踩着一地的香绸软缎走向她,她的歌声已似耳语,映衬得窗外雨声淅沥,爽脆如珠落玉盘。
我们听雨?我对燕姬说。
我们听雨。燕姬冰凉的身体被我搂住时,整个人发起抖来,像是我的热度灼伤了她。她贴着我的耳,着魔地吟了一夜,公子苏,哦公子苏。
是的,我是公子苏,雨声之中,夹杂着头牌歌姬的歌吟,她身体像一架瑶琴,轻轻一拨,便弹出不可思议的美妙乐音。
我以为她是脱俗的牡丹,岂知她仍是泥沼中的藤蔓,生得妖娆和风情,只为攀附一棵大树。天亮了,她问我,几时带她进门?我怔了一怔,外面的雨就真的停了,有小贩提了竹篮,在窗下唱似的叫卖:水灵灵的白兰花呀……我叫来小厮,买下花篮送给燕姬,她沉默着收下,我们假装都没听到誓言重重落地的声响。
你问我之后还见过燕姬吗?三十年前,我好像见过她,但又不确定是她。她是聪明女子,早该知道我这样的身份,不可能迎娶一个歌姬进门。但她只猜到上阙,未猜到血腥残酷的下阙。那年发生了很多事,母亲甚至未能从山寺许愿归来,父亲在朝廷受了奸党弹劾,我两个哥哥随父亲走了仕途,于是家中衰倒如山崩,哥哥们坐监,父亲的学生充军,家仆如鸟兽散,只剩我与母亲二人,逃过这场劫难。我是人们眼中放荡不羁的公子苏,从不涉足朝政,倒保了平安。母亲撑了几个月,年末病逝于山寺,而我开始浪迹江湖。
二十年后,我在渡江途中,遇到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艄公好心地劝我回舱躲雨,我谢过他,只借他多余的蓑衣和斗笠,穿戴好,依旧怔怔坐在船头,看这平整阔敞的江面,如同一面镜子,令人不敢细视,怕望见满脸烟火色,两行辛酸泪。雨下得天空低沉,黑云仿佛直压在小船顶上,淋雨飞行的群雁,惨烈又执着地扑打翅膀,从雨中挣扎飞过。大雁想来会越飞越沉重,岂不如同我的半生哀荣?我正想冲天空吹个唿哨,唤这些傻雁早早清醒,却见有叶小舟,飞快地擦过我们的船。舟上摇橹的是个女子,匆匆一瞥,只见侧面与背影。但我忽然就想起了燕姬,甚至认定船娘便是燕姬。她细细的歌声散落在雨中,那恰是定情夜她为我哼唱的吴地小调啊。可惜两舟很快漂离,我努力去看,漫天雨雾,不见斯人倩影;我努力去听,雨声刺刺,老天爷抖落了千万枚银针入大江,入我心。
现在,我已七十岁了,和父兄相比,实在是活得太久长了,久长得我早已忘了他们,也忘了人们曾称我为“公子苏”。慧空,谢谢你的热茶,不如,今晚我就坐在这里,听阶前雨滴到天明吧。人生多少悲欢离合,繁华苍凉,也不过是一场茫茫大雨,瞬间就能将前尘往事,洗涤一空啊。
慧空随着公子苏抬起视线,两双闪着老泪的眼,齐齐望向屋檐,天色已向晚,仅剩一点儿薄薄微光,看那檐下雨滴,是断了线的离人泪,是五十年的漂泊苦,是多情更是无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