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歌唱生涯?我这个人居然大言不惭地书写起我所谓的歌唱生涯而非配音生涯,是否痴人在说梦?不,我清醒着呢。我是想写一点我游走在歌唱界边缘的趣事,自觉颇有点意思,也或许都是我的音色惹的祸。
音色无非是好听二字。其实我知道,我的声音条件中,缺点、局限多多。比如:声音干,特干,缺少水分,声音特单薄,音域也窄。但话又说回来,我这方面的优点和这些缺点、弱点组合在一起,又会有一种特别的效果,至少声音的辨识度高,一听就可听出,无论老少受众都乐意接受,此种妙处我是至今说也说不清楚的。这就要联系到唱歌,坦白说,除了音色之外,我自己知道,声音条件、音乐素养、乐感等等方面,都乏善可陈。所以,居然也敢勇气十足地在此说点歌唱生涯,着实是因为读者朋友(多数是我们上译厂的忠实粉丝),是可以对我随心所欲地瞎说一笑了之的。
远远地想到我的小时候,有两件事令我印象深刻,难以忘怀。一是三岁前,我几乎是人见人爱。那回在厂里,孙道临老师见到我幼年时的儿子道:“希望这孩子不要长大。”我小时候大约就是这样。因样子好看,又笑得迷人,还极会表演,那回照相馆的伯乐师傅当即决定免费为我拍摄,又经我妈妈同意,放大了数张,统统摆放到橱窗里去,让我在这方小小天地里“招摇过市”。我母亲为此得意了一辈子,当然后来又被社区里的朋友们封了她一个“佐罗妈妈”的名号。二就是上小学时,音乐课上老师老把我从位子上叫起来“独唱”,尽管我已大不如幼年时那般天不怕地不怕,但班里同学们居然听得陶醉,渐渐地我也就“醉”得一塌糊涂,以为将来考上音乐学院不在话下呢。不过,奇怪的是从来就没做过这方面的梦。后来被外国小说和外国电影所吸引,而听配音、迷配音成了我中学生活中的最激动人心的内容,那才真叫一个快乐,亦是我每天的希望,每天的想象。1973年的一天,我真的进入了上译厂。可惜,因为褪去了神秘感,见到了我崇拜的配音演员的真面目,看到了录音棚里表演是怎么一回事,反觉得不是那般快活了。
到上了中学,有时下乡参加劳动,有空时就用紫竹调什么的填了词为乡下农民同志们演唱,也挺得意的,感到我们的歌声是把田头的观众给吸引住了;还不知疲倦,因为边上有若干小女生陪着我一起唱呢。还记得,市西读高中的一两年,学校里有个“沪剧兴趣小组”,那“女魔头”(她舅舅是沪剧大家王盘声)见了我,也没考我,二话不说就吸收了进去。没几天,又二话不说就拉我参演沪剧《星星之火》片段,饰演日本鬼子手下的狗腿子——凶狠残暴的监工,戏中还洋洋得意唱了几句:“十字花押……啊,可怜一见了人还脸红的文弱书生的处女秀、处女唱。”不过,也难忘,让我演大反派,其审美那时已能如此超前。是啊,若不是配音梦,否则去报考沪剧团也恐非惊人之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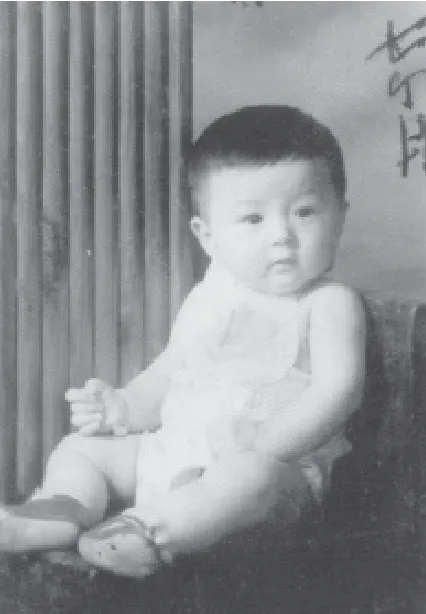
童自荣童年照
上海戏剧学院是我的大学母校,除了开设表演课、台词课、形体课,音乐课一周亦有一次。教声乐的老师毕业于上音,我可算是她的“拳头产品”。如果她还健在应当近百岁了,愿老天保佑她。但上音乐课,目的当然不是为了成就我的歌唱事业,而是为上台表演服务的,即如何让声音可打到最后一排去。那时候,小小音乐教室对面便是另一个小教室,是塞满三十个同学的音乐理论讲习间。我从没意识到,我“依依、啊啊”的练习声是足可穿透两道门而传到高班同学们的耳朵里的。不过,后来他们班上有的同学对我笑说,当时他们很享受我的歌声,老师的讲课反被很惨地干扰了。我也笑了,颇有几分成就感,就可惜不是表演课,表演课若能频频获得在场观摩人员的喝彩,那才叫棒呢!
记得真正像样的一次小戏演出,那里头我连个前台龙套都没挨上,只是埋在后台为前面的戏伴唱,当然在一群龙套里边,俨然是个主角。那回我唱的状态很放松,反正也没观众盯着,领唱的歌声颇嘹亮、结实,不费力地传到观众席上。这只是我自我欣赏之举,居然会引起现场排戏导演——我们敬畏的朱端钧大师的注意,还侧头问了一句:“这是谁在唱?”哇!这龙套跑得真痛快,当同学不经意地提到这个信息时,我心里乐开了花,啊,真爽!还有什么呢,好像记忆中的这些事儿可怜也就这点。
“文革”时则很特别,大约有七年时间呆在学校里,努力干“革命”,亦不必回避。那些年里,没唱什么,光喊口号了,多数是高呼口号。喊一回,哑一回。反正隔壁就是华东医院,去喷嗓子就是,至于保护嗓子早已扔到九霄云外去了。这种超负荷破坏性地用嗓,还是种下了祸根的,以后几十年轻轻重重的慢性咽炎,嗓子经常闭合不好,声带不干净,就从这时候开始的。
蛮搞笑的,“文革”十年之后,凡上戏校庆活动的发起人,都会有意把我“忘却”。可能因为怕我来了以后,万一一激动跳出来要求也发个言,或演个节目,朗诵也好,唱歌也好,又会勾起台底下老师们的噩梦,这可如何是好!(因为那年代广播台白天晚上的吆喝声,对于“牛棚”里的人们而言,太熟悉也太恐惧了。)
1973年终于踏上社会,分配进上译厂。三十年里,我若极难得地说了一句上海话,或哼个什么歌,前辈演员都会大为惊讶,亦感到很新奇。配音的时候,碰得巧也须自己学着哼哼唱唱(如果不借用原片的话),我没想到通过话筒录音,出来的声音比平时生活里的还要好,不但人家感觉到了,后来我自己意识到了,我选择走幕后之路真还走对了,我心里想。而这也为以后上舞台演唱建立了信心。
20世纪90年代末,正是我事业上与无所事事挂起钩的开始,最后配的两个主要角色,即美国片《婚礼歌手》与澳大利亚片《心心恋曲》。原本也轮不到我配,两个原定的演员一个跟厂里闹别扭,另一个太过年轻,于是就落到我身上。可巧,影片里刻画的两个主角都是倒霉蛋,后来他们都遇到了好运,但我这个为他们配音的,却依然是倒霉蛋,一直失意到四年后退休。后来的一回“壮举”,颇出乎朋友们的意料,我居然破天荒上电视台去演唱,参与淘汰制的上海“五星奖”演唱比赛。其实我是主动想找些事情做做而已,无所事事的状态令我难以忍受,而并非如这个节目组的导演所好心鼓动我的话语:你再不出来,观众要把你忘却了。另外,也正像电视台那位曾和我有过配音合作的领导对我那位搭档所言:这是老师在提携你啊。此话说得中肯,我确有此意。跟我合作演唱的那个学生,本是上译厂学配音的小学员,通过参赛,是否有可能被哪位星探看中呢?我知道她就是最喜欢为大家唱歌,为人单纯,目的也很单纯。可惜,后来未能如愿。之后听说上海有一帮小邓丽君,她好像也跻身其中,也有机会去某种场合一展歌喉。我想,只要不是冲着钱去,而是为老百姓倾心演唱,日子过得充实、快活就好。这个也算和唱歌搭界的一档子事。是啊,想当初颇有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味道,现在则是接受电视采访尚可,而比赛之类找上门我肯定关门大吉了。
退休前几年及退休之后,我算是有机会从幕后到了幕前粉墨登场了,开始了我的另类篇章。尽管我们的掌门人老厂长在世时,从不鼓励我们上台去演出,甚至不赞成拉一支队伍外出去帮忙配音。市场经济大潮袭来,令老厂长的晚境很是无奈和悲凉。
我下功夫为观众演唱的第一首歌是《康定情歌》。一个青岛的导演,因我们有过几次配音的合作,于是他也注意起我想为大家唱歌的动向。有一阵子,几乎天天找时间听我练习“跑马”的成效。我倒不至于会为了某种程度的成功而飘飘然,但确实我没有从他那里听到过任何一个对我的表扬或点赞。我一遍又一遍地唱,却难以让他满意,弄得我也很沮丧。心想,一个人就是具备某种条件,要成为歌唱家还是谈何容易啊!我这个“笨鸟”简直就是不开窍。后来在不断的大拼盘式的小分队演出实践中(往往是朗诵以后我加一个唱),掌握了一点要领——嗓子闭合好,有激情,还需得放松。可惜,这位导演大哥却因为身体欠佳,离开了艺术界,也就没有机会当面向他汇报。说起来,上头提到的这位伯乐,是我的“歌唱生涯”中的第一贵人,我忘不了。接下来的一位贵人,便是我的老婆大人。
我的老婆欣赏我的配音,亦把听我任主角的作品,作为她生活中的最大爱好。我感到安慰,因为我总算可以有一些东西来回报她几十年来付出的辛苦。然而在我不太有把握的歌唱活动中,她也奋不顾身为我摇旗呐喊,如此高调就弄得我有些恼火了。她一有机会就煽风点火,卖力地把我推出来,我也只好眼睛一闭听天由命矣。这样,于2003年1月,我独自策划组织的“向往崇高”音乐朗诵会——一次货真价实的大型商业演出中,我尝试唱了那支青海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我听到观众鼓了掌,总算没有让期待我的观众朋友们失望,大概是因为唱得还好听,也因为是“佐罗”在演唱,有一分好奇,可能还因为我在唱这一支歌之前加了一句话:“我因这句歌词而被深深打动,它说:我愿抛弃了财产,跟她去放羊。这才叫爱情啊!”
还有一些贵人的提携,我亦不会忘记。特别是前不久去世的上海歌剧院歌唱家任桂珍老师。其实在以往各种活动中,我并未和她会过几次面。但以她的造诣和声望,给予我的肯定和鼓舞非同寻常。那是一次公益晚会,我照例说完了“佐罗”之后,讲了几句搞笑的感言,然后为大家演唱我最熟悉的歌《在那遥远的地方》。那天我自觉嗓子状态还可以,因此唱得也尽如我意。观众听完报以热烈掌声,还要拉我再唱一个。兴奋地回到后台贵宾休息室,就见有人把任桂珍夫妇引进了房间。原来他们俩就坐在第一排,听我的朗诵和演唱。我迎上前去,手足无措地不知说什么。她一边满脸是笑,一边热乎乎握着我的手说:“这样就对了,就这样唱,就这样唱。”我亦紧紧握住她的手(一定把她握疼了),我光会说:谢谢,谢谢,谢。她的老公也是位男高音歌唱家,站在一边,含着笑赞许地频频点头……
从此之后,我知道,只要我嗓子状态好,又带有情绪——(一种冲动、一种表演欲),我是可以把歌曲唱好,是可以给大家带去快乐和享受的。至于,问我是采用何种方法。我也很糊涂,大概是非纯粹的美声法吧。
总之,话又说回来,我有多少斤两,我自己心里有数。我所谓的“歌唱生涯”,也就是一种业余爱好罢了,再多的掌声和赞誉,不会让我飘飘然、忘乎所以。我最引为欣慰也最在乎的是,对我来说除了配音和朗诵,我还能以歌唱这样一个新的手段,用心报效我的祖国,报效哺育和培养我一天天坚实长大的我的衣食父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