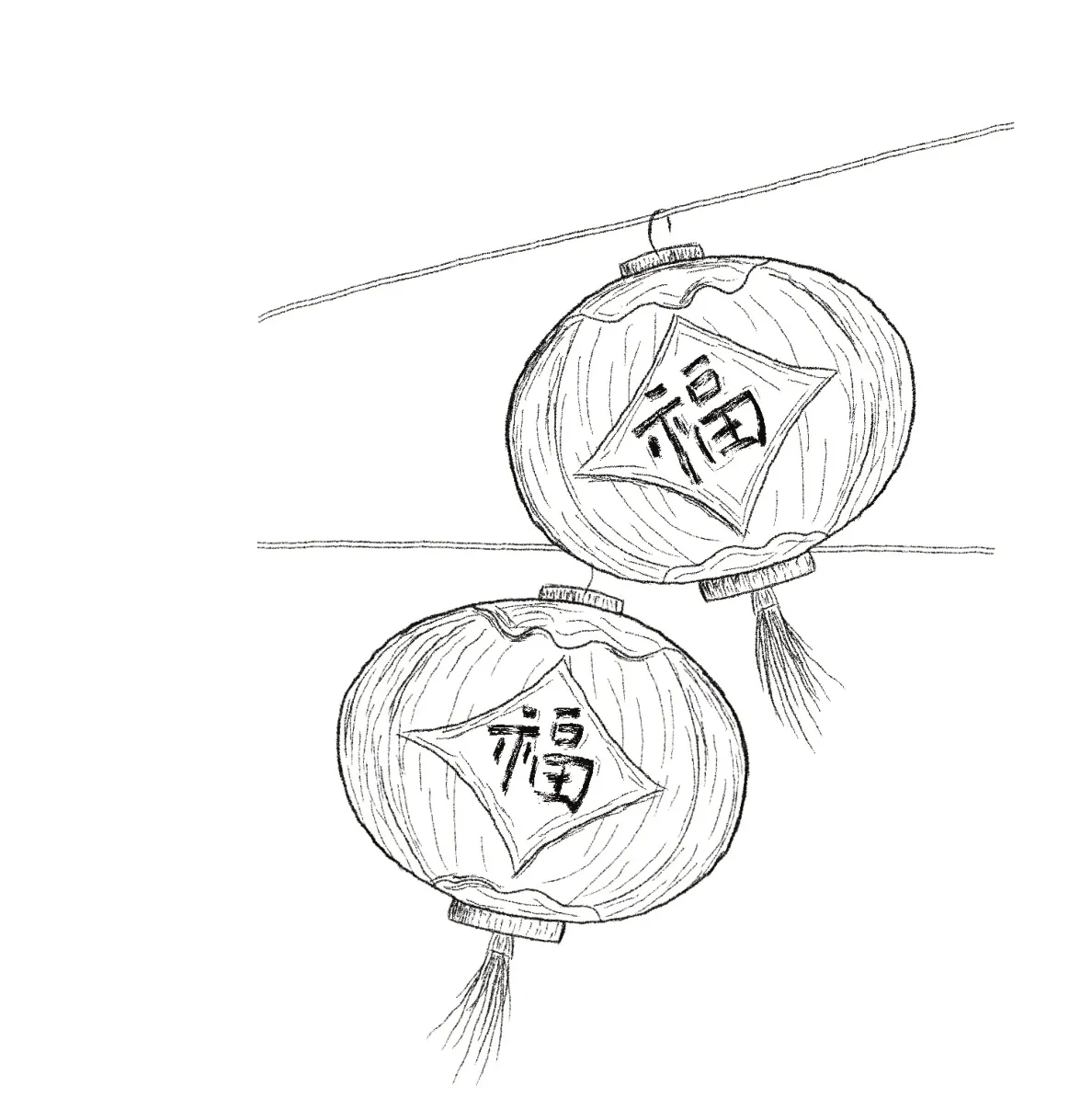
每到过年,总有一些记忆泛起,涌在心头,我也为此写下过一些思念的文字,扫家、写对、看灯等等,今天写写吃糕。
平定有过年吃糕的习俗。
一盘黄澄澄、热腾腾的糕,置于年夜的饭桌上,不是主角,胜似主角。“趁热!趁热吃!”趁热夹一筷,软糯甜香,弹牙可口,为口福,也为来年的幸福。
庄户人家的自留地里,大多会预留一块“条条”地,即使是荒地,重新耕种,或者新垦,反正不用多少投入的那种。等大多农作物都已耕种在地,抽空或顺路在预留地里撒下种子,除去间苗,几乎不再打理;秋天收获了,这便是黍,平定也叫糜黍、糜子。这种作物抗旱、耐贫瘠,产量还不低。它不管在多么荒芜的土地里生长,去了外皮的果实却粒粒晶莹,像极了玲珑剔透的小珍珠。上碾、去壳,仿佛一个个黄色的小圆球,这才是真正的果实——黄米。黄米比小米稍大,颜色稍淡,是蒸糕的主料。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过了腊八,年就真的近了。大人、小孩都各有事做,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年的喜庆、新的希望。腊月二十前后,母亲提前把黄米泡上,泡发的黄米浸在水桶里,水面没过黄米,泛着一个个乳黄色的梦。母亲嘱咐我们看着点石碾的情况,我们被过年的激动和期盼怂恿着,都十分乐意当这个勤务兵。弟兄仨轮流从家到碾窑,从碾窑到家,有时候隔着院墙,有时候站在窑顶,一遍又一遍向母亲汇报“侦查”的结果。事实是,那几天,石碾已忙得不可开交,常常是这家的还没碾完,那家就早早排上了号。磨道里的小毛驴戴着眼罩,不紧不慢地围着碾台转圈。碾墙上的人们不厌其烦地享受着这热闹的场面。终于轮到我们家碾米,要是不借用邻居家的毛驴,我们仨就是推碾的帮手。母亲一会儿用笤帚把碾压出磨盘的黄米扫在碾磙下,一会儿用粗箩收拢了碾碎的黄米去筛面。时间一圈一圈流逝,米香一股一股散发而来,我们对糕的盼望一阵比一阵强烈。
母亲是远近邻居中蒸糕的好手。她蒸的糕,软而不泻,筋而不硬。鲜香的黄米面躺在簸箩里。煮好的红小豆、眉豆粒和大红枣,颗粒饱满,光泽耀眼。炉火正旺,坨六锅里的水正幸福地翻滚着白色的水花。案板、瓷盆、笼床(蒸糕的砂制品,扁圆柱状,无盖,底镂空、布满钱币大小的孔洞,类似现在的蒸屉)都已清洗,正焕发着崭新的容貌。我们跟在母亲身后,进进出出,欣喜若狂。母亲告诉我们,古话说,蒸糕的时候,不能有生人,要不糕就蒸不好了。我们都不是生人,却都担心糕因为我们的捣乱而蒸不好。弟兄仨温驯地听从古话的教导,却并不走远,在院子里坐立不安,心烦意乱。
母亲娴熟地把掺了红小豆、眉豆粒的黄米面握在手心,轻轻挤成一个小团,一个一个紧密地铺进笼床里。她把铺满一层小面团的笼床坐在锅沿上,娴熟地用黄米面把笼床和锅沿的缝隙封严。笼床里氤氲着白色的水汽,水汽弥漫在热气腾腾的厨房里。母亲用小碗盛了黄米面均匀地撒在笼床里,又抓了一把大红枣撒在上面。她娴熟地一边把握火候,一边掌握着笼床里水汽的大小。我们在院子里追逐、嬉戏,院子里升腾着枣糕的浓郁的香气。
中午饭,照例就是一碗新鲜的糕。就算没有菜蔬,我们个个也吃得津津有味。我想,幸福就是那一碗糕,它采用最普通甚至最廉价的食材,缀以日常的苦乐酸甜,经历生活的淬炼和时间的打磨,最终得以传承和延续。
有了糕的日子,从此就多了一份选择。蒸好的糕放凉、定型后,母亲把它分切成小块,手掌一般大小、薄厚。除开送给舅舅、姑姑家的和春节、元宵节吃的,其余的就冻在院子里的墙角。我们在外面玩累了,跑回家,掀开铁锅,拿两块儿放在炉火边,慢慢等着火口的热度将冷冻的糕块儿唤醒,烤热,直至外皮焦脆、内里软糯。性急的我们常常一边烤,一边吃,吃完烤完,烤完吃完,哪里等得到外焦内糯。也常常是你吃了我烤的,我吃了你烤的,弟兄仨谁也说不清,辩不明。找母亲评理,母亲对我们说,不管谁烤,就多烤几块儿。
争抢着吃糕的日子,甜蜜而幸福,却再也一去不返。
今天,糕已成为我们的家常便饭。儿女喜事,吃喜糕;亲友聚会,吃炸糕;变换口味,吃馅糕……自己做,超市买,还有专门的店铺出售。每到饭时,楼下常会有“枣——糕——枣——糕”的叫卖声不绝于耳。中国人都爱吃糕,虽然地域不同,做法各异,但“糕”“高”谐音,吃的是香甜,听的是高兴,寄予的是人们对生活“节节高、步步高、年年高”的美好愿望。
又快过年,我对母亲说,该泡黄米、蒸糕了。母亲说,腊八不是才吃了糕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