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的农民文学理论问题并不能被简单地视作一个文艺理论问题,它自身的政治发生语境及其强烈的意识形态性,使我们无法忽视20世纪30年代前后,“农民文学”理论生成的复杂的历史背景。对于拥有丰富“乡土文学”传统的“乡土中国”而言,“农民文学”概念的提出是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事件,这是由中国革命的性质所决定的,否则也没有在“乡土文学”之外再提“农民文学”的必要。而笔者注目于“后五四”时期“农民文学”理论的发生,并不仅仅是要提炼“农民文学”理论的核心质素,而是希冀在更广阔的政治、民间视域抽绎“农民文学”,还原政治与文学以及文学内部不同利益群体相互激发与相互生成的复杂的互动关系,进而彰显中国现代“农民文学”理论发生的时段性特质,即一种兼具复调性与狂欢化的历史症候。
一、 从小资产阶级的问题谈起
1930年7月,在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的《农民小说集》的序言中,译者朱云影说:“中国还没有所谓农民文学。有的,都不过是田园文学或乡土文学。那些,诚然是诗人的书斋,小姐的闺房所必备的上品的装饰,及为怀着旧感伤主义的周作人教授等欣赏咀嚼的好资料,然而却不是我们的时代所需要的。[……]田园文学或乡土文学是向‘土’去,是田园生活隔绝者的解渴的清凉剂;盖疲于骚音,彩色,人与人间的应酬的他们,有时自不能不想起茅舍,清溪,绿光的田野。农民文学却是从‘土’来,欲使生自土的纯真的生命有意义地育长于土,是农民自身所要求的日常面包。”(“农民小说集”1)由翻译日本农民小说而见到中国乡土文学、田园文学与农民文学之异同,这位曾东游扶桑,出版《日本必败论》《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的国民党左派人士,因何在1930年突然生发中国没有“农民文学”的感慨,个中缘由是颇耐人寻味的。一方面,为何在1930年代而非“五四”才提及“农民文学”,难道之前在国内并没有出现以农民及其生活为描写对象的文学作品吗?另一方面,为何译了日本的“农民文学”才有此感叹?或者说才能够如此深刻地感受到唯有“从土中来”“育长于土”的才是真正的“农民文学”?这其实已然关涉到“农民文学”理论发生的历史局限性与域外理论资源的跨文化接受问题。就前者而言,朱云影对“农民文学”与乡土、田园文学异同的比较,其实已为还原1930年代的历史语境提供了重要线索。换言之,在文艺形式差异的相较之下,其实隐含着阶级与政治的价值评判标准。正因为诗人、小姐以及“士大夫”与农民的阶级分野,所以旧的乡土、田园文学才不能、不配作为“农民文学”。两年后,朱云影在《中国农民诗集》的序言中说得更明白:“我编这本诗集的动机,便是因为不能满足士大夫阶级的自慰歌吟的,换句话说,即要求歌咏其本身的生活感情的别一群新读者,又从时代的潮头出现了。”(“中国农民诗集”391—92)这个从时代潮头出现的、被呼唤显身于历史舞台的“别一群新读者”就是农民阶级。朱云影对“农民阶级”的注目其实与1930年代政治历史语境是息息相关的。譬如,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就显示了不同政治利益集团及其内部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及其农民命运的焦虑。因为中国是农业大国,要认识中国社会的本质就必须重新认识中国的农村与农民。而毛泽东于1927年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①更是对农民阶级予以重识、重估的标志性事件。为了回击来自党内外的质疑、不满与责难,反击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右派,澄清中共党内对农民运动的偏见,毛泽东以田野调查的实证方式,科学地分析了农民阶级内部的不同阶层,对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进行了重估,明确了建立农民革命政权及其武装的必要性,这成为1930年代对农民阶级认识的重要分水岭。因此,农民阶级及其理论问题成为1930年代的焦点也就不难理解了。
农民阶级在1930年代的重识与聚焦已无需赘言,然而一个极为重要却往往被研究者忽略的事实是: 在中国革命初期,农民与小资产阶级的界限是模糊的,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及其作用也尚存争议。因此要理解为何在1930年代中国不同党派与个人争相译介“农民文学”理论,提倡“农民文学”创作,仍需从1920年代中国革命中的小资产阶级问题谈起。
从1920年代中国革命家的表述看,农民与小资产阶级似有重叠,甚至等同。譬如,陈独秀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中就说,“约占农民半数之自耕农”属于“中小资产阶级”(1—9);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列举的小资产阶级就有“自耕农”(1—13)。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在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国际和中共曾判断,中国人口的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他们不能接受中共的领导和纲领,因此力图发展出一个能代表小资产阶级并与中共密切合作的国民党‘左派’来领导国民革命”(李志毓78—94)。但是随着国共分裂,不同政治派系都需要重新评估中国社会各阶级力量,以确立革命进一步前进的策略和方向。对于中共而言,寄望于国民党“左派”领导国民革命希望的破灭使得确立自身政治主体性变得尤为迫切。而以工农运动为主要革命斗争方式的中共在现实的革命中也越来越感到农民阶级所蕴含的巨大政治能量与革命精神,于是他们开始更注目于农民在中国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与作用。譬如,1927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来武汉,清算了国共合作时鲍罗廷推行的分化、联合国民党“左派”的策略,并带来了将中国的革命转变为土地革命的最新指示(诺斯、尤丁9—10)。反之,对于国民党来说,日益声势浩大的工农运动也让他们感到恐慌,感到农民的群体性行为给国家政治控制带来的实质性威胁,于是国民党也开始有意区分农民与小资产阶级,甚至对农民内部的复杂性也开始细加区别。譬如,陈克文认为只有贫农才是一个阶级,而富农是具有压迫性的,中农是有摇摆性的,因之对农民的革命性要细加甄别(1—8)。为此,1930年12月30日国民政府正式颁布了《农会法》,重建农会。②而除了国共两党之外,那些党派并不鲜明的知识分子也需要将农民与小资产阶级有意区分,不过,这里的小资产阶级主要指的是“智识阶层”。因为原本与农民同属中间等级的知识分子其实经过了一个从新中间阶级到小资产阶级的复杂演绎过程,而“几乎所有认同革命理念正当性的人都认为,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有着相似的特征——他们没有固定的阶级斗争立场、左右摇摆不定、既愿意参加革命又容易背叛革命等,因而很容易把知识分子归入小资产阶级”(张广海41—46,95)。因此,唯有将农民与知识分子分割,才能使农民获得独立的阶级性与革命性。
随着农民作为重要的政治力量走上历史舞台,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文艺自然责无旁贷。然而如此复杂的政治意义与利益诉求显然是传统的乡土文学理论所难以承载的,于是援引域外相关理论资源来阐释中国文学中的农民问题就成为一种可能的选择。而被赋予阶级、革命等政治意涵的“农民”观,显然深刻地影响到国人对域外文艺理论资源的译介。譬如由于1930年代国际共运与中国革命的密切关系,译者显然更青睐于循迹苏俄或假道日本,以期在源头上探求“农民文学”的革命本质。譬如,毛一波翻译了石川三四郎的《土民艺术论》(10—20),他的《农民文学论》也“均系抄译本(木)村毅之农民底文学一书中之第一章而成”(毛一波,“农民文学论”139—52)。“柳絮”转译了木村毅翻译的《托尔斯泰的农民文学论: 谢苗诺夫的“农民的故事”的序》(97—105)。再如早在1922年叆叇就在《东方杂志》介绍了乌克兰农民文学家柯洛涟科(83—86)。易康的《俄国的农民文学》指出俄国“农民文学”“十足的代表着斯拉夫民族精神”(106—108)。张香山1936年在《东方杂志》连载的《苏联农民文学的一个考察》则以潘菲洛夫的《布罗斯基》(贫农协会)、萧洛珂夫的《静静的顿河》和《开拓了的处女地》为例,以期为中国“农民文学”“与以最良好的一个轨范”(93—97)。此外,东欧弱小民族的“农民文学”的译介也值得注意。譬如早在1928年茅盾就译介了波兰农民小说家莱芒忒(1),化鲁(胡愈之)也对莱芒忒格外关注(1—2)。
从这些译介的“农民文学”理论或作品的评述看,农民的阶级性与革命性问题也是著者和译者共同关注的焦点,这其实仍与小资产阶级问题密切相关。因为在中国革命的语境中,小资产阶级不仅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更是一个具有批判功能的意识形态概念。由于农民与小资产阶级的界限模糊,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动摇性、妥协性也被相应地迁移到农民身上,所以1930年代前后域外“农民文学”理论译介对农民革命性与阶级性的垂注,仍是1920年代悬而未决的小资产阶级问题的延续。
从小资产阶级而谈起中国的农民问题,逐步彰显的恰是中国的农民文学理论问题从一开始被纳入讨论之时所具有的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批判性。这其实也是农民文学理论被政治化的根源所在。1930年代前后“农民文学”理论的热译正是由于不同政治派系、个人完成农民与小资产阶级的分割以实现切身利益的需要,这是政治与历史的必然。对于中共而言,这关系到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原则问题,对于国民党来说,则是稳固政权、加强政治统治的客观需要,而那些坚执民间立场的“农民文学”论者也需要在阶级革命的谱系中解构知识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启蒙权威,从而完成自我启蒙与民族自决。于是,这种具有共时性、对话性,并没有显豁的主次之别的利益主张就成为一种政治的抑或意识形态性质的复调。
二、 革命、阶级与大众的纷争
然而希冀通过域外“农民文学”理论来解决中国的农民文学问题,非但没有彻底厘清农民文学的政治意涵,反倒使得歧义丛生,这恐怕是1930年代前后那些文艺理论家们始料未及的。究其缘由,不过是假道苏俄、日本的理论资源时,对国际共运及其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内部矛盾的错位、差异性接受使然。譬如,在1930年代前后的国际共运中,斯大林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的政治斗争一度是共产国际内部的主要矛盾,在文艺上,它主要表现为深受苏联“拉普”影响的“革命文学”提倡者与“同路人”文学之间的论争,这其实也是“农民文学”理论围绕革命性问题产生分歧的主要根源。我们知道,1930年代列宁主义文学论对普罗文艺理论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对中国革命文学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影响。③譬如,在陈望道翻译的日本冈泽秀虎《苏俄文学理论》的附录“伊里基论文学”中,列宁认为,“文学底工作必须成为全体普罗列答利亚特任务底一部分,成为劳动阶级底意识的前卫所发动的,单一而伟大的社会民主主义这机器底‘一个轮子或一个螺旋。’文学底工作非成为组织的,计划的,统一的社会民主党活动底一个构成部分不可”(冈泽秀虎374)。由于中国现代农民文学理论与普罗文艺有着密切的关联,所以列宁对“普罗文学”阶级性和党对文艺工作的组织领导的强调,也对“农民文学”有着间接的影响。然而“劳动阶级”并未明示农民阶级归属,而“拉普”又强化了无产阶级文艺中工人阶级对农民阶级的领导。所以深受“拉普”影响的“革命文学”虽认同农民文学的阶级性,但对其是否具有无产阶级文艺本质则充满争议。反观,托洛茨基所谓“革命的文学同路人”指的则是“不整个地了解革命”,“对共产党理想生疏”,“多少都爱迈过劳动者底头,怀着希望注视农民”的无产阶级艺术的同路人(特洛茨基68)。这一表述虽然也未将“农民”等同于“劳动者”(工人阶级),否则也没有必要说“迈过劳动者底头,怀着希望注视农民”,④但是它并不否定同情农民的文学的合理性乃至最终向无产阶级文学转化的可能性。因而对“同路人文学”的批评不仅是对农民革命地位的质疑,更是苏联十月革命后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确立的需要。
因此,农民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关系及其在革命中的地位问题不仅是“拉普”影响下的“革命文学”与“同路人”文学的分野,更是“农民文学”理论中极为关键的理论核心问题,而对此问题的不同回应也构成了“农民文学”理论迥异的政治倾向: 一是维护工人阶级在无产阶级文艺中不可撼动的领导地位,而将农民视为被工人阶级领导的,落后的、需要改造的、不可靠的革命对象。二是将农民阶级看作在中国革命中不容忽视的、可以信赖的革命力量,是“无产阶级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毛泽东1—13)而非“辅助阶级”,⑤这两种对待农民的不同政治倾向在农民文学的理论主张中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反映。维护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及其担负着领导和改造农民任务的持论者往往将“农民文学”纳入“普罗文学”来阐释,以赋予其革命意义。譬如署名“杨柳岸”的作者就认为,“农民文学的意义狭窄地说来,是必须含有一种功利思想,作为一种运动的意义在内的”(55—60)。可见他所说的农民实指具有反抗斗争精神的农民,那些有缺点的、落后的农民是被排除在外的。沿此理路,那些激进的“革命文学”论者将鲁迅对农民的国民性批判视为“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冯乃超3—13),甚至诅咒那个“死去了的阿Q时代”(钱杏邨1—24),自然不足怪哉。而那些肯定农民在中国革命中作为无产阶级“同盟军”地位的持论者则一方面强调“农民文学”与“普罗文学”革命目标的一致性与不分轩轾的同盟地位;一方面又对“同路人”文学同情农民以致弱化甚至忽视农民斗争性的态度充满警觉。譬如任白戈就说:“农民文学既不是一种同路者的文学,也不是一种与主导者分离的独立的文学;由于中国目前这种社会变革运动底任务与担当者底合流及其命运与前途底同一,它本身就是属于这种运动的一种集团的战斗的文学。”(19—22)
然而颇值得玩味的是,无论是肯定抑或否定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这些持论者都更乐于以“大众”来指称“农民”。这一将农民“大众化”的阐释策略其实仍然隐含着前述复杂的政治矛盾与意识形态冲突。譬如为了凸显“工人阶级”之于农民阶级的权威地位,这些持论者以“大众”指称“农民”时大多淡化了“农民”的个别性,而强化了其作为“劳工大众”的普遍性。譬如,华汉就曾指出,普罗文艺在本质上必然是关于千百万工农大众的(1600—619)。郑伯奇认为“大众”所欢迎的文学,无条件地是普罗列塔利亚写实主义的文学;在王独清看来,所谓“大众”应该是“我们底大众——新兴阶级底大众”;而陶晶孙则认为“文艺大众化”的本意不是以找寻大众的趣味为能事;郭沫若更是将“文艺大众化”视作“无产文艺通俗化”,甚至“通俗到不成文艺都可以”。⑥由此可见,农民已在大众中隐身,大众完成了对农民的覆盖。但在理性的启蒙者眼中,作为农民的“大众”则是作为精英启蒙的对象而存在的。譬如,鲁迅反对文艺“俯就”大众,认为“迎合和媚悦,是不会于大众有益的”(鲁迅,“文艺的大众化”639—40)。许杰则指出五四以来周作人所主张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与“文艺大众化”有着内在的一致性(121—28)。因此,精英知识阶层的“大众”概念其实更接近公民的概念,譬如,郁达夫在《〈大众文艺〉释名》中就说:“我们只觉得文艺是大众的,文艺是为大众的,文艺也需是关于大众的。西洋人所说的‘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of the people’的这句话,我们到现在也承认是真的。”(1—3)因此在革命吃紧的时候是需要提倡这种“泥土的文艺”“大地的文艺”的(郁达夫,“农民文艺的提倡”17),“因为这是极有效力,极经济的宣传方法”(郁达夫,“农民文艺的实质”21)。知识精英虽然与那些激进的“革命文学”倡导者并不构成明确的政治冲突,但是他们对于农民的大众性的不同阐释还是表现出了尖锐的意识形态冲突。
而在基于民间立场的“农民文学”论者那里,作为农民的“大众”则更趋近于一个社会群体概念而非意识形态批判概念。他们更注重“农民文学”的底层性、群体性以及通俗性。譬如,在施孝铭(施章)看来,“我们中国的大众,百分之八十都是农民,所以提倡表现大众生活的文学,农民文学自然居其中的主要位置”(“农民文学”39—66)。这里的“大众”主要指“农民”,“农民文学”则是以“农民生活意识形态”为基础的,“表现农民们普遍的社群的集团心理的共和”,且符合农民审美习惯的、通俗民间化的文学形式(“农民文学”39—66)。因此施章对歌谣、传说、地方杂剧格外青睐,而地方杂剧即是“农民文学”/“民众文学”主要的艺术形式,具有“创造性”“国民性”“时代性”的特质。可见“施孝铭是将农民大众化了,他的农民文学概念指向了大众化、通俗化的审美标准。这从其论作对民间文艺形式的反复强调可窥一斑。反之,郁达夫的‘大众’观其实更接近于‘民众’的概念。‘农民’是‘大众’,确切的说是‘民众’的一部分。‘大众文艺’即是将农民作为底层的、有着落后国民劣根性的重要启蒙对象来看待的”(冯波56—62)。
由上而论,“农民文学”理论的倡导者虽言必称“农民”/“大众”,但实不可以道里计。革命的农民/大众是要论证“农民文学”作为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合法性,以巩固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被启蒙的农民/大众是要呈现知识精英的理性精神以宣示其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话语权;而民间的农民/大众则是要回到乡土的、民族的语境中去历史地呈现本地现代化的诸种可能性。因此,1930年代前后关涉“农民文学”理论在阶级、革命、大众等方面的纷争都不过是一些并不成熟的理论家们对农民的阶级属性、革命特质及其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作用的差异性解读罢了。
三、 缺陷与偏见互现的历史表征
对农民的阶级、革命内涵的差异性解读充分体现了不同党派、个人的功利性需求。无论出于政治的抑或审美的目的,1930年代前后的“农民文学”论争都不是单纯的义气之举,浮躁的功利诉求加固了彼此的心理壁垒,他们的私见显然大于共识,理性的、持续深入的系统理论建构自然也无从谈起。于是我们看到,这些并不成熟的理论最终成为缺陷与偏见互现的历史症候,它们虽有分合,但实无交锋;虽有激荡,但少有浪花,它们的未完成性与其努力彰显的主体性同样突出。从主观方面说,无论是有意为之还是无心之举,不同的政治背景、知识结构、审美趣味都会对农民文学理论的政治倾向、审美内涵产生具有个人倾向性的选择。加之援引域外文艺理论来阐释中国的文艺问题时可能出现的“水土不服”,都可能使得域外文艺理论的本地化出现偏颇的“误读”。尤其是理论的旅行本来就存在着难以控制的“变数”,不同阶段的理论内涵已有差异,甚至自相抵牾,那么当国内译者去选择性接受域外理论资源时,就存在着赓续矛盾而不自知的可能。此外,传播过程本身出现的延迟、滞后也会使得理论的本地化产生差异,这些本地化的错位接受都使得“农民文学”理论的“傲慢与偏见”不可避免。譬如,日本的“农民文学”理论部分来自苏联,并且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1930年藏原惟人赴苏联参加“世界普罗文学大会”后回国倡导的“农民文学”,其要义“不是单纯的提倡农民文学,而是怎样使农民成为无产阶级同盟者的一环的文学”(凄其85—87),但随着日本普罗左翼作家同盟的解体而无果而终。二是1935年左右出现“因为广阔的有力的呼喊,而使日本全国各地的农民作家醒觉起来”的创作,“一种描写各农村的地方上的孤立,在深刻的恐慌下垂死的农民群的文学”(凄其85—87)。前者是将农民纳入普罗,而后者则强调的是农民自身。譬如鲁至道所翻译的立野信之的《农民小说论》,作者就将“普罗文学”阐释为“工人及农民们的文学”(立野信之87—96),显然他接受和认同的是日本“农民文学”理论传播早期深受苏联“普罗文学”影响的观点。
再如,鲁迅曾说:“在四五年以前,中国又曾盛大的绍介了苏联文学,然而就是这同路人的作品居多。这也是无足异的。一者,此种文学的兴起较为在先,颇为西欧及日本所赏赞和介绍,给中国也得了不少转译的机缘;二者,恐怕也还是这种没有立场的立场,反而易得介绍者的赏识之故了,虽然他自以为是‘革命文学者’。”(《竖琴》“前记”5)这段话中的关键词是“革命”,反映的是鲁迅对“同路人文学”的态度。前述我们已经论及“同路人文学”在对待农民问题上与“拉普”等带有“左倾”的无产阶级文学的龃龉,那么此处鲁迅对“同路人文学”的“革命”问题的论述对于理解“农民文学”的革命性就颇为重要了。其实鲁迅所言“革命”实指“思想革命”,这与“革命文学”论者的“政治革命”不可相提并论。“革命”的各自表述使得负载“革命”之责的“农民文学”也成了“一家之言”。
从客观方面说,中国现代“农民文学”理论的“偏见”与“缺陷”其实也是政治斗争的必然结果。首先,从1930年代国共关系上讲,由于国共合作破裂,它们都需要通过文艺来服务政治。对于中共来说,党内急需纠正以往“左倾”忽视农民以及对中国革命性质及方向的错误判断,因此他们需要凸显农民的反抗性、战斗性及其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农民文学”的提倡自然是重要的政治宣传手段,但共产国际的内部矛盾导致了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们对“农民文学”的解读实有差异。因此消除“普罗文学”概念化、公式化对“农民文学”的影响,剥离“农民文学”与“同路人文学”的纠缠就是必然的选择。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及其知识分子通过反思“农民文学”的理论自觉也是确立自身政治主体性的实践,是中国革命中政治主体自我反思、自我约束的历史进程。反之,对于国民党而言,他们同样需要通过文艺的方式争取农民。譬如在1932年6月11日的《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制定之农人训练暂行纲领》中,就要求训练农人以使之“明了共产主义及其他违反三民主义各种思想之谬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488)。
国共分裂后,在严肃的政治斗争面前,这些有着鲜明政治立场的所谓文艺“争鸣”“商榷”显然不可能有丝毫妥协、让步。在国民党文人的“农民文学”理论中,打着部分共识的幌子,批评左翼文学的“概念化”“公式化”以质疑中共发动“农民”作为中国革命重要力量的合理合法性就颇具迷惑性。譬如毛一波倡导的“民众文学”(“农民文学”)一方面批评“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不承认农民为无产阶级,以城市劳动者为中心谋“农民”工人化,认为唯无产阶级文艺工具化“有陷于文艺上的无产阶级独裁的危险”(“文艺杂论”97—124);另一方面又重视“民众”的社群属性,称许木村毅视“农民的文学,即是农民自身所从出的文学”(“文艺杂论”97—124)。毛一波以“民众文学”(包括农民文学)的大众化来批评左翼革命文学概念化、工具化绝非文艺上的纠偏那般简单,从他“所谓无产阶级文学,完全是列宁党之政争的工具”(毛一波,“关于现代的中国文学”23—7)的断言以及在汪伪背景的《抗议》上连载《马克思主义之崩溃》⑦看,其实潜匿着否定中共以“农民文学”鼓舞农民进行无产阶级斗争的政治企图。而他预言“未来的社会,也必要如克鲁泡特金所说,工业和农业联合,都市与农村合一”(“文艺杂论”97—124)的观点又闪现着“无政府主义”的倾向。⑧因此,毛一波的“为民众而艺术”的“民众文学”观虽也重视“农民”,强调地方性,但他说的“农民”其实是“三民主义”视域内的“国民”,谈的“地方性”是“三民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杂糅的“民间性”。这种论述逻辑在国民党文人中并不鲜见,譬如苏由慈的观点也可作如是观。⑨
而对于那些立足于农民本身、重视通俗化形式的农民文学论者,他们的“商榷”抑或“二三意见”并非现代性冲击下被动的防御性拒绝,它并不构成对农民阶级革命性的反向书写,反之,它也是要努力探寻地方文化与意识形态化的现代“中国”之间的微妙互动,即接续传统民族记忆探寻其现代质素以争取对“正宗”的文化中国的阐释权,从而构成对“农民文学”民族品格的美学追求。这使得他们的理论“偏见”更具狂欢化,他们重视“农民文学”的语言特质,重视民间通俗文艺资源与文学的融合,在那个谁没读过两本马列就自感落后的时代,这种立足“边缘”,不慕时髦的现代理论建构成为抵抗权威启蒙救亡话语的独特表达。一方面,为了否定知识精英的启蒙话语权,他们强化“农民文学”有别于“新文学”的通俗性、民间性、乡土性等特质。譬如汪锡鹏就说:“只有在民众文学里可以直接地‘开门见山’地去指出那作品里的种族性、环境性和时代性。”(5—7)施章(施孝铭)也认为“由艺术与人生的关系上着眼,这总算是比住在‘象牙之塔’内过幻想生活的文人之作品,与高唱‘到民间去’的假哭佯啼的文学家之作品,有价值的多了”(“民众杂剧概论”21—34)。在施章(施孝铭)看来,胡适将易卜生看作“只开脉案,只说病状,却不肯下药的社会问题的病理诊断者”是大大的误读,这是“中国人以功利的问题剧的眼光”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易卜生的创造精神”16—26)。因此,他一再声明唯有农民才能创造“农民文学”,成仿吾等革命文学的鼓吹者不过是站在十字街头用革命的洋喇叭向着民众(农民)吹,他们智识阶级的属性决定了他们难以真正启迪民众(农民)。另一方面,他们也在努力通过对旧形式的“奥伏赫变”(扬弃),在“现代”的层面赋予“农民文学”合法性。他们注目乡土,深入刔发那些经过“奥伏赫变”或“奥伏赫变”后依然保留的旧形式的重要意义。譬如黄绳就提出民间文艺的扬弃要重视“旧人”、作品的“趣味性”(739—40)。
同时他们又吸纳新文学和西方文艺理论资源以实现对“农民文学”传统民间性的现代转化。这不仅是为他们所谓的“农民文学”的现代性正名,更是全球一体化背景下,以地方乡土独特性凸显民族主体精神的文化战略。譬如施章(施孝铭)就指出“农民文学”本质上体现了一种“永久的”“原质的”民间性,即一种永恒的人性叩问与追索,一种集体的、普遍的人类精神痛苦。他认为法国维勒得拉克的《商船“坚决号”》是人类对于自由的哲理沉思(“读了‘坚决号’以后”1239—246)。杂剧《朱买臣休妻》(《烂柯山》)“又何尝不是中庸的和平的全无果决的国民性的表现;又何尝不是被征服的奴隶性的表现”(“民众杂剧概论”21—34)。
在1930年代“农民文学”纷繁复杂的论争中,如上的“偏见”其实也是“缺陷”,它其实正是对启蒙理性、民族革命或世俗民间价值取向的极端化呈现。出于斗争国民党的反动文艺与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纯洁性的需要,无产阶级政党及其知识分子需要坚执“农民文学”的革命立场,于是“革命”被不断强化;面对激进革命的文艺政治化,精英启蒙者同样难以苟同,于是“理性精神”成为“农民文学”可贵的精神资源;而要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显示本地现代化的自觉,“世俗性”自然被不断肯定。因此我们看到,当面对一个新兴概念、理论时,为了实现个人的政治利益或者审美期待,这些仿佛真理在手的文艺理论家,往往究其一点不及其余,迅速确立边界,他们付出代价的同时也放弃了原本应有的部分,这使得他们亢奋的理论阐发更像是一场“圈地运动”。中国现代“农民文学”理论的缺陷与偏见都在各执一词的争辩中格外突出。
中国现代文论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影响下发生的,离开了这个前提,就不能很好地理解中国文学的现代生成。这对于“农民文学”的理论建构而言同样概莫能外,“农民文学”理论在1930年代前后的论争其实正是中国革命历程中诸种矛盾的历史性呈现,这一强烈历史症候由不同党派的不同政治目标、功能与个人的审美实践而决定。加之跨文化“越界”及其本地“协商”的不确定因素的增加,新兴理论空间的自由度更加难以把握。于是我们看到,中国现代“农民文学”理论的阐释过程实际成为不同党派、阶层、群体实现自身利益诉求的一种途径与方式,从而展现出一种特殊的时段性特质。
这种理论的时段性特质或曰历史症候使我们无法忽视那些受政治驱动的艺术理论建构的复杂性。一方面,文学要服务于一个它所维护的政治意识形态,这使得它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与斗争性,尤其对于指导具体文艺实践的理论建构而言更是如此。但是由于政治表述的差异,又形成了自身内在的矛盾。于是我们看到,理论的争鸣其实是壁垒分明的政治立场的对峙,理论形态的外部大多是偏颇的,其内部则是分裂的。另一方面,被政治绑架的文学显然不愿束手就擒,政治愿景的艺术体现过程同时包含着质疑与否定,于是个人化、世俗化在所难免。功利性的复调喧哗与民间立场的狂欢成为了此类文学理论建构过程的普遍特征,它不仅是政治理论化的结果,也因理论政治化而更为显豁。假如这种政治驱动不仅来自本土,而且由域外输入,那么情况可能更加复杂。在本地与域外、政治与审美、庙堂与民间等种种张力中,政治驱动的文艺理论建构的矛盾衍生就不仅是一个本土理论的建构问题,它所触及的中国文论的世界性问题更令人深思。如果我们继续追踪20世纪30年代之后“农民文学”论争渐趋一体化的阶级诉求与多元文化间难以通融的过程,就会不断放大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一旦与多元文化理论接触,就必然简单化处理的尴尬。
注释[Notes]
① 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用三十二天的时间,考察了湘乡、湘潭、衡山、醴陵、长沙,在调查的基础上,毛泽东于1927年3月间开始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报《战士》周报、汉口《民国日报》、《湖南民报》等连载此文。3月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上发表了前两章,4月在汉口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以单行本出版发行。
② 参见魏文亨: 《国民党、农民与农会——近代中国农会组织研究(1924—1949)》第三章“国民党执政后的农会重建”(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70—94页。
③ 列宁的文艺理论对中国革命文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1926年12月6日《中国青年》第144期发表一声节译的列宁的《论党的出版物和文学》(即《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之后成文英(冯雪峰)根据日译本重新节译了这篇文章,题为《论新兴文学》发表在《拓荒者》1930年第1卷第2期。1930年,上海南强书局出版的钱谦吾(钱杏邨)的《怎样研究新兴文学》也将冯雪峰翻译的《党的出版物和文学》列为重要的理论参考文献。此外,夏衍在1930年也译介了《伊里几的艺术观》,介绍了列宁与德国女革命家蔡特金谈话中阐述的著名论断:“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这一经典论断对于无产阶级文艺的路线和方向影响深远,甚至成为1930年代“文艺大众化”的重要理论依据。参见列宁:“论党的出版物和文学”,一声译,《中国青年》144(1926): 482—86;成文英:“论新兴文学”,《拓荒者》2(1930): 1—6;列裘耐夫:“伊里几的艺术观”,沈端先译,《拓荒者》2(1930): 659—70;钱谦吾: 《怎样研究新兴文学》(上海: 南强书局,1930年),第55页。
④ 从1992年外国文学出版社的版本看,译者则直接将“劳动者”译作了“工人”。译文为:“他们没有从整体上把握革命,对革命的共产主义目标也感到陌生。他们程度不同地倾向于越过工人的脑袋满怀希望地望着农夫。他们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艺术家,而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艺术同路人(这个词用在旧社会民主党使用这个词的含义上)。”参见托洛茨基: 《文学与革命》,刘文飞等译(北京: 外国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42页。
⑤ 彭述之认为:“农民因为经济地位的落后,阶级观念的守旧,无论无产阶级革命,无论国民革命,始终只能作一个主要的辅助阶级,而不能作领导者。”彭述之:“谁是中国国民革命之领导者”,《新青年》4(1924): 4—18。
⑥ 《大众文艺》1930年第2卷第3期开辟“文艺大众化座谈会”专栏予以讨论。参见郑伯奇:“关于文学大众化的问题”,《大众文艺》3(1930): 635—38;王独清:“要制作大众化的文艺”,《大众文艺》3(1930): 638—39;陶晶孙:“大众化文艺”,《大众文艺》3(1930): 633—34;郭沫若:“新兴大众文艺的认识”,《大众文艺》3(1930): 630—33。
⑦ 《马克思主义之崩溃》一文选载、连载或特载于1939年的《抗议》。参见《抗议》1939年第9、10、13、14、15、22、24、25、28期。
⑧ 早在1926年毛一波就对克鲁泡特金的妇女观甚为叹服,1929年他又译介了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斯丁纳(今译施蒂纳,Max Stirner)的《个人主义的哲学》,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德国施蒂纳的生平、学说、著作,以及普列汉诺夫和克鲁泡特金关于施蒂纳的评论。参见毛一波:“克鲁泡特金的妇女观: 我的读书录之一”,《新女性》5(1926): 357—58;斯丁纳: 《个人主义的哲学——斯丁纳学说的介绍》,毛一波译。上海: 光明书局,1929年。
⑨ 苏由慈也注意到了“农民文学”创作中的“情节的公式化”“人物的观念化”的弊端,并将其创作归纳为“地主豪绅官吏的压迫+农民自发的或组织的反抗=一幕壮烈的斗争”,“农民文学”要“以破产中的农村的特质为特质”,必须保护“地方性”,以“地方性”为基础。参见苏由慈:“农民文学简论”,《文化批判》2(1934): 1—9。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叆叇:“乌克兰农民文学家柯洛涟科——一八五三至一九二一”,《东方杂志》6(1922): 83—86。
[Ai Dai. “Ukrainian Peasant Writer Vladimir Korolenko: 1853-1921.”TheEasternMiscellany6(1922): 83-86.]
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前锋》2(1923): 1—9。
[Chen, Duxiu. “Chinese National Revolution and Social Classes.”Vanguard2(1923): 1-9.]
陈克文:“中国农民是不是一个阶级”,《中国农民》9(1926): 1—8。
[Chen, Kewen. “Are Chinese Peasants a Class?”ChinesePeasants9(1926): 1-8.]
冯波:“三十年代多元理论资源的选择与‘农民文学’之辩”,《文学评论》2(2017): 56—62。
[Feng, Bo. “Multiple Theoretical Choices in the 1930s and Peasant Literature.”LiteraryReview2(2017): 56-62.]
冯乃超:“艺术与社会生活”,《文化批判》1(1928): 3—13。
[Feng, Naichao. “Art and Social Life.”CulturalCriticism1(1928): 3-13.]
华汉:“普罗文艺大众化的问题”,《拓荒者》4、5(1930): 1600—619。
[Hua Han. “The Issue of Popularizing Proletarian Literature and Art.”Pioneer4 & 5(1930): 1600-619.]
化鲁(胡愈之):“再谈波兰小说家莱芒忒的作品”,《文学》156(1925): 1—2。
[Hua Lu (Hu Yuzhi). “Reconsidering the Work of Polish Novelist Wladyslaw Reymont.”Literature156(1925): 1-2.]
黄绳:“关于文艺大众化的二三意见”,《文艺阵地》11(1939): 739—40。
[Huang, Shen. “Opinions on the Popularization of Literature and Art.”LiteraryPosition11(1939): 739-40.]
石川三四郎:“土民艺术论”,毛一波译,《新时代》3(1931): 10—20。
[Ishikawa, Sanshiro. “On Peasant Art.” Trans. Mao Yibo.NewEraMonthly3(1931): 10-20.]
片冈铁兵:“普罗列塔利亚小说作法”,朱云影译,《新文艺》2(1930): 344—57。
[Kataoka, Teppei. “On Writing Proletarian Fiction.” Trans. Zhu Yunying.NewLiteratureandArt2(1930): 344-57.]
木村毅:“托尔斯泰的农民文学论: 谢苗诺夫的‘农民的故事’的序”,柳絮译,《现代文化》(上海)2(1928): 97—105。
[Kimura, Ki. “Tolstoy’s Theory of Peasant Literature: Preface to Semyonov’s ‘Farmer’s Story’.” Trans. Liu Xu.LaModernaKulturo(Shanghai) 2(1928): 97-105.]
李志毓:“中国革命中的小资产阶级(1924—1928)”,《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3(2015): 78—94。
[Li, Zhiyu. “The Petty Bourgeoisie in Chinese Revolution (1924-1928).”JournalofNanjingUniversity(Philosophy,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 3(2015): 78-94.]
鲁迅:“前记”,《竖琴》,鲁迅编译。上海: 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3年。5。
[Lu Xun. Preface.Harp. Ed. and trans. Lu Xun. Shanghai: Liang You Book Printing Company, 1933.5.]
——:“文艺的大众化”,《大众文艺》3(1930): 639—40。
[- - -. “Popularization of Literature and Art.”LiteraturoporHomaro3(1930): 639-40.]
毛一波:“文艺杂论”,《万人月报》1(1931): 97—124。
[Mao, Yibo. “Miscellaneous Notes on Literature and Art”EverymanMonthly1(1931): 97-124.]
——:“关于现代的中国文学”,《现代文化》(上海)1(1928): 23—7。
[- - -. “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LaModernaKulturo(Shanghai) 1(1928): 23-7.]
——:“农民文学论”,《橄榄月刊》17(1931): 139—52。
[- - -. “On Peasant Literature.”OliveMonthly17(1931): 139-52.]
——:“都会文艺的末路——新农民文学的提倡”,《新时代月刊》1(1932): 3—4。
[- - -. “The End of Metropolitan Literature and Art: The Advocacy of New Peasant Literature.”NewTimesMonthly1(1932): 3-4.]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农民》2(1926): 1—13。
[Mao, Zedong. “Analysis of the Various Classes in Chinese Society.”ChinesePeasants2(1926): 1-13.]
罗伯特·诺斯 津尼亚·尤丁: 《罗易赴华使命——一九二七年的国共分裂》,王洪、杨云若、朱菊卿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
[North, Robert C., and Xenia J. Eudin.M.N.Roy’sMissiontoChina:TheCommunist-KuomintangSplitof1927. Trans. Wang Hong, Yang Yunruo, and Zhu Juqing.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1981.]
冈泽秀虎: 《苏俄文学理论》,陈望道译。上海: 开明书店,1933年。
[Okazawa, Hidetora.Soviet-RussianLiteraryTheory. Trans. Chen Wangdao. Shanghai: Kaiming Bookstore, 1933.]
凄其:“日本农民文学的新动向”,《文化》1(1935): 85—87。
[Qi Qi. “New Trends of Japanese Peasant Literature.”Civilization1(1935): 85-87.]
钱杏邨:“死去了的阿Q时代”,《太阳月刊》3(1928): 1—24。
[Qian, Xingcun. “The Elapsed Era of Ah Q.”SunMonthly3(1928): 1-24.]
任白戈:“农民文学底再提起”,《质文》4(1935): 19—22。
[Ren, Baige. “Reconsidering the Peasant Literature.”Essays4(1935): 19-2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3)。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Second Historical Archives of China, ed.CompilationofArchivesoftheRepublicofChina. Vol.5.1, Politics 3. Nanjing: Jiangsu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94.]
施孝铭(施章):“农民文学的商榷”,《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15(1930): 39—66。
[Shi, Xiaoming (Shi Zhang). “A Discussion on Peasant Literature.”NationalCentralUniversityFortnightly15(1930): 39-66.]
——:“读了‘坚决号’以后”,《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7(1930): 1239—246。
[- - -. “After Reading ‘Merchant Ship Resolute’.”NationalCentralUniversityFortnightly7(1930): 1239-246.]
——:“民众杂剧概论”,《云南民众教育》1(1933): 21—34。
[- - -. “An Introduction to Popular Drama.”YunnanPublicEducation1(1933): 21-34.]
——:“易卜生的创造精神”,《长风》(南京)3(1930): 16—26。
[- - -. “Henrik Ibsen’s Creative Spirit.”StrongWind(Nanjing) 3(1930): 16-26.]
立野信之:“农民小说论”,鲁至道译,《乐群》13(1930): 87—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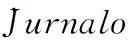
特洛茨基: 《文学与革命》,韦素园、李霁野合译。北京: 未名社出版部,1928年。
[Trotsky, Leon Davidovich.LiteratureandRevolution. Trans. Wei Suyuan and Li Jiye. Beijing: Wei Ming Publishing Department, 1928.]
汪锡鹏:“民众文学与民族性”,《黄钟》7(1934): 5—7。
[Wang, Xipeng. “Popular Literature and Nationality.”HuangZhong7(1934): 5-7.]
谢六逸: 《农民文学ABC》。上海: 世界书局,1928年。
[Xie, Liuyi.PeasantLiteratureABC. Shanghai: World Book Publishing Company, 1928.]
许杰:“文艺的大众化与大众文艺”,《浙江青年》12(1936): 121—28。
[Xu, Jie. “Popularization of Literature and Art, and Popular Literature and Art.”ZhejiangYouth12(1936): 121-28.]
雁冰(茅盾):“波兰的伟大农民小说家莱芒忒”,《文学》155(1925): 1。
[Yan Bin (Mao Dun). “Polish Great Peasant Novelist Wladyslaw Reymont.”Literature155(1925): 1.]
杨柳岸:“农民文学概述”,《微音月刊》3(1933): 55—60。
[Yang, Liu’an. “An Overview of Peasant Literature.”WeiYinMonthly3(1933): 55-60.]
易康:“俄国的农民文学”,《前锋周报》14(1930): 106—108。
[Yi, Kang. “Russian Peasant Literature.”VanguardWeekly14(1930): 106-108.]
郁达夫:“《大众文艺》释名”,《大众文艺》1(1928): 1—3。
[Yu, Dafu. “Explaining the Name ‘LiteraturoporHomaro’.”LiteraturoporHomaro1(1928): 1-3.
——:“农民文艺的实质”,《达夫全集》(第四卷)。上海: 北新书局,1933年。19—32。
[- - -. “The Essence of Peasant Literature and Art.”CompletedWorksofYuDafu. Vol.4. Shanghai: Bei Xin Publishing House, 1933.19-32.]
——:“农民文艺的提倡”,《达夫全集》(第四卷)。上海: 北新书局,1933年。13—17。
[- - -. “The Advocacy of Peasant Literature and Art.”CompletedWorksofYuDafu. Vol.4. Shanghai: Bei Xin Publishing House, 1933.13-17.]
张广海:“论何谓小资产阶级及其与知识阶级之关系——一项从民国辞书出发所做的考察”,《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4(2012): 41—46,95。
[Zhang, Guanghai.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etty Bourgeoisie and the Intellectual Class: A Study Based on the Dictionarie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JournalofShantouUniversity(Humanities&SocialSciencesEdition) 4(2012): 41-46,95.]
张香山:“苏联农民文学的一个考察”,《东方文艺》2(1936): 93—97。
[Zhang, Xiangshan.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Soviet Peasant Literature.”OrientalLiteratureandArtMagazine2(1936): 93-97.]
朱云影:“序言”,《农民小说集》,朱云影编译。上海: 神州国光社,1932年。
[Zhu, Yunying. Preface.ACollectionofPeasantFiction. Ed. and trans. Zhu Yunying. Shanghai: Shenzhou Guoguang Publishing House, 1932.]
——:“中国农民诗集序”,《读书杂志》1(1932): 391—92。
[- - -. “Preface to the Chinese Peasant Poetry.”ReadingMagazine1(1932): 391-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