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几年,徐钺的诗歌写作发生了一些相当重要的变化。他以往的诗,大多以一副锋利异常的面孔示人,这副面孔总是希望以某种神速去尽快抵达超验的境界。尽管肯定无法完全剥除日常经验的杂质,但是他在诗歌中努力“剥除”的姿态是清晰而决断的,因此,他这一阶段的诗歌在超验意义和精神高傲的层面上具有着极好的纯粹性。也就是说,他在这些诗中总是拒绝去接纳那些与纯粹无关的事物,至于拒绝的方式,也绝不是在有限的文本容量中间通过对它们的胜利而获得精神贵族身份的晋升,而是以精神贵族的身份对它们施以高傲的放逐(这事实上为他的诗歌招来了一些批评,批评的声音通常是“他眼里没有当代社会”)。因此,徐钺以往的诗在整体上会给我留下这样的印象,这也构成了他这些诗歌的重要抒情特质和发声方式,即以光年为计量单位,诗中的声音和形象一俟启动,就一头扎进超验的无影无踪之中,诗歌也因此呈现出巨大的跳跃性,仿佛可以在有限与无限之间自由穿梭而无需给出路线图和理由。这样的姿态想必和他当时对诗人、诗歌的认识密切相关。事实上,他曾在一篇名为《信使》的随笔中,把“信使”指认为如今诗人的使命性身份,其使命是在世俗中等待,等待向神祇飞翔的时刻和可能,等待接纳神的意旨而无需沾染世俗的尘垢。在这个意义上,这篇随笔结尾处的两行诗性表达可作为对徐钺这一阶段诗歌文本、诗学意识的整体性象征:
一个人,正站在船帆远离堤岸的锋利时刻
擎着黑羽毛般欲飞的双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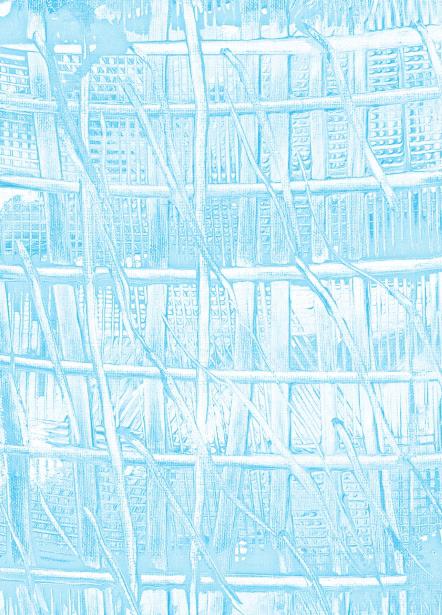
然而透过徐钺的诗歌作品,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前文所说的“杂质”侵入了他的诗歌。当然,“杂质”其实还有很多好听的别名,比如“当下历史”“现代经验”“日常生活实践”等等。然而重要的是,“杂质”的侵入并未如病菌般使他的诗歌坏死,而是恰恰相反,为他的诗歌生出崭新的肌质,也就是说,徐钺个人的写作史上,一种新的写作可能在诞生。这意味着,“杂质”在他的诗歌中获得了接纳。接纳,并不是个简单的词,因为并不是谁都有能力接纳,很多人的诗非但不能接纳,反倒会被淹没。接纳,也并不意味着诗人要与“杂质”在诗中握手言和,正如有论者所说:“徐钺书写的初衷不是为了描摹经验,不是为了顺服于经验。对他而言,经验不一定是束缚,但至少是需要突破的东西。”这就是说,对“杂质”的书写并不是要与以往的高傲断裂,而是在更为开阔的领地中实现高傲,这样的写作,实质是对过往的打开和扩大,它在自由穿梭中获得了给出之前所缺失的路线图和理由的意识和能力。
二
对“杂质”的接纳,意味着对当下时代的书写成为了徐钺诗歌创作的崭新使命。从本质上讲,任何诗人都被动地置身于自身所处的时代之中,但这并不意味着诗人对于时代就毫无主动权可言。诗人虽然无法选择自己的时代,但诗人完全拥有将时代放在某个他想要的位置上进行打量、评价的能力和特权。无论是盛世还是乱世,苦难史还是庸常史,真正有创造力的诗人总有准确书写“时代脉搏”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讲,时代对于诗人来说不啻于一场梦,诗人要做的是不断寻找契机从梦中醒来,醒来之后,诗人处于“梦的暗面”,而在这里,诗人才往往看到时代的真相。
徐钺正是属于这一向度的诗人。他的诗往往开始于“梦的暗面”(这也曾是他一首诗的题目),而其质地又往往构成对时代进行书写的提示。比如“我在冬夜的眼睑上坐着,在十二月/那略多于虚构的寒冷里。”(《关于沉默的讲座》)“七月之末昏睡的城市。历史在梦游,用寿命称量你我。”(《挽歌》)“此刻,梦和窗帘渐渐稀薄。风像岁月吹来/把燥热的申请陈述翻动。”(《暗之书(或论历史)》)这些开头清晰而强劲地展示着徐钺诗歌的发生学。它们就仿佛赌场里或者神婆手中翻开的第一张纸牌,预示着一次赌局或者占卜的开始。“梦的暗面”正是意味着诗人亲手将这第一张牌翻转,对于时代的书写由此在诗歌中发生。然而诗人并非历史学家,诗人对时代的书写与其说是一种力求客观的讲述,不如说是在亲手营造的诗性空间里进行的梦境描绘,它具有着月亮的属性,它所追求的虽然不是真实,但却完全能够抵达对时代真相的揭示。从这个意义上讲,上述引诗中的三个动词“虚构”“称量”“翻动”就相当重要,它们完美阐释了这种时代书写的本质,也揭示了诗人与时代之间关系的本质:诗人对时代的书写是创造性的,是一种以诗意为砝码的权衡,每一次书写都是以命相搏,命运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在纸牌的翻动中紧密结合。相应地,徐钺诗歌的结尾往往带有“梦醒的终结”的意味,也就是说,由“梦的暗面”返回“梦的明面”,这意味着诗人与时代之间一场诗意搏斗的尾声,也意味着诗人的一次时代书写之完成:“你挥一挥手,掀开茶杯。有人站了起来/窗外,黑色的雪也正在升起。”(《关于沉默的讲座》)“当你瞳孔里星群转动如历史席卷——我知道/在某个清晨,在你的乳房上,我也将死去;那一天,皇帝/将更早地惊醒。”(《挽歌》)“不是过去,而是那些危险的尚未到来的命运/在阴影里呵气:黎明时分/那不管你意愿的、愈加稀薄的窗帘。”(《暗之书(或论历史)》)
三
布罗茨基在为曼德尔施塔姆遗孀娜杰日达所写的悼文中有这样一段话:“说伟大的艺术离不开苦难,这是一种卑鄙的谎言。苦难会让艺术失明失聪,会摧毁艺术,时常还会杀害艺术。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在革命前即以成为一位伟大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如此,玛丽娜·茨维塔耶娃也同样如此。即便俄国没有经历过本世纪那些众所周知的历史事件,他们也依然会是大诗人,因为他们富有天赋。一般来说,天才是不需要历史的。”在这段话的逻辑中,历史与苦难具有同构性质。布罗茨基这样说,实际上并不是要否定历史或者陷入唯艺术论之中,而是意在打碎“苦难出艺术”这一荒谬的神话并让暴政彻底无地自容。我们不妨如此翻译布罗茨基的话:“天才诗人有能力在任何历史形态中成为大诗人,写出天才诗篇,因为他们富有天赋。”这样的观念也回应了罗伯特·穆齐尔的那句问话:“诗人究竟应该是时代的孩子还是时代的创造者?”毫无疑问,真正有创造力的诗人绝不会是吸附于时代船底的贝类,而是船帆之上张开翅膀的信天翁,在敏锐的飞行中“辨认低沉的海的速度”。因此,无论身处任何历史形态下的伟大诗人都有能力书写自己的时代,并创作出伟大的诗歌作品。这些作品既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又能超越其上,抵达一种普遍性的历史高度,或者说汇入伟大诗人们的历史合唱之中。
中国的当下语境显然不是布罗茨基笔下的苏俄苦难史,相比之下,它显得平静而庸常,但暗中隐藏的褶皱却也更加秘而不宣。它在更多层面上更为隐性,看似松散随意,但实际上压制性的因素并不缺乏。诚如耿占春所言:“正像压制性的因素倾向于取消真实的个人存在也倾向于取消历史真实性一样,要抓住匿名的、某一瞬间的个人经验中的历史质量是极为困难的。”也就是说,当代的历史现实更多地被压制进当代的历史褶皱中,长久的习焉不察终将把它们遗落在历史无意识的阴影下。我们日常眼中的所见,很可能并非时代的现实,只是被压平的时代图像。在这个基础上讲,徐钺“时代书写”的努力,很大一部分正是要穿过图像,写出巨大的遮蔽背后时代的某种真相,虽然他并不是要证明这些理论,而只是要完成一首诗。概括来讲,徐钺面对这时代的书写方式便是“吃着时代冗长的低语”。它首先意味着诗人对这时代平静、庸常状态的指认,其次意味着诗人对这一状态的咀嚼,并在这耐心之中书写出时代低声里暗藏的气味。因此,徐钺的近作中出现了很多当下时代的生活场景,它们在经验层面是每一个“同时代人”都极为熟悉的:“旧式录音机发出钝涩的声音,停住/一个年轻的学生跑去拨弄它。”(《关于沉默的讲座》)“我站在窗前。探出身体:潮湿新鲜的恐惧。有那么一会儿/几乎能听见窗玻璃的阴影像医院门前的草坪疯长。”(《吃着时代冗长的低语》) “但一阵更强的风使过街天桥上的小贩慌乱/匆忙——压住零钱和帽子。”(《静淑苑——仿友人》)相比这些句子,徐钺诗中还有另一些与这时代的“冗长低语”更为气质相近的句子,比如:“我的安静的妻子,我的安静的生活。”(《暗之书(或论历史)》)“二月,他在下午醒来,家人/正在洗刷碗筷。”(《静淑苑——仿友人》),它们在徐钺诗歌中的作用非常类似于《诗经》中的“起兴”,实际上是一种情绪和环境的肇始和积蓄,相比之下,前面所引的那些诗句无疑承载着更大的爆发力和能量,也就是说,徐钺对时代的书写,并不导向与时代的同构,而是穿过时代图像进而揭示某种真相的努力,它们虽然是时代的日常经验,但其实是纳入“梦的暗面”之后的经验书写,由此,它们就不再是阳光下干燥、烦冗,习焉不察之物,而是沾满了梦的湿渍的存在,也就是说,在徐钺这里,经验往往被置于经验的“反环境”中进行书写,正是在这样的错位中,他所等待的时代真相如冰山般浮出水面,或者像赌局里夺命的“红心A”倏然一闪。

上述所谈正是徐钺书写时代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他的一句诗让我印象深刻:“风。那穿过看不见的生活的重量。”(《静淑苑——仿友人》)犹如卡尔维诺将城市书写为“看不见的”,将骑士书写为“不存在的”,徐钺所书写的生活往往是“看不见的”,因此“风”对于他就显得弥足珍贵,唯有“风”的出现,他的时代书写才可能发生,时代才可能在诗的显影液中显现。在这个意义上讲,“风”构成了对通向“梦的暗面”的可能性之隐喻,而他无疑是那位“天空中狂热而天才的士兵”,或者站在暗暗翻动的窗帘前冥思的孤独者(二者构成了诗人的雅努斯两面),一次次勇敢而耐心地“等风来”。
2016/9/10 于北京 蒲黄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