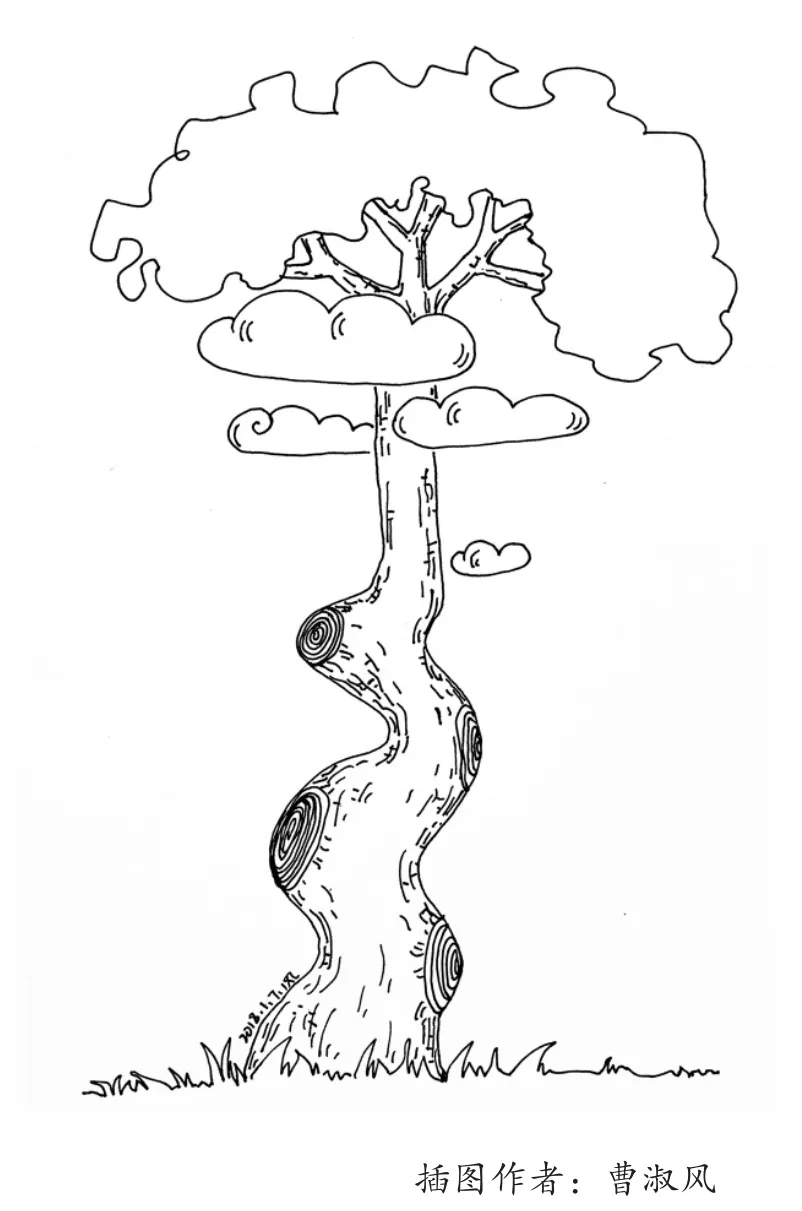王小勃的短篇小说《柳树巷》是一篇关于记忆的小说,也是一篇关于成长的小说,只不过这个记忆有点另类,这种成长有点异常。当然,在这里,另类和异常并不带褒贬,它们是中性的。之所以说它另类,是因为这个记忆不同于大多数孩子关于童年的记忆;之所以说它异常,是因为这种成长带了些民间传说的意味。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这篇小说通过对记忆的勾陈,写出了童年的孤独和执拗,也写出了生命的无限可能。
我不知道该怎样说童年的孤独和执拗,因为它并不属于显性的存在。按照一般意义来理解,童年都是幸福的,即使是苦难中的童年,也一定有隐含的温暖和无处不在的神迹。然而,这只是一种大众化的形而上的定义,并没有整体意义上的形而下的证明。生命是一个概念,但对于生命个体而言,它只能是具体而又唯一的存在。他的感受,他的体验,他的思绪,也许与其他的生命个体有重叠的部分,但也注定有不同的空间和维度。许多时候,我们愿意把这种差异置于大多数的同构,以解释生命的含义,那也许并非乡愿,而是一种惰性。我们不愿意面对个体,不愿意倾听那种有别于我们熟知的生命定义与灵魂命名。然而,作家的责任恰恰是记录这种陌生的感受与记忆,用一种文字方式粉碎另一种文字方式,用一种生命表达解构另一种生命表达。所以,王小勃用他的故事还原了童年的某种现场,用他的记忆打破了我们习惯的童年构想。
作者把故事的背景设定在了乡村,这是一个可以衍生出无限可能的场域。相对于城市而言,乡村有太多源于传说的元素,有太多神秘的戏剧性。一条小巷,一座老房子,一场婚礼或葬礼,一个印象,一句话,甚至一种似是而非的暗示,都可以引发一种伦理的冲突与裂变,都可以打开多年前的家族恩怨,这样的故事并不少见。相反,在城市,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到处都是人的欲望和挣扎,缺少那种与生存无关的演绎背景。从这个角度来看,作者这种背景设定还是别有意味的,起码它不是随机的。在柳树巷,“我”绝对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存在,当然,这个故事不是我们熟悉的故事,它缺少那种固化的起承转合,缺少那种我们期待的矛盾和逆转,它是发散的,甚至是虚化的。但是,它并非毫无因果,而是有自在的逻辑和秩序。
在正常人的眼里,“我”是不正常的,尽管奶奶说“我”是仙,不是凡人,但这种老人一厢情愿的人物设定显然无法让所有人都相信,更不用说承认了,尤其是奶奶去世之后,“我”这种常人眼中的“不正常”并没有随之消失,反而愈演愈烈。和村子里的同龄人相比,“我”是那样的特别,“我”可以远远地看着他们勾槐花,但不会参与;“我”可以自己爬到树上,但并不希望与他们分享。而这种疏离感,恰恰是一个正常孩子要努力摆脱的状况。更让人不解的是,在槐树上,“我”看到的不仅仅是槐花,还有那让人炫目的阳光以及与阳光同在的奶奶。追逐着阳光,尘世的一切皆为幻影。于是,“我”从树上摔了下来;于是,“我”在他人眼中更加“不同凡响”。而在现实中,这种不合群的孩子并非个案。然而,一旦有人刻意放大这种怪异,这种怪异也便真的成为怪异。这就是尘世。我们欣赏特立独行,但在成长过程中,我们更鼓励从众,更习惯一个孩子融入孩子们中间。或许,这也是一个永恒的悖论。
在小说中,作者并没有解释“我”出生之时的怪异,也没有交代奶奶在世时“我”令人匪夷所思的言行,他只是通过奶奶对“我”的特殊关照一带而过。这是一种简约的处理方式,需要读者自身的人生经验。老人都格外关照有问题的孩子,这是伦理的常识。所以,作者这样处理既是留白,也是伏笔。因为,从故事的发展来看,“我”绝对不是普通意义上的问题孩子,和大多数孩子相比,“我”只不过是多了一些超越年龄的深情和执拗,少了一些同龄人的天真与“没心没肺”。“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这是汤显祖在形容爱情。其实,亲情、友情又何尝不是如此。对于孩子而言,他可能过分依恋某一个人,而当这个人离开之后,他极有可能陷入一种思念的深潭而无法自拔,这应该是正常的反应。然而,在成人眼中,这种深情和执拗却成了“问题”。这是一种严重的认知错位,但在人世之中,这种错位却成了日常。所以,没有人理解孩子的真实世界,孩子的孤独无边和辽阔。
正如小说中的“我”,不仅仅迷恋阳光,还对阳光下的柴油情有独钟。而这又是一个不正常的例证。在这双重例证的压迫下,村里人冷言冷语,“我”的父母也几近崩溃,开始商量把“我”送给算命先生。于是,在惊恐和绝望之中,“我”不仅主动反击,还在月夜下离家出走,并最终在大地的怀抱中,确认了父母对“我”的真实情感,也最终确认了自我,回到了所谓正常轨道。这几乎就是小说的梗概,没有多余的情节,没有多余的铺陈,只是小说主人公的主观观照和主观感受,但读者却可以从中感受到一种无处不在的孤独与不安。这种孤独来自成人世界的不理解,这种不安来自对成人情感表达的不确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故事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孩子独特的印象和感受。
是的,这篇小说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写出了“我”对世界和人世的印象和感受,只能如此,也必须如此。因为,如果是上帝视角,那种秘密也就不复存在,那种印象和感受也便有了旁观者的通达与明了。而孩子的世界必须是含混的,他的感受、他的印象和他的表达,虽然都关涉主观世界,但却是客观的存在。可以这样说,作者选择第一人称是准确的,也是成功的。在这种视角下,孩子对世界的凝视才有了不被理解的可能,孩子那无法排遣的深情才有了清晰可感的纹理。在我看来,这篇小说的主人公并不是个体的“我”,而是那种被遮蔽的童年的印象和感受,是童年的孤独和执拗。
这个故事充满了生命的隐喻,阳光、柴油以及月光,都具有无限的抽象意味。在“我”的眼里,阳光不仅仅是奶奶的化身,更是一种尘世的温暖,它让那种无法言说的情绪有了物质的落点;柴油也并非一种特殊的味道,而是有别于日常生活的存在,它值得我们去凝神、去关注,值得我们把想象注入其中;而那月光,更是让我想起莫泊桑的经典《月光》,在莫泊桑的月光下,一个神父最终放下了偏见,认识到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也在上帝的祝福中。而在《柳树巷》里,“我”同样在月光中确认了伦理的质地,并拥抱了误解中的血缘。至于小说的题目“柳树巷”,它既是故事的背景,也是一种需要被我们凝神并关注的时空,在那个时空里,充满了孩子们的成长轨迹和心理细节。而小说的语言和这种隐喻叙事高度匹配,它不重故事的构建,而是尊重思绪流动的自然属性,灵动、多义,充满不确定性。再加上小说里反复出现的歌谣,使得小说具有一种独特的诗意之美和运动之姿。
我喜欢这篇小说,因为它写出了一种不应该被我们忽略的成长法则——孩子的世界并非一览无余,孩子的世界藏着许多成人缺乏耐心去理解但应该理解的秘密。或许,对于一个人的成长而言,这些深藏于孩子记忆中的印象和感受,才是一个人性格形成的内在原因。然而,我们习惯了日常的成长,却忽略了这种成长的内在机制,这是我们的遗憾。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这篇小说并没有写实,而是在表现,用那种自由而又多向的思绪表现心灵的成长,它有余华《在细雨中呼喊》的影子,不需要唯一而又明确的主题,也不需要读者去刻意把握,它只需要我们能静下来,去倾听一个生命最隐秘的呼喊,去感受一个生命最私我的感受,然后留下一个大致的印象——曾经有生命这样感受过,还会有生命这样感受——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可以给那些看似发呆的孩子们留下足够的时间和理解。能如此,这篇小说便实现了它的价值;能如是,我们也就在理解生命的道路上又多走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