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暖阳(外一篇)
■伏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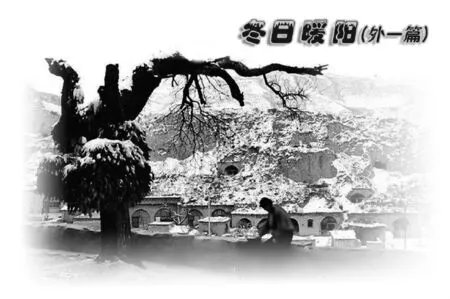
一
独爱那冬日暖阳。爱它的温度,温热而不灼人;爱它的光亮,温和而不耀眼;爱它的性情,温良而不张扬——就像一杯捧在手心里的温开水,指间传递的,恰是爱的温度。
总记得欧·亨利的《最后一片叶子》里的老贝尔曼——一位穷困潦倒的老画家。在病中的年轻画家琼珊因为窗外逐日凋零的常春藤叶而一点点放弃生的欲望的时候,他奉献出一幅以生命凝成的作品——那枚永不凋零的常春藤叶。在琼珊的世界里,老贝尔曼就是一道冬日暖阳,为她驱散了生命中的凄风苦雨,给她逼仄的人生之路抹上了一层淡淡的暖色。
这个世界上总会有许多的阴霾和凄冷。正因为有阴霾和凄冷,一轮暖阳才弥足珍贵。即便是那些挥之不去的阴影,因了这道暖阳的映射,亦会镶上璀璨的金边。
二
在我的世界里,外公就是一轮冬日暖阳,为我和我们家带来融融的暖意。他是一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农民,如同浩瀚夜空中一粒微不足道的星辰。他的双脚上布满了老趼,但他人生的半径却始终没有突破他家和他的儿女家的距离。
当外公有了孩子,孩子便成了他生活的全部——即便孩子们成家立业,过上了远远优裕于他的生活。他在世时,每个月都会往儿女家运送自己种植的蔬菜大米——对他来说,我们永远是一群未曾断乳的孩子。为了儿女们的这些绿色食品,一个个微熹初露的清晨、烈日炎炎的午后、月明星耀的夜晚,外公都会辛勤耕耘在那片热土上,不知疲惫。
当家族中的第三代诞生,他便坚持让外婆离开老家进城照料孙辈,而他一人扛起了这个家族的“后勤”的重任。孤独劳累的他,最终积劳成疾。这个树一样扎根在田间的老人,只有在生命的最后几日才静静地躺在病床上,接受着他的儿孙们的反哺。
外公不善言辞。他与我唯一的交流便是拉起我的手,轻轻地摩挲着,再给我一个温暖的笑意。临终前,他也是这样——拉着我的手,轻轻地摩挲着。那掌心的粗糙,刺痛了我的双手,更刺痛了我的心。透过晶莹的泪光,我看到他温暖的笑意就像一道冬日暖阳,映照在他身边的孩子们的身上和心里……
三
生命中那些难得的温暖,有时候不是来自文学殿堂,也不是来自亲人之间,而是来自一个完全与你无关的陌生人。记得高二的寒假,我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参加一个补习班的学习,要一个人坐车来回。一月的风仿佛带了刀子,在脸上硬生生地刮蹭,车厢也不见一丝暖意。那天可能着了凉,头隐隐作痛。上车后我倚在车门上,尽力支撑着。这时,一个小男孩走了过来,眨着一双亮晶晶的大眼睛,对我说:“姐姐,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我带你去坐我的座位好吗?”平时我是绝不好意思坐一个小孩的座位的,那天实在太难受,就依从了他。男孩一直站在我身边陪伴着我,他比我早两站下车,下车前还嘱咐我:“姐姐,你要记得去医院看医生哦!”面对这个也许正读一二年级的男孩,我的心中蓦然升起一股前所未有的感动:“谢谢你,小朋友!因为你的座位,姐姐休息了一会,现在已经不难受啦!”他得意地微笑着,对我做了个V形的手势——那张笑脸我一直记忆犹新!
后来,我还遇见过许多像这位小男孩一般的陌生人,他们以自己的一个别人也许并不在意的细节向他人传递着一种善心、一种爱意——比如一个亲切的微笑、一个欣赏的手势、一句善意的提醒、一次绅士的礼让……这一切,就像冬日里一道道细碎的阳光,不经意间温暖了你的心房,温润了你的心情,让你的人生之旅,不再冷寂、孤单……
别人温暖了我们,我们温暖了别人——从此,这个世界不再苍凉。
广场边的卖艺人
上学、放学的时候,路过市中心的铜马广场,总会听到阵阵喑哑的二胡声。那是广场边上的一位卖艺的老人,埋着头,在兢兢业业地营造着那份苍凉。
还是在很小的时候,我跟着妈妈到市中心的书店买书,就见到这位卖艺老人低着头坐在那儿,自顾自地拉着一把二胡。当时我对二胡一窍不通,加之年龄尚小,便对那胡子拉碴的老爷子由衷生出一股崇拜之情——以为他是一位很有水准的艺术家。
于是,带着这最初的印象,听着这不甚了了的二胡,度过了许多岁月……
一天的音乐欣赏课上,老师郑重地捧出一盒珍藏已久的磁带:“这是阿炳演奏的《二泉映月》。”听着那凄切忧伤而又婉转圆润的旋律,我不禁悲喜交集——喜,是因为卖艺老人所拉的,正是这首曲子;悲,是因为我不曾料到卖艺老人的技艺与大师竟是如此悬殊!
此后我每次路过,总忍不住多看老人几眼,目光中虽然少了几分崇拜,却多了对其不堪命运的悲悯。我几乎没有看到过老人抬一抬头,他仿佛完全与外界隔绝,一个人完完全全地浸入到了音乐的意境中,浸入到了自己借音乐来宣泄的某种情感里……他是通过音乐来慨叹生活的艰辛?还是抒发对坎坷命运的自怜?抑或表达对过往的追忆和对未来的茫然?没有人知道。但在那不太圆润的粗糙的乐声中,人人都可以看到:他的须发在一天天变白,他几乎从不更换的破旧的蓝布衣衫渐渐看不出色彩,他的黝黑的脸上皱纹在一日日变深且爬满了脸部的每个角落……他几乎不抬眼看人,他也从不开口说话,搁在面前的布满裂纹的白色瓷碗里总是寥寥的几枚硬币——所有人都看得出来,这是一个贫苦的卖艺人。
但他毕竟是一位卖艺人,卖艺人有卖艺人自己的骄傲。他拥有的不仅是与他风雨相伴的二胡,更有以音乐换取生活的尊严——全不似靠出卖尊严换取同情和怜悯的乞丐!在那匹昂首奋蹄的大铜马下,他拉着他珍爱的二胡,在艰难的生命旅程中坚毅前行。
那首在他的手下变得有些支离破碎的《二泉映月》,似乎与他的身世极其相配。虽然老人没有阿炳高超的演奏技巧,也无法像音乐大师一样层层铺垫最终爆发出情感的洪流,但这又何妨?艺术女神公平地对待每一个人,即便是最卑微的卖艺人也可以在音乐中显示其独特的亮色。的确,他的音乐显得生硬,艰涩,难登大雅之堂,但这或许正是演绎他的人生、讲述他的故事的最好的载体……
尽管读中学的我变得越来越忙碌,但每次路过广场,我都会稍稍放缓脚步,向卖艺老人投去我关注的一瞥;甚至平时我会少用些零花钱,为的是能在那苍凉的乐声中稍稍驻足,向那只白色瓷碗中弯腰投上一枚硬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