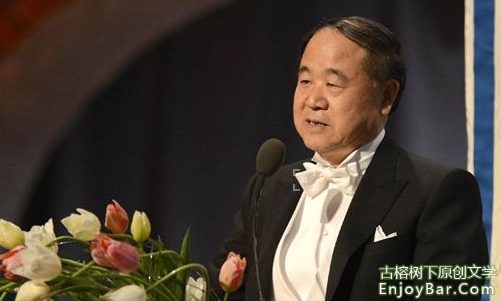
中国作家为什么获不了诺贝尔文学奖?
马悦然答别问瑞典学院,问自己
马悦然
瑞典人,著名汉学家,1952年在斯德哥尔摩大学获博士学位,1956年到1958年任瑞典驻华使馆文化秘书。毕生致力于汉学研究,先后执教于伦敦大学中文系、澳洲国立大学中文系、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1975年当选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1985年当选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并且是惟一精通中文的评委。他把众多的中文作品,如中国古代、现代、当代的文学作品翻译成瑞典文,他的译作包括《诗经》(部分)、《楚辞》(部分)、大量的汉代诗歌、唐诗、宋诗、宋词、元曲、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诗人郭沫若、闻一多、艾青、臧克家等人的作品。此外他还翻译了《水浒传》、《西游记》和沈从文、李锐等现当代作家的作品。
“中国伟大的诗人好像是我的好朋友”
马悦然,大名如雷贯耳。
他不仅是著名的汉学家,更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中惟一懂中文的评委。
因此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上海文学》主编陈思和先生一告诉我马老在复旦的消息,我立即中断在外地的采访,返回上海。
会面的地点在复旦校园内一家小咖啡馆里。匆匆途经步行街上四家书店,总算觅到一本马悦然的大作《另一种乡愁》。这本三联版的散文随笔集,收集了马悦然有关中国的文章。
一头银发的马悦然早已在咖啡馆内等我们。见到马先生,首先是恭恭敬敬地捧出先生大作请他老人家签名。马老把我的名字翻成英文,“马先生为什么不写中文?”“怕写不好。”“那你平时怎么用中文写作?”“用电脑。”“用什么码?”“我习惯用拼音。”
1946年,马悦然开始跟随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学中文。学了两年的古文后,获得美国“煤油大王”的奖学金来中国,在峨眉山古刹报国寺中精心研究成都方言的声调在句中的变化。他曾说:“1948年到1950年,我开始对中国早期的诗歌感兴趣,读了不少汉朝、南北朝、唐、宋诗人和词人的作品。中国伟大的诗人好像成了我的好朋友。我书房里藏的诗集特别多。虽然空间和时间的距离不允许我随时去找他们,但我可以请他们到我家里来:我想跟李白摆龙门阵或者跟稼轩居士干一杯酒,我可以到书房去找他们。因此,我不感觉寂寞。”
楼乘震(以下简称“楼”):您认为汉语难学吗?
马悦然(以下简称“马”):不难。当年高本汉教我们时从《左传》开始,在读过《左传》之后,我开始阅读春秋三传的其他两传——《公羊传》与《谷梁传》。当时《道德经》就有30多个译本,我们不知哪个最好。高本汉说他的最好,我们就读他的译本。我们请老师教一点现代点的东西,老师就说教一点陶渊明。就这样。1948年到1949年我在报国寺住了8个月,老和尚非常有学问,每天早上跟他学两小时汉朝五言诗、唐诗宋词。我教学生也是这样,不读课本,读名著。读《故乡》、《逝水》比课本好。汉语语法非常简单,只有语法没有构词法。只要知道一个词在句子中的位置,在语音上很自然学会。我的学生每天半小时,四个月就能讲中文了。
看得上眼的中国当代作家只有李锐?
马悦然近年来翻译了山西作家李锐的大量的作品,去年秋天,他时隔多年后到中国内地访问,就去了李锐小说中的原型——插队时的小山庄,住在窑洞里,还特意请房东杀鸡宰猪,款待全村的老乡。他回来后十分兴奋,逢人就说我去过吕梁山了,“我原以为那里很穷,结果发现大家过得挺好的。窑洞特别漂亮!”
难道马悦然看得上眼的中国当代作家就只有李锐?这不仅是我的问题,许多作家也颇有微词。
楼:您平时对中国文学动态是怎么掌握的?
马:有互联网,大家都会给我发E-mail,我还会收到许多刊物。
楼:你对哪些当代作家比较熟悉?
马:我翻译了包括《厚土》、《万里无云》、《旧址》等在内的大部分李锐作品。李锐一直关注吕梁山区的农民生活,写的是典型的“农民小说”。此外,苏童的《米》、阿城的“三王”、冯骥才的《三寸金莲》、王安忆的系列作品我也很喜欢。我最近翻译的作品是曹乃谦的小说《到黑夜想你没办法》,他是一个山西大同警察,很穷,写1973年到1974年农村的生活,有30篇小说,运用了典型的农民语言,是一种山西地区的“要饭调”,但这不是“要饭”,是当地的一种情歌,其文学价值不可小看。他懂音乐,会拉二胡,吹笛子,耳朵很灵。我是去年到山西时李锐介绍给我的。明年春这本书就可在瑞典出版,明年7月香港也会出版。你看过他的小说吗?发表在《山西文学》上。
“中国有《诗经》时瑞典人还披着熊皮在森林里呢”
组织者曾事先关照,马悦然此次来沪十分低调,只是想会会老朋友,所以不接受任何媒体专访,更不要提有关诺贝尔奖的问题。因此这个问题在我嘴里含了好长时间,终于吐了出来。
楼:非常冒昧地问一下先生,中国作家要达到什么水平才能得诺贝尔奖?
马:经常有人问我,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为什么冰岛、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都能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而我们却没有?首先要搞清楚的是,诺贝尔文学奖是给作家个人的,不是给国家的。是的,中国有悠久的历史,《诗经》是全世界最古老、最优秀的诗歌,《左传》、《庄子》是世界文学史上最优秀的作品,那时瑞典人还披着熊皮在森林里呢。前几天我去看王元化,他是研究《文心雕龙》的权威,世界上有哪部著作可以与《文心雕龙》比?中国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现代文学是最好的,鲁迅、郭沫若、闻一多、艾青等等。四十年代后,许多人就不写了。沈从文也去搞考古了,原因不必由一个外国人来告诉你。六十到七十年代,有哪些文学价值高的作品出现过?除了浩然,还有谁在为读者写作?有什么作品可以吸引我?所以,这个问题不应问瑞典学院,而是要先问自已。
曾听说,美国人很早就翻译了沈从文的《边城》,但翻译得不全。后来马悦然翻译了沈从文大量的作品,瑞典文学院的同事们都比较喜欢。沈从文1987年和1988年两次被提名。从当年同事们的评论来说,他是很有希望得奖的。当年,龙应台把沈从文去世的消息告诉了马悦然。马悦然打电话到我国驻瑞使馆核实,但使馆接电话的那位老兄居然不知沈从文是谁,使他非常恼火。当后来证实沈从文确实已去世,马悦然难过了好长一段时间。
“诺贝尔文学奖的标准非常主观”
楼:那么,获诺贝尔文学奖有什么标准?
马:只有一个标准,文学价值!头30年确实给了一些不应该得的人,如法国一位诗人,卞之琳气得要命,说太不象话了。但是最近五六十年,我觉得还是成绩比较好。但我告诉你,这个文学价值是非常主观的,我爱读的作品文学价值就很高。比如刚才说的曹乃谦,有人认为他的语言粗、脏,看不下去,而我却认为好,没有客观的标准。18个院士也不要意见一致,只要半数以上通过,这个奖就给谁。院士中懂中文的只有我一个,我的工作是做说服。是的,非常主观!(马悦然坦率地再次强调。)
几乎每年,我们都会看到几位旅美华人组成的“推荐委员会”说某某今年要获诺贝尔奖,事后证明完全是炒作,但炒的不是某某作家,某某作家往往也很反感,炒的是他们自已。但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过程到底是怎样的呢?读者肯定很关心,我得寸进尺想问一下。
楼:马先生是否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程序?
马:好。诺贝尔文学奖不是作家申请的,而是要有人推荐的,不能集体推荐,要个人。有推荐资格的人很多,作协的主席、副主席,笔会的主席、副主席,大学文学系、语言系的教授、副教授。光一个复旦大学就有几百个。推荐在每年2月1日前结束,然后由一个五人小组进行整理,往往有二百到三百个,到4月份就筛选到20多个,到5月份就只有5个了。6、7、8三个月就看他们的作品,9月份每星期四开会讨论。10月份投票,一次,二次,三次。最后决定谁是获奖者。今年比较轻松,因为今年5位中,2位是前年的,3位是去年的。只要看一些今年的新作品就行。如果我一个人喜欢,别人不投,我投了也没意思。去年对某作家我很不满,想把书扔出去,但没办法,只好读下去。
我在翻译中文作品时一般要看三遍,才动笔
楼:今年的5个人中有中国人吗?
马:(顽童般笑着说)你可以问我,我可不能告诉你。
楼:评委中只有您一人精通中文,影响其他评委的是不是关键在翻译?
马:对!翻译的水平太差,完全没有了原著的意韵,这是个老问题了。巴金的《家·春·秋》的英译本,对话部分翻得还可以,但很多叙事部分因为译者觉得烦琐竟被大量删除,偷工减料。五十年代我请老舍吃饭时,他就说有人把他《二马》的结局改成好莱坞式的大团圆,真是哭笑不得。我在翻译中文作品时一般要看三遍,才动笔。等到你感觉到作者通过书在和你交流,你能感觉到作者的呼吸,四川话就是“拍子”,这时我才开始翻译。而且现在翻译的稿费很低,我翻李锐的一部长篇只有一万元港币,当然我不在乎这个,那青年翻译家呢?
楼:外国作家用中文写作恐怕不多,《上海文学》上发表你的“小说九段”,今天又得到您的这本《俳句一百首》。您怎么想到会用中文写作的?
马:莫言在今年《上海文学》第一期上发表了“小说九段”,莫言创作长达几十万字的小说多年后,又开始尝试微型小说,其创作能力着实令人吃惊。我模仿他的,也写几段微型小说,一下子写了四十多段,还有用古文写的,就从中选了九段发表。
楼:那您认为哪首写得最满意?
马:(不假思索)当然是第100首!
我翻到最后一页,只见第一百首只有一个字:空。我赶紧问,为什么说它最好?马大声回答,空嘛!(众哈哈大笑)
上海今年的夏夜闷热得烦人,可是这一夜聆听这位81岁瑞典老人用普通话夹杂着四川方言和英语单词的谈话,心里真够爽的。
作者:楼乘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