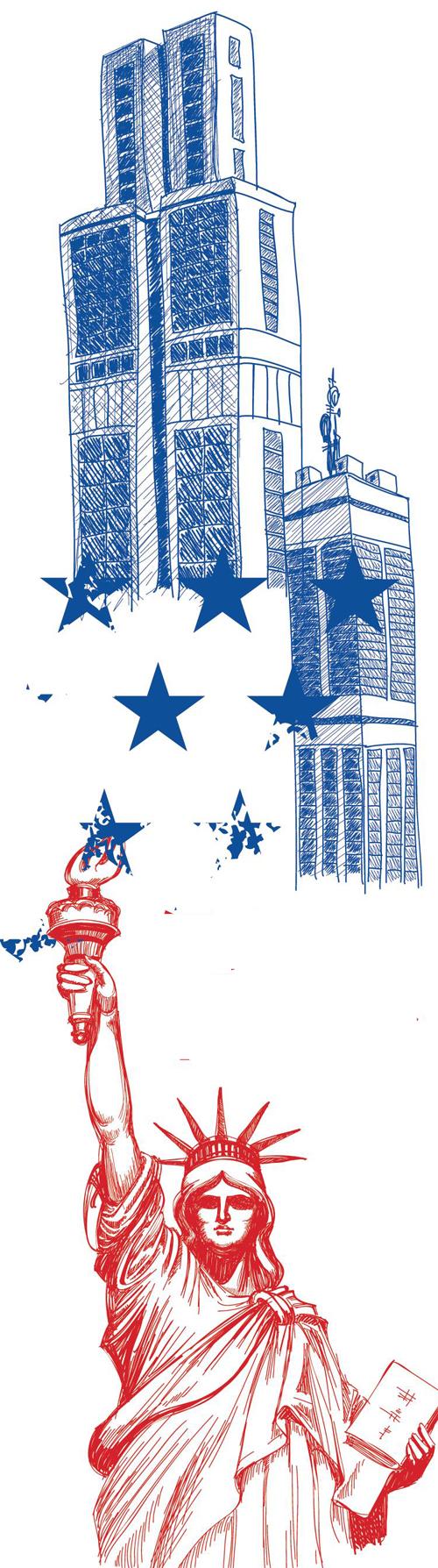
家里有亲戚从中国来美国旅游,纽约这站我做地陪。这个活儿原本不难,在过去的18年里,我已经不止一次扮演过这个角色,接待过好几位亲戚、朋友或亲戚的亲戚、朋友的朋友。不管是来开会的,来旅游的,来培训的,来考察的,到了纽约,不过都是按图索骥,在大都会博物馆、联合国大厦、自由女神像、华尔街这些举世闻名的景点匆匆走上一圈,咔嚓咔嚓拍些照片,再到唐人街的中餐馆吃一顿似是而非的中国饭,大家就都心满意足,而我也算得上仁至义尽、功德圆满了。但最近这些年,情况变得复杂起来。
比如这次,我们一行人在曼哈顿逛了一整天,最后来到霓虹环绕、流光溢彩的时代广场。坐在广场中间的观景台阶上,众亲戚发话了:“这就是时代广场啊?这么小!”
“是啊。”我语带歉意地说。
“这些霓虹灯什么的还不如我们国内的好看呢。”
“是吗?”我讪讪地说。
“这儿好像也没什么呀。”
“就是嘛。”我随声附和。
“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大名气呢?”
这个问题我本可以用一场两小时的PPT演示解答,但亲戚们显然并不感兴趣,没容我开口就抛出下一个问题:“那我们来这里看什么呢?”
“嗯……看人吧。”我实话实说。
所有人都笑了,但我是认真的。
多年来,我在采访来自中国的移民或游客时有个习惯,总会问一问初来乍到的时候纽约留给他们印象最深的是什么。这本来是个无心之问,为的是给接下来的对话暖场,但这些答案串在一起,竟能在只言片語里折射出时代的沧海桑田。
一个在20世纪80年代初来美国的艺术家说,那个年代中国的牙膏还是铅皮包装,曼哈顿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让他目瞪口呆;一个在20世纪80年代末来的国企职员说,纽约超市里丰富的商品让她眼花缭乱,她曾经在洗发水货架前站了半个小时还是不知道上面摆的十几种大小、颜色各异的瓶瓶罐罐该买哪个好;一个在20世纪90年代初来的大学教授说,他很想逛逛第五大道上的名品店却没敢进去,觉得自己太寒酸;一个在20世纪90年代末来的高中生说,第一天上学时学校里发了纸盒牛奶,他花了好长时间都没搞清应该怎么打开——他从来没见过纸盒里装的牛奶。一直到2000年,我来美国留学的时候,公园和运动场上随处可见的饮水器还让我好奇了很久,特意拍了张喝水的照片发给爹妈去显摆。
这些现在听上去就像老相册里那种在冲洗的过程中加涂红脸蛋的照片,色彩鲜亮却蒙着岁月的烟尘,一看就知道属于另一个年代。最近这些年,这个问题的答案清晰明确,却也变得越来越千篇一律,大抵都是:“纽约,不过如此。”
移民来的人一落脚就开始怀疑来这里是个错误的决定,慕名而来的观光客也难免像我家亲戚那样摸不着头脑:这里的地铁站光线昏暗,轨道上老鼠横行,远不如中国的敞亮气派;高级餐馆鲜有包间,用的餐具看上去都很有年份,远不如中国的光可鉴人;曼哈顿动辄千万美元一套的豪华公寓,外表看上去也不过就像中国大城市里随处可见的现代化高楼;中央公园不过是一大片草坪,华尔街不过是几步就能走到头的小巷子……真的,我们来这里看什么呢?
说实话,这年头在纽约已经找不到能让见多识广的中国人有兴趣抬抬眼皮的丰饶阔绰和富丽堂皇,财富、奢华、“高大上”早就开始悄悄地转移阵地,成为中国的景观。如果说纽约还有什么是在中国不常见到的东西,那只能是由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共同构建起的多元文化。
有一次,我和一个中国来的朋友走在曼哈顿街头,他突然说:“这里好像没有多少美国人。”我知道他指的是白人。在纽约的850万人口里,白人占比不足一半,将近四成是外国出生的移民。但他们就是美国人,或者说他们就是纽约人。他们带着各自的文化和习俗,来到这个被称作“大熔炉”的城市划地而居,形成了“唐人街”“韩国城”“小印度”“小加勒比”这样特色鲜明的城中城。因此也有人说纽约并不是“大熔炉”,它更像一个“色拉碗”,人们并未真正融为一体,而是各自为政。
也正因为有了这些各自为政的小区,连接时代广场和华人聚居区法拉盛的地铁7号线才会被称为“国际快车”——据说这趟地铁从头坐到尾所经过的地区,人们说的语言有100多种。一趟车下来你可以品尝到众多国家的特色美食,欣赏到不同的民族服饰,在沿街的小店里见到各种稀奇古怪的玩意儿。
对中国游客来说,逛这些地区大概需要勇气。非主流的美食未必能吸引根深蒂固的中国胃,非主流的样貌也未必能满足中式的审美,非著名的景点图片发到微信朋友圈也不见得有人点赞。更重要的是,移民聚居区往往是他们祖国面貌的潦草翻版,而居住在地铁7号线近旁的移民,他们的祖国大多在经济上远远落后于中国。谁愿意不远万里来到世界之都,去看一些破旧衰颓、杂乱无章的第三世界景观呢?
在这个越来越以“我们”和“他们”划分的世界上,“我们”对“他们”的信任、接受和欣赏是个漫长的过程。如果每年来到纽约的100万中国游客,能从纽约的见闻中更贴近地了解多元之美、拓展包容之心,从这里开启一段对“异类”同理相待的旅程,那就真的算是不虚此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