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爷山下二营城
牲畜有牙口,人也有;牲畜有尾巴,人却没有。有尾巴的牲畜与人无法语言沟通,只好借用尾巴的摆动来表示对人的服帖、敬重或是恐惧。牲畜以外,鸡犬鸭鹅鱼虾鳖蛇通常也用摆尾的方式表情达意。然而,人们有时候关注的不是它们的尾巴,而是它们的牙口。一匹马的价值,包括它的年龄、祖宗,都含在它的嘴里。马贩子衡量一匹马,只需掰开马嘴看一眼,从不在乎马的脸势。
我快临近原州区头营镇二营村半颓的古城时,几个农民正在大道边指手画脚地谈论着他们身边的一匹枣红马。这匹马很像电影剧照上见过的李世民的爱骑——波斯“什伐赤”。
这几位农民不像闲聊,他们说话声大得像吵架。我老远就听到了他们对这匹马的不同假设。假设把它赶进动物园和东北虎、云南大象一起做展览会不会有人专意花钱去看它。假如把它牵到城里,备上漂亮的鞍子让城里人骑在它身上照相会不会狠赚一把。后者认为,现在驴马骡子快绝种了,人都想图个稀罕,耍个骚轻,留个纪念。马的主人却一声否决,摇头否定。他以为这匹马已然派不上用场,不如趁牙口尚好把它牵到集市上卖了。或许别人还有用场,还能出个差不多的价钱。他的这种想法受到了其他好几个人的反对和挖苦。有人说,别忘了,咱处在回汉杂居的西海固,马肉不值钱,牵到集上去买,这马恐怕还不值一只大羯羊的价。也有人提议不如趁现在驴肉吃香,把它杀了,剥了皮,剔出纯肉,卖给城里汉民开的驴肉馆。这是一个比较大胆的设想,说得所有人都哑然了。
这个提议会不会被马的主人采纳,驴肉馆里的老板会不会不识货或有意不识货,驴肉馆里的厨师能不能把马肉加工出驴肉的味道,不得而知。但我以为这不是什么上策,据说,马肉是酸的,而驴肉是腥的。
二营,明代是座马营。不远处那座古城,就是铁的见证。这几位农民朋友就站在二营古城对面的村道边,他们谈论马的牙口和马的价值时,谁也没抬头。他们对站在身边傻乎乎地甩尾巴的枣红马不屑一顾了。
暂且放下他们不谈。我们来看看这座因马而立的二营古城吧。
为了保证军马的供应,明朝政府很重视军马的繁殖和牧养。由于固原所处的政治、军事重要地位,和良好的自然牧马环境,成化年间,朝廷设置了陕西三边总督,从而奠定了固原在力行马政时的重要地位。《嘉靖固原州志》记载:当时朝廷苑马寺设立在固原州境内的苑监有一监三苑,即长乐监,在州城东北隅。所属三苑:开城苑,在头营,圉长3员,领8营(头营至8营)马房,草场6所,马圈13处;二营内置苑马行寺,南北长126里,东西阔180里……又据《固原历史纪要》记载,开城苑所属有八个营;头营、二营旧有城堡,但城的空间都很小。后二营在本城南面拓展,周围295丈。
以上是二营古城当初的有关记载,如今,眼前的二营古城仅剩不高的几垛残墙。只有建在古城东南角的苑马寺内城,尚属完好。
苑马行寺不是寺院,而是和苑马寺一样属于官府掌管马牧的一个机构。苑马寺属三品衙门,有长官一人,从三品。掌管所属各牧监、各苑之马政,听命于兵部。弘治(1488—1505)中,因这一职位缺员,朝廷便简选各布政司参政和按察副使其中有才望者给予提拔填补。到了嘉靖(1522—1566)时,苑马寺卿权力更大,不仅管马,还可以兼辖部分卫所的军民。而二营的苑马行寺则只是辅助开城苑行使马牧管理的基层官衙,只有七品权力。可见,当时二营城的政治地位次于头营城,与所属开城苑的其他马城有所不同。
说到明代的马政,少不了要提到三边总制(嘉靖十九年即1540年改为总督)杨一清。他是明代五十六位三边总制中唯一历任三届的总制。在杨一清总制延绥、宁夏、甘肃等处军务兼督马政期间,他亲自体察边情,复兴马政,根据地理环境奏请朝廷建筑定边营至横城的(边)墙三百里。虽然后来只筑成了三十里,但他的一生,为明代的边防与马政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我高一脚低一脚上到二营苑马行寺的城墙上,低头见一位中年农民正在自家的场院里牵着耕牛碾场。他专心致志地看着脚下麦穗里碾出来的每一颗麦粒。他身后,一头红犍牛牵着一柱石碌碡跟随他的步伐不紧不慢转着圈。我在城墙上选了一块平整的地方坐下来,想静静地看看一个农民与一头牛间的默契程度。可我坐了没几分钟,就站了起来。我发现刚才谈说马的那几位农民朋友不见了,是不是他们搭伙去屠宰厂了?说不上他们其中有人早就备好了刀子,说不上明天驴肉馆肉案上会“吧唧”丢下一大块马肉。说不上这马半道上就被人买了去,给它背上扣下一副花里胡哨的鞍子,再给马嚼铁两旁拴上两朵鲜艳喜庆的小红花……
但我还是为能在这座五百多年前的苑马行寺古城附近,看见一匹欢实的枣红马而感到欣慰。因为,也许再过五百年,这座古城就完全隐没了,马就只能去动物园里欣赏了。
马和人一样,都是大地上最原始的动物。人一辈一辈都落了土。马呢,曾经死在战场上、死在路上。据说,人死了可以转世,能转世成马,叫人来骑,叫人用鞭子抽,但不知道马能不能转世(有人说驴也可以转世,武则天就喜欢过转世的驴),转世转成人,再骑到转世成马的人身上。
碾场的农民和红犍牛已经碾完了一场麦子,停了下来。他们相互望着对方。人有点疲惫,像劳累的牛,牛麻木不仁,像发愁的人。如果把这个农民这头牛和刚才那匹枣红马那个马的主人联系起来。以后,如果再不用牛来种地碾场,用机械,那这头牛会不会也落得个马的下场。眼下,这头红犍牛还在服轭,还没有卸下拴在屁股后面的石碌碡。它望着它的主人,有一下没一下地摆着尾巴。以后是什么样子谁也不知道。我只是希望这头牛到了晚年,干不动活儿,牙口不行了,它主人能喂它一把嫩草吃。
抑或焦赞城
固原城边有座土城,有人叫焦赞城,有人叫大堡子。叫焦赞城的原因并不是杨家猛将焦赞在这里驻扎过,而是想以此拉近自己与忠义之士的距离。叫大堡子的原因是其中居住着几十户人家,每家都有一个不大不小的院子,院内有树,有牲口圈,有各式各样的老房子。焦赞城,究竟是何起源,众说纷纭,可是谁也不敢说自己的说法完全正确。
说不清,我们就不说了,还是叫它大堡子吧。大堡已经是这里定了型的地名,这座村子的村名就叫大堡村。
大堡子,离固原城原本不过十里。现在,固原城向西南扩张,大堡村已经与城市接壤。据说固原市下一个五年计划中要在这附近建几万套居民住宅,那时,我不知道它还存不存在。
大堡子旁,有一条柏油马路,通向了远远的山里。岔开柏油路通往大堡村的路,只是一条狭窄的小道。狭窄的小道也没正对着大堡村,而是弯弯曲曲的,仿佛大树主干旁生出的一股斜杈,遇到林艺师修枝正叶的剪刀,“咔嚓”一声就给剪没了。
我去大堡子的次数太多了。小时候拎着弹弓打麻雀,隔三岔五去一趟。大堡子里面不但有桐树、杨树和柳树,堡墙上也长着不少榆钱树。麻雀从粮食地里飞起来,落到高压线上。稍有惊动,就会钻进榆钱里,或飞到堡内的大树上。为此,我后来写过一句诗,自己觉得美得很:树的存在在于包容/不仅包容鸟窝,包容风/还想包容几根鸟毛,包容风带走的鸟鸣。
记得原来有一次我看见一只麻雀在柳树上嗲声嗲气地叫唤,便拉开了弹弓。这时,我身后传来了一声咳嗽。一位老人走过来,啥话不说,硬生生地盯着我的弹弓,一直盯到我手里的弹弓皮筋松弛下来。他仿佛想告诉我,这麻雀是他饲养的。但当时只见他嘴皮翕动,没见他出声。
上中学时,我们班里有一位同学的家就在大堡里。同窗两年,他沉默寡言,很少与同学往来。课外活动或班里做什么游戏,他也不参与,只一个人悄无声息地在一边旁观。老师提问,他从不举手。老师点名让他回答问题,他要么摇头不语,要么小声小气地说他不会。
步入社会之后,他来找过我一次。大冬天,我知道他无事不登三宝殿。我给他点了烟、沏了茶,请他坐到火炉边取暖,并找借口和他聊天探问他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事。他只是一个劲地搓手抠指甲,什么也不说。直到最后站起来跺跺脚准备走了,才冒出一句:听说老班长喝醉酒倒在雪地里冻死了,我今天坐在家里没事,不由自主就想起了许多同学,就想来你这儿坐坐,解解闷儿。
他骑上自行车走了。他落寞的背影,叫人想起了他所居住的“大堡子”。
关于大堡子,我查阅了地方志和许多资料,均无任何可靠的说明。《固原地区志》寥寥一笔:“1938年回族农民起义,马英贵率领两个团的回族起义军在这里发起冲锋,击溃了前来堵截的政府壮丁队,击毙了五人,起义军乘胜追击包围了固原城。”
还有《宁夏五千年史话》叙述“夏宋定川之战”时,提到“葛怀敏……擅自领兵向养马城进军,也就是深入今固原城西郊的大堡村”。再就是《固原县志·文物志》中提到的宋代“南郊寇庄堡寨址(俗称焦赞城),位于南郊寇庄村”。
以此简略的文字记载来定论,焦赞城并非这座大堡子。寇庄是寇庄,大堡是大堡,都在固原城西南,二者之间还有五六里路。
那为什么大堡村也要争这个焦赞城的名字呢?唯一可以解释的就是大家都喜欢焦赞这个直爽重义的人。焦赞城就焦赞城吧。古代传下来的地名确有似是而非的谬误。再说,寇庄故城谁也没见过它的痕迹。
大概有意思的事情,本身就是一个谜吧。人在世上走来走去,走到什么境地才算明了?谁也不是神仙。就拿焦赞这样的人来说,掰着指头算,算来算去,从古到今也没多少。焦赞,无非只一人,且无法篡改无法改名换姓。活在世上最多的不过是些普通民众,普通民众除了最基本的生活需求,除了具有相似的爱憎、荣辱和苦乐外,其他过于复杂的理念、真理与他们都没多大关系。焦赞,不仅家喻户晓,我也特别喜欢这个人。
大堡子里面居住的基本上都是普通人,如果有权势,有资产,谁也不会把自己圈在又高又厚的土墙里。近在咫尺的固原城里,有的是高楼大厦和公寓别墅。
大堡子西南角内居住着一位六十开外的长者,见我老在他家对面的土台边常转悠,便心生疑窦。虽然嘴里没问,但他的眼神告诉我,他对我这样一个没事在别人门前瞎转悠的人是存有戒心的。当然,我也因此自问,闲来没事一直盯着这些即将消失的土城古堡干什么?在“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吗?我还没到那个境界,没那样的觉悟。我不过喜欢猎奇,习惯猜谜,或是按自己的爱好找点事干而已。
多次的试探之后,我发现这位健壮的长者虽然不言不语,却很和善。他不光精于农活,爱清洁;他有清扫院落、门口和往晾绳上晾衣服的习惯,还喜欢秦腔。因此,我才大着胆子走进了他家。
他家院内有十多棵高达十数米的椿树。这些树一棵棵挺直了身子,把头伸出高高的堡墙,侧耳听着堡墙外的动静。
走进他住的老屋,砖铺地,纸糊顶棚,白灰墙,大热炕,老式“北京组合家具”。桌上摆着一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时兴过的“燕舞牌”收录机。看到收录机上的铭牌,我记起了它当年轰动大江南北的广告语:“燕舞,燕舞,一路歌来一路情……”
尚能转动的收录机里,播放着秦腔戏。干炸的唱腔和收录机咯噔咯噔的转轴声叫人难受。抬眼一看,挂在墙上的老式相框里一张相片也没有,全是秦腔录音带的封皮。有《下河东》《游西湖》《张良卖布》《苏武牧羊》等,最顶头的是《三岔口》。他见我贴近身子去细看那些封皮,便扭动收录机音量旋钮,使喇叭里的锣鼓家什顿然嘹亮起来。随即,他摆开架势,做了一个戏剧动作,吹胡子瞪眼睛地白了一句:“咳,这也罢了。解差,将你二太爷这刑法去掉!”
这一声“咳”,吓了我一跳,后面的说辞又令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他见我不懂,便拉我坐下,关掉收录机对我讲起来。原来他刚才说的是《三岔口》里,焦赞要解差为他打开刑具的道白。听他讲秦腔何等耐人寻味,听他讲焦赞令人何等敬佩。我一听就听了大约一个小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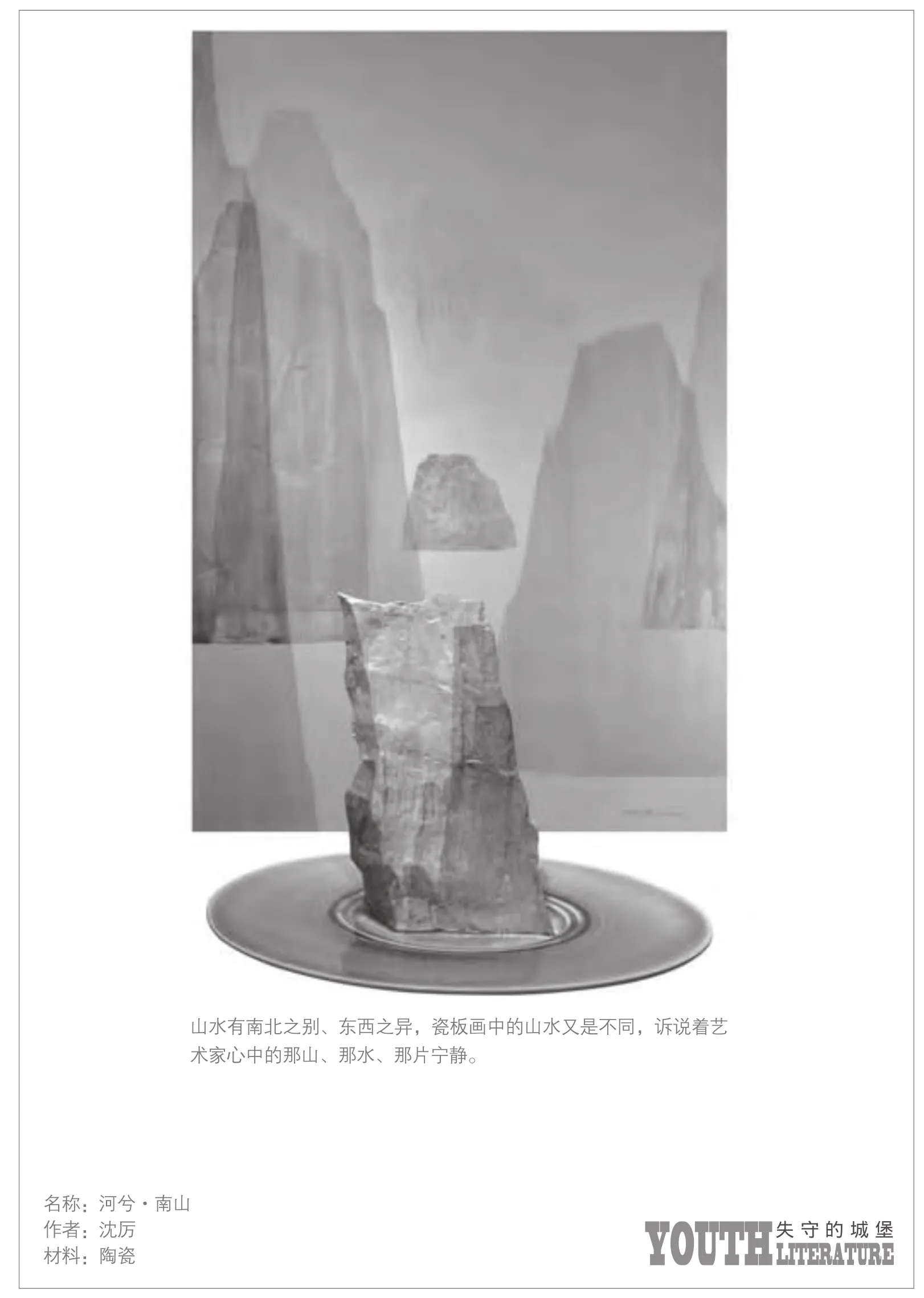
春节,固原下了一场喜人的春雪。我在家里待不住,就带上相机又去了大堡子。我想给这座老建筑再拍几张照片。走近大堡子,踩着还没有脚印的白雪,我边走边照,不觉间就走到了古城的西南角。这里已经扫出了一条雪路。响亮的秦腔戏已经越墙钻到了我的耳朵里。我想听清这到底是在播放录音还是长者自己在唱,可听了半天也没有听清楚。
我看着他家闭着的两扇黑门,门扇上贴着两张红彤彤的门神:一张是挥着铁锏的孟良,一张是握着月牙斧的焦赞。
我忽然记起这座大堡子被称为焦赞城的事来。我用敬慕的目光看着那一对门神,那虽然只是两张纸,但在我眼里,它们却是正义的化身。
姬家堡滚出一只空背篓
宁夏固原与甘肃环县交界处有一条沟,叫芦草沟,也叫芦草湾。沟也好,湾也好,都在山区公路的腰部。公路绕到沟底,再绕上梁顶。如果这时候从车上下来立于梁顶,你就会看得更远,能看到起伏的山峦,看到夹在大山中的平川,或许还能同时看到白晃晃的月亮和黄澄澄的落日。
如果一条路通向沟去,车辆就会一猛子下去一猛子爬上来,再一猛子下去。这时,人一般不会回头看,假若回头,会发现路只是在这里闪了一下腰,或挺了一次胸。如果沟在道路侧面不断出现,路就会在湾里湾外不断缠绕。车如果在道路上一上一下一左一右接二连三颠簸和躲闪,就说明这是条老路或无人问津的路。路上的波折多弯子多,路边的悬崖多,人们往往会越走越清醒,就会记住沟和湾,也会边走边遗忘。
芦草湾在彭阳县罗洼乡的地界上,203省道侧着身子盘绕到这里,撇下一块里程牌,撇下一组倒退的数字:432。
芦草湾,芦草挺拔,株株相伴,一株一株又不依恋,像众草之王。秋风将来,芦草会抖掉头顶的缨絮,亮出银针般的穗芒;秋风吹过,芦草随风摇曳,身子要么猛然折断,要么与根相连,抓住泥土不放;秋风一去,芦草也会撇下一把种子,无论脚下的土地多么贫瘠,无论隆冬多么凛冽,死亡多么恐惧,来年都会生出新的芦芽。芦草是一种杂草吗?是。芦草,是一种生命。
芦草湾住着一些姓扈的人家和一些姓马的人家。这些人家我都不认识,但都很顽强,他们不出芦草湾也能活过这辈子。他们有西北人典型的抗旱能力和抗寒能力,有与穷乡僻壤做殊死斗争的精神。
因为,我看到过他们撇在崖畔上的窑洞,看到他们新建的砖瓦房,看到一片片玉米田,一垛垛粮草,还看到了他们扛着锄头或拉着架子车要走的一条条小路。芦草湾有芦草湾的风格,这里除了芦草多,风多,黄土多,一户离一户人家的距离也远。
当然,再远我也得找几个人聊聊,因为他们其中总有一些人与我有缘见面。没有缘我也要找这个缘。虽说我找上门的人与我不相识,但不意味我们就没有共同语言。撇下他们的生活不说,单就当年当地大财东姬涚诚弃在芦草湾东崾岘洼上和砖院壕边的两座塌堡子,我们就有说不尽的话题。
这样的交谈,双方都习惯站着。他们讲起姬家堡子,就像讲起自家的锄头和铁锨。他们说姬涚诚一家当年是芦草湾唯一的大地主,满山满洼的农田,满沟满坡的牛羊,堡子里满窑满笸箩的粮食,堡外满园子的杏树,都是他们家的。一人深割到能扎扫帚的芦草就不用说了,就连忽然从沟坎背后钻出来的兔子、狐狸,猛然飞起来锦鸡、呱啦鸡都像是他们家的,都能吓人一跳。
姬涚诚一家两座堡子,一座在东崾岘,一座在砖院壕。东崾岘就是东崾岘,在大路边。砖院壕原来却不叫砖院壕,叫二爷壕,只因为后来在二爷壕建了一座砖瓦窑,在砖瓦窑前边圈了一所院子,人们才改口叫起了砖院壕。
再说,二爷壕不好听。壕与嚎分不清,猛一听以为是二爷在嚎。再说,二爷壕会让人联想起姬家二爷姬涚诚的弟弟呼天抢地的事来。
姬家二爷不知是招惹了大名鼎鼎的王慎子,还是因为富得流油刺激了土匪。一夜之间,王慎子带着他的还乡团(有人说是保安团)“扫”了姬家二爷的窑。
扫窑,不光是“扫”,还得加上用铲锅子(锅铲)铲。王慎子一伙连扫带铲打扫的干净程度,不次于秋风吹倒的芦草。他们“扫”过窑之后,窑里一粒粮食也没落下,圈里一头牲口以及一根拉牲口的缰绳都没留下。二老爷哭了,心里骂着,嘴上却向王慎子央求着,眼睛犹如他最爱吃的那把酸菜,不用攥,酸水就扑啦啦往下淌。
“扫”了窑,就等于和穷人一样了,堡院里只剩下一口碍眼挡路的空背篓。姬家二老爷哭了,大老爷却笑了。二老爷爱财,大老爷却爱笑。姬家大老爷边笑边把自己的种子、牲口分了一半给弟弟,边告诫他以后再不要张狂。他说:“人狂惹是非,狗狂挨砖头,猪胖挨刀子。”
后来王慎子让红军(芦草湾的人把八路军、解放军、游击队统称红军)给扭了,关在甘肃的夏家窑。这个作恶多端的土匪头子自感罪孽深重,不用别人整治,就在夏家窑自杀了。和王慎子一起混的另一个土匪头子吕文狂妄地踏了乡政府的地面,打了乡干部的脸,被逮住押到毛井子枪崩了,芦草湾才算是安宁了。
姬家大老爷不光待人和善,识文断字,还能识时务。他曾自诩:“识时务者为俊杰嘛。”除此之外,他不仅善待上门乞讨的穷人,也热情接待过穷人喜欢的军队。一天,他从王洼赶集回来,突然动员二老爷把所有的田地、粮食、牲畜、水窖和家当分给长工短工和雇工,带着妻儿老小,卷起铺盖卷回了镇原七里河老家。在那里,他们购置了几亩薄田,过起了实打实的清贫日子。
姬家的两座堡子就这样撇下了,撇(闲置、丢弃)在了东崾岘的半坡和砖院壕对面的洼上。这一撇等于把堡子撇给了放羊娃娃。放羊娃娃遇到大雨大风无处躲藏,就钻了进去。
姬家人没有忘了每年回一趟芦草湾。他们清明要到后洼祖坟里烧一趟纸,再到前川里转一圈和老乡说几句闲话。至于原来撇下的两座堡子,姬家的后人们记不记得,搁没搁在心上,看不看一眼,和我交谈的人说,没谁见过没谁说过。
离开芦草湾,我沿着山路向西行驶。三十公里之后,不知绕了多少弯子,翻了多少沟,也不知把多少座山峁撇到了身后,但撇不下大脑中那个眼睛淌酸水的二爷和塌堡子前的几株直挺挺的芦草。
芦草的茎秆很细,很直。当时我蹲着,我当时如果要稍稍弯一弯,头再低一点,那几株芦草就挑起了月牙。但芦草的腰不能再弯,再弯就会出问题。
现在,我记忆中的芦草湾已经不是当初离开时的印象,不是一道湾、一条沟、一座堡子、几株芦草的事,而是与我谈笑风生的好多芦草一样的人,他们把锄头使唤成了月亮,把筛子笸箩锅盖车轱辘当成了太阳,他们还在那里安安稳稳地过着似乎与世隔绝却又无法与世隔绝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