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的人类和人性本质的显露
□马明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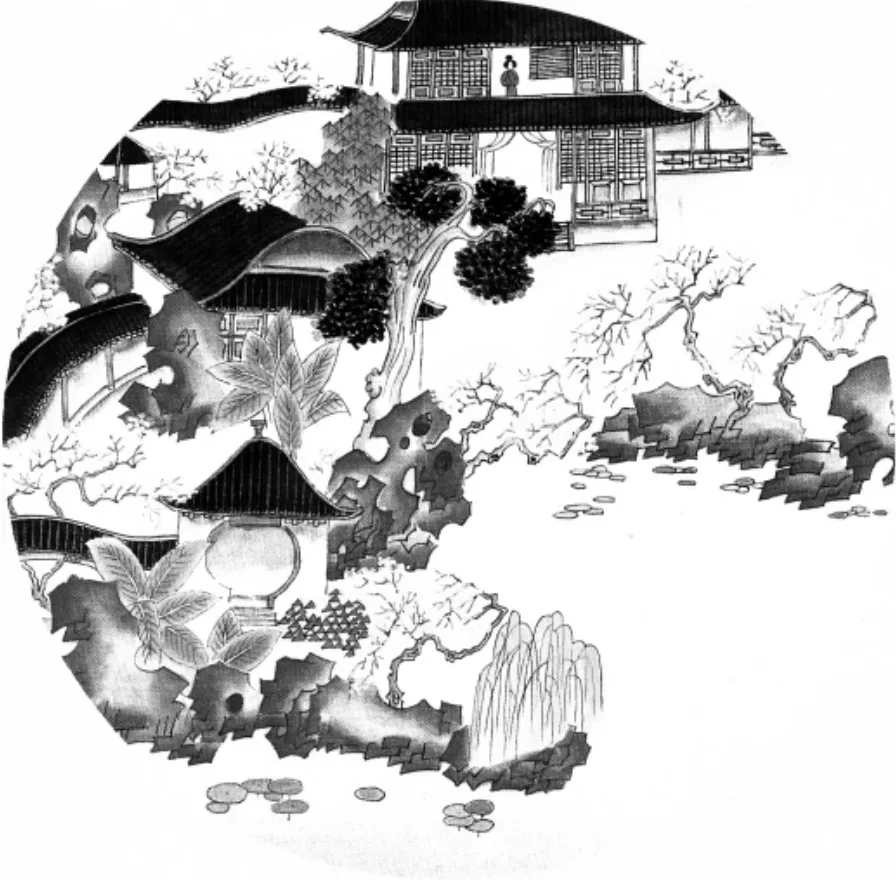
一
有足够的理由表明:玉水将视野从社会拓向历史、再拓向自然的进程中,不仅有过深挚的对于大地和人民的感恩情怀,而且逐渐产生了如此凄艳美浓的宇宙畅想,这种畅想似乎也不可以简单认定为是一种童心诗意的恢复,更主要的倒可能是一种失落,一种对于古老世界进入昏暮症候的悲悼。换言之,《九龙山,龙吟河》里对于二狗媳妇的跪拜,《白狐》里对于冬梅姑娘的悲默,无不隐喻着一个事实:那种苦难中相依相傍、生死间相知相应、超越荣辱、立定沉浮的“情”正在消弥,否则,作者为什么呼吁、悲悼并且如此的铭心刻骨呢?
《九龙山,龙吟河》是一部凝重的反思历史之作,以二狗媳妇为代表的乡村人民在民族和国家遭遇大难的关头,只是出于通常情理的善恶之辨、伦理亲情,以死保护了魏将军和他的战友们。那时,魏将军与二狗媳妇是生死相依、血肉相连的亲人,并不存在为执政党建构起来的拯救和感恩关系,亦即二狗媳妇并不是为了拯救谁,只是为了图生存,与魏将军往来奔波;魏将军也只是因为患难与共而产生了朴素的感恩心理,本质上讲,两者都是一种美好的人类和人性本质的显露,此种本质是超越任何社会历史阐释而自在清明的。可是,在“文革”的特殊年月,却遭到混乱的社会阐释,这种阐释近乎污蔑。魏将军或执政党的悲哀并不在于忘失了那份本该记牢的感恩之情,事实上他们没有也不曾忘怀,悲剧在于执政党的逻辑理性或感恩之心并不能抵御或阻绝这种混乱阐释,亦即“文革”的暴力和劣行并不能从感恩报德这一传统美德的丧失来阐释,也不是说革命的本质就是六亲不认、颠倒是非。而是一种革命性的执着一旦走到尽头,走向绝对,不但失去了准确的对象和应有的分寸,而且丧失了主体,变成自己革自己的命。革命在这里成为一种抽象自然力,一种孽缘。一旦革命对象变成自己,革命的主体就成为自己的敌人,亦即自己成为自己的敌人。冲击二狗媳妇和魏将军的并不是日本帝国主义或国民党反动派,而是劳动人民自己。小说虽然竭力渲染了愣秋的智力、品德以及“左派”疯狂症候等负面因素,但是愣秋绝对属于劳动人民。革命变成革自己人的命,这是执政党一直以来没有悟出的一个逻辑悖论。玉水的小说反思到这个程度,不可谓不深刻。但问题的更深刻处在于:一旦悟到这个悖论,革命就成为反思对象,革命的逻辑——历史逻辑和人性逻辑,就会遭到颠覆,这是另一个话题,不谈。
《白狐》正是这样一种规避革命话语前提下的诗性畅想。封建伦理的代表赵四爷并没有像过去那些模式化的阐释一样被写成十恶不赦的坏人或敌人,而是一个十足的小地主,一个顾念着自己的外甥女的命运,又逞示着一己权力意志的封建家长。亦即阶级性小于他的伦理亲情感,这是一个合理也合适的阐释。玉水没有囿于反封建、争自由的主题,而是在描述了夏葵放失心爱的人、回归家庭伦理的悲剧之后,尤其描述了他与冬梅的令人凄楚的阴阳之隔、生死之恋。这里有漫天皆白的雪原和山坳,有凄冷干冽的风寒和雪天,有昏鸦暮烟,有贫寒人家,尤其是还有一只温婉可怜的小白狐——它自始至终参与了这双生死恋人的宇宙悲情。由于白狐的存在,夏葵和冬梅的爱情不再是社会意义上的封建与反封建之争,不再是人世间一份知交背离、相宜不契、爱而不能的情感悲剧,而是一个用心灵和爱情铺就的宇宙之桥:不能行车走马,却能济渡灵魂。通过这座桥,夏葵与冬梅双双走入灵性感知的世界,走入爱意相融的真境,走入人与自然、人与世界、人与自己心心相印、情意相商、美美相互的圆融之境。我在读《白狐》的时候,常常幻出《红楼梦》白雪红梅的影子,幻出十八世纪初叶出现在贾府大观园的一幅贵族少女争奇夺艳图:宝琴和宝玉,以及众儿女,在沉郁凄冷的天空下,美艳洁白的雪地上,隔了梅花树,有非常非常遥远的笑语声传来……然而是那么低弱地消逝在世纪的阴冷的风气里,很久很久没有回荡起来了。可是,我们在玉水的小说中听到了回声,他激起我们非常深远而美丽的宇宙之思和诗意之想。这种美丽之思的更深层的意蕴在于忏悔:对于尘世杀戮和人间情爱的忏悔。打死金钱豹和生下胖小子是同一天,这在夏葵的人生中是双喜临门的大喜事、大美事,尤其是他获得一张豹皮可以给他的冬梅的坟头上添加一床皮褥,他的爱就这样与杀、与生同一了!这是一个宇宙奇迹吗?美中不足的是,他顾及不到那只小白狐。生儿子、杀豹子、祭冬梅,这一切成为俗世间最值得庆贺的庆典,可是小白狐的出现和消失,将这一切都冲淡了,他的生命也走到终极。虽然作者努力从因果报应的传统文化旨趣中灌注了生态科学的理性因素,但是小说的真正动人处还在前者,在于超越唯物主义和科学主义的诗性畅想和神性强调。比起这个世界的权力迷信和科学崇拜来,对于鬼神和形而上世界的追寻,已经不是迷信,而是一种人之为人的存在理性了!
二
《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原载 《草原》2008年12期)既是开篇之作,也是扛鼎之作。在反思执政党的政治结构方面,作者所达到的文化深度和所持有的现代意识,是令人赞叹不已的。
首先,小说勾勒了一幅典型的中国式的政治结构图式。以何天晴为权力端点,直线而下是县委书记郑方羽,第三个层级是县委办公室赵主任,由此散开一个扇面:谢老根、魏大头、侯局长、姜四眼儿、郭大炮……这像是一个一个的神经乳头,何天晴正是通过这些“乳头”紧紧地抓牢着他们身后成千上万的人民,顺利实施着他的政治意志和权力分配。当然,对于这个结构的分析或阐释可能是社会学家的事情,但是我们的确看到一个自上而下,渐渐落实的政治过程:何天晴的抽象的政治意脉经过郑方羽的相对单一的政治代言,再经过赵主任的苦心孤诣的政策落实从而具体化,变成人人可以理解的、但是无权擅自阐释或进行权威鉴定的政治实践。这是一个一贯而下的专制和强制过程,也是一个心不由己的分散和模糊的过程。可以想见,任何政治动意一旦进入这一过程,不是令行禁止,就是渐渐消散,关键在于权力端点对于下位的掌控能力和施力效应。这就像牛魔王手里的那把铁扇子,既可以煽风点火,亦可以逍遥自任,要玩得得心应手。
从这样一个政治结构的整体看来,县委书记郑方羽其实是个智力和能力都不超异的庸常之辈:捧枚大针认铁棒。何天晴根本没有把一票之失看作一回事,激动或见怪的是他自己。专制体制下的政治激情由此可见一斑:忠诚后面潜隐着的是恐惧和把持。在这一点上,已经从封建时代的宇宙道德之思和天地人生之念颓堕下来,他们并不怀有更为超越的政治诗情,只是为了把持住已有的权力和利益,这是一眼就能够看穿的事实。郑方羽的所谓政绩其实是一种专制和暴力的合力,就其个人品质和智慧看,几乎一无可言。即使是这样,郑方羽还是一个可圈可点的人物,他至少不私自瞒藏什么,也不至于拿捏虚拟什么。这就够了。一个不依恃权力而胆大妄为的忠实的政治家,就是人民的福音。所以郑方羽的急躁里其实也包含了对于一方人民的利害得失的焦虑和关怀,这又使得这个政治极端分子统治下的晴川县隐喻了一个时代的政治幻想:对于党的忠诚,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官员能够实现对于人民的关怀的政治保障和人格保障!
第二,小说浮世绘式地描绘了以赵主任为代表的一群机关干部的人生百态。作者的现实主义手法娴熟自由,几乎在一篇诉述过后,人物就跃然纸上了。玉水的高明处在于:小说并没有停滞于人物的性格化表述,比如赵主任的圆滑能忍,谢老根的正直诚实,魏大头的精明强干,侯局长的萎琐秀慧,姜四眼儿的清风明月,郭大炮的粗蛮刚直……而是以此为基准,进一步呈现了他们在强权和暴力面前各自的焦躁心态和应急方式,那样一种文化人格状况。我们多么遗憾:清风明月自诩的姜局长,已经意识到一票之失并不足以说明什么,可是,他并没有太多的政治关切,尤其没有去拷问围绕一票之失所进行的政治追逼究竟意味着什么。最令人叹惋的是郭大炮,我们对他的预期是一个能够放下一切政治得失之念,坚持人格尊严的带有豪侠心性的人物。事实证明,他不过是一个玩具式的小人物:夸张足够,奔突也足够,闹到最后不过是冲到何书记面前忏悔了一番,表现了十足的小精明和小得失。一种政治品格和人性尊严,一种政治决心和人格特色,就那么糊里糊涂地幻化为一种小孩子顽皮式的政治淘气。换言之,在政治强权和专制意志下,每个官吏的政治操守中并不含有深刻的人民性的思考和个体性考究,只是一味服从。在专制链条上,他们都是一个个的转换器,把权力顶点的政治意志转换为千千万万人的实践,个人的和智性的政治一点点也不存在。这是长期以来张扬天人合一的中国文化对于专制体制的人格方式,也是文化状态,其中以个体的意志消弥乃至消失为前提,也是为特色。
第三,玉水的小说以按键的方式给古老世界的昏暮症候点了穴,赵海忠称为“按键效应”。我们不禁想问:说到底,不就是郭大炮昏昧之际按错了投票键而已,怎么就激起郑书记那么大的恐惧以至形成几乎席卷了晴川县的巨大政治恐慌呢?可以说,郭大炮的昏昧(作为本能或特色的生命昏睡状态)本身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这样的人怎么能够进入权力中心,并且自诩为一种政治风范呢?事实上,郭大炮是肉体昏眠,大多数官吏是政治昏昧,这倒是与古往今来的专制政治下人性和理性的昏愚麻木状态非常吻合,某种意义上说,玉水的小说抓住了这一要穴,他是有象征意义的。其次,按错了键,只须声明登记,重新认证,一共十来个人,此种政治宣布是完全可以顺利操作的。可是郭大炮不敢,一直遮掩到忍无可忍。原因不在于郭大炮的胆小如鼠,而在于,这个键按到了昏暮世界的要穴上。投票机作为一物,是现代性或民主化的象征,它本身就是一个符号。于专制体制铁一般的内幕里突然出现这么一个投票机,其象征意义远远超过其现实主义的细节的异域。这是一个“错接”,古老世界的昏暮症候里包藏了一个现代性或民主化的机钮。如果现代性或民主化不是以错谬的方式从内部发生,就会以模式化或性格化的政治品质的颓堕和没落将政治主体实现为专制的死灭。玉水说,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可是我们能说,社会还是那个社会吗?晴川还是那个晴川吗?
《月亮还是那个月亮》的现代性远远超过其现实主义品格,进入某种荒诞,这是玉水的超迈之处,也是中国政治的无奈之时。我们欣赏玉水推出每个人物时的那种概述式手法:将人物停滞在一个阐释立场上,从人物性格化的框架里灌注生命真实的内涵,灌注人性事实的东西,这使得他笔下的人物不仅真实,并且亲切,而且携带了玉水本人的评价和观点。就叙述而言,玉水的政治身份是小说政策分寸的一个客观限定,我们正是由此获得这样的信息:中国政治改革会在这一代政治家手中成功。玉水对于执政党政体的反思一点也不亚于那些文学家或思想家的深度,而且极有勇气和魄力。这既是他的政治的成熟,也是文学的成熟,我们为之感到欣慰。
〔责任编辑 阿 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