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龟裂石说起
从世界地图上看中国,状似一只雄鸡,辽东半岛似尖尖的喙。此刻,喙正闲着,不左观右望,亦不低头觅食,好像在静等破晓而啼。其实,从亘古开始,辽东半岛更多的时光是混沌和荒凉。相对于漫长的地质演化史,辽东半岛不过是某一次地质演化之后的短暂定格,正巧被今人遇见。
我居住的城市大连,在辽东半岛南部,也就是雄鸡的喙尖。左边一个黄海,右边一个渤海,南边一个山东半岛,东边一个朝鲜半岛,大连与辽东半岛被夹在中间。与内陆城市相比,大连地理有一种难以复制的辨识度。自古以来,这里就是海上航线必经之处。自古以来,这里就是一个历史过道。而且,大连从古代到近代发生的一切故事,都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
正因为如此,我要占用一章的篇幅,说说辽东半岛的沧海桑田。也许离题太远,但对于文化稀薄历史并不雄厚的大连而言,这一章却不可或缺,也无法绕过。
许多年前,我曾走近过一块石头,这块石头已经在黄海岸边站立了6亿年,以地球史有46亿年计算,似乎不算什么,刚刚占了一个零头。但是,记得那天,不远处就是潮汐鼓噪,而它一直斜斜地静卧在那里,当我弄懂了该石头从何而来,姓甚名谁,它便突然激发了我对地壳变迁的兴趣,对乡土地理的好奇。
石的质地呈赭红色,表面布满了巴掌大小的淡绿色网格,看着就像上苍之手画出的谜语。石旁有个标牌,说它来自震旦纪,因状似龟甲,被称为“龟裂石”。它的样子,既让我感到陌生,也让我充满好奇。
于是,龟裂石成了一个标本,一块敲门砖。我就此知道,在鸿蒙未开时代,地球大部被海水覆盖,无数的微陆块,如幽灵一般,在无际的水面上碰来撞去,胡乱地拼接着,无主地漂移着。
直到35亿年前,“华北岛”如一颗上苍赐予的石质胎盘,成为中国这只方舟最原始的陆核。而25亿年前的一场“鞍山运动”,惊醒了蛰伏在水下的辽东古陆,使它从海底褶皱里轰然隆起。自20亿年前开始,则以“吕梁运动”为代表,地球时不时就会来一次或大或小的山颠海覆,而在无数的跌宕起伏中,辽东半岛始终是辽东古陆甩不掉的小尾巴。当地球幽幽转动到了10亿年前,又因为一次剧烈的地壳下陷,让辽东半岛有长达4亿年淹没在亲亲老家般的海水里。6亿年前,它才随着地壳缓慢抬升,光鲜如美女出浴,得见蓝天丽日。也是自那一刻起,大自然以时光为斧,镂刻出这块沉默如金的龟裂石。
然而,在这片海岸,龟裂石并不孤独。漫长的6亿年间,又发生过许多次地壳运动,许多次海陆交替。因为这里是震旦纪喀斯特地貌,因为坚固的岩体或被一次次地壳波动碾压断裂,或被亿万年的大风和海浪冲击变形,最后化成了各种生动怪异的鬼斧天工:恐龙探海、贝多芬头像、鳌滩、玫瑰园、七彩虹霓......
曾有一位艺术家在海边驻足说,这是神力雕塑的公园。我却有点心疼,这些崎形怪状的岩体,不过是某一场地质运动的遇难者,一些被地壳遗弃的无用的边角余料。只是,当龟裂石与伙伴们抱团取暖似的拥挤在这片海岸上,竟意外获得了另一种永生。
在我眼中,龟裂石是地球史上的但丁。
震旦纪是隐生宙最后一个纪,寒武纪是显生宙第一个纪,龟裂石恰好站在两个宙之间。石面上那些神秘如天书的网格,我给看成了隐生宙的休止符,显生宙的预言。如果隐生宙是柳暗,显生宙就是花明。
事实证明,显与生,皆拜太阳所赐。5.4亿年前,地球一不小心被这位天外来客捕获,从此以后便郞才女貌,天作之合,不离不弃,你侬我侬。显生宙有三个代:古生、中生、新生。故曰,生命之宙。就是说,显,即是生。
不过,太阳虽然把地球照亮了,催成了生物大爆发,却也随之带来了生物大灭绝。而且,天地失色、万劫不复的大灭绝,竟连着发生了五次。好在,龟裂石是石头,不是花草,它一直乖得像块狗皮膏药,紧紧黏在辽东半岛身上,从未失联。所以,它不但看见过侏罗纪恐龙怎样成为巨无霸,也目睹了它怎样给那颗撞入墨西哥湾的小行星作了殉葬。
小小一块龟裂石,竟以本自具足的神性,活得比恐龙还长寿。我想,它之所以穿越6亿年时空,以6亿年笃定,深情地等候在这里,就因为它相信总有一天,会与后天来到的人类相见。
却没想到,人类来得那么晚。
二、胶辽古陆的沉浮
在大连的地质履历表上,可与龟裂石等量齐观的风景,还有胶辽古陆。有人说,它形成于6亿年前的震旦纪,也有人说,它形成于7万年前的大理冰期。或许都有道理,胶东半岛属于华北古陆,辽东半岛属于辽东古陆,胶东与辽东,打断了骨头连着筋,比邻而居的两个半岛,不知有多少次拉勾上吊,直到贡献出一个这么婉约,又这么雄浑的地理名词:胶辽古陆。
庄子《逍遥游》云:“北冥有鱼,其名为鲲。”这是个由鱼化鸟的上古神话,一条三千里长的大鱼,因为向往自由,突然在海里待不住了,变成了一只扶摇九万里的大鹏。庄子说了,他引述的神话出处有二,一个在《商汤问棘》,一个在《齐谐》。庄子之所以搬过来用,就为了抒己之志,为了无束无止的自由。
神话里的北冥,其实就是渤海,赶上冰期,缩成了一个湖。正因为如此,《逍遥游》不只是一篇道家经典,还是一部胶辽古陆秘史。
当然,不论是6亿年前,还是7万年前,胶辽古陆只要出现,一定是冰期来了。几十亿年地球史,不知发生过多少次大冰期,每一次生物大灭绝,都会降临一次大冰期,怎么知道胶辽古陆不是在震旦纪那一次大冰期横空出世的呢?
地球上最后一次大冰期,发生在新生代。
第三纪最大的事件是造山运动。喜马拉雅原本是海洋,竟一点点长成了地球第三极,华北古陆原本是平川,东缘这一角竟慢慢凹出个渤海。
第四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大冰期。虽然长达260万年,却并非铁板一块,分四次冰期,四次间冰期。基本画风是这样的:冰期一到,胶辽古陆就要升起,渤海就退成了湖,黄海则退成了大平原;间冰期一来,胶辽古陆就要下沉,渤海湖和黄海大平原复又汪洋一片。海陆变身,冷暖交替,演得如川剧里的变脸。
四次冰期最后一次,叫大理冰期,时间在11万年至1万年前,不但气候一直寒冷,还曾有过两次极寒。
第一次在7万年前。渤海水面下降了50多米,变成了一个内湖,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全都露出海面,白茫茫一片胶辽古陆真干净。
第二次在2.2万年至1.5万年前,寒值远远超过了前一次。冰川厚如危崖,海面直降140多米,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无缝对接,朝鲜海峡、对马海峡、津轻海峡、宗谷海峡、鞑靼海峡、白令海峡、楚克奇半岛与阿拉斯加十指相扣。

这也就是为什么说,中国和日本一衣带水,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华北古人类是印第安人的祖先。
第四纪是冰河纪,也是人类纪。有一个说法让人类很没面子,就是把46亿年地球史换算成一天24小时,人类在最后3分钟才登场。其实,人类要是知道地球到处冰天雪地,寒风凛冽,也许还觉得来早了呢。
胶辽古陆,仿佛是天造地设,给迟到的古人类铺就了一条迁徙通道。高丘深谷,悉如女人胴体,整个东北亚都赤裸在地平线上。于是一支支古人类便被动物吸引着,诱惑着,义无反顾地离开华北,向东北亚大陆走去,向北美大陆走去。
彼时,在古陆上如如不动的龟裂石,应该目睹了这样的场面:那些不倦迁徒着的古人类,曾经路过它身边,或靠着它避风歇息,或停下来撕吃捕获的动物。冰天雪地里,龟裂石给过他们一只手的温暖,因而让他们走得更远。
也有留下不走的。他们也是古人类,或者说,他们是大连最早的先民。
据《大连通史》载,在辽东半岛现身的古人类,大致有两个来源,一是从辽河流域南下的金牛山人、庙后山人,二是从中原北上的山东半岛人。其实,不如说他们都是在古人类大迁徙时代留下不走的人。
迄今为止,大连境内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古人类遗址有两个,一个在骆驼山,一个在古龙山。有意思的是,这两座山都在我老家附近,这里过去叫复州,现在叫瓦房店。
在骆驼山洞穴内,出土了数万件动物化石,其中剑齿虎和纳玛象,在东北地区是首次发现。专家说,骆驼山动物群与北京周口店动物群是同族,跟庙后山动物群反而不是近支。
在那堆化石层里,发现了疑似人工打磨的石制品,并且有疑似古人类烧过的咖啡色火塘。这个发现说明,骆驼山不是单纯的古生物遗址,而是有古人类活动的文化遗址,时间在距今50万年至20万年。
就是说,骆驼山人的资历,把金牛山人和庙后山人甩在了后面。当专家们把大连骆驼山与营口金牛山、本溪庙后山、喀左鸽子洞勾连起来,便画出了一幅完整的中国东北远古人类活动图谱,看来看去,居然都与周口店山顶洞人有血缘关系。这说明华北古人类有的压根没走,有的走在半道不想走了,有的一鼓作气走到底。留在东北的古人类,就是半道停下那一拨。
骆驼山在复州古城西南,山势巍峨,其形如驼,故名。复州诗人张俸曾写过一首《登骆驼山》:
万丈云霄外,登临意豁然。
耸肩思荷日,引手欲攀天。
沧海千寻浪,荒村数点烟。
东南遥望处,城郭小如拳。
但是,这么美的一座山,最终也没留住骆驼山人的脚步。也许因为,他们在食物链上,靠追猎可食动物裹腹,动物离开了,他们就得离开,然后就忘了回来。
古龙山距骆驼山只有几十公里,虽然也是旧石器时代遗址,时间却近多了,距今只有4万年至1.7万年。
与骆驼山洞一样,古龙山洞也出土了数万件动物化石。当它们被拉到大连自然博物馆化石库,分门别类地摆放在开放式储物架上,从美国和德国来的专家吃惊地问,这难道是从同一个洞穴里出土的吗?回答是肯定的,它们都来自古龙山洞。
动物最多的是马,而且是野马。有200匹个体马骨,6000颗马牙,古龙山简直成了它们压倒性主场。而且,经过测定,这些马是现在已经灭绝的独特物种,与欧洲野马是近亲,反而和东北内陆的中国野马亲缘关系较远,专家便给了一个命名:大连马。
事情并没有完。大连马的马骨和马牙证明,它们正值青壮之年,死亡的原因不是自然淘汰,而是被人类围猎捕杀,然后将它们全部拖进山洞并吃掉。专家由此推断,古龙山人喜食马肉,他们是一个庞大的狩猎集团,于是又给他们一个命名:猎马人。
我曾专程去了一次大连自然博物馆,并在库房里看过动物骨化石。馆里专家告诉我,他们当年发掘的只是一个岔洞,主洞已经被采石者炸没了。从埋藏学的角度分析,这些动物骨头是人类啃吃过的,唯一的解释,就是他们住在主洞,把岔洞当作垃圾场。
古龙山猎马人的踪迹,消失于最后一次冰期结束之前。他们可真是果决,说走就走了。那一次次快乐无比的激情猎杀,一场场大快朵颐的饕餮盛宴,都被他们抛在脑后,只扔下一堆吃剩的动物骨头,几件剁肉用的打制石器,留给后面的人考古。
考古者当然知道,历史更多的是混沌。面对那么多的说不清,那么多的暗角,只有尽可能的去寻找线索,然后在线索里打捞细节。
骆驼山人和古龙山猎马人,就是这样被打捞出来的。如果没有他们,大连历史是不完整的。因为有他们,这一段看似有太多空白的历史,便具有了质感和别样的生动。
三、稻作之路
近代地理学奠基人A.von洪堡认为,人是地球这个自然统一体的一部分。他的“人地关系”学说,随后便成为一个著名的科学论题。中国人也懂人地关系,在中国人嘴里,这么深奥的哲学问题,只用七个字就讲明白了:一方水土一方人。
两种观点没有高低,只是参照系不同。洪堡讲的是地球和人,看得高远,中国人讲的是山水和人,更接地气。
人与地,的确有一种天然的依存关系,地理是物体,人是物种。换句话说,地理是“皮”,“人”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是《左传》里面说的。
大连地理之“皮”,就是辽东半岛,但与胶辽古陆相比,辽东半岛实在是太年轻了。《大连广鹿岛区域老古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 2018年)载:
地球上最后一次冰期结束后,气候又逐渐变暖,海平面上升,最终形成了现在的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这样的地理格局。
《大连通史·古代卷》(人民出版社2007年)载:
最后一次海进发生在距今9000年。在距今6000至5000年前后,黄渤海海峡及渤海地貌形态基本形成,辽东半岛海侵达到高峰。
就是说,它成为半岛是因为海侵停止在5000年前,然后形成了它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这样一个格局。同样,山东半岛也是如此,于是才有了两个半岛如一道海上城墙,骑在黄海和渤海之间,让渤海成了内陆海,让黄海成了边缘海。
写到这里,我想用全能视角描述一下辽东半岛。它其实是一脉欲断又续的丘陵,近看是千山余绪,远看是长白山末梢,如一柄锋利的犁铧,耕入浩瀚的黄海与渤海,并给它们划出一条清晰的分界。
正因为辽东半岛一脉青峰如脊,三面碧海环绕,形成了它独特的天然肌理,那就是无所不在的曲线。
竖着看它,山是波纹样的,北境的老帽山,中部的大黑山,南端的老铁山,一波三折,凸凹有致,给半岛带起了性感的节奏。
横着看它,岸是游蛇样的,半岛两翼的黄海岸和渤海岸,像从老铁山手里放出去的两根风筝,一根飞落到辽河口,一根悠扬到鸭绿江口。
这两根风筝线,长达2000多公里,线上还冰糖葫芦般串着无数个海湾,一个海湾,就是一个渔歌唱晚的码头。最有名的一个,叫大连湾。后来,大连就成了半岛城市的名字。
距半岛海岸不远处,还有数百座岛屿,它们就像一不小心从辽东半岛项下扯掉的祖母绿珠子,星散在黄海和渤海的深蓝里。这些大大小小的岛屿,还有另一个称呼,离岛。
一个离字,道尽悲欢。岁月静好时,却发现是天赐之美。
距陆地最近的一个离岛,叫广鹿岛,属于北黄海长山群岛一员。从上个世纪初开始,中外专家就在广鹿岛作了一个世纪的考古。《大连广鹿岛区域老古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 2018年)载:
距今5.7亿年前,辽南大陆是原始形态的古老地块,后来地球发生造山运动,地壳出现一系列西东北南交错的断裂,逐渐分离为现在的长山群岛诸岛地貌。辽东半岛南部,地质学上称为“辽南平原中丘”,当时的广鹿岛与辽南大陆相连为一片丘陵山地。
这个时间,几乎与龟裂石同龄,这段考证,也让我窥见了它当年所处的天时地利。却原来,辽南曾是一片平原中丘,因发生断裂和分离,又变成一片丘陵山地。正因为如此,海侵之后,那些丘陵变成了无法淹没的岛。
广鹿岛也是,原本与陆地相连,在成为离岛之前,就已经有人定居于此,而且在此升起了大连历史上第一缕炊烟。如果广鹿岛是“皮”,这一缕炊烟就是“毛”。皮与毛一起,构成大连新石器时代最早的人文故事。
记得,有位专家朋友告诉我:一万年前是旧石器时代,出土文物叫化石,一万年后是新石器时代,出土文物叫河滩淤积。这话如醍醐灌顶,让我一下子分清了历史经纬。
叫河滩淤积,是因为气候正在变暖,山野吐出绿色,人类已经走出山洞,可以选择一个风和日丽的地方定居下来。广鹿岛最典型的河滩淤积在小珠山,它是一个有7000年历史的贝丘遗址。那堆洁白的贝壳,仍带着腥鲜味的贝壳,就像骆驼山和古龙山那些数不清的兽骨,也是通过人类之手,抛掷成堆。从使用工具看,小珠山先民在岸边拾贝的同时,还向大海捞珍,叉鱼、射鱼、网鱼,曾是他们惯用的三种姿式。
我发现,小珠山先民不光吃海鲜,也吃鹿肉。叫广鹿岛,就是鹿多的意思,因为鹿群挤挤,小珠山人便在河滩淤积里留下一座6500年前的鹿骨作坊。因为彼时海水还遥远,广鹿岛尚未成为离岛,在陆地上奔逐狩猎,仍是小珠山人熟能生巧的老本行。
然而,小珠山最让我大吃一惊的,不是贝壳,不是鹿骨,也不是具有下辽河文化特征的玉斧,刻有之字形纹的陶罐,而是在先民的房址里,居然有可以当主食吃的荞麦。这些荞麦显然不是从野地采回的植物种子,而是经过播种和收割的田间作物。
我的吃惊,是因为我听专家说,荞麦起源于东北,然后一点一点向更旷远的地方传播。在它走过的线路上,都留有荞麦的形迹,唯独在它的出生地未见一粒。就是说,伟大的小珠山荞麦,将中国农业考古一个重要空缺给补齐了。
正是这个结论雷着了我,也成了我为小珠山激动不已的理由。据我所知,远古东北土著有三大族系,东胡族系是游牧者,肃慎族系是渔猎者,唯独秽貊族系以农业和城栅为生,而且下辽河流域新乐人,就以黍为主食。小珠山先民,应与秽貊沾边,他们或许也吃黍了,只是没有实证。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种荞麦是把好手。因为有了荞麦,而让小珠山上空炊烟袅袅。
在小珠山之后,便是郭家村。5000年前,海侵已然停止,因为一支先民在半岛最南端的老铁山落脚,便在这里留下了另一片河滩淤积。
郭家村与小珠山一脉相承,但比小珠山更纯粹。小珠山文化有一种杂然性,既有下辽河新乐,也有山东大汶口,只是与大汶口血缘更近。郭家村因为后发,本地只学小珠山,外面只接大汶口和龙山,于是灌了浆似的水灵而饱满。
两个千年,两个文化层,最后都是因为一场大火烧成了废墟。于是,焦结的红烧土,煮饭用的陶罐,砍砸用的石斧,缝补用的骨针,捕鱼用的网坠,祭祀用或给孩子玩的小陶猪等等,统统作了那两场大火的说明书。然而,郭家村同样让我大吃一惊,因为在4000年前的一堵墙根下,有一篓炭化了的黍。
在这个地球上,谷物起源地有三处,西亚是小麦,美洲是玉米,中国是小米和水稻。所谓小米,即黍和粟,两者的区别,粟是不黏的小米,黍是有黏性的小米(俗称黄米),原产地皆在黄河流域。郭家村人吃的黍,与新乐人吃的黍,应该来自同一个地方,只是新乐人吃得更早些。
由此可知,小珠山先民嘴里咀嚼的,是土产的荞麦,郭家村先民灶房内弥漫出的米香,是从中原舶来的黍。我猜,来到郭家村的黍,无非两个渠道,一是中原耕夫从山东半岛渡海携带过来,二是郭家村先民渡海过去载回来。因为4000年前,郭家村先民就制作出了一只工艺先进的陶舟,相当于现在的船模。这只陶舟的船首呈流线形,前突上翘,劈波斩浪的速度会快。船底不是一块整板,而是多块拼接,严丝合缝,能保持行驶稳定。两舷等高,外凸,呈弧形,这样平衡效果会好。内里是个大通舱,可以多装货物。如此复杂的航海器,在半岛南部还是第一次发现,说明郭家村先民已经告别原始的独木舟,改撑多木拼接而成的舢板。有这么豪华的大船,什么货载不了呢?
在小珠山和郭家村之后,还有大嘴子。它依然属于河滩淤积,不同在于,小珠山和郭家村是新石器时代遗址,它是青铜时代遗址。
彼时,大嘴子先民已经学会了砌墙,不是用土夯,而是用石垒,一共有三道,最长一道有30多米。环绕着村庄,建造坚固的石墙,显然是人口稠密了,有更多财产了,石墙是一种守护,可以让好日子不被侵犯。
比石墙更令我刮目的,或者说,再次让我大吃一惊的,是在一座屋址内发现了炭化的稻米和高粱,它们被分装在六只陶罐里,整整齐齐地摆放在地上。又有两种不同的米香,在3000年前的大嘴子袅袅升起。
稻米是水田作物,来自长江流域,高粱是旱田作物,来自黄河流域。稻米标本,在新石器和青铜时代就遍布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东北一直是个空白。大嘴子遗址的意义,在于它将中国栽培稻从北纬37度15分,刷新为北纬39度2分6秒,成为中国最北界稻作地点。
还有更爆的,中外专家一致认为,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栽培稻,最初都是从中国传入的,历史上从南到北,曾有三条平行东去的“稻作之路”。途经辽东半岛这一条,属于北路。有人写过一本小说叫《高纬度战栗》,大嘴子种的是高纬度水稻。
大嘴子太牛了,它以实物的方式,证明了自己在稻作之路上的不可或缺。因为在中国栽培水稻向外传播路线上,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是一传,山东半岛是二传,辽东半岛是三传。下一站,是朝鲜半岛,再下一站,是日本列岛。如果大嘴子自私,或懒得再往东传,历史就不会有这么精彩的一笔了。
写到这里,我觉得笔下的每一个字,仿佛也都变成了一粒粒稻米,一粒粒在半岛与半岛之间行走的稻米。
不知为什么,高粱没有随稻米一起向东传播,而是从辽东半岛向北铺去,把黑土地染得红彤彤一片,把东北地区的高粱栽培史整整提前了1000年。于是,在东北流亡学生唱的歌里,就有了这样的词句: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大嘴子先民用六只陶罐储存种子,说明家口大,土地多,也说明雨量充沛,可以种大面积水田。要雨有雨,种稻得稻,说明他们赶上了一个万物生长的好年景。
然而,从大嘴子挖出来的红烧土告诉我,同样是一场大火,终止了他们所有的盘算和想往。
小珠山,郭家村,大嘴子。它们是三堆厚厚的河滩淤积,更是三个人间烟火的村庄。我很任性,那里有那么多可书可写的东西,但我只选择了种在不同时代的米,选择了带着烟火气的米。因为我喜欢它们种在地里的样子,喜欢它们在陶罐里煮熟的样子,喜欢它们跟着人在半岛之间行走和传播的样子。总之,不论哪一种样子,我都喜欢。
米是物质,能续命。也是精神,象征着生生不息。所以,即使被冲天大火烧成了炭,它们仍以炭化的籽粒,留在世间。也许,这就叫物质不灭,能量守恒。
四、青丘的背影
驻足在辽东半岛,或途经辽东半岛的古人类,曾经与冰期动物一起,奔走在漫长的无名时代。不管今人如何踮起脚尖,向历史深处张望,他们的面孔与表情,仍然是模糊的。因为石器时代尚无族属概念,只能是在哪里被发现,便以哪里人名之。历史在青铜时代改写,因为从这个时代开始,大连有了一个地名,青丘;大连先民有了一个正式身份,貊人。
《大连通史》(人民出版社 2007年)载:“青铜时代大连地区的居民属于东北夷的青丘、周头等部。”话说得很肯定,青丘和周头都是大连居民,而且不只这两个部。但是《东北各民族文化交流史》(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2年 孙进己等著)一书,却持另一个观点,认为周头聚居地在丹东的小娘娘城山遗址。
就是说,周头确与青丘为邻,但青丘在半岛南部大连境内,周头在半岛东北丹东境内。那么,确切的说法,只有青丘是青铜时代的大连居民。对于大连初史,知道这一点十分重要。
我注意到,各类地方史书对青丘的叙述大都一带而过,民间书写者对青丘却显得十分在意和踊跃。因为在写大连传,我对青丘的态度就是一定要凑近了看,放大了看。
青丘之名,最早出自两部典籍,《山海经》和《逸周书》。有趣的是,它们的成书年代,都在战国至周初,不知谁抄了谁的作业。两书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神话,后者是史书。
在《山海经》里,青丘是神话发生地,神话主角叫“九尾狐”。《山海经·大荒东经》载:“有青丘之国,有狐九尾。”
《山海经·海外东经》载:“青丘国在其北,其狐四足九尾。”
《山海经·南山经》载:“青丘之山,其阳多玉,其阴多青?。有兽焉,其状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婴儿,能食人,食之不盅。”
青丘是国名,也是山名。这里盛产一种仙狐,狐之魅惑,碾压了青丘,狐之气场,也把青丘甩出去好几条街。青丘是舞台,垫场的,狐是角儿,闪着光。
更有甚者,自九尾狐在《山海经》现身,就不曾在人间消失,始终摇着一丛迷人的尾巴,从上古传说、秦汉典籍、明清小说里翩然而出。一直到现在,仍有人以《山海经》为百宝文奁,把青丘和九尾狐写成各种仙幻类剧情。
九尾狐如此神奇,也引发了青丘究竟在何处的各种猜想,从古至今,想找到它具体经纬的人熙熙攘攘。现在去网上搜,也是有说在山东,有说在青海,有说在福建,还有说在辽西的朝阳。真真是,乱花渐欲迷人眼,争论者的脑子,好像被九尾狐给下了迷幻药。
要怪就怪《山海经》,把一个神话反复说了N次,仍语焉不详,故意要喷人一头雾水。要爱就爱《山海经》,其实它已经说得很具象了。
《山海经·海外东经》载:“亦有青丘国,在海外。”
西汉司马相如《子虚赋》云:“秋田乎青丘,彷徨乎海外。”
东汉服虔注:“青丘国,海东三百里。”
西晋孔晁注:“青丘,海东地名。”
海外,即渤海之外。海东三百里,即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的海上距离。然而,即便说得这么清楚,因为《山海经》被学界或非学界过度翻抄附会,关于哪里是青丘,仍在嘈嘈切切中。
好在还有《逸周书·王会篇》。周成王七年,正逢新都洛邑宣告竣工,作为天下共主,年轻的周成王为了给自己立威,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剪彩典礼。他是武王之子,西周第二代王,由他主办的这次成王之会,既是他即位后第一次会盟诸侯,也是西周历史上仅有的一次全家福,史官自然要打起精神,记下明细。
在出席会议的报到簿上,光是有名有姓的东北夷,就忽啦啦来了十五个:稷慎、秽、良夷、扬州、解、发、俞、青丘、高夷、独鹿、做孤竹、不令支、不屠何、东胡、山戎。
其实,还有一个东北夷周头也来了,不知何故,报到簿上青丘赫然在列,周头却被打入另册,只在贡品清单里露了一回脸,座次倒是挨着青丘。《逸周书·王会篇》载:“青丘,狐九尾。周头煇羝互,煇羝互者,羊也。”
周头与大连无关,只说青丘吧。这场王会,至少透露了两个讯息:其一,青丘是东北夷名正言顺一分子;其二,青丘给周天子进贡的地方特产是“狐九尾”,而不是“九尾狐”。
对《逸周书·王会篇》所记青丘,《中国东北史》(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8 年 佟冬主编)曾作如下解释:
东北南部的貊人,因居地或部落之不同而有不同称呼。文献记载,在辽东半岛上有两个貊人的小部落,一称周头,一称青丘。两部均为‘海东夷名’,并谓‘青丘在海东三百里’。这里的海指今渤海而言,所以两部之地当在今辽东半岛之上。这两部的代表性特产,青丘是九尾狐,周头是煇羝——毛色光亮的公羊,因此他们可能是以狩猎兼畜牧为主。
读过此书,青丘已不再是东北夷那么笼统,地理上有了具体指向,辽东半岛;青丘居民族属也不再那么模糊,他们是海东夷,貊人。
海东夷即远古的东夷。史载,在距今8500年前,东夷人就活动在山东和苏北。《礼记·王制》云:“东方曰夷。”汉朝经学家孔安国《书传》云:“东表之地称嵎夷。”
《后汉书·东夷传》载:
夷有九种,曰畎夷、干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昔尧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巢山潜海,厥区九族,“是以九夷为嵎夷也”。
在一张今人绘制的上古地图上,我看见辽东半岛南部和山东半岛东部被涂成同一种颜色,像给渤海岸镶了一道花边,上面只写了两个字:嵎夷。
想想也是,彼时他们从一个半岛蔓延到另一个半岛,只有两个可能,或是在海退之后,他们在胶辽古陆追杀猎物跑过了头,或是在海侵之后,借舟楫之便,摇橹撑帆,一苇以航,见岸则登。
但是,《中国东北史》对周头所贡的羊,说得惟妙惟肖,对青丘所贡的狐,却基本上原文照抄,有点令人费解。我认为,《山海经》里的“九尾狐”是以“灵狐”形象出镜的,既是灵狐,何以捕捉?又怎能入贡?《逸周书·王会篇》里的“狐九尾”是以“凡狐”之貌现身的,所以它只是一种动物学意义的狐狸,青丘拿它当贡品,非以狐尾取悦,而以皮毛贵重献之。
也许青丘确有长着九条尾巴的奇葩狐狸,但是至今也没看到任何可以采信的记载,倒是《艺文类聚?卷九十九》更加坚定了我的猜测:“《周书》曰:成王时,青丘献狐九尾。”写在这里的“尾”,显然与量词“只”同义。彼时,去给周成王上贡的东北夷,贡品大都是实实在在的地方特产,青丘怎敢如此魔幻?
我想,对青丘和九尾狐作各种猜测演绎者,或者没读过《逸周书·王会篇》,或者就是要臆造出什么青丘帝姬、九尾白狐、四海八荒第一美女,就是要闭着眼睛拿《山海经》来大赚票房。
可以看出,青丘之国得名于青丘之山,那么在辽东半岛南部,就应该有一座山叫青丘。金毓黻自1923年开始搜集整理东北地方文献,对东北文化系统研究,《东北通史》是1941年出版的中国第一部东北地方性通史专著。他认为,辽东半岛最南端的老铁山,就是《山海经》里的“青丘之山”。载曰:“老铁山,其色焦黑,因以得名。”而《山海经》所谓的“海外”“海东三百里”,用的正是中原视角,而从山东半岛泛海东来,首先进入眼帘的,就是老铁山的森森之貌。更何况,站在庙岛群岛最前端的北隍城岛,肉眼即可看见一脉青峰矗立。
不管怎么说,真要感谢那场成王之会,让大连人知道了曾有一个名叫青丘的东北夷活跃在西周之世的大连。只是,青丘第一次出场,竟是千里万里去朝贡。
在青丘故地,至今仍触目可见的青铜时代遗迹,就是那些极具神秘感的石棚。
它是高大的棚状建筑,三面竖石壁,留一口朝前,在石壁顶部,盖一块向四面突出的石板。这样的石棚,在大连境内不止一座,而是几十座,它们或独立自处,高大威凛,咄咄逼人;或大小混处,长幼有序,尊卑分明。石棚的造型,线条粗犷,风格大气,质感厚朴。虽经3000多年风剥雨蚀,却不能奈它何,被史家称之为“巨石文化”。
许多年前,我曾走遍辽南丘陵山地,一座一座去寻访它们。记得,看这么多石棚祼然而立,感觉造它的主人并没有走远,抑或,造它的主人知道自己有一天会烟逝云去,便用石棚来抵抗消失和遗忘。
石棚也叫石桌坟、支石墓、姑嫂石、石庙子,等等。字面上看,显然与葬俗有关。有专家说,它“很可能是东夷族青丘部的文化”。(参见孙进己《东北各民族文化交流史》)
青铜时代,半岛南部正是青丘之地,石棚极有可能是貊人葬俗。然而,面对那一座座神秘的石棚,我确曾有过一种超出了历史常识的困惑。
后来发现,不只我一个人困惑,许多石棚研究者也同样困惑,直到现在,仍因为无法确认,作了三种猜想和假设:其一,它是一种巨石坟墓,意义如同埃及的金字塔;其二,它是一种宗教祭祀建筑物;其三,它是原始氏族部落举行活动的公共场所。
我想,如果是貊人葬俗,那么作为生活在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时代的有神论群体,他们的主观意愿不外以具象的石棚为依托,表达对天地万物的敬畏和信仰,不外用巨石给逝去的自己筑造一座永生宫殿。却不曾想到,几千年后,在这一方水土之上,这些石棚居然成了无法磨灭也无法删除的文化之厦,成了无法解读又无比崇敬的地上文物。
其实,石棚并非辽东半岛独有。在欧洲、非洲、亚洲乃至中国许多地方,也都有石棚或与石棚相类的巨石建筑。德国人叫“巨人之墓”,比利时人叫“恶魔之石”,葡萄牙人叫“摩尔人之家”,法国人叫“仙人之家”和“商人之桌”。英语则有一个专门词汇:Dolmen,意为“用石头架成的史前墓石牌坊”。
有人据此认为,巨石建筑虽与墓地有关,但逝者不太可能葬在巨石内部,它的造型便像是供亡灵出入墓室的大门和通道,因为Dolmen近似于最原始的发音——道门。这个道门,有点像中国皇陵入口处那座高大的牌坊,以示神圣与威仪。这也印证了石棚研究者的猜想,石棚并非单纯的墓葬。
正因为巨石建筑如此相似,有人说它应该是同一文化族群全球传播的结果。比如英国索尔斯伯利平原上的巨大石柱群和杜灵威环石墙,比如法国被称为“石林路”的史前巨石文化遗迹,比如黎巴嫩重量在1200吨以上巨石建造的神殿遗址,比如智利复活节岛的高大石像,都与这个文化族群全球迁徙有关。
一言以蔽之,人类在探询未知的时候,最大的兴奋点就是对“起源”的追溯。巨石文化似乎没什么神秘,看懂了人类迁徙路径,认同了文化传播规律,也便会心和释然了。
中国境内的石棚,最早出在商周之际,有关石棚的文字记载,最早见《后汉书·五行志》:
孝昭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正月,泰山莱芜山南匈匈有数千人声,民视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围,入地深八尺,三石为足。石立处,有白鸟数千集其旁。
泰山莱芜山,古为东夷旧地。2000年前的东汉,仍有如此生动的竖石场面,说明石棚文化余绪未断,至少绵延了1000年。
金代官员王寂巡按辽东半岛时,把复州境内的一座石棚写入了他的《鸭江行部志》:
游西山,石室上一石,纵横可三丈,厚二尺余,端平莹滑,状如棋盘,其下壁立三石,高、广丈余,深亦如之,了无暇隙,亦无斧凿痕,非神功鬼巧不能为也,土人谓之“石棚”。
此外,他还作诗一首,“以纪其异”:
片石三丈方纵横,平直莹净如楸枰。
旁榰石壁做大室,人力不至疑天成。
中国别的地方也有石棚,但以辽东半岛为多,辽东半岛又以大连为最。于是,石棚成了大连远古史一个标志性文化符号。
成为符号的石棚,便有了某种说不清的亲和力。有一次,当我走到一座石棚面前,竟有一丝恍然,觉得那就是貊人当年的坐姿,只不过在数千年的岁月里石化了。
曲刃青铜短剑,历史留给大连的另一种惊艳。
每每看到它,我都会意识流似的想起石棚。质地,一石一铜;形体,一大一小。在辽东半岛南部,在远古文化体系里,它们都是一种有力度的存在,一种叠加起来的神秘。
有出土文物证明,剑主活着的时候,将剑紧握在手中,死去的时候,把剑放在身边陪葬。因为在无数的墓穴里,都能看到曲刃青铜短剑,有的甚至经过焚烧。剑是逝者的爱物,逝者轻盈的灵魂,与凝重的剑相绕相缠,在火光中一起“升遐”了。
当然,曲刃青铜短剑也在墓外。有学者在老铁山下那片耕地里,一下子发掘出十五柄曲刃青铜短剑。之后,在黄海和渤海沿岸,有更多的曲刃青铜短剑出土。于是就有了一个专属命名:曲刃青铜短剑遗存。
剑是冷兵器,有不同风格,北方风格的短剑,主要有两种形制:一种是匕首式短剑,剑柄与剑身连铸在一起,主要分布在蒙古草原东南边缘。持剑者带着它南下中原之后,剑身也随之加长。
另一种是曲刃式短剑,主要分布在辽河流域,日本学者叫“辽宁式铜剑”,韩国学者叫 “琵琶形铜剑”,中国学者叫“曲刃青铜短剑”。作为兵器,此剑最特殊之处,就是宽叶、曲刃。
其实,岁月漫长,剑的款式和造型,也随时光在变。最早的剑身,只有曲刃,而无剑柄,像一个成人玩具。后来,变成一个复杂的组合,由曲刃剑身、T型剑柄与剑尾端加重器连成一体。曲刃也从宽叶变成窄叶,对剑柄还作了美化,刻有三角勾连纹饰或羽状纹饰。于是就听过一个说法,曲刃青铜短剑的造型和纹饰,让人想到浪花细腻的线条,有浓重的海洋气息。
我甚以为然,持剑者滨海而居,他们造出的剑,怎么会少了海的韵致呢?此外,一柄曲刃青铜短剑,从西周到战国,流行了数百年时间,一支持剑者部落,潇洒地生活在秘境般的半岛南部,也算一页文化传奇吧?
但是,关于持剑者身份,考古界至今仍存争议。《大连通史》(人民出版社 2007年)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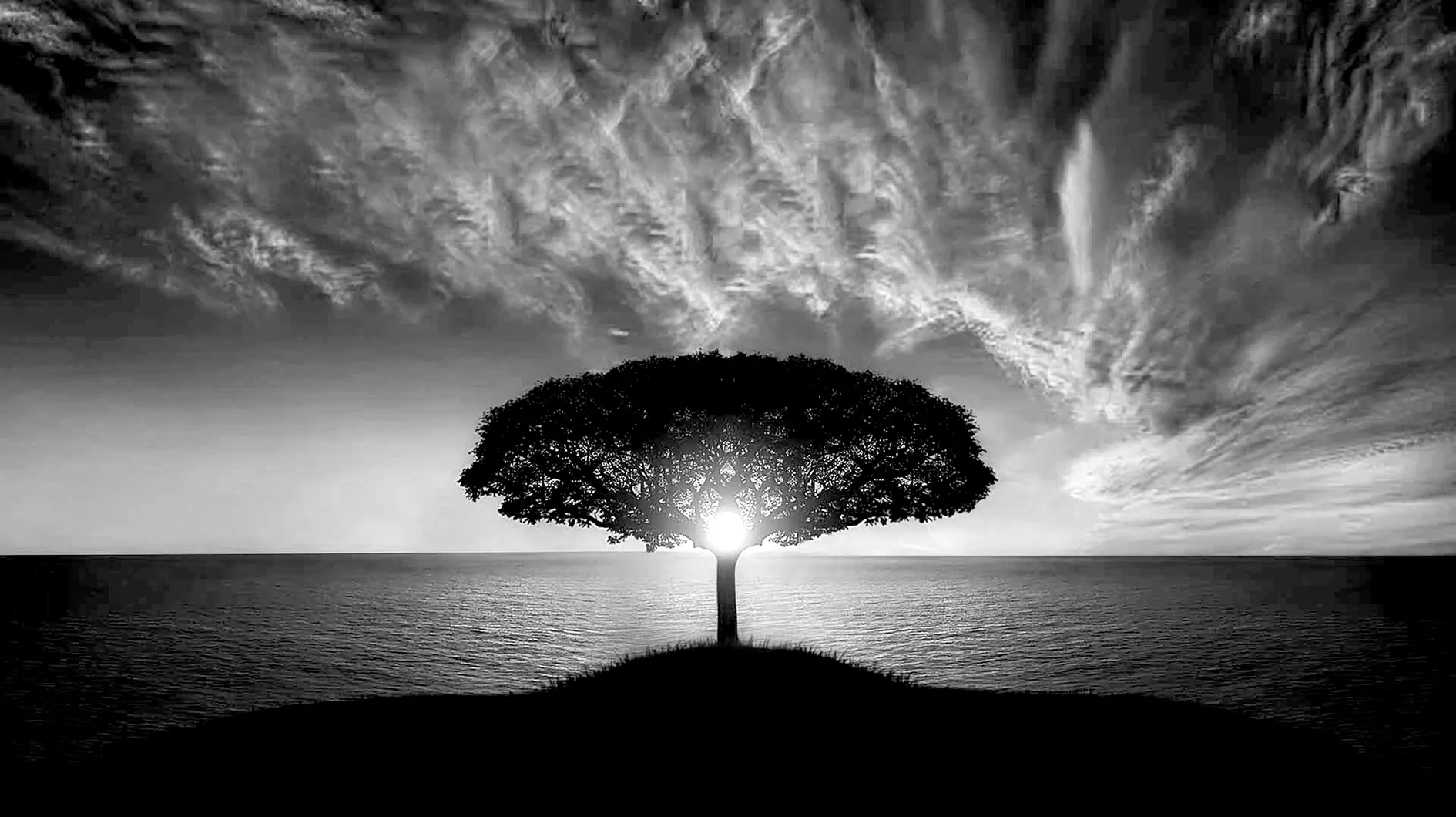
大连地区生活着一支以使用曲刃青铜短剑为主要特征的居民。……这支使用曲刃青铜短剑的居民,从西周中期开始,直到战国后期,一直活跃在大连地区。
一支以使用曲刃青铜短剑为主要特征的居民。这个定义比较模糊,没说明白,也许是说不明白。
我目前看到的争论,主要有两种。
多数人说,曲刃青铜短剑是青丘部貊人的文化遗存。他们的依据是墓葬,在各种石棺墓内,皆有曲刃青铜短剑,在那些高大的石棚内,也有曲刃青铜短剑。毫无疑问,这是同一部族、同一文化体系的葬俗。
少数人说,曲刃青铜短剑出自东胡、狄人或夫余人之手。因为中原军队是车战,多以长戈为武器,游牧民族是骑兵,更喜欢短剑。所以,它流行于北方诸多游牧民族,不能将其归属某个特定的部族。
我更认同多数人的说法。一种剑式,原创者只能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个族群,不可能由诸族共同发明。只能说,它曾被别人大量拷贝,样式或许还作了一些改变,在北方诸族间,配戴它逐渐成了一种流行和时尚。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与石棚一样,曲刃青铜短剑在大连出土最多。当然,更早的时候,握在青丘部先民手中的利器是石镞、石斧、石铲和木棍、木叉,那是为了捕杀猎物。后来,时代不同了,人与人,部落与部落,有了各自的山头,有了利益争斗,便造出了金属利器,便开始手持曲刃青铜短剑,开始有了刀刀见红的肉博。当曲刃青铜短剑造得越来越锋利,那是因为天下进入战国。
半岛南部,终于迎来了那场你死我活的厮杀。燕国被打得粉身碎骨,青丘也跟着吃瓜落儿。但是,当风云散尽,尘埃落定,曾经拿九只狐狸去给周成王上贡的青丘,曾经用一座座石棚刷存在感的青丘,曾经铸造出海洋风曲刃青铜短剑的青丘,仍以独有的气质,让后世引颈仰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