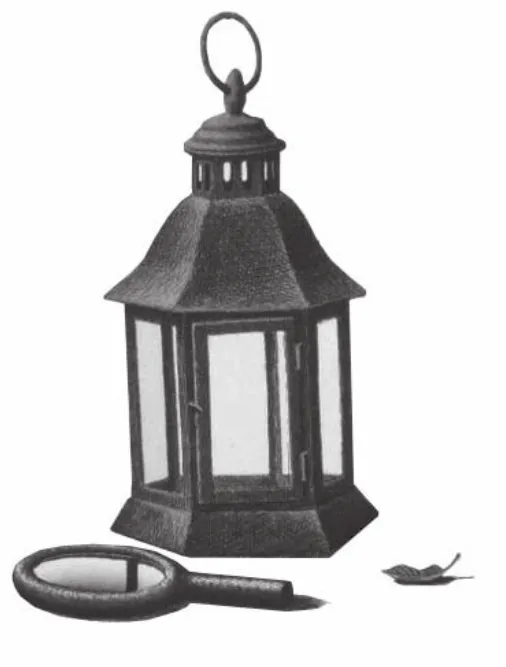
格式化、标准化……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元素。人自然也不例外,同样被格式化了,从思想、语言到衣食住行、工作等等。什么叫格式化?举个例子容易说清楚,比如参加任何一个大型的会议,首先要通过严格的安全检查,安检人员的面目是没有表情的,语言是没有温度的,像机器人一般。过完安检走进会堂,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我们通过电视画面可以看到,会场摆放的水杯都是一条笔直的直线,服务人员隔一会就走着一条线般整齐的步子出来加水,但实际上大家都不敢喝水,怕去卫生间,众目睽睽之下,谁也不愿意惊动全场去上厕所。以前曾觉得中国人的膀胱都非常了不起,直到最近才知道,这是被成人纸尿裤给“格式化”了。
同时被格式化的还有大脑,学术界称现在的时代为“同质时代”,大家吃的差不多,开的汽车差不多,接受的信息也差不多,大家都生活在一个大致相同的“格子”里,生活在一个相同质量的环境中,作家又能说出什么新鲜话让大家感兴趣呢?因此,现代人的故事很少,文学中好故事也少,边缘化是自然而然的。文学边缘化之后,随之而起的是铺天盖地的段子、荤笑话,填补人们对故事的需求。中国的小说创作,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有过“反故事”、“反人物”、“反情节”的潮流,流来流去,把文学流向边缘化,读者越来越少。有趣的是,当初“反故事”、“反人物”的作家早就又回来写故事、写人物了。
当今世界正处于“多事之秋”,事故不断,甚至经常会有“非常事件”发生,事故几乎成为常态。事故多发的一个原因是现代人竭力在追求“精变”。“精变”这个词语是我创造的,与人们常挂在嘴边的“社会转型”的意思差不多,社会转型,人也转型,怎么个转法?“精变”,人人都想“成精”。物质上有香精、鸡精、味精、瘦肉精等等,西红柿、青枣等等农产品,想让它变红变熟,用药水一喷一洒,转眼就变红变熟。过去一离开海水就死的鱼鳖虾蟹,现在都变成了鱼精、蟹精、虾精,被顾客买回家里还是活蹦乱跳。文化上,有各种各样的精英,政治精英、财富精英、商业精英、教育精英……引导社会潮流,掌握话语权,如今多是各类精英在讲他们成功的故事。五六十年代,中小学生们的志愿往往是长大后要当工程师、老师、战士……五花八门。现在则清一色都当富翁。前些年媒体报道给小学生做测验,99%的小孩子想当比尔·盖茨。宁波也曾提出过口号,要培养1000个乔布斯。这不就是活脱脱用金钱对孩子进行“格式化”。
人人都想“成精”,要当“人精”。“精变”在现代社会意味着成功。本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就像马有马的故事,骡子有骡子的故事一样,马累了就不走了,骡子没有主人的命令就一直走下去,它要倒下那就是累死了。所以我主张不要活在别人的故事里,要找到自己的故事。找到自己的故事,就是找到最好的自己。其实追求成功,想当人精,无可厚非,成精就是想成为强者。也一定要看到“精变”是有风险的,一个不变的事实是,世上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为人精,就像世界上的16亿人不会都成为比尔.盖茨和乔布斯一样。在这些年的反腐风暴中,有成千上万的贪官落马,他们都曾是令人称羡的各种精英,是他们所在部门的人尖,原想进行一场“精变”,最后却成了“恶变”。人像电脑,格式化操作有误,就会死机。
为什么还说现在的人没有故事,“恶变”的故事不是很多吗?到目前为止我们还讲不好“恶变”的故事,一讲就雷同,就是套子。可能还有人说,怎么会没有故事,现在是一个故事满天飞的时代,官员讲故事,媒体也在讲故事,手机上讲故事,电视也在讲故事,到处都是故事……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怎样区分故事与事故。
“事故”不是故事,有些听起来像故事,却不能打动人,那是“假故事”,就是人们习惯说的假大空。事故和故事是不一样的,事故发生的那一刻,生命力就结束了。我们通过媒体第一次听到哪里出了事故,当知道了这场事故之后,别人再跟你说起它,你就会觉得索然无味。但故事不一样,故事的生命力是永恒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聊斋志异》里的故事,什么时候说起来,说的人有激情,听的人有兴趣。
可见,故事是有标准的。
故事的标准很简单,赫尔曼的观点认为,我们给孩子讲故事,是为了哄他们睡觉,我们给成年人讲故事,是为了让他们清醒。这就是故事的第一个标准:故事就是要有吸引力,让人听了前面还想听后面,不是让人打瞌睡,而是让人清醒。
故事是一种力量,它不单单是小说家的虚构。为什么故事是一种力量?柏拉图说,谁会讲故事,谁就拥有世界。15世纪到16世纪的时候,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西班牙成为欧洲第一个殖民帝国,这是西班牙人在讲故事;18世纪,工业革命的成功使英国渐渐成为日不落帝国,英国人开始讲故事;二战之后,是美国人在讲故事,直到现在还是美国人在讲故事。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一身的故事。他一年只领一美元年薪,他的女儿、女婿也都放弃原有的高薪工作,成为无薪资的白宫高官。特朗普是制造故事的,他创造故事,他用故事搅动世界。中国人对故事太敏感了,故事就是社会最敏感的神经。
美国的一个统计数据显示,现在16岁到39岁的美国男女当中,单身者占52%,这就是说单身占到一半还多。为什么?美国耶鲁大学的心理学家斯坦伯格的研究认为,一段感情是否幸福,很大程度取决于双方的故事是不是匹配。夫妻间的故事相匹配、相互补,容易白头到老。这个研究非常有趣,现在各式各样的相亲本身有很多故事,国内最大的相亲地、成功率最高的是广东的观音山,山下见面,双双上山拜观音,在爬山的过程中有故事的,相亲就成功了。中国有一千多个婚恋网站,还有各式各样的相亲角、电视相亲等等,实际上,它们都在寻找适合自己的故事。
一部小说,一个公众人物,包括一个领导者,或者一个优秀的教师、一个老教授,他都有自身的故事吸引一批人。民国时期出了很多大师,章诒和先生讲,那个年代的人,实在是非常漂亮、每个人都有故事。写小说也一样,真正吸引人的是故事,故事才能给小说以魔力。任何一个人生来都对故事迷恋,人的诞生就是故事,耶和华按照自己的样子捏了人,吹口气就活了,故事就发生了,亚当经不住诱惑偷吃禁果,于是有了人类。从伊甸园走到现在,人类世界发生了多少故事。我们的经典,《诗经》是西周到春秋的故事;《论语》里孔子讲了好多故事;《庄子》也是一个个的故事。西方也一样,《荷马史诗》《圣经》都是故事。我们每个人小时候都是听着故事,听着故事睡觉,听着故事笑,听着故事长大……
小说家的经验是通行的,都是先从写故事开始,或者说一个作家存在的主要价值,就是提供好故事。经典的作家,甚至包括司马迁的《史记》,都是一个一个的人物、一个一个的历史故事。更不要说那些经典小说,光是京剧改编的《三国演义》就有三百多出“三国戏”,根据《水浒传》《红楼梦》改编的“水浒戏”、“红楼戏”也有百余出,历代都能长演不衰。当我们提起托尔斯泰,就会想到《复活》《安娜卡列琳娜》《战争与和平》中的一堆人物、一堆故事;一提起到雨果,就会想到《巴黎圣母院》的敲钟人,立刻就有故事,就有人物在大脑活跃起来。在公交车上、地铁里、马路上,大家称低着头看手机的人为“低头族”,他们想看的是故事,也可以称为“故事族”。不过他们看到的大多是事故,哪儿又出新鲜事了,哪儿又有了爆炸性新闻……
但,有些事故里会藏着故事,有些故事不过是个事故。故事和事故,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地理,是可以转换的。在美国,师生恋是违法的,那是事故,中学的女老师跟自己的男学生恋爱会被判刑。但在法国,现任总统马克龙和他的夫人,是典型的师生恋,中学时期马卡龙迷恋自己女老师,十几年后终于结为夫妻,成为故事,成为佳话。无论日后马克龙夫妇的关系怎么发展,只会让这个故事更加一波三折。有些事故,还可以慢慢演化,由事故演化为故事。前些年在泰国曼谷闹市区有一尊脏兮兮的水泥佛像,粗糙,脚边堆着垃圾,那可能是一场事故的产物。有个小和尚却老是在心里放不下这尊粗陋不堪的佛像,决定想办法把它搬到寺庙里去。这个和尚通过化缘积攒了一些钱,选好了日子开始搬运佛像,在搬动的过程中,佛像上的粗劣的水泥产生了裂缝,小和尚发现水泥的裂缝里边闪闪发光。工人们继续搬动,水泥开始逐渐脱落,发现粗糙的水泥里面竟包裹着一尊熠熠生辉的金佛。或许是在战乱动荡的年代,有人为了保护这尊金佛,用水泥将佛像封起来。是当初的一个“事故”把金佛藏在水泥中,现在通过一个灵感、一个善念,又让金佛重现于世,成为一个美好动人的“故事”。
托尔斯泰说,活着就是为了讲故事。托翁本人一辈子都有故事,他七十岁的时候就想把版权、土地全部分给农民,到了八十多岁托翁还离家出走,死在一个小火车站……我记得那是一个大雪没膝的冬天,我在托翁庄园寻找他的墓,就在路边的大树旁边,没有墓碑,没有高丘……托翁死后还在讲故事,还在讲他死以后的故事,多厉害。世界最大的梦工厂好莱坞,有一个部门叫做“故事部”,他们每年会从全世界搜罗三万个故事,从中选择三百个故事,改编成电影剧本投入拍摄。对故事的选择真是万里挑一。所以好莱坞的故事,大多都有点新东西,不会重复,不会一个晚上几个频道都在播放“抗日神剧”。好莱坞绝对是讲塑造美国英雄,但它塑造的美国英雄会让人有真实感,不是刀枪不入,拿菜刀可以把飞机砍下来的英雄。美国作家麦基说,一个作家75%的劳动都要用在写故事上。
那么当下的小说故事出了什么问题?在讲小说之前先说说作为文学创作环境的社会文化是一种怎样的态势,以音乐举例,著名作曲家徐沛东说,我国每年生产的歌曲有万首之多,但大部分是废品,质量相当差。难怪看完一个春节晚会,竟记不住一个旋律。影视界,著名演员王志飞面对采访公开宣称,国家每年生产剧本的数量巨多,但大部分是垃圾。在文学方面,国家版权局的前任局长柳斌杰,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的时候说,我们国家每年出版数千部长篇小说,大部分不堪卒读,尤其缺少支撑民族精神的文学作品。书籍是可以嫁接人生的,可以想象如果一个一辈子不读书,只凭自己那百八十年的经历,其人生将是多么单薄。读了《红楼梦》,大观园中的各样人生故事自然会嫁接到自己的人生感悟、人生经验上来。当读了《三国演义》《水浒传》《史记》等,我们的人生就非常得丰厚,我们会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人,还有这样一种活法,我们的精神就不一样。好的小说应该是能够改变社会,由公共阅读形成社会记忆。我们这个民族假如没有那些经典,没有《老子》、《庄子》、孔子,没有《史记》、四书五经等等,我们民族的精神就会极端贫乏,甚至会处于黑暗之中。现在民间看到一个人性格暴躁,说他是张飞,一个女孩子长得很娇弱,就说她是林黛玉,成熟能干就是薛宝钗……等等,这许许多多民族性格的营养成分来自于文学。
当下的社会就缺少公共阅读与社会记忆,在文化发达国家,几个人凑在一起常会说起正在或刚刚读过的一本书,对这本书的感受。当几个中国人凑在一起时,很难聊到同一本书,很少碰上几个人都在读同一本书。现在已经没有了共同阅读,很难再有小说能形成社会记忆,这或许也是“碎片化”时代的特点,每个人的阅读都是零碎的零散的。美国作家辛克莱的《屠场》中,描述了美国肉类加工行业的种种内幕,其中写到一个巨大的高温煮锅,老鼠、猫等各种小动物,只要不小心掉进煮锅,顷刻间跟猪肉一起进入下一道工序,最后都变成香肠送上美国人的餐桌。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边吃早餐边读《屠场》,读到这里时大叫一声“我中毒了”,把盘中剩下的香肠抛出窗外,据传他就是从那天起开始吃素,并直接推动了1906年的《纯净食品及药物管理法》的通过。一部小说,改变了美国的社会,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习惯,这就是小说、故事对人类对社会的贡献。
其实并非只有小说需要好故事,诗歌、散文也一样。诗有“诗眼”,诗眼常常来源于故事,散文则必须要有一个情节,一个有味道的细节,借以表达一个思想、一种精神。文学作品要抒情,情要有附着物。情是什么呢?情是血脉,是动力,是滋润,所有的创作都一样,想象力也需要感情滋润,现代人想象力不足,所以没有办法写出“飞流直下三千尺”那样的诗句,也写不出极度夸张的美感。近几年支撑中国诗坛的都是有故事的人。女诗人余秀华,她本身就有故事,她的诗中的直率、坦诚,就有惊人的冲击力。近两年领诗坛风骚的是张二棍,我喜欢他的诗,如他的《哭灵人》中有这么一句“用膝盖磨平生死”,传统文化对哭是有说法的,有声有泪叫“哭”,有泪无声叫“泣”,有声无泪叫“嚎”。现在好多年轻人回家奔丧就是嚎,没有泪,也没有多少真情实感。而哭灵人,又有声又有泪,他们真哭,他们借着哭死者,也哭生活、哭自己、哭人生,哭自己用眼泪换取养家糊口的钱。向未的诗歌我也很喜欢,向未是寺庙里的方丈,但他的诗不是看破红尘,而是深入尘世,写母亲对他思念:“眼是一口老井,纵使百年干旱,也能打出水来”。写故乡:“生我的人死了,养我的人死了,埋葬了他们,就是埋葬了故乡”……
爱因斯坦有一句话,兴趣体现在业余上,而兴趣决定一个人与别人的差异。在同质时代,差异就是优势,经历就是财富。从事文学创作一定要承认一个事实,文学创作永远不能高于、不能大于人类的社会生活。人类的社会生活是大于文学创作的。但是人类的社会生活,又是文学的土壤,文学的根脉,千年老根黄土里埋。当代文学之所以太软,就像无土栽培的花草,无土可以栽培花草、蔬菜,能长成真正的树木吗?更不要说是参天大树。如今很少看到实实在在的硬碰硬地反映生活矛盾的小说了,看不到有勇气反映社会现实的小说了,“软玉温香”类的小说太多了。如今文坛才子当道,现代才子都很聪明,凭聪明写一个点子,离开了现实生活的土壤。而故事的结构、故事的骨骼,是思想、是灵魂、是精神。好的故事是有个“原点”的,这个“原点”应该具有精神含量,思想品位是故事的核心。古人有一种说法,笨也是一种天赋。文学太过轻灵,缺少下笨功夫写出来的厚重、深邃。下笨功夫后所产生的灵感,才是最靠得住的。写作需要灵感,没有灵感就是平庸,有灵,才是灵魂;灵魂无灵,那是鬼魂、亡灵。但有灵没有魂,定不住魂,光靠灵气就会太轻飘,现在就是轻飘飘的东西太多了。
金圣叹说,作家的才华概括起来无非就是两个字,“材”与“裁”。“材”应该有两层意思,一是作家本人是什么材质,先天的和后天所具备的条件;二是你要写的是什么素材?你是什么材料决定你写什么小说,为什么叫找到自己的故事,就是不要活在别人的故事里,不要把所有的时间,所有的才华都浪费在别人的生活中,那不是你的故事。我自己最看重的一部书是《农民帝国》。有人问我,你写工业题材的,为什么又去写农村。我认为,写农村不一定就不是工业题材,我写的农民的工业性,工业性对人性的影响……成熟的作家不应受题材的局限,文学就是文学,不管是什么行业,进入你的小说,它都是文学。《农民帝国》写的是农民的工业性。我写工厂,写的是工业性对人的改变,工业性的不彻底,农民的命运总是在转圈儿。这几年反腐败曝光的许多贪官,把钱藏在冰箱里、暗室里、角落里等等,这和过去的土地主把钱藏在瓦罐里埋在墙根底下不是一样吗?他们在精神上、灵魂上的农民性没有去掉。所以,不了解农民很难理解我们这个国家。金圣叹的第二个字,剪裁的“裁”。你找到材料,这个材料也适合你,你要怎样它写成好的故事,好的文章,这就是技巧,这就是剪裁。同一块布料,不同的裁缝做出不同的衣服,每个人的修为不一样,对语言的感觉不一样,决定了笔下故事的魅力。
你是什么材质,就会对适合你的材料感兴趣,所谓“找到自己的故事”,就是找到适合自己,只有自己才能写好的故事。好故事一定是从灵魂里开出的花朵。怎样才能找到自己的故事呢?首先是开掘自己,有人自己的故事就非常丰富,像博尔赫斯、毛姆,他们主张所有文学都是自传性的,对自己的故事有极深刻的体会,且能用奇怪的意象表达,让人们还误以为这不是他个人的经历。相当多的作家起步甚至成名,都是写自己和自己熟悉的人和事。
还有就是行走,可以去寻找故事,也可以说让故事找到你。行走才有奇遇,爱默生说,谁能走遍世界,世界就是谁的。行走可治愈麻木,日本重要的作家都叫“行走作家”。司马迁、陈寿应该是行走作家的祖师爷。凯瑟淋·布获得过普利策奖,40岁毅然辞去《华盛顿邮报》主笔的职务,到印度、巴西寻找“离自己的心和世界真实更近的故事”,4年后写出《永恒美丽的背后:孟买幽暗生命、死亡和希望》,当年被美国两大报评为“年度十佳图书”。前两年获得诺奖的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赛叶维奇,全部是靠采访成为了伟大的作家。苏东坡认为自己的成就都是因为被贬到黄州、惠州、儋州的结果,柳宗元、刘禹锡、王昌龄、王阳明等等也都被贬过,西方叫流放,英国的拜伦,德国的海涅,法国的雨果,俄国的索尔仁尼琴等等,
作家的灵魂是没有家的,灵魂永远处于行走状态,寻寻觅觅,紧跟自己的心,找到故事并活在自己的故事里。
(本文系蒋子龙2019年6月20日在大连理工大学“文苑”讲座的演讲稿,刘博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