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铁生: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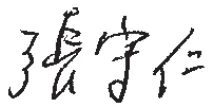

张守仁
张守仁,1933年9月生,上海市人。1957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精通俄语、英语。 1961年毕业分配到《北京晚报》任副刊编辑。 后到北京出版社工作,与同事创办《十月》杂志。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作有《废墟上的春天》《文坛风景线》《你就是爱》《寻找勿忘我》等书。 译作有 《道路在呼唤》《魏列萨耶夫中短篇小说选》《屠格涅夫散文选》等。散文《林中速写》被编入数十个散文选本以及中学阅读课本。 曾编辑出版了《高山下的花环》《世界美文观止》等多部名作,被文学界誉为京城“四大名编”之一。
在798艺术区
史铁生离开我们已经六年多了。他离去时坐在轮椅上安详的背影,一直在我眼前晃动。我可能是铁生写的《午餐半小时》最早的读者之一。不是其后陆续发表在北京《今天》、贵阳《花溪》、北大《未名湖》上的那篇小说,而是更早刊发在西安民间杂志上的那个版本。1978年我参与创办的《十月》发行后,就有近百家杂志强烈要求和我们交换刊物。那年秋末我接到曾在陕北插过队、西北大学中文系学生方竞主编的《希望》。读到其上的《午餐半小时》,眼睛为之一亮。小说写得沉郁、精练,颇有鲁迅余风,堪与经典短篇媲美,内心颇受震动。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命运将双腿瘫痪的史铁生限制在轮椅上。近四十年来,他坐的轮椅运载着内心的沉思、忧郁、痛苦、梦想、爱恋、探寻、追问,行驶在雍和宫附近的街巷里,徘徊在地坛柏荫下的草地上,出现在北京、上海、杭州及纽约、北欧的文学集会、笔会上。这是当代文学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他的轮椅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千万文学爱好者的目光。我和陈建功、刘恒、甘铁生、刘孝存、王升山、孙立哲、王克明们在不同的场合,争着推过、抬过他的轮椅。在推、抬的过程里,在近距离交谈、接触中,我在铁生的小眼睛里看到过羞涩、感激的表情,但他的脊梁始终是挺直、坚韧的。这是我站在轮椅背后时他的身躯留给我的印象。
2001年12月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作为被大家选出的监票人,关在大厅二楼密室里计票过程中,惊喜地发现铁生获得的选票,几乎和巴金一样多,可见他作品影响之广,人格魅力之大,可谓众望所归。
我在担任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评委期间,曾对铁生的参评作品《病隙碎笔》写过这样的评语:“史铁生的《病隙碎笔》思考着生与死、残疾与爱情、苦难与信仰、写作与艺术等重大问题。他不断拷问自己、看清自己。这是一位残疾者所拥有的健康灵魂的哲理思辨,是一本充满人道和爱愿、诘问生之意义的玄思录。书中隽语睿句随处涌现,思想火花繁星般闪烁。他虽坐在轮椅上,身躯被病痛所折磨,但在精神上却把自己从困境的限制中解放了出来,因而显得自由、开阔、明慧、豁达、宽厚、诚实……”
自称“主业是生病、写作是业余”的史铁生曾经说过:“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世上只有善于哲思、钢铁般的汉子,才能如此从容地踏上生命的归程。2010年12月31日凌晨3点46分,铁生因突发脑溢血,匆匆离开了我们。仅仅过了四天,即2011年1月4日铁生60岁生日,在京东大山子798艺术区那包豪斯建筑风格的高大厂房里,由徐晓、陈雷等铁生密友发动、举办了有上千人参加的追思会。厂房墙壁上挂满了上百张铁生放大了的、笑容可掬的照片。这不像是追悼会,既没有花圈、挽联,也没有眼泪和哀乐,倒像是一次盛大的生日party。会场入口处,彩照上的史铁生,坐在轮椅上微笑着迎接每一位进门的来宾。照片下红纸白字摘引着他写的诗篇《节日》中的句子:“啊,节日已经来临/请费心把我抬稳/躲开哀悼/挽联、黑纱和花篮/最后的路程/要随心所愿……”会场四处分散摆放着一千枝玫瑰花,燃烧着、摇曳着60支红烛。中央电视台的张越,在轻播着的《安居主怀歌》宗教背景音乐陪衬下,拿起话筒主持“与铁生最后的聚会”。铁生夫人陈希米身围粉红色披肩,站起来首先发言。她说: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给史铁生过六十周岁生日。史铁生一辈子最大的福气是朋友多。是一帮又一帮老友新朋,帮助铁生度过一次又一次危机和灾难。是朋友们给他的帮助,给他的爱,保佑了他。来自你们的爱,是他对这个世界最大的留恋。他曾说过:“我一直要活到我能够坦然赴死,你能够坦然送我离开。”如今他坦然做到了,我也做到了,所以我们不再悲伤。我们今天的会场上到处是美丽的鲜花和温暖的烛光。我由衷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来参加铁生的生日聚会。
中国作协主席铁凝携来了一筐史铁生生前最爱吃的红樱桃。坐着轮椅的残联主席张海迪,献上60朵鲜艳的红玫瑰祝贺铁生诞辰。铁生文学创作的启蒙老师柳青,带来了北京城里最大的生日蛋糕。从延安赶来的陕北作家曹谷溪送来的礼物是宝塔山下的一撮土和延河里的一瓶水。北京作协副主席刘庆邦捧来三束鲜花。他说:“铁生是我的同事、我的兄长。铁生高贵的心灵、高尚的人品、坚强的意志,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铁生的作品是我们整个民族的精神财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著作会越来越放射出璀璨的艺术光辉。今天是铁生六十岁诞辰,我捧来的鲜花:一束是我送的,一束是我代表在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发起追思会的王安忆送的,第三束是代表《我与地坛》的责任编辑姚育明送的。”与会、送花、献词的还有曹文轩、白桦、余华、格非、邹静文、肖复兴、张锲、杨承志、周国平、李锐、徐坤、徐小斌、阿城、郑也夫、钟晶晶、林白、刘索拉、皮皮、林莽、解玺璋、李青、刘孝存、邢仪、牛志强、甘铁生、宗颖、刘惊涛、岳建一、章德宁、濮存昕、顾长卫、蒋雯丽、文洁若等;还有铁生在陕北的“插友”、清华附中的同学以及来自各地的数百位铁生粉丝、在京的媒体记者和从台湾赶来的贵宾。挤挤挨挨,满满一堂。高大的厂房里,人头攒动,鲜花飘香,烛光闪烁,热气腾腾。

史铁生塑像
铁生的至交们站起来向众人回忆他的写作天赋,以及能画画、会针灸、善待人、乐于助人的细节。听过铁生作的“人生就是与困境周旋”讲座的人,站起来动情地说:“七年前,史铁生与我们一起探讨人生,探讨生命的意义,与我们一起经历坎坷和苦难。十年过去了,我们成熟了、坚强了,铁生老师却走了,但他的灵魂和作品与我们同在。正如诗人臧克家的著名诗句说:‘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铁生老师就是这样的人。”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院长鲁景超教授,特地带领一批最好的学生上台,声情并茂地朗诵了铁生《我的梦想》的片断。从天津红十字会赶来的邓永林大夫向全体与会者报告了最新消息,说根据史铁生捐献肝脏的遗愿,已把配型好的脏器移植入一个38岁的患者身上,如今那位患者已能下地走动——会场上响起狂风暴雨般的掌声,声浪几欲把厂房顶掀开。医生说:铁生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一直坚持着,弥留之际挣扎着等到天津红十字会来取器官的大夫奔进医院走向他床边,他才吐出最后一口气,好让所捐献的器官一直处在血液正常灌注的鲜活状态。(只要铁生停止呼吸15分钟,所存器官便完全失去了捐献的意义。)除肝脏外,铁生还捐出了角膜,已使另一患者复明。还捐出了脊椎和大脑,供医学研究。肝脏移植国际权威、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教授动情地对大家说:“史铁生二十多岁就因下肢瘫痪坐到了轮椅上,无法像大家一样站起来走路,但是他的死却让他稳稳地站立起来,还攀上了道德的高坡,成为一个爱人超己的生命典范。”
我听到这儿,眼睛湿润起来,深感铁生的精神境界已臻极致:他悄悄地走了,没有带走什么,只留下爱,把还有用的器官一一分赠给急需的生者,祈盼他们活得更好。啊,铁生,我的好兄弟,我要拥有什么样的语言才能赞颂你如此洁净、如此崇高的灵魂!我抱憾于、痛恨于自己文学语汇的贫乏,笔力不逮,以致不能生动描绘你真实、无私的形象。
我这辈子参加过数以百计的文学集会。从没有像这次以史铁生的名字招引、凝聚来的盛会这样令我热血沸腾、感动肺腑、终生难忘。我同时获悉,两天前即2011年1月2日,海南《天涯》杂志倡议在全国文学界举行追思活动。那几天海南、上海、河北、陕西、湖南、湖北、广东、宁夏、山西、四川、云南、江西、青海等许多省、市的文友们都在举办类似的追思会。听到这个消息,我异常激动。平时看多了文场上德行滑坡、模仿抄袭、争名逐利、钻营评奖等丑行,我心痛楚,不时发出悲观的叹息、含怒的谴责。如今有幸来到这个盛大的会场上,看到了、听到了这一切,使我对播撒真、善、美种子的文学事业,又恢复了信心,又坚定地怀抱起虔敬之心。寒冬腊月里上千人前来聚会,表示要继承铁生的精神,足以清楚地昭告我:人间追求崇高情操的火种,仍在传递、蔓延、燃烧。这最后一次铁生生日party所呈现的动人场景,不正是对人们内心到底崇尚何种文学,崇敬何种品格的一次展示、一番检阅、一种测试吗?
我深受感染,沉浸在798艺术区温暖、美好、亲密无间的氛围里,情不自禁挤开人群,艰难移到后边用玫瑰花枝做别针的留言墙上,拿起金色的签字笔,在一长方黑纸片上留下我的感言:“铁生,你是我们的荣耀,你是我们的骄傲。我们将以你为镜,铭记你,敬慕你,追随你!”
在陕北清平湾
哀思会后,我们组建了由陈建功、王安忆、张炜、韩少功、张海迪、周国平、岳建一等组成的“写作之夜”丛书编委会,编辑、出版了由邵燕祥作序的《生命——民间记忆史铁生》《极地之思——史铁生作品解读》《史铁生说》等专著。为把丛书编得更好,我们决定到史铁生插队的延川县关家庄体验一番。2014年10月14日,编委和插队知青们的车队离开延安大学窑苑宾馆,路过城东宝塔山,驶往延川县。车队离城向东北方向行驶。一路上沟沟洼洼、梁梁峁峁种上了不少树,群山郁郁葱葱,颇为悦目。
坐在面包车副驾驶座上的延川插队知青黑荫贵告诉我们:铁生下乡前参加过街道“红医工”培训班,学会了针灸,能诊治头疼脑热的病。到了村里,他拿着《赤脚医生手册》,带着同住一个窑洞的孙立哲给老乡看病。孙立哲跟了铁生一阵,胆子大了,拿狗做试验,竟给疼得要命的老乡割去了阑尾。他还给难产孕妇动手术,发现自己和病人都是O型血,就抽自己身上的血给她。老乡哭着求孙立哲:“你要倒了,谁来给俺看病啊!”孙立哲看好了许多病人,老百姓称他是“神医”“救命菩萨”。
车子走了一个多小时,抵达延川永坪镇。这儿曾是陕北苏维埃驻地,系红色根据地军政重镇。如今陕北石油公司在镇上建了许多基础设施,颇为热闹。在这儿,已有延川县领导们的车子等在路口迎接。两支车队汇合后,就沿着山谷夹峙的公路,向东开去。左边二三十米外,一直有条河相伴而行。黑荫贵说:“这条清平河,直通关家庄。铁生在几篇文学作品中称它为‘清平湾’。”哦,我们终于来到了心中向往的地方。
车子走了一程,拐过山坡,关家庄村外,立即响起了爆竹声、锣鼓声、欢呼声。砰!砰!砰!叭!叭!叭!咚咚咚!锵锵锵!巨大的声浪震得清平湾山呼谷应、地动山摇。全村乡亲举着“清平湾迎接史铁生魂归故里”“欢迎神医孙立哲重回关家庄”“庆祝知青回乡来”等横幅涌过来。花花绿绿的纸屑在阳光下纷纷扬扬。司机停车,知青们、编委们跳下车,冲入欢迎队伍。我站在路边高坡上,看见迎宾人群里有举旗帜的,有打腰鼓的,有吹唢呐的,有跳秧歌舞的,有唱信天游的,有跑旱船的,有撑彩伞的,有提灯笼的,有背大葫芦的,有手抱娃娃的……曾在这儿插队的女知青,搂着认识的婆姨,互呼姓名,嘘寒问暖。男知青跟一块儿干过活的老汉,相拥相抱,互诉思念之情。人们混在一起,招呼、拉手、推挤、拍打,亲如一家。
关家庄沸腾了。山笑,水也笑,崖笑,林也笑,连秋阳在蓝天里也咧开了嘴欢笑。你感到惊讶,这不大的山村,怎能一下子聚来千多个庄稼汉。你想不到这白毛巾缠头、朴素衣裳包裹、吃着普通饭食的躯体里,潜藏着火山喷发般的热情。不亲临其境的人,怎能想象在陕北山沟沟里,一个平常的日子,竟出现了比闹元宵更红火、热烈的场景。
站在我身边的牛志强,是《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的责任编辑。他告诉我,1984年作品获奖后,他和几个朋友用轮椅推着铁生回过关家庄。乡亲们把他团团围住。一双双粗糙大手抢着把他抱起来。一声声亲切问候,使他来不及应答。一个50多岁、名叫“康儿妈”的婆姨,撩起衣襟抹拭眼角,跌跌撞撞挤进来把铁生揽进怀里,又蹲下去抚摸他瘫痪的双腿,哆嗦着嘴唇说:“心儿家辛苦了,心儿家不简单,这个样子还写书哩!”那回铁生在关家庄住了两天,竟被乡亲们强请去吃了九顿饭。临走那天,村里人给他送了许多土特产,还有鞋垫、铺炕暖腰的羊毛毡。有个泼辣的婆姨,竟要把牵着的小娃娃送给铁生:“送他个小儿吧,心儿家苦哇,咋能成个家啊!?”感动得铁生热泪盈眶,泣不成声……
锣鼓、唢呐、鞭炮声中,人们在拥挤、堵塞的路上慢慢往前挪蹭着、笑谈着,花了半个多小时,才来到医疗站较宽的院子里。那儿院墙上写着一行大字:“知青回家不容易,全村人民欢迎您!”
我们歇了一会儿,喝了茶,吃了老乡做的臊子面,迫不及待去探望铁生住过的窑洞。村外铁生和同学们住的两孔窑洞,属靠崖式结构,坐北朝南,冬暖夏凉。当年铁生和孙立哲等几位同学住东间。如今空在那儿,窗外挂着“史铁生故居”的牌子。我贴近窑洞,从窗户外往里窥看,内有大炕、灶台。炕旁放着些家具。久无人住,蒙上尘土。
窑洞背靠崖畔,顶上杂长着几蓬蒿草。它东边小坡上,有十几株细高的枣树。铁生初来这里,身体壮实,粮食不够饿肚子时,曾爬上枣树摘枣充饥。
我们的领队请关家庄78岁张老汉站在窑洞前给我们介绍情况。张老汉说:分到俺队的20来个学生娃开始啥都不会,不会推磨,不会烧炕,不会上山砍柴。这眼窑洞里5个小伙子砍的柴,还不如一个12岁娃砍的多,这成了村里婆姨们嘴里的笑料。可这些娃娃肯吃苦,经过几个月摔打,锄镰镢耙样样会使,成了好受苦人。张老汉说他教过铁生喂牛。铁生喂牛那个细心劲,玉米秆和草拾掇得干净,和主料拌得匀和,一夜几次起来照料,干活精心。铁生娃为了让牛多吃草,每天早早把牛揈出村子,天黑才回。中午就着泉水吃干粮。娃回队后晚间还要锄草,俺村以前许多人家做柜子,都要花钱请画匠。铁生娃画得好,串门免费画柜子。有天暴雨夹着冰雹落下来,铁生娃在野外,浑身淋湿了,受了寒,腰腿落下了病根。唉,娃在俺村受苦大了,俺们一直想念他……
孙立哲站在他和铁生住过的窑洞前,对大家说:我给村里人治病,是铁生带着我学的。史铁生实际上是我当赤脚医生的领路人。他是我们村里第一个赤脚医生,带着我给老乡看病。我们找到了专治当时正在流行的伤寒的药,然后我们就给病人打针。我那个时候劳动不行,身体也不好,陕北人说话:“这个娃娃受苦——满不行哩。”有时我们在干活的时候,老乡在下面喊:“知识青年,你们谁个能看病哩,快下来!”这时候铁生就让我去打针。经过一个时期的锻炼,治好了一些人的病,我成了被老乡欢迎的赤脚医生。所以我对铁生怀有感恩之情。
同来的延安大学文学院院长梁向阳对我们说:“我的成长受到史铁生文学精神的影响。这次随大伙来清平湾所见所闻,让我终身难忘。”
接着编委章德宁、宗颖、刘惊涛、查建英、柳青以及当年的赤脚医生们排列在窑洞前朗诵铁生写这儿日常生活的《插队的故事》《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的片断。知青画家邢仪拿出纸笔速写窑洞风景。她告诉我们:“铁生最喜欢我在陕北的写生,尤其是那幅《山桃花》。他说,那时整年在山里放牛,到春天山沟沟里还没有绿色,但最先是粉红色的山桃花开了,满沟的山桃花真美啊。这幅画让他想起当年陕北春天的情景。”编委王克明、庞沄等人则唱起了陕北民歌“崖畔上开花崖畔上红,受苦人过得好光景”,歌声调动了叶廷芳编委的兴致。他主动站起来说:“我们前面流淌着清平河。想当年铁生会在月亮出来的时候,到河边看流水。那我就唱一首《小河淌水》吧。”接着他放开嗓门唱起来:“哎……月亮出来亮汪汪,亮汪汪,想起我的阿哥在深山……”唱得委婉动听,声情并茂,余音绕山梁,博得一片掌声。
然后人们排成几行,站在铁生窑洞前合影留念。
在参观村子时,延川人梁向阳对我说:延川多名人,历史上延川籍状元、进士、举人,多如河滩里石头。因《平凡的世界》荣获茅盾文学奖的路遥,就是延川人;曾任《延安文学》主编的曹谷溪,也是延川人。1969年2月到延川插队的两千多名北京知青中,作家辈出。除史铁生、孙立哲外,还有作家陶正,他和高红十合作的长诗《理想之歌》,诵遍大江南北,编入当年的语文课本。
我说:你们延川还出了位陕北剪纸大师高凤莲女士。今年5月,我在北京专程去中国美术馆观赏了”大河之魂——高凤莲大师三代剪纸艺术展”。我被陕北民间艺术的雄浑、大气、创造力、想象力彻底征服。延川东临黄河,世代受到大河魂魄的熏陶。
梁向阳兴奋地告诉我:“高凤莲知道插队知青今日回来,也到了关家庄,我带你去见见面吧。”
我欣然前往。走进卫生院西侧一间房子,见大炕上盘腿坐着一位七十多岁的婆姨。她花白的头发,宽阔的脸盘,红润的面色,硕大的耳朵,慈眉善目,一副祥瑞佛相。梁向阳把我介绍给她,她脸绽笑容欢迎我,拍拍炕沿,说:“请坐,请坐。”我说:“今日意外见到高凤莲老师,实在是幸运。我在中国美术馆看到您的剪纸,太精彩啦。我想问,这手艺是谁教您的?”她笑道:“俺延川妇女会生孩子就会剪纸,上炕剪刀下炕镰嘛。俺这儿女人一多半会这手艺。”我听了心想,有了连绵高原的基础,才能拱出巍巍巅峰。梁向阳向我介绍:“高凤莲心灵手巧,干啥像啥。她担任过民兵连长、妇女主任、村支部书记。还是秧歌队的‘伞头’,村里办喜事时主持‘结发上头’的民俗高手。她是俺县的大能人。”高凤莲叫她女儿刘洁琼拿来一册精装的剪纸收藏集《大河之魂》送给我。我把沉甸甸的剪纸集收进怀里。这是我到延川意想不到的另一份收获。
傍晚离开关家庄前,我独自踱到清平河畔漫步。十月的秋风,掠过远处苹果园、近处枣树林,使空气里夹带着成熟的甜味。温暖的夕阳也西移至村后窑洞边的崖头。清平河拐了个弯,逶迤远去。我望着对面山丘上一块块坡田,想象着当年铁生在这儿揽牛、砍柴时留下的足印和歌声,意识到清平湾记载着他难忘的青春年华,这儿是他心灵的栖息地,也是当代文学版图上一道亮丽的景观。我想起前天在延安大学图书大楼学术报告厅举办的“史铁生的精神世界与文学创作”研讨会。会上韩少功、孙郁、李建军、甘铁生、解玺璋、岳建一、王克明、查建英等人发言之精辟、深刻,是我在北京众多文学讨论会上很少听到的。会议主持人最后邀我上台说几句话。我说:铁生小时候,他奶奶告诉他一则童话,说:地上死了一个人,天上就多了一颗星星,给活着的人把路照亮,让他们在黑暗中大胆前行。铁生相信,每一个活过的人,都能给后人的路上添一丝光亮:也许是一颗巨星,也许是一把火炬,也许是一支含泪的红蜡烛。我愿铁生离去之后,他的心魂会在苍穹里变成一颗亮星,从高空持续照耀着、温暖着、指引着活着的人们……
霞光照红了山坡,黄昏来临,暮色逐渐浓重起来。我从山坡上回到村里,和同来的人乘上回程的车子。当我们的车队,在老乡依依惜别中,缓缓驶离关家庄时,我突然感到:从今以后,铁生遥远的清平湾,对我来说,已不再遥远。
在北京地坛
明初皇帝把天地、日月、星辰、云雨、风雷诸神供在一起祭祀。到了嘉靖九年(1530年)才把众神分开祭奠。于是在南郊建天坛,在安定门外北效建地坛,并在东西郊建日坛、月坛。地坛是明清皇帝每年夏至日祭祀土地神的地方,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400多年后,两腿瘫痪的史铁生摇着轮椅来了。是他的思考赋予了地坛新的生机,注入了新的灵气,使它成为广大读者向往的圣地。
史铁生先后住在前永康胡同40号、雍和宫大街26号,都离地坛南门很近。在长达15年时间里,他向北摇着轮椅,从南门进园,到过地坛每一棵古树下,碾压过那儿每一寸草地,苦思人为什么生,如何去死,为什么要写作?经过反复思考,他想明白了:“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那么还得活着,活着就不得不写作,写作就是为了活下去。他悟透了,人是千差万别的,无差别便不成为人类。人要接受万物的差异:要是没有了残疾,健全是否会因其司空见惯而变得乏味?要是没有了愚钝,机智还有什么光荣?要是没有了恶劣和卑下,善良和高尚如何界定成为美德?是丑女造就了丽人,是懦夫映照了英雄,是众生超度了佛祖。人即便是一株残树,为什么不试着以它不多的绿色,美化周围的土地?为什么不享受病树也有的生命呢?于是,铁生的躯体虽束缚在轮椅里,他的心灵已长出翅膀,飞升到头顶天空,悟透生死,遨游苍穹。他在这古老的园子里,已由残疾者转化为思想者。他轮下碾压的地坛,于是演变为思想翱翔的天坛。
史铁生于1991年在《上海文学》发表了《我与地坛》,媒体好评如潮,迅速被编入语文课本,一时洛阳纸贵。之后这个古园就成为文学界的一块地标。作家韩少功说:“1991 年的文学即使只有他(铁生)的一篇《我与地坛》,也完全可以说是丰年。”当时全国有许多作家、许多读者都学习、讨论、赞美这篇作品。例如北大、人大、清华附中、北京四中、北师大二附中的学生们,都开过《我与地坛》的研讨会、朗诵会、学习会。
今年春天,出版过两部长篇的云南作家林青打电话给我,说要到北京来,除了游长城、故宫、颐和园外,邀请我陪她参观我住家附近的地坛——因为是史铁生的作品,给了她力量,摆脱疾病和离婚的阴影,不再轻生,活下来努力写作。
2017年3月19号,是个春暖花开、柳丝飘拂的晴日。我带着林女士沿着铁生习惯的路线,来到地坛公园南门。我指指南门外西侧的金鼎轩酒家,告诉她,那儿是“创作之夜”丛书编委会经常讨论史铁生选题的地方。进入园内,皇祗室外两株百年巨柏迎接我们。向东走去,面前是一大片森然的柏林。林青问我:“为什么地坛内种植那么多柏树,内坛红墙全被苍绿的柏林包围?”我说:“我国古代封建王朝均定有社树,犹如今日的国树、市树。‘夏侯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明人延续殷商之礼,种植大片柏树,反映了先人对大地上绿色环境的企盼。”
我们沿着方泽坛东侧红墙和柏林之间的夹道向北走去。有一株柏树粗大得两个人都抱不住,显示了这座古建筑悠久的历史。柏林空地上,有人安闲地打着太极拳,有个姑娘坐靠着长椅背埋首读书。绕过红墙往西,见北郊一所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们,围住一方空地,正在抑扬顿挫地朗诵史铁生的作品。我和林青站停下来,怀着浓厚的兴趣,和围观的人群一起听完朗读。接着买票进入红墙内,踏着一级级石阶,登上高高的、正方形的坛中之坛。坛中央置一黑色大香炉,令人遥想起往昔皇帝亲率百官,在此鼓乐齐鸣、钟磬咸响、焚香宰牲、祭拜地神的盛大场面。从坛顶下了台阶,走进南边的祗神室,细看挂在室内柱上的编钟、玉磬等乐器,观赏玻璃柜内的名瓷祭器,按序察看摆放在桌上的先帝们、神仙们的牌位。徐行一周,走出祗神室,迎面左右耸立的两株白玉兰正开得繁盛。不时有羹匙形的花瓣飘落下来。我捡起一片落英,闻闻,有微香。从方泽坛出来,在方泽轩北一排银杏旁的木椅上,我们坐下来歇息。林青打开精致的手提包,拿出一份《春城晚报》的剪报给我看,说昆明一个因车祸致残的中学生看了铁生的《我与地坛》后,克服困难,写了一篇题为《人生的拼搏》的文章,夺得了征文大赛一等奖。可见铁生作品影响之广大。
我们面前的宽道上,人们你来我往,各自走着自己的路。有三个老妇人说着闲话慢慢踱过去。一个跑步的人,从西边跑向东门去。两个摇轮椅的残疾人向北门驶去。其中一个驼背的矮个子,对另一个残腿的同伴说:“史铁生那时候这里是个荒园,杂草丛生,危墙坍塌,并没有目前这样干净、齐整。”腿残者说:“荒凉也有荒凉的美。过分整齐、洁净,倒反显得单调、划一。”
我和林青听了转脸对视,莞尔一笑——想不到那残腿者竟说出这样非同寻常的话来。
一只灰鸽子从身后柏林里飞到路面上,它捯动着小细脚,伸缩着小脑袋,一路啄食过去。还有一只喜鹊展翅飞到银杏树梢上,翘起长尾巴吱吱喳喳叫唤。从远处传来若有若无的口琴声。在这安详温馨的氛围里,我和林青想到铁生母亲来到这园中树林里焦灼寻找儿子的情景,回忆起文中提到的那对老夫妇,那个爱唱歌的小伙子,那位腰间挂着酒瓶、走一程喝一口酒的老头,那个具有天赋却屡遭不幸的长跑者,以及一个弱智的小姑娘和保护她的哥哥……
太阳从西边照射过来。我看见西门那边有十来个男女青年围成一圈共踢一个大毽子。他们单踢、交叉踢、前踢、后踢、联接踢,技巧娴熟。他们的腿脚蹦跳起来迅捷如猿猴,落地时轻盈若燕雀。看他们用脚欢快自如地踢毽子,我对林青感慨道:“对于健康的人来说,跑路、蹦跳多么平常、简单;可是对于两腿瘫痪的铁生来说,路只能在他轮下。整整十多年,铁生摇着轮椅在这古园里徘徊,思考着宇宙、时空、天地、古今、生死,最后获得了顿悟,给人以永久的启迪。”
林青说:“铁生失去了用脚走路的能力,却获得了深邃思考的机遇。上帝关了他一扇门,却给他开了一扇窗。‘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他在精神上比我们肢体健全的人还更健康。”
我说:“作家们对铁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铁凝说,‘史铁生的精神品格和他的文学创造,是中国当代文学理应珍视的宝贵财富。’莫言说,‘在他面前,坏蛋也能变成好人,绝望者会重新燃起希望之火。’陈建功说,‘他的涅槃之路,烛照了我们,使我们自惭形秽。’张炜说,‘纵横交错的声音震耳欲聋,却难于遮掩从北京一隅的轮椅上发出的低吟。’而我认为《我与地坛》是中国20世纪最佳美文之一,是名篇中的名篇,经典中的经典,故文章虽长,我还是决定把它编入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世界美文观止》之中。我在导读中说它‘思想深刻,沉郁苍凉,感恩忏悔,震撼文坛’。”
林青感谢我,说:“您送我的这本《世界美文观止》,现已成为我的案头书、枕边书,每晚看一篇,作为安睡前的精神享受。”
我告诉她:“‘创作之夜’编委会,还有许多读者,都呼吁在地坛立一座史铁生的青铜塑像,但申请报告递上去之后,至今没有得到同意的批复。这令人费解,北京是全国文化中心,这应该是合情合理的事啊……”
临近傍晚,地坛里的游人逐渐稀少,一切都安静下来。我望着夕照中的古园,感觉红墙在沉思,苍绿古柏在沉思,黄琉璃瓦在沉思,白石方泽坛在沉思。不,这北京硕大无比的整个地坛,像是一位四五百岁的哲学老者,在晚霞映照的蓝天下,陷入亘古的思索……
离开地坛西门那座金碧辉煌的庄严牌楼时,林青女士跟我拥抱、告别:“张老师,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会一直铭记这次地坛之行。谢谢您陪我游园!”
2017年3月19日是星期天。回家之后,我就把先后在798艺术区、在陕北清平湾、在北京地坛的所见所闻所思,一一详细记下来,希望它成为当代文学史的资料,妥为保存。
最后请允许笔者借用俄罗斯伟大诗人普希金名作《纪念碑》中的诗句,作为本文的结尾:
“不,我决不会完全死去:
我的灵魂在遗留下的诗歌中,
将比我的骨灰活得更长久。
…………
我所以永远能被人民挚爱,
是因为我曾用诗歌,
唤起过人们善良的感情……”
2017年3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