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曙:在我们对话之时,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正在评审,中国当代文学云端上的红门又一次缓慢打开,当代文学体制巨大而锈蚀的红色轮轴依然在转动。而同时,一部神幻影片《捉妖记》正创造共和国的票房纪录,超过五千五百万观影人次抬起了二十亿元的票房。影像专制的时代,文学在败退,在失效,文学作为建构世界的方式正被更多的人放弃。余亮兄,你成名于80年代中期的诗坛,新世纪以来又建树于散文和小说创作,以你三十年的文学旅程以及对文学多层次的深入探寻,你觉得,在今天,继续煮字生涯仅是作家们的积习与惯性吗?文学的意义和价值何在?
庞余亮:此次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五部作品我读过四部,没有获奖的,我读得更多。有的小说,我是读进去了,还重读过一次。有的小说,我承认我没有读进去。这不是作家的问题,也不是读者的问题。年轻的时候,也就是80年代刚刚写诗的时候,是多么渴求一举成名的光荣。可越过中年,就越清醒。属于自己的边境线不长,甚至很短,不会超过一根鼠标线。有几次,我和孩子们提起80年代的那些诗人,除了海子,连顾城也是不知道的,更不用说梁小斌等人了。失败,放弃,或者遗忘,是每个作家注定的命运。而我心中的优秀作家,恰恰承担了书写失败之书的使命。三十年过去了,我们身边的文学人口一天天流失,但文学面对的问题一点也不比三十年前少。用固执己见对付纸背后的虚无,比在泡沫中幻灭更有价值。所以,继续煮字生涯,不仅仅是积习与惯性,更多的是文学蜗牛所背负的“壳”,白天三尺,夜里两尺。或者是白天两尺,夜里三尺。在人性的深井里,文学的意义就是能够在幽暗的深井中看到白天的星星。这比喻似乎有些陈旧,但每天的星星都是不一样的,尤其是白天的星星。
孙曙:谈谈你的小说吧,我脑中又浮现出你的小说处女作《追逐》中在清晨带露的庄稼地里赤着身子奔跑的“父亲”,你的长篇小说《薄荷》中卖咸菜的尼姑慧清……请原谅我的阅读偏好,我喜欢的不是循规蹈矩的叙事,而是能将想象给文字插上双翼飞翔又带来人类新鲜的生活经验的叙事,余亮兄,你的叙事有偏好吗,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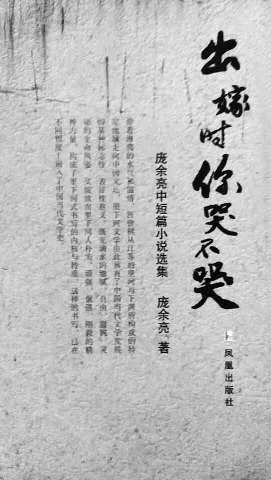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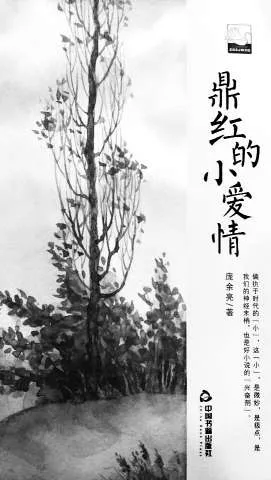
庞余亮:可能是长期从事诗歌写作的原因,我喜欢在小说的叙事中冒险。虽然这样的冒险可能是徒劳的,要知道,在太阳下,没有任何事物是新鲜的。小说的叙事艺术也不例外,我们以为是新路,其实是踩在了别人的脚印上。但既然从事了小说写作,那就得尽力去完成自己。比如,在小说叙事中找到自己的叙事腔调。《追逐》《薄荷》,包括《秒史》《最完整的清晨》,我都有这样的追求。“循规蹈矩”是体力活,而“双翼飞翔”就不仅仅是体力活了,而需要匀称的身体和有力的翅膀。《秒史》和《最完整的清晨》这两篇小说,我用了近半年的时间,打磨,再打磨,把脂肪化为肌肉,把诗性化成羽毛。这样的偏好赢得的是“小众”,但很快乐。这样的快乐,秘密,有“小偷”般的快感——不知道这个说法准确不准确。
孙曙:创作者是偷得上帝“创世”之功的小偷,在上帝愕然并失落之际快乐。余亮兄,对于你的一部分小说,我曾经用过“少年叙事”这个概念,“暴力”“性”纠缠砍削中裸露的成长,我可以列出《十字正吊》《白鲸,白鲸》《黄毛子,短颈项,越打越犯犟》《为小弟请安》《向日葵》等等一长串名单,《薄荷》也是,你甚至将这类叙事追摹到历史中,比如《一根细麻绳》,叙述12岁的烈士遗孤如何被教会杀人,我认为这是你在当代叙事中最具独创性的部分,当然,近期你的小说创作已经离开“少年叙事”了,回头看,你怎么看待这部分创作?
庞余亮:苏童说过,小说家只需要18岁之前的经历做素材。我在那个四面环水的村庄生活了15年。贫困、窘迫和屈辱。这是我的秘密成长史。我做梦都想逃离。之后我出门求学,寒假和暑假又必须回到村庄,那些疼痛的历史一次又一次重现。那弥漫着人畜粪便气味,那个充斥着脏话俚语的村庄,那个大地上破败的、陈旧的,却又是倔强的低矮房屋,全是我内心的鱼骨。有评论家说:“村庄像一个巨大而又隐秘的胎盘,至今仍将脐带连接在庞余亮的身上,源源不断地向他输送着养分。”是的,胎盘。在那样的胎盘里秘密成长,永远不会长大,就像是铁皮鼓中的主人公,暴力和性,在《十字正吊》中,在《为小弟请安》中,在《向日葵》中,在《一根细麻绳》中,“暴力”驱使着我的笔向更黑更深处前行,所以,编发我小说处女作的毕飞宇先生说:“你的小说漆黑一片,里面完全没有任何光亮。”再后来,你又发现了这个问题,你说我的里下河是“在汪曾祺士绅的里下河之外的,是贫苦农民的里下河,是乡野小子的里下河,是另一个中国。”说实话,我是多么喜欢汪曾祺,喜欢他的《大淖记事》《受戒》《故乡的食物》,可要我写出那样的里下河,等于我要去完成姚明式扣篮一样不可能。
孙曙:这些小说中,《纸龙船》是一个顶点,一个被亲人和村庄抛弃的小水鬼雨来,架着送鬼的纸龙船飞驶,虚实叠映,人鬼莫分。余亮兄,在日常生活中你是一个温和的谦谦君子,怎么在叙事中这么狠?雨来的名字和小学课文《小英雄雨来》中主人公同名,有意的吗?
庞余亮:毕飞宇在其《玉米》创作谈中说到“我们内心的鬼”。那“内心的鬼”叫“人在人上”。人在人上——在村庄生物链最底层的我们何尝不需要“人在人上”?《纸龙船》中的雨来,的确套用了《小英雄雨来》的主人公名字。在我的童年,值得表扬的总是那些贴在墙上的榜样好少年,比如雨来,还有和偷辣椒地主斗争的刘文学,和周扒皮斗争的高玉宝,草原英雄小姐妹。他们被描述得浓眉大眼,聪慧勇敢,完全是我们“鼻涕虎”“惹祸精”的“对立面”。如此的“仇恨”也一定存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内心中,永远有那些被抛弃的,被孤立的,被凭吊的,就如小水鬼雨来一样,妄图披着“好孩子”的名字,却必须承受着坏孩子的命运。
孙曙:当然你的叙事视野开阔,面向更宽广的现实的“底层叙事”也占了很大部分,在《鼎红的小爱情》的封面有你近乎宣言的几句话:偏执于时代的“小”,这“小”,是微妙,是极点,是我们的神经末梢,也是好小说的“兴奋剂”。这些小说呈现了存在的卑微,粗砺、不幸、刻薄、伤害、麻木、腐烂以至恶臭,是“黑暗照亮的叙事”。余亮兄,原谅我问得尖锐点,当“底层叙事”成为时下创作的一种潮流,你的坚持是什么?
庞余亮:王德威先生说:“小说是想象中国的方法。”我从不认为我是一个“底层叙事”者,我写的是我的中国。在我的面前,有很多优秀写中国的汉语小说,比如鲁迅的《阿Q正传》,比如萧红的《呼兰河传》,比如莫言的《欢乐》,比如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比如毕飞宇的《青衣》和《玉米》,等等,他们用出色的才华和艰辛的努力重新想象了我们的中国。他们都是小说的君王,撒豆成兵,点石成金。每次翻阅那些优秀的汉语小说,都能够感受到它们的根系之深和枝叶之繁,对我来说,它们都是我提神的森林氧吧。我多么想写出我自己的中国,而作为一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出生,八十年代成长,跌跌撞撞地闯进了新世纪的小说写作者,远远不够的恰恰就是对自己的完成。算起来,我已经先后走过了两个世纪,五个年代,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是既年轻又苍老。这样的想法就令我多了中年焦虑感。写作是缓解这种焦虑的好方法。《鼎红的小爱情》中有篇我自己喜欢的《越跑越慢》,这个题目是修改过的。原先在春风文艺出版社《布老虎中篇小说》上发表时叫《杀妻》。从《杀妻》到《越跑越慢》,我是有野心的,而这样的野心却是如此的言不达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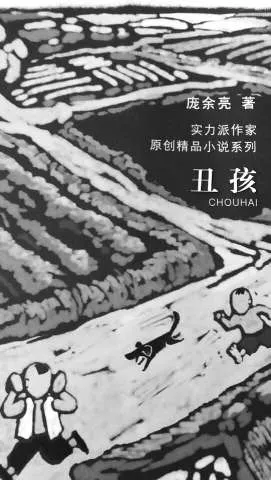
孙曙:对你来说,你写的中国也可以叫做“里下河”,你曾经说过,“我的心中,活跃着一整座的县城”,这座县城是你的故乡里下河之地兴化,其实一个人一辈子是走不开故乡的,当理论家们把汪曾祺到毕飞宇包括你在内圈出一个里下河文学流派,你认可吗?你觉得故乡和你的文学之间有何连接?
庞余亮:我记得你的《盐城生长》,那洋溢出来的不是河水,而是海水。15年前,我从里下河来到了长江边。河边也好,江边也罢,心中的故乡才是文学的大海。任何一个文学流派,离不开文学的本质,向文学致敬的流派,才是最有气象的文学流派。对我而言,我很清醒,不要去做顺流而下的“浪花”,而想做一个有淹没一切欲望的“漩涡”。
孙曙:我还注意到你关于小说创作的另一句话:相比诗歌和童话的创作,我感到我陷在了小说的围墙中,我看到的不是彩虹,而是遍地的碎玻璃。围墙与碎玻璃的比喻令我惊讶,对于你,叙事有这么压抑与艰难吗?
庞余亮:诗歌和小说,对于我来说,犹如一张纸的正面和反面。在创作小说之前,我在诗歌和童话领域里自给自足,很快乐。后来到了小说领域,先后创作发表了200多万字的小说作品,越来越感到小说的辽阔和苍茫。苍茫之余,就是自我的压抑。这是“不甘”酿成的后果。如此的后果,也令近几年我的小说叙事变得枯涩艰难。有人说是创作的瓶颈,我自己认为不是瓶颈问题,而是只“实心瓶子”!还没有“开窍”呢!
孙曙:叙事是门技术活。余亮兄,我倒是看着你的小说在开窍呢,你一直讲求叙事艺术并且独有建树,在每一篇小说中,都能够看到你对叙事的推进。你的小说叙事往往采用对位的方法,故事中套着对位的故事,《螃蟹为什么颤抖》中三姐妹的婚恋复合着父母的婚姻、《越跑越慢》中唐王高的婚姻生活复合着他的犯人苍蝇屎和他姐姐的婚姻生活、《鼎红的小爱情》中鼎红隐秘的爱情复合了张红霞与张定国隐约的感情、《秒史》中秒的成长复合了他父母的童年;在故事的对位之上还有虚与实的对位,文本中会安排一个贯穿的意象或场景成为象征,如《螃蟹为什么颤抖》中的螃蟹,《越跑越慢》中唐王高跑步的梦与幻觉,《鼎红的小爱情》中的馒头等等,这些对位叙事的复合形成了文本丰富的织体。我越来越觉得,你的小说,虽然叙事越来越向现实的深广敞开,在叙事结构上确是越来越紧致的内在化,牢牢地牵引着叙事向狂欢的或是反讽的结尾驶去,这种内在化的叙事结构与人物、情节、内涵紧密粘连。当然,作为阅读者我很可能是郢书燕说,余亮兄,具体说说你在小说艺术上的探求。
庞余亮:短篇小说讲速度,而中篇小说的容量相当重要。在《螃蟹为什么颤抖》中,核心是家人与外人的陌生感,老丈人逼着女婿们为小舅的新房卖单。在《出嫁时你哭不哭》中,暗结珠胎的女儿纠缠在传统风俗的履行中。在《秒史》中,秒的名字意味深长。在《十字正吊》中,在《和痞子抱头痛哭》中,都有我设置的叙事“悬崖”,沿着生活的台阶拾级而上,可到了悬崖上,却无路可走。小人物在新时代中,总是越跑越慢。写作犹如“雕塑”,要去掉多余的部分,留下有价值的部分。可能我“雕”的工夫多了,而“塑”的部分少了,小说探求之路还没有走通,“艺术”之誉更谈不上了。
孙曙:在《最完整的早晨》与《追逐》中,明显地体现了你的小说创作的另一些鲜明特点:那就是诗性与寓言化,这也是你有意为之吗?
庞余亮:我记得你说过:“《最完整的早晨》就是《阴×(男根)独白》。”的确,这小说的叙述者就是“男根”。男根如每个少年,热情过,不安过,奔腾过,却是压抑的,疲劳的,最终,会有一柄剃须刀等着他,成为网上的“太史公曰”。我有想法的,但不知道读者有没有感受到。另外,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这个短篇本来是长篇的构架,我发现我的力量还没有达到。如果有一天,那力量“附”到我的身上……
孙曙:《最完整的早晨》是颗神秘的种子,我期待它使你燃烧起来日夜不宁,长成陈忠实说的“死后可以当枕头的书”。我们说说语言吧,很多人喜欢你《乡村教师手记》《丑孩》《薄荷》等早期写作的语言,清新如画,风格鲜明,但你近年来的小说似乎越来越有意识地避开那些单纯优美的风俗画描写以及相应的明丽晓畅的语言,是这样的吗?出于什么样的动机?
庞余亮:每个作家其实不仅仅是一种人生,而是有无数个人生。早期的书写是清澈的,但到了中年,必须是混浊的雄厚的。有时候,“多面性”中就有窑变的可能。
孙曙:本期新作《手执钢鞭将你打》,小说的情节导向与内涵动机不明确了,叙事有了更多的毛边,单向的线性叙事被弃置,作者的叙述点放在了高志国的“生活场”,完整细密地切入生活的混沌,这是你创作上的新追求吗?
庞余亮:越向前走,创作的问题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一个人的写作是瞒不了自己的,一个问题解决了,另一个问题又随之产生。更多的缺陷不是缘于书写问题,而是缘于自己和文学的约定,每一个写作者都必须完成自己。赵广超先生有一本解读《清明上河图》的书,读完很受启发,开封是张择端内心的开封,而我自己的内心呢,面对自己的“开封”,怎么还没有强大到把我生活过的五个年代两个世纪放到内心的疆域中呢?也许,《手执钢鞭将你打》就是阅读《清明上河图》之后的新收获,我希望我在今后的小说中能够完成问题的斗争与解决(或者和解)。
孙曙:你的“和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的文学情怀?在你的文学情怀中,也惟有文字,才能怀抱世界和人心。余亮兄,近阶段有什么样的创作计划?
庞余亮:“怀抱”一词特别妥帖。我一直说有一个长篇等着我。肯定不是已经出来的两个长篇。这两个长篇,一个是2005年面世的《薄荷》,一个是2008年面世的《丑孩》。我在写作这两个长篇的时候是有野心的。但我的身上似乎有一种不好的东西,那就是“自我否定”。每次我写到某种很好的状态,我就有破坏这种状态的冲动。然后,我会真的破坏这样的状态。接着,会花很长的时间去寻找下一个好状态。周而复始,成了我写作生涯的“恶之花”。我正在写一个长篇,被搞得焦头烂额,我希望它能够无限地接近我的“文学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