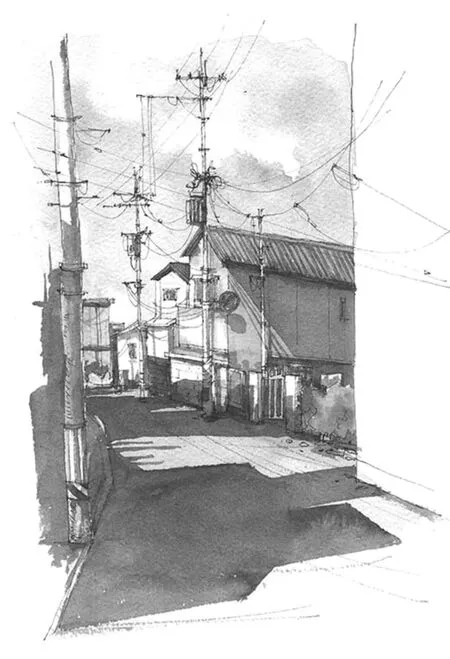
托 盘
刘百顺到高丕发家做客。刘百顺是村支书,常到别人家做客。高丕发留支书吃夜饭,刘百顺想了想,答应了。高丕发的老婆给他们做饭,炒一个菜,用托盘送到桌上,下去了,又炒一个菜,用托盘送到桌上,又下去了。女人每送一个菜,刘百顺就盯一盯女人手里的托盘。女人很美,他却不盯女人——女人也不看刘百顺,但她知道刘百顺关注的是什么。两个男人吃菜、喝酒。不搭理女人。他们吃两三口菜就碰碰杯,仰脖喝那么一盅子。吃两三口菜,碰碰杯,仰脖又喝那么一盅子。盅子不大,白瓷的,比大拇指大那么一点点,酒也不是什么好酒,是散酒,是村里某人自己烧出来的酒,一升子玉米换一斤酒。一斤酒足够刘百顺和高丕发两个人喝这一顿了。他们酒量都不大,只是好酒而已。
高丕发的老婆给他们用托盘送了第四个菜了。天已经快黑了,酒也喝得差不多了,两个人都晕晕乎乎的,有了一些酒意了。刘百顺盯着女人扭出去的背影,突然感叹一声:“你老婆,人长得不错!”
“不错?”
“真不错!我要是有一个这样的老婆就好了,这辈子就没啥想头了。”
“中看不中用。你觉得她好?咱换了!”
“嗯?”刘百顺没有搞明白。
“我是说,你觉得我的老婆好,我还觉得你老婆好哩,咱们换了老婆成不成?”高丕发跟刘百顺是老表,他不怵他这个老表的支书身份,“我这个老婆,做饭炒菜,倒是有一手。”
“真换?”刘百顺想了不到半分钟就答应了:“换了就换了!”
那时新中国刚成立,高丕发的老婆是地主家的女子,凤凰落架不如鸡,她也不是什么娇小姐,虽说是个小姐,却也得干活,她在那个地主家庭时,也要做饭、炒菜、做家务,天天如此。如今地主家的女子身价更是一落千丈了,能嫁给高丕发就已经不错了,就这,高丕发还看不上她哩。高丕发嫌她不会干农活。
“你答应换?”
“我没啥不能答应的。”
“答应换,你走时就可以把她带回去。”
“你也得去。”
“又不必送亲,我去干啥?”
“把我老婆带回你家来呀!”
高丕发一拍脑门子:“哦,也是,也是。”
刘百顺站起来就去了厨房,他到了厨房,站在女人身后小声问女人:“高丕发要跟我换老婆,我也想换,你去不去?”
女人看了刘百顺一眼,不说话。
“那就跟我走!”刘百顺出了厨房,女人跟在刘百顺后面,也出了厨房。两人一同出了院子。
“等我一下!”高丕发追了出来。
“干啥?”刘百顺问。
“我把你的女人领回我家来。”
这回轮到刘百顺拍脑门子了:“也是!也是!”
都出了院子了,都走在出村的路上了,女人突然发声:“等我一下!”
两个男人对视一眼,眼里都对对方说,等一下就等一下。也等不了多久,也不赶这么一点儿时间。
女人反身,小跑进屋。不一会儿就出了屋,来到他们身边。
“走? ”
“走! ”
女人手里多了那只送菜的托盘。
“她从娘家带过来的。”高丕发这么跟刘百顺解释,“她嫁过来时,就带了个这!”
“哦!”刘百顺说。
三人各揣心事,一路没话。
好在两个村子相距并不远。
到了刘百顺家,刘百顺跟女人说明了情况。
刘百顺的女人干农活是一把好手,家里地里都靠她,人也是个直肠子,缺点是长相差了些——她倒也爽快:“我走也行,我的儿子,我得带走。”刘百顺的女人已经给刘百顺生了一个儿子了,儿子已经两岁了。
“儿子也要……带走?”刘百顺停了一下,才说,“想带你就带走吧。”
这两个男人都是真男人:想到了,就能做到。
那个跟过去的儿子改姓了高。刘百顺的女人后来给高丕发也生了一个儿子。
高丕发的女人给刘百顺一口气生了五个儿子,一个女子也没生。
刘百顺活了七十八岁。刘百顺死后,有人找上门来,要买那只托盘:“你开个价!”来的人不止一个,不止一次,不止一拨。他们都是走乡串户的小文物贩子,赚也赚个工钱,不会更多。五个儿子都先后劝过老母亲:“也没什么用,卖了就卖了吧?”她只回头看一看劝她的那个儿子,也不作声。
这个女人幸亏跟了刘百顺:刘百顺当了一辈子支书,后来大大小小的运动,谁也没敢提支书女人那个地主女儿的身份。她活了九十一岁,二〇一六年才死,她也是两对夫妻中最后一个离开人世的。她要是跟高丕发过,运气肯定不会这么好。
女人死了,托盘还在。
这里的人,不兴陪葬:死者生前喜爱的物件,能烧的,烧“头七”时,家人就拿到墓地来,在死者的坟前,烧了,也算是一种陪葬吧。
那只托盘,也这么烧了,尽管儿子们没有一个舍得烧了托盘的,却还是烧了——小文物贩子再也没什么可惦记的了。
有病的女人
这个女人有病,说的是气管炎,但好像不只是气管炎那么简单。村里人都认为她肯定还有别的什么病,但她到底还有什么病,却是无人知晓,也不便于打听,问了,她家的人,无论是谁,也无一个肯说的,他们的回答往往千篇一律:“就是一个气管炎嘛!”生产队时,她的男人是队长,她可以不出工,也是从来不出工。她的每一天都是这样度过的:起床后吃饭,吃完早饭煮中药喝中药,喝完中药吃午饭,吃完午饭煮中药喝中药,吃晚饭,吃完晚饭煮中药喝中药,睡觉。每天如此。在吃饭与煮药喝药的间隙里,她从不走出自家的大门。大门对于她,仿佛是不存在的。
这个女人从来不做饭,不洗碗洗锅,不喂猪,也不给家人缝缝补补,她生了两个儿子三个女儿,做饭喂猪洗洗涮涮都是两个大一些的女子的事,她幸亏生了三个女儿。她的儿子女儿,大一些的在读小学五年级和四年级,小一些的在读小学二年级和一年级,最小的女子还不到上学的年纪。学校就在村里,出门绕过偏房,穿过阳沟,就到了村小学的操场边,从她家后门出来也到了村小学的操场边,后门出去,就是厕所。专门挖开那么一个类似于狗洞的后门,只是为了让她上厕所方便些。后门也是她专用的门,她打开后门上完厕所,后门就从里面闩上了。那扇后门几乎从来没有对孩子们打开过,孩子们都是绕过偏房穿过窄窄的阳沟去上学、溜回家。这是他们最近的路了。两个较大的女子也是这么来回走的。她们总是做了早饭吃完早饭才会急急忙忙去上学,课间回来,母亲已经吃过了,她俩就分别地,洗碗的洗碗,喂猪的喂猪。上课铃响了,又急匆匆扔下手里的活儿,穿过阳沟去学校上学。她们的两个哥哥都不用这么跑,他俩课间也不怎么往家里跑,跑回去也不用做什么,仅仅是看看。做家务是女人的事、女孩子的事,不是男人的事、男孩子的事,习惯就是这样。
前面说过,这家的女人有气管炎,她的呼吸像用水烟锅抽水烟,也像猫睡觉——她喉咙里总是“呼噜噜噜”“呼噜噜噜”响。她似乎也很冷,也怕冷,无论夏天冬天,她总是坐在火塘边,火塘里总有一堆忽明忽暗的火,她总是坐在一只小木凳上一边打盹儿,一边煮中药,一边在烤火。她偶尔也在下午阳光强烈的时候,出门坐在院子里或屋檐下,晒一会儿太阳,但时间很短,不会超过十分钟,之后,她仍然回到火塘边,打盹、煮药、烤火。从未见她走出自家的大门,她似乎更喜欢屋子里的暗。外面光线越强,她家屋子越暗。她的最小的女儿要么在院子里独自玩耍,要么在上课的时候,偷偷跑到学校的操场里去,独自玩耍一会儿。她要是去了学校的操场,下课后,往往会被两个姐姐揪回自家院子里来。
她一脸灰暗,全无活力。她的男人却长得高高大大端端正正的,是村里头一名的美男子。她的男人下工回家,除了给社员们开一个大会,天黑之后几乎不出门。她的男人对她客客气气的,恭恭敬敬的,村里从无有关她男人的一句半句闲话。
后来,先是她的大女儿不想上学了,回家专门做家务。接着,她二儿子也不想上学了,给生产队放牛。退学是孩子们的自愿行为,无人劝退也无人拦着。上学是很正常的事,退学也很正常。那时许多孩子不上学读书,或者,许多孩子读不完小学就不愿读书了,就退学了,没什么好奇怪的。
后来就包产到户了。包产到户后,她还那样。她的生活似乎永远不会变。变了的似乎只是生了五个孩子后,她的队长男人请来了卫生院的大夫,专门给她放了节育环。她从此就再也没有生过孩子了。
包产到户大约五年后,她死了。这是大家预料中的事儿,谁也不奇怪,谁也不惋惜,人们都说她“还是死了的好”,仿佛她是十恶不赦的人。她当然不是那样的人。她死了十多年了,她的男人都已经六十开外了,才经人介绍又找了个老伴。她的男人找老伴的时候,她的儿女们,该娶的,娶了,该嫁的,嫁了。空荡荡的家里只有她男人一个了。
她死之后,她家那个似乎多余的后门,也给男人砌了石墙抹了泥,又堵死了。
她的男人找了老伴之后就去了新老婆居住的那个村。只是,每逢她的忌日,男人总会独自回到村里来,带一些纸钱,到她坟头烧了之后,男人又在坟墓一侧坐下,一坐就是一天。天黑的时候男人才会再一次回到那个空荡荡的家里,独自睡一晚,第二天天不亮就走了。
到他新老婆的那个村子,路比较远,他要走好几小时才能到。他的新老婆,他从不带她,去她的坟头。
守在夜里的女人
男人好串门,吃了晚饭丢下碗,用手抹抹嘴,站起来就走了。她不用问,她知道他又要去串门了。她一直准许男人去串门。冬天本就没什么事做,冬夜又这么漫长,不串门,在家又能干什么呢?老夫老妻的,早已没有多少炕上的热情了。那时村里还没有照上电,也没个电视什么的,用来打发时间,不串门就没什么好干的了。她就是这么想的。再说了,男人要是去串门了,就会猫在别人的家里,跟一帮男人打扑克,也就省了家里的煤油了。男人出门之后,她才洗碗刷锅,这些都要尽快做,赶在天黑之前,做完。天黑前做了这些了,这一个晚上,她就用不着再点家里那盏唯一的煤油灯了。那时,一个家庭,点灯的煤油是一笔很大的开支。
洗完碗筷刷完锅,再把刷锅水烧热了,给猪烫猪食。刷锅水里有一些饭碴子,猪在冬天能吃的却一直都是糠。对猪来说,涮锅水就是细粮了,倒掉当然太可惜,也是不可能的,猪吃了也就物尽其用了。
给猪烫完了糠,她最后才会把锅洗干净。洗完锅,天也黑尽了,她也可以松一口气了。
男人出去之前,几个孩子都急急慌慌吃了饭,匆匆忙忙丢下碗,去玩了。男人和孩子们什么时候回来睡,她心里没底,却也是用不着管他们的了。
休息一会儿之后,她又接着烧炕。先烧孩子们睡的炕。先烧的炕,总是先热。孩子们会回来得早一些。她最后才烧她和男人睡的炕。烧炕的时候,顺带着,也就烤了火了。山区的冬天总是太冷,不烤火是不行的,好在整个冬天,没事干的时候,她都在背柴,家里不缺柴,但柴毕竟是花了功夫花了力气才背回家来的,能省一点就得省一点。
山也大,沟也深,山脚下的村子,晚六点一过,天就已黑尽了。她烧完炕,往往已快九点了,这个时候,村里,别的女人都已经睡了,她不。她把身子转移到厅房的火塘边,加几根柴,把火烧起来,又在火焰上方的钩子上挂一个烧水壶,一边烤火一边烧开水。热水灌在开水瓶里,今晚洗脚,明早洗脸,都用得着。她安安静静地烤火,安安静静地,等时间流逝。是火就有亮光,有了这点儿忽明忽暗的亮光就已足够了,煤油灯仍然是用不着点的。
男人无农活可干,女人在家却有做不完的家务。她有些困了,因为整整一天的累。她困还因为已经到了该睡觉的时候了。
她不睡。迷迷糊糊中,她的左肩和左边的头、脸,都不知不觉靠在火塘边的墙上了。迷迷糊糊中,她听见去玩耍的孩子们陆陆续续回来了,但她用不着搭理他们。他们都已经十来岁了,会自己倒水洗脚,上炕睡觉。她继续把左肩、头、脸,靠在墙上,继续迷糊着。孩子们的一举一动她都是知道的,却也是不用多一句嘴的。
最后回来的大儿子洗了脚,回了睡屋,又转来,轻轻推了推她的肩:“妈,你还是先睡去吧。”
“你睡去吧,甭管我。”她温暖了一句。
大儿子犹豫了一下,俯下身子,把火塘里残留的柴拢了拢,让火明亮了一些了,才又出门,回他们的睡屋,睡了。大儿子出去后,把厅房的门也轻轻地关上了。
很久之后,火塘里的柴“扑通”一声,轻轻塌陷下来,火光明显地又弱下去一些。屋子里更暗了。她轻微动了动身子,却已不想再管火塘里的火了。她微微睁了一下眼,外面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小风从门缝里缓缓吹进来,让她觉得全身冰凉。
村子里安安静静的,偶尔传来几声隐隐约约的狗吠。
男人去串门,也该回来了。
男人去串门,不到后半夜是不会回来的。
男人去串门,多半都是跟村里老老少少的男人们,围在一起打扑克。他们玩的是一种名为“升级”的扑克游戏。不是赌博,只是玩玩。他们谁也输不起。
男人回来之后,总是先推开厅房的门,进到漆黑的冷冰冰的屋子里了,才会划一根火柴,点燃旁边柜子上的煤油灯。才会走到她身边,摇醒她。男人知道她会一直等着他,他知道她不会独自上炕睡。无论多晚,她都等他。她迷迷糊糊说一声“你回来了啊”之后,夫妻二人才会一起洗脚,上炕睡觉。
可是,这天,她醒来后,天都快亮了,她都要起身生火做早饭了,她的男人,仍然没有回来。她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到现在了,还不回来。莫非那种被称为“升级”的扑克牌游戏,会一直玩到天亮吗?
铁匠与巧云
每年,村里要请一回铁匠。不定谁请——你请也行,他请也行,总得有一个人出面请才是。也不定多久,少则一二十天,多则一月有余。时间往往是冬天,冬月或腊月。这个时候,村里人多半闲了,也该为明年的生计准备准备了。请铁匠干什么?打铁。打铁也是一种准备,农具的准备。把坏了的折了的修补修补,再添置一些新的、缺少的。铁也好找,捡一些废铁,也可以买铁,集市上就有贩铁的小贩,家里废弃的农具也可以回炉。
一般,一个家庭请铁匠打铁,最多也就三五天的时间,不会更多。没那么多要干的。有一部分家庭,这一年,甚至不需要铁匠,也不必打铁。
远远近近只有这一个铁匠,姓张。张铁匠是个独眼。他这个人有些怪。他的左眼不知怎么瞎了,瞎了就瞎了呗,却换了一只狗眼,这么看来,他是有一双眼睛的,他那一双眼睛,细看却不怎么一样:一只有神,骨碌碌转动,另一只却呆滞,也不转动,泛出一些幽暗的蓝光。左眼只是一只眼珠子而已。既然已经有了这只无用的眼珠,就无必要将这只眼睛遮挡起来了吧?可是不,张铁匠用一片三角形的小黑布做眼罩,将那只眼蒙着,一年四季都蒙着,一天到晚都蒙着。夏天那么热,打铁时那么热,他还蒙着。只有到了睡觉的时候,张铁匠才会摘下眼罩,搁在枕边。既然要用眼罩,就没有必要装一只假眼了呗,可他还是又装了假眼。
因为他的眼罩,在孩子们眼里,张铁匠这个人就有了一些说不出的神秘。
后来才听说,张铁匠的眼睛是生产队放炮时给飞石打瞎了的,炮响过之后,躲炮的人从藏身之处纷纷跑出来,朝天上望,张铁匠也跑出来,也朝天上望,可是,张铁匠刚一抬头,一颗不大不小的石子就钻到了张铁匠的左眼里,仿佛那飞石一直等他跑出来,一直等着张铁匠抬起头来似的。别人都好好的,只有他的眼睛受了伤。那时是生产队,飞石也没有长眼睛,打瞎了就打瞎了,没准儿的事,怪谁?谁也怪不着。张铁匠的眼瞎了,只是休息了几天而已。他未因此得到什么好处,比如补贴一些工分什么的,心里就一直愤愤不平的。他也只能愤愤不平,他也只能把自己的愤愤不平装在自己的肚子里了。
一般,村里不管请什么匠人,如果大家都需要,都是谁第一个请的,就住谁家。或者,谁家用着这一个匠人的时候,这个匠人就住在谁家。张铁匠到了这个村,却是只会住在巧云家。请他的人即使给他腾出床来了,他也不去住。叮叮当当干完一天的活儿,到了晚上,吃了晚饭,喝了小酒,张铁匠总是摸着黑提着屁股上巧云家里去。张铁匠跟这个村里的任何人,非亲非故,跟巧云也是。他为什么非得住在巧云家?他跟巧云也不是相好,如果他跟巧云是相好也还说得过去,可他俩不是那一种关系。
张铁匠一到巧云家,就把眼罩摘下来了。他把眼罩搁在旁边,露出那只泛出蓝光的假眼。过那么几天,眼罩就给汗水浸湿然后又给灰尘弄得脏糊糊的了,张铁匠摘下眼罩,就会顺手递给巧云,巧云就知道,他是让她给他洗洗。巧云接过眼罩,什么也不说,无声去洗了,晾干,或直接烤干。第二天早晨,眼罩会在张铁匠起床前出现在他睡着的床头柜子上。
巧云是个漂亮的女人。张铁匠眼睛没有瞎之前,也是一个高大帅气的男人。他们的年龄也差不多,巧云比张铁匠只小了三岁。村里人都猜测,张铁匠和巧云年轻时,肯定是有故事的。至于那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就是无人知晓的了。他们对铁匠和巧云,也有一种由衷的敬畏。人们从不猜测他们之间,现在还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关系。
巧云的男人,也不这么猜。
老燕和他的女人
老燕到那个家的时候已经六十出头了,他皮肤黧黑,脸上油浸浸的,似乎老是向外面渗油一类的东西,渗出来的油一类的东西里还总是混合着灰尘和汗渍,因此,老燕的脸上、身上、衣裤上,永远都是黑乎乎的样子,像长期在油坊里做活的伙计,不像一个庄稼汉。生产队时,老燕也不出工,不参加任何集体劳动。他也不是饲养员,也从不为生产队做点儿什么。老燕仅仅是到那个家里生活了几年,仅此而已。老燕是个外地人,这是可以肯定的,他具体是什么地方的人就无人知晓了。他的女人,可能知道,他的两个儿子,可能也会间接地知道,但村里无人对老燕感兴趣,也就没人打听这些。老燕也不是手艺人。那时偶有出外谋生的人在远远近近的村子里落户,多半都是四川出来的手艺人,且以木匠为最多。老燕无四川口音,肯定不是四川人。那时,偶尔在附近的村里落户的,也有货郎。货郎或背或挑,背篼或箩筐里装的是针线、顶针、指甲剪、梳子、篦子、掌心那么大的小镜子、各色毛线(头绳)、洗鞋的小刷子、糖精、糖果、肥皂……货郎用这些小东西换乡下姑娘们剪下来的长辫子,还有猪鬃。货郎的货物,也可以花钱买。货郎一村一村挨个儿走,他一进村就被婆娘女子和娃娃们包围起来了,他们等货郎已经等了很久很久了,许多东西都是等着要用的,都已经等不及货郎的到来了!老燕极有可能是个落了户的货郎。很多货郎,在家乡无家,无妻儿,但手里有一些微薄的积蓄,快老的时候找个比较合适的半路女人,混掉余生,是很正常的事儿。老燕应该就是这样的人。
村里人无论老小,都管老燕叫老燕,他姓燕。他叫什么名字,十有八九不知。没人在乎他的名字,也没人问过他的名字。老燕的女人那时可能四十左右吧,她的男人没了很久很久了,找个老燕这样的人养家,也是正常,她不领着孩子回娘家已经很不错了,她要是回了娘家,两个儿子兴许都不姓王了!谁也不能再要求她什么了。女人先后生了两个儿子,都姓前夫的王姓。大儿子那时已经十几快二十了,叫王来宝,还没有结婚,二儿子那时只有五岁,叫王代成,比我还小一岁。王来宝和王代成,一个大头圆脸,一个小头长脸,明显不是一父所生。小儿子王代成仍姓王,不跟老燕姓燕,跟老燕也就没什么关系。事实也是如此。老燕到那个家庭时,王代成已经满地跑了。女人的两个儿子,包括女人,也把老燕叫老燕,不叫爸爸,不叫“我家那口子”。
我比王代成大一岁,算是同龄人。小时候,我偶尔会跟着王代成到老燕家去玩一会儿。我们去了,从不将老燕放在眼里,老燕也不将我们这些毛孩子放在眼里。我们总是各行其是,相安无事。在我的记忆中,不记得老燕是哪一年到了这个家里的,也不记得他是不是真的做过货郎。在我的记忆中,老燕仅仅是王代成家多出来的那个老头儿。在我的记忆中,老燕的女人——也就是王代成的妈究竟长什么样子,我也没有任何印象了。她总之不是一个出众的人。依稀记得她老是坐在火塘边,一动不动烤着火。她面前的火塘里总是围着一只被烟火熏烤得黑乎乎的陶罐,女人过一阵子就把汤药滗出来,晾凉,喝掉,又给陶罐续满水,继续煨在火塘里。女人也不怎么说话,更不走出家门,走出院子,到谁家串门。村里人也不上她家里串门去。去了,没什么要说的!没什么能说说的!这是一个宁静的女人:少言语,不走动,冷冰冰。村里也无关于她的一句半句闲话。她的存在仿佛不存在。她还不如老燕这个人让我记得那么深。
老燕和他的女人一起生活了没几年,在我童年的时候,他们夫妻就先后死了。好像还是女人先死了的。后来老燕家就只有王来宝和王代成两兄弟了。两兄弟也不怎么和好,他们常常对骂,语言还很恶毒,具体骂什么我却一句都记不起来了。估计和各自的父亲有一些关系吧?现在,我这么猜。现在,我用成人的思维方式猜老燕的女人,总觉得她家的大门,令人生疑:那大门一直没有门,仅仅是个畅通的出入口而已,任何时候任何人都可以自由走到女人睡屋的窗下。女人睡的炕,也在窗下。窗是活动的,一推即开。她的男人走了之后和老燕到来之前的那一大段空白,对这个女人来说,也许不是空白,或者,不那么空白。王代成极有可能就是这么生出来的吧?可村里为什么又没有关于这个女人的闲话呢?这又让人费解。莫非因为这个女人长得不怎么好看,觊觎她的男人就很少,没几个?有没有因觊觎而最终得手的人,大家更是无所谓?
总之,王代成不是前夫的遗腹子,也不是女人跟老燕生的,这是不争的事实。
老燕和他的女人,都死了,他们带走了只属于他们的秘密。或许也不算什么秘密,只是当时无人对他们的事感兴趣而已。老燕和这个女人的一生,当然,也是一生。完整的一生。
别人跟他们比,兴许好不到哪儿去。
用家乡人的话来说:“咋样活都是一辈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