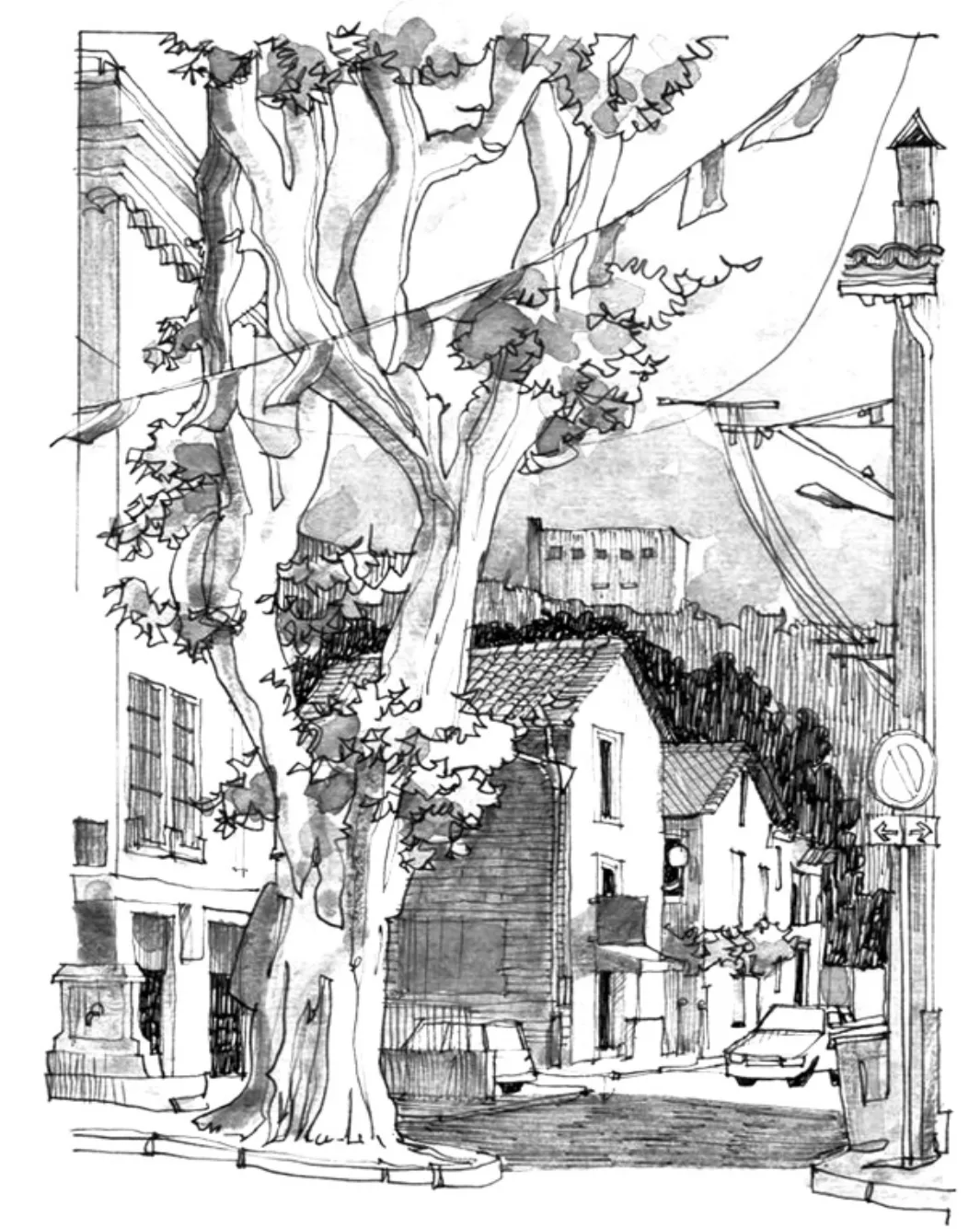
米兰
西关老街住着一群老人,天气好的时候,都会拎个马扎或小凳子到马路边儿,三个一伙,五人一堆,坐那里闲聊,一边扯闲话,一边看光景。也有打牌下棋的,有一搭无一搭,凑个摊子,图个乐子,消磨时光。还有不算老的闲人混入其中,人堆里乱窜,一脸精明,嘴巴和耳朵都不闲着,像是打探或传播什么新闻。马路上自是断不了行人,多是住在这条街上的熟人,对了眼点点头打个招呼,或笑上一笑,然后你聊你的,我走我的。有行色匆匆的,步伐急乱,火急火燎,有人便嘟囔句:火上房了咋的,还是急着去投胎?有人却说:一定是买彩票中大奖了,不下一千万!引起一阵笑声,朗朗的,沉闷的气氛一下活起来。有一个年轻女子,经常会从西关街上走过,是“万人迷”。这个名字不知谁先叫起来的,一直都这么叫着,是褒,是贬,说不清。有人说这女人叫小米,是姓米还是名字叫小米,不得而知,并没人去查询,吃饱了闲的?但大家都相信,能让万人着迷,说明这女人有不同寻常之处,说得直接点,就是长得应该是十分漂亮、迷人。其实,“万人迷”长得并不算极出色,现在漂亮女人有的是,一个比一个靓丽,大眼尖颌,细腰盈盈一握,仙女一般,就连那些被称作小鲜肉的男子,也分外妖娆,力压群芳。“万人迷”皮肤是白皙的,五官说不上精致,却也协调得体,看着顺眼。身高大约一米六多点吧,身材匀称,杨柳细腰,穿高跟鞋,看着比实际身高要高出不少,有点婀娜了,像T台上的时装模特儿,袅袅婷婷。
主要还是穿着,一年四季变换着各种时装,也不怎么特别,大街上很多女人都在穿,但穿在她身上却有特别的一种风韵,也说不出好在哪里,就是看着舒服,养眼,受看。特别是夏天,她喜欢穿一件红底碎花长裙,满裙的碎花儿似蝴蝶翅膀上的斑点,颜色醒目,招摇欲飞,也像细碎的花朵,如繁星缀满天空。上衣是紧身的白色短衫,纤尘不染,透着亮儿,闪着光儿,看上去洁白恬静,卓尔不群,那应该叫亭亭玉立了。走起来,长裙随风摆舞,婀娜多姿,把人们的眼睛搅得错乱迷离,目光齐刷刷随着人去,远了,看不见了,方才不舍地收回来,互相看一眼,也不说话,心思都在眼睛里。
有个闲人说了句:浪货,大街上招摇个啥呢?其他人听了不说是,也不说不是,有的撇撇嘴,有的咂咂舌算是回应。一个叫齐爷的,八十岁了,见多识广,德高望重。他很少说话,但说一句出来如铁板钉钉。每次见那女人走过,大家都看齐爷,期望他能给出个评价。齐爷不看女人,只顾低头下棋,或摇着蒲扇喝茶,嘴唇绷着,不吐一字。那天女人走过去,大家追着她看,齐爷却冷不丁唱了句京戏:这个女人哪……不寻常!大家扭回头盯着齐爷看,却咂摸不出什么意思。张三金凑过去说,齐爷,您这是把这女人比作阿庆嫂啊?阿庆嫂可是地下党,英雄人物,这女人一看就是个骚货,您老什么眼神?张三金四十多岁,没正当职业,常年买彩票,从没中过奖。他是混迹于老年人当中的闲人,抽空子向老年人推销保健品,也怂恿老人买彩票。齐爷乜一眼张三金,也不说话,伸出手指朝天指了指。张三金抬头看天,正好有一只鸟飞过去,黑漆漆的,是只乌鸦。张三金撇撇嘴,心里骂道:老不死的,咒我呢,也日怪了,这黑鸟好像是他养的,怎么说来就来呢?
后来,有关“万人迷”的传闻多起来。说她快三十岁了,还没结婚,整天不务正业,到处勾引男人,似乎干那种龌龊勾当。还有说她傍了一个大款或是一个大官,是个小三,正逼着那男人离婚呢,闹得满城风雨,众说纷纭。张三金自然是最活跃的,上蹿下跳,添油加醋。他买的彩票刚好中了一个二百元奖金,他笃信好运就要降临,一说话就手舞足蹈,眉飞色舞,很有感染力。再见到“万人迷”从街上过时,人们的目光变得扑朔迷离,甚至有点暧昧,心里的想法也比较复杂了。后来传闻越来越多,越来越奇,有鼻子有眼,似乎手里抓着真凭实据,人们的目光便得到高度统一。善良正义的人大都疾恶如仇,一旦记恨起一个人来,往往同仇敌忾。再看她艳丽的穿着,简直就是一颗炮弹裹着糖衣,苗条的身材,也成了一只得了邪道的狐狸,妖媚十足,甚至与腐败挂上了钩,说那些贪官有一个算一个,都败在女人裙子底下。“万人迷”一从街上走过,人们就把目光盯在她的身上,锥子一样尖利、刻薄。有的人似乎还在小声地咒骂,脏话不堪入耳,好像不这样,就会与这个狐狸精同流合污了。但是,从他们不断闪现出暧昧之色的眼睛深处,似乎能读出别样的意味。什么呢?难讲得明白。只有齐爷,微微闭着双眼,若有所思。
尽管如此,“万人迷”还是“万人迷”,该怎样招摇还怎样招摇。她几乎每天都会从街上走过,像一只流动的花儿,又像一朵飘浮的云,飘着,旋着,洒一片芳香,播一路风情。
临近过年,小城该热闹起来了,可突然之间,小街两旁的人都不见了,像屏幕上按了删除键,清空了。“万人迷”自然也无了踪影,像一片云飘走了,无声无息。突然而至的疫情像一团乌云重重压在小城上空,人们都关在家里,以躲避病毒的侵袭。偶尔见到有人在街上匆匆而过,也是全副武装,戴着口罩,衣服把身体捂得一丝不露。熬过了几个月,国家全民动员,倾力抗疫,终于取得了初步成果,小城疑似病例全部清零。解禁的人们长长舒一口气走出屋子,迎接这个特别的春天。人们又来到街上聊天下棋,生活恢复到原来的模样。
那天,天上的太阳格外灿烂,亮得有点晃眼。“万人迷”擎一把红蓝相间的花阳伞,从铺满阳光的路面上款款走过。那伞红得鲜艳,蓝得耀眼,阳光洒在上面,一晃一闪,色彩变幻,似有无声的音符一串串流淌出来。那时刻,马路上出奇的平静,又有一种不祥的异样,但大家都说不出,究竟与平日有什么不同。有时候,人的直觉是很准确的,看着,想着,事情就突然发生了。那时刻,对面突然驶来一辆卡车,速度有点快,有点野,司机像喝了酒,或昏了头,车吼叫着,卷起一路尘埃。此时,一个男童,突然向马路中间跑去,他的一只皮球滚到了马路中央。
吱——刺耳的刹车声如晴空里一声霹雳,把人们从昏昏然中震醒。人们看到,鲜艳的花伞像一只蝴蝶,在空中飘飞起来。
孩子得救了,“万人迷”却在紧急关头一把推出小孩,自己的一条腿被车轮轧伤。花伞悠悠落下来,盖在倒在地上的女子身上。
再见不到“万人迷”,大家的心里觉得少了点什么,空落落的。
有人宣布一个确凿的消息:“万人迷”是县医院的一名护士,真名叫米兰,前段时间参加了援鄂医疗队,据说还立了功,电视新闻里都播了。
人们把目光齐聚在齐爷身上,觉得老人家应该有话要说。齐爷站起身咳嗽一声清清嗓子大声说:没错,我孙女也在县医院上班,她们一起去的武汉。
托着鸟笼子的巴老家里养一院子花,他对笼中的画眉说:咱家有一盆米兰对不?枝繁叶茂,满树的花儿,如满天的星星。那个香气啊,清雅淡泊,却……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哦,沁人心脾,对吧?也是怪了,那个香味啊,是在空中悬着的,飘来飘去,可你凑近花儿去闻,却闻不到一丝香气,真是世间奇花啊!
一位爱好古诗词的老者悠悠吟诵一句:花如米状,味同兰香。
张三金一拍大腿高声说:我就说嘛,这女子一看就不寻常,感觉就像个英雄,不然怎么会冒着生命危险救下那个小孩?大家随声附和,众口一词夸赞着那个叫米兰的女子。齐爷瞪张三金一眼,又伸手指指天空。张三金一愣,心想,那黑鸟又来了?抬头看时,却见一只硕大的蝴蝶飘在空中,嫣红的翅膀上布满细密洁白的碎花儿,似有清雅的香气当空弥散。蝴蝶下面一个小男孩仰头看着天空,手里牵着一根长长的线。
很多天以后,人们看到,一个高大英俊的青年挽着一个女孩的手从马路上走过。他们走得很慢,女孩的腿似乎有点跛,试探地迈着步子,像在一步步丈量马路。天上没有太阳,男人手中却擎着一把鲜艳的遮阳伞覆在女孩头上,跟那天女孩手中的那把一模一样。
有人喊了一声:米兰!有人跟着喊:米兰——更多的人齐声喊起来:米兰!米兰!米兰……
红梅
那年县剧团下乡巡回演出,在离城二十多公里的山区。山里人很少看到城里的剧团演戏,剧团每到一地儿,村里人像过年。各家都把邻村的亲戚请了来,有的相隔十几里地,说来听戏,没有顾惜脚力的,老的少的,男男女女,早早来了。这边早就备好酒菜,菜虽普通,山里人看来却是丰厚。割两斤肥肉,锅里煮了,煮肉的汤把白菜萝卜炖透,顺上粉条,满满一锅。肉切成薄薄的大片,盖在萝卜白菜的碗上,油光白亮,香气四溢。鸡蛋要炒几个的,家家都养了鸡不用花钱去买。搁上葱花或干椒,用筷子搅匀了,热油锅里一泼,滋啦喷出油气,香了半个村子。存放半年的咸鱼切成指甲盖大的丁儿,裹了厚厚的面糊,走油一炸,满院子腥香。院子里的狗熏得掉了魂,夹着尾巴转过来,转过去,口水扯出老长。人们吃着喝着,打着酒嗝,说着戏文,漾满脸笑意。有爽气男人,酒至半酣,张口吼两嗓子,硬硬的,朗朗的,裹起一阵肆意的笑声。
那天晚上演的什么戏,记不起了,但那天台下看戏的人多得让我们惊讶,人头攒动相互拥塞的情景记忆如昨。台下看戏人渴望和满足的目光,让台上演戏的人不敢有半点懈怠,全都使出浑身解数,心劲儿提起来,精神头足,嗓门也亮,把戏演得风光火爆,整个山村醉了酒般,在锣鼓点儿和男女的唱腔里摇摇晃晃。
正演着戏,雪就毫无征兆地落下来。老百姓很少看到城里剧团唱大戏,戏来,雪也跟着来了,真是好兆头。顶着一天的雪,眼巴巴看着戏台,几乎没有人离去,戏文融进雪花里,飘飘悠悠,洋洋洒洒,清润如春。
雪似乎憋足了劲儿,整整下了一夜。我们住在村边的一所小学校里,用厚厚的麦秸搭了地铺,蓬松温暖。演员们习惯了这般流动简陋的生活,累一天,都睡得酣透。早上出门一看,漫山遍野白茫茫一片,昨天的小山村已是面目全非。厚厚的积雪埋没了上下山唯一的路,我们被隔在山上了。
近中午的时候,小学校里进来一个小女孩。女孩七八岁的样子,虽然衣着破旧,但掩不住一脸清秀面容,在白雪映衬下红扑扑的甚是可爱。她站在我们宿舍门口,手里攥一把雪,慢慢揉团着,眼睛一眨不眨呆呆往里面看。她在看什么呢?哦——这些昨夜在戏台上抹了脸子又唱又跳的人,下了台是什么样子呢?那个演谁谁的在哪里呢?孩子的眼睛里藏不住东西,好奇的眼神像一只小手向里面探。一位年长些的女演员出门看见女孩,眼睛蓦地一亮,脱口夸道:“啧,啧!这闺女长的,可真俊!”然后俯下身问她:“小姑娘,你是谁家的孩子,找谁呀?”女孩咧嘴笑了笑不说话,小脸因羞怯变得更是红润了。女宿舍里的人几乎都被引出来,见了女孩纷纷称奇,说山沟沟里竟能生出这样俊俏的女孩子,真是稀罕!这脸盘,眉眼,怎么看怎么好看,像年画里画的小人儿。那位年长的女演员突然说:“这小脸蛋儿若是化上妆,还不知能俊成什么样呢。”一个叫红梅的年轻女演员趁机问女孩说:“小姑娘,让阿姨给你化妆吧?”女孩点点头,接着又摇摇头小声问:“什么是化妆?疼不?”红梅抿起嘴笑了:“就是打脸子,怎么会疼呢。”说着抬手在自己脸上描眉画眼比画着,然后轻软地对小女孩笑着。这次女孩使劲点了点头。一伙人嘻嘻笑着,夸着,簇拥着女孩进屋,张罗着给女孩化妆。记得有人曾问过女孩的名字,大概叫桂香或者玉香,记不清了。
红梅是剧团里最漂亮的女演员,长得轻盈婉约,一双秋瞳,顾盼传神。不仅扮相好,唱得也好,嗓音清亮,字正腔圆,韵味十足。心地更是善良慈悲,脸面似乎总在浅浅笑着,深得大家喜爱。观众对她更是爱慕有加,无论在哪里演出,她走在街上,围观者便匝匝而来,惊奇,叹羡,献媚,各尽其态。红梅呢,就那样轻盈地笑着,传达着对大家的亲切和感激。红梅虽然还未结婚,但特别喜欢孩子,看到谁家的孩子都要好好瞅一瞅或者抱一抱。红梅一见这个农村的秀气女孩,就切切喜欢上了。
红梅牵着女孩进了屋,搬个杌子让她坐了,然后就收拾化妆盒准备给女孩化妆。红梅先用浸了温水的毛巾把女孩的脸擦拭干净,用一块勒头布把头发束起来,女孩的小脸便干净如刚打磨好准备上漆的木板儿。红梅平摊了手掌,在上面调好底彩,然后往她脸上轻轻拍色。两只手交替着,拍一下,倒一下,油彩在女孩脸上均匀摊开。女孩的脸开始油光闪亮,还散发着油彩独有的香气。然后,画鼻梁,描眉眼,拍腮红……红梅画得细致,一笔一抹都不马虎。红梅动作轻柔,细长的手指在女孩脸上缓缓游走。女孩的脸在红梅的手中一层层变幻,明润,生辉……
女孩走出屋来的时候,就连我们这些男人们也都给惊住了。女孩化了妆的脸鲜艳无比,眉眼儿精神闪亮,站在雪地里像朵花一般盛开着。这时有人突然发现,院子里墙角处的一株梅树,一人多高,枝丫繁多,上面蓄满了花蕾,有一两朵竟悄然绽放了。梅花艳红的颜色,花片透着亮儿,嫩黄的花蕊颤颤地,不断向四周洋溢着无可言喻的芳香。便有人称奇,说这女孩莫非梅花变的不成?
突然地,红梅眼睛一亮脱口而出:“梅子,你就叫梅子吧。”有人笑说,“你是大梅,她是小梅,你这么喜欢孩子,就认她做干闺女得了。”红梅抿着嘴笑,也不作声。那女孩甜甜笑着,然后郑重其事地点了点头。
女孩带着“脸子”径直回家去了,大家都还在议论着这个俊俏的女孩,说她应该去剧团做演员,待在农村就浪费了。说得更多的是,想不到小山村里竟然能出落这般美好的女孩,把城里的女孩子都比没了。红梅也不言语,呆呆看着那株梅树,脸上的笑靥一丝丝牵出来,如那花蕊微微颤动。不一会儿,女孩复又回来,手里牵着一个女人,是女孩的母亲。女人看上去比女孩还显得羞涩拘谨,脸微微红着,似笑非笑的。她手里提着一个布包,按照女孩的指点,她把布包送给了红梅。女人搓着手说:“俺农村也没啥稀罕东西,自己摊的煎饼,今年下的新小米,尝尝鲜吧。”红梅推辞了一下也就收下了。为了回报女孩的母亲,她说:“你这闺女长得真好,过两年让她到城里剧团考演员吧。”女人开心地笑着连连点头,然后扳着女孩化了妆的脸一眼一眼看着。
大概三年后吧,文化局安排剧团到农村体验生活,我们又去了那个小山村。到村里后,红梅第一件事是打听那小女孩。一个坏消息让所有人都拉下脸来——那女孩已于一年前生病死了。红梅说什么也不相信,抹着泪说:“怎么可能,不可能的,那么水嫩一个孩子……”女孩得了白血病,当时全村人都凑了钱,让女孩到处求医,省城的大医院也去过了,最终却没能挽回她幼小的生命。就像一株庄稼,这才刚刚生出青葱水嫩的幼苗,就拦腰折断了。女孩的母亲含泪对红梅说:“孩子临死前瞪着一双大眼睛对我说,娘,我快死了吗?我不想死,我叫梅子,还要到剧团当演员呢,我想再化一次妆……那次你给她化妆,她好几天舍不得洗,带着脸子吃饭,睡觉。”
两个月后临近过年,我们结束体验生活的日子,打点行装回城。还未出村,天上突然开始飘落点点雪粒,然后变成大朵的雪花。
车开出村子,经过村头小学校时,红梅突然提出去看看那株梅。
院子里已铺了厚厚一层雪,孩子们放假了,院里悄无一人。我们不约而同朝那个长着梅树的角落看去——干硬的枝杈挂满了白雪,但仍不屈不挠傲然挺立着,蓄势待发。
一阵风过,打着旋儿,雪在风中毫无规则地舞动,翻卷,乱人眼目。
裹着雪花,突然地,从院外走进一个女孩,穿着鲜红颜色的棉袄棉裤,像一捧火,红得耀眼。她站在那里微笑着盯着我们看。
红梅眼睛蓦然一亮,疾步跑过去抱起小女孩:“梅子,梅子,你终于来了!”
我们都定在那里,恍若梦中。
红梅抱着女孩左看右看,脸上绽开少有笑容。红梅扳起女孩的脸急切地说:“来,阿姨给你化妆。”
女孩仍不说话,就那么微微笑着盯着红梅看。
两个人就坐在雪地上,开始化妆。我们几个人也坐在雪地上围在她们身旁静静地看。这情景,像一个庄严肃穆的仪式,又像一幅从天际落下来的画图,自然而神秘。
红梅掏出手帕轻轻为女孩擦拭脸庞,然后在手掌上配底彩。油彩轻轻地均匀地拍在女孩脸上,女孩脸上呈现出鲜艳的肉色,白里透红,仙气氤氲。红梅捏住眉笔,在女孩鼻梁两侧轻轻勾上两条褐色实线,然后翘起无名指把两条线均匀地向两侧摊开,女孩的鼻梁便清晰地突出起来。红梅调了大红的油彩,轻轻涂在女孩的眼窝和脸腮,慢慢摊匀,女孩的脸便层次分明,婉约飞扬。
红梅的手经过这段时间修建梯田的劳作,虽然略显粗糙,还磨了几个硬茧,但仍不失纤巧,还是那样轻盈灵动。勾完最后一笔,红梅长长舒口气,像完成了一件神圣的使命,脸上露出舒心的笑容。女孩站起身,仰脸冲红梅甜甜笑着,一朵硕大的梅花灿然绽开。
红梅又盯着女孩呆呆看了一会儿,然后把化妆盒放在女孩手上说:“以后你自己学着化妆,女孩子化上妆就是一朵花儿。梅子,你要好好上学,长大了去考剧团,像阿姨一样当演员。”女孩点点头开心地笑着,红梅紧紧抱住女孩,不停地小声叫着:“梅子,真的是你,梅子……”
蓦然,一声软软悠悠的呼叫传来:“英子——回家了——”红梅脸色陡然一变,噗地吐出一口鲜血,雾一般喷洒在梅树上。梅枝上殷红点点,似一树红梅灿然绽放。
若干年后,退休多年的红梅去省城拜访一位多年未见的朋友,在省剧院的朋友家见到一名年轻女演员,是那位朋友的学生。朋友说她现在是剧院的台柱子,国家一级演员呢。女演员一直盯着红梅看,眼神中蓄着渴望和期待。红梅也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似曾相识。经过简短对话,女演员突然紧紧握住红梅的手说:“老师,您当年曾经给我化过妆的,您不记得了吗?”红梅一惊,疑惑地看着眼前这个漂亮的女演员。女演员提示说,“那个小山村,下着大雪……”红梅眼前蓦然现出多年前那个飘雪的日子,还有那株一直让她念念不忘的梅花。
“你是梅……”
女演员说:“那年您也曾给我姐姐化过妆,她叫梅子,我叫英子。”
红梅目光缥缈,潸然泪下。
红梅看到,一树梅花在漫天大雪中灿然绽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