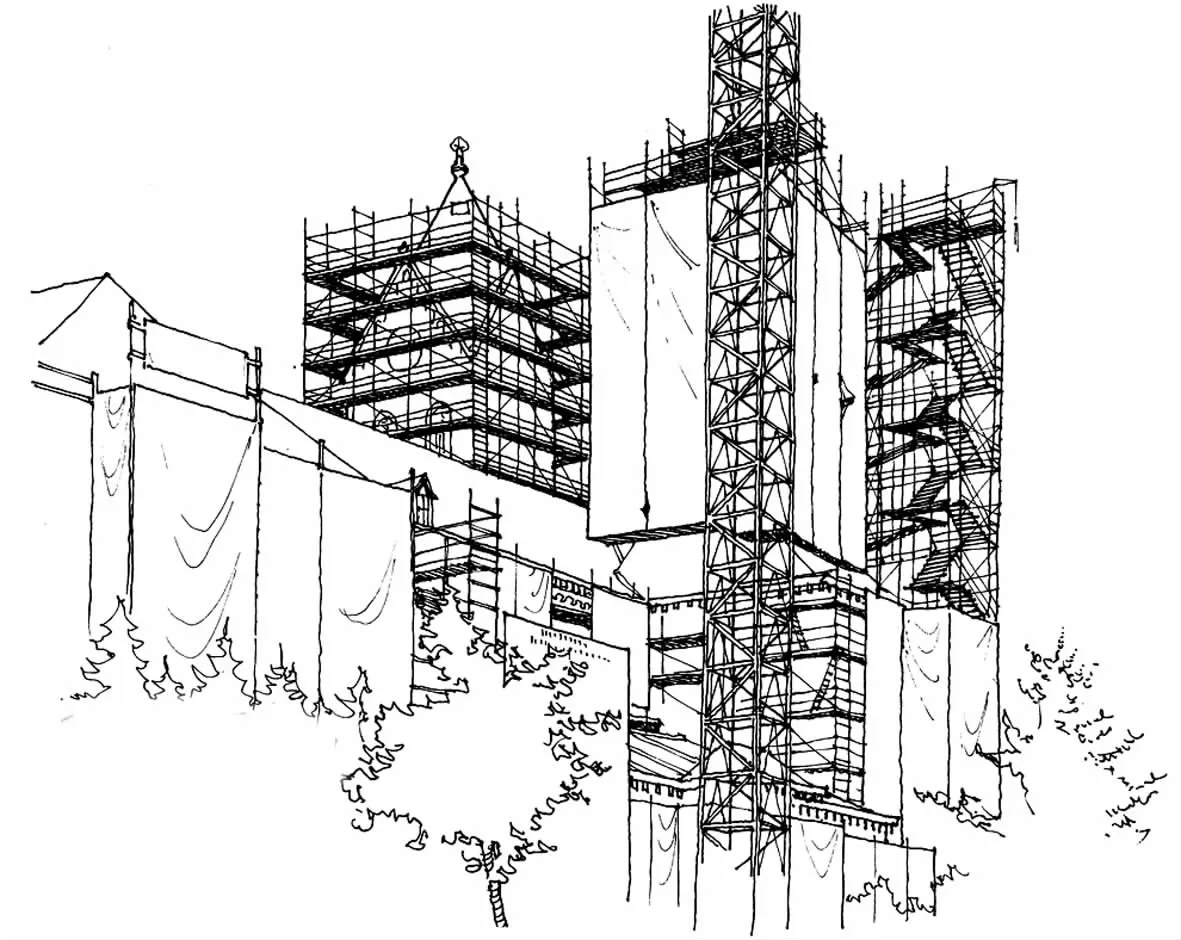
我目光柔和,心绪宁静,
我蹲下来,静观默察
人间繁忙的事物
缓缓移动的阴影——
在幻想和梦境里,
在另一个世界的声响中。
——[俄]亚·亚·勃洛克《我咀嚼着秘密激荡在我体内的》
我的朗朗走了。
它走得很突然,突然到令我都无法相信,它就这么走了。
我都不晓得该拿我自己怎么办。在没有它的家里,空空荡荡,心就像缺了一大块,常常为一根偶然发现的白毛,或一丝依稀熟悉的气息,而引发无穷的哀伤。我恨我自己,常常忘了它已经走了,一旦我意识到这一点,就顿时泪流满面。
在我的丈夫还只是我的男朋友的第一个冬天,他带我去他的一个朋友家聚餐,我在那个朋友家的阳台上,碰到了朗朗以及它的母亲,和三只与它拥挤在一起抢母乳的兄弟姐妹。它们周身洁白如初雪,没有一点杂色,或者说瑕疵,简直太漂亮、太可爱了。
那天我待在客厅里,和人待在一起的时间,还没有在阳台上和它们待在一起的时间多。我独自蹲在阳台上,双手抱着膝盖,距离它们不远也不近。我倒是想跟它们近一点再近一点来着,但我觉得朗朗的母亲不允许我这么做,它侧身卧在墙角里一块棉铺垫上,任由四只小家伙在肚子上闹,却一直侧着头,一对狐狸的黑眼睛,虎视眈眈,紧紧地盯住我的双手。
它一眼就看穿了我的心思。尽管我努力将自己的双手钉在自己的膝盖上,但我仍然按捺不住内心的激荡,很想伸出手去,抚摩那些可爱的小家伙。如果有可能的话,最好把其中一只抱在怀里,抱上一会儿。毛茸茸的、软嘟嘟的它们,就像一个个雪白的毛线球,抱在怀里一定很惬意。但我想如果我这么做的话,无论我伸的是右手,还是左手,朗朗的母亲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把我的手指咬下来,当零食吃了。我从它的眼神里,能读出这个意思来。
所以,我蹲在那儿,一动不动。
所以,它卧在那儿,也一动不动。
我不想跟它造成如此紧张的局势,我以柔和的语调,向它介绍起我自己来,我是谁,和它的主人是什么关系,等等。我甚至还谈到对它们的感觉,我是如何喜欢它们,热爱它们。我想以此来博得它的好感。但它无动于衷,连喊都不冲我喊一声,始终那么紧盯着我的双手,以防我乱来。
我不晓得他的朋友是什么时候站到我身后的。我都没有注意到脚步声。他应该来了有一会儿了,直到我重重地叹了口气,他才开口问我:“你喜欢狗吗?”我被他吓了一大跳,像做贼被人抓获在现场,莫名紧张地直起身来,扭头冲着他发呆。
我随后笑了笑,才问:“这不是狐狸吗?”
“像,但不是。”他说,“这是银狐犬。”
难怪瞧着这么像狐狸,我对自己的浅薄而感到抱歉,又朝他笑了笑。我只知道田园犬,也就是土狗,还有狼狗。除此之外,就一律以为是宠物狗,不再有具体的名字了。
“喜欢,”我说,“太喜欢了。 ”
他说:“那就送你一只吧。”
“太好了!”我脱口而出。
但我认真地想了想,又不无遗憾地说,就是没有地方养呀。
我和两个同事住在一间集体宿舍里,而集体宿舍是禁止养狗的。狗又是个活物,据说头几会天因为环境陌生通宵达旦地乱叫,难保不被宿管大叔发现。他肯定会没收的,结果就成了他的盘中餐。另外,这两年我除了工作,业余时间都在读夜校,我想把文凭再往上升一升,实在没有时间去养一只狗。老实说,我就是连我自己都照顾不全呢。
他笑道:“那有什么关系,先让冷鬼养在家里嘛。”
冷鬼是我男朋友的绰号,他的大名叫林贵。他的朋友们都这么叫他。
就这样,我参加那次聚餐的最大收获,就是他的朋友送给我一只幼小的银狐犬,还倒贴了一只金属的小狗笼——那是他的朋友从宠物市场买朗朗的母亲时附带的狗笼,是他买的第一只狗笼,只能关小狗。他家阳台上有一只大狗笼和三只小狗笼,我就恭敬不如从命。
朗朗就寄养在他家里。他几乎每天都向我汇报它的近况,因为那是我的狗。我们之间也突然多了话题,一改以往无话可谈的尴尬局面;而只要谈到小狗,我的心就会变软,连语气也更柔和了。小狗就是这么个尤物,能够激发我的母性,时常会有照顾它一辈子的冲动。这就让他也连带着占了不少便宜。既然我要照顾它一辈子,那就是家人了。有天我对他说,你别老是小狗小狗地叫,多难听哪!我们给它取个漂亮的名字吧。为此我们讨论了数日,他就像给自己的儿子取名字一样,非常积极。
他最初叫它“小白”。
我说庸俗。
他又改叫“白妞”。
我说轻浮。
他再改“一尘不染”。
我说太直白,不像个名字,你就不能动一动猪脑吗?
几天后,他终于败下阵来。我喜欢看到他懊恼、垂头丧气的样子,尤其在我面前,他满头抓痒的青春面孔,惹得我哈哈大笑。他就批评我这不行,那不行,就你行,那你倒是取一个好听的呀。其实我早就取好了,我之前不说,就是等着他的这句话。我非常霸气地给它取了个响亮的名字——朗朗。我十分傲慢地问他:“怎么样?这个名字够大气,够含蓄吧!”
“什么呀?”他就冷笑道,“我怎么没感觉呀。”
“朗朗,是朗朗乾坤的朗朗。”我强调道,“确实不是你这种男人能感觉到的。”
那两年,他善于利用朗朗,制造和我见面的机会,而我也确实太喜欢它、太爱它了,一有空我就会想到它,一想到它我就想把它抱在怀里,我那时候真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才好,养在他家让我心里非常不爽。他太清楚我的心思了,就会偷偷摸摸地带它来到集体宿舍前面的横道上,大声地叫我一起去遛狗;朗朗也是个聪明的主儿,在那儿汪汪一叫,我就会奋不顾身地冲出去。
他马上就把牵狗绳交到我手上。
他说:“朗朗,想死妈咪啦。”
是他自己想我了吧?臭男人,谁要理他呀,我才不理他呢。我就蹲下身去,使劲地抚摩朗朗的小脑袋,把它的头发都弄乱了。我双手叉住它的两条前肢的胳膊窝,将它高高举起来,在空中不停地摇晃它的身体。它明亮的眼睛忽闪忽闪的,像阳光下新疆的紫葡萄。小家伙心里跟明镜似的,害得我都忍不住想亲它了。
“啵!”我亲了它。
“啵!啵!”我又亲了它。
可把那家伙给馋的,口水直流,哈哈。
我每次见到朗朗,总要先和它亲热一番,才肯放过它,才牵着绳子和它,也和他一起散步。
即便是我们三个在一起散步时,我的关注点也永远都是它,我的朗朗。
他都忌妒它了。
哈哈,我都笑死了。
我悄悄地对它说:“朗朗,有没有听爹的话呀?”
它才不理会别人呢,总是绕着我的身体向前走,绳子在我身上绕了一圈,又绕一圈,绕得我手上的绳子都快没了,最后就把我和它都绕住,绕在一起走不了路了。我笑着将绳子反向绕回去,松开后又将它抱在怀里,它就乖乖的,伸出小舌头,哈哈地向我讨好。
说来也真是奇怪,朗朗是他养着,但它对我比对他更亲,真是个通灵的动物。
只要我有整块的时间,不论他在不在家,我都会去他家里的,和朗朗待在一起,没完没了地逗它玩。每次我走到他家的楼梯口,它就在家里汪汪两声,然后迅速跑到门口,头抵着铁门板,发出呜呜的低吟声,向我撒娇呢。
这个臭东西!谁想不喜欢都难。
两年后,我夜校毕业,拿到了硕士学位,转身就和他结婚了。这倒不是我有多想嫁给他,而是朗朗让他攒了不少分,因为我想把它接到属于我自己的家里来养。我们住到较远的崇贤镇,那边房价相对便宜些。我们按揭了一个大套,开始了可恶可恨的房奴生涯。当然,也开始两人世界。不,应该说是三人世界,爹地,妈咪和朗朗。
对,小家伙现在可是我家最重要的家庭成员,它也是有户籍的啊!
就因为有了它,我提前进入了准妈妈行列。不说每天吧,至少两天总得给它洗澡,吹干头发,像这样浑身长头发的婴儿,世上应该少有吧,但它毛发蓬松时的飘逸和纯洁,宛如仙子一般,是任何一个异类妈妈都要爱死的。我坐在沙发上,让它站在我并紧的双腿上,我给它细细地梳头发,把它全身的毛发都梳得顺顺溜溜的,漂漂亮亮的。我能在它身上花大量的时间,我都佩服我自己,我怎么会有那么好的耐心呢。每年我都要去宠物医院给它体检,打疫苗,这不就是培育婴幼儿的套路吗?它感冒咳嗽了,它拉稀了,我都是第一时间送去宠物医院。
有一次它小便不利落,每次只尿一点点,而且尿时还浑身颤抖,我看是看到了,但没有多想,因为任何一只狗都渴望自己雄霸天下,无论它的个子有多小,也无论它的力量有多弱。我每次带它出门遛弯,都不难看到它走一炮仗路,见到一棵树就兴奋地冲过去,后腿一掰,就在树根上部撒上两三滴尿;又向前走一炮仗路,见到一辆停泊在路边的汽车,它又兴奋地冲过去,后腿一掰,对着汽车轮胎撒上两三滴尿;再向前走一炮仗路,见到一个人站在那儿,它也兴奋地冲上去,后腿一掰,朝人家的裤管上撒上两三滴尿……我知道狗尿是世上最金贵的东西,那是上苍赋予的至高无上的权力,那是它们圈地运动的铁桩,那是扩张自己势力和地盘的撒手锏。尽管连它们自己也未必就相信,单单靠这几滴尿就能让自己独霸一方。
我知道它们是绝对不肯一次性爽爽快快地把尿尿干净的。在狗身上,尿急尿频尿不净绝对不算是个毛病,结果我就大意了,直到我见它想尿又尿不出来,浑身抖着抖着就“砰”地跌倒在地上,四脚乱颠,我这才意识到异常,就赶紧送它去宠物医院。
医生事后告诉我,要是我再晚送半个小时,它就没命了。医生当即动了手术,将它体内憋了个把礼拜的尿液全部导出体外。那个量,乖乖,吓得死人的。医生说朗朗的生殖器感染了,有炎症,不但红肿,而且把尿路堵死了,它压根儿没法尿尿。我都不敢相信,这世上还真有被一泡尿憋死的事情。医生警告我,你可不要轻视了,平日要注意卫生呵!
这话说的,就像是我身上不洁似的。
但我没有去反驳他。
朗朗术后还要在医院里观察一周,才能健康出院。
从那以后,我就每天给他洗澡。我就不信,在我家里,这样的事情还会发生第二次。
我相信朗朗不只是为了有一口吃的,也不只是以宠物的身份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的,它是我唯一的闺密与知己。但凡我情绪低落或郁闷的时候,它比他都看在眼里,它比他都心里清楚,就噌地跃到床上,扑进我的怀里。我会和它说话,交流思想,我都不愿意和他诉说的那些事,我都会跟它说。而它会用前肢轻轻地抓我的衣服,吻我的脸颊,乌溜乌溜的眼睛盼着我笑,汪汪地回应它听懂了我的话,表示理解……这种相依为命的感觉,为何只在人与狗之间产生呢?我好生感动,也好生奇怪,这世上的人都干吗去了?
我现在越来越不愿意和人说话。
但我每天和朗朗有说不完的话。
我和他是春天结婚的,到秋天就怀上了。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我对培育自己的小宝宝怀有极大的信心,因为我从朗朗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我自信对养育人类的孩子也自有一套。可是,怀上三个月后,我却流产了。妇科医生让我先别再怀了,眼下把生命的伊甸园修复后再怀也不迟。我听进去了,直到第二年夏天,我才又怀上的;三个月后,气候刚进入秋天,我竟然再次流产了。妇科医生就怀疑我是习惯性流产。
这个问题就大了,就严重了,得查清楚。
于是,我就跑医院使劲地查。先查我的,没有问题。我又逼他去医院查,也没问题。于是,就再查他的精子与我的卵子结合后是否有问题。比如,两者犯冲相克。有时候会有这种情况,精子和卵子自身都没问题,但结合到一起就会相互伤害,像天生的死对头,聚到一起就非得你死我活,结果就两败俱伤。但我们还是没有问题,那就奇怪了。于是,再查我们的生活环境。当妇科医生得知我们养了一条狗,而且我和狗比较亲热,连睡都睡在一张床上时,这位早已进入更年期的妇科医生,终于松了一口大气,蛮有把握地感叹,这就难怪了。
她说了一大堆术语,估计也不是为了让我听懂,而是彰显她的绝对权威;然后她用专业的逻辑推理来告诉我,我两次流产的罪魁祸首就是朗朗。听了妇科医生的话,我不禁联想到朗朗身上的某种细菌,就像一根根细长的白毛,通过我的伊甸园直道,侵入孕育生命的宫殿,忽然变成一把把锋利的长剑,刺破呵护小生命的胎衣,将小生命残酷地杀死……
这么说,我们之前种种昂贵的检查都白忙乎了。
她还警告我,如果我不处理狗,在受孕到生产期间,我还是与狗有接触的话,就会造成习惯性流产,这么做的后果非常可怕:我即使能怀上孩子,孩子将来也会有胎里疾;又或者,我将再也怀不上孩子。她断言,如果我第三次流产,那我将因此而孤独终老。
这简直就是晴天霹雳啊!
这天夜里,我梦到自己被人开枪打死了。开枪的人是一个蒙面人,一身白衣,连蒙面的布也是雪白的。他朝我的腹部连开数枪,枪枪击中我的子宫,鲜血如注,在我的下身流淌成河。我倒在一片黑土地上,构成了三色板:黑色土地、白色蒙面人和红色的血泊。
我惊出一身冷汗,醒来像自己真的已死过一回。
可是睡在我身边的他倒好,竟然因为是朗朗的缘故,而大大松了口气,甚至轻飘飘地对我说:“妈咪,我们先把它送去我妈家养吧,等我们有了孩子,再把它接回来嘛。”是呀,我们结婚三个年头了,公公婆婆眼巴巴地盼着抱孙子,盼得眼珠子都酸了。而且之前我已经让他们从惊喜突然掉进失望的冰窟窿里,一次不够还来了两次,这下可不能再有第三次了。
痛定思痛,只有忍痛割爱。
经过几天几夜的思想斗争,我终于狠下心来,为了家庭的长治久安,只能暂时牺牲小爱了。我和朗朗亲亲密密地度过令人终生难忘的数天后,决定在第二天——也就是周六——的傍晚,将它再次寄养到公公婆婆家里。就在我与它即将告别的这天早晨,我最后一次牵着它去外面散步。我在外面把它的牵绳给解了,我就想让它自由自在地奔跑一回吧。
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念头,事后把我的肠子都悔青了。
自由还真不是个什么好东西,当朗朗横穿斑马线时,一辆飞驰而来的捷达汽车将它撞飞了。先是把它抛到前面的马路上,然后又一次从它身上碾了过去。我的朗朗哪里还有什么活路呀,一个活生生的小生命,顿时就像一只压爆的气球,在马路上只留下飞溅的血泊和血肉模糊的肉饼。
这时候人行道上是红灯,我只能站在马路边眼睁睁地目睹发生的一切。
像一个噩梦。
为什么狗就不是人呢?为什么狗能够把人当狗一样看待,而人却不能把狗当人一样看待呢?为什么当它横穿马路时,汽车就不能慢下来或停下来,让狗安全通过呢?
为什么?
难道悲剧发生时,死去的仅仅只是一条狗吗?
我的朗朗走了。
这往后的日子,我非常想念它。门铃响起时,家里不再有吠声。我回家晚了,也没有谁在那里焦急地等着我,更不会在我走到楼梯口时,它就夸张地汪汪两声,亲切地和我打招呼,然后冲锋一般赶到家门口,鼻子印在铁门板上,都挤得扁扁的,呜呜地朝门外的看不见的我撒娇;一旦我开门进去,它就兴奋地抱住我的一条小腿,头仰了个天,一对狐狸般的黑眼睛,水汪汪地盯着我,渴望我把它抱在怀里,抚摩它,亲吻它,就像我的爱人。
不,它比我的爱人还爱人。
然后,这一切都成了回忆。
令人伤心的是,我在家里,在我们的床上、沙发上和衣服上,还能到处发现它的白毛。我称之为朗朗的头发。我把它们细细地捡了起来。我知道我应该把它们扔掉的。他也是这么强调的,他做我的丈夫已经第三年了,说话口气再也不似当男朋友那几年温柔,他都不知道自己的口气硬了多少,尤其在对于朗朗的问题上。或许他还是不肯原谅它吧。毕竟因为这只狗宝宝,让他的人宝宝夭折了两次,让他失去了两次当人类爸爸的机会。但我一再地和他争论,直到我说他跟一只已经死去的狗有什么好争时,他才软下来。
死者为大,哪怕是一只狗,他也是争不过它的。
在我心里,朗朗永远是我的朗朗。
我说:“那是我们仅剩的和朗朗有关的东西了,我不愿意把它们扔掉,我甚至有一个疯狂的愿望——只要我们收集到它足够多的毛发,我们就能把朗朗给拼凑回来。”当然,这里的“我们”,仅仅是指“我”,他是不可能会有这种愿望的。尽管他知道它的毛发对我,或者说对我们孕育下一代是有害的,但他还是容忍我这么做。他应该清楚我是收集不到这么多白毛的,我的愿望完全是痴心妄想。结果不出他所料,我只收集了拳头那么大的一团白毛,我把这团白毛装在一只很小的塑料袋里,扎住了袋口,然后藏在一只装饰布袋里。
他倒是勤快的,在我收集完白毛后,他就把家里彻彻底底地清理了一遍,干净到一尘不染。
我还不知道他的小心思呀!
我本想拼凑不了整只朗朗的话,至少能拼凑到一只狐狸般的小脑袋,但就是这个,也是不可能的了。那一小袋狗毛,就静静地挂在我们书房里那只竹书架上。
第二年春节来临时,他在家里大扫除。清洁到书房时,就大声地问我,这只脏兮兮的小袋子还要留着吗?确实,大半年下来,装饰布袋蒙尘了,看上去很脏。我撑着粗腰,肚子里已经又有了五个多月大的胎儿。我犹豫再三,在他第三遍这么大声问时,我才吞吞吐吐地说不要了吧。他就迅速将它从书架上摘下来,扬手就扔进垃圾桶里,而且一投一个准。
我的朗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