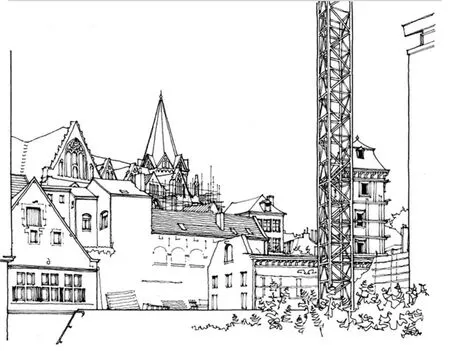
遇见特木尔,绝对是偶然,如果特木尔遇到了其他人,就与李春阳没什么关系了。可那天就那么奇怪,下了零点班,他没有和以往那样,回宿舍补觉,而是鬼使神差地走向了草原。草原深邃,蓝天白云,没有悠哉的牛羊和骏马。他突然想把自己变成马,在草原上撒欢儿。这也难怪,和秦老大的五年之约,日子一天天近了,原本期待的心情却淡了下来,就像眼前的草原一样,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他回头望向中转站,绿色的围墙护栏里,银光闪闪的六座庞大储油罐,白色的房子蓝色的边檐,被纵横交错的粗壮管道悬空连接在一起,两根百余米高的烟囱吐着火舌。与中转站相邻的,是一座五层的灰色大楼,顶部是红色的。大楼的两侧是两层的小楼,这些建筑同样都被绿色的护栏围着。中转站和办公生活区的地面都铺着灰色的水泥地面,两者相连的,是一条水泥路,如果从空中鸟瞰,像镶嵌在草原上似的。工作区和办公生活区泾渭分明,加之四周散落的抽油机,形成了草原上独特的一方世界。
这是个远离尘嚣的天地,离最近的巴尔虎旗还有一百多公里。两年前,他读了一年多采油培训班,从油城坐了一夜火车,在海拉尔总部集训了一周,就被大客车送到了这里。同行的十二个男女,离开市区看到一望无垠的草原,都惊喜得坐不住了,欢呼雀跃难以自制。但没多久,眼里就剩下枯燥和疲惫了。大客车如一叶轻舟,在没有尽头的草原上飘荡,偶尔有吃草的羊群,漫步的牛马,还有零星的蒙古包。两小时后,有人问司机还有多远,司机是个中年汉子,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说,快了。坐在副驾驶位置的陈干事,一脸灿烂地扭过身来,倡议说,我们唱首歌吧,我起头,“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他率先唱了起来。
远处有百灵鸟在歌唱,他闻声望去,看不到踪影。他有种迷离之惑,仿佛在梦境中醒来,一切又回归于本真。昨天,秦老大在视频里对他说:“老五,我这就等你了,五年,真快。”
秦老大霸气,大学报到的第一天,李春阳就被这份豪爽折服了。
同寝六个同学,报到那天就按照年龄排好了名次。秦老大说,既然我是老大,晚上我请兄弟们撮一顿。喝了一杯酒,同学们都血气方刚了,名字用数字代替了。李春阳对李五这个新称谓很适应,胖三有点抵触,他说你们不能把我的姓丢了吧?秦老大说,丢不了,毕业证上有。或是排行靠后,李春阳以秦老大马首是瞻。秦老大家是鸡西开煤矿的,有钱就是有范,再说吃人家嘴短,腰也不直溜。第三次聚餐的时候,王老二提出AA制,大家举双手赞成,只有胖三略有失望。胖三家是伊春的,父母都是林场工人,下岗后他父亲开出租车,母亲开了家小超市,这样的家庭不应该寒酸吧?开学的第二个月,胖三就贷款买了部苹果手机,还说什么是自食其力,这让靠父母的同学都汗颜了。胖三说,谁家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都是父母汗水摔八瓣挣来的,我爸起早贪黑骑电驴子跑活儿,他问我每月生活费要多少?我说五百,我妈不干,说这咋够呢,饿瘦了咋整,没办法,就定成了八百。告诉你们,我下个目标是苹果笔记本。
胖三话里话外大家都懂,秦老大沉思片刻,果断地拍了下大腿说,胖三的钱算我的。在大家没反过味儿的时候,胖三不愿意了,他瞪着秦老大说,老大,如果是你挣的钱,兄弟笑纳了,可都是家里给的,兄弟受之有愧。谁都没想到胖三这么有骨气。秦老大先是一愣,随后就哈哈大笑起来,用赞赏的目光瞅着胖三说,行,胖三,这话接地气,哥们儿聚时你要缺席,看我不踢死你。胖三扬了下脖子说,行,缺席,哥几个一起踢我。
李春阳哭笑不得,胖三典型的穷装,昨天在食堂吃饭,就鼓动他一起卖贺年卡。胖三胸有成竹地说,虹博地下批发市场有货,两毛五一张,最贵的批发价才五毛,快过年了,咱们学院有两万多学生吧,一张赚五毛,就发了。见李春阳没反应,就伸手搭在他的肩上说,兄弟,这是个机会,小试牛刀,咱们入学的时候,你看学长们向咱们推销过锁吧,还有床垫子,你不也买了吗?李春阳心不在焉地说,三哥,咱们上高中玩的东西,这可是大学,太俗气了吧?胖三心有不甘,在李春阳肩上拍了两下说,大学怎么了,我调查过,大一的学生都会给同学互寄贺年卡,千里相思寄卡中。
现在想来,李春阳不禁感慨万千。此刻,他坐在草地上,看着远处的抽油机,一上一下地叩着大地。钻出泥土的小草一寸多高了,还有紫色、黄色的小花儿,贴着地面昂起了花蕊,在春风中颤动着。他随手牵下一朵花,这么美丽的小花,怎么是草原的毒瘤呢?蒙古族的员工是这么说的,他没好意思问。记得第一次看到草原时,草原像大海一样,在他胸腔里波涛汹涌,这种美带给他无尽的向往,有了一种久违的感觉。对母亲的怨与恨,在这个绿意盎然的天地间淡化了。
大学毕业那年,母亲还愁眉苦脸地纠结,说你那死爹也没本事把你弄回油田,你说早几年多好啊!油田年年招工,咱娘俩的点儿怎么那么背呢!嘤嘤的哭声从电话里传来。他安慰母亲说,妈,您放心,我和几个同学约好,到杭州发展了。他心里话没敢对母亲说,在学院的招聘会上,他抱着简历经过了石油招聘的条幅,秦老大说得对,资源型企业发展都是有限的,说他父亲挣得盆满钵满,转行搞房地产了。什么铁饭碗。李春阳想到了父母,不禁悲催起来。他相信,他的计算机专业、满学分、学生会干部,这硬件投给石油一投一个准。
秦老大送他到机场,痛心地说,兄弟,谁让你是独生子女呢,陪在父母身边,也对。秦老大有两个姐姐,他的话语间带着同情。秦老大张开臂膀,用力抱了抱他说,老五,等我打下一片天地,你就回来,五年,怎么样。李春阳用力点着头,泪哗哗地流了下来。他说,老大,我让你失望了。秦老大说,天大地大没有父母大,哥理解阿姨。
到杭州创业,除了胖三和陈六,其他人都跟秦老大来了,还把他家在杭州的房子当成了根据地。哥几个各有分工,被秦老大安排到了不同的影视公司里。秦老大的要求是,把制作手法学到手,最好能复制拷贝到软件,他负责熟悉市场。秦老大高瞻远瞩目标明确,在实践中摸索,五年内成立公司。大学的时候,秦老大是校电视台的记者部主任,兼职主持人。李春阳是节目制作,两人一个镜前一个镜后,配合得严丝合缝。正要着手创业的时候,母亲的电话打过来,说有好消息通知他,而这个消息,对他无疑是个梦魇。
母亲痛哭流涕地说,阳阳啊,有个正经工作妈才安心,从小到大妈容易嘛,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培养你上了大学……难怪母亲伤心,在他成长的路上,母亲都安排好了,各种补习班目不暇接,他就像个陀螺,转得慢了,母亲就会给上不疼不痒的一鞭子。
五岁那年,一个暴雨梨花的夏天,母亲用塑料布把他包裹得严严实实,然后就抱起他下楼。他坐在自行车后架上,母亲推着自行车,艰难地往书法班走。书法班在艺术活动中心的二楼,老师是个长头发的瘦男人,有一面墙上贴着老师的获奖作品,还有复印的获奖证书,另一面墙上贴着学生的作品。他说不上喜欢但也不排斥,第一次去,认认真真地临摹了老师的横,老师看了,夸赞说有天赋,起笔落笔水到渠成。母亲兴奋不已,说我家阳阳就是悟性好,一岁多就在墙上画画,不让画就哭。老师捏了下他的鼻子,爱惜地说,有天赋。
母亲的蓝色条纹塑料雨衣扎得严实,身上绑了两条绳子,口也扎紧了。母亲一手扶着车把,一手扶着他,路上积满了水。风呜呜地吹着,扬起的雨珠打在身上叭叭响。红色的雨靴踩在水里,溅起了水花。李春阳在杭州听到母亲电话里的哭诉,脑海里就出现了那双踏水而行的雨靴,那雨靴像是血染红的,勇往直前义无反顾。
而如今,他转了一圈又回来了,母亲那激动兴奋的神情,仿佛中了一千万的双色球彩票。安排他到天价补习班恶补了两个月,以第五名的成绩考进了采油班,这种回炉重造绝对是创举,颠覆了知识改变命运的初衷。他打电话告诉了秦老大,秦老大说,可惜了你四年大学了。李春阳说,我算个屁,班里还有研究生呢!秦老大说,当初不拦你就好了,签回去就是干部了。李春阳说,拦得对,在杭州三年,让我受益匪浅。秦老大说,什么意思,我欺负你了?李春阳说,谁都他妈能欺负我。
人的生命,就像草原的草,需要阳光雨露。李春阳这么想着,就看到不远处的那片花海,兴奋地跑去拍照。他躺在花海里,黄色、白色、紫色的花朵争奇斗艳,他的思绪飘到了蓝天上。远处传来了马蹄声,他坐起身来,看到一匹枣红马急奔而来,马上的人影挥舞着马鞭。近了,那马嘶鸣了两声,停在了十米远的地方,一个戴着宽檐毡帽面色黑红干瘦的男人跳下马,露出了一口白牙说,兄弟,是石油人?李春阳站起身点了点头。
那就好!干瘦男人松了马缰绳,右手的马鞭向地上的花抽了一下,嘿嘿笑了起来。
李春阳毛骨悚然,牧民们抵触油田开发,说是打的井抽去了地脉,草原的水没了,草原的毒花多了。李春阳听了有些困惑,花点缀着草原多漂亮啊!现在,他盯着走来的男人,深吸一口气,肌肉紧绷着攥紧了拳头。
干瘦男人掏出了烟,向李春阳走来,这是个善意的举动。李春阳脸上挤出了笑,和牧民处好关系,牧民是水,石油人是鱼,鱼水情深。来油田报到的第一天,培训的老师就多次强调,作业区的经理书记队长班长都千叮咛万嘱咐。
我叫特木尔,来,抽支烟。走到李春阳的对面,干瘦男人自我介绍,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递了过来。李春阳迟疑了一下,接过了香烟,笑着说,我叫李春阳。
这个叫特木尔的男人头发蓬乱,深蓝色的夹克服,灰色宽松的裤腿塞进了皮靴子里。他低头从烟盒里叼出一支,就把烟盒装进衣兜里,随手带出了一只绿色的打火机。他用胳膊夹住马鞭,另一只手挡着风,示意李春阳点烟。
这是李春阳第一次接触真正的蒙古族人,按照当地划分,草地蒙古族才是真正的蒙古族人,作业区在当地招的蒙古族员工,与汉人没什么区别。
特木尔说话舌头发硬,似乎不会打弯。他说在附近放羊,听说石油人的手套好,想要一双。李春阳想都没想,就让他在这里等他,小跑着回驻地了。李春阳在宿舍找了两双线手套和两双喷胶的布手套,急匆匆跑出办公楼,看到特木尔骑着马,在大门口等待着。他看到了李春阳,就跳下马,满脸的兴奋。
特木尔绝尘而去,李春阳若有所思,蒙古族人太直接了,接过他递过去的手套,跳上马就走了。至少,得说句谢谢吧。李春阳突然惆怅起来,他选择到草原上工作,也是一种逃避。当初母亲逼他回来,他的心情一直压抑着,光明和前程断送了,他还无力反抗。他偶尔向秦老大诉苦,秦老大安慰他说,怎么都是活,有吃有喝抱怨个屁呀。秦老大突然转变的态度,让他的心拔凉拔凉的,转念一想,秦老大肯定受挫了。这些年自媒体如雨后春笋,网红都带货了,秦老大的影视公司肯定要挺不住了。
目送特木尔消失在草原深处,李春阳回宿舍补觉了。作业区倡导家文化,室外有篮球场,室内有台球、乒乓球和羽毛球场地,同事间相处和睦,工作氛围融洽和谐,没有尔虞我诈。过生日食堂还有长寿面和生日蛋糕。但在他的心里,自己不过是个过客,与同事间的交往,都蜻蜓点水。人情薄如纸,交往深了绝对不是什么好事情,在杭州的时候,不论到哪家公司,起初大家见面都互相客气,实质是互相防范,虽然不争吵,可也没笑声,让人如履薄冰,一不小心,就掉到阴冷恐怖的深渊里。
但用不上两个月,矛盾就莫名地浮现出来,谁不想干来钱快又轻松的活呢。工作间永远是最阴暗的,他面对电脑编辑画面制作特效,嗡嗡的机鸣声和叭叭的敲击键盘声,想说句话都找不到对象。而在作业区,想不说话都难,吃了吗?几点班?晚上打球去呀?虽然都是客套话,但充满了真诚。这样的环境到了秦老大的嘴里,却说成了混吃等死。他说,人脱离不了动物的本能,丛林法则你懂吧?就是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弱肉强食。李春阳若有所思也不反驳,每月拿着比杭州低了两倍的工资,心里就有了躁动和期待。
办公楼前的篮球场上,几个人在打半篮,看到了李春阳,有人停下来喊他,春阳,过来扔两个?他摆着手说,不了,下夜班,补个觉。有人问,骑马的兄弟是谁呀?他说,特木尔,来要手套的。
李春阳的工作是三班倒,每月有八天假回油城休息。起初,母亲不挑剔他的工作,只要是个铁饭碗就行。可现在变了,张罗着给他调工作,如果没个好工作,找个媳妇都难。他觉得母亲咸吃萝卜淡操心,高中就有过女朋友,大学交往过两个,如果不是看女孩奢侈虚荣,他不会放手的。秦老大就说他不会脑筋急转弯,上了床解决问题再说,可他怕说不清。
一个月前,胖三考上了公务员,在视频里喜形于色。同学里胖三攀比心最强了,贷款买的苹果手机刚入手,就和他的三星手机比,对六寸屏的三星赞不绝口。这手机就是屏幕大,但没有苹果精致,你们看这手感都不一样。言外之意,李春阳的手机不入流。靠在床头打游戏的秦老大看不过去了,挖苦胖三说,胖三,你真是个穷逼,下里巴的眼光,李五的手机能买两个苹果。胖三惊得哑口无言,结结巴巴地问,李五,老大说的是真的吗?李春阳笑了笑,不置可否。秦老大说,你上网查查。胖三真查了起来,过了一会儿,笑呵呵说,老大,能买一个半,你夸张了。
李春阳的手机是高考后第二天买的,母亲带他到市里最大的电器城,在手机卖场,给他选了新款的苹果手机。母亲笑眯眯地瞅着他说,阳阳,妈以前不是舍不得钱,就怕你和同学攀比影响学习,高考完事了,咱就买最贵的。他嗤之以鼻,没有攀比心是假,只是不表现出来。他说,妈,我的手机挺好的。母亲说,上大学了,咱不能比别人差,会让同学瞧不起的。他说,能不能考上还说不上呢。母亲说,儿子,要对自己有信心。李春阳讨厌苹果,泛滥的牌子显不出个性来。他犹豫了一会儿,瞅着玻璃柜上的苹果手机说,妈,我不想和别人用一样的。母亲怔了怔,很快回过神来说,是呀,我儿子是谁,咱要找个比苹果还苹果的,让人咬了一口的苹果,多恶心啊!
特木尔是三天后来的,他骑着马在办公楼的院子外高喊,李春阳,李春阳!他隔一会儿喊两声。在书记的眼里,李春阳稳重寡语,别看长得人高马大,不是惹是生非的人。书记考虑到民族矛盾,就警惕地打电话到中转站,让李春阳赶紧回来平事儿。
特木尔看到从中转站跑出来的李春阳,就策马扬鞭迎了上去。他手里还牵着一匹白马,目的不言而喻。
特木尔探了下身,把缰绳递到李春阳的手里。他毫不犹豫地接过缰绳,手扶着马鞍,脚伸进马镫,双膀一较力,人就飞到了马上。李春阳骑过马,是在杭州的一个马场,秦老大拍宣传广告片,他装公子哥,在驯马师的指导下,策马奔腾了一回。
在特木尔惊诧的目光中,他一气呵成地完成了这些动作。特木尔没再说话,一提缰绳,双腿猛地磕了几下马肚,那马咴儿咴儿叫了几声,箭一样向草原深处射去。李春阳调转马头,没待他喊驾,这白马通了灵性似的追了上去。
特木尔呼喊着,声音如天空的飞鹰长鸣,尖锐地冲霄而上。李春阳被感染了,把内心的抑郁都在号叫中宣泄了出去。
敖包附近有一棵榆树,树龄有百年以上了,奇形怪状的树干充满了沧桑,枝叶蓬勃伸展开来,像一个巨大的伞。这是百十公里唯一的一棵树,是长生天授意让鸟儿带来的种子。特木尔说着,就在树下跳下了马,他一屁股坐在地上,从怀里掏出了一瓶二锅头,还有塑料袋装着的马肉干花生米,他把拧开瓶盖的酒递给了李春阳,目光灼热充满了期待,豪气冲天地说,李安答,喝。李春阳坐在他身旁,接过酒瓶仰脖喝了一大口,火辣辣的液体冲进了喉管,呛得咳嗽起来。特木尔递给他马肉干,他抓过来用力咬,没咬动,他只能含在嘴里,冲特木尔笑。特木尔又拿起一条马肉干,用指尖撕成了肉丝,一条条地如火柴棍那么粗细。
特木尔说,你们喝酒吃,不好,我,尊重安答。他把塑料袋放在李春阳面前。花生米好,油炸的,香。他抓出几粒,一粒一粒地送进了嘴里。
特木尔在海拉尔读过中学,毕业到饭店打过工,家里牛羊多了,父母照顾不过来,前不久又回到了草原。他说城市好,热闹,有酒。李春阳说,还有KTV。特木尔说,KTV不好。蒙古族人能歌善舞,KTV就是唱歌跳舞的地方,怎么不好呢?李春阳疑惑。看特木尔的年龄,与他相仿,怎么才读到初中呢?
特木尔说,城市好!
李春阳问,城市好,为什么还回来呢?
特木尔摇了摇头,又摊开双手说,没文化,工作,找不到好的。
李春阳把酒瓶递给特木尔,若有所思地撕着马肉干。特木尔接连喝了两口酒,注视着碎石堆起的敖包。那敖包不是很大,上面插着几枝干树枝,树枝上挂着红色、蓝色、白色的布条。
李春阳说,特木尔,你们为什么说草原上花是毒呢?特木尔说,开花的草原,就没草,羊不吃,饿死啦。
李春阳看向吃草的白马,那是匹温顺的马,一路行来,跑得平稳、不急不躁,他说,特木尔,你的白马漂亮。
特木尔笑了,眼睛眯缝着瞅向白马说,阿茹娜的马,她到北京上学去了,让我照顾它。特木尔又补充说,我妹妹阿茹娜,像白云一样纯洁,她学习好,上了民族大学。他加重语气说,北京!首都!红太阳!
李春阳眼前浮现出一个漂亮的姑娘,穿着蒙古族色彩绚丽的服装,在翩翩起舞。
特木尔抓起了酒瓶,喝了一口,嘴里哼起歌来。李春阳起初没听懂,以为是蒙古的长调,他跟着特木尔哼哼,渐渐地,他找到了韵律,情不自禁地哼唱起来……教拳脚武术的老板、练铁砂掌、耍杨家枪,硬底子功夫最擅长,还会金钟罩铁布衫,他们儿子我习惯,从小就耳濡目染,什么刀枪跟棍棒,我都耍得有模有样,什么兵器最喜欢,双截棍柔中带刚。特木尔突然提高声说唱起来,想要去河南嵩山,学少林跟武当,干什么(客)干什么(客)呼吸吐纳心自在。李春阳高声地喊,干什么(客)干什么(客)气沉丹田手心开,干什么(客)干什么(客)日行千里系沙袋。
特木尔的说唱声戛然而止,目光闪亮起来,流露出惊喜之色。他说,《双截棍》,周杰伦,你,喜欢?
李春阳点了点头。
特木尔伸手搂住李春阳的肩,激动地用力摇晃。我的,偶像。
李春阳承受着巨大的重力挤压,这力量来自特木尔对偶像的虔诚。周杰伦和 《双截棍》是他初三时喜欢上的。放学回家的路边,有一家学生用品超市,那里有笔墨书本,也有复读机光碟。有一天,他路过超市,门口的音箱播放着《双截棍》,当时他就蒙圈了,从没听过这样好听的摇滚说唱。
音箱里重复播放,他听了一会儿,就走进了超市,认识了穿着MV黑背心的周杰伦,果断地买了一本光盘。他开心地往家走,哼唱着,岩烧店的烟味弥漫,隔壁是国术馆,店里面的妈妈桑、茶道、烧烤……日行千里系沙袋,飞檐走壁莫奇怪,去去就来。他当时感觉很酷,简直酷毙了。回到家,他就拉着母亲去烧烤店吃烤串。后来,他的房间墙壁贴的都是周杰伦。他还特意跑到体育用品商店,买了一根木质的双截棍。上高中后,他喜欢上了篮球,周杰伦换成了乔丹、科比、勒布朗·詹姆斯。
特木尔遇到了知己,他站起身拉起李春阳往敖包走。在敖包前,特木尔点燃了三支香烟,并排摆在敖包的一块石头上,回身按着李春阳一同跪在地面上。他高声说,我,特木尔,今天与李结为安答,长生天做证。说完,他目光火热地注视着李春阳。李春阳感到心口发热,他高声地重复说,我,李春阳,今天与特木尔结为兄弟,长生天做证。
夕阳西下,草原笼罩着金色光晕,低伏的小草染成了浅绿、鹅黄的颜色,天边那牛乳般的云朵,也变得火焰般鲜红。作业区的大门旁,李春阳注视着一人两匹马,渐渐地融入光晕里,他心中莫名地泛起了五味杂陈。特木尔的率真令他猝不及防,所有的一切都是被动而为的。兄弟,安答,对这个突然多出来的兄弟,幸好没发誓说同生共死。
遇到特木尔,李春阳有种心灵被洗涤的清爽之感,他突然迷恋起这片草原了,轻声吟唱起来,呼吸吐纳心自在,干什么(客)干什么(客),气沉丹田手心开,干什么(客)干什么(客),日行千里系沙袋,飞檐走壁莫奇怪,去去就来……他仿佛看到了特木尔家的蒙古包升起的袅袅炊烟。他相信,与秦老大约定没有结束,和兄弟安答特木尔的交集才刚刚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