哗啦,哗啦!朱梅梅用力打开家里所有窗户,凉风一下子涌了进来。茶几上的一张小纸片被风吹起来,像一只白色的蝴蝶在空中飞舞。那是她昨天用来记菜谱的。自从她要帮儿子还房贷,待在店里时间就比较长,不怎么有空烧饭。难得做一次饭,总会忘东忘西。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上学的时候做老师的总是再三叮嘱,现在终于用到了。把要买的菜记在纸条上,省得到菜场又忘了。
她大口喘着粗气,一手叉腰站在窗前,另一只手张开像蒲扇一样扇着自己的脖颈,任那纸片在空中飞舞。仿佛如此一来家中的浊气和心中的浊气都可以一下子置换干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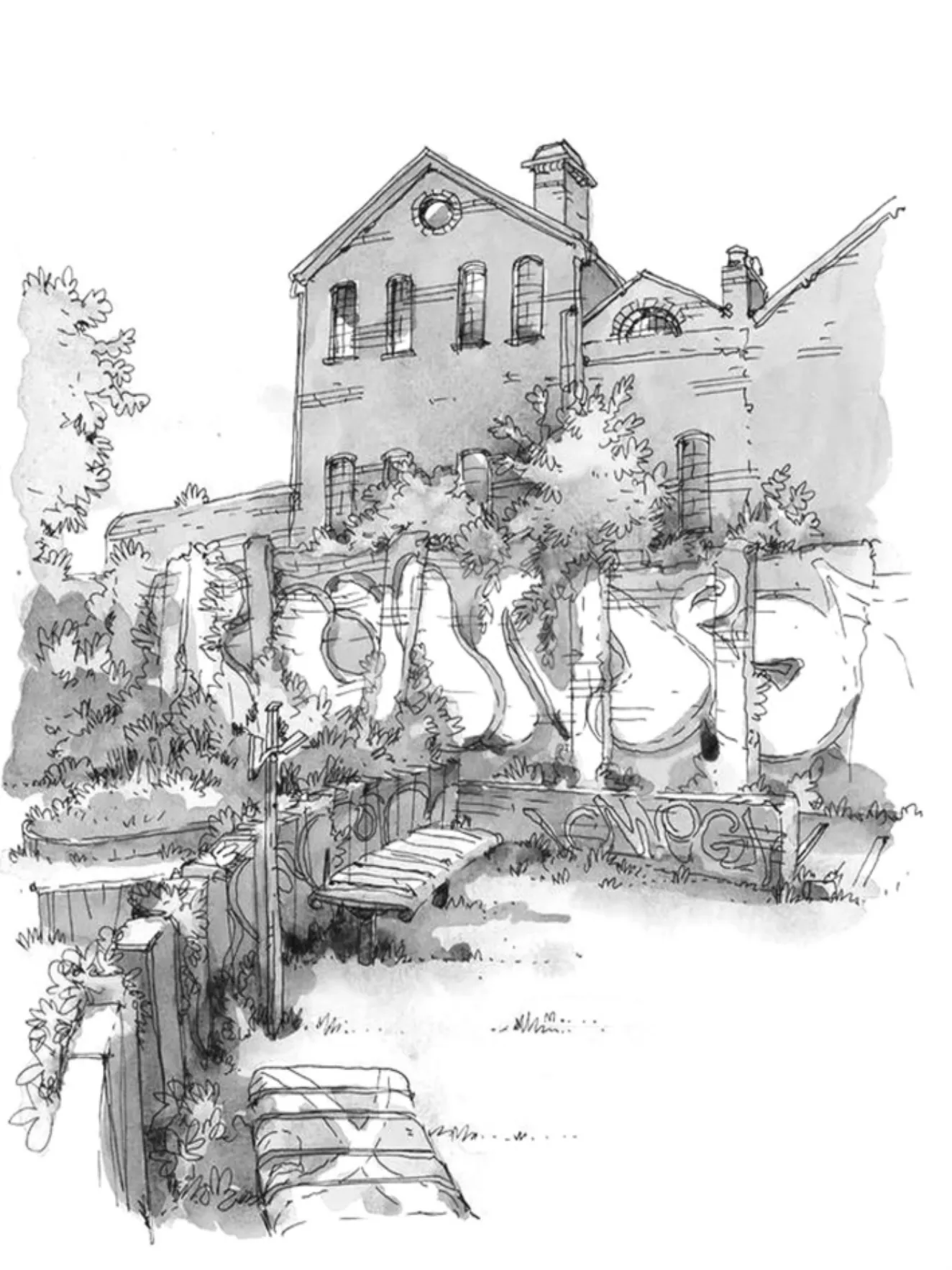
然后开始清扫。她先将厨房里昨晚烧的饭菜扔进垃圾桶,洗净碗碟。又去卧室,扯下床上条形图案的床单、被套和枕套,一股脑儿地皱成团摔在地上。然后把空调被和枕头都搬到阳台上去晒。热辣辣的太阳照得她睁不开眼睛。眼前突然一黑的她坐在沙发上闭上眼睛休息了一会儿,又生龙活虎地腾挪家具。把本来呈U字形的沙发,摆成面对面的火车座。餐桌则被横了过来,一头抵着墙。这一来跟顶上的餐灯就不对称了。朱梅梅抬头看看,管它呢,只要跟以前不一样就行。她本来还想将床和衣橱掉个个儿,床靠墙摆。那一边的床头柜也不需要了。她向那边空落落的床头柜瞥了一眼。这样一来,房间的空间会宽阔一些。但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她一个人无法完成。
忙完这些,她又翻箱倒柜,搜寻他落下来的东西。终于发现了漏网之鱼:一只袜子、一只漱口缸子、一支用旧的牙刷。她下意识地捏着鼻子,把这些连同换下的床单被套一起塞进一只大号塑料马甲袋里,放在门外。那支牙刷毛已经倒掉了。朱梅梅跟他说过多少回,刷牙要轻一点,这样才能保护牙齿和牙龈。另外,牙刷也要经常换,最好一个月换一次,顶迟也得三个月换一次。可他依然我行我素。说了也没用。朱梅梅明知道说了也没用,还是忍不住要唠叨上两句。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道理人人都懂,然而女人往往置之不顾,总爱做男人的生活导师,告诉男人这样不能那样不能,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女人总觉得那是为对方好,谁领情呢?郝晨实在忍不住了,就回她:“你管这么多烦不烦啊?”
房间里的光线暗了下来。她去阳台收被子,被子有些回凉,没有了太阳的味道。她把被子扔在床上,然后取出刚买的四件套给套上。这是她特意选的,樱花粉底色上缀满小红心,小红心又组成一个大的心形图案。那铺天盖地的粉以及一颗颗闪烁的小红心温柔地将她包围。现在这里是她一个人的天下了,她想要怎样就怎样,不必顾忌任何人的想法。她要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尽管此刻的心情依然糟糕。
朱梅梅满头大汗,累得浑身好像散了架。她先给自己倒了杯水,坐到餐桌边咕噜咕噜地喝下去。喘了两口气之后,感到风吹在脸上有一丝凉意,便去卫生间用热水洗把脸。她抬起头,被镜中的自己吓了一跳,那张脸竟然一下子苍老了许多,蜡黄、憔悴,好像几天几夜没有睡觉。她冷着脸对镜子说:活该。
倦意一阵阵袭来,她躺到客厅的沙发上,闭起双眼,灯也懒得开。此时,她四肢乏力,只想把自己放平,彻底地放下来歇一会儿。
自从今天早上郝晨拖着两只大行李箱离开之后,朱梅梅的心情就没有好过。郝晨啥也不说就走了,完全出乎她的意料。这一切让她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颓败感。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人生了。她真的搞不懂郝晨怎么会为了那么一点儿小事情就真的走了。也许他早就想走,昨天的事不过是一个由头。
那不是什么大事,这不是根本原因,朱梅梅知道。
暑假期间,郝晨的儿子从国外回来,他带儿子去西南部自驾游。出去了将近一个月。
昨晚郝晨一到家,发现家里花残柳败,顿生不快:“这些是怎么回事?”朱梅梅正在厨房里做饭。她今天特意早点回家,给郝晨做他爱吃的糖醋鳜鱼。当时她正对着手机百度上的操作步骤准备炸鱼,听到外面动静,知道是郝晨回来了,赶紧关了煤气,迎了出来。没想到一出来就看到郝晨臭着脸。啥也不问,先问他的那些玩意儿。朱梅梅也不大高兴了,便说:“你不知道我们去上海检查?”
“你中途就不能先回来?”
“我中途回来?带着我妈?来回几百里路?就为了你这些花?”
郝晨旅游的那段时间,朱梅梅回家看望她的父母,父亲告诉她母亲体检查出肺部有结节,她便带她母亲去上海检查。去上海看病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各种排队就要耗去许多时日。好在有亲戚的房子借给她们住。朱梅梅想这两年子宫肌瘤一直在长大,当地医院的医生建议她切掉,自己不如顺便也到红房子医院去查一查。
虽然两人都没事,但这样一折腾,两个星期就过去了。等回到家里,郝晨养的那些曾经生机勃勃的花和绿植全蔫了。
“我从福建山里运回来的,八百多公里日夜兼程辛辛苦苦,你根本不在乎!”
朱梅梅问他:“难道我不如你的这些花花草草?”
“你这什么意思?这是两回事。”
“我在你眼里根本就不如你这些花花草草!”
“你纯属无理取闹,这本来就不是一码事。”
“我们检查的情况,你问过吗?”
“你肯定没事,这我知道。你这人一贯很虚,总是怀疑自己这里那里得什么病,每次都这样,不都好好的吗?再说,有问题,你不早就说了?”
“难道你希望我有问题吗?”
“莫名其妙,无理取闹。”
郝晨把行李箱一脚踢到墙边,一屁股坐到沙发上,然后盯着那些枯枝败叶抽烟,便不再说话。
朱梅梅解下围裙,把它挂在餐厅的椅背上,又“啪”的一声将餐椅推到餐桌肚里。郝晨似乎什么都没听到,继续抽他的烟,目光透过袅袅上升的烟雾投向遥远的虚无,一脸忧伤。
现在朱梅梅再也看不上郝晨那副忧伤的神情了,而且相当反感他那副死样子。每次争吵过后他就那副死样子。一声不吭,任你怎么说,他就是不睬你。你打出去的拳头都落在棉花上,让人心里憋得慌。朱梅梅知道没啥好说的,便去卧室躺下。
直到半夜,听到客厅里的呼噜声,朱梅梅知道今天的争吵到此已画上了一个休止符。她蜷缩在大床的一角,翻来覆去睡不着。朦胧的月色从窗子照进来,那张空荡荡的大床在月色的笼罩下,显得格外空阔。夜深了,外面起了风,朱梅梅感到一丝凉意,便从床上爬起来到卫生间去洗漱。洗漱发出的一些声响也没能吵醒郝晨。刚才起床的时候,她发现脑袋胀胀的,冲了一个澡之后也没有减轻。也许是事情想多了。这一晚上,她的大脑不由自主、一刻不停地活动。她越想越觉得这样过下去真的没意思,还不如分手算了。她思忖着明天早上如何跟他说,她甚至在心里盘算,他走了之后她的经济如何安排。她还得从她有限的收入里再划出一部分用来付房租。想来想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
恍惚间门铃响了,难道是郝晨又回来了?今天早上他将自己所有的衣物装进两只大行李箱,然后将钥匙放在餐桌上,一句话也没说就走了。当时朱梅梅气愤地对着他的背影吼道:“今天从这里出去就不要再回来了,永远不要回来了!”朱梅梅走到厨房,看着郝晨的背影消失在后面一栋楼的转角,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用力打开厨房的窗户。
是不是他后悔了?朱梅梅可有点后悔今天的过激行为。她爬起来开了灯,用手梳拢一下凌乱的头发去开门。尽管如此,还是不能便宜了他,想走就走,想来就来,他当是菜市场啊?于是把脸拉了下来。打开门,外面站着的竟然是姜少春,还是那副油头粉面、油腔滑调的样子。
自打他们离婚后姜少春还没来找过她,倒是她去找过姜少春。找他商量儿子买房子的事。当时他赌咒发誓说一分也没有。害得她背着自己的弟弟,拿父母的房产去抵押了。难道他现在学好了?有钱了?良心发现了?朱梅梅心想,你姜少春要早点有些担当,我朱梅梅的生活也不至于落到如此地步。
郝晨离婚的时候是净身出户,也没有房产。他们是租房住的,想等孩子们都出手了,再买一套自己的房子。他们刚结婚那段时间,的确很快乐。朱梅梅的儿子刚好找到了满意的工作,郝晨的儿子还在上大学。他们只要负担郝晨儿子一个人,还不算太吃力。当然,除了生活费、学费,儿子还不时地发信息跟郝晨要钱,支付一些杂七杂八的费用。只是儿子来信息,除了要钱,跟郝晨几乎没什么说的。如果不要钱,从来不主动跟他联系。郝晨联系他,他也不拒绝,但是话很少,只回一个字“是”或“忙”。郝晨知道他离婚儿子心里不好受。婚虽然是他妈要离的,起因却在他这边。这让郝晨越发愧疚,总是想方设法关心儿子,主动问他要不要这要不要那。这次的自驾游也是郝晨攒下一年的年假主动给儿子的陪伴。这些都是不小的开支。“他儿子花这些钱我说过什么了吗?”朱梅梅心想,“我不过觉得只要孩子学习好,将来能找个好工作,我们就可以老无所忧了。在他那一边这一切好像都是理所当然,怎么到了我这里就成问题了?”
当初朱梅梅儿子的女友意外怀孕,只好匆忙结婚。孩子生下来没房子就无法入户,将来入学都是个问题。朱梅梅的儿子工作没几年。工资虽然不算低,但是在南京这样的省城,生活成本高,根本攒不下来多少钱。而他爸爸完全指望不上,他的钱都不够他自己吃花叨米的,怎么可能支持孩子?况且他也没那份责任心,他要有责任心也不会那样了。所以,这让朱梅梅很心焦。
那日晚饭后,郝晨坐在桌边玩手机,朱梅梅收拾碗筷。她刚把饭碗筷子摞起来,又坐了下来,看着郝晨说:“跟你商量一件事。”郝晨继续盯着手机,随口“嗯”了一声:“什么事?”朱梅梅说:“你能不能放下手机?”郝晨又“噢”了一声,过了一会儿,他放下手机,看着朱梅梅,但郝晨看他的目光并没有聚焦在她的脸上。朱梅梅知道这事儿不太好说。不过不管怎样总得要办,要办就得跟郝晨商量。朱梅梅提出先帮儿子付个首付。朱梅梅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这是她儿子的大事情,她不能不管,不能不帮忙。郝晨沉吟了半晌,方说:“照理,这事儿该他父亲负责。儿子是姜家的,孙子也是姜家的。”
“他父亲能指望上,我还用跟你说吗?”
“这是责任问题。”
“我也有责任。”
“……”
“他也是我儿子,我就这么一个儿子,我不帮他,谁帮他?”
“问题是钱从哪里来?欣欣快大学毕业了,这几年就业形势也不好。他说想出国读研究生。”欣欣是郝晨的儿子。
“哦,你儿子是儿子,我儿子就不是儿子了?”
“这不是一个钱、两个钱的事,关键是钱从哪儿来?教育费用,家长必须出。至于结婚买房,那就要看家庭条件了。有条件的嘛,支持一点也可以。没条件就另当别论。”
“欣欣不是还有一年多才毕业嘛,到时候再想办法。先把这事办了,你看房价日日看涨,越等越贵。我们手头的凑凑,还可以贷款,先帮他把首付交了。”
郝晨说这事儿得好好想想,好好斟酌斟酌。这一想一斟酌就没了下文。其实郝晨心里的小九九算得噼里啪啦的,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除二。现在是买婚房,以后结婚、生孩子、孩子上学等,无休无止。供养一个孩子还算宽裕,供两个,就难了。而自己作为儿子的父亲,一个男人,一定得有担当的。这是一个男子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也是无可辩驳的,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儿子的事怎么能推给女方?
朱梅梅等了多日,不见郝晨拿出个主意,便问他同不同意办贷款。郝晨支吾了半天说,那我要跟他谈谈,钱我们暂时帮他垫上,以后欣欣这边要花钱,他还得帮忙拿出来。朱梅梅听他说出这话,好似被一盆冷水浇了,冷到骨子里。还有什么意思呢?当时一个叫“外人”的词突然从她的头脑中冒出来。“外人,毕竟是外人。”朱梅梅在心里冷冷地说出这句令她幡然醒悟的话。就算是郝晨的收入高一些,朱梅梅也不想讨他的便宜,于是对郝晨提议他们AA制。郝晨说:“这可是你说的。”
郝晨认为如果他们的经济能够分开,彼此独立,可能更好一些,矛盾也少一些。不过他不想先提。
话虽由朱梅梅自己说出来,郝晨竟一口答应,还是出乎她的意料。这家伙该不是早就这样想了吧?那一刻她怀疑他们之间的感情,或者他们之间是否还存在着感情。一点点的经济问题都无法经受考验。在婚姻这个经济共同体和生育合作社里,他们生育合作已不可能,现在经济共同体也面临瓦解。那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室友?依她的性子,那会儿就想将郝晨赶走。冷静下来想一想,还是忍着了。主要是面子上过不去。已是二婚,当时闹出那么大动静,还过不好,不是又叫人家笑话吗?
姜少春本来是腆着个脸来的,没想到朱梅梅是这般情景。他将头探进屋里,左右张望了一下说:“你这是怎么了?郝晨呢?你们吵架啦?”
“你来干什么?”朱梅梅双手抱在胸前,挡在门口,并没有让他进来的意思。
“门也不让我进吗?你这也太不够意思了吧!”姜少春边说边往里挤。朱梅梅侧身一让,姜少春就一脚跨进屋里。
“噔噔噔,噔——”姜少春唱着从后面拿出一朵红色的鲜花,送到朱梅梅面前。朱梅梅瞥了姜少春一眼,哼了一声:“别拿那套对付你那些小妖精的手腕来对付我!有话快说有屁快放,老娘我还有事。”
姜少春把花放在餐桌上:“嘿嘿,这可是康乃馨,献给母亲的花,妈妈。”
“别放屁,谁是你妈妈?”
“你呀,刚刚你还自称老娘呢,现在又不承认了?你管了我那么多年,比妈妈还厉害。”
“切,我还管得了你?我若真的能管得了你,你还会不停地跟小丫头们勾搭?”
“就是你心眼小,我那不都是逢场作戏嘛。哪个男人不这样?难道郝晨不是?他怎么勾搭你的?”
“他跟你不一样,我们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的?他那时没老婆吗?”
“瞧你那副德性,我死的心都有了。我只想过安稳平静的日子,不想天天为你操心。”
那时,朱梅梅从一家半死不活的企业枯燥无味的会计岗位离职,开了一间茶社。因为姜少春在外面交了一帮狐朋狗友,替人家担保拿银行贷款。那人跑路了,银行找到他。为了保住姜少春的工作,他们卖了房子,还了债务,剩下的朱梅梅才开了一家茶社。主要想自己干,能多挣点,这家指望不上姜少春了。
姜少春爱玩,这是由来已久的。他是一个信奉享乐主义的人。市面上流行的所有的花头,他都乐此不疲。在外面游乐几乎占据了他所有的业余时间。从朱梅梅怀孕开始,他就经常不着家,没个深更半夜他是不会回来的。朱梅梅总是一个人孤寂地守着。多半就是捧着个电视遥控器,打发一个又一个漫长又无聊的夜晚。开始的时候朱梅梅还会打电话给他。他嘴上说快了快了,马上马上,墙上的时钟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就是到不了他的那个快了。朱梅梅本也是个爱热闹的人,可是怀孕了不方便外出。而姐妹们在这个年龄,也是各忙各的,生活仿佛一下子孤立了,就像海水突然退了下去,露出一个一个暗礁,每个人都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孤岛。一段时间,朱梅梅孕吐得厉害,以致夜不能寐,便打电话给姜少春。他竟然在那头嬉皮笑脸地说,哎呀呀,没事的没事的,女人怀孕不都这样?我又不是医生,回去有什么用呢?电话那头他的那帮牌友听了他这话,也都哄堂大笑。他那句“我又不是医生,回去有什么用呢”,成了经典名言,在他朋友间流传。那时那刻朱梅梅只是希望有人陪在身边,心里得到一丝慰藉而已,但是没有。朱梅梅只能独自落泪。那个时候朱梅梅常想,人为什么要结婚呢?特别是女人,结婚就是为了变成一只孤雁?直到儿子出世,朱梅梅的精力转移到孩子身上了。可姜少春玩着玩着,还玩出了花头。开始的时候,他也是掖着藏着的。但常在河边走,难免不湿鞋。姜少春也不是一个认真的人,又懒得去做得天衣无缝。朱梅梅跟他哭过闹过。姜少春反倒劝慰她说,不过是逢场作戏罢了,又不是认真的。家里还不是你做主,一切听你的。朱梅梅看到他一脸无所谓的表情,只觉得反胃。她也想过离婚,特别是他在外面给人家担保,将家都弄没了。但是想想孩子还小,怕对孩子有影响,便忍了下来。
姜少春伸手捋一捋朱梅梅的头发,叹道:“你看你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你可从来没有过这么不修边幅啊,头也不梳,妆也不画。是不是郝晨那赤佬欺负你了?我去找他算账。”
朱梅梅说:“有事去吧!要你管?该你管的你不管。儿子买房子,你干什么去了?哪里像个做老子的?你现在是不是良心发现,想帮儿子还贷款了?”
“我哪里有钱!我要有钱会不给吗?再说了,儿孙自有儿孙福,你也别老替他操心了。都把他培养工作了,对得起他了。”
“儿子是你培养的吗?你还好意思说。你一辈子都没钱。你这样不学好哪来的钱?家都被你败光了。”
“哎哎,别讲得那么难听好嘛,这家可是你拆散的。”
“我跟你过的是什么日子?我过得下去吗?”
“现在你幸福了?幸福成这样?”姜少春摊开手掌,将朱梅梅从头到脚比画了一下。
朱梅梅依然双手抱在胸前,抬起高傲的头颅说:“那也比跟你过强。”
郝晨是有次饭局之后,被人喊去茶社打牌,才认识朱梅梅的。
当时朱梅梅正在吧台里低头按计算器,听到有人来了,便抬起头来跟他们打招呼,安排服务员来收拾桌子、点茶、拿扑克牌。看她调配有度、指挥若定、干脆利落的样子,郝晨估计这女子就是老板娘了。后来他们常去打牌,有时候人不够,老板娘朱梅梅也过来帮他们凑场子。朱梅梅的牌风跟她的性格极为相似,敢打敢冒风险。
渐渐地,郝晨习惯了每天下班后去茶社报到,或打牌或下棋。没人时,朱梅梅也会跟他下两局,或只是陪他坐坐,偶尔也聊聊,聊象棋聊围棋也聊扑克牌。郝晨少言寡语,在那一帮牌友里是个另类。那些家伙总是吵吵嚷嚷,吵得认认真真。郝晨却淡定多了,仿佛置身事外,也有些心不在焉。有人怪他,他那略显忧郁的眼神就换成歉意的微笑。朱梅梅觉得郝晨那样子很特别、很迷人,像极了梁朝伟。朱梅梅说你打牌倒不喜欢吵哦?郝晨说,有什么好较真的,本来就是打发时间。朱梅梅就问他,天天那么迟回去,老婆没意见?郝晨摇摇头说,她每晚陪儿子学习,他回去反而碍事,电视也不让看,话也不让说,走路还得轻手轻脚的,跟坐牢似的。朱梅梅点点头说现在孩子教育确实是个问题。每家一个孩子哪个家长不上心?再说现在学校好多事都甩给家长了,检查家庭作业、听写单词,好像家长是全能。孩子累,家长更累。郝晨问她:“你家孩子呢?你天天在店里,他爸爸管?”朱梅梅说:“没人管,革命靠自觉。他爸爸自己还玩不够呢。”朱梅梅轻轻摊开两手,口气蛮轻松,眼神却无奈。
看姜少春那副吊儿郎当玩世不恭的模样,再看看郝晨的沉稳、大气,朱梅梅心想,人跟人的差别怎么就这么大呢?跟郝晨在一起,其实他们也聊得很少,大多数情况还是下棋。朱梅梅喜欢看郝晨白皙细长的手指夹着棋子停在半空中,凝神静气,然后轻轻地“啪”的一声在她面前落下。棋子落下的清脆的声音,就像一只轻巧的鼓槌,咚,咚,轻轻地敲击着朱梅梅的心。这种特别安宁温暖的氛围让他们迷恋。他们越来越觉得需要这样的陪伴。他们彼此对望的眼神慢慢柔和起来,渐渐地长出一片片羽毛,轻轻地、软软地撩拨对方的心田。
有一天,这样的宁静祥和突然被打破。那天他们没有下棋,在聊天。当他们正沐浴在彼此温柔的目光中时,一个女人冲了进来,“啪”地给朱梅梅一个嘴巴。郝晨抬眼一看,原来是他老婆。他的脸色顿变,惊愕了半天,对他老婆说:“你干什么呢?胡闹!”“胡闹?谁胡闹?”这个女人更是怒气冲天,索性将茶社砸了个稀烂。这样事情就闹大了。表面平衡一旦被打破,事态的发展就必定向某一处倾斜。郝晨的老婆可不像朱梅梅那样能忍辱负重,她毫不犹豫地将郝晨扫地出门。郝晨与朱梅梅的事情,就向着所有这类狗血故事的方向发展,毫无悬念。
今天姜少春突然跑过来,又不知道出了什么幺蛾子,以前朱梅梅也没少给他擦过屁股。
朱梅梅说:“没钱帮儿子还房贷,你来干什么?”
姜少春说:“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这几年我一直在流浪。”
姜少春又低三下四地说:“你能不能借我……”然后他伸出三个指头。
“三千?”
姜少春摇摇头。
“三万?”
他点点头。
“什么?要这么多钱干什么?又闯什么乱子了?”
姜少春摇摇头告诉她,是他现在的小女友的父母。人家一个二十多岁的黄花闺女,跟着他两三年了。女方父母不放心,逼着他跟她订婚,还要付给女方父母三万块彩礼钱。最近手头紧,拿不出来。问朱梅梅能不能看在以前的情分上出手相救。
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也只有姜少春这种人才能想得起、做得出这样的事来。当初离婚时,他的惊人之举,早就成了熟人间的大笑话。今天他又突发奇想。
当初朱梅梅找姜少春谈离婚的事,虽然姜少春并没有打算和妻子离婚,但他也没有不打算离。他对此事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不过,有一点他是有所谓的,那就是他不能这么轻易放她走,便宜了郝晨那家伙。于是,他就想了一个遭人耻笑的损招。
姜少春有好长时间不去茶社了。早先他倒是常在茶社陪客人打打牌,有时候也拿出老板的派头来管管这儿管管那儿,看上去一副妇唱夫随天下太平的样子。后来姜少春跟茶社一个小丫头不仅明里眉来眼去打情骂俏,暗里还搞到一起,搞得朱梅梅脸上很难看。于是辞退了那个小丫头,也不许姜少春再踏进茶社。
郝晨被他老婆踢出门之后,朱梅梅便让郝晨在找到住处之前,先住在茶社。她觉得事情因她而起,很是过意不去。茶社里有一间很小的杂物间,朱梅梅平常也用来午休。收拾一下,先让郝晨住着。后来郝晨干脆以茶社为家,俨然男主人。那天姜少春来到茶社找郝晨,那些服务员相互使着眼色,抱着幸灾乐祸的心理跟他打招呼:“嘿嘿,姜总来啦!好久不见。”姜少春也跟她们打趣道:“丫头们几天不见越发漂亮机灵啦,想我了吗?”边说边往里面一个小包间走。以前姜少春常来茶社的时候,郝晨就认识他了。那时候姜少春还跟他称兄道弟地套近乎呢。此时这种状态下见面好不尴尬。郝晨见姜少春进来,对他点了一下头,便坐在里边一言不发。空气似乎一下子凝固了。姜少春却笑嘻嘻地走上前,去拍了一下郝晨的肩膀道:“伙计啊,你抢了我的老婆,就想白抢吗?说得过去吗?”郝晨一脸疑惑地看着他。“不明白?”姜少春伸出三个指头捻一捻:“你得付给我损失费,也可以说是转让费。”“什么?你这是讹诈!到底是谁损失?梅梅跟你过不下去了,你不看你这么多年都干了些什么!梅梅跟你幸福吗?”“那是我家里的事,跟你无关。现在是你插上一杠子,不然我们不会离婚。我们这么多年也没离婚。现在是你毁了我的家,你就得付出赔偿。”“无赖,无耻。”郝晨轻声说道,也不看姜少春,像是自言自语。他压根儿不想跟这种人讲话。“谁无赖?谁无耻?你这个第三者还好意思说?告诉你姓郝的,你若不给我这个数,别想得到朱梅梅!”姜少春向郝晨伸出右手一正一反翻了一下。郝晨说:“你想钱想疯了吗?没有。”姜少春说:“那就一只手,五万。我老婆难道五万都不值吗?”郝晨不吭声。于是,姜少春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小纸条递给郝晨说:“这是我的银行卡号,什么时候到账我什么时候签字。”说完,拉门出来,门外的几个小丫头一哄而散。私底下,这件事又成了茶社服务员和那些常来的客人茶余饭后说笑话的谈资。人家都说姜少春把老婆卖了五万块钱。没想到在现代社会,这还能作为一个生财之道。
“哈哈哈——”朱梅梅大声笑道,“你怎么好意思这么想,这不是笑话吗?我们离婚,你要转让费,还嫌没被人笑话够吗?现在跟前妻借钱订婚,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亏你想得出。赶紧给我滚,都给我滚,通通给我滚,滚滚滚。”朱梅梅拿起桌上的康乃馨扔出门外。然后一阵拳打脚踢,将姜少春赶出门去。
朱梅梅关上门后,用尽所有的力气对着门外大吼:“去你妈的,都他妈去死吧!”然后一屁股瘫坐在地上,号啕大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