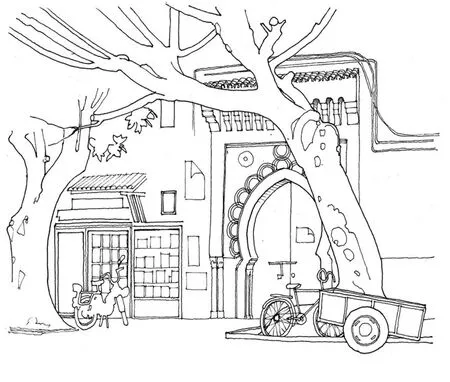
鸡叫头遍,富顺老汉就起了床,蹑手蹑脚把门打开一条缝朝院坝里张望。
月亮应该还在雾的头顶照着,这倒好,可以省了电筒照路。富顺老汉轻轻掩紧门,回身到床边叫老伴,你起来给四娃做点吃的,我们早点出发。其实不用叫,老伴已经翻起身穿上衣服了,正扣坎肩的纽襻。
灶屋里响起洗锅掺水与扒拉柴草声音的时候,四娃也起来了,虽然天黑后就早早地睡下了,但基本上都是迷迷糊糊地一晚没睡着。四娃摸黑往灶屋里去,想把猪草提前斩好。
四娃听见父母在小声说话。母亲说你去拿两个鸡蛋来,父亲说不行,再凑够三个就能拿街上去卖了。母亲就没再坚持,说你把火搭大些,我刮面疙瘩了。
灶台上点着一盏煤油灯,灶门口吐出来的火舌把篱壁照得红彤彤的,头顶上吊着的15瓦电灯泡便显得多余。
富顺老汉挽一把胡豆草准备往灶孔里送,转头见四娃进灶屋来,说再多睡一会儿,今天不要你斩猪草。四娃说睡够了,我先收拾一下。收拾啥呢?行李铺盖早都捆好了放在堂屋八仙桌上的,就等吃了饭出发。北京太远了,老早就得做好准备。
四娃拿水瓢去石水缸里舀水。洗脸刷牙完毕,母亲已经把一大瓷碗面疙瘩端到八仙桌上,两包行李被移到板凳上了,电灯泡这时候不顾浪费地放射出耀眼的亮光,四娃感到有些奢侈。面疙瘩刚好满满的一大瓷碗,热气直往电灯上扑腾,倒像那灯泡冻得正需要吸热气似的。
四娃望了一眼电灯又望着瓷碗里的面疙瘩,说这么大一碗吃不完。你给老子装秀气,莽起吃!富顺老汉板了脸说,你吃饱了好赶车,下一顿还不晓得哪阵儿才吃得上呢!四娃就埋了脸喝口汤吃点面疙瘩,又喝口汤吃点面疙瘩。
今夏收成好,五百斤麦子封存在好几个釉缸里,要吃的时候舀一瓢出来,去灶屋旁边的石磨上磨了,拿箩筛反复筛,麦麸喂猪长膘,面粉人吃。今年家里没去大队农机房做挂面,母亲说吃到肚子里都是一样的,不去花那个冤枉钱,父亲立即赞同说要得,挂面还莫得面疙瘩经饿。四娃当时站在一旁没吭声,虽然都是细粮,一样的东西,但挂面多一道工序,吃起来比面疙瘩入味,口感好。做不做挂面无所谓,只要不顿顿吃红苕酸菜就行。
四娃厌恶吃红苕,肠胃大概被红苕撑坏了,总是胃酸,像蚊子在心上冷不丁地咬了一口,大人们叫得形象生动,说是“叮心”,那股从肚里冒上喉咙里来的怪味刺鼻刺喉得恶心。
有一回四娃正“叮心”哩,母亲上楼解下吊在梁上的蛇皮袋,抓了一把花生来叫四娃吃。生花生治“叮心”疗效特别好,灵丹妙药似的。但花生多金贵啊,哪能每顿饭后都吃几粒生花生呢?好在土地下户了,米面比大集体时多了起来,不用再顿顿吃红苕酸菜了。
那时候四娃感到奇怪,同样的土地,啷个分到户后米面就多起来了呢?但这个多也是有限的,人太多,土地太少,还是得用红苕酸菜轮换着吃,否则到年尾就只能喝西北风。岂止是年尾,翻年过后的二三月,余粮没了,红苕也没了,地里的蔬菜还没长起来,干菜、干苕果、干萝卜挂挂也没多少,从记事起就是红苕酸菜当家,不是逢年过节或者家里来了客人,是吃不到细粮的。
出门的时候刚好鸡叫二遍。雾似乎更浓了些,经过牛圈时,四娃说:爸,我给牛喂下草。富顺老汉说牛吃早饭还不到时间,想了下又说,要不今天喂早点。四娃反过双手放下背包。见有人过来,牛已撑起前蹄站起来,耳朵一扇一扇地鼓着眼朝四娃看。四娃抱起圈门边的半筐青草丢过去,顺手抚了抚牛脸。牛伸出舌头来舔四娃的手。霜打过的青草发枯发黄,是四娃昨天傍黑种完麦子后,看看天色尚早攀到滴水岩悬崖上割的蓑衣草。
有东西扑打着裤腿,不用看都晓得是黑虎。四娃把手缩回来去摸黑虎的头,狗东西尾巴摇得更欢了。刚出村口,黑虎对空 “汪汪”两声,像吠那些茫茫的夜雾,又像在喊“出发了”。黑虎往前一蹿五丈开外就停了下来,等四娃与富顺老汉走近了又再往前跑去。
山路在脚下开始蜿蜒出至少60度角坡度的时候就快到枣儿垭了。翻过枣儿垭,就真正离开村庄了。四娃说爸你歇一下吧,富顺老汉说要得。刚才穿过竹林时雾浓得很,伸手抓一把肯定都捏得出水来,竹叶上嘀嘀嗒嗒地掉落,跟下雨似的,弄得头上身上都是水。露水也重,道旁的狗尾巴和铁线草被惊醒,恼火地把一身的湿漉漉发泄到裤管上来。
枣儿垭没有枣树,天晓得先人们为啥给这垭口取这名。枣儿垭只有一棵黄葛树,在四娃看来树龄应该有三、五百年,那些枝丫肆意伸展,覆盖面积可能有半亩地。上学时每周星期六和星期天经过都能亲近一回的,四娃觉得黄葛树像一幅西方画家笔下的油画,又像这村庄的一面旗帜,风吹过呼啦啦的响声像自己内心的呐喊,呐喊什么倒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倒是在心里早早有了想法,二回考学就考美术学院,一定要把这棵黄葛树画出来。
可是四娃的梦想在去年那个热得人绝望的七月破碎了,离上线差了3分。3分是一道大鸿沟,二蛋只差0.5分都被刷了下来。四娃想过复读,但富顺老汉不肯。
四娃大哥六年前考上了大学的,去体检时被挡在了大学的门外。大哥得了肺结核,为治病已掏空了家财。四娃也想过像二哥一样选择去部队当兵,但很快就打消了念头,部队不会收近视眼。要么跟三哥一样去镇上当学徒学做川菜?那也不得行,四娃觉得自己是个有想法的人,不安心就学不会手艺。
去外面闯闯的想法其实落榜后就有了。那个南方渔村正在如火如荼建设,整个大环境都适合自己去伸胳膊展腿试试,问题是暗暗摸排了好久,亲戚朋友熟人老乡就没一个与之有关联的。做盲流南下?那不得行,胆怯,不能打没有准备的仗。转念出在强哥从北京回来探亲的那天中午。
当时四娃正在井台上打水,农历八月的阳光中送来村小朗朗的书声,一桶蓝天白云晃荡出郁闷的颜色与气味。强哥背着个背包站在四娃身后。强哥说四娃你那么好成绩没考上大学么,四娃露了笑说落榜了。强哥又说那就窝在家里么,人多地少浪费人力。四娃默然,好像看见数年后的自己跟村里的兄长们一样,娶妻生子、扛着锄头犁耙披星戴月、为了田边地角鸡毛蒜皮恶言相向甚至扯皮打架。
后来的事情似乎只有四娃心知肚明,强哥回北京后,四娃常往强哥父母家跑,帮着挑水劈柴耕田耙地,一样也没落下,父母与四娃心照不宣,有时也来帮强哥家干活。
接到信是十天前,正农忙。强哥说四娃忙过了你到北京来挣钱。北京,噢,北京!乡下孩子的首都是县城。四娃只在去年参加高考时去过县城,也是离村子最远的一次。
四娃似乎看到了一道亮光,感觉把这四面青山围着的村庄撕开了一道口子。四娃夜里做梦看见一只穿山甲在房后的山脚刨土,很艰难的样子。四娃拿了铁镐跑过去帮忙,那穿山甲见有人来一溜烟跑了。四娃扬起铁镐挖土,铁镐却从手里飞了出去,消失在一沟的雾气里不见了。没了铁镐也要刨!四娃愣了会神下定决心用手替代铁镐。刨着刨着,双手愈发锐利有力,一副铠甲这时候从天而降,“咔”的一声披挂到身上来。四娃突然变成了一只穿山甲,四脚着地朝着山体内钻去。山体内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管它哩,四娃不稀罕看见,莾起劲往前钻。风在耳边呼呼地响,四娃钻过山的肉身、骨头、心脏……不晓得过了多久,四娃钻出山体的时候,一道光射过来,身上的铠甲“砰”一声炸开了。四娃恢复回人形,看见眼前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一块宽阔得似乎无边的广场前矗立着一幢城楼,金碧辉煌霞光万丈。这是哪里?哇,北京!哇,天安门!四娃兴奋得大叫,踩着碎了一地的铠甲狂奔起来……
醒了,四娃躺在床上不想起来,睁着眼出神,梦中的天安门太令人神往了!北京那么大,去了整天干活挣钱,有没有机会去看天安门呢?强哥所在的东四胡同离天安门远吗?
四娃把行李放在黄葛树下的长条石上,围着堡坎转了一圈,伸手摸摸苍老的树身。黄葛树早已经老得没了树皮,那些根系纵横着钻出石条的缝隙来钻进地面的土层里去了,苍劲的力度像父亲的手插入泥土里揪出某个向下生长的红苕。黑虎朝坡下的小路“汪汪”了两声。四娃拍了下就近的一个树根,口气有些坚决地对父亲说,爸,我们歇下再走。富顺老汉说不忙,我看个究竟。
四娃顺着父亲手指的方向看下去,斜坡上有两个黑影在往上冒。是一头牛和一个人。四娃听见隐约的牛蹄声,用手推了下鼻梁上往下滑的眼镜对父亲说。富顺老汉听了就忙往斜坡方向前进一步,刷地打开了手里的电筒。是哪个?声音与电筒的光亮一起传到坡下。是我是我!那人扛着把犁头,一头老水牛紧紧地跟在身后。富顺老汉明显听出声音来了,把电筒的光亮铺在那人脚下问,根红老弟?你啷个这么早?根红笑了笑,说没办法,自家养不起牛,借人家的,天亮人家要用。顿了一下问,是富顺老太爷么?这么早去哪里还是从哪里回来?富顺老汉手里慢慢移动着电筒的光亮说,是我,送四娃去赶车。来回的问答中人影和牛影就爬上坡来了,根红放下犁头就忙去兜里掏香烟,富顺老汉早拿了烟在手里说抽我的。
四娃看见坡坎下又拱出个人影,疑惑说那是哪个,那人影倒叫起四娃来,黎豹你安逸噻,去闯北京。四娃说苗红你不上学哇,啷个跑来跟你哥耕地。苗红把背篼放下来歪着给四娃看,说上哩,书包都带上的,我来给哥做伴壮胆,顺便在地边割点牛草劳慰人家牛。
说不了多少闲话,赶路要紧。四娃与富顺老汉告别根红哥俩加紧脚步,沟里已经传来鸡公的第三遍打鸣,离上车的油毡厂还有五里地。岭上路宽阔些,也没什么雾,两旁的枯草上有霜,显得路面更白亮。富顺老汉问四娃,照亮不?四娃说不,看得到。富顺老汉便交代一些话给四娃说,不要挂牵家里,那点儿地我和你妈轻易就能收种,忙不过来还有你大哥三哥哩!虽说他们结了婚分了家都各忙各的,看我们忙不过来能不帮吗?这两年责任到户吃饱肚子是莫得多大问题了,就是莫得钱,又人多地少,难得找到出路。到了北京好好干,听你强哥话,记着感谢人家。四娃说晓得。
天色开始暗下来,不大看得清路面,黎明快要来了。富顺老汉打开手电照路,父子俩说着话不知不觉已经转过两道垭口,再有一个垭口就是搭车的油毡厂了。天边这时候已开了亮色,富顺老汉关了电筒的光亮问歇一下不,四娃说不能歇,天一开亮班车就到油毡厂了。富顺老汉又把电筒打开照了下手腕上的“上海牌”手表,说不急,五点半才从县城发车,怕要过一二十分钟才到得了。富顺老汉把表从手腕上褪下来交给四娃。四娃不要。富顺老汉说你拿着,这一路去盐亭到绵阳,出门没个时间盯着不好转车。又说庄稼人本来就没必要戴表,鸡公打鸣就是时间。四娃接了表,默了一下往手腕上戴了。
到油毡厂还差五分钟才六点。路口上已经聚着一群人,大包小包的行李和被盖卷散放在马路上,跟地里长起硕大的花菜包菜似的,不用问都是来赶车去外面打工的。
“黎豹!”
有人喊着奔过来,四娃看清楚了,兴奋得叫起来:“春水!好巧啊,你也要外出?”
四娃跟春水是同学,在校时交往得好,一起落的榜,后来就没再碰见过了,两人激动地抱在一起。交换了一些言语,两人都忙把自己的父亲介绍相识。还没有去外面后的固定通信地址,方便以后互相联络。
走得急,地上虽然铺满了霜花,风也小声呜呜着,但富顺老汉仍感到身上热乎乎的,毛刺刺的,便解开胸前的两排纽扣。爸你不要着凉了,四娃说。富顺老汉咧了嘴说不关事,包里有鸡蛋、豆腐干和花生,记得路上饿了拿出来吃。四娃说晓得了。
四娃说晓得时公路转弯处叽叽喳喳过来一群人,是去大河坝镇中学上早学的学生,一路打打闹闹蹦蹦跳跳而来。一对追逐的小家伙跑过四娃面前时踩在路边打了霜的草上,脚下一滑两人摔倒在地滚作一团,两只铝合金饭盒“咣啷”掉在马路上,其中一只弹跳着抛出一排大米和两个红苕,一个红苕飞到马路中心,跟打“地牯牛”似的转圈。一群稚嫩的声音望着红苕笑不停,两个还滚在地上的小家伙盯着红苕停止了舞蹈,一个对另一个吼你赔我午饭来,另一个对一个说我赔你铲铲,是你要跟我打仗的!两个小家伙不依不饶,重又扭到了一起。
四娃伸手抓着两人的衣领提离开来,对一个说你去把他的饭盒与红苕捡起来,摸着另一个的头说别闹了。四娃伸手把裤兜里的五块钱拿出来,抽了两张一块的塞给小家伙,说中午去街上买饭吃。四娃转过头看父亲,还好,父亲正专注地盯着班车将要来的石梯坡方向。
爸,四娃说,二婆私下给了我10块钱盘缠,我留了五块钱放在你枕头下面了。富顺老汉回头说:要你二婆的钱干啥?她都老得干不动活了,哪还盘得到钱!四娃说我晓得,她硬要给,等我以后回来还她的情。富顺老汉就笑,说你记得就好,其实她不会图你还情的,我们今后多帮衬她就是了。
四娃回应父亲说晓得的时候,一辆客车从大河坝方向转过垭口开过来了,一声清脆的汽笛声打破了山野早晨的宁静。
“黎豹,车来了。”春水边拿行李边说:“别忘了联系。”
“一定!不会忘的。”四娃伸出双臂紧紧地拥抱了一下春水。多年后回忆起来,四娃仍旧感叹这一场偶然的遇见,一去北京三年自己混得毫无起色,多亏了春水相邀南下,从此如鱼得水似的。
从大河坝开往县城的班车刚走,从县城发往绵阳的班车便鸣着汽笛从远远的沟底公路开过来了。在班车奔来的方向,山头上的天空由白到红,朝阳很快就要探出头来了。
“嘎——嘎——”一群早起的山鹰从山头上冲向天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