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芒的家在菜场的东南方向,地铁则在菜场的西北方向,所以去地铁站一定要穿过菜场,以及它周边的一片待拆迁区。晓芒一般都选择走大路,哪怕远一点,她害怕那一片区域里三五成群的野狗,以及小路两侧的碎砖乱瓦,特别是在这样的夜晚,虽然时间不过九点,但对于深居简出的晓芒来说,那几乎是半夜了,至于她为什么这个时间还破天荒地在外面,原因很简单,她本该在家里练字的,突然想起公交卡上只有一块钱了,这个假期太漫长,一直窝在家里也不觉得,可明天就要上班了,一块钱只够上班,下班怎么办?现在都电子支付了,身上从不带现金,一块钱虽小,要是上了车掏不出来,也是够尴尬的,公交卡对于不开车的晓芒来说是生活必需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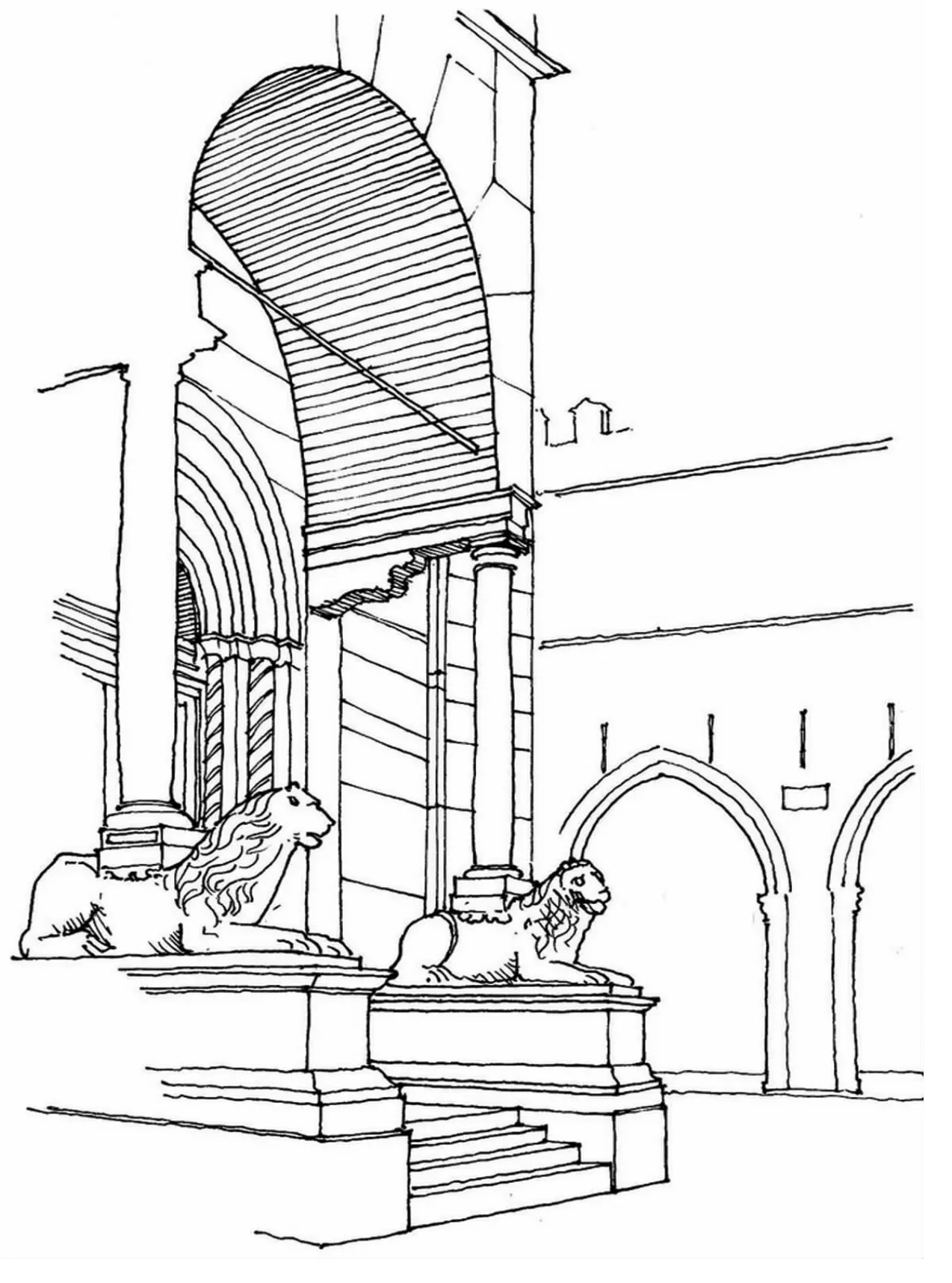
看看时间还不到九点,又兼在家里枯坐了一天,晓芒决定去一趟地铁站充值公交卡,顺道也散散步。七天长假,对于晓芒来说,从女儿三号返回杭州就已经结束了,她恢复到一个人的生活,简单,也寂寞。女儿难得回来,工作很忙,而且她总说回到小城来,除了妈妈,很难再找到可以说到一起的人,在家里无非是吃吃睡睡,整个人都要颓废掉了,还是回去工作比较靠谱。从性情上说,两母女十分相像,都是那种心思重,责任感和原则性很强的人,活到这把年纪,晓芒已经不觉得那是个优点了,她只希望女儿能活得轻松一点;女儿呢,总是懂事地安慰她,生活已经很好了,妈妈才应该活得轻松一点。晓芒苦笑了一下,她活得不轻松,连远在杭州的女儿都能感觉到,可是她已经习惯了,这不关乎经济或别的什么,她就是一个很难轻松生活的人,并且,她也不羡慕那些貌似活得很轻松的人,个性无好坏,自己可以把控就好,晓芒当然也不愿意装作活得很轻松,这个年纪,不是讲究活得真实吗?真实,在晓芒的生活里是沉重的。
她倒不是多么想女儿,杭州也很近,有微信和电话可以每天联系,总之她是一个人惯了,一个人除了上班有大把的时间和空间,令她觉得无比自由,这自由让她沉静的性格更加沉静,有时双休日待在家里,整整两天都不说一句话,周一再去上班的话,整个人有种回不过神的呆劲儿,但晓芒并不讨厌这样的生活,也不渴望热闹,而且,她知道,往后的日子就是这样的,或者是更加孤单的,她先演练起来也是一种积极的表现。想到这里,晓芒微微笑了一下,笑容像一朵苍白的花,在嘴角处一瞬即逝,但晓芒也不是不快乐,她只是平静,没有什么可以让她的心里掀起波澜,是的,没有什么了。
大约因为过了限制进城的时间,马路上的重型卡车多了起来,灯光下,扬起尘烟滚滚,晓芒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自己的头发,刚刚洗的头,不想蒙了灰,这么想着,她顺道就拐进了右侧的小路。小路两侧是高大的香樟树,这里有一大片香樟树,是一个被废弃的小区游乐场,往里走,灯光惨淡,偶尔走过一两个人,行色匆匆,形迹可疑。晓芒突然意识到这条小路是熟悉的,在过去的几年里曾许多次经过,前面转弯处有一张石桌,还配有四个石礅子做椅子,对啊,这就是菜场西侧的那片待拆迁区,没想到这么久了,它还在,还是以待拆迁的状态存在着。晓芒下意识地看了看脚边,还好,没有三五成群的野狗,这残垣断壁的,几乎已经没有了住户,野狗也很清楚这情形,去了别处觅食吧。
晓芒的心情一下子低落下来,再勉力,也无法回到刚刚的平静,她感到胸腔里剧烈起伏着的一股股气流,马上就要喷涌出来,那将是止不住的眼泪,这个过程也无比熟悉,两年内,这感觉像一头寻着了熟悉气味的怪兽,无数次抵达和离开,只是最近半年的频率没有那么多了。晓芒找了棵树,慢慢靠上去,并努力保持深长的呼吸,她想把这情绪的巨浪压下去,没有成功,热泪夺眶而出,无法扼制,令她失控一般小声抽泣起来,过了很久,她才缓过来,慢慢往前走。前面,细碎的说话声稍稍分散了她的注意力,果然,石桌子那边有两个人,一男一女,从身形看,应该是不年轻了,男的坐在电动车上,脑袋伏在车把上,似有无限的苦衷,女人尖着屁股坐在桌上,说是坐,只挨了一点点边,两个人的状态都像是随时就要离开似的,声音也是断断续续的,不是因为远,而是因为两人于长长的沉默中偶尔说一句话,听起来倒是别有一种味道。晓芒立即判定这两个人并不是夫妻关系,这一想,让她本能地想绕道而行,可从这儿往地铁站的路她只认识这一条,再回到大路上去,时间更晚了,而且那重型卡车扬起的灰尘让她望而生畏。晓芒放轻了脚步,尽量不打扰这一对不知道是什么关系的男女,她没有什么好奇心,是的,经过这么多事,她已经对什么都不好奇了,不管他们是什么关系,自己可以承担就好,与他人何干呢?
再过去是一个小小的坡,晓芒记得真切,往家的方向是下坡,往地铁的方向是上坡,她记得那时候,早上去往地铁站,凉生都要她下车,自己推着电动车上坡。四年前,凉生已经生病了,但外人看来,他仍是那个高高帅帅的凉生,五十岁,看上去像三十多岁,他是那种天生丽质的男人,一直轻而易举地保持着健美的身材,白皙的面孔,眉目清秀,在晓芒看来,外形与内心,凉生都没有成熟过,更何谈老去,可是,他居然生了那么重的病,生命像一条奔涌的河流,瞬间被拦腰截断。医生说他的左肺已经失去功能达一年之久,CT片子里,左肺白茫茫一片,什么也看不到,因为一切都浸没在了胸腔积液里。人真是可怕,手指上破了个小口子都痛得生无可恋,可是整个左肺几乎烂掉了却毫无感觉,那时凉生还在工地上干活,每天早出晚归,连咳嗽都没有一声。出事之后,晓芒往前面的生活里去寻找,真的连蛛丝马迹都没有发现啊,这让她一直痛悔自己粗心的自责稍稍消解。
生活如同无情的巨掌,一把将他们推入了无尽深渊,万劫不复。
两年时间里,不断寻医问药,将医生判定的刑期努力延后。因为几乎失去了手术化疗等所有机会,最后辗转寻得了一个南京的老中医,每个月的一号,两人都要去一次南京,一开始情况不错,非但没有恶化,反而有慢慢好转的迹象,去南京便像是一次短途的旅行。凉生的重病,瞬间把从前家庭里那些严重的矛盾都消解了,仿佛回到了刚刚成家的时候,大敌当前,一致对外,两个人都觉得,只要生命在,一切都有重来的机会。但晚期癌症,这是一场不可能打赢的战争,在勉力坚持了一年半的中医治疗后,终于撑不住了,情况急剧而下,一去不返,凉生在晓芒的怀里彻底安静下来。
眼前的这条小路,正是凉生和晓芒每次去地铁站时走过的路,凉生开着电动车,两人骑到地铁口,然后坐地铁去高铁站,一切顺利的话,两小时可以到达南京的医院里,当天来回很方便。凉生总有些小聪明,从前这样,生病了也是如此,这条小路,住在附近同样十多年的晓芒却一无所知。凉生得意地说,你呀,就是个生活的小白痴。在他们的生活中,这样的时刻并不多,晓芒是比较强的那个,凉生反之,原因很简单,整个家庭经济全部依赖晓芒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凉生是那种有心气却没力气的人,他做什么都不能坚持,所以五十年里几乎一事无成,虽然晓芒懂得他的心,但在坚硬的现实面前,小聪明是远远不够的,貌似强大的凉生很快在瘦小的晓芒面前软弱下来。晓芒心里不是没有怨气的,但她从未想过离开这个男人,就像她不再指望他有一天能真正成熟有担当一样,日子流水般地过去,过得去就行,晓芒不是有野心的人,所以,长久以来,就这样磕磕碰碰地过着,孩子也一天天长大了,对生活的心也慢慢淡了,只求平平安安就好。可是,生活可不想就这样饶过她。想到这里,晓芒苦笑了一下。
在凉生离开的最初,晓芒的心情是松快的,两年来时时紧绷着的神经终于断裂了,除了那一声脆响,整个世界都空了,晓芒感觉到那种漂浮的,无所依着的轻松,事情办完后,她大睡了三天三夜,整个人像死过去一样,不吃不喝,昏睡不醒,女儿守在床边,紧紧抓住她的手,这个二十二岁的孩子生怕刚刚失去父亲之后又失去母亲,晓芒偶尔睁眼,看到女儿,侧头又睡过去,直到第三天的傍晚,才真正醒过来,她拉着女儿的手,轻轻晃了一下,虚弱地笑着,妈妈不过是累了。
那种掏心剜肺的痛苦是此后才到达的,像一列晚点的火车,隆隆地开过来,将晓芒的日子整个地辗作了尘土。三个月后,晓芒去看了心理医生,她搞不懂的是,结婚二十多年来,这个家是一直由自己撑着的,不管是经济支撑还是家务琐事,女儿也几乎是自己一个人带大的,凉生的存在,只不过是一个父亲的符号,而且,他的离开,是因为他自己生病了,可是为什么他走之后,自己心里是如此的内疚,这内疚像一只牙齿锋利的小动物,一点点噬咬着她的心,仿佛也要把她拖入死亡的黑洞才甘心。咨询师很专业地告诉晓芒,那是一种叫完美自恋的因素在作怪,就是晓芒潜意识里觉得自己是完美的,万能的,足以挽救凉生的,结果却没有成功,因此深深自责。晓芒虽然不是很懂,但听着似乎有理啊,在以往二十多年的生活里,无论凉生闯下多大的祸,晓芒都能以她的办法将它摆平。她虽然性情安静宽容,但毕竟不是圣母,因此,久而久之,总难免抱怨,说出刻薄的话来,就像凉生虽然无话可说,但心里总也会因为晓芒那些刻薄的话留下痕迹吧。为了孩子,为了让生活正常进行,没有离婚,勉强凑合着,总想着孩子大了会好的,晓芒知道会好的是自己的心态,而不是凉生变得挣钱负责顾家了,事实上,随着年岁上去,挣钱对他来说越发难了,但是五十岁的晓芒已经不在意这个,她唯一想的是对于女儿来说,有一个完整的家,或者家是完整的样子,就可以了。
可是,如此卑微的要求却被命运无情的獠牙撕碎了。当然,凉生的病,也把生活中原有的那些琐碎熨平了,他们立即变成了同舟共济一致对外的战友,以及恩爱的夫妻,晓芒心里涌起真正的疼惜,这个男人再不堪,到底是她生命里最重要的男人,世上那么多男人,她只和他在一起,有一个共同的女儿,这些宏大的主题里容不下抱怨与计较。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她都坚定不移地站在他的身边,成为凉生坚不可摧的护卫。凉生因为生病而心安理得地变得更加软弱了,他不敢面对医生,不敢面对每一次体检,不敢将自己的病情说与人听,他变得像个孩子,而晓芒成了他的母亲,可惜她竭尽所能也没有护佑住他,心理医生说得对,她对他因此深深负疚。
晓芒的朋友海音说,晓芒,凉生的离开和你的更年期,可能要撞在一起了,亲爱的,接下来,可能是一段艰难的日子。海音建议晓芒去学画画,她有点基础,性格好静,很适合。晓芒答应试试。
上国画班有一个多月了,晓芒感觉到了自己的变化,那就是一天天宁静的心境,专注而投入地画画,偶尔看点心理学方面的书,晓芒觉得自己快要渡过难关了,而且,那可怕的更年期好像也没有到来。可是,今夜,路过这条小路,晓芒想起凉生,和凉生一起去南京的日子又电影般浮现在眼前,凉生的音容笑貌清晰得触手可及,那熟悉的内疚感又缓缓上来,但已经不是早先那让人透不过气来的密度,稀疏的,网状的,可以呼吸的。好了,这就是活过来了。晓芒对自己说。如果这是一场战役,那么面前的满目废墟里唯一让她感到安慰的是,没有人看到凉生与晓芒感情的真相,那些破碎与厌倦,刻薄与颓丧,紧紧裹挟在凉生病了这巨大的灾难里,被洗涤,被沉淀,被风干,然后,换了模样,那模样就是,五十岁的晓芒成了一个失去伴侣的可怜的女子,她曾经可是有一个美满婚姻的。
成人国画班几乎全是女生,年纪在三十五到六十五岁之间,五十岁是中等偏上的年纪了。晓芒坐在第一排,同桌是班上唯有的两个男生中的一个,叫徐梓平,看起来四十多岁,有一张温暖的笑脸,每次上课前都为晓芒调好墨汁,铺好画纸,晓芒十分过意不去,对他谢了又谢。晓芒很快注意到,徐梓平很受女同学欢迎,有天晚上上课时,她赫然发现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同学居然带了一杯奶茶给他,而这种叫X的奶茶刚刚落户在小城,买一杯要排上两个多小时呢!晓芒心想,这女生真是有心,而徐梓平呢,十分不好意思地拒绝了,他大约不赶这种潮流,不知道这是一杯那么难买到的奶茶,他说他血糖高,不喝奶茶的。女生略略尴尬地请了另一位女同学喝。不知道是不是晓芒的敏感,她总觉得那女同学此后没怎么给她好脸色。徐梓平倒是一如既往地对晓芒好,但有一次晓芒问他网上哪里有卖合适的宣纸,能不能加个微信把网址发给她。他立即打开手机,让晓芒用淘宝扫一扫打开网店,而忽略了晓芒说的加个微信,这让晓芒心里十分释然,又觉得自己有点可笑,心理医生说得对,她就是个有完美自恋情结的人。徐梓平就是一个纯粹而善意的男同学,这样很好。但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再次让晓芒不安起来。因为去得早,晓芒和徐梓平一直同桌,画桌很大,但是坐两个人嫌大,坐三个人嫌挤的那种大。那天晚上,那个送奶茶的同学硬是要坐在徐梓平和晓芒中间的椅子上,徐梓平当然不能说什么,等女生走开时,晓芒悄悄说,我坐后面去,三个人施展不开的。再下一次,徐梓平见晓芒仍然坐在后面,便对她说,你坐前面来,我把中间的椅子搬掉,那样她就不好意思挤在这里了。这行动让晓芒心里有异样的感觉,有些不舒服,也夹杂一点说不上来的感觉。
偶然的机会,晓芒知道了徐梓平和自己读的是同一所高中,只不过自己比他高了五个年级,这样,她找到一个机会,轻而易举地将她和徐梓平之间的微妙消解了。89届?真的吗?我以为你至多和我同届。徐梓平不可思议地看着晓芒,晓芒顽皮地说,小看我啊,叫学姐!那以后,徐梓平还是和晓芒同桌,叫她晓芒姐。
小路的尽头,灯光蓦然亮了起来,晓芒停住了脚步,这里,离地铁站还有一点路,记忆中是一片废弃的荒地,居民们在上面栽了玉米、毛豆等各种菜蔬,可是,什么时候变成了一片宽敞的停车场了呢,灯光照得它明亮如同白昼,两个保安肃立在进口处。晓芒揉了揉自己的眼睛,以确信这里的改变。突然,身边涌过一群年轻人,互相嬉笑打闹着向地铁口走去,像是刚刚参加了什么聚会。
地铁真是一种神奇的存在,不是说它的快捷,而是说它提供的氛围。一走进地铁,你就意识不到时间的存在,晚上八点或早上八点没有多大的区别,其次,地铁立马让这个三线小城有了一种大都市的洋气。晓芒站在高高的电梯口向下望去,那电梯几乎是笔直向下的,她本能地抓住了扶手,让它把自己带到了地下一层的充值机边上。她估算了一下,充一百块钱,只用于上班下班的话,差不多可以用上四个月,四个月后,就该是春节了,女儿又要回家了。
夜风已凉,晓芒走在回家的路上,她打算走大路,哪怕回家重新洗个头呢。心里想到那片被结结实实改成了停车场的废墟,不知道为什么,有种踏实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