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秋厘远远地看着小虎,小虎坐在那尊石像旁,两条前腿撑着它高高昂起的头,两只铜铃似的眼睛,亮闪闪的,一眨不眨地盯着盛秋厘。
盛秋厘倚靠在银杏树干上,一片银杏叶悠悠地从她的头发滑到她的鼻尖,转了半个圈,悄悄落到地上。老张最喜欢秋天,最喜欢秋天的银杏树。老张说秋天的银杏叶像极具韵味的女人,尤其那黄色,不媚不佻,亮丽中不失端庄。关于这句话,老张是和盛秋厘饭后散步时,随口溜出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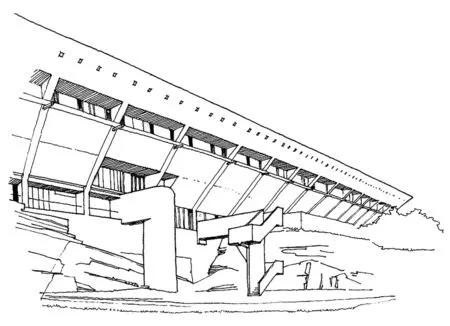
老张说完这句话,盛秋厘看了老张一眼。盛秋厘眼里的老张就是个闷葫芦,和老张生活几十年,还真不知道他这闷葫芦里装的什么药。按理说,他这木头似的人,怎么可能看花非花,看叶非叶呢?
盛秋厘在想老张的比喻,怎么偏偏把银杏叶比喻成女人呢?可不可以比喻成蝴蝶?她还没把老张的这个比喻琢磨透,老张又开口了,说这叶的外形,也是蛮精致的,该流线条的流线条,该直线的直线。这老张研究银杏叶还上瘾了?盛秋厘反问一句,那么秋天的树叶哪个不是黄色的有流线条的呢?也对呀,小厘说得有道理,怎么就对着银杏叶说疯话呢?老张不说话了,默默拉起小厘的手,继续散步。
后来盛秋厘独自一人来到公园,坐在老张常坐的那张长条木椅旁,看着隔条小道的银杏树。满树黄黄的银杏叶密密的,金灿灿的。那密,那金色,完全不是凋零的气味,简直真的像一个完全成熟的少妇,肆意地绽放着她的美。再看看木椅后面的无患子树,首先叶形还真的不如银杏叶精致,再看看颜色,黄中带枯,色泽暗沉,何况叶子掉得像老人的头发,稀稀疏疏的,确有很浓的朽的气息。盛秋厘心里服了,老张是有眼力的。
金黄的银杏叶还在,有眼力的老张却不在了。老张走了一个月了,走得很突然,就一个跟头的事,老张就永远地把自己深埋在这个秋天,把他所有的喜怒哀乐存封在那永远闭着的眼睛里。盛秋厘收起目光,低下头,踩着沙沙的银杏树叶,朝小虎走去。小虎站起来,从石像走向长条木椅,围着木椅转了一圈,然后乖乖地走到盛秋厘身边。这畜生似乎每次都是故意赖着不走,非要盛秋厘在过去的时光里走一段,直到盛秋厘泪流满面,或者哽咽,或者身子软得站不住蹲下去,小虎才肯回家。这小虎其实不小了,都六岁了,但叫它老虎,似乎又不太妥当。
小虎是老张母亲遗物中的一件,老张母亲去世的时候,小虎才三个月。老张把小虎领回家时,盛秋厘一百个不情愿。母亲去世的那一年,老张儿子刚结婚,住出去了。老张也正好退休,天天在机关忙碌的他,突然退休,闲得慌,弄条狗陪着,挺好的呀。
盛秋厘不愿意,就算老张照顾小虎像当年照顾儿子一样。可是儿子长大会洗脸刷牙,会上抽水马桶,会给盛秋厘倒杯水,这小虎会吗?家里不知道会被小虎糟蹋成什么样子呢。儿子身上有乳香,可小虎身上,老张哪怕一天给它洗澡十遍,它身上就是有狗腥味。盛秋厘是个小有洁癖的舞蹈演员,小虎领回家的第一个年头,老张不知受了盛秋厘多少无名火。老张这人就是脾气好,一辈子没有对盛秋厘高声过,对的错的全都包揽。盛秋厘的闺蜜周小雅,跟盛秋厘聊天的时候,话题转着转着就绕在老张身上,周小雅说老张的优点数不胜数,一辈子也聊不完。年轻时的盛秋厘不觉得自己有多幸运,甚至觉得老张有点怂。但老张也不怂啊,老张在机关是出了名的有能力的干部,从一般科员干到一把手局长。盛秋厘有时想想都觉得好笑,这么个半哑的人,怎么个当领导的。为这事,盛秋厘还专门溜进了老张的报告厅,台上的老张那哪是老张啊,中年妇女的偶像啊,连盛秋厘这样心高气傲的女子都被折服了。风度、才学、磁性的声音,依稀的皱纹和白发都看不见了,英俊得很。打那以后,盛秋厘觉得自己确实嫁对了。
盛秋厘领着小虎走一步歇一步,大衣被风吹得贴在身上,越发显得单薄。本来身体纤瘦的盛秋厘,在老张走了的这一个月,像夏天出了冰箱的冰淇淋,化了一大圈。除了这瘦,再看看她那蹒跚的步子,这哪像一个全市闻名的舞蹈演员,她的左腿麻木得快迈不动步子了。
明天就要被儿子接到另一个城市了,本来老张刚死,儿子就要接走盛秋厘,盛秋厘不走。盛秋厘认为自己可以的,可以在这里再和老周待些日子,却不知道自己的身体败得这么快,怎么浑身都是病了呢?前些日子,早上刚起床,莫名其妙地脚下像踩空了一样,一跪一趴就那样摔倒在地,头晕目眩。好一会儿都爬不起来,不知道是哪里使不上劲。盛秋厘当时就哭了,怎么可以活得这样狼狈!
最近腰疼得连扫地都干不了了,扫个客厅都要去沙发躺两次。还有要命的左脚掌,有次盛秋厘狠狠掐自己的左脚掌,却没有痛觉。那次盛秋厘气疯了,去厨房里拿了把菜刀,要宰了自己。可她不知道从哪里下手,该砍哪里可以一刀了结这条残命?
还有小虎,这一个月,只有四个休息日,小虎是吃饱了肚子的。休息日盛秋厘儿子都过来,盛秋厘儿子来的日子,盛秋厘像个没事人一样,她不想让儿子替自己担心。可儿子一走,盛秋厘有时候一天都不做饭,蒸一个红薯可以是一顿午饭,买一个包子可以是一顿晚饭。
终于有一天,盛秋厘倒在床上,连口水也喝不上,她头晕腰疼脚麻,身体的三个重要部位一起袭击她时,她妥协了,答应去和儿子一起生活。当时的小虎在客厅和房间之间转来转去,小虎这一个月也明显瘦了,它浑圆的身体有了骨感,甚至连走路都是哲学家般的踱步。和老张散步时,小虎从来都是奔跑着的,它跑一阵子,把老张甩下一大截,然后再跑回来,如此来来回回,每晚的散步它大约都要跑四至五倍的路程。老张看着前面蹦跳着的小虎,心情会无理由的陡好。据说泰迪犬最长寿命是15年,没有了老张,小虎成不了长寿的那个。是你命不好。盛秋厘叹息道。
次日,盛秋厘来公园就是和老张说一声的,和老张的银杏叶道个别,和老张的长条木椅道个别。夕阳照在盛秋厘的头发上,有几根白发自动跳出来,在风中飘啊飘的,说不出的伤。这黄昏时分,公园里有三三两两的散客,可谁能认出,这是当年市剧团自编自演拿了省一等奖舞蹈《闪闪的红星》的领舞呢?
盛秋厘走一步回一下头,她希望老张在她的哪次回头中,会突然现身。她知道那只能是幻觉,可她希望出现一次幻觉,她就要离开这个城市了,难道走了一个月的老张,已经不来这里了?这一个月,就算下雨,盛秋厘打把伞,也是要来这里转一下的。老张在世的时候,一年365天,他至少有300天都会来这里坐坐。老张曾经说过,小厘啊,心闷的时候,来这里坐坐,就觉得好多了。有老张的日子,盛秋厘从来没有心闷,只有心火,但有了心火,冲老张发,发完就罢。
这一个月,盛秋厘心也闷啊,可来这里,不奏效啊,心似乎更闷了。在盛秋厘的记忆里,老张在这公园的时间比在家长,偶尔在家,老张基本上都在书房。老张在书房捣鼓什么?盛秋厘有次悄悄溜进去,老张真的在电脑上改讲话稿。盛秋厘进去,老张没有和盛秋厘说一句话,不知道有没有看见她,如此两三次,盛秋厘没有讨到老张的半句只字,每次看见的都是老张眉头紧锁盯着电脑。从此,盛秋厘再也没有进过书房。
老张走了的这一个月,有次,盛秋厘打开书房的门,才跨进去一只脚,她就赶紧把脚收回来,关紧了门,书房里一丝阳光都没有,可她隐隐约约看见电脑前的老张,满头刺眼的白。盛秋厘常常盯着老张的照片,希望看出一个幻觉,可以和老张说几句话,问问老张,如果那天不去钓鱼,老张会躲过这一劫吗?那天和谁钓鱼的呢?怎么会摔趴在河岸上呢?
盛秋厘希望在任何地方遇上幻觉中的老张,就是不想在书房。盛秋厘心里有点恨书房,发过誓的,绝不踏进书房半步。毫不夸张地说,老张从没在书房和她说过一个字。她以为老张走了,她可以与书房和平相处的,哪知还是气场不合。
儿子来了电话,约好了第二天接母亲的时间。盛秋厘在家里左看看右看看:厨房,上班时,老张基本不在家吃饭,退休后,老张学做饭,好像没天赋,一直没学会,就放弃了,盛秋厘煮什么他就吃什么,从不嫌咸嫌淡;客厅,就那沙发,老张坐着看新闻的沙发,在白如昼的灯光下,不残留老张的一丝气息;再者就是床了,除了出差,老张无论早晚,哪怕有时是三点,他也坚持天天回家的。到了床上的老张,都是听盛秋厘说些闲事,是最有耐心的倾听者。老张还是小张的时候,蛮有活力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小张突然成了老张。刚开始时盛秋厘还不习惯,故意找茬生气。老张把盛秋厘往怀里搂搂,拍拍她的头她的背。盛秋厘在老张怀里象征性地挣几下,就平心静气了。渐渐地,这种和平的睡觉方式成了习惯。那么这床,好像也没有被老张打上更深的烙印。
儿子张守一按约定时间来接盛秋厘的时候,盛秋厘和小虎都坐在沙发上。张守一环顾四周,没见行李箱,丝毫不见要出门的迹象,母亲不会要变卦吧。自从父亲去世后,张守一每晚都要打一个电话给母亲。有一次正和母亲通话时,母亲说的眩晕病犯了,没说上几句话,手机里传来“啪”的一声响,然后手机里就没了声音,急得张守一差点当晚就从八十公里开外的城市赶过来,好在隔了一会儿,手机里传来了母亲的声音,母亲说的是茶杯摔在地板上了。
这次一定要把母亲接走,张守一自己动手给母亲收拾行李,来到母亲房间,房间里有点乱。床上的被子分不清横竖正反,自由又散漫地卧在那里;衣服像被猫玩耍过的线团,没有源头挤挤挨挨地团在沙发上,衣架上倒不见几件衣服。除了这些,房间里还有一股很浓的膏药味。张守一鼻子一酸,这哪像自己心目中母亲的房间。张守一的印象中,母亲是这个城市中最讲究的女人。张守一最初的记忆里,不谈衣服,就是红领巾,母亲也要把儿子脖子上的红领巾整理得服服帖帖,才肯带儿子上学去。
母亲还有点小洁癖。记得有次放学,来接儿子的盛秋厘远远看见,儿子和“鼻涕王”黄毛手拉手排在散学队伍的第三排。当天晚上,张守一的手不知被母亲洗了多少遍,向来疼儿子的母亲突然心狠了,张守一小手被搓得通红,像是不被洗掉一层皮,母亲就不罢休。第二天的放学,老师安排张守一排到队伍的第二排,手拉手排队出校门的换成了一个干净的女生。此后,张守一似乎懂了母亲的心,不是迫不得已,手决不碰脏东西,以至于在后来的很多年,成了一种怪癖。现在的张守一也是尽量避免跟人握手的。
磨蹭了半个多小时,盛秋厘把小虎送给了小区门卫,拜托门卫用点剩饭剩菜给小虎一条活命。小虎是不宜带到儿子家的,孙子才五岁,有条狗在家是不安全的。
忙妥了所有,终于出门了。张守一边开车一边时不时从后视镜看母亲。自父亲去世后,母亲陡然老了,从前的母亲,哪怕退休后,也是不化妆不出门,母亲说的不化妆的脸就像脸没洗干净一样,走出门会不自在。可现在后座上的母亲,不要说化妆了,就说那头发,今天早上母亲肯定没有梳过,至于昨天或者前一天有没有梳过,也是不确定的。
汽车在高速上急驶,母子两个都沉默不语,各想各的心事。盛秋厘看着迅速往后倒退的绿化带,很多心事来不及整理,都一闪而过,像跳跳糖,没法停留,乱七八糟的蹦蹦跳跳。她抬头看看天,还是云朵安静,无论汽车怎么飞驰,云朵都安静地悬浮在天空下。记得老张退休后的第一天,坐在公园的长凳上,拉着盛秋厘的手说,小厘啊,以后我们的生活就是“望天上云卷云舒,看庭前花开花落”。当时盛秋厘把另一只手搭上去,紧紧地握着老张的那只手,安慰老张失落的心。
如今的她,成了需要安慰的人。她理解儿子的苦心,儿子是舍不得她这个母亲,可儿子不知道母亲的用心。
媳妇叶拉是个独生女,她的出生是个意外,她是她母亲四十五岁怀上的,能够在这个年龄怀上并生下她,实在算个奇迹。叶拉自小到大都是公主的做派,偏偏儿子吃那一套。叶拉的父亲在叶拉十六岁时就去世了,叶拉和张守一结婚时就强调过,她母亲是要一起过来的。张守一回家跟父母商量了这事,盛秋厘不愿意,可不久叶拉就怀孕了,这婚事就是提前到来的宝宝给促成了。
婚后叶拉母亲相当于免费的保姆,这也正合盛秋厘的意。所以从儿子结婚的一开始,盛秋厘就不怎么去儿子家。
如果不是自己的身体不争气,盛秋厘还是不愿意去儿子家的。现在的情况更复杂了,叶拉的母亲已经中风在床了,所有的家务都保姆干,保姆也不知道换了多少个了。不是工资的事,是保姆觉得活实在是多,接送孩子上幼儿园,照顾在床的老人,还要买菜做饭打扫卫生。从早到晚真的是屁股沾不到板凳,忙个不停。
就在盛秋厘想儿子家事想得头大的时候,张守一问母亲要不要进服务区。盛秋厘说自己不需要去,随儿子进去不进去。张守一和母亲拉起了家常,说最近的这个保姆是个乡下人,肯吃苦,人勤快。让母亲过去了之后,有什么事,尽管让母亲使唤保姆。还说把母亲接过来,他这个做儿子的心里踏实多了。母子俩聊着聊着,盛秋厘居然睡着了。老张去世后的这一个月,盛秋厘从来没有睡得这样安稳过。
一进儿子家门,保姆就赶紧从鞋柜里拿拖鞋。盛秋厘换鞋时看了一眼客厅,还算整洁。再看看保姆,确实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村妇女,年纪有点偏大,约莫六十几了,有些粗壮,不过看上去干干净净,干活也利索。
盛秋厘先去了叶拉母亲的房间,和叶拉母亲聊了几句,其实不是聊天。就盛秋厘说了几句,然后再猜猜,叶拉母亲虽说话很努力,盛秋厘是听不懂的。叶拉母亲嘴巴不关风,声音从嗓子出来,不经过嘴巴的处理,是形成不了语言的。
晚饭的时候,叶拉带着儿子多多回家了。叶拉叫声“妈”。又让正换鞋的多多叫“奶奶”。多多眼睛盯着沙发上的iPad叫了声 “奶奶”,就奔向了沙发,玩起了iPad。盛秋厘看着多多,心中悲喜参半。张守一招呼大家吃饭,保姆到叶拉母亲房间喂饭。
盛秋厘就这样在儿子家住下了,生活又是另一番样子。每个上班时间,家里就剩下三个老人。保姆送孩子买菜的时候,家里就盛秋厘和叶拉母亲两个人,这个时间盛秋厘总在家里转来转去,房间里的叶拉母亲总是在哼哼唧唧的,不知道在说什么,盛秋厘进去问她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她总是摇摇头。这个时间盛秋厘如果出门,把叶拉母亲一个人扔家里,她觉得有点不近人情,但天天听着叶拉母亲吐字不清的发音,盛秋厘特别难受。
每次,保姆买菜回来,把菜往厨房一放,就去叶拉母亲房间。保姆是个讷言的人,每天只做事,不多话,你不问她不说。盛秋厘决定进去看看,盛秋厘一推门,估计只看了半眼,就迅速关上了门。她看见了叶拉母亲光着的下半身,那是怎样的两条腿,已经完全萎缩成两根骨头了。还有一旁的保姆,正在给叶拉母亲换尿不湿。
盛秋厘回到自己的房间,往床上一躺,又赶紧坐起,她觉得自己想吐,她去客厅喝了几小口水。以前盛秋厘在家的时候,总是悲伤老张走得太快,这几天她看着叶拉母亲的卧病在床,她倒觉得老张前世积德了的。未来的自己如果也像叶拉母亲这样,倒不如早点了断自己。可是,未来谁知道呢?说不定未来的自己不想死呢?
盛秋厘盯着从叶拉母亲房间出来的保姆,接下来保姆应该做饭,盛秋厘看她洗不洗手。保姆直接进了厨房,盛秋厘看见保姆在厨房里用水冲了一下手。盛秋厘让保姆去卫生间用洗手液认真把手洗一下,保姆没有任何异议地接受了。
环境对人的影响是暗自发力,不动声色的。儿子张守一并没有对母亲说什么,盛秋厘自来了儿子家后,虽说还是时不时思绪就绕到老张身上去,但她的日常已经渐渐地又变回了从前的她。现在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口红也用上了。
是啊,在这个家里,如果盛秋厘再不注意自己的形象,她就和叶拉母亲站成一队了。儿子是外企的高管,叶拉是外企的翻译,自然每天都打扮得鲜亮的。孙子多多自然不要说了,叶拉给多多买的衣服都是上千的,好在盛秋厘是见过世面的,不然还真的会常常被孙子衣服的价格惊到。保姆虽是农村人,但每天都把自己拾掇得清清爽爽的。盛秋厘有次问了儿子关于保姆的工资,月薪7500。这工资在一般的小城市,就是高薪了。可是没有这般价格,谁肯天天忙屎忙尿的。
有人群就有矛盾,盛秋厘平日里跟保姆说不上三句话,开始时盛秋厘和保姆的相处,是一问一答,她们虽是同龄人,可毕竟层次不一样,三观不同。后来她们之间好像做不到和平相处了,是从气味开始的。
保姆每天下午将碗筷洗好后,有一个小时的空闲时间,这一个小时,保姆在卫生间基本要呆上半小时。有一次保姆刚从卫生间出来,盛秋厘刚好进去,盛秋厘一进去,一阵异味迅速穿过鼻孔,直往五脏六腑里钻。盛秋厘赶紧退出,找来电风扇,放在卫生间门口,开最大风速,朝卫生间里面吹。
不管保姆是什么文化层次,盛秋厘此举一出,保姆脸上憋得通红。保姆嘴角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盛秋厘做完这些,嫌弃地看了保姆一眼,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盛秋厘和保姆之间的关系就此紧张起来。但保姆买菜煮饭接送孩子,还真的做得无可挑剔。保姆平时做饭处处还是挺小心的,不知出于什么心理,对叶拉母亲的饭菜总是有点含糊。比如有次盛秋厘就看见叶拉母亲专用的碗筷没洗干净。也没有进消毒柜。如果是偶尔的一次,也就罢了。可是盛秋厘发现,保姆不将碗筷放进消毒柜,已是常态。
但盛秋厘知道了这事,她却没有和保姆说,难道盛秋厘觉得其它碗会染上相同的气味不成?问题出在一次晚上的鱼汤。保姆做好饭后,盛了一小碗去喂叶拉母亲,就在保姆低头端碗的时候,一缕头发从保姆耳边垂下来,直接晃进了鱼汤,头发在鱼汤里划了一个漂亮的弧线。保姆走向卫生间,仔细地洗了那缕头发。收拾完那缕头发,保姆继续端着那碗加了头发味的鱼汤,向叶拉母亲房间走去,盛秋厘往保姆面前一横,挡住了去路。狠狠地盯着保姆,保姆迎着盛秋厘的目光,毫不退却,只是人绕了圈,从盛秋厘旁边走向了叶拉母亲房间。
盛秋厘站在叶拉母亲的房门口,看着保姆喂那碗鱼汤。叶拉母亲似乎饿极了的样子,用尚能动的一只手,不停地拉碗,要往自己嘴里灌。可她的嘴像坏的,保姆的一勺鱼汤,只能进去半勺,还有半勺都顺着嘴角流在了围脖上。
一碗鱼汤很快见底了,叶拉母亲突然用没有中风的那只手,一把抓住碗,随即摔在地板上。保姆习以为常地捡起碗。
碗当然没有被摔坏,难道叶拉母亲摔碗是常事?怪不得专用碗是不锈钢的。
盛秋厘还是站在叶拉母亲的房门口。保姆把碗勺放回洗碗池,又去叶拉母亲房间,给她解围脖。叶拉母亲不知道是不是没吃饱。她含糊不清的语言,很是愤怒,像是在咒骂,同时用她尚能活动的那手掐着保姆的手腕,指甲抠进表皮,血印子都出来了。
保姆忍不住了,接下来的一个动作,让盛秋厘触目惊心,保姆朝叶拉母亲脸上狠狠地吐了一口痰,转身就离开。
叶拉母亲几乎是嗷嗷叫了,怎么叫也没人搭理,盛秋厘愣在门口,保姆没事一样在厨房忙活。叶拉母亲看着盛秋厘,声音渐渐低下去,用她那只没中风的手,从枕头边拿出一张抽纸,擦去脸上的口水。
当天晚上,还没等盛秋厘想好,要不要让儿子辞退保姆,保姆却先开口了。保姆跟张守一说,到了发工资的时间了。张守一疑惑地看了保姆一眼,还是拿起手机转账了本月的工资。这保姆来这里半年了,从没主动开口要过工资。果然,后头还有戏,保姆说明天要回趟老家,家里老人生病了。
第二天保姆真的走了。付了工资再请假,这都是有预谋的,肯定就是不再回来了。
张守一联系中介,让尽快再找个保姆。中介回复,他这家保姆难找,要找个不怕苦不怕脏的,关键还要力气大的,所以急不来。
没了保姆,盛秋厘当然要候补上。早饭很简单,鸡蛋牛奶面包。接着送多多,多多幼儿园离家五百米。不知道是没睡醒还是什么的,没走到一百米,多多要奶奶抱。盛秋厘因为老张的事伤心过度,大伤元神。哪抱得动多多走几百米路。盛秋厘左哄右哄,多多就是蹲在路边不走。后来盛秋厘发火了,多多才勉强起来,边走边哭,说这个奶奶没有保姆奶奶好。
盛秋厘的心里被多多给弄得乱糟糟的,去超市买了两三个菜。回到家,叶拉母亲的声音一阵高过一阵,对的,换尿不湿的时间到了。换还是不换呢?
纠结中的盛秋厘先去厨房,可叶拉母亲的叫声越来越响,最后几乎是惨烈。盛秋厘只能硬着头皮上。叶拉母亲看见盛秋厘进来,嘴里叽里咕噜的像是抵抗。她虽中风,脑子还是好使的,她不肯亲家母伺候自己。
虽然叶拉母亲没有交谈的能力,盛秋厘还是告诉她,保姆有事回家了。说着盛秋厘轻轻掀开叶拉母亲腿上的被子,瞬间,臭味像刚放出笼的鸟儿,立刻飞满了整个房间。盛秋厘一阵反胃,她忍着,给别人擦屎擦尿,除了自己的儿子,这辈子还真的没干过,可儿子的屎尿没这么臭啊。就算是多多,盛秋厘也没有给换过几回尿不湿,多多是叶拉母亲带大的。人这一生啊,该有多少劫,半劫都逃不过,这不是还债来了?
叶拉母亲已经哭得出了声,盛秋厘来不及哭,换完尿不湿就奔卫生间干呕,干呕几口清水后,盛秋厘也泪流满面了。
这才小半天,盛秋厘已经觉得日子是熬不下去了。保姆什么时候来,是个未知数。
中午的饭只准备两个人的,盛秋厘煮了青菜粥,番茄炒蛋。她把鸡蛋夹成小碎块,放在菜粥里。盛秋厘先给叶拉母亲系上围脖,然后喂她,只能半勺半勺的喂,不然外溢的较多,房间里还有难闻的浑浊气味,床上是瘫痪的形容枯槁的老人,叶拉母亲边吃饭边流泪,盛秋厘从心底涌上一股悲凉。
下午的时间是打扫卫生和煮晚饭,还要接孩子。好在多多放学时没有要奶奶抱,好像精神十足。盛秋厘和多多恰好相反,此时她已经很疲倦了。等到把晚饭忙好时,盛秋厘头晕,美尼尔氏综合症犯了。她饭都没吃,就上了床。
张守一和叶拉一进家门,叶拉母亲在房间拼命叫,小夫妻俩来到床边,猜测了半天,才知道叶拉母亲,要求把自己送进养老院,不送进养老院,她表示自己再也不吃饭。
小夫妻俩又来到盛秋厘的房间,喊盛秋厘起来吃晚饭,盛秋厘头晕得起不来。叶拉在一旁道歉,说都是因为照顾她母亲给累的。
当晚,小夫妻俩联系了本市最好的康复医院,决定将叶拉母亲送进康复医院。
所谓康复医院,其实就是个养老的地方。条件相当不错,日夜有护工照顾,像叶拉母亲这种生活不能自理的,护工每两个小时要给病人翻一次身,护工不可偷工减料,有摄像头呢。每个人的食谱都要针对个人的情况特定的。
张守一又请来了保姆,这次请保姆容易多了,少了一个身体健壮的条件,来了个二十几岁的小姑娘。
盛秋厘身体时好时差,腰疼要贴膏药,活血要吃中药,弄得家里像药房,时时弥漫着浓浓的药味。如此的光景持续了一个多月。叶拉的脸色没那么好看了,有时候连晚餐桌上小夫妻俩也在争论。不过,到底争论什么,盛秋厘听不懂,估计在说这药味的事。不然,他们为什么用英语争论,为什么偏偏让自己听不懂呢?盛秋厘自己去办手续,也住进了康复医院。
刚开始住进去,盛秋厘感觉还好,像她这种能下地活动的,上午九点还有个保健操时间。没有了一个人住在家里的寂寞,也没有了住在儿子家的不安。
几个月后,盛秋厘感觉就不大对劲了,一些能做保健操的人有几个相继躺床上去了,一些躺床上的又相继有几个变成空床位了。像这深秋树上的叶子,只见掉落,不见新生。
老张已经走了十三个月,这些天盛秋厘总是梦见老张,她想回家一趟,去公园坐坐。
盛秋厘坐在那条斑驳的长条木椅上,轻声说:“老张,我看你来了”。出去了整整一年,盛秋厘发现,自己的心突然安静了,魂还是在这里。盛秋厘环顾四周,公园里的一切照旧,只是树叶有些稀疏了。老张喜欢的那棵银杏树,没几片树叶了,像老人的头发或牙齿,屈指可数。
小虎!真的是小虎!不知它从哪里冒出来的。小虎更老了,它的毛发像枯草,那雨水沾不住,油花水亮的毛发,遗落在岁月里。它围着木椅转了一圈,对着盛秋厘摇了摇尾巴,就又坐在那尊石像旁,依然那个姿势,依然那个位置。
盛秋厘泪光闪闪地看着小虎,又突然转头向上看,她看见老张在云端向她招手,并真真切切地喊了她一声:“小厘!”
盛秋厘觉得自己的身子越来越轻,越来越轻,像飘向天上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