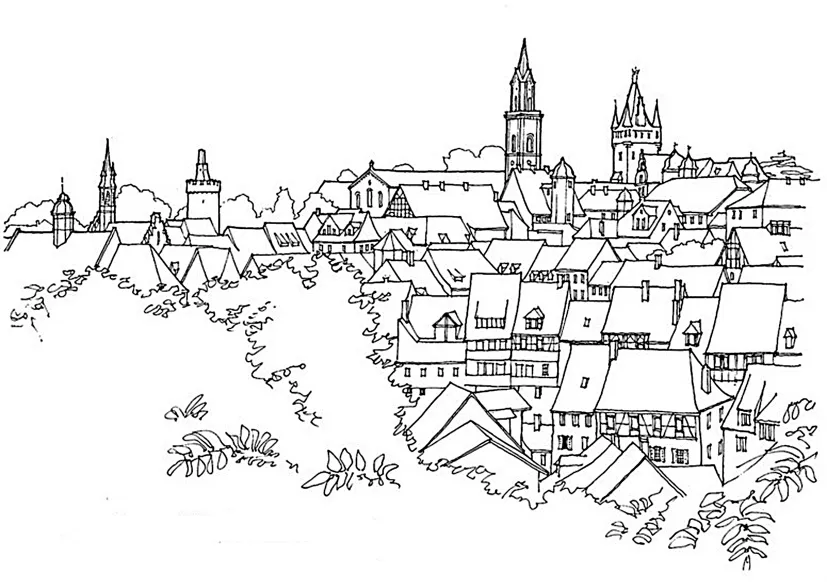
1
今年清明没有下雨。小毛坐在小卖部门口嚼着口香糖,他想吹一个大泡泡,试了好几次,泡泡没吹起来,口香糖倒粘一脸,他把脸上的口香糖扯下来,再塞进嘴里,又嚼了起来。最近到桔村赏油菜花的游客越来越多,小卖部的生意也红火了起来,以前两三个月才去镇里进一次货,现在隔几天就要打电话给供销社,叫他们派人送货过来。小卖部的葛老头瞧着小毛悠闲的样子,心里添火,说话直撵小毛走。小毛当没听见一样,鸟都不鸟他。
屋外头的大樟树沙沙作响。小毛一抬头,枯叶哗哗地落在他的脸上,似乎有东西沿着树梢向着界山岭那边游去;小毛回过头,眼睛骤然放光,一口啐出口香糖,高兴地喊着二苕。只见在河对面,二苕沿着田埂一路小跑,不管去哪儿,不管距离有多远,二苕只会跑,心情好的时候,他奔跑的速度非常快,一溜烟,土路上扬起一层灰尘,他已经从田畈对岸跑了过来。
二苕不是本村人,他什么时候来到桔村,没人说得清楚,反正嫂子们刚嫁过来、年轻人都穿着开裆裤的时候,就见到二苕在田野中奔跑。二苕的体力异于常人,吃饱一顿饭,能跑上一整天,穿过树林,蹚过河流,只要在土地上奔跑,他就很满足了。
葛老头刚想喊二苕过来捆纸箱子,小毛抢先一步,跑过去拉住二苕,说东扯西。二苕乐呵呵地笑了,他穿着大一号的旧校服,捯饬得有模有样,像是辍学在家的学生,一开口说话,嘴里含了石子似的,呲呲的,除了几个简单的字眼,根本听不清他说什么。大多时候,二苕也只能通过比划手势与别人交流。
小毛跟别人不一样,他喜欢跟二苕说话,要么是从七姑八婆那里听来的玄乎故事,要么是没油没盐的家长里短,无论说多久,无论二苕是否在倾听,小毛说个不停,还不会感到疲倦。他也有想过,是不是要好好教一下二苕说话,免得总是自己一个人说,聊天这种事当然是两个人有呼有应才好。
葛老头见状,不大高兴了,嫌小毛闲得没事做,光碍事,于是对二苕连连招手。二苕没有理会他,径直走进小卖部。每次路过小卖部,二苕都会钻进去拿两包干脆面,他不多拿,就拿两包,他不拿别的,就拿干脆面,而且从不给钱。葛老头也没打算找二苕要钱,他直接把干脆面摆在柜台上,随二苕拿去,一天两袋干脆面,一个月 60包,顶多 30块钱,而自己一个月的低保就有好几百,别说一天两袋干脆面,就连一天五袋他都顶得住。
村里的劳动力统统上桌打麻将的时候,二苕就帮人干点砍柴、种地、喂养畜生的粗活营生。干完一天的活,别人给他一张10元,二苕会生气骂人,他要十张1元的;别人要给他二十张五角,他就更高兴了。二苕不认识钱的面额,简单地认为钱就是数张数,越多越好。村里人发现这个规律之后,每次去镇上办事顺便散一把零钱,回来吩咐二苕干活,顺手塞给他几十张一角。二苕拿到零钱,欢欣得要死,点头哈腰地说,好人啊,好人。好人这两个字,二苕发音发得最清晰,也最响亮。在营生方面,二苕也有自己的原则——帮葛老头干活坚决不收钱。
二苕吃干脆面嚼得嚓嚓响,他喜欢这个声音,一听到这个声音,面饼也变得好吃了起来。他正准备转身离开,葛老头一把拉住他,歪着嘴说道:“你吃了人家的面,总得听人家说几句话吧。”
二苕望着葛老头笑了笑,露出两颗黄色的大门牙。
葛老头心里想,跟二苕说的那件事,二苕肯定接受不了。他一向快言快语,这会儿却犹豫了,支吾了半天,竟一个字也没说出口。
二苕指了指河对岸的界山岭,他要到山里挖天麻。葛老头摆摆手说,不是那个事。二苕见葛老头扶着老腰,猜测他的腰病又犯了,跑过去一脚把纸箱子踢飞,比划了两下,老家伙不讨媳妇,赚那么多钱干嘛。二苕又乐呵地笑了起来,他不管葛老头明不明白他手势的意思,掉头就跑。葛老头的话还没说完,跟在后头,无论怎么喊二苕,二苕头也不回。
2
这个季节油菜花开得正灿烂,百亩花田在春风中分出一条小径,阳光洒在花瓣上,闪烁金黄色的光芒。二苕喜欢这种被阳光刺得睁不开眼的感觉。他常常在正午跑到山坡上望太阳。村里人骂他疯,三岁的小孩都知道正午的太阳最耀眼,可是二苕觉得阳光射在眼珠上,刺痛之后,全身就舒服了。在一片白花花的光芒中,他能看到许多特别的景象,最令他惊奇的是那一条巨大的鲤鱼。二苕也不知道为何能看得见大鱼,或许是山影,或许是流云,或许只是因为他怕尖锐的鱼刺,始终不敢吃鱼。
大鱼常常悠闲地出没在田野、森林、河流,它喜欢在农作物和树枝里游荡,青色的鳞甲发出彩色的光线,那是一副迷人的景象,特别是它的眼睛,水汪汪的,像是一泓清澈见底的泉水,水面波光粼粼,多望两眼就会让人上瘾。二苕跟在大鱼的后面,雀跃地奔跑,从山丘到河谷,从村庄到田畈。大鱼游弋得很缓慢,像是故意在等待二苕,然而,二苕无论使多大的劲,就是追赶不上它。二苕不停地奔跑,喘着粗气,直至筋疲力尽,实在跑不动了,才瘫坐在田畈里,凝望着大鱼渐行渐远。这时二苕笑了,他笑得很开心,尽管没有追赶上大鱼,他晓得自己迷恋上了这只自由自在的大鱼。
在路边,二苕随手摘了一把油菜花,一朵接着一朵辫成他喜欢的椭圆形,然后扎成大鱼的形状,今天肯定会遇上大鱼的。他把编织的大鱼举过头顶,一边奋力地跑动,一边想象着大鱼在油菜花海里游弋的景象,不由得欢呼雀跃。二苕对自己的作品很是满意,他想把这个玩意送给冬梅。冬梅一定会高兴的。
二苕忘性大,他忘了许多事,但是,他忘不了初次见到冬梅的情景。那年闹饥荒,饿死不少人。家里搬得动的东西都拿去换了芋头,连做饭的铁锅都换了四个馒头,只剩下一口没人要的破缸。实在没办法,为了活命,二苕被他娘拽着出去要饭。路上听说桔村田多粮多,娘儿俩咬定牙,下狠心,就是走也要走到桔村。他们忍饥挨饿走了三天,拖着烂草鞋,硬是走到了桔村。娘只剩下一口气了。一进村,一条狗一只鸡都没有,房前屋后安静得有些诡异。他娘一下子明白这个村子也没有了余粮,就痛哭了起来。
蹲在一边的二苕不知所措,他转头发现一个拄拐杖的小女孩躲在门后,正目不转睛地望着他。二苕不由自主地跑了过去。女孩怯弱地问他是不是饿了。他点了点头。女孩打开门,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炒米递给他,说外面冷,叫他把他娘带回去。
二苕愣了半天,听她娘哭得厉害,他才转身跑了回去。不一会儿,二苕又跑了回来,一声不吭地望着女孩。女孩说她叫冬梅。二苕好像听了进去,又像没听进去,没等冬梅说完,他哼唧几声走了。二苕打那时起就记住了冬梅。
3
小路越往前走,油菜花开得越发喜人。这片肥沃的土地是何强家的自留地。
何强是冬梅的堂哥,也是桔村为数不多没有外出务工的青年,结识了几个小混混,学得流里流气的。山头有一块集体经济林,何强承包下来搞药材种植,天麻的价格一路走高,一年也赚了不少钱,他没上缴过半毛钱的租金,嘴上还骂村里不给他申请担保贷款,好把天麻种植的面积再扩大。桔村人少,党员更少,村党支部都是几个老头子,再死几个,连举手表决的人都没有了。党支部看中了何强的年轻,能为村里打点大小事,见他天天嚷嚷着山林的事,干脆拉他进班子充人头,至少落得个清静。何强巴不得进入村委班子,好发展他的天麻种植。两者一拍即合,先让何强火速入党,随后被选举为村委会委员兼治保主任。
上次,二苕爬到大槐树上掏鸟蛋,无意瞧见何强跟年轻的女人在油菜地里脱光了。那女人的皮肤真白,水嫩水嫩的,何强松垮的肉紧紧压在女人的身上。二苕从未见过这样的场面。他觉得睡在那个女人身上肯定很暖和,连何强的表情也变得和平时不一样,横肉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脸的畅快。二苕感觉自己也有些不对劲,他一低头,裤裆硬邦邦的,吓得他从树上跌落了下来,红着脸,飞快地跑了。自那以后,二苕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他觉得身体里有一条虫子在蠕动,导致全身酥痒痒的,他跑到河里洗澡,可是无论怎样清洗身体,就是消不掉身上的异样。是不是得病了?二苕郁闷了。直到有一次他无意间在小卖部前看见两只狗在交配,于是凑过去仔细观察,瞅瞅摸摸的,把两只狗吓得分不了身,不知如何是好,叠着身子往屋后跑。葛老头生气地敲了几下他的脑壳,狠狠地骂他“下流”。二苕大概明白了些什么,似懂非懂地傻笑了起来。从此,他无论是喂猪、挑粪还是扯花生,都自顾地笑着,脑子里一遍遍回放着两只狗交配的画面。他傻笑了好几天,嘴差点笑歪了。这时盘桓在他头顶的大鱼也嘶嘶地叫了起来,很明显大鱼也看透了二苕的想法。
二苕走累了,干脆在田埂上躺下,从口袋里掏出一袋干脆面。干脆面嚼起来像炒米一样香脆。油菜田不远处,一群游客趴在地里专注地采摘野菜。南方气温稍稍升高,野菜就疯狂地滋长,把裸露的黄土地裹得严严实实的。当下正是吃野菜的时候,比如说田畈里的软萩,桔村人会拿它做成软萩粑,香甜糍糯,是农家春季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佳肴,而在城里,新鲜的野菜和地道的土味都是紧俏货。无需门票,还能带土特产回去,这样的旅游行程最受中年妇女的喜爱,她们一窝蜂地涌入桔村。桔村人看出商机,麻将都不打了,重新抄起旧家伙,熟练地在田间地头挖野菜,再转卖给游客,这种钱挣得太简单快捷了。他们从光屁股蛋子的时候就在田里摸爬滚打,自然对土地熟悉,知道哪儿的野菜长得肥,重秤。
游客、野菜什么的,跟二苕没有丝毫关系,他不认识野菜,只知道那些随处疯长的东西就是贱,不值钱,更不会好吃。二苕将手臂枕在头下,仰头望太阳,眼前白茫茫的一片,空空如也,怎么也寻不着大鱼,它躲哪儿去了?二苕的脸色一下子变得阴沉,大鱼不见了,就会发生不好的事。上一次大鱼不见了就是在他娘死的前一天。一整夜,娘都在不停地吐血,二苕见过血,却没见过那么多血,乌黑乌黑的。他端着一个大木盆,接了满满一盆。娘生了三个儿子,机灵的都在为过日子精打细算,只有二苕守在娘的身边,娘的心比灶门星子还凉。二苕刚开始还觉得吐血蛮好玩的,他学着他娘吐血的样子,咳咳卡卡的,滑稽可笑,娘也笑了。等二苕发现娘的脸苍白得如同一张白窗纸的时候,才觉得事情不对头,他赶紧跑到灶头,拿了一块软萩粑塞到娘的手里。软萩粑是他前几天去后山偷来的,那儿新建了一座寺庙,来了一位讲四川话的老和尚,老和尚说话的声音像是唱歌一样,很快就吸引一群虔诚的妇女围着他打转,软萩粑就搁在老和尚的柜子里,柜门也没锁,一共五个软萩粑,二苕只拿了两个,自己只吃了一个。他娘捧着冰冷的软萩粑突然哭了,有气无力地喊道,儿啊,娘要死了,把你托给谁啊,你两个哥哥连娘都扔下不管,肯定不会管你的,你还是跟娘去那边吧,免得活受罪。
二苕干瞪着眼,看着娘又笑又哭,他觉得有些莫名其妙。娘怕是疯了吧。二苕觉得娘要是疯了那该多好玩。
娘知道命又不是能哭出来的,很快就平静了,她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瞅着那一块软萩粑,软萩粑是由糯米做的,粘性大,中间夹着芝麻糖心。娘知道自己吃不下一整个,她只能咬一口,这一口最好是把芝麻糖心全咬下去。芝麻糖心是软萩粑的精华。娘爱吃甜食,日子过苦了总希望能尝到甜味。如娘所愿,她一口咬下了整块芝麻糖心,只不过这好不容易到口的甜味,如何使劲都咽不下去,芝麻糖心卡在了她的喉咙里,娘急了,双手紧掐着脖子,没挣扎几下就断气了。二苕对死亡的概念或许就是软萩粑上凌乱的牙印,他也想吃芝麻糖心。
一连几天,二苕怎么叫都叫不醒娘,他扇了娘好几个耳光,娘还是没反应。他就跑到寺庙里找老和尚扯皮。老和尚阿弥陀佛了老半天,才叹气地说,埋了吧!
4
躺在油菜花地里的二苕惊愕地跳了起来,干脆面撒了一地。他想起了瘦如干柴的娘,也想起了老和尚的话,“埋了吧”这三个字反复在他的耳边咬。埋娘是一件轻松活,他在大哥房屋后面的山坡上挖一个坑,把娘拖到坑里,再盖上土,压上石头,完全不费力气。他做完这些事,没花几个钟头,他哥根本不知道娘被埋在了自家的屋后。有没有娘对于二苕来说毫无改变,他像是没事的人一样。只不过偶尔发觉来来去去总是自己一个人,行影孤单;特别是睡觉的时候,没有娘捂脚,脚背总是冰冷。现在关键的不是娘,二苕心想,是大鱼消失了。一旦大鱼消失,就会发生不好的事情。他怕不好的事情会与冬梅有关。
二苕在油菜花田里踏来踩去,寻找大鱼。它到底躲哪儿去了?大鱼是从来不会胆小的,它吃过何强家的豆子,吞过葛老头的钱匣子里的硬币,它庞然大物的体型能躲到哪儿?二苕不停地奔跑,金黄色的油菜花蕊快速地从他眼角划过,浓郁的花香扑鼻而来。忽然,冬梅的笑容出现在二苕的跟前,二苕的心一下子温柔起来,笑着露出两颗大门牙,叫唤冬梅的名字。二苕从小就爱笑,笑多了别人骂他是傻子,他没有心思理会别人说什么,只希望能天天见到冬梅。
冬梅患有脑瘫,双脚不能行走。他爹死要面子,生了丑姑娘见不得人,一直把她关在家里。等她长到足够大的时候,他爹才意识到不能将她老锁在家里,会闷死人的,这才把她放在门槛上,好歹也能看门。冬梅从未走出过院子。
只要是晴天,冬梅都会坐在门槛上,只不过半人高的砖石围墙挡住了她的视线。她跟父亲说过,想把围墙拆了,种上油菜花,旧挂历上的油菜花黄黄绿绿的,好看极了。他父亲并没有理会她,径直地走进后院,埋头劈柴。
二苕埋了娘,自己又跑回了桔村。他只想做一件事,告诉冬梅有关大鱼的一切,那是二苕能想到的最好玩、最美妙的事情。他一路快跑,三天的路程,只花了一天半。一进桔村,他直接冲进冬梅家的石墙院子。此前,他偷偷来过许多次,对这儿的一切都熟悉。二苕见到冬梅,就迫不及待地向她描述眼前绚丽的景象,也许是太紧张了,他的舌头像是打了结,以前能清楚吐出的几个字眼也蹦不出口。冬梅叫他慢慢说,他急得用手左比划右比划,看得冬梅一头雾水。一番折腾,毫无进展,二苕气得扇了自己几个耳刮子,一屁股坐在地上,差点就哭出了声。冬梅扔了一根竹棍给二苕,自己也拿起一根竹棍,在地上画一座小房子。冬梅开始教二苕画画,这是她能在院子里做的为数不多的游戏。二苕如获至宝,他扔掉了竹子,麻溜地钻进竹林,找来了一根粗竹竿。断断续续地在地上画了一条大鱼,光鱼头足足占去了大半个院子。二苕无法将大鱼画得和他看到的那样逼真,甚至线条都是歪歪扭扭。他也管不了许多,恨不得要把冬梅塞进他脑子里,一起观看那条梦幻的大鱼和那些绚丽的画面。二苕一边画画一边回头看冬梅,冬梅正认真地欣赏着地上的大鱼,时不时发出惊叹的声音。他心满意足了,卖力地打造他的首幅画作。然而,就差画完大鱼尾巴的时候,何强突然拐进院子,见到兴颠颠的二苕,话没多说,一脚把他踹在地上,叫他赶紧滚。二苕最怕何强了,每次瞧见何强像是见了门板上的门神,躲得老远。这次挨了何强的一脚,也只能欠欠身子,赶紧爬走。
冬梅他爹闻着声音出来了,问什么事?
何强是来问冬梅他爹要山头的地,那块地正处于山沟的半阴半阳处,种植天麻再合适不过了,但是何强不说田地,却说,叔,你是老糊涂了,冬梅妹子怎么和二苕搞在一起?我们何家是要脸面的。
冬梅他爹大喝了一声打断了何强,气愤地说,我家的事不用你管,拉着冬梅往屋里走。二苕没走远,他趴在石头墙边,瞅了一眼冬梅,只见冬梅的眼睛红彤彤的,泪水直流。二苕的心七上八下,不是滋味。
5
田边采摘野菜的游客发现了二苕的异状,她们杵在田埂上,像一群鹅伸长脖子四处张望,急着要去挖掘乡村八卦。桔村的油菜花长得比人还高,二苕淹没在油菜花海里,见不着头,望不见脚。他一口气跑得老远,骤然打不着方向,一个踉跄摔倒在地,压倒大片油菜花。二苕瞅着黄灿灿的油菜花,脑海闪过五颜六色的光芒,好一会儿,他才缓缓睁开眼,太阳明晃晃的,望着特别舒服……
二苕忽然觉得耳朵灌入了风,凉飕飕的,难道是大鱼的呼吸,他惊得坐起来,左右打量,不见任何踪影。奇怪的是——冰凉的风又往他耳朵里灌,弄得他浑身酥麻,八成是大鱼的恶作剧,大鱼常常玩这样的戏法,但是耳廓敏感搔痒的滋味让他忍不住想起了交配的场景,何强身子下面的裸体女人扭动的身子,发出性感的呻吟。他闭上眼,女人光滑的皮肤、丰满的胸部,像是贴在了身上,热乎乎的,无论他怎么甩都甩不脱,他又好奇又羞怯,或许,此时此刻大鱼正卧在他的身上挑逗戏弄他,大鱼比二苕更懂得这些秘密。这种舒服的感觉,也让二苕想到冬梅。然而,一想到冬梅立马睁开眼,翻身起来了,他明白想象冬梅裸露的身子是可耻、要不得的。他赶紧查看四周,没有大鱼的任何踪迹,却发现茫茫花海之中,自己孤零零的一个人。他有些寂寞,也有些失落,更加想念冬梅了。
要是搁在以前,他干脆跑到冬梅家,找她说会儿话。冬梅每次都是门槛上,似乎除了门槛,她就没有在别的地方出现过。她捧着一只纸风筝,左右端详,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直夸风筝五颜六色,真好看。
风筝是葛老头做的,鸢儿画得有模有样,再贴上五色花纸,栩栩如生。葛老头祖上是糊灯笼的,手艺是天生的,他最拿手的就是做纸活。以前他一年也只在农忙,没人来打麻将的时候,才糊上几只风筝,自己把玩。二苕见着风筝,嘴里发出呼呼的声音,张开双臂在院子里跑来跑去。他似乎把自己当做一只风筝,呼啦啦地想要飞上天。
我们去放风筝吧!冬梅小声说道。二苕没反应过来,傻愣在一旁。冬梅把风筝举过头顶晃了晃,放风筝啊。二苕疑惑一小会儿,明白了是怎么回事,猛地点头答应。
我不会走路,那你得背我。冬梅嘘了一声,说道,小声点别让我爹知道了。
二苕点点头,放慢动作,数着后院的砍柴声,一步一回头,如临大敌般走到冬梅跟前。冬梅被二苕滑稽的动作逗笑了,纵身一跃,趴在二苕背上,“走”字还没说出口,二苕一股劲冲出了半人高的石墙院子。冬梅仿佛看见二苕在地上画的那一条大鱼打了一个激灵,活了起来,左右摇动着尾巴,铆足劲带着她冲出水面。她紧紧地扣住鱼鳞,身子贴近鱼背,红通着小脸,她好想大声地喊出来,又怕惊动了他爹,只得紧咬着嘴唇,把兴奋气憋在小小的心房里。
出了家门,冬梅一把拉住二苕,用力将他拉上了鱼背,他们俩并排坐着,二苕从没追上过大鱼,也没坐过鱼身子,这是第一次,他怕冬梅掉下去,特意扶着冬梅的肩膀。大鱼向着山那边缓缓游动,冬梅耐不住内心的喜悦,东张西望,她从来不知道家外面有一口塘,倒是那几只走来走去的大白鹅,每天都会见到好几次。塘边种有一排叫不上名字的树,除了石头墙里的樟树,她也不认识别的树。这些树还开着白色的花骨朵儿,她猜测这些天闻到的花香就是从这儿飘来的,大鱼从树梢游过的时候,顺手摘了一朵小花,她塞在鼻子里,真香。石头墙外面到处都是新鲜的东西,冬梅的眼睛都看不过来,头晕目眩。她完全忘记了门口的那条光滑的门槛,也忘掉手中的风筝,只催促着大鱼游快点,去更远的地方。二苕见冬梅笑了,他也乐开了花,欣慰地拍了拍鱼身。大鱼也喜欢冬梅,它摇动鱼鳍,游得更快了。
他们一同游过桔村的白墙乌檐,几只雀儿懒散地漫步在石板路上,哪怕人走到身边,它们还不愿飞去。老老少少都去摘野菜卖钱,村子寂静无声,静得有些奇怪。二苕很少说话,冬梅却一遍一遍重复着再远点、再远点。大鱼游了十几里地,翻过山头。大鱼在天空游荡,二苕和冬梅坐在山丘上,眺望着生长在河岸边的百亩油菜花,那些数不尽的黄色小花朵像是一条碎花长裙,冬梅恨不得把它穿在身上,喃喃自语道:这么多花一同开放,是不是也会一同凋谢,要是这么多花都谢了,真可惜啊。
二苕管不了油菜花可惜不可惜,他躺在山坡上,看着冬梅的背影,骤然又想起了那位赤裸的女子,他无法阻止这样的想法,心怦怦地跳动。他想冬梅睡在自己身边。二苕拍了拍冬梅的肩膀,示意冬梅躺下。他没想到冬梅真的会躺下,一下子不知所措,眼睛直愣愣地盯着天空。天是灰蒙蒙的。二苕听到了冬梅的呼吸声,润如春雨,搅得他的心乱七八糟。二苕好想翻过身睡在冬梅身上,他晓得那样做不好,但是他又禁不住那样想。他一动不敢动,四肢僵硬,全身发麻,似乎下一秒就要晕死过去,即便如此,他还是面带微笑地望着冬梅。一旁的大鱼嗷嗷地叫了起来,这让二苕不知如何是好,直骂大鱼是个坏家伙。
今天的天也是灰蒙蒙的。二苕踩着油菜花站了起来,他眺望着界山岭,或许,他的大鱼就在山的那边。
6
那天,二苕摘了一大把各式各样的花儿送给冬梅。冬梅接过着花束,咿咿呀呀胡乱地唱着歌,这些歌是从大鱼那儿学来的,大鱼在高兴的时候,会哼唱古老的歌谣。冬梅他们又计划去山的另外那边,然而刚出门的时候,就被冬梅她爹发现了。他爹愣了半天,才回过神,缓缓闭上眼,一副欲哭无泪的样子说:我何某粗人一个,一辈子是要脸的人,就听不了别人笑话,生了你,我的脸系到了裤裆,今天,我的脸算是贴在了地上。
他爹一把将冬梅提进门槛,不由分说地痛打了她一顿。冬梅叫都没叫一声,眼睛像灯泡一样瞪着她爹。他爹见状,气不过,下手更重了。站在门外的二苕鬼哭狼嚎,像是棍子全都落在他的身上一样,在地上痛哭流涕地打滚。他爹一把锁了大门。
二苕悄悄躲在院子外,站了好几个小时,直到屋子里没有一丝声响,他才离开。那天的夜黑得特别早,二苕像是一块抹布,歪歪扭扭地甩在石板路上。他心疼冬梅,埋怨他爹下手真狠,比何强还狠。二苕没看清路,一把撞倒了葛老头。葛老头的酒喝了不少,扯着二苕发酒疯,他拍着二苕的脸说道,咋了?想媳妇了?一个二苕,一个瘫子绝配啊。二苕一听,的确他和冬梅蛮配的,心中的怨气一消而散,呵呵地乐了。
葛老头问二苕想娶冬梅不?二苕拼命地点头。
五千块。葛老头竖起五个手指,你只要有五千块钱做聘礼,你就可以娶她了。上次我和冬梅他爹喝酒,冬梅他爹亲口说的。
二苕高兴地从裤裆里掏出一个破旧的皮包,拿给葛老头看。葛老头说,这里头都是分分角角,值不了多少钱,都是那些丧尽天良的骗你干活。你得学会认钱。五千块你知道多少吗?你只要从你哥手中把你低保的折子要回来,何止五千块,要多少有多少,到那时,你领国家的工资,也算吃皇粮的。葛老头忍不住骂道,你哥算是个狗屁的监护人,拿你的低保花,又不管你的死活,他怎么不断子绝孙啊。
二苕摇头,自从把娘埋在他哥的屋后,他就再也不想回到那个地方去了,更不想见到他哥。
葛老头悻悻地说道,我儿子要是还活着,和你一样大,也要娶媳妇咯!说完,葛老头醉卧在石板路上不省人事。二苕也兴高采烈地挨着葛老头在大街上睡了下来。终于可以娶冬梅了,一想到这儿,他一夜没合眼。
认钱是第一步,二苕在这方面真花了不少工夫。最后还是小毛聪明,他给二苕想了个办法。小毛让二苕什么面额的钱都不认,只要能识别绿色的50元人民币就行,干一天活,只要一张绿色的纸币,其他的一概不要,谁家想赖账,就去谁家躺着,赶也不走,别人肯定会给的。二苕一下子就学会了这个法子。葛老头还特地给他做了一个牌子挂在身上,教他哪儿都别去,就在小卖部外头坐着,总会有生意上门的。
果不其然,二苕的第一笔生意很快上门了。何强叫他去挖天麻,而且预先给了一张绿票子。虽然何强有这样那样的不好,但只要他给钱就行。好歹何强也是冬梅的堂哥儿。一想到这里,二苕从裤裆的破皮包里掏出了那张绿票子,左看右瞄,又心满意足地塞进裤裆。摸到了钱,二苕立马浑身是劲,有钱就可以娶冬梅了,他越跑越欢,界山岭近在眼前。
7
二苕没走几步就听到小毛在后头喊他。小毛跑得一身汗,喘着粗气拉着他说:冬梅被一群外地人强行接走了,车上都贴着喜字,听说她要嫁到隔壁省,光彩礼钱就是八千元,还带来不少物件,你快去看看。
二苕开始还听不大明白。小毛又重复了好几遍。二苕明白冬梅被接走了,大鱼在他心里骤然破灭,他一下子蹦哒了起来,面红耳赤地往村子跑去。等他冲进冬梅的家,迎亲的车队早已离开,石头墙院子摆满了贴着囍字的嫁妆,冬梅他爹一脸失落地坐在门槛上。何强瞅着二苕恍恍惚惚地溜进来,一把拉住他,叫他赶紧走。
骗子,你们都是骗子。二苕一肚子的怒气爆发了,冲上去和何强扭打在一起。二苕不及何强身强体壮,没占到丁点优势,很快就被何强按倒在地,他彻底放弃了抵抗,任凭何强的拳头落在脸上,鲜血直流。他发出杀猪般的嘶叫,仿佛挨顿打,能让他舒服点。
二苕不哭不叫,一动不动地坐在地上,表现得出奇的安静;反而是何强喘着粗气,嘴里骂骂咧咧的。二苕立起来,一米五八的个头不高,但足以让何强感到一股不寻常的气势。二苕死死地盯着冬梅他爹,好一会儿,才走出了院子。
望着二苕离开的背影,冬梅他爹捂着脸,骤然哭了起来。
二苕一路小跑,回到了土地庙旁的小棚子,土地庙不属于任何人,没人叫他从那儿离开,那块地方就成了他唯一安身的家。土地庙不大,大概只能放得下一张八仙桌,二苕在旁边搭的棚子可比土地庙大得多了。土地庙有络绎不绝的信徒朝拜,摆满各色祭品。二苕觉得跟土地神做邻居刚刚好,饿的时候还可以跟土地神借点吃的。只不过信徒总会烧大把的往生钱,烟太大,能把他熏得泪流满面,土地庙什么都好,就这一点让他不满意。
二苕躲在棚子的最里面,辗转反侧,像是身上长了虱子,怎么调整姿势都不舒服。他想,冬梅去那么远的地方,她该怎么办?冬梅走了,自己又该怎么办?大鱼突然在二苕的脑海翻腾起来,仿佛要把他的脑门给挤破。二苕不停地摇头晃脑,想要把大鱼从脑海中甩出去,大鱼如同感应到了他的所思所想,转头向他的脑海深处游弋。这时,二苕看到了他娘在床边吐血;冬梅被一队轿车带走,这都是令他伤心的事,偏偏发生在大鱼消失的时候。都怪大鱼!他迷恋大鱼,追赶大鱼,大鱼却跟自己结了仇似的,老欺负自己,简直太坏了。一想到这儿,二苕的身子也跟着颤抖起来。要不是大鱼在油菜田里突然消失了,他也不会有这么多的噩运。二苕刷地站起来,打定主意要去找大鱼复仇。他从袋子里摸出一把镰刀,这是何强给他去割天麻的工具。
二苕冲出棚子向油菜田跑去,他知道大鱼一定躲在某个不显眼处,好让他找不着。他钻进油菜花田,肆意地踩踏着油菜,而且越踩越有劲。他把所有的劲头都撒在这一大片油菜花上。如果把这些油菜花统统都给踩烂踏平,大鱼自然没有地方躲藏。正在这时,油菜花里传出了簌簌的响声,夹杂着微弱的呻吟声,是大鱼在嘲笑他吗?二苕拿着镰刀循着声音跑了过去。呻吟声越来越急促,越来越强烈。他走近一看,何强又和那个女人光着身子缠在了一起。二苕第一反应:这是不好的事,是下流的行为。他看见年轻女人甩动的乳房,他耳根子通红,心里热血沸腾,由此骤然想到了冬梅。他将体内的那股冲动转化为怒气,两眼放着绿光,对着何强挥舞着镰刀,从喉咙里发出嘶吼,仿佛要把何强四分五裂。这可吓坏了何强和那个女人,他们顾不了光着身子,东躲西藏。何强诺诺地说,冬梅的事跟自己无关,他只想得到那块田地,把冬梅卖到隔壁省是她爹的主意,不是卖,是嫁,呸,卖就是嫁,嫁就是卖,卖和嫁是一回事。他给冬梅找了一户好人家,有的是钱,不会亏待冬梅的。一提到冬梅,二苕就没了主见,他傻愣了一下,想捋顺事情,脑子里却乱成一摊浆糊。难道冬梅真是被她爹卖了?
何强趁机一把夺过二苕的镰刀,一脚把他踹倒在地上。二苕顺势闪了过去,抢走他们堆在一旁的衣服,撒腿就跑。
天完全黑了下来,桔村家家户户一边收看着《新闻联播》,一边讨论着今天冬梅出嫁的事,有人愿意娶她,也算是没白当一回女人。外头石板路上,二苕手舞足蹈地甩着手里的衣服。他大声喊叫,吸引了不少村民围了过来。葛老头拍了拍二苕的肩头,问他怎么了?这不是何强的衣服,从哪儿搞来的?
二苕对着葛老头翘起了两根手指,趴在地上学着何强的动作,臀部蠕动着,嘴里发出呻吟的声音,脸上一副享受的样子。村民一看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一哄而散。只留下葛老头,他语重心长地对二苕说,你别闹了,快走,回到家里去。
家?二苕痴痴地望着葛老头。
对,家,你娘生你的那个家。
没家。二苕泄气地躺在冰冷的石板路上,不愿起来,像是一只忍饥挨饿的流浪猫,等待着漫漫长夜早点过去。他翻过身,望着亮铮铮的月亮。好大一轮圆月,月光落在他眼里,呈现出一片白茫茫的景象。大鱼从他的跟前悠然游过,他伸手去抓,似乎能抓住一片闪闪发光的鱼鳞,鱼鳞上映着冬梅的脸。冬梅说,她想去更远的地方。的确,她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
冬梅喜欢大鱼,大鱼也喜欢冬梅。二苕抹干了眼泪,即便为了冬梅,他也要找到大鱼。他再次冲到田畈里,发疯地奔跑,一片片油菜花被他踢倒踩烂。何强报了警。警察没来之前,他作为治保主任组织村民围捕二苕。
追捕行动一直持续到夜晚,桔村百亩油菜花田,大批油菜倒弋在田埂上,村民追逐着二苕。二苕开心地笑着、叫着、做着鬼脸,嘲笑那些掉在他后面的老老少少。突然,他一脚踩空,一下子滚到了田沟里,腿折了,趴在地上一动不能动。就在这时,他觉得耳朵灌入了凉飕飕的风,是大鱼,他愤怒地抬起头,大鱼正安静地看着他,鱼鳍旁伸出了一只手,冬梅探出了头,喊他上来。二苕喜出望外,应了一声又一声,全身又有了劲,轻灵地从地上爬了起来,拉着冬梅的手,跃上了鱼背。
大鱼游向了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