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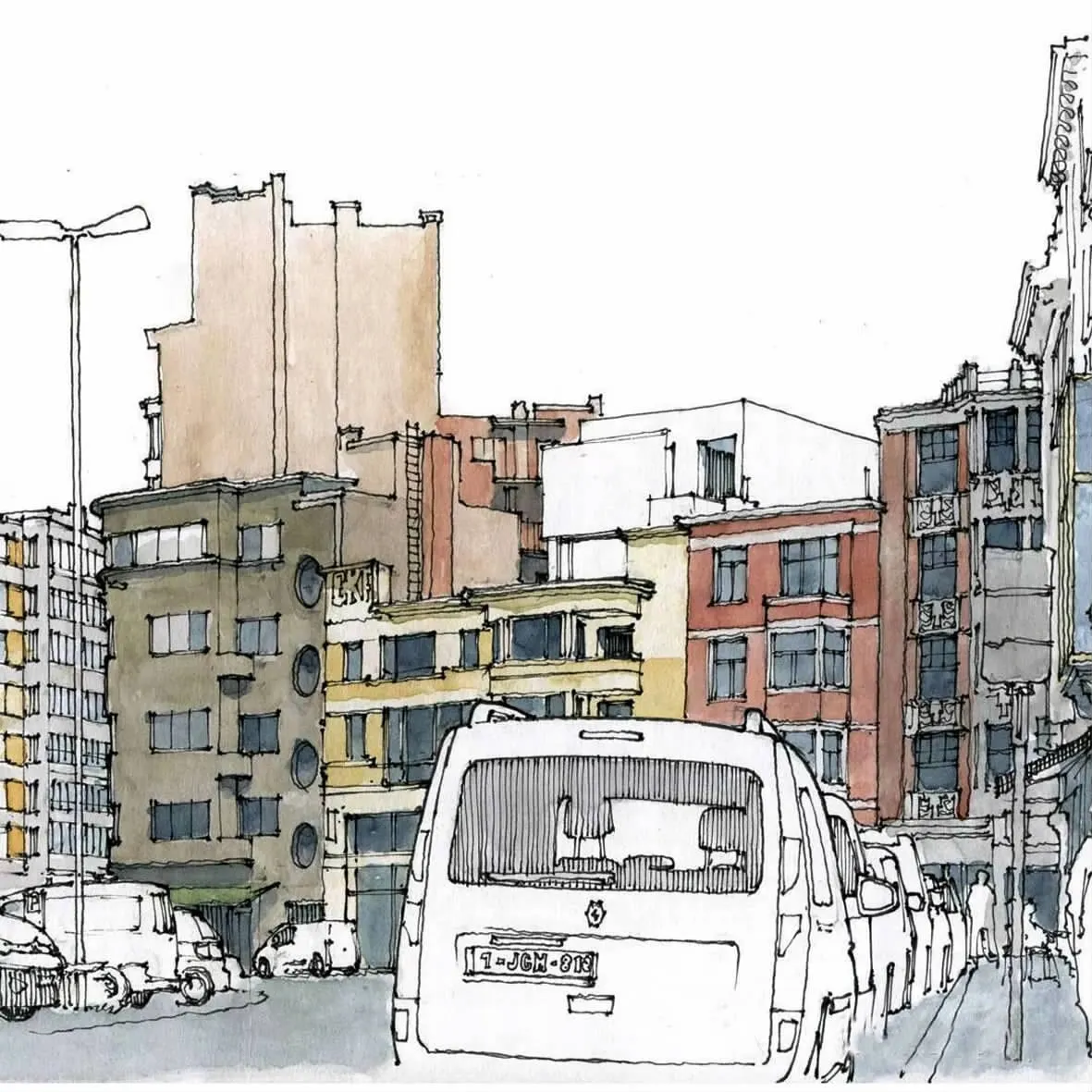
我是在下午六点到的宝丽金酒店。我给马路打电话,他说他在五楼洗澡呢,让我上去,也冲个澡。我没有马上起身,而是陷在大堂的沙发里用眼睛又逡巡了一圈,金碧辉煌的环境让我的双腿微微颤抖,我知道自己在这里有些自惭形秽,何况我坐着班车颠簸了一个下午,我的晕车症相比小时候并没有好多少。我深吸了一口气,瞥了瞥偌大的鱼缸里静止不动的那条大鲵,它也盯着我,却镇定自若,它大概都有些瞧不起我这个乡巴佬。
前台的小姐也看着我,她长着一张娃娃脸,娇小可爱。刚才进来时,我对她说我来找马路,我是马路的表弟。她问我用不用她帮我打个电话,我说我自己打吧。她说,哦,好的,您请坐。她伸出右手指了指不远处的皮沙发。老实说,我没想坐到沙发上,她那么说了我就客随主便,不能让她看透了我的慌张。我再从沙发上起身后,还是走到她跟前,问了问楼梯在哪里,她微笑着说,您可以坐电梯上去,电梯就在旁边。
我在电梯间里还是晕得慌,比坐班车好不了多少。到了五楼,我问了一个服务生,找到了洗浴房的位置。再给马路打电话,他穿着短裤出来迎接我。马路剃了板寸,精气神很好,他的皮肤白皙中透着健硕,右胳膊上不知什么时候文了一条青龙。
来,进来。马路拍着我的肩膀,把我带进洗浴房。洗浴房很豪华,和我们乡下澡堂的局促狭小截然不同。马路先带我在大浴池里泡了会儿,我瞅着他的文身,问他是什么时候弄的,他说刚整的,装逼而已。他问我要不要也弄一个,我说还是算了,我还得为人师表呢。他抿着嘴笑了笑,说,那倒是,你是文化人,要不我咋请你帮忙呢。对了,你书看得怎么样了,我感觉你肯定没问题。
书是没问题,关键是这样做行不行啊?我疑虑地问。
放心吧,不是啥大事。马路肯定地说。
出事你负责啊。我担心地说。
我负责,我负责。马路的语气还是毫不迟疑。
在浴池里泡了一会儿,马路说我们冲冲凉吧。到了花洒下,马路褪掉短裤,露出了裤裆里的家什。他的大家什让我惊诧起来,尤其那两个蛋卵大得骇人,卵皮子黑黢黢又红扑扑。我开玩笑说,你不是处男了吧。马路努努嘴,呵呵地笑了两声。
当天晚上,马路叫了几个相好的哥们儿,在保安宿舍旁的路边摊上吃了一顿烧烤,算是对我的款待。我是第一次吃羊肉烤串,勉强喝了一瓶啤酒。马路的酒量很好,他喝的啤酒怎么说也得有十来瓶。马路吸烟的姿势也很潇洒,他甚至能够吐出漂亮的烟圈。
现在想来,那晚吃饭的保安们我基本都忘了模样,他们的吃相也不怎么好,我在他们面前也倒渐渐有了些底气。我虽然没喝多少酒,但碰碰杯子,说两句场面上的话倒还应付得了。
我唯一记住的是那个长得雄壮的保安队长,我听见马路频频地叫他宝哥。宝哥话语不多,也没有说什么大话,但他自有一股气场,能让人明白,他就是这群人里的老大。
吃过饭,马路带着我走了走城市里的马路,路边灯火通明,站牌下熙熙攘攘的人,等待着来往的公交车,我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
马路说,坐公交车的都是穷光蛋。对马路这样武断的说法,我不大能苟同,甚至有些反感,因为我就是到了公共汽车站再倒路车来找的马路。不过,再细想想,我还真是个穷光蛋。
我问马路,你不坐公交车吗?马路说,坐,现在坐,但总有一天,我得开上自己的小汽车。马路这样说着,眼睛里闪着一团火。我又觉得他有些吹牛,在当时,有几个普通人家能有私家车呢,何况马路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酒店保安。
2
Q市,是一座开放的港口城市,有山,有海,有公园,有广场,有商厦,有酒店,车水马龙,繁华喧闹。这么多年来,我去过Q市几次,见到马路,只有三次。2002年的夏天,也就是他在宝丽金酒店当保安的时候,算是第一次。
第一次去见马路,我在他的怂恿下干了一件很不好的事。现在想想,如果谁再让我去干那样的事,除非打死我。打不死我绝不会去干。当然,打死了我也就干不成了。
当晚,我住在马路的保安宿舍里,他虽然在星级酒店里当保安,但住的宿舍并不比我上师范学校时住的宿舍好多少,也是那种上下铺的木板床。夜晚,蚊子嗡嗡地飞来飞去,好在蚊香把它们熏得摇摇欲坠,但它们还是没皮没脸地聒噪。我和马路拉了一些家常,彼此打听了双方老人的情况。
马路管我母亲叫大姑,我管马路的父亲叫大舅。我母亲是我大舅的亲姐姐。我母亲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也就是我的二舅、老姨,马路管他们叫作二叔、老姑。拉了会儿家常后,我的酒劲儿上来了,迷迷糊糊地睡去。在我睡去之前,我听见马路说,打工没出息,要成功,还得给自己干。
好吧,还是说说马路让我干的坏事吧。他是要我去给他当替考。是这样,初中毕业后,我考上了中等师范学校,马路呢,上了个普普通通的技校。
那时候,中师还包分配,但中专就不管找正式工作了。学校的老师还算有责任心,我们上学的时候,班主任都会教导我们在上学期间考一考社会自学考试的大专。我算是不错的,在中师毕业的时候一并把大学专科学历拿到了。马路上技校的时候也参加了自学考试,他说他过了几科,还有几科没有过。
马路技校毕业后,自己找了个酒店保安的工作,他说他这一段时间看不下去书,他请我替他考两科。我问马路,你当保安,还考那个干嘛?马路说,没什么用,瞎考考吧。
我在考场里差点儿吓得尿裤子。监考的是两个小年轻,一男一女。其中一个男的,文文弱弱的,他负责检查身份证、准考证。他拿起马路的证件反复地看,再反复地端详我的模样。他甚至轻轻地问我,你是马路吗?我咬着后槽牙,肯定地说,是啊,怎么了?
文弱男离开了我,他绕到那个女的身旁,欲言又止。大概那个女的是个主考。我在心里祈祷,佛主保佑,千万别出事。大概是佛祖真的显了灵,文弱男终于没有和那个女的说什么,但他在考场里走来走去,总会在我的身边停下那么几秒。在他停下的时候,包括他离开的时候,整个考试期间,我躬下腰,蜷着身子,努力摆出一副老实巴交的样子。大概我的谦卑感化了他,他到底没有对我痛下杀手。
不用说,我顺利地帮助马路考过了那两科,其中一科是英语。马路其实是和我说了假话,那两科其实是马路一直没有考及格的两科。那两科过了以后,马路的大学专科证书也就到手了。后来,我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我觉得马路不该对我撒谎。不管该不该吧,马路就是对我撒了谎。而且,我想,后来他对我撒的谎不止这一个。
我走出考点,马路在门口等着我,和他在一起的还有一个丰腴好看的女人,我想起来了,我见过她,她是宝丽金酒店洗浴部的女当班。昨天傍晚,在我和马路洗完澡出了浴室后,她和马路说了好一会儿的俏皮话。
马路挥手叫了一辆出租车,我们三个上了车,我坐在前面,马路和那个丰腴女坐在后面,我从反镜里看见他们俩的腿靠在一起,轻轻地蹭动,丰腴女的眼睛里掩藏不住喷薄的骚情。
3
回到家后,已经是傍晚了。我又晕了一道的车,在公共汽车上我强忍着没有让胃里的薯条、鸡块涌上来。中午在肯德基我又丢了丑,马路问我吃什么,我怎么知道,我从前根本就没到过这种地方。我说随便吧,你们吃啥我就吃啥。丰腴女点的餐,她点了薯条、可乐、脆皮炸鸡以及玉米沙拉。吃饭的时候,我镇定下来,看他们怎么吃我就怎么吃,我终究没有再现太大的眼。但我感觉在他们面前,我仿佛是个电灯泡。吃完饭,马路说,再住一晚吧。我说,算了吧,明天我还要上课呢。马路没有再说挽留的话,他说,好吧。然后,他又叫了辆出租车,把我送到了汽车站。我目送马路和丰腴女离开,我想,我这个未来的表嫂姿色委实不错。
晚上,我和父母说了我给马路替考的事。我母亲脸上露出喜色,她应该是觉得我帮助她的娘家人做了事,是值得她骄傲的。我父亲却沉默了一会儿,说,你不应该干这样的事,这是犯错误的。我暗笑他的迂腐,这都什么年代了,他一个土里刨食的农民懂得什么。马路打来电话,问我到家了没有,我说平安到家,不用挂念。我笑着问,你和我表嫂在干什么?马路愣了一下说,什么表嫂,没有的事。
我还是惯常地上班,到小学校去当一个班的孩子王。其实那时候,连孩子王都是虚的,我刚刚上班没两年,一个月开那么可怜的三五百,没有人瞧得起我们这些臭老九。
我那时候写点儿矫揉造作的豆腐块,想赚几块烟钱,可是发表的东西寥寥无几。我的经人介绍的对象在另外的一所小学教书,她干干瘦瘦的,长着一副水蛇腰。我给她写了几封肉麻的情书,展示一下才情。我说我的梦想是当一个作家,她不以为然地说她想当个商人。
从很早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三观不合。慢慢地,我听到一些风言风语,意思是说我对象的小学校的男校长是个老流氓,他手下的女老师基本上都难逃魔掌。
这一段时间很烦,一天要上六节课,累得要命。另外,学校领导欺负新人,把一些临时性的脏活累活总是派给我干。更重要的是那些流言蜚语让我寝食难安。马路打来几次电话,我以为他有什么事,就在电话里问,什么事啊?马路说,没事,你上课呢吗?我说,哦,我上课呢。或者说,我马上就要上课了啊。就挂了电话。其实除了心烦外,我还心疼电话费,那时候一分钟要三毛多钱呢,没事打什么电话啊。有病。
其实,当时我也能够隐约明白,假若马路给我打电话没什么紧要事的话,那么他可能是想和我联络联络。
我们的老家原本在另外一个市下面的一个穷县里的一个穷乡。我大舅、二舅在一个村,我母亲和我老姨嫁到了几里之外的同一个村。
小时候,在亲戚家的一大群屁孩儿当中,我和马路最要好。我们俩都不是什么好鸟,惹过不少的祸。他割过蟾蜍头部的疙瘩,差点被白色的液体滋瞎眼睛。我扒过小蛇的肉皮,恶心得一天吃不下饭。暴雨过后,我们合力把水井旁的大石头翻进井里,并成功地嫁祸给别的孩子,惹得那个倒霉蛋挨了一顿打。至于上树偷果、鸡窝里偷蛋之类的事情就更是不胜枚举。
我和马路也偶尔打一架,某次我们在白滑滑的沙滩上摔起了跤,我掐着他的脖子把他按在身下,他揪着我的头发不撒手。我们保持这么一个姿势至少半个小时,直到我母亲喊我们回家吃饭。起身时,我们瞅了瞅对方乱蓬蓬的脸,又扑哧一下都乐了。
至于我们离开那个穷乡,是因为1994年的一项省级的水利工程。简言之,我们的老家现在已经成了水之底。我家和我老姨家是第一批离开的,我们迁到了Q市L县C镇,我大舅、二舅家的村子是第二批,他们要抽勾决定去哪里,在十个勾里有八个也是Q市L县的,马路摩拳擦掌地,却抽到了Q市Y县X乡的勾,我大舅、二舅两家人嚎哭了好半天。马路突然就成为了罪人。
这样我们这些亲戚就被分到了两地,相距足有四百多里,那时候,四百多里俨然有两万五千里那么远。从那时起,我们基本上就失去了联系。只是大人之间偶尔借用别家的电话座机互相通个音信。
我终于与那个水蛇腰的对象了结了关系。某个傍晚,我骑着自行车去接她来我家吃饭,我在她的办公室找不到她,打她的手机也无法接通,最后她从那个小学校的体育器材室里出来,她的脸蛋红扑扑的。体育器材室里还有一个人,就是那个传说中的老流氓校长。我推开门,看见那个老流氓正襟危坐地玩着电脑,体育器材室的地面上放着一张软乎乎的海绵毯子。体育器材室的窗帘还紧紧地拉着。
我甩给水蛇腰一记响亮的耳光。
4
第二次见到马路,是在他的婚礼上。那大概是在2006年。马路的新娘并不是那个丰腴女,相反,是个娇小柔弱的女孩。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她应该就是那个站在宝丽金酒店前台的小姐。
婚礼很隆重,一记丘比特之箭从司礼台穿过玻璃走廊,直中十几米外的两颗红心,引来宾客们的一片欢呼。我坐在餐桌旁,高举双手鼓了鼓掌。我为马路祝福,但我压抑不住这几年对马路的不满。
这么说吧,马路的婚礼我原本不想参加,是我母亲生生地拉着我来的,我懂得她朴实的心。我之所以不想参加马路的婚礼,是因为我的婚礼马路并没有参加。
我和水蛇腰分手后,又经人介绍结识了我现在的老婆。为防夜长梦多,我在和我老婆相识三个月后就结了婚。我们的婚礼在农村庭院里举行,没有什么大场面,但我们依然觉得甜蜜幸福。我们大体上相敬如宾,过着平静的生活。我老婆很快就给我生了儿子,在我儿子的满月礼上,马路依然没有到。
后来,我母亲举行六十岁的寿宴,还是没有见到马路。当然,我的舅舅们还是坐着公共汽车从四百里之外赶来。
我大舅说我表哥很忙,腾不出空来。我大舅妈则是唉声叹气。我二舅一家冷着脸,一言不发。在这期间,从老人们的话语里我大概知道了马路这几年的生活轨迹。我大舅泄露了马路的一个秘密,他说多亏了马路考了个专科学历,连英语都考过了,才应聘到Q市的一家大超市做了采购员。我大舅说这小子脑瓜子还真算好使。
我这才知道,马路要我为他替考,并不是瞎考着玩。这家伙原来是早有蓄谋。这样说来,是我帮马路考取了学历,谋到了新工作,而他却在我办事的时候不到位,就更加可气。
还有,马路在这期间,偶尔给我打来电话,竟然不是为了联络感情,而是跟我借钱。一次是说想在市里买套房子,一次是说想自己单干做点儿买卖。我没能借给他一分,一是因为他的行为令我本不想借,二是因为我根本就没有一分钱的闲钱。
我在酒店的角落里看见了宝丽金酒店的那个保安队长宝哥,他穿着一身得体的休闲装,静静地坐在那里,眼神淡定。那次一起撸串喝酒的那些保安,只来了一个宝哥。
我们从饭店吃完饭,回到了马路的家里待了三两个小时。马路到底还是在市里买了个八十多平米的楼房。除去公摊,显得很是逼仄。马路把我大舅家所有的积蓄都拿了来,但一定是杯水车薪。这样我又暗暗地佩服起马路来,不管怎样,不管他怎么办到的,他到底是做了城里人。
我逗了逗娇小可人的表嫂,她有礼貌地盈盈一笑。我和马路到另一间卧室待了一会儿。
我抽出一支烟,递给马路,马路摆摆手说,早不抽了。
我问,怎么呢?
马路说,你嫂子不让我抽。我笑了笑,问他,喂,那个丰腴女呢?你给人家白睡了?
马路赶忙止住我,用眼神往外面扫了扫,又站起身,把屋门关上。
马路说,什么丰腴女啊,千万别瞎说。她和宝哥在一起呢。
我说,你可真行,就这么糟蹋宝哥啊。
马路说,什么啊,他俩挺好的。
我问马路,你还在超市里吗,采购员这样的肥差,油水不少啊。
马路叹了口气,说,难啊。马路又若有所思地说,苏艳是个好姑娘。
我问,苏艳是谁?
马路笑了起来,就是你说的那个丰满的女人。
5
回来的路上,我就想,马路为什么说那个丰腴女是个好姑娘呢?我在脑海里虚构了一些情节。也许马路说的是和苏艳睡觉的感觉,随之我否定了自己。也许是那么回事,但绝不单单是。
马路有了学历,大型超市录用了他,但怎么就把采购员的差事给了他呢?或许是超市的某个肥头大耳的领导去了宝丽金酒店,而那个领导在某些机缘下又“耕耘”了苏艳也说不定。算了,这只是我的想象而已。但这样的想象力倒有助于我成为一个蹩脚的小说家。
我是在家人的言谈中,大抵了解到马路的老婆是怎么回事。原来,马路的老婆牛晓丽早就看上了马路。马路去超市后,牛晓丽也从宝丽金酒店辞了职,跟到了超市。牛晓丽的老爹是个破落了的社会混子,但在市里还有些排面。这样看来,马路选择牛晓丽也情有可原,他一个外来户,要在市里落下根儿,总需要些虚张声势。但我隐约觉得他们俩不大合适,因为一个姓牛,一个姓马,风马牛不相及嘛。
后来,牛晓丽的做派到底是出人意料,也或者说是在某种意料之中。牛晓丽从不去我大舅他们那个小农村。对了,她只去过一次,就显现出不可掩饰的嫌弃。牛晓丽是个独生的女儿,她喜欢在年节的时候,让马路去她的娘家。她生了孩子之后,只允许她的亲娘看护,我大舅妈去市里看了几天孩子,就被遣返回去。
说说我自己的烦心事吧。
几年之间,被我打了一记耳光的水蛇腰不知道用了什么妖法,竟然也混上了小学校的中层领导。我的一个写小说的朋友慨叹着说,一个“遍地精卵”的年代,发生什么事情都不新鲜。我以为他说的是“痉挛”,他特地强调说是“精卵”。
我对他的话不置可否,但作为一个体制内的人我还是有些觉悟,我总不会说那样的话。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时代,能给所有想奋斗的人提供舞台。如我表哥马路那样的外来客,都好歹在不小的城市里站住了脚跟。我不希求那些虚名,不想追求什么所谓的富贵与权势,我只想照顾好我的家人,维系好我的亲情。
真的,这不是我的矫情话。但我老婆却不这样想,她说有几次遇见那个水蛇腰,水蛇腰分明在趾高气昂地向她挑衅。
对于我这个当小老师的老婆的怂恿,我没了办法,我拗不过她。拗不过她,就只好去想别的办法。我拿着写稿积攒的钱去托门路,找关系,慢慢地也在小学校里干上了小领导。当我对我从前的同事发号施令的时候,我都有些瞧不起我自己。而且,也不大有人好好听我的话,他们都知道我不过是个异乡人。
马路偶尔打来电话,我能感觉出我们彼此没有什么话说,慢慢地,电话也就没有了。
6
后来马路混得不错,他最终从超市离开,自己单干。这是我预料之中的事。马路干采购员的时候,没少从里面捞回扣,终于事发,被扫地出门。其实即便不发生这样的事,马路早晚也要主动离职,他本来就讨厌给别人打工。
在超市干了三两年,他却摸到了门道,明白了超市运作的套路以及里面的利润情况。马路夹起了小皮包,到下面县城的有规模的超市谈生意,入驻摊位。他主要是做小食品和儿童玩具。起先,他自己买了辆面包车亲自送货,两三年后就买了辆霸道,开始拓展别的生意,送货的事就交给了一个过往的哥们儿。
我大舅说起马路眉飞色舞,骄傲之情溢于言表。我大舅妈却仍是唉声叹气,因为她很难见到他的儿子,还有孙子。我二舅家的表弟结婚的时候,马路没有到场,我大舅说他去了上海。我老姨家的闺女结婚的时候,马路也没有来,我大舅说他去了泰国。我们这些亲戚对于马路的缺席有时候嗤之以鼻,但终于习以为常。
我母亲很是能为他开脱,我母亲在公开的场合说,马路忙,大家都理解,不能责怪。私底下,我有时候和母亲顶撞,我说,他再忙,也不可能每次都忙吧。我母亲说,他以前混得不好,不好意思回来。我追问,那后来呢?我母亲说,后来是因为以前的时候没来,再来的话前面的会挑礼。
我摊开手,只能哑口无言。我不明白我母亲何以袒护她的娘家人到这种程度。我父亲倒是会吵我母亲两句,该干啥干点儿啥去,没事儿闲的!我父亲是个传统的老农民,他到底看不惯一些事。
再后来,我老姨父也做了点儿买卖,他向我开口借钱,我给他拿了一万。我跟我老姨父说,你和马路借点儿啊。我老姨父说,马路都是贷款,手里没啥钱。我笑了,怎么可能。
按照我大舅的说法,马路的摊子越铺越大,做起了高档服装的生意,据说又和市政府合作,做了两家大型3D体验类项目。马路还在Q市的风景区购了一套别墅,装修完毕已经入住。不管怎么说,要说马路没有钱,死活我都不信。我信不信没有关系,但我大舅、大舅妈仍然没有福气入住别墅倒是真的。
这几年,我带着老婆孩子去过Q市游玩,我也买了辆几万块的私家车。去Q市,我没有再联系过马路,我不想听到他说他又去了哪个大城市,或者又去了什么国外。
闲暇时间,我还是写点粗俗的文字,偶尔和我那个写小说的朋友在小县城见见面,喝点儿小酒,聊聊天。他说起话来,还是疯言疯语,满是对这个世界的不满与嘲讽。我说,哥们儿你别这样,你这样的话连小说都不好发表。他抿了一口酒,指着我哈哈地笑,他的嘴里叨咕着说,你啊,你啊。
7
是的,我能够听出我的写小说的哥们儿对我的一丝鄙薄。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也变得世故起来。这委实是可悲的。
某个夏天的某个夜晚,我在八点钟驱车进了县城,我像一条狗一样守在局长家楼下的停车场。夜还没有黑透,在楼下过往的人让我胆战心惊,我以为他们都窥透了我的肮脏的小伎俩。我把车座放倒,想把自己藏起来。
天终于黑了,我的心稍稍安定,我睁大眼睛盯着六楼局长家的屋子,他家的后窗台上放着一盆不知名的绿植。灯没有亮,我知道局长还没有回家。大概是八点半的时候,局长终于回了家,我看见他穿着雪白的衬衣走进了单元门口。再等了两分钟,六楼的灯终于亮了。我拿着鼓囊囊的档案袋,下了车,向局长家走去。
我的心里直打鼓,没有一点底气。灵通人士告诉我,办大事,只能找主要领导。在白天的时候,我进了局长的办公室,自报家门,说了自己更进一步的想法,局长很和蔼,他说年轻人要求进步是好事,他会考虑我的想法。为了避嫌,我没有把档案袋拿进他的办公室。
那么,我想今天晚上他应该不会拒绝我的虔诚。
我终于站在他家的门外,我提了提裤子,伸出右手按响了门铃。门没有开,我向门旁边移动了两步,躲开猫眼,又按了按门铃。门终于打开。局长认出了我,他叫出了我的名字。我说,局长您好,我来拜访一下您。说着的时候,我看见他用眼角瞟了一下我的档案袋。
这时候,我的手机铃响了。铃声很大。就在那么一刻,局长显出了不耐烦。他摆摆手,说,你回去吧。随后,他就关闭了房门。
电话是我母亲打来的,我恼怒地挂断了电话。我又按响了门铃。我连续按了几次,都没有再能够等到开门。我只好懊丧地退了下来,我想只能择日再找机会。
进了车里,我给局长发了个短信:对不起,打扰您了。然后,我回拨了电话,我生气地问我母亲,你早不打晚不打,这个时候打电话干嘛?!我母亲愣了一小会儿,她虚虚地说,你表哥出事了。
天空中突然传来了隆隆的雷声,豆大的雨滴顷刻从天而降。我启动了车子,驶出了小区。在调头的时候,车轮蹭倒了小区里的垃圾箱。我像一个被追赶的贼一样,狼狈地逃回我的小农村。一路上,雨越下越大,雨刷开到了最大挡,也刮不开肆虐的雨水。我看不清前面的路,索性把车子停在路边,道旁的杨树在狂风中发出怪叫,我在车子里泪眼滂沱。
我老婆也打来了电话,她问我事办成了没有,我只是吼了她一句,滚!
8
马路的胸口被插进了一把瑞士军刀。我终于第三次在Q市见到了冰冷的马路。他安静的脸庞中显出疲惫,倒是没有看出死亡前的一丝丝应有的惊恐。我大舅妈哭得昏死过去,我大舅铁青着脸,说马路瞎了眼,用错了人。
我的眼睛湿润了,终于大哭起来。这么多年,我一直觉得马路与我们渐行渐远,这一次他到底是要真的消失了。我在马路的遗物中,发现了一个笔记本,在笔记本的扉页上,我看到了一首无题诗:
一条曲曲折折的羊肠小道
在沟沟壑壑的山麓上穿行
我不是谁的行路
我是我的坦途
我大体猜到了凶手是谁。我见过他,我也见过他的眼睛。在他的淡定的眼神中,我曾经看到了另一团跳动的火焰。凶手很快就找到了,他栽倒在了Q市的护城河里。他自己的胸口也插上了一把瑞士军刀。这是一桩说不明白的凶案。动机、过程一概不得而知。后来,主管马路3D合作项目的市政府的某个官员忽然就落了马。我甚至想,马路的死亡也许并不是简单的凶案,说不定生者或死者之间竟有同谋。我知道我的臆想症又犯了。谁让我是个狗屁小说家呢。
我又去了一趟小县城,找到了我的那个写小说的哥们儿。
我对他说,我表哥消失了。
我说,也许是我丢失了他。
我说,我现在真想给他打个电话。
我的写小说的哥们儿干了一杯酒,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又翘了翘嘴角,郑重地说,是你太多情善感了。在现如今,普通人家到了表亲这一辈儿,还有几份有走动的呢?所有的走动都需要铜臭作为资本。我们不缺情感,恰少铜臭。这么说吧,不光是你,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人都有一个消失的表哥。你要说是丢失,也完全正确。当然,有些走动,没有铜臭亦可,譬如你有权柄或美色。
我愣了一下,举起手中的酒杯,一饮而尽。我的眼泪滴在了热气腾腾的水煮鱼里。那条死鱼的眼睛已经糜烂,但它还是恶狠狠地看着我。我瞅向窗外,不远处的广场上,载歌载舞,人群如织,灯火辉煌之下,满是一派祥瑞之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