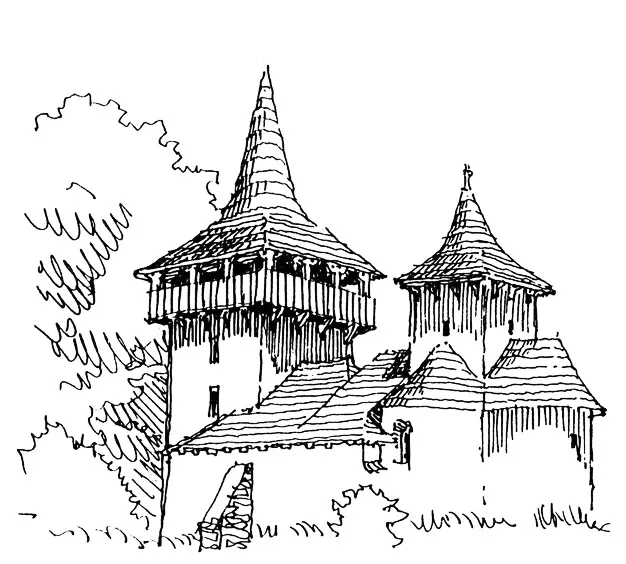
1
土地刚承包到家庭的头两年,农民对粮食有一种膨胀的贪欲,特别是对麦子,贪欲就像在心底挖了一个大坑,这个坑没有底。无论年老的农民还是年轻的农民,都是一样的心态,土地到了自己手里,就是要看自己的能量和土地的能量,到底能打多少,他们实在不满于集体合作化时代的土地产量。高省力全家分了十二亩地,七口人,父母、妻女,还有两个妹妹。两个妹妹都没成年,一个在县城读高中,一个在镇上读初中。高省力娶了媳妇后没有与父母分家,父母年纪大子,土地承包到家,庄稼地里干不了重活了,再说两个妹妹还没有成人,他理所当然地要担起这个家来。土地承包后的第二年,农民尝到了土地承包后第一年的甜头,对粮食的贪欲完全调动起来了,这时的农民处于单纯的粮食阶段,心里一味地是粮食,人民公社实在是缺粮缺怕了。他们对粮食的渴求变成贪欲,一种报复性贪欲,他们把食放在第一位,可惜农民到底不能靠种地翻身,待他们对钱的需求决定生存发展的时候,农民的本质改变了。
高省力第一年尝到了麦子的甜头,土地承包到家的第一年麦子大获丰收,这不但不能让他满足,反而起了更大的贪心。他觉得第一年麦子没种足,管理上也没有使足劲,这让他非常懊悔,所以这一年狠狠地种了八亩麦子,一半以上的土地都拿来种了麦子,如果丰收了,三年吃不完。第一年的小麦丰收,就让高省力和高省力的爹娘慌得不知所措,他们根本想不到土地会有这么大的能量,会有这么大的潜力。高省力的爹,这个老农民,自小就记得麦子的产量,亩产一二百斤,有的年头只有几十斤,听老辈讲,爷爷的爷爷那个年代,小麦产量更底,亩产仅有一斗,一斗是三十斤,麦子只能当细粮吃,不能当口粮吃,口粮是地瓜。农民一辈辈都是吃地瓜长大的,对白面馒头遥不可及。他们对麦子有一种报复性渴求。从来都是人舔乎麦子,没想到麦子也会舔乎人,舔乎人就是给人产量让人给它更大的面积。种地就是人和土地一条心,种麦子就是人和麦子一条心。高省力有了麦子的甜头,过去的老皇历翻不得了,土地和麦子的老皇历也翻不得了,麦子有了一个历史性翻身,麦子和农民同时遇上了农业的好时代。
高省力的爹自麦种播下就开始围着麦子转,他就是要看看儿子种出什么样的麦子来。麦子喜欢深耕细作,麦子根扎黄泉,麦子喜欢吃庄户人的土杂肥,也喜欢吃美国的二铵。麦子还喜欢水渴望水,麦子一冬在坡里憋着劲,一冬没有闲着,它在积蓄力量,经历风雪与经历春风春雨一样重要。它是见风就长的作物,一场春风麦田就绿了,再一场春风田野就起了绿浪,绿浪无边无际。雨,还有雨,麦子呼唤雨,雨和美国的二铵一样有劲,一场雨洒下来,麦苗恣意在地上打滚,那个绿,黑油油的绿。如果老天不给雨,农民也不会放弃,花钱浇,雇机器抽水,渠水在田头奔跑,流满渠,洋溢的渠,一股水顶着一股水,冲着草屑和水沫,高省力拿着铁锨跟着渠头跑。转眼麦子就没膝深了,转眼吐穗了,农民看到粮食了。天气越来越热了,河边与村庄转眼成了绿成林了,人们开始打收麦的谱了。家家开始抹水泥缸,去年抹了一茬,没有足够的打算,今年要加倍添水泥缸。高省力看自家麦子的势头,少不了再添十口水泥缸。抹水泥缸先在地上做一个缸的模型,这个模型是用鲜土筑成的,用铁锨一边筑一边拍打,拍打结实,然后用铁锨不断地修理整形,沿是沿,肚是肚,棱是棱,然后在这个模型上抹水泥,抹的就是一只缸。待水泥干定了,先在缸下挖洞,掏出里面的土,缸里的土掏得差不多了,缸就轻了,翻过来晾晒,一口口水泥缸张着大口歪在地上。这些水泥缸一般都抹在村头的闲地或河边的空地,这些缸从地上翻过来并不急着往家搬,而是就地晾着,躺着的,歪着的,一个人搬不动,搬的时候只能在地上滚,让缸半立起,缸底的一个边棱着地,一个大男人扶着缸在地上滚。
2
麦熟两晌,蚕老一时。要说麦子的耐力可够折磨人的,它在坡里一秋一冬,这就够长的了,哪有这么长周期的庄稼,它好像和土地和冬天一同休眠了,有人似乎忘掉了它的存在,一到春天它就开始翻身,但还不是很抢眼,它的引起人的重视和心慌其实只在几十天的时间,甚至三两天的时间。正月麦子不见动静,二三月开始返青,没大动静,万物都怕倒春寒,你来我就退,你走我就进,四月半还只是小动作,下半月拔节扬穗,让人刮目,一个月的灌浆结籽让人觉得漫长,南风一吹,三两天忽然黄了。人们看到麦子,发现了季节的紧迫感,快得就像拉大幕,忽闪一下田野变了颜色。仿佛就是在瞬间,南风到了地头了,麦子熟到脚边了,布谷鸟不舍昼夜,从田野叫到村头,从村头叫到田野,从早晨开门叫到黄昏关门,半夜醒来到院子里撒尿,它还在村头上叫。布谷鸟是跟着南风来的,南风一来就是急的,布谷鸟一来也是急的,嗓子渴得就像那个神话中的夸父。南风急布谷鸟急,布谷鸟急南风更急,这就是麦口,麦口就像一个大火炉一样烤人。所有的农人都惊慌失措,粮食到了嘴边,到了嘴边的粮食让人提心吊胆,天急地急,风急鸟急人急,没有哪一样庄稼能这么惊天动地草木皆兵。因为麦子太隆重了,民以食为天,什么样的粮食都可以活命,可麦子不同,麦子不但饱人,还可以让人吃好,大饼大馍地吃,放开肚子吃,既吃饱又吃好,非麦子莫属。所以麦子的来临就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不来则已,来则惊天动地,来就来得有声有势,南风就是大阵势,从天边铺开的大阵势,以大麦田为幅度,以掀动天地的气势,让人措手不及让人惊慌失措。
太阳像个火红的炉灶,大地被烘透了,烘熟了,南风端着簸箕来,一簸箕一簸箕往麦田里泼,一簸箕一簸箕往麦田里倒,田野是麦香,地头是麦香,村庄是麦香,农人的衣袖里脖子里嗓子里鞋子里全是麦子的气息。村边空地上的那些敞着口的水泥缸,河边空地的那些歪倒的水泥缸,还有路边沟底的那些横七竖八的水泥缸,开始被人往家搬了。快节奏开始放慢了,在季节的节骨眼上忽然停住,全民蓄势待发,全民如临大敌,村庄出现了空前的紧张与宁静。
3
高省力五更起来磨镰。磨石在院子水缸根,一半埋在地下,一半露在地上。家里所有的镰刀都从檐下收集起来,一并抱到磨石边,有十来把,都生了锈落了灰。高省力拉开门头灯,门头灯可以照亮整个院子,高省力舀了半盆子水,他用手把盆子里的水撩到磨石上,一手握着镰柄,一手按着镰刀,在磨石上噌噌地磨,磨好了,手指在镰刃上轻轻地拭,锋利不锋利全凭手指的感觉。镰刀挂在檐下经过了一冬一春,锈迹斑斑,经过这一磨,便露出了一指宽的白刃,白刃在灯光下像镜子一闪一闪。他用抹布把镰刀上的水渍擦净,放在一边,一把接一把磨。一堆镰磨完,哗啦啦收拢起来,抱到手推车上,手推车是天明推着下地的。他为什么要磨这么些刀呢,有他用的,有妻子郑香用的,还有爹用的。爹虽然老了,割麦子还是个好手,郑香也不弱,娘虽然不能割,可总是个帮手。这一抱镰刀大有好处,用钝了一把就换另一把,割起麦子来就没时间磨镰了。
爹娘也起床了,在锅屋里烙油饼,一个烧火,一个掌锅。庄户人最拿手的美食莫过于葱花油饼。这油饼城里人叫什么千层饼,到底没有庄户人的油饼地道。油饼面忌软,却又不能太硬,油和葱花最关键,一定要足。庄户人烙油饼用的是八印大锅,烙油饼要不断地翻锅并抱起油饼在锅里不断地拍摔,这样烙出来的油饼才起层掉渣松脆。烙油饼能香遍一条街。捎到田头,田头也闻着香。高省力的爹娘要烙四张油饼,准备两顿饭,早晨一顿,中午一顿。另外小锅里熬粥,还要炒上香椿鸡蛋。粥是大米粥,农忙干累活都要准备最好的饭,最好的饭有讲究,一是可口,二是填饥,油饼大米粥香椿鸡蛋就是既可口又填饥的饭。高省力的爹娘与高省力起得一样早,郑香是个特例,她还没有起床,其实早醒了,在床上奶孩子。孩子是个丫头,一岁半,叫娜娜,“娜娜”是这一时期城乡文化相接最流行最新潮的乳名,十个女孩八个叫娜娜。头胎生丫头没有什么不好,按政策还可以生二胎,二胎说不定生个小子。再忙也要把孩子照顾好,孩子只有吃饱喝足才不会淘气,大人才能安生干活。
爹娘拾掇饭,吃饭,两张油饼切花端到桌上。大米粥一人一碗端上来。一大盘香椿炒鸡蛋香喷喷的。高省力吃得狼吞虎咽。粥盛在大花瓷碗里,还很热,但碗沿一圈凉得快,高省力抱起碗在嘴上吱溜一下转了一圈,喝了一大口。他吃饭快,吃完嘴一抹,到天井里收拾车子。他把一个大篮抱到车子上,用绳子绑牢了,大篮是放孩子的,还有孩子铺的小包被之类,虽然是夏天,孩子如果在地头睡了,下面还是要铺东西的。还有一包绳子,也扔进了大篮里。早起磨的那一抱镰刀早已放到车子上了。一家人下田,娘提着一把暖壶,挎着一只篮子,篮子里放了一把茶壶和四个茶碗,割麦天热,不能缺水。预备工作一样都不能少,一切行动都要服务于大局,麦收就是大局。一出门,大街小巷全是呼儿唤女下地割麦的人,差不多都赶在一个点上了,太阳刚刚冒红,眨眼从麦岗上跳出来,像个大火球。不用说,今天又是个大热天。割麦子都是这样的天,像下火。这一场麦收,让人摩拳擦掌,让人又喜又怵。粮食到了嘴边,哪能儿戏。一场麦收下来,无人不累得像大病一场。
4
高省力到了自己的地头,把车子放下,把一抱镰刀从车上抱下来,撂在地头上。这一家人,被自家的麦子陶醉了。
麦田像戏台一样平整一样厚。风擀着麦田,麦子涌到脚下,厚厚的麦垅,齐头齐脑的麦穗,有没有粮食看麦穗在风中的姿势就知道了。那股新麦的气味扑面而来,灌满衣袖。高省力噌噌噌在麦地里割出一条胡同,割出一块空地让妻子放孩子。郑香把娜娜的小包被铺在地上,放下娜娜,又把娜娜头上戴小花布斗笠摘下来,小花布斗笠只是路上遮阳,路上美观,到田里就不戴了,郑香在女儿头顶架起一把花伞,给女儿遮阴。就在妻子给孩子撑伞的这个工夫,高省力的五垅麦子已经蹿出老远了。农地里的活,最苦最累不是挑担推车,是割麦子,割麦子不是弯腰向前,而是蹲着,一手揽麦,一手用镰从前往后掏,镰要快,刷地一镰掏进怀里的麦子就是一抱。高省力个头虽然算不上高大,却是个虎背熊腰的汉子,这样的体格更适合庄稼地,也最搁摔打。他的两臂粗壮而长,揽得多,掏得多,一揽就是一抱,一掏也是一抱。一流割麦手蹲着跑,割麦子的速度如蹲着跑一样,二流割麦手蹲着走,蹲着却可以像走一样快,三流割麦手蹲着挪,速度相当于蹲着挪步。但这都是真正会割麦子的人,不入流的站在地里弯着腰割麦,割一把,放一把,工夫全耽误了。高省力就是一流的割麦手,正如蹲着跑一样,自己割自己捆,一个人挨五垅,掏一镰放在腿上,再掏一镰还放在腿上,掏到第三镰或第五镰腿上就放不下了,这时随手抻出一把麦子,头对头打一个结接起来,用来捆麦子,快得只在一瞬间,一个麦个子就捆好了,随手撂下,继续往前割。高省力的爹虽然五十多岁的人了,割麦子还是把好手,只是体力差了,蹲长了吃不消。郑香割麦子也很快,割麦子既是个体力活也是个技术活,妇女割麦子也有快手,快手不比男子差。
麦子不断地放倒,孩子便不断地跟着挪,从地头挪到了地中间。孩子如果睡着,就睡在花伞的阴凉下,如果醒着,坐在花伞的阴凉下玩。郑香顾不得孩子,她忙着割麦子,婆婆一边干活一边照看孩子,除了归拢麦个子还要拾麦穗,一只蜘蛛,一只蛤蟆,甚至一条奔跑的蜥蜴,都在她的监督中。一块地割完了又挪到了另一块地,高省力家的麦田是连成片的。
婆婆给壶里沏上茶,把茶水冲到茶碗里,喊儿子、儿媳、老伴来喝茶。割麦子离不了茶。休息喝茶两不误。三个人围过来喝茶,公公茶碗还没端,先摁上了一袋烟,吧嗒吧嗒地抽,嘴角溢出烟圈来。高省力拉过身边一个麦个子坐在屁股下面,抽出一支烟,趴在爹的烟袋锅上吸着了,从两个鼻孔里冒出两股烟,烟真是男人的好东西。有工夫抽烟没工夫喝茶,抽烟急不得,喝茶是三口两口的事,冷了再喝也不迟。割麦子不但是个累活,也是个脏活,高省力的嘴唇、鼻孔、眉毛全是灰,麦杆麦叶麦穗里存满了灰土,割麦子往怀里揽,哪能不沾灰。但那口牙是白的,笑起来更白。高省力很兴奋,他对今年的麦子实在满意,镰刀往怀里一掏,碰在肩头的麦穗沉甸甸的全是粮食。郑香摘下头上的花头帕解开怀给女儿喂奶,她的两个奶子鼓胀得又大又满,奶水把胸前的衣服洇湿了一大片。娜娜刚睡醒,小脸蛋粉嘟嘟的,两只眼睛像葡萄一样黑一样亮,小胳膊小腿胖得一股一股的。郑香是个丰满的女人,生了孩子之后更丰满了。她把孩子揽在怀里,放在膝上,把奶疙瘩塞进孩子的嘴里,孩子的两腮立刻一鼓一鼓地吸起奶来。一家人在一起,儿媳解怀喂孩子不避公公。婆婆把暖水瓶的塞子拔下来放在麦个子上,茶壶的盖也拿下来放在麦个子上,让茶水凉得快些。离天晌差不多还有两个小时,早饭吃得早,午饭也要提前吃,婆婆把茶壶倒满,暖瓶空了。她要回家做午饭,饭是现成的,早晨烙下的油饼重新加热,再熬大米粥炒鸡蛋,这是农忙时最切实的饭。另外还要熬一罐绿豆汤,后勤工作也不轻松。儿子、老伴和儿媳忙得一刹也离不开麦地。
5
高省力全家的麦子割了三天。割完要往麦场上搬。
麦场在村头。村东有一条很宽的机耕路,机耕路两边全是麦场,在分地的时候特意留出一片地每家四分划作麦场。这四分地平常不耽误种,有的种大麦或豌豆,大麦豌豆比小麦早熟十来天,可以提前轧场。也有种小麦的,拔了小麦轧场也来得及。轧场也是个急活,麦收所有的活都赶在一起了。轧场先要把地整平,用筢子一遍一遍地搂,搂平了,然后挑水泼场,家家泼场,忙得人仰马翻,担钩水桶碰得哗啦啦地响,水渗透后,地面晾硬,上面再撒一层细沙,这样轧场不沾碌碡。碌碡上套一个弓子,弓子两头有榫,镶进碌碡两头的石卯里,绳系在弓子上,人拉着碌碡轧场,吱吱嘎嘎地响,家家轧场,碌碡响成一片。这是个体力活,一个人背着绳子拉,来来回回拉,转着圈拉,连场边都不能放过,即使场边的墒沟,也被轧得像场面一样光滑结实,墒沟虽然是一个凹面,却也是个光滑的凹面,这样迸到墒沟里的麦子也能扫起来。轧好的场平整光滑,不起土不裂缝,场一轧好,立刻就成了孩子们的乐园,孩子们跑场上追逐打闹,在场上用扫帚扑蜻蜓。农忙时节,妇女都下田,大小孩子都交给婆婆,婆婆便把这些孩子带到场上,既守着孙子,又守着田里干活的儿子儿媳,把孩子放在场上也省心,磕不着碰不着。儿媳们收工先到场上找孩子,蹲下身解开怀就给孩子喂奶,麦场像家一样亲。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场就是为麦子准备的,家家开始往场上搬麦子。麦子在地里割倒随手就打成捆,俗称麦个子,麦个子不大不小,七八岁的娃娃也能往车上抱,大人一手提一个,或一手提俩,搬起来非常方便。路好就雇拖拉机拉,路不好就用手推车推,连手推车都进不去的地块就用扁担盘到路口。车装得又肥又大,棒劳力用大车推,半劳力用小车推,老老少少往返搬麦子。各家各户的场挨在一起,场边的这条机耕大道上车拥车动麦垛在动,拖拉机装得比麦垛还高。推车的也都一个比一个贪,车子垛得几乎望不到前面的路。场与场之间只隔一条浅浅的墒沟,这条墒沟也在回碡时轧得像场面一样光滑了,所有的麦子集到场里,挤成片连成片,麦个子都站着排放,密密匝匝,这样既能接受日晒又节省空间。那么多麦子,场面当然放不下,便排放到场外的大路上,再放不下的便放在场边的空地里。大多数人家还在往场上搬麦子,有的人家开始打场了。打场都急,都想先挨到机器,有的人硬争硬抢,劳力强的人家占上风。搬机器抬机器需要棒劳力,土地承包到家也暴露了一个问题,没有劳力也就是没有儿子的家庭处处被动,生男生女就是不一样,人强马壮才是土地上的强者。
高省力很快联系到了机器。高省力虽然是家里唯一的男子,可堂兄堂弟一大群,关键时刻一齐上阵,自家搭伙最放心。割麦子可以一家一户自己干,打场必须好几家子合伙,机器一开,分秒必争,就怕人手不够,老少上阵,能上机器的上机器,能挑穰子的挑穰子,能拿筢子的拿筢子,能抱麦子的抱麦子,打麦场上人手多多益善。打麦机面场安放,让打下的麦子都落在场上,打场前麦子都要从场上拾掇到场边,垛成一个火车箱式的长垛,这样可以节省出更多的空地,一打场,场里场外全是麦穰子。柴油机带动脱粒机,脱粒机圆滚子上长满齿,转起来速度极快,一个麦个子脱不透,要破捆,不能用手,手工太慢,用镰,一剁即开。有人破捆分丛,有人往机器上传递,脱粒机上第一个人接过传过来的一把麦子,两手抱住,放到飞转的脱粒机滚子上,麦粒立刻像火星一样乱溅,这把麦子在脱粒机上打了一个滚,接着传到下一个人手里,脱粒机上一溜四个棒劳力,一把麦子在每个人的手上就几秒钟的工夫,从最后一个人手里脱手时,麦粒就脱完了,剩一把麦秸随手扔掉。有人在一边挑麦穰,还有人拿着木叉把麦穰往外倒,场边麦穰堆积如山。机器转动那股力量很大,站在脱粒机后面打麦子的人,要双手抱住手里的麦子,抱不住就被机器抽走了。麦堆眼看着增高,很快就堵在了脱粒机下,必须有人用木锨不断地往外倒,或用筢子往外扒。还有打散的麦秸,同样落在了脱粒机前,要有专人用叉往外划拉。整个打麦场尘土飞扬,麦秸麦穗里积满灰土,打场时全部飞起来了,男人的脖子里缠一块毛巾,这样可以减少落进脖子里的灰土,口鼻眉毛和整张脸暴露在外面,全成了黑的了。只剩下一口牙是白的。机器隆隆,麦粒迸溅,麦皮麦糠满场飞,脖子上缠的那块毛巾一脱落,麦粒麦糠乘机往脖子里钻。大姑娘小媳妇则头上扎一个花头帕,从头顶系到脖子下,只露着脸儿,有的爱干净,袖子上还套了套袖。打麦机上的人不敢睁眼,不怕麦粒打脸,就怕麦粒打眼,眼皮能报警,麦粒来了知道眨,一眨一眨,躲避麦粒。场上挑穰子的人不断地用一只胳膊遮着脸,一进一退,在场上抢活干。
高省力家的麦子打完了。他和堂兄弟一共四家子搭伙,从过午就开始一直打到天黑,掌上灯继续打,高省力家的麦子是最后打完的,打完已是夜里十二点。所有打场的人都还没有吃晚饭。高省力家的麦场上,那一堆麦子连糠带皮堆成了山,四周的麦穰子堆得人都进不来出不去,高省力的爹用木叉挑出一条路来,以便出进,按说这时最需要的就是一袋烟,一袋烟最解乏,可打麦场上不能抽烟。麦子到了这一步,就算收了,高省力一家悬着的心,这一刻可以放下了。天明把这堆麦子扬出来,找足麻袋装麦子就可以了。高省力这一刻真想倒在麦穰上不起来。
6
要不是出了一点意外,高省力和妻子郑香还有父亲就可以放下这堆麦子回家吃晚饭了,而且吃完晚饭上床安歇了。高省力墙西的邻居,男人叫王均花,一窝闺女,没有儿子,王均花两口子带着一群闺女种麦割麦皆一包劲,可打麦犯了愁,闺女不能抢机器抬机器,没有人愿意与他们家搭伙。高省力与堂兄弟四家搭伙,轮到最后,王均花的三个闺女跑过来帮着抱麦子。按说这是厚脸皮的事,可三个闺女眼看着自己家的麦子上了场,眼看着老爹年老无力束手无策,便瞅准了高省力这个机会。高省力家的麦子打完了,有人上来抬机器,王均花的三个闺女急在心里,不好开口,高省力心里有数,邻居家的三个闺女跑上来帮着抱麦子他便知道又多了一份活。高省力说话了,他说,我们还有一户,捎带着打了吧。是商量恳求的语气,抬机器的人看高省力的面子,只好退让。高省力叫上三个堂兄弟把机器抬到王均花家的麦场。三个堂兄弟抬完机器就想走,他们累了一天,晚饭还没有吃。王均花一家五口人,高省力场上三口人,共计八口人,这当然不够用,高省力又把两个堂弟叫住了,这样打场就有了十个人,十个人虽然不够用,但可以开机。有牛使牛,没牛使犊,有三个男人上机,王均花的大闺女也上机,守在最末尾,那把麦子到了她手里已撸得差不多了,在机器上碰一下就可以扔掉。王均花的大女儿还不满十八岁,头上也扎一个花头帕,正是女孩儿出息的年龄,俊俏中带着憨,这个憨是发育成长中的特点,与这个年龄的小伙子的憨有点相似,很让人喜欢,不过,小伙子的憨是真憨,憨相憨心眼,女孩子的憨往往憨中带精。因为人手不够,中间停了两次机,停机大家一齐抱麦子,把路上的麦子和场边空地上的麦子集中到机器前。高省力对王均花一家来说,真可谓大恩大德。
男人打完麦子,跑到河里一洗,从头到脚的灰全部随着河水冲走了。麦场前面就是一条河,高省力打场前就准备了一块肥皂,打完了场,拿上肥皂和毛巾同两个堂弟一同下河了,不但从头到脚洗了个净,连身上扒下的衣服也擦了肥皂搓洗干净,拧一拧,就穿到身上,这样回家上床睡觉不但一身干净,而且身上还带着一股肥皂味。当他到家躺到床上的时候,已是凌晨两点了。夏天四点钟天就亮,他还能睡两个小时。
他没有吃晚饭,累到这个程度是吃不进饭的,最好就是先睡一觉。妻子郑香还没睡,她到家时婆婆搂着孩子睡了,本来坐着等,等到最后,在床上一歪就睡着了。郑香把锅里的饭热了,给男人留出来,自己和公公吃了,吃完饭高省力才回来,回来就上床了。郑香这会才腾出空来可以洗一洗了,她准备了一身要换的衣服,身上的衣服脱下来不洗不能穿了。水缸在院子里,郑香瞅瞅公公屋里的灯关了,又等了一会,才敢脱衣。她脱光了,站在水缸旁一扇废旧的石磨上,从水缸里舀了一桶水提在石磨下,弯腰从桶里舀了一瓢水,从头往下浇,放下瓢前后搓洗,然后再舀起一瓢水从头往下浇。洗完了身子又洗头。女人就是这样,再忙再累,梳洗打扮也不会偷工减料,头洗了一遍又一遍,洗完了,又一遍一遍地梳。郑香是个漂亮女人,脸面红润,端庄大方,稍有点黑,却非常耐看,如果白皮肤,那便与观音相差无几啦。她属于那种宽背宽腰的女人,这或许与从小庄稼地里劳动有关,蜂腰形女人在庄稼地里实不多见。郑香的娘家就是当庄,与婆家一条街上,相距不到五十步,没订亲之前,一个大姑娘一个小伙子在同一条街上出出进进,互不相干,碰了面也只是打个招呼。有一回当街的一个妇女看到了这两个人,一个出门,一个进门,进门的是郑香,这女人多事,就跟到了郑香家里,郑香的父母都在家,这女人对郑香的父母说,她在街上看上了一门亲,郑香的父母便问,她说看上了郑香和高省力。一句话提醒的郑香的父母,捧心地愿意。这女人又到高省力家里一提,高省力父母没二话。婚姻这东西真是天意,要不是三个人在街上同一时间碰面,郑香怎么会和高省力成为一家人。等郑香上床,又一个小时过去了,就是说,从现在到天亮只有一个小时了。男人没关灯,赤条条躺在床上,这是他睡觉的习惯,从来都脱得一丝不挂,四仰八叉。高省力有护心毛,护心毛像猪鬃一样,从心口窝一直长到裆,看着那毛,就让郑香心惊肉跳。她的身子还没干,躺到了床上,躺在男人的身边。她拉过男人的手,放到自己的胸上,从胸口往下拉,拉到下边,按了一下,问,今晚行动吧。郑香是个欲望很强的女人,无论农活多忙多累,夫妻晚上从不耽误行动。高省力没有反应,郑香看到他嘴角一丝苦笑,知道无望了。回家应当先喂孩子,可孩子睡着了,天黑前婆婆把孩子抱到麦场上喂了一回奶,可这会两个奶子又鼓得发胀,她很想让男人给吸两口,她不甘心,往男人怀里拱,男人没反应。他实在太累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