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编辑/何为
(一)弦歌
纠缠我一辈子的、如诉如泣的曲子,又在几声夜晚出没的猫叫之后,随着江风的吹拂,伴着晾晒江鱼的鱼腥,拼命挤进我的孤独,密密匝匝又似有似无地包裹着我。在垂垂老矣的今天,我竟然不知道是该爱它还是恨它。听到镇子上的老人提起她时,我总是静静地躲开。这个世界上,没人知道我和她的故事。

她是在1937年的初冬来到镇子上的,跟她来的还有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她来到镇子上那天,街头巷尾的男人都像打了鸡血,其中也包括我。那时我十七岁,在大通理发店当学徒。
那天是霪雨霏霏的天气,细若牛毛的雨丝,零零碎碎不时飘落片刻。她二十三四岁的模样,身穿浅灰色羊毛大衣,开襟处露出素雅的藕荷色旗袍衣角,左手拎着有些泛黄的藤条箱,从镇子的西头袅袅婷婷地走来。她是那么瘦弱,仿佛一阵风就能将其刮走,苍白的面色,杏仁般的眼,不高不矮的鼻梁,施了胭脂的红唇,并不十分隆起的前胸,和翘挺的、随着走路一摆一颤的臀,勾着巷子上老老小小男人们的眼睛,也让年轻女人们,无端地生出酸意。她们突然感觉到危机,心里恨恨地想,得看好自己的男人。待看到她身后跟着的男人,悬着的心又有了一点儿落地感。
跟女人来的男人很是高大,骨骼强壮,腰杆挺直,后背背着、双手拎着重重的包裹,不紧不慢、亦步亦趋地在女人身后跟着。他稍微低着头,面无表情地走着,既没看前面的女人,也没有看路旁的人。镇子上的人们都猜测着这两个人的关系,看年龄和两人行走的距离,不像夫妻,可这孤男寡女的一同来到镇子上,不是夫妻又是什么呢?在猜测的过程中,男人们的眼神里,就射出了锐利的刀子。
两个人在汪家刚搬走不久的老宅里住了下来。宅子正在我学徒的理发店对过儿。从此,在没有客人的时候,我就站在店门口,盼望着能看见她。每到夜晚的时候,在师父给我的铺盖上,我垫上一块折叠起来的布。
汪家老宅自从她俩来了以后,热闹起来。白天晚上总会从阁楼上的窗户里传出曲声,门口也经常停一些镇上人很少见的汽车。我听不懂弹的是什么,只是觉得很好听,有时候听着听着又会觉得心酸。女人偶尔走出院子,拿着一些糖果,分给在她家院子不远处那棵大槐树下玩耍的孩子们,或者用一些食物喂流浪的小猫小狗。这样的时候,女人的眼角和嘴角都会挂着浅浅的笑意,她的笑容在阳光下,闪着光亮,我看着看着,便痴痴地忘了自己。偶尔,她似乎感觉到我的注视,会冲我悄然一笑,然后一扭身子,闪进宅子。
到理发店理发的客人,议论最多的就是新搬来的这户人家。有的说,这个女人实际上是那种女人,别看她长得文文弱弱的,其实骚得狠,要不怎么那么多男人去找她;有的说,别听那些人胡咧咧,人家可是从东北逃难来的大家闺秀,她弹的乐器是古筝,不是大家闺秀谁能学得了这个;有的说,来她家的客人什么人都有,帮会的、军队的、经商的、教书的,还有日本人呢,离她们家一定要远着点,可别摊上啥事儿。
我在这些议论中,逐渐理清一件事,跟她来的男人是她家的家仆,又聋又哑,据说他能通过眼神、动作,知道别人的想法。有几次深夜,我被咿咿呀呀的声音吵醒,打开窗户往外看,看见他拎着去他家的男人的衣领,把他们扔出大门外。我还看到过他夜半的时候,悄悄走出镇子,或一日、或二日返回来。他不在的时候,汪宅的大门始终紧闭着。
转眼到了三八年的春天。日本鬼子占领了我们这里,还在镇西头建了俱乐部。镇子上的人经常听到从那里传出来毛骨悚然的嚎叫声和淫荡的大笑声。
来女人家的客人明显比以前少了,女人也很少走出院子。来店里理发的客人也越来越少,我更加频繁地坐在理发店的门口,师父以为我想招揽客人,其实我是害怕错过任何一个能看她一眼的机会,这样我就有了新发现,发现她有时会偷偷地从欠开一点点的门缝里往外看。
一天晚上,我实在耐不住难熬的念想,围着她家的宅子转来转去。宅子里又传出来听过很多遍的,让我想哭的乐曲声。我倚在大槐树下,闭上眼睛,眼前出现了她艳若桃李的红唇。突然我听到乐曲声中,有压抑着的、低低的哭声,乐曲突然停了,过了好一会儿,聋哑的家仆背着一个包裹走了出来,匆匆地往镇外走去。
他这回走,好些天都没见回来。
从此,夜晚我到她家门外转悠的次数越发多了起来。又一个夜晚,我睡了一觉醒来,心里感觉很不踏实,披上外衣走出门。还没走过对面的小巷,差点撞上一个斜披着军服的日本军官。我赶紧躲了躲,他含混不清地骂了句“八嘎”,走远了。
不祥的预感突然涌上心头,我急忙跑到女人的院外,看见大门开着,从里面传来女人的哭声。我忘了自己是谁,也忘了我是不该走进这个院子的,疯了一样闯了进去。阁楼上,女人衣衫不整地斜靠在床上,头发散乱,一张刻花檀香木古筝躺在离床一米的地上。她看我闯了进来,一惊,蹭地站了进来,瞪大了眼睛看着我。
我看着她受惊的样子,开始后悔,站在那儿不敢往前再走一步。
我俩就这样怔怔地站了好几秒,女人突然像想到什么事,走到书桌旁,拿起毛笔,在一张纸上写下了一串数字。转身来到我面前,轻声地说:“弟,姐可以求你件事吗?”
我还没有从自责、害怕中缓过来,看她的嘴唇动了几动,竟没听清她跟我说了什么。
她看我没言语,皱了皱眉,眼神里充满了祈求,又重复了句:“弟,我可以求你件事吗?我现在只能求你了!”
我缓过神儿来,语声颤抖着:“姐,你说,什么事我都答应你!”
她把写好的纸条递给我,又翘起一块地板,从里面取出来一块缺丫儿的大洋,也递给我,然后攥住我拿着纸条和大洋的手,悄声在我耳边说了一段话。
“记住了吗?你再重复两遍。”她有些紧张地看着我说。
我一听她让我做的事很害怕,有些后悔答应她。但一看到她眼里的泪水,瞬间心软了,重复了两遍她说的话。她重重地点了点头,竟微微笑了。
我转身就想往外走,她拽住我,把我的手拽进她怀里,开始一粒粒解本不整齐的旗袍扣。我的血瞬间冲上头顶,嘴唇也干出血来……
我坐在床上穿衣服的时候,看见雪白的床单上,有几片和古筝上的花纹相似的花瓣盛开着,可我丝毫没有觉得美丽,而是恨不得将床单用刀划得稀烂。
走出院外的时候,我听到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紧张的乐曲声,接着又是一阵呜呜咽咽的乐曲声……
过了二年,我在队伍里意外看到了那个聋哑人。他看见我并没有吃惊,而是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有力地握住我的手,语声清晰地说:“你的事我都知道了,香凝在你带出来的情报里,简单说了你的情况,小伙子,欢迎你加入我们的队伍!”他的眼睛蒙上一层水雾,哽咽着继续说道:“都怪我没有保护好她……香凝是从东北逃难过来的大学生,组织上还没有完成对她的集训,因为有紧急任务,皖南地委派她来协助我工作。这份她用生命换来的情报,为我们赶走古镇上的日军,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她!”
那天我第一次知道,女人叫香凝。她在我走后,用那个盛开着花瓣的床单上了吊。
解放后我结了婚,结婚那天,我的耳畔响起了呜呜咽咽的古筝声,将我蹿起的火焰瞬间浇灭了……
后来,我终于知道,她离世前弹奏的曲子是《十面埋伏》和《昭君怨》。
(二)弦歌背后
1937年初冬,我和他来到大通古镇。那天是个霪雨霏霏的天气,天空不时飘落着细若牛毛的雨丝。一入镇口,晾晒过的、江鱼的鱼腥随着江风的吹拂扑面而来。我从怀中掏出丝帕,掩住鼻息。他跟在我身后大约三步远,他的脚强有力地叩击青石的声音让我安心。能单独和他在一起生活,虽然可能随时都有危险,我仍然觉得值得。强忍着回头看他、跟他并排走的冲动,我挺着胸,昂着头,往巷子深处走去。
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去年的三月。那时我是东北大学补习班的学生,而他是陕西农林学院的助教。
“九一八事变”后,沈阳沦陷,日本南满公学学堂堂长来我校慰问,要求我们照常上课,称经费由日本政府供给。校方和一些师生悲愤至极,感到莫大羞辱,有的导师言说,“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不久,校方决定,学校迁徙北平。
我的家在哈尔滨,此前父母托人带来书信,说哈尔滨更在动荡之中,希望我安心读书,能学有所成,为找一佳婿奠定良好之基础。于是我带着父亲送给我的古筝和几件换洗的衣服,跟随导师和同学来到北平,不久又迁至西安。
来西安的路上染上风寒,整天冷颤发热,昏昏沉沉,到西安那天才见好转。
我们的新校园是陕西农校,坐落于城南里许,南屏终南山,西枕渭水,大小雁塔耸立于前,阿房、镐京遥接于后。校外农场约良田二十余亩,栽满各种不知名的树木、蔬菜和花卉。见眼前美景,似多日沉疴之良药,我深呼一口长气,暗暗祈祷,就此可以长久落脚,再不受颠簸之苦。安顿时才知,农校只让出一半房舍,学生每五人一间,教授则二三人一间,到了夜晚,寝室只能用油灯和蜡烛照明。
当晚,我们五个女学生摸着黑,裹紧棉被,躺在冷冰冰的床上。本不善言谈的我听室友议论,恐怕再也回不去东北了,突然心生无限感伤,竟忍不住啜泣起来。室友听我哭泣,围拢过来,摸头的摸头,拉手的拉手,怕我病情加重。好友曼娜更是跑出寝室,没一会儿,他带着一个女人跟在曼娜后面走了进来。
后来我知道他叫汪慎之,带我去古镇的时候叫“哑叔”,其实他真名叫什么,我是从不知道的。那天他是带校医来给我看病的,可是校医怎么给我看的病我忘记了,从他进来的一刻起,我似乎忘记了呼吸。
他与我父亲像极了!短短的平头棱角分明,发丝很坚硬,根根直立,似可扎破皮肤,眉毛极浓、极黑,粗而散乱,眼睛不大,眼角有一处伤疤(我父亲没有),唇线如弓,清晰可见。他进来时并没有看向我,而是打量了整个房间,在女人给我把脉的时候,眼神才着落到我脸上。我并未看到想象中的关心和注意,它就那样轻飘飘落下,又轻飘飘移开。那瞬间,我忍不住又哭了……
从此,在任何可能看到他的地方,我都会想办法出现。为了经常看见他,我参加了他组织的文学社。在一次诗会之后,我和几个同学被他留住,他跟我们讲了很多,关于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命运,还有我们这些学生应该为民族、为人民做些什么。其实,他说的这些我是不大懂的,但我知道,我们的学校因为日本人的入侵,不得不停课,不得不辗转来到这里,我更知道,我已经好几年没回家了,都不知道父母现在身体怎么样、会多么多么惦记我。记得当时我很激动,看着几个同学同样激动的样子,我控制不住地表现得更加激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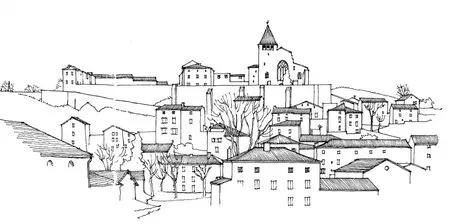
我和他在一家老宅里安顿下来,宅子的主人汪老先生,被他在部队上的儿子动员,暂时搬到乡下去住。老宅的院子不大,天井旁边种着一棵桂树,打开卧房的窗户,可以清晰看到尖顶树叶的纹路。我似乎闻到了八月里桂花的香氛,没来由地开始喜欢这里。他住在楼下,每天准备早饭的时候,他在桂树下练一趟拳脚。我想象着,这将是我未来的生活,甚至还想象,会有我们的孩子。
在来古镇前,我和他在铜陵“华东商行”董事长汪猛家住了一段时间。那时我的公开身份是汪猛七岁女儿的古筝家教。不知是因为我古筝弹得好,还是因为汪猛的大力宣传,或许还有别的原因,我很快在铜陵小有名气。
到了大通古镇后,还有人特意从铜陵赶来,有的只为听我弹曲,有的似乎根本听不懂,只是因为别人来了,他们也要来,更有的是不怀好意。
时间一转眼就过去了,我们迎来了热情奔放的夏哥哥。夏哥哥送走了温柔的春姑娘,火辣辣的阳光照射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让人感觉连空气中都弥漫着阳光的味道。大树爷爷伸出了茂密的枝丫,为我们撑开了一把绿色的大伞。每次下课,我们都会到“大伞”底下乘凉,嬉戏玩耍,银铃般清脆的笑声传遍了校园。
慎之也就是哑叔,在有客人的时候,会备好茶点站到屋外门口。客人以为他又聋又哑,都不在意他站在那里。有些男人实在很无耻,无论我怎么样表示冷漠,仍然口出不逊,集挑逗之能事。一天晚上,青龙帮三当家带着一个手下来了。他们自带了很多酒菜,非说听曲岂可无酒。上次他来的时候,话里话外透露出,青龙帮已经和日本的“大岛株式会社”签订了江上运输协议。哑叔告诉我,“大岛株式会社”实际上是日军的特务组织,他们想利用青龙帮在古渡口的船只和势力,运输物资和武器,他要求我,如果三当家再来,一定要套取更多的信息,最好能搞到运送物资或武器的具体批次和时间,以便部队部署或防御。
哑叔将桌台摆好,悄悄对我使了个眼色,冲着三当家咿呀两声,哈了哈腰,走出屋外。
“三当家,您有日子没来寒舍了。”我故意用手指调弄琴弦,有些心不在焉地说道。
三当家紧紧盯着我的脸,恨不得要剜下一块肉去,“怎么,香凝姑娘可是想我了?”
我假装生气地白了他一眼:“我从东北逃难到这里,权且是讨生活,能来寒舍捧场的都是我的客,谁不来香凝都会想的。”
说完,也不等他再说什么荤话,弹起《梅花三弄》。三当家咽了口唾沫,闭上嘴,和他手下吃喝起来,偶尔装作听懂的样子,摇头晃脑。一曲终了,三当家酒劲上涌,脸色开始潮红。他冲手下使了一个眼色,手下站起来,对我说,“香凝姑娘,我拿点酒菜给哑叔送去,再和他喝上一杯。”
说完,从怀里掏出一沓法币,放在桌台旁黄梨木花架上。
我看都没看一眼,继续弹《关雎》。三当家又喝了一杯,站起身来,脚步微晃地来到我身边,伸手就要摸我的脸。
“三当家,请您坐好。香凝虽说来到这儿人生地不熟的,但想必您也知道,我在铜陵是有些好朋友的。”
我的手指虽然仍在琴弦上拨弄着,但曲调已经走了模样,好在他根本听不懂。他迟疑了下,又坐了回去。
“香凝姑娘,这样吧,一会儿你陪我喝上几杯……”话还没说完,手伸进怀里又掏出一沓法币,我突然想起哑叔嘱咐我的话,用眼角瞟了几眼钞票,犹犹豫豫地说道:“三当家,香凝敬您是英雄,想必英雄是不会为难小女子的。”
“香凝姑娘,你这说的哪里话,我只要姑娘赏脸陪我喝上几杯,以解我相思之苦,这些法币就都是你的了。”
他拿钞票的手在我眼前晃了几晃,我见火候到了,站起身,坐到他的对面,举起酒杯。
“来,三当家,香凝敬您一杯,以后还要三当家多多关照呢。谁不知道三当家在这大通古镇是响当当的人物,要是有您为香凝撑腰,谅是没人敢欺负我了。”
三当家被我这几句话说得哈哈直笑,连着喝了两杯酒下去。
“三当家,听说贵帮和日本人做生意了,发了不少财吧?”我看似无意地随口问道。
“那是,香凝姑娘,我告诉你,以后你就跟了我得了,何必赚这种小钱呢,以后我会有的是钱的。日本人的钱真好赚啊,上次给他们运了一批棉花,运费竟然超出市价三成,你说日本人傻不傻?”
我心里暗骂了句,败类。嘴上却说道:“我可不相信日本人傻,小心你们被骗了。”
三当家一听我不相信,眼睛都瞪圆了,“你看你还不信,你知道为啥我今天来不?我今天赚了一大笔,昨天日本人寄放在码头200箱东西,箱口封得严严的。我听工人们说,箱子特别沉,就长了个心眼儿,晚上偷摸撬开一箱看了下,你猜是啥?全是枪。”
我一听全是枪,紧张起来,又不敢追问,给他满上了酒,撞了下杯。他一饮而尽,继续道:“早上,大岛株式会社的川崎来码头,我有意无意地点了他句,他当时就跟我说,让我去他那取支票。”
三当家不无得意地说着,我暗中盘算,怎能套出运输的时间。
我假装微醺地站起身转到他那侧,头靠着他的肩膀又给他满了一杯酒:“三当家,我从来还没见过枪呢,能不能让我看看枪什么样啊?”
“女人家看那东西干什么。”他顺势搂住我肩膀,将我的身体往他怀里带,我用力推了下:“人家这点好奇心都不能满足,还说什么喜欢人家?”
我嘟起嘴,挣脱开他的手,又转回桌台的对面。
“香凝,你是我心肝儿,你要月亮我都去给你摘。我不是不想满足你,今天上午来了一队日本人,把货场看得死死的,我都不让进了。后天这批货就运走,据说过几天我们镇上就会有日本军队驻扎了。”
三当家说完打了一个酒嗝,臭烘烘的气味差点让我把吃的东西吐出来。他看我皱着眉头,以为还在为不满足我的要求生气,晃晃悠悠走到我身边,猛地抱住我,一下子撕开了我的旗袍纽襻。我吓得大声叫起来,这时,哑叔撞开门进来了,一把薅住三当家的衣领,狠命地把他拎了起来。
三当家根本没想到哑叔的手劲这么大,一拳向哑叔打去。哑叔避都未避,另一只手像铁钳一样,牢牢地攥住他手腕,嘴里“啊啊啊”地喊着,拽着他就往门口走。三当家发现他在哑叔手底下讨不到半分便宜,只得认命地被哑叔拖到门口,扔出院外。
我站在卧室窗户旁往外看,发现对面理发店的窗户开着,店里那个眉清目秀的小伙计正在往这边张望。我赶紧关上窗,走下阁楼,示意哑叔关上院门。
记不清从哪天开始我注意到理发店小伙计的,总觉得他时常出现在我的视线里。有时候是我家院外的大槐树下,有时候在理发店的门口,有时候他从理发店的阁楼里探出头往我家这边观望。他还不到十八岁吧,嘴上的绒毛还没褪干净,如果他再大些,我都要怀疑他爱上我了。
那天夜里,哑叔莫名其妙地狠狠训斥了我。
“你到底要干什么?如果帮会那个小混混儿没走,我被他缠住,你怎么办?!”
哑叔的脸有些扭曲,眼睛里布满血丝,“我刚才恨不得杀了他……”
我见他的样子,突然开心地笑了。开始是抿着嘴,后来竟笑出声来。
他见我竟然没心没肺地笑了,更加生气,“你笑什么?我带你出来,不希望你有任何危险,知道吗?”
我拽住他袖子,拧起麻花,轻声细语、假装委屈地说:“我知道了,下次一定注意,别生气了,我还不是为了工作吗。”
我把头试探着靠过去,他竟然没有躲开,这是他第一次任由我靠在他怀里。我闭上眼睛,将手环住他的腰。他并没有抱住我,而是手指松垮弯曲地垂立在两侧。我就这样一动不动地静静靠着他,多么希望此刻就是永恒,多么希望时间从此停摆,大约二分钟后,我听到他轻轻叹口气,“香凝,刚才是否打探出来什么消息?”
除了情报,难道就不想别的吗?我知道这话是问不出口的,我也悠悠地叹口气,把我听来的消息一字不漏地说给他听。
他粗散的浓眉挑了几挑,眼角的疤在灯光下显得比白日深沉。他对我说:“香凝,今天你得到的消息太重要了,我必须亲自走一趟,把情报送出去。”
转眼到了三八年的春天。一天,一个日本人带着翻译,来到我家。他说他叫藤田,他对中国的古典乐器非常感兴趣。在看到我的古筝后,说了一段话,翻译官翻译完他摇了摇手,竟用中文说:“香凝小姐,您的筝真是难得一见的好筝,这古筝的紫檀筝码,垂直向下,上嵌牛骨,搁弦槽的深度为对应琴弦的三分之一。”
我一听,他如此懂行,不禁对他另眼相看。
“香凝小姐,能为我弹奏一曲《十面埋伏》吗?”他的眼里射出向往的光芒,我的心情突然很复杂,手指搭在琴弦上竟忘了言语。
他收回视线,对我深鞠一躬,“可以吗?请您弹一曲《十面埋伏》可以吗?”
我点点头,弹奏起来。第一节“列营”还没弹完,他突然走过来按住琴弦,脸色微愠,“香凝小姐,请停下来,你的心很乱,轮拂手法用的也不到位,太让我失望了。”
说完,他神色复杂地看了我几眼,对翻译官说了句什么,转身就往外走。快到门口的时候,回转过身,对我再次深鞠一躬,“对不起,我刚才失态了,今天就到这里,希望我下次来的时候,您能让我听到全身心投入的《十面埋伏》。”
他走后,哑叔对我说,“香凝,这日本人不简单,你看他中文说得多好。之前在镇上没看到过这人。”
他停了停,竟破天荒地拉起我的手,将我的手轻轻举到他的眼睛下,我的心“怦怦怦”地跳了起来。
“你的手真美!”他端详着,似乎不放过任何一根手指上的纹路。我突然很想哭,很想,但我怕一哭,他就不看了,我忍着不让自己的眼泪掉下来。
他悠悠地叹口气,“香凝,这几天你抓紧练下《十面埋伏》吧,我想他一定还会再来的,他想听《十面埋伏》,除了喜欢曲谱外,更是将我们中国军队想象成项羽啊!你得设法打听到他的真实身份,我有个预感,觉得这个人一定会为我们提供非常有用的情报。”
那些天,日军从早到晚轰炸大通、和悦洲、铁板洲。镇上的百姓人心惶惶,来我们这里的人越来越少,很多人都迁徙去了四川。那个日本人很久也没有来,我快将他忘记了。后来听说国军县党部迁到董店那边的山区,临走时一把大火就把繁华一时的大通、和悦洲化成了一片废墟。
日本人到底占领了大通。他们来之后,立刻设立中华轮船公司大通办事处,分别开设了由芜湖至大通、大通至安庆沿线往返航线。并在镇西头建了个俱乐部,从那里经常传出毛骨悚然的嚎叫和淫荡的大笑声。
一天,那个日本人又来了。这次他并没有带翻译来,进门开门见山,还要听 《十面埋伏》。我想象着国军将日本人赶走,倒也弹得铿锵有力,这次他比较满意,临走时说一定会常来的。
他走后,哑叔对我说:“香凝,从他走路的姿势和强壮的骨骼来看,这个人是军人无疑,我怀疑他是驻扎在这里的日军一个高级长官。”
后来证实了哑叔的判断,这个日本人叫松井一郎,是日军138联队的队长。从他那里我慢慢了解到,驻守铜陵的日军是130旅团下辖的133联队、138联队。旅团部驻扎在大通天主教堂,对外称“大通警备司令部”。旅团长兼大通警备司令是三浦加门。旅团部和联队均下设报导班和看守所。所谓的报导班,实际上就是搜集情报特工班。
不久,上级派来一人与我们联系,他和哑叔足足说了小半天,基于保密制度,我并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当天晚上上级派来的人走了以后,哑叔把我叫到他房间,告诉我他要离开一段时间,有新任务派他去完成。
“香凝,我走后,你不要再继续活动,我回来前,你一定要保持静默,尽量不要接待任何一个人,你记住了吗?”
我怔怔地看着他,说不出一句话,他要离开一段时间,这一段是多长?如今兵荒马乱,他有什么任务?他的任务怎么能不会有危险?我的内心翻滚着,我觉得自己的喉咙突然肿了,肿胀到堵住了呼吸的门,我的眼泪一滴滴地滴下来,我不想去擦拭,也想不起来去擦拭。他看我这个样子,突然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香凝,别这样,等我,我一定会回来的,一定……”
说完,狠命地推开我,背上早已准备好的行李走了出去,竟然都没有回头看我一眼。
我趴倒在他的床上,那上面还有他的气味和体温,我抱住那床前几天我给他晾晒的棉被,将头埋在里面,放肆地大哭起来。
哑叔离开的第三十三天,那个被我二次拒之门外的藤田又来了,这一次他既没带下属,也没敲我的院门,而是在夜色中不知怎么弄开了门栓,摸了进来……
我将那床满是耻辱的床单拧成了绳,拴在高悬的吊灯上。此时我的眼泪已经干了,眼前出现了父母和慎之的幻影,他们的影子并不能阻挡我必死的决心,我轻轻哼起了“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声。君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想象着虞姬拿起宝剑,搭在自己的脖颈之上,决然地将头伸进高悬的索套,踢倒了垫在脚下的木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