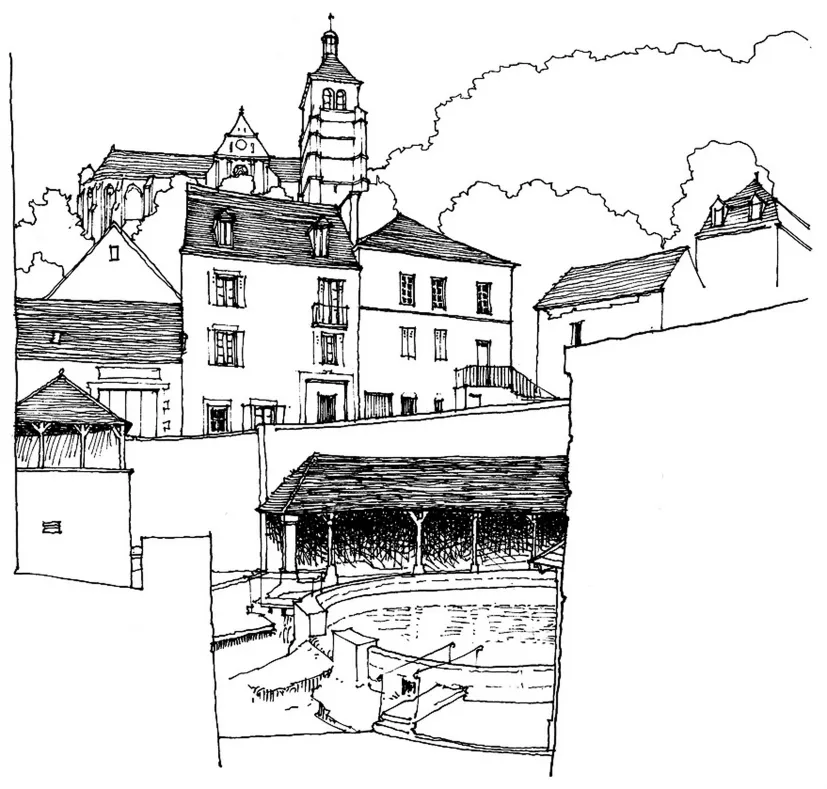
胭脂考上了县一中。一中是全市的重点高中,镇中上线的考生,数来数去拢共也就十来个人。土根本来就有点结巴,得到这个消息后,更是激动得“你你你、我我我”的,愣是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索性不开腔,只龇了牙,一个劲地搓着手。
可是,胭脂一点也不高兴。
她抹着眼泪,噔噔噔就往屋后的山岗跑去。一路上都有胭脂花追着她的脚步,郝家大山的人没那闲工夫去种什么花,偏偏这胭脂花开得哪儿哪儿的都是,路边、坡上、田间,再陡峭的崖壁都敢去,都能开得闹哄哄、亮灼灼。就更别说人家的院落了,一到下午,它们就打开紫红色的花瓣,吹起一曲曲意气风发的小喇叭。
这个时候,太阳正忙着往山的另一边赶路,吼了快一天的知了,也要歇上好一会儿才吱呀吱地,勉强咧咧嘴巴,不过这会儿的胭脂花精力旺盛,一只只紫红色的小喇叭,正啪啊啪地打开。
胭脂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呆呆地望着身边那些神采奕奕的小喇叭,换往常,早摘下一朵,掐了尾抽出花蕊,含在嘴里,唷嘀唷嘀地吹起来了。这时候,她再没心思去倾听它们发出的细而清亮的声音了,耳边盘旋着的,全是土根刚才说出的那句话。土根的嗓子虽然有些低,又有些沙哑,可那句话,却无疑平地响起的一记炸雷,哗嚓嚓滚过她的头顶:
“胭脂,你妈妈,你亲生的妈妈找,找你来了,我,我们已经说好了,你,你明天就回,回你的家去吧。”
土根是50岁那一年,从徐家大沟一位大嫂的手中得到胭脂的。刚满月的小女婴,生了一张秀秀气气的鹅蛋小脸,像是知道自己不讨人喜欢,也不哭闹,就那么睁着眼睛,安安静静地看着土根。
土根姓郝,郝家大山的人说他就是个苦根。矮个子,胭脂一上初中就和他一般高了。腿有残疾,一长一短,走起路来就一颠一颠的。两道眉毛长得也挺有特色的,像两把扫帚斜挂在额头上,看上去就是一副苦相。而那张苦巴巴的脸,打年轻时就爬上了一道道褶子,所以好像从来就没年轻过。土根独自生活了大半辈子,不想一下子当上爹了,兴奋呢,连声道:“划,划得着,划,划得着。”笑得那脸上的褶子跟波浪一般,一圈圈地淹没了五官。
小女婴被土根抱回家的时候,房前屋后簇簇丛丛的胭脂花,怒放着,像天边,一片片娇美的云霞。
“丫头,我看你就叫胭脂吧。”土根怜爱地看着怀里的女婴。胭脂花贱,好养活,哪儿都能长得好好的。
土根以前爱抽叶子烟,有事无事都握着一管两尺长的烟杆吧上几口,现在抽得少了,说添人口了,用钱的地方就多了,节约一个是一个,再说也别熏着胭脂,那么娇嫩的一个小人儿。村里人笑他,这下子捡回个金元宝。
胭脂早就知道,自己是土根从外面抱回来的。见过土根的同学都说,胭脂的爸爸怎么看都不像她的爸爸,长得难看就不说了,还那么老,爷爷还差不多。
不过胭脂从来没有觉得土根不好看。那时候,她学其他孩子吹胭脂花,吹不响,憋得脸红筋胀,一双眼睛都突了出来也不行,土根就说:“莫急,莫急,爸爸来教你。”其实土根也没吹过胭脂花,活了几十年了,对花儿草儿的都没拿正眼瞧过,有了胭脂后,那一朵朵紫红色的、散发着淡淡清香的小花儿,就一朵接一朵地,别上了他那张黧黑粗砺的脸膛。当胭脂嘴里的小喇叭终于唷嘀唷嘀地响起来时,那张气急败坏的小脸,那张笑纹荡漾的老脸,都同时开出绚烂的花来。这样的一张脸,怎么会难看?
胭脂也不觉得土根的腿有残疾。那时候,她在他的背上,翻过山,走过一条又一条狭窄的田坎。有一年,胭脂生病了,赤脚医生看了也不管用,土根就背着她去镇上。那会儿村里还没通公路,三十公里山路,土根一颠一颠地走着,一会儿往上,一会儿向下,他的背摇晃着,但传到胭脂耳朵的心跳,虽紧促却沉稳有力,一点也不摇晃。那一年,胭脂10岁,土根60岁。住在卫生院里,胭脂问土根累不累,土根拍着他的腿,笑呵呵地说,不累,爸爸的脚杆劲大,大,大着呢!这样的一双腿,哪儿有残疾?
可是谁能想得到呢?就是那样疼爱着她的一个人,却狠得下心来把她送走,只因为当年抛弃她的那个人,又转了念头让她回家。
“你让我回什么我的家?你难道不知道这里就是我的家?”胭脂昂着头,一张鹅蛋脸上结满了寒霜。
“你妈妈,她,她想你回去了呀!从,从前是她不好,现,现在她要好好待你。”
妈妈,这个已离开胭脂整整15年的称呼,多么陌生又多么熟悉、多么排斥又多么向往的一个称呼啊!胭脂再度将脑袋往上抬了抬,不许集结在眼眶里的泪珠子滚下来。
“她要我回去我就回去呀?她只顾自己,就不管你的感受,也不管我的感受吗?”
土根坐在门槛上,点燃手中的那管叶子烟,狠狠咂了一口,不想一阵咳嗽暴风骤雨一般迅疾爆发,直把他呛得昏天黑地。有一段时间没抽烟了,似乎不大适应了。胭脂赶紧绕到土根身后,给他捶背。
土根喘着气,一把抹掉呛咳出来的眼泪,歇了会儿,说:“对,对了,还有你爸爸,也想着你,他在外,外头打工,干得好,每个月都给家里寄,寄钱呢。”
“我爸爸没打工,他叫郝——土——根,他就在郝家大山呆着,哪儿也没有去。”
土根叹了口气,脸上那深如沟壑的褶子,便一圈圈的缠绕得更紧密了,于是那张脸,看上去也就越发的苍老枯瘠了。“你上了高中,开,开支就越来越大了,我也……”烟杆子往鞋底上磕磕,收了起来。这才接着说,“不大负,负担得起了。”
“这才是你的内心话,到底不是你亲生的。”胭脂的声音猛地变冷,把土根冰得哆嗦了一下。
“还说什么别人找来了,我看是你去找的别人吧!”胭脂丢下话,跨过门槛就往屋后的山岗跑去。
胭脂说的是气话,可还恰恰就说对了,正是土根去找的胭脂的妈。
郝家大山和徐家大沟相距七八里地,那一天,土根气喘吁吁出现在一幢两层小楼前,胭脂妈张大了嘴巴,按住了心口,怕心脏不小心扑腾出来。
在那栋贴着磁砖的楼房里,两人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土根的身子越来越矮,而胭脂妈的眼睛越来越红。
土根临走时,还生怕胭脂妈不愿要回女儿似的,一个劲说胭脂如何地能干懂事,如何地让人骄傲自豪。
“大妹子,你相信我嘛,这朵胭脂花呀,将来,准,准能开到北京去。”
土根要把胭脂还给她的亲妈了,郝家大山的人一下子闹麻了,说什么的都有。
有人说土根太傻了,养了15年了,就是块石头也焐热了,焐软了,那婆娘凭啥想要就要回去?你土根又凭啥就依了那婆娘?
有人说是土根心好,那家人日子过得不错,胭脂以后上高中上大学就不用为钱发愁了,土根是为孩子的将来考虑。
也有人说,兴许是那家人给的钱多?
话音刚落,就有人掷过去一个冷笑,这是说的啥呀?土根是那样的人吗?
附和的声音四处冒了出来,都道,别说土根,哪怕就是个钱钻子,不也得想想,把辛辛苦苦养了十几年的娃儿送走,不就是把以后老了动不得了,有个端茶递水的指望给送走了么?
归根结底一句话:人善被人欺。养儿为防老,养了十几年的女儿却被别人收了回去,土根在这件事上算是输了,输在太老实,太软弱。
村里的云婆婆平时基本不出门的,听说了这事,也在重孙子的搀扶下,上土根家来了。按辈分云婆婆是土根的伯母,快90了,银发挽了个小髻,说话颤颤巍巍。一进门,就拿拐棍在地上敲敲打打。
“土根你这个哈笼包!养个娃儿当养个猪儿嗦,说送走就送走!”
“伯妈,胭脂上,上高中了,要用钱,钱的地方,就越,越发的多了,跟着我,就只有吃,吃,吃苦。”
“土根你这个哈笼包!只看到眼前,再哪个样子苦法,也是要过去的嘛,一过去,好日子不是就来了么?”
“伯妈说,说得是,但胭脂她,她妈不是想她回去了嘛。”
“土根你这个哈笼包!她妈想她回去就得回去?问题是人家胭脂不愿意回去,你还非要把她送走。你看看你这张脸,老腊肉样,半点血色都没得,胭脂在你身边,好歹也有个照应嘛。”
“我也想把胭脂留在身边,可她打生下来就还没喊过妈呢,如今她妈找她来了,胭脂也有妈可以喊了,这是好事呀,我得成全,不能阻拦呀!”
结巴土根,竟然顺顺溜溜的,一口气说出一段话来,郝家大山的人,再也无话可说,再也无人来劝。
太阳已赶到山的另一边去了,知了的吱呀吱也愈发含混,胭脂仍然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块大石头上,坐了有一阵子了,土根丢到她耳边的那声炸雷,仍然让她晕晕乎乎,回不过神来。眼前是举着紫红色小喇叭的胭脂花,脑海里,却是一团扯不清的乱麻。
“胭脂!胭脂!”土根焦灼的呼喊从半山腰传了过来。不一会儿,草丛中就露出一个白发苍苍的脑袋。
他的头发怎么全都白了?上次回来不还是花白的吗?胭脂的鼻头一酸,却在他一瘸一拐的身影出现在面前时,嘴一撅,腮帮子一鼓,起身就从另一个方向下山了。
才吃过早饭,土根就说:“胭脂,我们走吧,这阵凉快些,等一阵太阳就更大了。”
两个人,一人背一大包,一人扛一大包,胭脂走前面,土根一摇一晃,紧紧地跟着。
路上的胭脂花,朵瓣闭合,一律低着脑袋,一言不发。胭脂同样如此。而土根走得张着嘴巴呼呼喘大气了,照样有说不完的话。
他说,回家了要,要听妈妈的话,就算话说重,重了也莫生气,那,那都是为你好。
胭脂不说话。
他说,这些年她也记挂着你,要不然,怎么会,会来找我,怎么会,会把你接回去嘛。
胭脂不说话。
他说,你别怪你妈,她当年,也,也是没有办法。
胭脂不说话。
也许是这样的吧,胭脂出生时,已经有个三岁的姐姐了,家里穷,可还得再生个弟弟,胭脂妈只好托人把她送走。不过,是这样又怎样呢?胭脂加快了步伐,毫不费劲就把土根和他那些不停的叨叨,远远甩到后面去了。
大胭脂三岁的姐姐初中一毕业就到外面打工去了,家里还有个上小学的弟弟,黑黑的皮肤上像抹了层油,个子小,却分外结实,活像块铁疙瘩。天上掉下来的这个生得好看成绩又好的姐姐,如同磁场,牢牢地吸住了这块“铁疙瘩”,跟个甩不掉的小尾巴似的黏着胭脂,讲些稀奇古怪的事情,问些稀奇古怪的问题。胭脂虽有些烦他,却也觉得,没有这块稀奇古怪的 “铁疙瘩”,这个注定郁闷透顶的暑假必定会更难捱。
胭脂妈很疼她,整日“胭脂、胭脂”地喊着,跟土根一样疼她,仿佛下了决心,要把抛弃她的15年的空白时光补回来。但胭脂总是爱搭不理。胭脂妈现在对她这么好,以前却不要她;土根以前对她那么好,现在却不要她;胭脂妈明知土根会难受却要把她要回去;土根明知她会难受却不要她留下来。大人的世界怎么这么复杂?
既然人家郝土根都不要自己了,自己为什么还要“郝胭脂”?她对胭脂妈说,“我不想叫郝胭脂这个名字了,你去公安局把我的名字改了吧!”
胭脂妈却笑了笑,说,“郝胭脂,多好听的名字呀!”
胭脂成为高一新生不过一个多月,土根就过世了。
是放月假回徐家大沟时,胭脂妈告诉她的,说土根就葬在郝家大山和徐家大沟交界的山洼洼里。胭脂心中猛一格登,回家的路上就发现那儿垒起了一座新坟,怪不得当时说不出为什么,心里头一阵一阵发紧,发慌。
胭脂突然间明白了什么,放下书包就往回跑。
斜阳下的山洼洼已有了秋意,到处都有胭脂花的影子,但走进十月的小花儿,一朵朵的已开得有些憔悴,犹如一颗颗紫红色的硕大的泪珠,滴落在山洼里。
胭脂扑在坟头,哇哇地哭。
“我就知道你在骗我,我就知道你不会不要我!”
是的,土根,把她捧在手心里,把她背在背上,一天天看着她长大的土根,怎么会不要她?
几个月前,土根觉得身体不对,平日里有个头痛脑热的,都在赤脚医生那儿拿点药,但这次感觉和从前不一样,便坐上车,到了镇上的卫生院,然后又到了县城的医院,城里的医生说晚了。土根心头一凛,要医生告诉他有多晚。回答说也就几个月的时间吧。嘱咐他想吃啥就吃啥,想喝啥就喝啥。
回到郝家大山的土根没时间琢磨吃喝,全拿来琢磨胭脂的将来了,自己倒是一口气上不来一了百了,胭脂一个人怎么过?于是他登上了徐家大沟胭脂妈的家门,他要让胭脂妈接受胭脂,也要让胭脂接受胭脂妈。想来胭脂妈那儿应该不那么难,不过胭脂这儿可就没那么简单,像她那样的倔脾气,那么要强的性子,不想个周全些的办法,是决计不肯回家的,就算万不得已回去了,只怕也是过得别别扭扭,不痛快。
胭脂垂着一双红肿的眼睛从山洼回来,不说话,弟弟“铁疙瘩”绕着她转,追着她问也不开腔。胭脂妈挥挥手,让“铁疙瘩”先一边去,然后进了卧室,拿出用毛巾包着的一叠钱来。
“你土根爸爸存了五千块钱,说等你去县城读书好用。他拿给我的时候,我不收,他就说,不是给我的,是给他女儿胭脂的。胭脂,妈妈不如你的土根爸爸呀,妈妈对不起你。”
胭脂捧着钱,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
胭脂妈陪着她滴泪,土根送回胭脂的来龙去脉,就顺着泪水流淌出来。
胭脂一跺脚,“这个爸爸,生了这么重的病也不告诉我。”
“他就是因为生了这么重的病,才不愿意告诉你。胭脂,你要活得高高兴兴的,你土根爸爸在那边,才会安心。”
胭脂点了点头,说:“妈妈,不要改我的名字好吗?”回到徐家大沟三个多月了,胭脂第一次将“妈妈”喊了出来。
“不改。”胭脂妈一把搂过胭脂,擦着眼睛,哽咽道,“我们一个字都不改!”
回到学校后的胭脂,仿佛变了一个人,不再像一个月前那样郁烦,也不再觉得孤单。
三年高中生活忙碌而充实地成为过去式,就要去北京念大学的胭脂,去跟土根告别。
山洼洼里很安静,小小的胭脂花却不忘把动静闹大,这儿一丛那儿一簇的,怒放着,像天边,一片片娇美的云霞。
泊在团团紫红“云朵”中的那方坟墓,被打理得规规整整,干干净净。每到清明,胭脂妈都会到这里来转一转,坐上一坐。“铁疙瘩”对胭脂说,妈妈老喜欢跟土根伯伯说话,碎碎念念的,也不知道说的啥。
“你土根伯伯知道。”胭脂拍了拍“铁疙瘩”的肩膀,微微一笑。
是的,土根都会知道的。胭脂坐在坟前,不停地同土根说话,说话,笑着,流着泪。
太阳就要落到山的那一边去了,炊烟的味道飘了过来。
“好了,我得走了。”胭脂站了起来,“明年再来向你汇报哦,爸爸,我的土根爸爸。”
胭脂转身离开的时候,身后的胭脂花,在草间,在树旁,在石头的缝隙里,灼灼地,亮艳艳地,开呀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