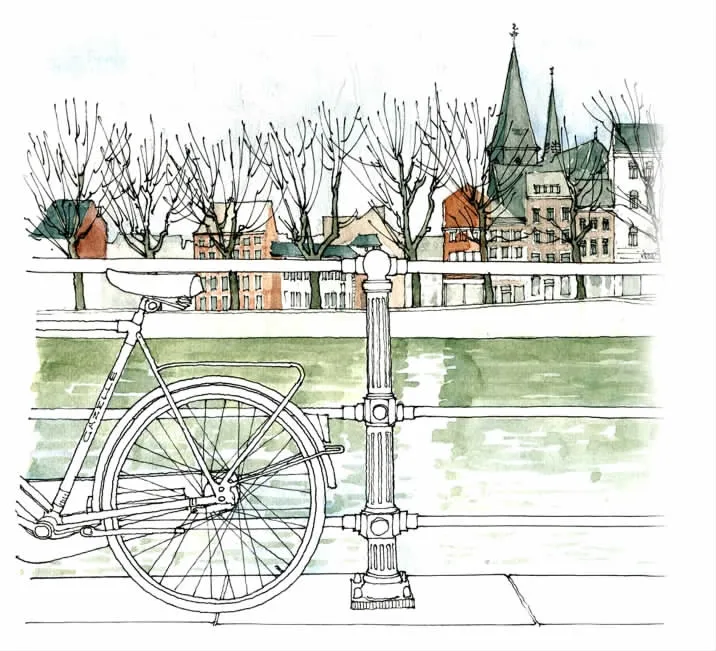
一
下了公共汽车,沿着河堤走约十来分钟,就能抵达诺婶入住的老人安养中心。这处外观纯白的安养中心得天独厚,依山傍水,取森林之精华而建。大门口正前方有一座直径约十二公尺的喷泉池,放养着一群白天鹅,视觉上给访客一种相当隆重的欢迎。四、五公尺高的水花在水池中央迎风飞舞着,天鹅们仿佛陷在一个圈套里,只能顺时钟绕着池边游移,一圈又一圈,浑然不知一条可以自由遨游的河道近在咫尺。
如果不说,单由外围的环境,会让人以为这是一处门禁森严的高级豪华度假中心,不但有会客接待室、图书馆、艺术展示馆、有氧健身房、三温暖蒸气室、森林花园步道等,还有严密的闭路监控系统,访客须先登记才能入内。
除了市中心区那栋宏伟的政府办公大楼外,素珍从来没有拜访过这么堂皇、讲究的地方。镶嵌着投射灯的百合白墙壁,营造出难以言喻的温暖氛围。古典音乐隐隐回荡在空间的每个角落,绿色盆栽错落有致,点缀在窗户两旁。她局促地坐等在会客室那张颜色梦幻、材质松软的沙发椅上,心想:相较于自己租住的那栋陈腐的老人公寓,诺婶应该会相当满意如此精雕细琢打造出来的居住环境。
素珍是在读书会认识诺婶的,参加的是一群退休的长者,而诺婶是义务的阅读指导老师,习惯推荐一些作者名不见经传、极其冷僻的书给会员。她认为,人类不应该辜负这些书的智慧和内涵,珍珠不会撒落在海床上,它们永远藏身在粗陋的贝叶中。唯有剥开贝叶,才见得着珍珠的光泽。她常说,书籍可以说是我们精神生活上的盾牌,有深度的阅读是达到自我肯定的一种方式。它能消弭生活所带来的耗损,抗衡内心那股深沉的恐惧和无助。
诺婶算是一个容貌相对美丽的老妇,她的美丽是经由内在的思想,透过言行举止表露出来的那种善意的美丽。她经常以一种饱满的特有笑声来表达她的感受,一身宽松、飘逸的淡雅长衫衣裤,是她对身躯自我解放的宣示。她有极其辉煌的生活经历,游历过上百个国家,会说多国语言,更是一位见广识多的古董鉴定专家。
入住安养中心之前,诺婶一个人住在一栋年久失修、带有前后院的大房子里,一栋包裹着太多回忆和内涵的古宅。她知道这样住是不符合比例原则的,但对一个年过七十且孤寡的老年人,任何的变动和迁居都是不堪的。但更确切地说,诺婶之所以难以离开古宅,是因为她始终割舍不去那些已经编织在自己生命中所有的美好回忆。
记不得丈夫是何时过世的,但诺婶清楚记得那是一个艳阳高照的早晨。前一天晚餐后,丈夫说,晚上他要赶写一份报告,不上床睡觉了。若累了,他会趴在书桌上小睡一会儿,再出门去送报告,别叫醒他。
这是丈夫最后的叮嘱:别叫醒他。丈夫说过,做完今年的研究就办退休,应该回归正常的生活了。
隔日一早,诺婶把为丈夫备妥的早餐放在书房的茶几上,就赶出门去。为了庆祝今晚她和丈夫三十周年结婚纪念日,她得出门带回一些鲜花和香槟酒。近午时刻回家,推开书房门,赫然发现茶几上那份早餐原封未动,她直觉意识到出事了。
“亲爱的——亲爱的,你还好吗?亲爱的——”诺婶震颤地声声呼唤着丈夫,但没得到任何回应,空气好似全被冻结在绝望中。
退回客厅,悲戚地跌坐在沙发椅上的诺婶打电话请来救护车。回想着早晨出门时的情景,望着趴在书桌上的丈夫,那疲惫的身影和均匀起伏的呼吸声让她深感不舍。轻轻为丈夫盖上保暖的毯子,她还低语:“亲爱的,我爱你……”
现在,书房里是一片密不通风的死寂,事情的发生已经远远超出了诺婶所能独自面对的局面。迅速赶来的医生宣告了丈夫的死亡,更叫人伤心欲绝的是,在一个理应被祝福的日子里,她失去了挚爱的丈夫。
死亡,因着不可逆的因素把丈夫给带走了,这变故正挑战着诺婶对生活的认知。从来不觉匮乏的她,今后是否她得独自迎来日出的朝阳,独自目送日落的余晖?独自面对壁炉里的火光,独自阅读每日的早报,独自散步于河堤步道上,独自啜饮餐前酒,独自拥枕入眠?独自……独自……独自……
丈夫于睡梦中如此泰然地接受自己的死亡,诺婶深信,丈夫必将梦醒于另外一个更趋完善的世界,那是不用出公差到远地、不用熬夜做研究、不用费尽心力赶报告、不用受困于难解的社会问题,一个理想国度。
生前少有病痛的丈夫,死亡报告的死因是“猝死”。丈夫未遂的心愿是“回归正常生活”,这就是人生。
遭逢生命中最为切痛的变故,也让身为古董鉴定专家的诺婶,重新有机会正视生命。原来,那些她花了大半辈子收购价值连城的古董,根本无法消弭她的丧夫之痛,根本无法填补她那如深渊般的孤独。
最后,诺婶出清了所有的珍贵收藏,独自凄然面对丈夫遗留下那好几面墙的藏书。奇迹般地从那堆她曾经很不以为然的藏书中,她终于找到了慰藉生命的密码。
最后几次出现在读书会,诺婶都是拄着拐杖来的,她笑称自己已经变成三只脚的稀有动物了。最近经常晕眩跌倒的她,家庭医生提醒她要做全身健检。其实,诺婶就怕这一天的到来。攸关生命之存危,她被医疗单位裁定强制入住老人医护安养中心。要改变多年来既有的生活轨迹,任谁都无法承受得起这种被剥夺的冲击。诺婶提出申诉,要求居家医疗照护,但她的病况不符合居家医疗条件,遭到拒绝。最后,她迫不得已卖掉古宅,申请入住郊区一家知名的老人医疗安养中心,素珍答应一定会去探望她。
二
退休后的素珍,目前栖身在政府补贴一半租金的老人公寓的一楼右侧边间。公寓相当老旧,老旧到租客必须放弃自身的优越感,克服难言的心理障碍才敢入住。屋外是一条市中心区人来人往、热闹非凡的大马路,但却无损屋内的阴冷和肃穆,无损屋内的贫乏和困顿。
从公寓的窗户往外望去,经常有一群野猫闲散地匍匐在屋外的墙头。一只瘦骨嶙峋的花猫意外地从开启的窗户误闯入屋,素珍趁机就收养下它。不,更精确地说,应该是那只花猫投靠了素珍,因为猫比人类更需要壁炉边的温暖。花猫不吵不闹,也不黏人,总是安静地待在角落,远远地观望着素珍,所以素珍管它叫 “距离”。
其实,花猫早就把素珍的生活看在眼里。主人的生活简直就像是一出一个人的独脚戏。它嗅闻不到一般家庭那种油腻、甜滞的氛围,那种人人渴求的亲密氛围,简直稀薄到宛若高原上的空气。除去外出,主人在家总是一个人很安静地读着书,一个人很优雅地听着音乐,或是忘我地望着窗外的车水马龙发呆。在这近乎透明的空虚中,没有人会刻意打扰她的存在。
说穿了,主人最大的嗜好是自言自语。那些呢喃听起来,像是一首诗,又像是一首歌。它常把主人想象成一串吊挂在旷野中的风铃,呼应着风的呼唤。它不会笨到去破坏这种平衡,或是傻到去缩短彼此的间距。它比主人更能享受这种疏离的生活模式。
物质世界中的素珍相形见绌,但在精神层面上,她是无限超脱的。她的经济相当拮据,但还没有拮据到让她活不下去。她的生活还算宽裕,但就是没有宽裕到让她可以去挥霍。她的智商颇高,高到可以把陌生人变成朋友,但却没高到可以把朋友变成知己。
素珍常说,生活上,有些事是不能主动期待,只能被动等待。似乎被动比主动更容易打发时间,更容易满足生活。有时候,生活就像是一首无法亵渎的诗,又有时候,生活更像是一团无法打理的乱麻。没有人能为生活设下停损点,没有人能为任何的意外背书,唯一能做的是紧握住心中那一份绝对的存在感。
私底下,素珍很少主动提及自己的过往,也很少主动讨论到自己的意愿。总之,她很少开口说话,就好像沉默是她天生的本能,寡言是她被赐予的天赋。一只花猫、一间陋室和些许私人物品是她仅有的,可以说她是一个极简的化外生活者。
她深知,无须借由外在的多寡来肯定自己的存在,这种存在感是来自于自我内在的感知。也许,自己的一生就此盖棺论定,既没波折,也无惊叹号,更不具传奇性。
生活上那些五颜六色的气球,终将消失于视野中,这时候就必须去珍惜停留在视觉上的那片空白,可以耕耘自己的那片空白,可以绝对自在的那片空白,可以窥视生活真相的那片空白。清空欲望,把自己还原于空白,闭上眼睛,把自己释放于想象中,让生活体验回归到最基本、最原始的感知。
像谜一样的素珍,拥有一个徜徉于时间外的灵魂。就在某一天早晨睁开眼睛醒来,她忽然发觉自己再也不用为工作赶早出门挤公共汽车,再也不用绞尽脑汁过日子。退休生活就好像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时间忽然多到用不完。如何打发这些莫名其妙就多出来的时间,素珍发现最经济也最实惠的方式就是阅读。从此,餐桌上总是摆着一本摊开的书,她也加入社区读书会,认识了诺婶,一位值得去倾听与交会的启发者。
三
工作人员笑容可掬趋近,带着素珍前去见诺婶。沿着打磨到已经发亮照人的鹅卵石走道,一路来到诺婶的房舍前,推开虚掩的门,诺婶已等候在里面。此时素珍眼中的诺婶看似整整瘦了一圈,那是一种对生活失去激情的消瘦。
“近一个月来,我还没读完过一本书。你就知道他们是如何在帮我打发时间,如何在忙碌于照顾我的健康。来,坐近一点,真高兴你能抽空来看我。”
“你瘦了!不习惯这里的伙食?”素珍边说,边靠近诺婶坐过去。
“是瘦了,我这样的体重正符合安养中心的要求。这里几乎是一对一的照顾规格,他们分分秒秒都在关注你血压、血糖的高低,关注你心跳、脉搏的快慢,关注你食欲、胃口的好坏,关注你体重、腹围的增减。他们竭尽全力在延长你的寿命,至于精神和心灵的状况、情感和个别的差异性,他们显然爱莫能助。工作人员始终维持着一贯职业性、没有温度的对话和互动,没有人愿意扮演上帝的牧羊人去探讨你的内心世界,去摸索你的性向好恶……”诺婶语意委婉地道出自己心中的疑惑和尴尬的处境。
“你是怎么来的?”递过来一杯热茶,诺婶问道。
“转了两趟公共汽车到终点站,再沿着河道步行过来。真没想到有这么一栋‘优美’的安养中心在市郊。”素珍把到嘴的“豪华”改成“优美”。
“‘美’的表面往往让人无法透视问题的核心……”诺婶尝试扩大解释她对安养中心的认知。她说,这里没有一个人是真心快乐的,就算有,也只能是大家为你唱唱“生日快乐歌”那种只能满足虚荣心的表层快乐。试想,扣除掉阿兹海默症和帕金森氏症,总的来说,只有百分之十的老人尚能行动自如。百分之三十是坐在轮椅上的,另外的百分之四十是靠辅助椅或拐杖行走的,其余是举步维艰,需要搀扶。还有半数是沉默寡言的重听者,半数是口齿不清的。更有为数不少的手抖症需要他人喂食,也有一些咀嚼不良的只能进流质,几乎百分之七十都须终日穿戴纸尿裤……
一旦观察到这些数据就会发现,在这拥有最多资源和关照的世外桃源,却是一个最充满无力感、最叫人绝望的世界。
避开素珍一脸胶着的表情,诺婶把头转向窗外的深秋,继续她那自觉式的剖析:中心的这群老人包含我在内,仿佛被置入一场实境秀,与社会连结的脐带被彻底切断。节目用最完善的制度和最先进的医疗设备来考验你对生命的态度,来耗尽你的尊严、来拖垮你的意志力。
最终,老人们封闭起自己敏锐的感官,不再有所坚持,完全放空自己,放弃我执,把自己退化回幼童的心智。就像是一群被圈养的家畜、一堆被置放在培养基里的活体,不在乎世局的变化、不在乎四季寒暑的更迭,抑或是天光的明或暗。老人们已经忘记自我的步履和自主的权利。妥协,就是妥协往往比拒绝更容易让人理解到你的存在。面对无法自主切换开关、无法自主拔掉插头的人生,老人们只能在记忆的残片中推进,倒数计时自己的日子。
望着窗外深秋瑟瑟的诺婶,忽然回过头来,淡定地对素珍说:“别怀疑,一开始你会喜欢过上这种养尊处优的生活。接着,你会强烈质疑这样的生活品质,然后,你又会全然无条件地接纳如此适切的安排。小心,一旦你顺应了,对生活就再难有兴奋、激动之情了。真的,生活就变得乏善可陈、一潭死水了,就好像你已经预先进入了一个没有风吹、日晒、雨淋的大坟场。”
“让我带你出去散散步吧!老实说,这中心只适合散步,不适合居住,房门就让它开着。”诺婶解释说,基于某种安全考量,房门是无法上锁的。医生、护士、清洁人员、义工,任何人敲个门,就可以进入你的房间,你无法拒绝这些打扰。在这里,任何角落你都无法安静待上半天,个人隐私是奢侈到没有存在的必要。
“其实对我而言,安静与独处和阳光一样重要,都是增进健康的要素。”诺婶怏怏不乐地说。
外出前,她们在大厅短暂停留,天花板挑高的大厅有一面收览全景的落地窗,正前方角落摆放着一架平台式钢琴,这是一个适合热闹的大厅。从落地窗往外,可以看到义工们正轮流带着长者在户外散步。几个轮椅上或闭目、或远眺的老人聚集在落地窗前晒太阳取暖,其中一位拿着笔在画素描,也有拿着报纸在玩填字游戏。
大厅正中央一张木制彩绘圆桌围着几位女士,埋头打理手上的毛织物,大厅右后方角落,一群老人也聚精会神地玩着纸牌。几位行动自如的长者沿着大厅走道,来回踱着方步,医护人员神采奕奕地穿梭在大厅中。
素珍发现,整个被阳光祝福的大厅听不到谈笑声,每个人都在专注着某一件事,某一件必须专注的事。
“很难以想象,这么美好的环境竟住着一群无法逾越围墙的人。安养中心没有围墙,这里不需要围墙,老人自身就是一道围墙,困在自己的身体里。”诺婶举目环顾四周,惆怅道:“我们回去吧!再走下去,就失去散步的意义了。”
“不用再来看我了,这里不是一个可以向往的地方。”在会客室里,诺婶眼眶湿润,依依不舍地和素珍道别。
四
素珍再一次去安养中心,是去领回诺婶指名留给她的一大箱书籍。她被告知,诺婶搬离安养中心,不知去向。诺婶最珍视的两本手边书:纪伯伦的《先知》和泰戈尔的《飞鸟集》也被留置在书箱里。显然,对离去的诺婶而言,任何一本书都已过于沉重。
“中心里的老人就像树下那堆落叶,真正需要的是一阵能够助其飞翔的飓风,而不是一场令其腐朽的骤雨……”这是当时在散步时,诺婶语带保留的一番话。
当时,素珍隐约领会到话里的意境。她也相信,诺婶最终能为自己找到一个向阳且迎风的落脚处。
“也许,生命最为完美的句点,就是能像落叶般随风翩然而去,不是吗?”踏出安养中心,愕然的素珍如此自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