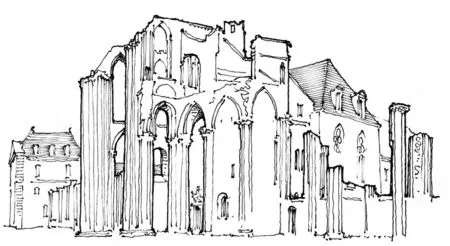
1
上了岸,机动船那哐哐哐的声音,便渐渐没了脾气。我和爸妈沿着菜地中间一条一米多宽的土路,向张姨家走去。
安静极了。除了阳光哗哗地泼洒在菜叶上,除了知了追着耳朵吱呀吱呀地扯着大锯,除了妈妈不时冷冰冰地叮嘱我,到了张姨家要记得喊人哈,要懂礼貌,听到没有?
菜地树少,没个遮阴的,而太阳虽至夏末,依然剽悍不减,我抹了把汗水,闷声闷气地应着。我素来不愿跟着爸妈串门子,尤其是,为了在以后两个学期的中午混口饭吃,而去串一个素不相识的门子。我讨厌在他们的安排下喊这个叔叔那个阿姨的,我言拙口钝,在大人们眼中是一个嘴巴极为不甜的人。妈妈为此很是不解,她说奶奶在我出生时,是拿蜂蜜抹了我嘴皮的。
妈妈以前同我说话不是这种语气的,尽管絮叨,可并不像现在这样跟吃了冰块似的。自从我落榜后,她声音里类似于吴侬软语的成份,就急不可待地撤退了。
是的,我是个落榜生,1988年的夏天,我连东安县城一所镇属中学的高中都没考上,更遑论东安中学了。常来我家走动的几个小伙伴,继续马驹子一样,在那个草原般宽广的省级重点中学纵意驰骋,撇下我,被爸爸的冷眼和妈妈的怨尤包围。
落榜是意料之中的事。一个除语文和历史外,上课要不就用一本小说,要不盯着窗外的树和树上的鸟就可打发一节课的人,一个睡觉时在被窝里用一支手电看金庸笑傲江湖,或是听琼瑶阿姨诉说“好心痛好心痛”的人,能考上高中?
落榜之后有两个选择,一是成为待业少年,参加待业青年岗前培训,半年后去某某工厂当工人,一是再去一所中学复读一年。我不想读书,只是,让人头痛的是数理化的书,我喜欢唐诗宋词,一颗被豪放大气、婉约纤巧的诗意浸润着的心,怎么愿意整天陷在机器的轰鸣声中,做一名满身油污的车间工人?
爸爸供职于县政府,按说为我联系一所学校也不是件太难的事,只是在部队里一呆二十几年的他,身板挺得跟营房前的白杨树一样直,转业到地方也有六七年了,照样秉持着非此即彼的观念,考上就读,考不上就不读,他可不会为了我,去走一条在他看来显然不合规矩的路。所以,东安县糖果厂硬糖车间工人宋英同志——就是我妈,拿一块甜得腻人的水果糖抹了抹嘴皮,请同事帮忙为我找了一所乡村中学,学校在青石坝村,与县城只隔着一条涪江河。
说起来仅一河之隔,但隔河千里,即便是枯水期河面搭了浮桥,从家里到学校,没有个把钟头也是不行的,更休提涨水期拆了浮桥,要过河就得看那机动船的脸色了,没有凑满一船人,就算望穿了河水,它也是不会作声的。乡村中学不上晚自习,这午饭在哪儿吃就成了个问题。
宋英同志眉头皱了老半天后,眼珠子一转,电光石火般一拍大腿,哎呀,我怎么把这个人给忘了呢?
这个人就是张姨。青石坝人,几年前,奶奶住院时和妈妈认识的,和青石坝的农民一样,在那片平坝地上种蔬菜。糖果厂就在县医院对门,妈妈每次熬了汤送去时,总会给同病房的张姨舀上几勺子。张姨为此感激不尽,她总说她运气好,虽然生了场病,却多了个姐姐。这以后,张姨在城里卖菜时,只要碰到妈妈,必拿起一把菜往妈妈手里塞,若是推脱,定会急红了眼,吵架一般高声嚷嚷。
既然想到了张姨家这个可让我吃上午饭的地方,妈妈就喊上爸爸和我,拎着些糕点,过了河,再趟过菜地,去张姨家。
在走过一段平坦路后,那条土路就开始拽着我像绑了沙袋的腿,一直往上走。这条路怎么这样长嘛!我嘟哝着。古诗说“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却好像走了二三十里,才看到青砖瓦房子,倒不止四五家,连成片的。
古诗又说“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亭台是决计没有的,谷草绑成的草树倒是有六七棵。但是,我看到了花,红红粉粉的一片,从一堵院墙上倾泄成一道花的瀑布。
我一下就冲到了爸妈的前面,从小路左侧下得几步石阶,就到了那道花瀑前,也到了张姨家。
是蔷薇花,我们管它叫月月红。那么美,绯红、浅粉,宛如粲然的笑脸,亮匝匝的,晃花了我的眼。又那么多,密密麻麻,挤挤搡搡,总有成百上千朵吧,阳光下,静静地流淌,静静地喷溅着浓郁的花香。
乡村不缺花,不过开在地里的是菜花,开在山坡上的是野花,堂前屋后的,是桃树李树们开出的花,在家门前看到这成片的鲜花,算是头一回。我微张着嘴,目光呆傻地盯着那道蔷薇花瀑布。谁若递给我一本金庸或琼瑶的小说时,我就会露出这样的表情。
我顽劣异常,与很多女孩子不一样,比如打死也不肯认一句错,不肯抛洒一颗泪珠子因此讨来爸妈更为酣畅的饱打;比如迟到了没喊报告进了教室,老师叫重新来过,正为上节课看小说被班主任训话而一肚子气,便摔门而去,将一节数学课拱手让给东安中学那片无穷碧的荷塘。不过,我也和很多女孩子一样,喜欢花,特别是蔷薇科的花,玫瑰、月季、蔷薇,便是那野山坡上的野刺玫,也可轻易就将一颗老是昂着的头给按下来。
香花多半不好看,好看的花又多半不香,但这些玫瑰啊月季啊,又香又好看,所以只得生出密密的刺来,以便保护自己。直到现在,若遇见它们,还会心想着身上要有把剪刀就好了,也好偷偷剪下一两枝来。
2
哎呀,宋姐姐来了,快进来坐,快进来坐。一个农妇模样的人,急冲冲地从一幢青瓦房里走出来,一双眼睛里,全是闪闪的惊喜。见我傻乎乎地盯着些那蔷薇花,就笑嘻嘻地说,那是我栽的月月红,疯起长,把一堵墙都铺满了,喜欢就摘哈,多得很。又喊,外头热,快进屋里坐。
这是张姨。妈妈说,并暗示着深深地瞄了我一眼。
说实话,张姨长得不好看,脸黑黑的,眉毛粗粗的,嘴巴厚厚的,然而她嘴边的两个酒窝非常好看,圆圆的,恰似两盏微型酒杯,装满了迎客的酒。张姨一直笑着,那两盏酒窝就一直跳跃着。于是,排斥、戒备、羞怯,种种情绪都悄悄退到了一边去。
我口齿清晰地喊了一声张姨,绝不像以前爸妈说,招呼个人要吃多大个亏似的,像墨墨蚊(蠓虫)在哼哼。
张姨的丈夫周叔当过几年兵,复员后在一家工厂当工人。常听大人们说,一工一农永远不穷,张姨家的日子过得不比城里人差。周叔一看就是个憨厚人,微笑着,不大说话,偶尔说上几句还得把手不停地搓着。
张姨有两个孩子,大儿子周强,比我大两岁,跟周叔一样不多言不多语,小儿子周勇,小我一岁,但低我两个级,上初二。周勇的长相随周叔,白白的,眉目清秀。暗想那双眼睛要是生在我脸上就好了,圆溜溜的,又大又双,偏偏长在一个男孩子的脸上。性格却像张姨,外向,爱说爱笑。正在变声期,那声音,跟正在学打鸣的小公鸡一样,难听死了。
易爱军。周强在知道我的名字后,皱着眉头,喃喃道。然后摇着头,说,你这名字不好听,像个男生吔。
纵然我素来不喜欢解放军爸爸给起的这名儿,太不好听,一点不像女生的名字,可是只能我自己不喜欢。我把头一抬,使劲剜了他一眼,说,我觉得好听就可以了!
周勇,你都14岁了,还这么不懂事,快点喊姐姐!张姨也剜他一眼。
周勇嘴一咧,我才不叫她姐姐呢,她看着比我还小些。
过了一会儿,周勇又问我,易爱军,你爱看书不?
那当然。
嘿,我也喜欢,你喜欢看谁的书?
琼瑶。我一字一顿道。我本来是不愿对别人说起这个作家的,不好意思嘛,一天谈情说爱的,可不知怎的,好像置气似的,我偏就要对周勇说出来。
真没劲,你们女生怎么都爱看这个。
还有金庸。我又把头一抬。
哈,我最喜欢金庸了!周勇的眼睛一下子金光闪亮,我看过《射雕英雄传》,上下集看完了的。
这样啊。我冷冷一笑,那《天龙八部》《雪山飞狐》《倚天屠龙记》《书剑恩仇录》,你看过没有?我摇晃着脑袋,吐枇杷籽一样倒出金庸小说来,每说出一部,周勇就会倒吸一口气,眼睛也会配合着亮一下。停了会儿,我一个浅浅的微笑递了过去,还有梁羽生和古龙的,你看过没有?
周勇摇了摇头,有些沮丧,我只看过《射雕英雄传》,易爱军,你在哪儿看得到这么多书哦?
我有图书馆的借书证啊!我挑着眉,胜利的笑容再也憋不住,哗哗地全溢出来了。周勇凑了过来,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像搁在我脸上,可不可以也借我看一下嘛?我带你到河边捉螃蟹,网虾米。
这个交换条件听起来着实诱人,只恨不得现在就能把书交到他手上。看来周勇这小子也不是太让人讨厌。
我与周勇叽叽歪歪地说着,张姨和妈妈更有聊不完的话,听她们说,瞧这两个人,一见面就这么多话,活像老早以前就认识的。
张姨家还有个老外婆,七十多岁了,眉眼里聚满了慈爱。她迈着一对尖尖小脚,碎步碎步走到我面前,拉着我的手说,这个姑娘才生得乖巧哦。就这句话,让我激动得眼泪都快蹦出来了,好像从小到大,只听人说我和男孩子一样调皮,生得也像个男孩子,蛮拽拽的,没谁说过生得乖巧的。我从未见过我的外婆,真想和周强、周勇一样,叫面前这个小脚老太太为外婆,而不是妈妈说的,这是张婆婆。外婆挽着个发髻,白白净净的,眉眼也清秀,年轻时准像个坐在绣楼里做女红的小姐。
妈妈说明了来意,张姨连声道,要得,要得,就怕你们不愿来呢。妈妈拿出钱来,要张姨收下,张姨受了惊吓似的,一退老远。她瞪着眼,笑容也瞬间不见,她说要是再提钱的事,就不再认她这个姐姐。
坐了一会儿后,泡菜烧鱼的味道袭击了我的鼻子,香得我一连打了好几个喷嚏。不多时,老外婆就往桌子上摆碗筷了,一大桌,几样小菜不消说,都是现从菜地里采摘回来的,只说那碗红烧鲫鱼和一盘泡椒鸭胗子,咸鲜香辣,很多年以后,仍然勾着我的味觉。张姨说,这鱼是当门大河里的,鸭胗子是坝上做鸡鸭生意人家的货,新鲜得很。妈妈瞅了我一眼,说,我这个女儿就是个属猫的,爱吃腥味东西。话未落地,张姨和外婆就在我的碗里堆出一座小山来。
3
九月,我的初四生活开始了。
学校因为位于青石坝村而被称作青石坝中学,虽然对接受这所乡村中学作好了很充分的思想准备,可走进去一看,才发现我的思想准备很不充分。
严格说不能是走进去,而是走过去,没有校门的嘛。一间教室,其实也就一间石头垒成的破瓦房,低矮、破旧,孤零零地蜷缩在一面缓坡之上,一条碎石子路之旁。这间教室便是青石坝中学的初三,初三也就这一个班。初一、初二在坡下,或者是有校门的,谁知道呢?
教室黑咕隆咚,但伸出手来还是看得到五指的,有窗子嘛,极小,挂着被风扯成绺绺的布帘子。其实说是几个黑洞或者更准确。我在打量这几个小黑洞时,情不自禁地发出了铜铃般的笑声,因为我突然想起了课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书塾中传出来的那一句“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
四十来张课桌,有木头的,也有石头的,仿佛专为小学低年级学生量身订做,矮小得不像话,且缺胳膊少腿的,在绳子和木棍的支撑下,异常艰难地度日。
更加难以忍受的是,厕所在教室旁边一户农家的猪圈里,人怎么能去霸占猪的领地呢?所以,那滴嗒着泔水的长长的猪筒子,就会从烂兮兮、黑乎乎的木格子里钻出来,在人的屁股后面不满地哼哼。毫无例外,上一次“厕所”,就会惊恐万状地犯一回心脏病。
我的思想准备一次次被青石坝中学迎面痛击,以致土崩瓦解。
面目严肃的语文老师,在讲解岑参诗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的一句 “风掣红旗冻不翻”时,一字一顿道,边关的风太大了,所以红旗就翻动得非常厉害,所以看上去就跟没有动一样。在东安中学当了几年语文课代表的我,真想站起来啊,真想指着老师的脸,狂笑三声。不过我也只是想想而已,我低下脑袋,手抵额头以示拒听。语文老师非常尽职,他认为,很有必要提醒一下这个在老师授业时坐飞机的留级生,便努力用幽默轻松的语气道,这位同学,你是想举手发言呢,还是在摸你的鼻子耍啊?静默如冬夜的教室,立刻哗啦啦地,响起了春水般的欢笑声。
4
酝酿了很久的眼泪,并未掉下来。
还没走下小路侧边的台阶,院墙上,那道蔷薇花瀑布已奔涌而来,我一口气跑了过去,我可不像有的女孩子,动不动就哭哭啼啼。我怎么会哭呢?周勇那小子又该说我真没劲了,他本来就爱说我,易爱军,那些花花草草到底有什么看事啊,你怎么一天都盯着看呢?真没劲!
老外婆也迈着她那对小脚,碎步碎步打花瀑前走过。她常常对乡邻们说,我们家来的这个姑娘,最喜欢这些月月红了。可她还忘了对乡邻说,我们家来的这个姑娘,最喜欢吃我煮的红烧小鲫鱼了。
本姑娘也最喜欢看老外婆烧鱼了。烧鱼前先得把泡菜和豆瓣酱一起炒香,灶火熊熊,热烟滚滚,老外婆眯缝着眼睛,掺水,水涨后将鱼一条条丢进锅中,有的还摇着尾巴跳呢,外婆赶紧拿锅铲摁住,盖上锅盖,随那锅中噗噜噗噜地唱歌去。十来分钟后,揭开锅盖,切几棵香菜撒下去,那个香,只怕河对门都闻得到。
对了,我长这么大,头一回在青石坝与苤蓝相遇,比大头菜圆,长得也更好看,不像大头菜满脸的皱纹。口感特别好,脆脆的,炒肉或是凉拌都好吃。张姨和外婆都对我说,爱军,喜欢吃就多吃点哈,我们蔬菜大队没别的,就是不缺菜吃。说着说着就让我的碗冒了尖。
外婆弄的这几样菜就是好吃,饭都要多吃些,可是我只在张姨家吃了三个月的午饭,就当了逃兵。
那天中午,我在里屋写作业等饭吃的时候,周勇端着一把仿真玩具冲锋枪,“哒哒哒”地冲了进来,把我吓得一声尖叫。那家伙仰头大笑,眉毛都飞到了半空里。我“啪”的一下,把笔往本子上一拍,周勇你是不是发疯了啊?
周勇也不理会,说,易爱军,我叔叔送了把冲锋枪给我,你扣动板机就会有各种声音,你试一下嘛。他眯着一只眼睛瞄着那枪,不住口地发出“嘭嘭嘭”的声音。
一把粗糙的破玩具枪也能高兴成这样,本人十年前就在军营里看过手枪步枪了,一种浅薄的优越感油然而起,我接过周勇递过来的枪,敷衍地按了按板机后就还给了他。
不想那枪在回到主人的手中时,竟纯属巧合地成了哑巴。周勇捣鼓着那把破枪,声音里明显有了不耐,哎呀,你怎么回事哦易爱军,枪都不响了。
那一瞬间,我双眼圆瞪,脸涨得通红,我说不出话来,也不想说,只是喘着粗气,一动不动地看着他。
估计我眼中的怒火烧伤了那小子,他的脑袋就那么一抬:
易爱军你想怎样,像个母老虎,难不成你还想吃人啊?不过你得问问它答不答应!
周勇说着将拳头扬了扬,鄙夷地扫了我一眼后,转身走了。
我愣愣地站着,像被施了定身法。是,你妈妈收容了我在你家吃午饭,但你不能因为这个,就可以在我面前骄纵耍横!怔了片刻工夫,我从作业本上扯下一页纸来,像从前与同学闹矛盾后写绝交信一样,刷刷刷,几笔写下本人的严正申明:
一、我承认看过你的冲锋枪,但这是应你的请求,与我无关!
二、我承认冲锋枪在回到你手上后哑巴了,但这是它自身的原因,与我无关!
三、我承认在我你家吃白食了,但这是我妈和你妈之间的事情,与我无关!
四、从此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再不相干!!!
写好后,拿个墨水瓶压在桌子上。本想从后门走,可走后门须得经过灶屋,灶屋里,锅坐旺火上,老外婆正在用滚油炒豆瓣酱和泡菜,一会儿要烧小鲫鱼。涪江河里的小鲫鱼,那么鲜,又那么辣,呛得我的眼泪直想往外冲。
泪水憋在眼眶里,人往门外冲,眼角的余光被一天天凋谢的蔷薇花绊了一下后,那道忧伤的红色花瀑就迅速消失在我的身后。
冬日里,河风低吼着,寒意袭人,我本来应该像一只寒号鸟那样,缩着脖子哆哆嗦嗦,但我努力地昂着头,作悲壮相,大踏步向前走。
过了浮桥,我直奔码头边的食杂店,买了两个肉包子,没水喝,饿急了也管不了那许多,几口囫囵吞下。回教室后,同学告诉我,张姨来找过我,并加重了语气说,是一瘸一拐走来的。
是走到路上的时候崴了脚,还是摔了跤?我心中有些不安,慌慌的。下午一放学,我就幽灵一般潜行到张姨家后门外,周勇小公鸡学打鸣的声音,却又忽高忽低地撞着耳朵,便贼似的闪人了。
5
从张姨家撤退,上哪儿吃饭去又成了问题,不过,我很快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班上有两个女同学,都是外村人,其中一位的亲戚在青石坝村有一间闲置的房子,两人中午就在那里煮面吃,我找到她们,参了一股。
一株不知有几百岁的黄葛树旁,一间竹篾编的泥巴糊的房子探出头来,只小小的一间,空荡荡的,晦暗、衰朽、颓败,像残年的老人,颤颤巍巍,鬓毛衰,满面尘灰。
一个小柴火炉,一口补巴重补巴的铁锅,一把干面,大半茶盅加了盐巴的油辣子,三个女生用它们来加工午餐。面煮好了,却没桌子可安放,只能端在手中。这碗面,没几滴油水,有盐无味,一股干辣干辣的味道在嘴巴里左冲右突,说真的,极不挑食的我,也是想着红军在二万五千里长征时吃野菜、啃皮带,才顽强地将一碗面吃完的。
家中有几瓶富顺香辣酱,那个香辣味,单闻着都不知今夕何夕,是爸爸到富顺县出差时买回的,除了吃面,一般都舍不得拿来吃的。我对妈妈说给张姨带一瓶去,妈妈一双丹凤眼都笑成了一条线,直夸我懂事了。
中午煮了面,各自把那香辣酱挑得一点在碗里,拌了吃。三碗面,风卷残云般被消灭。那二位同学,咂吧着嘴回味,只怪我没有早些入伙。
午餐的问题算是解决了,可每天早晚经过张姨家又成了问题,张姨家那座青瓦房子在那条土路侧面,路过那一段时,我总是一溜儿小跑,绝不斜视,我怕那一挂蔷薇花瀑布前,会突然出现一对酒窝,或是两只小脚,或是,像小公鸡学打鸣的声音。
妈妈是去张姨家才知道这事的。张姨一个劲给我妈道歉,弄得她的宋姐姐好生过意不去。妈妈回家说起这事的时候,我竖起了耳朵,从妈妈的话里,去捕捉关于张姨那只脚的讯息,还好,妈妈并没提起,想来应该没事了。这才暗暗松了口气。
妈妈还带回一个笔记本,新的,塑料封皮,是我喜欢的蓝颜色,是周勇送给我的,这已经够让我无法相信了,却还有更令人觉得诧异的,扉页上有字,我瞪大了眼睛看那几行字——易爱军:你一定会成为一名作家或诗人。周勇赠。1986年10月1日。看日期是在我离开张姨家之前了。再一翻,那本子里,竟然还夹着几枚蔷薇花瓣,虽已干枯,仍暗香残留。心跳有点快,鼻子又忽地有点酸,赶紧来了一串假咳嗽,掩着嘴巴,别过头去。
妈妈呵呵地笑,说没想到周勇这个娃娃还挺细心的,知道我平时爱记日记,放国庆假时就买了一个,不过又没有机会给我。我哼了一声,心想这家伙真笨,找个理由都不会。
张姨还让你原谅周勇,说他不懂事。你看你这孩子,让妈妈都不好意思了。妈妈责怪道。
我才不原谅他呢。我眼睛一斜,不料斜过去的时候,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却出现在眼前,像阳光下的涪江河,闪呀闪的。
妈妈还说,张姨和外婆让她一定给我讲,还上家里来吃饭。妈妈要她们别管我,她说,我这个女儿我晓得,就是个犟拐拐,德性怪得很。
我无比赞同妈妈的晓得,就像我无比赞同东安中学的同学们,商量好了似的,把没有二十个,也有十九个的“古怪”“任性”这俩词,留在了我的毕业留言本上。
尽管我多么想每天都能够看看蔷薇花瀑布,能够隔三差五地,吃一回红烧小鲫鱼或泡椒炒鸭胗,可我仍然坚持着,在一间破朽不堪的小黑屋里,将一碗干辣干辣的干面吃到了上学期结束。
女儿如此草率地对付自己的午餐,作为母亲终是不落忍,东安糖果厂工人宋英同志,又踏上了东奔西走的求人征程。她抹下面子,再度用抹了水果糖的嘴巴给人说好话,终于托得一老街坊,那街坊又托了拐弯抹角的关系,总算为我在县城的一所镇属中学里谋得一张课桌。
9月里,我唱着电视剧《济公》中的“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甲甲(污垢)多”,到市里的一所技工学校报到。技工学校,一听这名儿就头大,跟周勇爱说的那句话一个模样:真没劲。
第一次离家在外,想家想得厉害,东安县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构筑成的天地里,关于青石坝的种种也不时顽强地挤进来。包括周勇。他也该上初三了,也会坐在半山坡上那间孤单单的破烂教室里了,他会遇到那个另类解读《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的语文老师吗?同样是一名语文科代表,不知他是否也会在语文课上,手抵额头,像是要举手发言,又像是摸着自己的鼻子耍?
就这么老在心里想着,憋得慌,便到学校的小卖部买来信笺纸,一口气写了两页纸。在问过周勇,以及张姨和老外婆后,我问起他家那片蔷薇,写到这里,那一道红的粉的花瀑,就哗啦啦地流淌于眼前。我不知道,周勇在路过那些红的粉的花儿时,会不会看见,一个梳着马尾巴的女生,正安静地站在花瀑前?不过是这么一想罢了,并未写到信纸上,脸颊却如同着了火,呼呼燃烧起来。
信写好了,却想,易爱军,你怎么能主动给一个男生写信呢?并且你还气势汹汹地给他发过一个严正声明。于是,这封信来得快去得也快,它在我的手中化成一群白色的蝶,盘旋复盘旋,最终消散。
空落的日子很快被来自市内各区县的同学填补。技工学校要管分配,所以安心地翻着小说,一两周就会与同学溜出学校去,逛街、看电影,三年技校时光一晃而过。
6
毕业之后,我满身油污地和闹哄哄的机器打了三年交道,之后考进一家报社,做了一名文字编辑,尽管没有成为周勇所说的作家或诗人,但没事也喜欢涂鸦几句,算是和文字有了缘分。
有时会在电话里说起张姨。
以前听妈妈说,张姨还跟多年前一样,在街上卖菜遇上了,依旧会吵架似的,把菜往她手上塞。
也不动声色地提到过周勇。说真的,我有点想不通,这小子平时对学习并不上心,加上又是那样的一所学校,但那一年,从那间石头房子里考上高中的学生,他却是唯一的一个,也在我读过一学期的镇中。高中毕业后,大学,报社,和我做着相同的工作。
妈妈见过两次周勇,一次是在张姨的六十岁生日宴上,妈妈说他长得人高马大的,精神得很,嘴巴也甜,见了她,宋姨宋姨地喊着。
妈妈说,周勇和你一样,也喜欢写东西,还写了书呢!她从张姨家带回周勇的书,是一部短篇小说集。
十几个短篇,其中一篇的题目,猛地攫住了我的眼球——《蔷薇花瀑》。这个当年声称看花花草草真没劲的人,细腻、深情而又有些忧伤地写花,写花一样的年华。
小说中的女孩离开了她心心念念的蔷薇花,去了另一个学校,男孩很难过,可又不能告诉任何人,他只能站在院里的那片蔷薇花瀑前,暗暗发誓:我一定要考上那所学校。
娇美的花。一只正在学打鸣的小公鸡。这是一对什么样的组合?尽管泪珠早已倚着眼眶向外探路,依然忍不住扑哧一笑。
时光如流水,却总有一些东西带不走,譬如那道蔷薇花瀑,一直挂在他心间,不曾凋败——是《蔷薇花瀑》中的一句。这么些年,工作,结婚,生子,我以为,我的心早被那些大大小小的事情塞满,却在读着这句话时,发现面熟得,简直像是从我的心底给抄袭了去。
回家看到的这本小说集,返程时,悄悄放进了行李箱里。
妈妈还见过一次周勇,是在老外婆的丧礼上。老外婆已近百岁,可谓喜丧,我的眼睛却在揭开那些旧事的封条时,渐渐迷濛。
几年后,周叔因病离世,大儿子周强便将张姨接到县城。张姨从此离开了青石坝。
7
我再一次走进青石坝的时候,当初那个走在菜地里,拉着一张长马脸的十五岁女孩,如今,已有了一个十五岁的女孩。
四月天,万物都复苏了,但青石坝上的泥土,泥土之上的莴笋、萝卜、大白菜……再也醒不过来。
我不知道为啥还会来到青石坝,在明知这个坝已不是当年的那个坝后,我的双腿依然顺着当年的线路踏上了青石坝。更准确一点说,也并非完全是当年线路,没有坐机动船,一座气势如虹的斜拉桥取代了浮桥与哐哐哐拍着耳朵的机动船。也无需踩着菜地中间那条一米多宽的土路,多年以前,那条我抱怨着老看不到尽头的土路,也终于被光阴抛到了尽头。
春日的下午,阳光很好,耀着人的眼,当然,也仅仅是耀着人的眼,你即便支楞起耳朵,也绝对听不到它们泼洒在菜叶上的声音。你最多能够听到,阳光与车流、与楼厦、与商铺中一个更比一个亢奋的音响互相碰撞所发出的声音。
不错,在这里,蔬菜已无立锥之地。
青石坝现在已不叫青石坝,它成功地融入了城市,并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很洋气。在纵横交错的楼群里走走停停的那个人,变化同样很大,但跟从前一样爱唱歌,这时候正顺手捡起一首老歌哼唱: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
这个地方曾经出产蔬菜,绿油油的扑你个满身满脸,如今出产楼房了,一座座你追我赶的,拔地而起,又冲天而去。
无边无际的楼群。我仰起头来,脖子酸,眼睛花。
在无边无际的楼群里,我数度像个迷路的小孩。
虽已面目全非,虽已有了一个更漂亮的名字,我仍然固执地称呼青石坝为青石坝。就算是,在这个叫青石坝的地方,我再也看不到张姨家那栋青砖瓦房,以及,我从未向人提起过的,那一道静静流淌的蔷薇花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