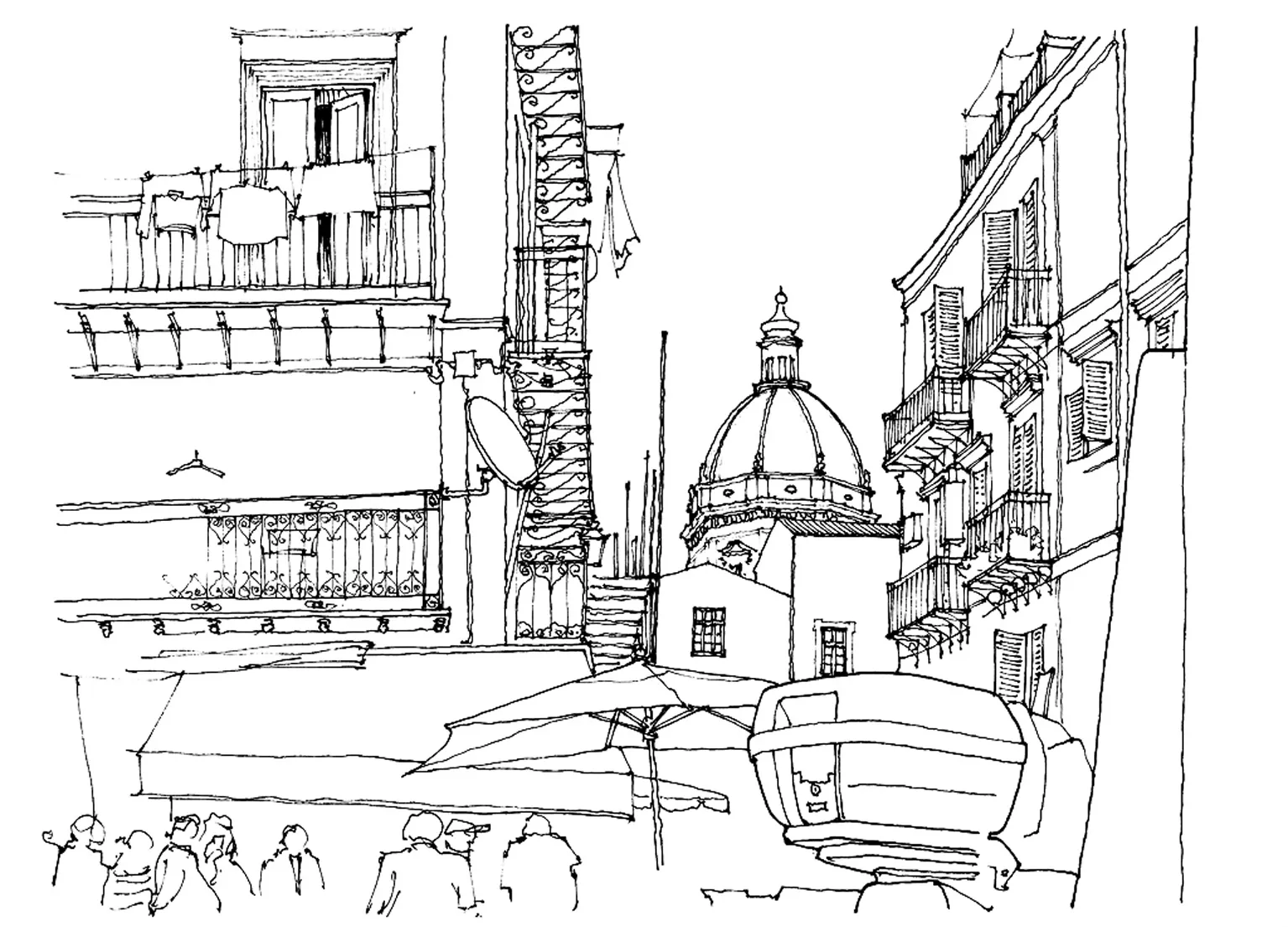
一抹斜阳落在绣着金丝花鸟的大红棉被上,小国弓着身子,鼻子贴近被头的粗土布,觉得自己正靠近一汪煤火,火堆上是萌动的一壶水。一只锈黑的铝水壶,壶盖上搭着两只微潮的条纹袜,正冒着若有若无的热气。小国缩进被窝,在黑暗里试图看清炉旁的景象,可通红的火光将他的泪灼得发烫。
房间外有人说话,然后是干咳,接着有人下楼,踩着磨光的水泥楼梯;旅客在楼下的柜台前似乎在敲击着台面,老板娘热情招呼的声音异常清脆。下午,离吃晚饭还早,小国低声对自己说。从看守所的小路上,走来一个背着军绿色大包的人,他在水泥路上快步走了几分钟,来到砂石路,靠着第一棵尚未成年的梧桐树歇了一会儿,平息喘着粗气的肺部。那是我,小国难过地对自己说,这个可怜虫就是我,我是一个无家可归的蠢货,一个顶着光脑袋,脸上写着“贼”的王八蛋!
隔壁房间的门开了,然后轻轻关上,没有反锁。一个男人在房间里卸下沉重的包袱,从包袱里掏出叮铃咣啷的一堆瓶瓶罐罐,小国听得真真切切。探视犯人的?和我一样刑满释放的混蛋?小国将头更深地缩进散发棉花香味的被窝,就这样打了个盹。
小国掀开被子,迅速起身,以便驱走围绕着自己的寒气。夕阳在窗玻璃右上角投来一块亮红色的光圈,旅馆正对着的街道左边那排平房瓦顶被抹上一层金黄色的晕,右侧那排楼房挡住了太阳和晚霞的大部分,留出云彩灰色的毛茸茸的尾巴。室外街道上购物的、下班的和闲谈的人们,制造出几分喧闹的声音,从窗缝、门缝传向小国的耳膜。小国分辨着这些声音,试图理解这些声音的含义。一定有两个相识的人在街头相遇,说着寒暄的话;其中一个推着自行车,一个则骑在电瓶车上;旁边有一个菜贩子在刮鱼鳞,嚯嚯声明白无误。
下了楼,旅馆大堂里没有人,柜台上摆着一本旅客登记表,旁边是一盆水仙花,肥厚的叶子在光影里绿得通透。站在走廊上,小国看到露天菜场正是热闹时分,一个管教干事的老婆正蹲在菜摊前挑挑拣拣,他忙扭过头,穿过水泥路来到对面的小卖部。店老板是个精瘦的中年人,正抓着一张报纸喃喃自语,见小国踱步进来,并不觉得奇怪,热情招呼说:“买点什么,来一包香烟?”小国默不作声低头看玻璃柜里的各种香烟,摇摇头说:“不抽了。”老板从柜台上的烟盒里抽出两根香烟递给小国一根,替他打着火说:“兄弟,刚出来?”小国接过香烟笨拙地凑上打火机的火苗轻轻吸了一口,烟没有点着,又凑到火苗上用力吸了一口,一股辛辣的气味直冲上颚,小国皱了皱眉头,强行将烟从鼻孔喷出去。店老板善解人意地笑了,鼻涕差点儿流了出来。每个月都有几个茫然失措的刑满释放犯在小镇的街头游荡,然后重新学会吸烟和喝酒,再踏上前途未卜的征途;有时候,这些剃着光头眼神空洞的无人收留的汉子,会将包里的全部家当抵押,换来几天酩酊大醉,再踉踉跄跄地消失在露天菜场的尽头,融入柏油马路的树影里。
小国摸索着口袋,里面有几张百元大钞,他不知道自己需要买什么,茫然看着货架上花花绿绿的货品。他最熟悉的是方便面和饮料,这是他在监狱超市最常买的物品。可这个货架上的各色饮料,有很多他没有见过,不由地研究了很长时间。监狱超市的大个子售货员老穆和他道别时嚷道:活出人样,好兄弟!小国苦笑一声,烟灰扑簌簌跌在深灰色夹克衫的前胸。
“兄弟,晚上到这里吃饭,喝一杯。”耳后是店老板热情的声音。小国举了举手,不知道是同意还是拒绝。他走出小店,向横街西头走去,响着音乐的店铺吸引了他的注意,他停下来向里面张望。挂满广告牌的店里,沿墙排列着方头方脑的电器,有一台紫红色的柜式空调外壳上喷着一朵巨大的花儿,仿佛在大口喘气,显得非常怪异;音乐声大了起来,音响似乎放在一只不稳当的木箱子上,发出刺耳的震动声,时不时会吱啦一声。我还是喜欢放风时的大喇叭,音乐嘈杂,分辨不出到底有几个人在里面哼唱。主唱的口齿不清,有三四个人伴着和音,“呼哈”、“哎呦”乱作一团。这不是打群架的声音吗,小国苦笑了。老板和伙计们,或许正躲在那个巨大的白色冰柜里发抖吧。
小国这才发现自己傻傻地站在店门的门槛中间,忙缩了回来。我这样鬼鬼祟祟地,被人发现了肯定要讨打。他耸耸肩,驱散暗沉光线中的寒气,向横街更深处走去。走了百来米远,水泥路戛然而止,眼前是一条土路,坚硬的土路尽头掩映在斑蝥草丛中;路两边的田地裸露着灰黄色的胸膛,被田埂分割成大块小块;田埂上的枯草被淘气的孩子烧过,到处是烧黑的痕迹。小国对着野地看了一会儿,转身返回。
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坐在水泥路边平房门口的小凳子上,双手捧着一只蓝边碗,扭着扎着辫子的小脑袋和身旁的一只花母鸡说话,竹编的鸡笼就在不远处的窗台下,笼子没有门,笼子里的那只土黄色的小母鸡正探头探脑地看着小女孩。小国停在离小女孩几步远的地方,想看清楚女孩碗里的东西,可看不太清,白白的,也许是冬瓜。转念想,这个季节不会有冬瓜的,难道是肥肉?也不会,监狱里都很少有纯肥肉了。每当周六加餐,两块肥肉上总会粘着一指厚的瘦肉。从女孩捧碗的姿势看,这碗汤并不烫,也许已经凉了,看不见热气。小国看了看四周,走近一步对小女孩说:“你怎么不吃啊,冷掉了。”说完不由得咽了一口唾沫,这才觉得自己真的有些饿了。隐约可以闻到一丝肉香,可碗中没有看到肉的迹象——白花花的“冬瓜”沉在碗底,几段小葱飘在厚厚的油水上,和油水凝成薄薄的面皮。小女孩看了小国一眼,眼珠像两颗小黑豆,她细声细气地回道:“没有冷呢。”为了证明自己说的话,她弯着可爱的脖子凑到碗边喝了起来,粉红的小嘴吧嗒着,显得有滋有味。“冷了,我说的不会错……”小国话没说完,从平房大门里走出一位穿着连帽棉衣的女人,她看了小国一眼,催促道:“丫头,还不快喝,就等你了。凉了吧……”小女孩哦了一声,一边低头喝着汤,一边抽出压在右腿下的筷子,扒拉着碗里的“冬瓜”。女人摸了一下小女孩的碗责怪道:“我说凉了,你还不信,给你再换一碗。”说完,女人端走小女孩的蓝边碗,进了屋子。小国心虚地缩了缩脖子,快步走开了。走了一段,小声问自己:“我还是贼吗?不是了吧,我已经被释放了。我被释放了,我干嘛还怕人家?贱。”他抽出裤袋里的双手,像风车一样大幅度转动着。这一刻,他觉得自己自由了,整条街都属于自己的。我可以随时走,坐上车,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明天就走,无论去哪里,去哪里都行。五年了,我终于要离开这个镇子,离开这个笼子,不是从长着芦苇的大湖游走,而是正大光明地从街上离开,走上在梦里反复出现的星光下的柏油路……可是,我要去哪里呢?
小国来到小卖部,店老板和一个头戴棒球帽的微胖中年人在柜台边的小方桌上喝酒,见小国在门口立刻招呼说:“兄弟,一起喝酒啊,等你好久了。”那个中年人似乎也知道小国的身分,端来一个小方凳搁在靠近门口的位置。小国坐到小方凳上问老板:“给多少钱?”店老板微微一笑说:“随你的便,十块八块都行。大男人怎么婆婆妈妈的呢?”小国默不作声,两只手夹在两腿之间盯着盘子里的葱爆牛肉。店老板给小国搛了几片牛肉,又倒了一杯大约三两的白酒给小国,盯着小国继续笑着说:“你叫什么名字?”“小国。”“好,小国,喝了这杯酒,大家就是朋友了。别瞎琢磨,我也是从牢里出来的,现在做正经生意。”店老板将酒杯端起放在小国手中。戴着棒球帽的中年人点点头也劝道:“喝了吧,有什么好愁的,应该高兴啊,都是朋友。”
小国疑惑地看着“棒球帽”问:“你也是刚出来的?”店老板哈哈一笑,和小国碰杯喝下,大声说道:“你觉得呢?吃菜。小国兄弟,这个镇子上有几个不是从里面出来的?”小国更加吃惊了,默默喝了一小口,追问:“老板,你的意思是这个镇上有很多从里面出来的?”脑海里闪出刚才在路上遇到的那个发广告单的年轻人,他和自己年纪相仿。
“棒球帽”喝得很快,喝干了杯中酒,又给自己倒了一杯。他一边吃着凉拌土豆丝,一边抽烟,抽空还会撮几颗花生米,忙得不亦乐乎;店老板不停调整着电火锅的按钮,火锅好半天没有沸腾,似乎电火锅出了毛病。小国想起旅店的老板娘,她也是从里面出来的?那是个保养得很富态的中年妇女,接待时热情得有些过分。小国敬了两个新朋友一杯,心里觉得敞亮了许多。原来和自己同样处境的人并不少,也不奇怪。刚进监狱头两年,父母兄弟以及朋友还来监狱看望自己,最后几年,他们就很少来探视了,尤其在被加刑两年半之后——自己和那个身上刺着一条眼镜蛇的家伙打了一架——再没有人来探视自己。小国偷眼看店老板和“棒球帽”的手腕处,没有看到刺青的痕迹,或许是藏在衣服里吧。火锅始终没有沸腾,店老板说:“这王八蛋的火锅,前天还行,今天坏了。凑合着吃吧,吃,吃,别发呆啊——”“棒球帽”紧接着说:“比牢里伙食好到天上去了,哈哈哈。”他被自己的幽默逗得大笑不止,筷子上的粉丝滑落到油迹斑斑的桌子上。“棒球帽”也不讲究,用手抓起桌上的粉丝塞进嘴里,还故意砸吧着嘴。
大家默默地喝了一会儿,店老板抬起头看着暗下来的屋外,起身点亮日光灯。回到桌边,他用平和的语气说:“小国啊,我也不问你是哪里人,以前干什么的。我那会儿见到你,觉得你不错。我这个兄弟也很不错,叫少华,你叫他华哥就行了。我,你就喊老郑。大家都是江湖上漂的人,不要见外。还有,你不要觉得我们要干什么坏事。什么人悔改了,什么人没悔改,我一眼就看得出来。”华哥连连点头,脱下棒球帽搁在玻璃柜台上。他的额头和两鬓已经冒汗了,光秃秃的前额亮晶晶地闪着白光。华哥说道:“我出来后遇到老郑,做他的伙计和司机,这些年,老郑没亏待我,我们虽然一个是老板,一个是伙计,但是老郑待我像兄弟一样。现在我日子过得挺舒坦。周末或者节假日,没有事的话,就去城里找小妹。”说完他对着小国眨眨眼,露出放荡的笑容。小国扫视了一下店内,又看了看老郑和华哥,突然觉得很温暖,肩头一紧,脖子和脸顿时发烫。他喝下杯中的残酒,脱口而出:“两位大哥肯收留我,我愿意跟着跑腿,什么活儿我都能干。只要……不违法。”老郑和华哥都笑了,老郑指着小国笑道:“坐牢坐怕了。”接着又补充道:“我和华哥都商量过了,如果你愿意跟着干,我们就将隔壁的门面租下来,弄个面馆,我做的面条是一绝,在里面的时候,中队长就爱吃我做的排骨面。我马上给你做一份尝尝。”说完老郑放下筷子,起身去了小厨房。小国和华哥又聊了几句,渐渐放心下来,知道这两位大哥都是正经人。
老郑端来了热腾腾的排骨面,小国尝了一口,味道确实不错,面筋道,排骨甜而不腻刚刚好。在这里安身,是个不错的选择,没有更好的了。小国吃完面条,想到自己的行李物品放在破旧的旅馆里,有些放心不下,况且在酒精的作用下,也的确想早点睡,便向老郑和华哥告辞,丢下一张百元大钞。老郑生气地大声说道:“小国,不把老哥当哥哥了吗?拿回去,以后一个锅里吃饭,还客套个屁啊。”小国只好说:“好吧,那么拿一条烟。”出了小卖部,吹来阵阵冷风,小国觉得身子很轻,脚步虽然有些摇晃,但他还能看清楚路上的坑坑洼洼,并没有磕着碰着。
在旅馆门口,小国看见水泥柱旁蹲着一个黑影,定睛细看,这个年轻人不正是自己下午遇见的发广告单的人吗?他从监狱外的小路走到镇头,第一个碰见的就是这个青年。当时这个年轻人突然往小国手里塞一张红通通的广告单,将低头走路的小国吓了一跳。年轻人说了声谢谢,继续向其他人发放。小国这才仔细看了一下广告单,里面印着各种空调和微波炉、电磁炉的介绍以及价码。“莫名其妙。”小国咕哝着,看了年轻人一眼。那个年轻人面色枯黄,身体轻微地颤抖着,趿拉着一双花卷般的皮鞋。他病了。
此刻这个年轻人蹲靠在水泥柱旁,手里抓着一块二两重的馒头,慢吞吞地嚼着。走廊上的节能灯将年轻人的影子投在门前水沟上,好似一颗咸菜疙瘩。小国摸了摸发烫的耳朵,走近年轻人问:“你在这里干嘛呢?”年轻人抬起头,嘴里含着一口馒头,痴痴地看着小国,眼睛陷在黑洞洞的眼窝里。小国看了看四周,街上人影稀少,大部分店铺都关门了,小卖部的小窗已经拉上了窗帘,透出暖暖的红烧肉一般的色泽。年轻人快速站起身,似乎有些害怕。小国从夹在腋窝里的那条香烟中掏出一包,拆开后递给年轻人一支:“抽烟吗?”那人愣了一下,哆嗦着伸手接过去。小国一摸口袋,没有火。年轻人掏出一个塑料打火机递给小国。抽了一口烟,年轻人似乎回过神来,问小国:“你和他们认识?”小国不知道他问的是谁,疑惑地看着年轻人。年轻人用烟指了指小卖部,小国这才明白,含糊地答道:“刚认识的朋友,你也认识吗?”年轻人抖了抖烟灰说道:“你要跟他们干?”话里有话,小国斟酌着词句问:“不好吗?”年轻人笑了一下,喉咙里发出短促的“咔”的声音,捂着胸口痛苦地说:“看怎么想了……他们要拉我入伙,我没干。”说完,他猛烈地咳嗽几声,将痰吐在水沟里。
一束光从小卖部的门缝透出打在马路上。小国暗忖:这个年轻人是在暗示我,老郑做的不是正经生意?线索是……他琢磨记忆里老郑和华哥的手,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两个人的脸,也并不像偷窃扒拿的脸。难道是干杀人越货买卖的?无数个念头浮上心头,纠缠不清。
年轻人抽完烟,捏着馒头不声不响地向西头走去。小国在他身后问:“你去哪里?”年轻人停住脚步,转身回道:“我住在那头。”借着路灯的光亮,小国看清了年轻人的脸和他背着的帆布包,那张脸是一张病人的脸,但眼睛沉默而倔强,似乎不承认自己病了。小国追上年轻人,指了指他的帆布包问:“你发传单,一天赚多少钱?”年轻人退后一步轻声说道:“不多,你也想干?”小国摇了摇头:“我的意思是,我们能不能干点别的,不违法,而且赚钱的?”年轻人突然狂笑起来,又咳嗽了好一会儿,眼泪都笑了出来。
小国窘迫地站在马路边,心想,我一定搞错了,他大概是个疯子,或者要饭花子……人家可怜他,才让他发传单挣一点钱吧……年轻人一扭身,脚下的烂皮鞋啪嗒啪嗒走远。小国听到年轻人在安静而黑暗的夜色中叫喊:“不违法,赚钱,哈哈哈……哈哈哈……”
小国反身走进旅馆大堂,老板娘的波浪头从柜台上露出一撮,她大概正趴在桌上打瞌睡。踩着光溜溜刚拖过的水泥台阶,小国走进自己的房间,开了灯。军用大包和两个塑料袋———全部行头——都在,很好。他觉得自己的头有些晕,脱了鞋子和袜子钻进大红色的被窝,心怦怦直跳。隔壁房间悄无声息,睡下了还是没人在屋里?他忆起杂货店的角落放着一个巨大的彩条布袋子,里面也许是老郑偷来的什么东西。可是,真的是偷来的东西?如果是,那是什么东西呢?小国猛摇了摇头,阻止自己的胡思乱想。
小国爬起来,倒了杯开水,站在后窗前边喝水边向外面看。旅馆后头是一片荒地,黑黢黢地在夜色中朦朦胧胧;三三两两的星星挂在夜空,远处的天空微红,那片天空下一定是灯火辉煌的城市;而通往那红彤彤的城市的柏油马路,我看不见。天一亮,我就去柏油路,也许可以赶上早班车。
小国将杯中已经凉了的水倒出窗外,然后关了灯,摸索着床铺。“好想喝一口热乎乎的肉汤,哪怕是一碗飘着肥肉的汤也好。”这个声音将小国吓了一跳:奶奶临死前说的正是这句话,口气也是刚才那样的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