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你,在雨中
◎方 淳
方淳,原名方从安,浙江省作家协会成员,曾出版长篇小说《病人》,短篇小说集《月是故乡明》,另在《小说月报原创版》《作家》《青年作家》《文学界》《西湖》《福建文学》《野草》《雨花》《当代小说》《浙江作家》《三角洲文学》等杂志发表小说、散文若干,有作品入选《小说选刊》。

我还能回忆起刚从人民中学毕业的光景。那一天,丁小兰为了庆祝我高中毕业,又和邵大兵一起带我看了一场电影。人民中学就在华光路上,是我们这个城市排名第一的高中。我不太喜欢妈妈的名字,什么兰啊,花啊的,要多俗有多俗,要是我,不会让这名字黏着我一辈子,一定把它给改了。邵大兵是我爸,后爸,他跟妈的名字可真配,我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就觉得好笑,他比妈妈小八岁,就冲这一点,你也知道,他俩都不是一般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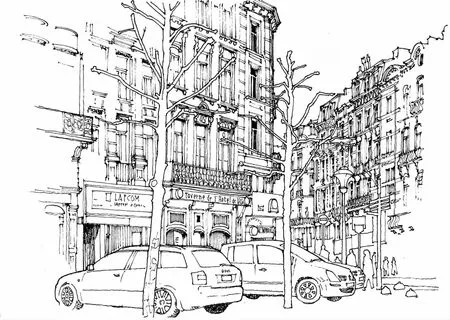
看完电影,已经七点半了。夏天,天还亮着,我们又坐进了利民广场上的披萨店。每个月看一场电影,是我们家多年来的习惯。我坐在10号桌靠西的位置,对面黑色卡座里坐着丁小兰和邵大兵,我第一次发现,他们竟然都还年轻,只是眼角看上去稍稍有些皱纹。
就在这时,窗外的雨淅淅沥沥下了起来,地面上的热气饱胀一天了,像突然被捅破了口子,哗啦啦地沸腾着。打开窗户,能闻得到水泥广场地面酸津津的气味。夜色均匀,底下,我们陷身在烦琐世俗世界。
我穿着一件针织短袖T恤,丁小兰喜欢用毛线织一朵小花缀在胸前,她觉得当妈的有责任打扮好女儿,塑造美丽形象吧。年轻时候,丁小兰就是这么诗意。我们就这样坐在披萨店里,百无聊赖,白色盘子空空的,不锈钢刀叉散发着冷漠光芒,纸巾折得规规整整,闻不出任何气味……我很奇怪,连丁小兰也没发出点声音。
通常,我觉得生活的本质是荒芜的,只是人们在为衣食忙碌中没时间去思考。许多时候,我都觉得自己被罩在一个套子里,对外面的世界不能分明,不能把握。与外面的尘世保持着疏离感,使我不能生活在真实的世界里。
我想,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一个安静的世界吧,在那个世界里,我就是一个幼稚园的女童,站在舞台上,天空下着雨,一对年轻男女伫立在远处,他们看着我。那个男人撑着一柄樱花伞,就像春夏之交,樱花如雨坠落在林荫道上,他站在樱花雨中,肩膀上洒落星星点点的樱花花瓣。
他,是我爸爸,我的父亲。
我看到他转过身去,向我挥了挥手。
我与母亲在一起的时候,通常,丁小兰都会制造一点声音。自从爸爸失踪后,也许是家里太寂寞了吧,也许是怕我寂寞吧,丁小兰叽叽咕咕的话就多了起来。我看过一本类似的小说,大体的意思是,一个女人,从父亲手里流转到丈夫手里,如果这次流转不能成功,那个被指定用来完成人生赛跑的男人,拿不动这棒接力,或者,他拿着接力棒倒下了,或者,他上气不接下气,就像我爸爸一样,突然隐遁,消失,那么,这个女人会长期置身于某种状态中。
父亲喜欢艺术,一个有着艺术基因的男人,对于婚姻这件事,多少有些不靠谱。丁小兰年轻时候显然没充分考虑,人生路上会经历这么多风风雨雨。她这棒接力很不成功。由于父亲的中途退场,丁小兰得另找一个男人把这赛程跑完。
这个过程,我看得很累。
父亲消失以后,丁小兰说话就有一阵没一阵。话多的时候像个话痨,不想说话的时候三天闻不到一个屁。我就在这种环境里长大。
后来,我渐渐感受到,这种环境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自由。家里从来听不到男人吆三喝四的声音。丁小兰给的钱不多,但足够我花。另外,我自认为最得意的一点就是,我继承了父亲的聪慧。艺术气质的男人通常聪慧,虽然他们大多不懂得如何生活,如何在战争硝烟中纵横智谋。他们单纯可爱,看看父亲的照片就知道。
我的前半生应该一帆风顺,就像父亲。父亲十五岁进入名校少年班,我继承了他的基因,成绩呱呱叫,在学校是风云人物,各种各样的光荣榜都有我的名字。钢琴,九级,绘画,全国少年山水画大赛金奖;播音主持;气象台观测组长;晚报小记者站站长。这些年,我把自己倒腾成学校的金牌学生了,打出去,劈倒一大片。
老实说,父亲的形象在我记忆里已经模糊了。他像是永远站在远处,不能靠近。照片上的他,天庭饱满,印堂发亮,金丝边眼镜下,是挺拔适中的鼻子,清秀文气的颧骨。长相英俊,一脸斯文,标准的江南书生模样。
小时候,我总为父亲戴眼镜担心。电影里的地下党,敌人接近的时候,偏偏眼镜掉了,他摸呀摸呀,就是找不着,真叫人急!我就担心父亲有一天也找不到眼镜。后来有了激光手术,我建议父亲做激光治疗,哦,不对,是妈妈建议,我的记忆模糊了。父亲消失的时候,我还是小不点,上大班,不怎么熟悉医院。我应该是听丁小兰说的吧,也许是丁小兰担心父亲,在我面前常念叨。总之,近视不妨碍父亲有深邃的双眼,他通常目光柔和,面带微笑,嘴角微微扬起。
他叫林之泉。
我记得父亲消失的那天。
那天,正轮到我们小组表演。大型文娱表演通常每年一次。那天是元旦。看,这张照片上,我穿着粉红裙子,绿色夹袄,胸前戴金丝闪亮的大红花,描眼睛涂眉毛的,我扮演拔萝卜的小朋友。
一直到我们上台,我都没看见爸妈,我以为他们不会来了。拔萝卜的时候,我分了心,不该倒地的时候,我居然向前一跪,倒在了地板上。下面的观众都笑起来了,我想,反正爸妈没看见,一边站起来,我一边向台下张望,心里又窘迫又盼望……这时候,我就看到了父亲举着一柄樱花伞,和妈妈并肩站在最后面。
那天天气不好,正下着毛毛雨。
这张照片一直留在我的日记本里。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林之泉。
父亲离开家后,我发过一次高烧。妈妈将我送进医院。大概是太渴望见到林之泉了,有一个晚上,当我睁开眼睛,居然看到爸爸就站在窗外。他撑着那柄樱花漫天的雨伞,外面下着雨,就像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一样。
我从病床上跳下来,走到窗边,才发现,没人。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每逢天气下雨,傍晚,我的眼睛只要朝向窗外,在黑色的夜幕里,林之泉总是微笑地看着我。他孤身站着,撑一把樱花漫天的伞,静静的,不说话。
我知道他想念我,挂念我,不放心我。
丁小兰说,父亲去了日本。他和一个日本女人结婚了。那女人是一个翻译,很年轻,比妈妈年轻多了。父亲喜欢上她了。丁小兰成了一个弃妇。
平时我们提到被遗弃的女人,总给人不完美的感觉吧。从那以后,丁小兰就变得唠唠叨叨的,我的心里也充满着同情。饭桌上,她总要向我倾诉生活的艰辛,我的手就会穿过餐桌,抚摸她的手,拍拍她的肩膀,安慰她,让她坚强一些。
但是,丁小兰对父亲充满怀念,她从来不像一个真正的弃妇那样对父亲的忘恩负义恨之入骨,她总是记得他的好。她将恋爱时光掰成一片一片,当饭桌上的佐料,喂给我。他是她的初恋,他低头给她系鞋带,黑亮的头发蹭到了她的鼻尖,她一闻,觉得像个好男人的气息,就嫁给了他。他们可以说得上是郎才女貌,天造地设。一切美美满满,谁能想象这样的经典搭配会出什么偏差。
二是词汇准确性不够。因中西方文化的不同,某些词汇在西方国家和我国有明显区别,易出现翻译纰漏。如“莲花”,长久以来我国赋予莲花高雅、正直的文化内涵,而英语中莲花-lotus则意为慵懒、散漫,lotus eater表示“过着懒散生活的人”。
一条没有波澜的光滑的河流。丁小兰总是这样总结她的前半生。她也会若有所悟地点点头,人生有点起伏也好,不然,太不精彩了!
我们都不知道女翻译什么时候走进父亲的内心,总之,这个家分崩离析,突然解体,丁小兰说,等她发现,已经没有任何思考挽回的余地。
你太不了解男人了。读了一些言情小说后,我想跟丁小兰交流男人问题。那时候,有几个高年级的男生已经给我写了情书,使我觉得自信满满,颇富经验。我听到满腹水流晃动的声音,河水汤汤,从嘴中喷溢,浪花就要溅到丁小兰的脸上。我觉得有必要教育妈妈如何对待男人。
丁小兰太天真了,太天真的女人容易上当。
丁小兰对我的那点儿经验不置可否。你懂个啥,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她总是这么说。母女在一起分享怎么征战男人,令我最感到亲切,仿佛我们成了姐妹。是的,我已经长大,个头超过妈妈了。妈妈站在我面前,就像一个娇弱无依的小女人,我能清晰地看到这些年她头上长出来的白发。
没想到,妈妈很快就找到了幸福。邵大兵不是突然出现在我们家的。邵大兵是父亲的司机。
林之泉婚后成立了一家中日合资公司,公司不大,有五个雇员,邵大兵就是其中一个。邵大兵是退伍军人,比父亲年轻许多。他总是很沉默。小时候经常看到他,他总待在我家楼下的车里。有时候,碰上过节,他载着我们一家出游,去南京,黄山,雁荡山。
不知道为什么,邵大兵很晚了也不成家,听说参军前有一个女朋友,等他退伍,女朋友已经嫁作他人妇,也许就此走不出漩涡了,如此说来,邵大兵很长情。
一天,我放学回家,邵大兵出现在厨房。我一点儿也不奇怪。父亲走了之后,他确实来得少了。也许公司有什么慰问品,或者父亲有什么礼物让他带来吧。确实,他带过不少礼物来。
我拿着礼物关上门生闷气。
丁小兰向邵大兵解释,她就是这么大小姐脾性。他笃笃地敲门,轻声细语安慰我。有一次,无论他们怎么安慰,我都止不住哭泣。开始只是啜泣,最后,忍不住嚎啕大哭。这么多年的愤懑与不满,就像黄河泛滥,我得借一个堤口把它排遣出去。
因为邵大兵在,我哭得肆无忌惮。
邵大兵终于说,林总说,让你去日本念大学,你有日本的弟妹呢!
从那天起,我就盼望快点长大。我希望跳级。我的成绩特别好。初二那一年,我考全校第一,比第二名超出三十分。我让丁小兰去学校申请跳级。丁小兰陪着我走进教导处,教导处戴眼镜的处长愣是说了一番脚踏实地的道理,没同意。回家路上,丁小兰不断摸我的头,说,别在意,不就一年嘛,很快就过去了,这日子,呼啦啦的,跟风吹一样,很快就会过去啦!
我点点头。
是的,就熬着吧!
我自学了日语。不想给妈妈增加负担,我报了初学班,了解一些基础的语法和发音,以后全靠自学。我想,翻译有什么了不起,我得给妈妈出口气。
我的理科成绩不赖,但丁小兰一直觉得我应该继承她的衣钵,丁小兰在报社工作,熟悉媒体圈,她希望我长大做个记者编辑什么的。
每年,我会收到爸爸的信,让我加油学习。爸爸仿佛就在身边,我依然能闻得到他的气息。一些雨夜,我望着窗外,看到他撑着樱花漫天的伞,就站在雨中,湿漉漉地睁着两眼,看着我。
邵大兵和我混熟后,就留在我家不走了。我默认了这个事实。一天傍晚,我在菜场边小摊上买了一束玫瑰,回家插到玻璃瓶里。餐桌上,我认真地祝福他们,并且,还叫了邵大兵一声爸。
邵大兵感动得眼泪都掉下来了。
终于把妈妈托付出去了。我想。丁小兰这样柔弱的女人,终要有个依靠的。而我,无论心智还是外貌,都是林之泉的种。虽然身为女流,我希望像林之泉那样心怀世界,征战沙场。林之泉少年就是大学生了,他是一个了不得的沙场健将。一把年纪了,还有女翻译投怀送抱。我不能像妈妈那样被他抛弃,有一天,我要站到他面前,让他看看,这么多年来,他弃我于不顾,是一种怎样的缺乏远见卓识的错误!
现在,这一天,就要来临了。
我高三就要毕业。我们就坐在利民广场尚泰二楼的披萨餐厅里。我想和邵大兵与丁小兰说说自己的心愿,听一听我的行程安排。
可是,他们谁也不说话,谁也不表态。
难言的寂静。周围的喧哗都与我无关。窗外,仍然下着细雨,雨丝从深杳寥远的天空坠落,我仿佛听到林之泉召唤的声音。
“你走了,妈妈会寂寞。”这句话,丁小兰不知说了多少次了。
“妈妈,你寂寞有爸爸陪。我是你女儿,我不可能陪你一生一世。我有自己的人生。”每次,我都要瞪着眼睛,努力诚恳地和她解释,既表达我的坚定,又要让她不至于产生被女儿抛弃的感觉。那对她来说,太残忍。和他们,我已经疏远好长一段时间了。
不只是丁小兰,邵大兵也是这种看法。
邵大兵的理由是,女儿不能离家太远,女孩子容易受欺负,让人不放心,尤其是妙龄十八的女孩。他从报纸、网络找一大堆女大学生、女研究生受骗的故事给我看,只看得我头皮发麻。有一天,我终于撂下狠话:“丁小兰,邵大兵,你们听好了!我是林之泉的种,我此生一定要见到他!你们不出钱,我拾破烂打工也要去见他!我,离家出走!”
我真睡到同学家去了。
他们着急地找学校,答应和我谈谈。于是,下午,我们看了一场电影,俄罗斯电影,战争片,够沉闷的,我已经许久没看过二战片了,尤其是俄罗斯电影。电影结束后,我们就坐在披萨餐厅了。我希望,林之泉此刻能够出现,就在窗外看着我,看着我和这一对被抛弃的男女谈判,看着我怎样告别他们,走向他,我日思夜想的他。
这就是血缘难以言说的秘密吧!
“时局不好,我们不放心。”邵大兵一脸沉重。
“什么时局不好?”
“你也看了,战争是残酷的。”妈妈没来由地说道。
“放个电影,就要打仗了吗?”
“钓鱼岛的争执,一直没消停。日本人民都游行了呢!”披萨来了,邵大兵难看地啃起来,爸爸一定不跟他一样。
“即使明天就打仗,我也要见到爸爸。越是打仗,我越要见到爸爸。说不定,这是我们最后一面。”我快要哭了。
“爸爸不让你去,他是保护你,怕时局不好,真的受伤害。”丁小兰说。
“我不信。”
丁小兰迟疑地摸出一封信。
我仔细地辨认了字迹,确定是林之泉的字迹后,就看了起来。
这是真的,他反对我去日本留学。时局不好,怕受中日关系的牵连。他让我安心在国内读大学。信后还附上了几张日本民众游行反对战争的图片。
爸爸。我心里默默地叫了他一声。他果然出现了。站在窗外的黑夜之中,像往常一样,他撑着那把熟悉的樱花伞,深邃的目光透过玻璃镜片看着我,落在我身上。他在向我点头。
不,爸爸。请你理解我。不,爸爸,这太残忍了。爸爸,我要见到你。
我趴在桌子上,放声大哭。十多年来,我从未这样哀伤地哭过。
我留意信封上的地址。我决定去一趟日本。我已经成年,没什么力量能阻挡我见到父亲。
“爸爸和你一起去。”邵大兵和丁小兰对望了一眼。
看得出,邵大兵也是第一次去日本。妈妈从前跟着爸爸来过一次。爸爸在国内读完大学去日本深造,是个日本通。九十年代,和日本朋友合作,开了一家中日合资公司,用日本技术在中国生产小型电器,贴日本标签出口。
虽然自学日语多年,临到应用,却不怎么熟练。但我们终于到了京都。搭乘京都本线在伏见稻荷站下车,步行许久,才在山脚的弄堂里找到这个地址。日本著名的景区千本鸟居所在地。爸爸住在这里,一点不奇怪,我在《艺伎回忆录》中见过千本鸟居橘红色的隧道,山景美不胜收。
林之泉,是个爱美的人。
在一处民宿小筑前停下,按过门铃,里面传来日本女人和蔼的应答声。我看了看丁小兰,担心她在女翻译面前失态。
门打开了。是一个身披紫纱精致和服的女人,她很谦和地鞠躬,欢迎我们入内。她的中文很流利。我打量室内的布置,又飞快地朝内张望。
林之泉,我终于要和你见面了。
在一张桌前坐下,女人为我们端上花茶。她说是春天从山上采下的,晒干后,用蜂蜜酿制,她让我们品尝蜂蜜。
邵大兵和女人寒暄,妈妈似乎见过这个女人,她的眼里居然没有嫉妒和愤怒,她温婉和气地和她聊天。女人说着离开中国后的生活。因为千本鸟居游客甚众,她就在此地售卖工艺品为生。她从架上取下几个鸟居模型,都是她设计的。
林之泉没有出现。
女人说完自己的生活,就沉默了。桌上一个木盘里插着新鲜的花艺,古朴而有禅意。书架一个相框边,点着一支香,烟气袅袅。我注意到相框里的照片,是一对年轻恋人。他们互相依偎,坐在山道上。
那个年轻的学生一般的男人,居然是林之泉。
女人突然流出了眼泪。母亲和她四目相对,也淌下了泪水。
“这张照片,之泉也有一张,我看到过……”丁小兰说。
女人用力地点点头。
“之泉说,您父亲侵略过南京,他不能娶你……不想,耽误您一生了。他对不起您。”丁小兰继续说。
女人擦擦眼泪,没有说什么。空气有一点沉闷。
突然,女人抬起了头。她鞠了一躬,表示道歉。“骨灰我当时留了一部分,埋葬在千本鸟居的山上了!这多年来,我陪伴着他。”
“这是晚霜,她长大了。”母亲拉了身边的我一把。“这是千代阿姨,她给你写了很多年的信。”
我惊奇地看着她俩。
当晚,我们在山脚住下。第二天早上,千代阿姨带我们观赏了千本鸟居。鸟居是日本神社建筑,代表神域入口。鸟居看上去就像中国的牌坊,一座连一座,从小到大,绵延千里,煞是壮观。
下午,我们起身去富士山。我们到了富士山山脚,千代阿姨领我们直奔森林深处。青木原,世界著名的自杀圣地,林荫蔽日,阴森恐怖。
丁小兰从背包里拿出一大包元宝和纸钱,邵大兵用打火机点燃了。千代阿姨又拿出一瓶清酒,洒在了地面上。
“之泉,你女儿林晚霜来看你了!”丁小兰的泪水喷涌而出。
“爸爸,我终于来看你了!”
原来,千代阿姨是爸爸的初恋。千代阿姨的父亲曾经侵略中国,爸爸不能娶千代,千代孤独地度过了一生。爸爸婚后成立公司,千代成为爸爸的翻译。小泉纯一郎任首相之后,六次参拜靖国神社,中日关系恶化,日本撤资,爸爸公司破产,来日本索讨债务未果,于青木原自杀。千代阿姨通过警方搜索发现了他的尸体,焚化后,骨灰部分埋葬于千本鸟居,部分寄还给母亲。
他们共同保守了这个秘密。
责任编辑/董晓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