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的思考必须在大安静中诞生,这种安静无关环境,而是一种心灵的安静,哪怕身处闹市仍然能不受其打扰并聚精会神提取出自己内心的悲悯、失落、孤独或幸福的部分。好的作品一定有语言、思想力、语感、技巧、美学、神圣感等多个方面的难度要求,而所有难度的堆积必须由时间毛垫上的细致化阅读、多维度扩展深思和对自己不同阶段创作困境的主动解决相关联,它也必然不是一种自私的主体产生,那会影响作品的格局和境界。主体本身一定对世界是有大包容的,源于他提前于时空的透彻与成熟,从而反射到具体的行为。所以,这份孤独是必要存在的,它会酿造一个天才的诞生,给他更多空间挖掘自己。但这份孤独有很多种涵义,有些事物是相信了依然孤独,与孤独共存从而消灭孤独;有些事情是看似喧哗但它有虚无的本质。重点是经历它的人愿意相信它是什么,从而就会呈现怎样的生活状态。没有什么是永恒的,孤独之于写作也是,重点是看命运把我们推向哪里、阅读把我们推向哪里、遭遇把我们推向哪里。
——主持人语(田凌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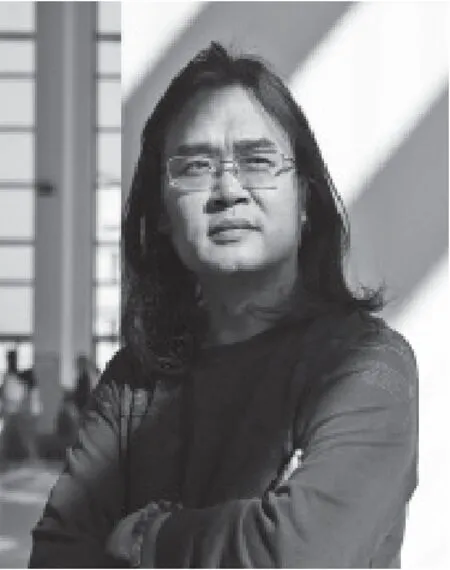
远 人1970年生,湖南长沙人,现居深圳。中国作协会员。著有长篇小说、历史小说、散文集、评论随笔集、诗集等十余部。
我觉得必不可少,甚至是必要的。我很难想象一个缺失孤独感的作家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不是说优秀的作品一定是对孤独的渲染,而是孤独感的存在,才可以使作家更深地沉入自我、沉入内心的点点滴滴。卡夫卡在他的日记里就坦诚,“我必须常常孤独,我已经做成的事,是一个独处的成果。”这样的话耐人寻味,就在于他几乎不自觉地写出了属于自己的写作秘诀。我们还不能忘记,为了写作,卡夫卡连婚姻也不敢进入,在他眼里,婚姻对写作构成的干扰和伤害是他无法承受的。在他眼里,婚姻的存在,就等于孤独感的灭杀。如果卡夫卡没有了孤独感,真还无法创作出他笔下的那些作品。当然不是一个人选择了当作家,就一定要拒绝婚姻,只是从婚姻角度看,也很少有哪个作家觉得自己在婚姻中获得了写作的幸福。陀思妥耶夫斯基算是例外的一个,我们又必须看到的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作之时,除了口授需要妻子速记之外,当他自己动笔之时,妻子是不允许进入其书房的。这里也就说明,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写作的时刻也就是孤独感将自己围绕的时刻,也是他必须对家人冷酷的时刻。
从写作内在来看,孤独感也必然是任何一个真正的作家最为需要的感受。作家需要观察生活,更需要进入生活和研究生活。当他将自己的感受行之于文的时候,他笔下的世界是一个完整的世界。为了笔下世界的完整,他这时需要的就不是再与生活保持平行,在写作与生活的距离当中,填满的必然是自己孤独感的来临。孤独感本身是最自我的感受,作家缺乏自我,实际上就不可进行写作。孤独感的存在才使作家的内心和外部世界成为最坚实的存在。作家终究要彻底面对的,也就是自己的内心和外部世界的所有反馈。作家的孤独感丧失,也就是最内心面对的丧失,对外部世界的信息接收丧失。这也是一个作家与一个非作家的最大区别。当一个作家宣称自己不需要孤独感,甚至排斥孤独感,我们看看他的作品也能发现,与持有孤独感的作家相比,前者始终达不到后者所达到的深度。

张作梗中国作协会员。祖籍湖北京山,现居扬州。作品散见《花城》《人民文学》《中国青年报》《诗刊》等报刊。
在我看来,适当的孤独就像一件隔音室,对于写作者来说,是剔除喧嚣、澄净心性、回归自我的一种必要的方式。但过于沉溺于孤独,甚至以修禅的心态渴望孤独来袭,则显然是一种病态了。因为等来的孤独有时并非是“真正的孤独”——尽管它会以“孤独”的面孔出现,但是伪装出来的“孤独”。它给予人的错觉甚至比孤独本身更令人走火入魔。
因此,写作者首要防范的,正是这些充斥在各种文本中的“假孤独”“伪孤独”“勾兑了二氧化碳的孤独”……它们遮蔽了人的情感和对世界的真实感受。它们怂恿写作者公然在“非孤独”的包装下,贩卖过期的或二手的“孤独感”。这种所谓的孤独的文学,不过是“假大空”文学的一体两面。
孤独是一种心灵的自然状态,就像喜悦是另外一种状态一样。来之,用心接待;走了,不必刻意挽留。

亚楠本名王亚楠。祖籍浙江。新疆作协副主席、伊犁州作协主席。作品见《人民文学》《诗刊》《中国作家》《十月》《青年文学》《大家》《北京文学》《花城》《钟山》等报刊,并入选各类年选。
从我阅读古今中外文学名著经验来看,孤独感无疑是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在西方文学中,以象征主义为开端的现代主义创作,完全超越了传统题材特征,深刻揭示出人类在文明社会中的孤独感和绝望感。很显然,这种孤独感是人与生俱来的,它就像一个幽灵,时隐时现,不经意间就会触动我们内心。因此,我挺喜欢台湾文化学者蒋勋所说的“孤独的核心价值是跟自己在一起。”
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孤独感对于写作很重要,甚至是必不可少。写作或者阅读不仅是人们逃离现实的方法,更是一种心灵慰藉,因而我把孤独感理解为人类灵魂的避难所。大作家黑塞曾经说过“人生十分孤独。没有一个人能读懂另一个人,每一个人都很孤独。”这就意味着孤独感来自内心,源于迷惘,是上帝赋予写作者与生俱来的能力。我一直都认为孤独感是作家在文学写作中生命和灵魂状态的写照,是他生活的本质特征。在那些以孤独感为母题的文学创作中,一种独立的思考状态就会凸显出来,它自由而超拔,不但是人的内在动力,更是一切精神创造活动的基础。
孤独感也是人类灵魂的过滤器。优秀写作者总是把孤独感当作财富,他们常常能够超越现实,在构思与写作过程中,让孤独感这种人类特有情愫成为一种独特的美学。比如创作出《百年孤独》等一系列经典名著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就非常善于“品味孤独的真谛”,他说:“只有孤独的人,才拥有丰富的内心世界”。孤独感并不是目的,它是一种附带的艺术效果。尽管我们知道,并非每一本书都是一幅孤独的图景,但我们却可能在孤独感中孕育,并诞生不朽杰作。
所以我赞成那种拥有孤独感的写作。不迎合谄媚,不丧失独立判断,耐得住灵魂的孤独、寂寞,做一个始终有良知的言说者。尤其是,要让孤独感成为文学表达的自觉意识,胸怀“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陈子昂诗)的大悲悯、大孤独,自由表达内心世界,把孤独感上升为一种哲学和美学意义的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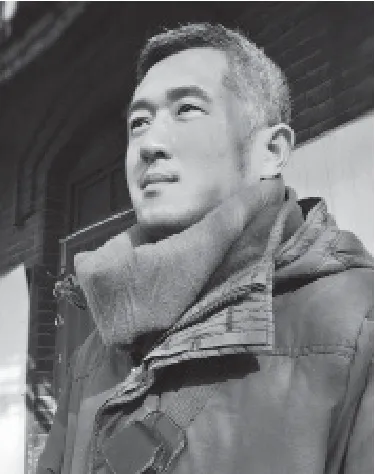
霜白上世纪七十年代生,居河北保定。曾在《十月》《诗刊》等报刊发表作品。著有诗集《挽留》。
孤独有两种,一种是横向的,一种是纵向的。
当一个人感到和周围的人或事物之间的距离超过一定的限度,他感到空旷、无所依傍。这是横向的孤独。他需要通过周围的人来确认自己的位置。他的一部分需要融合在别人那里。
当一个人把目光放到无限的时间的长河中,来反观自己。他也是在寻找自己的位置。他感到了自己是一个不断被推动被拒绝着的人,他同样感到空旷、无所依傍。同样,他想要找一个可以收留自己的去所,但他所接近的一切转瞬成为记忆的黄沙,消失在他的身后。为了挽留,他创造或写作,他在空茫的记忆里筛选、聚拢、提炼,然后捧出作品或文字的晶体。但它们一经出现就把它们的主人驱逐了出来。他永远只是一个形单影只的义无反顾的行进者。这是纵向的孤独,且永远无解。
两种孤独都成为一个人精神的内驱力,迫使一个人去找寻。这种找寻体现为两条途径:爱和创造。
横向的孤独产生爱情,纵向的孤独诞生艺术。
横向的孤独可以通过爱情(或其他感情)来排解。纵向的孤独通过艺术来慰藉,像一个个竹篮,不停伸到记忆的水面。
爱与创造同样源于追寻,目的也是一种——为了挽留。我们总感觉自己有一部分“应该”在“别处”,可是又总有一种分裂的、被流放的痛苦和焦灼,这种焦灼构成了我们的孤独。这种孤独让我们不遗余力地去把我们“本来应该有的”却丢失或分开的那部分重新放回“原处”。这部分“在别处”的自己通常被我们称作“寄托”。这种寻找的活动本身也成为我们活着的力量和意义。
爱与创造并不是两种不同层面的活动,它们其实互为彼此——爱即是创造,创造即是爱。
一个人可以因为孤独而爱一个人,因为爱一个人而孤独;同样,一个人可以因为孤独而写作,然后因为写作而孤独。两者中的后一种孤独更具体也更清醒,前一种孤独来自于茫然,后一种孤独来自于映照。前一种孤独是横向的,后一种孤独就有了深度,或者说,后一种孤独是立体的。因此后一种孤独因其背景的博大而更博大。
横向的孤独每个人都可以有,纵向的孤独不是每个人都有。
可能有人活在纵向的孤独里,他沉迷于此,像一个封闭的管子,他也拒绝了周围的人,他没有了横向的孤独,或者说这种横向的孤独对他来说不起作用。但我相信即使有这样的人,也极少。
倒是很多的艺术家,是活在两种孤独里,这可能也是他们的作品充满了旺盛的生命力的原因,比如梵·高。

纳兰本名周金平,80后,中国作协会员。出版诗集《执念》《水带恩光》《纸上音阶》。参加第35届青春诗会。2019年获诗探索·中国新诗发现奖(评论奖)。
听说一个说法“写作就是祈祷”。一个有写作经历和祈祷经历的人,内心必定有所依傍和支撑,不会被孤独感,虚无感所击溃。写作就是倾吐心声,既输出负面情绪、负面经验,也输出正能量、正念和正思维。我不同意说“孤独感对于写作是必不可少”这种命题,不是孤独了就会用写作的方式去化解孤独,也不是说写作就能摆脱孤独。一个人孤独的时候,可以望月、听雨、赏花,可以寻三五知己饮酒和闲谈。一个人写作的时候,他一定是沉醉在自己的世界里,忘记了孤独这回事,就像一个在纸上建筑世界的创造者。一个严肃的写作者,总是忙于更新自己的内心和输入更多的思想家的思想来提升自我的境界,而不是跟孤独本身纠缠不清。对于写作来说,对于“天、地、人、神”等关系的思考和感受是第一位的,而孤独感只是众多感受中的一种,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显然不是排在第一位的。

三色堇本名郑萍,山东人,现居西安。中国作协会员。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北京文学》《上海文学》《诗刊》等刊。出版诗集、散文诗集多部。获“中国散文诗天马奖”“中国当代诗歌诗集奖”等多项。
对于一个作家而言,写作本身就是很自我的事情,他需要在自己的精神向度里与世界对话。孤独是一种状态,一种境界。我认为没有哪一位作家会是在喧闹中成长的。他要学会在尘世间摒弃浮躁来承受孤寂。也许我们只有经历过孤独的磨炼,才会有灵魂的升华。
作家的孤独是高贵的,孤独者都是思想者,当一个人孤独的时候,他的思想是自由的,是深刻的,他面对的是真正的自己,人类的思想一切都源于此处。我的写作时常是在夜晚安静的时候,只有此时才是我进入内心的最佳状态。孤独是一种思维方式,不管处于什么样的环境都能让自己安静。诗人北岛说,作家就应该是孤独的。而且我认为孤独感对于一个作家是如此的重要。

后白月中国作协会员。曾出席全国第七届青创会。参加第31届青春诗会。鲁迅文学院第31届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著有诗集《白色》《天真》《亲密》。获第八届台湾薛林青年诗歌奖。现居重庆。
孤独感对于写作是写作中的一个发现,不是条件。不是孤独先在那里了,我去感觉一下它,或者求它给我一点感觉,让我写出点什么。
不是的,不是这样开始的。
是想写,就是想表达才开始写作的;是想继续表达,才继续写作的——也许想写才是必不可少的。但想写这个状态不一定是孤独产生的。
孤独感更容易使人失去欲望,更容易失去表达的欲望。它不是写作建立初期形成的,但它可能是结果。
一个写作者越追求独特,越有可能封闭,这种封闭看起来是孤独,但真正的孤独感是最后,在追求中进入更深的探索时发生的。越深的地方越黑暗,越想逃离,而在深洞中逃离的方法也许不是返回,是继续——挖。就这样写作成了孤独伴随的一种旅行。孤独感是写作者在写作中对孤独进行消解的过程里建立起来的。
孤独感是写作进程中的必经之路,是写作中的一个发现。但不是写作必不可少的条件。你可以有其他感觉,比如兴奋感,好奇感,捣蛋鬼感,疼痛感,搔痒感,金钱感,名誉感,疯狂感……
任何一种感觉,只要强烈得非写不可就可以。

梅依然四川遂宁人,现居重庆。中国作协会员。重庆文学院签约作家。著有诗集《女人的声音》《蜜蜂的秘密生活》等。曾获《诗选刊》“中国年度先锋诗歌”等,入选重庆市首批“巴渝新秀”青年文艺人才。
一次,和几个朋友聚会吃饭。两个在边聊天边吃饭,一个在旁沉默吃饭,一个在边看手机信息边吃饭,另一个在一边招呼上菜一边吃饭。突然,招呼上菜吃饭的朋友,朝一边看手机一边吃饭的朋友说:“看什么手机,手机比吃饭重要吗?”嗓音带着某种谴责和委屈。而以我的肉眼来观看,这应是一个慢镜头动作:这声音属于超声波式,从嘴里出发到抵达目标的过程,无疑像登山运动员攀爬喜马拉雅山那样缓慢困苦。每一个字如同每一次抬起的脚掌,重重地落在人们的身上,尤其是重重地落在看手机的那个人身上。人们都停止了动作,缓慢地转动着眼睛看着这个说话的朋友。“吃饭吧,看什么手机呀?”她又重复道。这声音的脚掌再次缓慢而沉重地落在人们身上,扬起一阵阵雪山将崩塌一般的冰屑。现场的气氛一下子由轻松变得凝重……
其实,从聚会一开始,孤独就已经存在。无论此时聚会的主题是“吃饭”,还是“聊天吃饭”,它都会有副题存在:看手机的看手机,沉默的沉默,吃饭的吃饭,聊天的聊天。“我想所谓孤独,就是你面对的那个人,他的情绪和你自己的情绪,不在同一个频率。”理查德·耶茨十分冷静自制地还原了孤独的真相。人和人聚集在一起,情绪频率相同的,几乎没有。即便是两个非常相爱的人在一起,也不时存在着这样艰难的情形。我们暂且把频率相近的情形称之为默契度,这默契度的高低与否,更是取决于人们相聚时间的长短和人们的性情、兴趣是否相投。
人们能够相聚在一起,不管出于友谊、交际或是别的什么需要,都应尊重一件事实:我们害怕孤独。因害怕,我们聚集在一起;因害怕,我们用孤独的写作方式来抵抗或者容纳这种孤独。我们也因为这种孤独从而将自己从人群中突显出来。那个孤独的我们,既高大又脆弱。
让我们理解和包容那个与自己不在同一个情绪频率的人吧,面对这个世界,我们都同样孤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