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刀三,生于重庆,现在某文化部门工作。以小说创作为主,兼写诗歌、随笔、散论。
重庆刀客
□ 燕刀三
燕刀三,生于重庆,现在某文化部门工作。以小说创作为主,兼写诗歌、随笔、散论。入秋已经很久了。
天气本该渐渐转凉,但是今年却不,秋老虎的余威不减,到了深夜,反而闷得人更加心慌。一朵黑云卡在群山之间,遮蔽了稀稀落落的星辰,大地因此漆黑。
田坎上歪着几排桑树,焉耷耷的,好像被扔进了大蒸笼。
“这鬼天气,蛇都死绝了。”罗宾咒骂道。
他举起火把,就着身旁的桑树递过去,干枯的叶子着火即燃,窜起一团火光,把趴在地上掏蛇洞的王跛子吓了一跳。他哈哈大笑,王跛子也大笑。
“罗宾汉!”王跛子跳起来,他跟罗宾一样,浑身上下只穿着一条火红的裤衩,其余部分光溜溜的,糊着稀泥,他说:“你烧荒是不?”
“你以为我不敢?”
“得了,你敢!”王跛子把手里边的火把晃了晃,说:“再怎么着,也得先办正经事儿。我都闻到蛇的香味了。”
“今晚没搞头,要下暴雨啦。天气预报说的。”
“天气预报?报天气的全是他妈的猪猡!”
“嗯,同意!猪猡!”罗宾说。
“你才是猪猡!”王跛子一拳擂在罗宾肩头,说:“我烧了你眉毛胡子,你信不信?”
“得了,劳改犯。得了得了,我信!”
罗宾和王跛子的家在施家墚,相隔一条田坎,距离西山坪劳改农场仅七里。王跛子在农场劳改了足足十三年,听说是他在年龄刚够得上法律惩办的那阵,提刀卸了仇家的挂子。十三年连一天都没减免,因为在狱中又与人斗殴,几拳致人重伤。
五天前出狱。家里二老没了,只好暂时在罗宾家落窝。罗宾自幼就孤儿一个,乐得有人相陪。
“跛子,河对面新修了条高速路,知道不?”
“听说了,还没见过。”
“直通重庆,二十几分钟就到。”罗宾说。
“关我什么鸟事?”王跛子不屑道。
“我也不喜欢。”罗宾说:“看见那些快速运动的玩意,我就头晕。我宁愿一辈子在施家墚打蛇。”
“真老土,我看你是怕嘉陵江淹死你吧?”
“我呸!淹死我?我的水性比你好。”
“我不信。你能举着火把泅过河?”
“不试试,你当老子是个球!”罗宾怒气冲冲道:“哥子我今天不光要过河,还要到重庆玩玩。有种你别去。”
“有种你才别去。”王跛子赌气道:“我输给你不成?”
“好,他妈谁散劲谁是瘟丧!”罗宾说。
罗宾几步蹿回家,从墙上摘下一副焦尾琴,斜背在背上,然后头也不回地朝河边走去。这些年,罗宾只要出远门,一定得把焦尾琴背着,这已经是他的习惯了,村里人知道他行事怪诞,在外边多与人不合,心想定是在琴里藏着机关,也就不以为奇。王跛子却不知道,伸着脑袋左瞧右瞧,瞧了老半天。
“背个什么破玩意儿,到重庆卖唱是不?”王跛子瘸瘸拐拐地跟在后面,一路大笑,笑得直不起腰,“就我们俩?多少钱一曲?一块还是一毛?也得逮个小姑娘陪着托铜盘才是。”
罗宾闷着头到了河边,一路朝河心走去。他的水性果然很好,火把没有弄湿就游过了河。王跛子的倒被河水冲熄了。
王跛子把湿漉漉的火把递过去点,突然“呱”的一声,一个黑物在焦尾琴上乱扑腾,把王跛子和罗宾都吓了一大跳。
罗宾就着火把一看,原来是个特大的癞蛤蟆,一条腿被两根琴弦缠住了,吊在半空,气囊一鼓一鼓的,睁着两只眼睛惊恐地盯着火。罗宾拨开水草,把它一把扯了出来。
“烧死它。”王跛子咯咯笑道。
“烧你个娘。”罗宾说:“留着,等会儿派得上用场。”
他们翻过两三道坡,再穿过一片竹林,拐个弯,果然有条高速公路横在面前。一道铁丝做的隔断挡住了他们的去路。王跛子捡块石头,几下就把隔断砸了个洞。他们利索地爬了进去。
罗宾扯下一根琴弦,一头栓住癞蛤蟆,一头栓块石头,然后扔在公路中间。王跛子问他干什么,他嘿嘿冷笑,只说让它死得有价值些。等了一会儿,开过来一辆大巴车,车开得并不算快,发出吃力的嗡嗡嗡响声,听上去就知道超了载。
车开过来,不出罗宾所料,好像正是从癞蛤蟆身上碾过的。
罗宾赶紧跳过去,抓起癞蛤蟆。那只癞蛤蟆还活着,只是左边前后两腿被碾成了扁平的肉饼。它痛苦地呼吸。王跛子立即明白了罗宾的用意,轻轻一蹿,挡在大巴前面,嘴里“嗬嗬——嗬嗬——”地乱叫。司机做梦也不曾想到,竟会跳出个举着火把、穿裤衩头的怪人拦在高速路上,他着实吃惊不小,赶忙踩住刹阀。那车刚好碰着王跛子的肚皮,停了下来。
“赔我蛤蟆,赔我蛤蟆!”罗宾提着癞蛤蟆跑上去,嚷道:“死瘟丧,赔我蛤蟆!你赔是不赔?”
“你敢不赔?不信我烧了这破车!”王跛子咬着牙威胁。
司机知道今天算是碰上踹客了,只好自认倒霉,叫售票员让他俩上车,每人给了十块钱了事。
车上座位坐得满满当当,连通道上也挤满了人。一个孕妇腆着大肚子,堵在门口,全身都汗透了。她瞥见罗宾和王跛子上车,赶紧把手紧紧扣住吊环,臀部却拼命往后面缩,想腾出点空间让他们过去。
罗宾扫了一眼那些落座的乘客。他们有的闭目养神,有的投过来好奇的目光,有的像什么也没有看见,两只眼睛空洞洞的。就近坐着一个胖子,他把头靠在后垫上,半张着嘴,死死盯着那只垂死的癞蛤蟆,也不知道他想些什么。
“喂,罗宾汉,他盯你的蛤蟆。”王跛子说。
“是吗?”罗宾说:“他为什么要盯我的蛤蟆?”
“他说你的蛤蟆好看。”王跛子想了想,说。
“他没说。”罗宾说:“他像猪一样,什么都没说。”
“他说了,我听见的。”
“他没说。”罗宾扭过头,问胖子:“你说没有?”
胖子气哼哼地别过脸去,懒得搭理他们。
“这么说,你真说了?”罗宾提高嗓门,同情地道:“你看它多可怜,你居然说它好看?你这没心肝的,我要让你说个够。”
“我没说。”胖子辩解道。
“你没说?”罗宾有点生气了,把癞蛤蟆凑到胖子面前,几乎贴着他的鼻尖,吼道,“你说没说就没说?”
“我没说。”胖子继续辩解。
“你说了。”罗宾说。
“你打个光条条儿,我就怕你?”胖子突然冒出这样一句话。
王跛子扑哧一声大笑。罗宾也忍不住大笑。
“他说你是光条条儿。”王跛子说,“哈哈哈,他说你没穿裤子。”
罗宾把裤腰橡筋拉起来,又放开,把肚皮弹得砰的一声响。
“听见没?”他说,“我穿着裤子。”
胖子不理他。罗宾猛地探出一只手,揪住胖子的衣领,轻轻一提,将他举过头顶,然后手腕轻轻一送,谁也没看清他使了什么法子,那肥胖的身躯就像一片树叶似的,从窗口飞了出去。司机本想停车,被王跛子喝住。
罗宾示意孕妇坐上空位,孕妇又感激又害怕,胆战心惊地落了座。
“这招叫什么?”王跛子问。
“沾衣十八跌。”罗宾说。
“狗屁。”王跛子说。
“就叫沾衣十八跌,真的,不骗你。”罗宾说。
“狗屁。”王跛子说。隔一会,又说:“那老头儿教你的比我多。”
“你做劳改犯那阵,他又来过。”
“就为教你这招?”
“不是。”罗宾说,“他教我用刀。”
“刀?”王跛子说。
“嗯!”罗宾说。
“菜刀,是不?”王跛子忍住笑,“你的刀呢?”
“刀无处不在。”罗宾脸上露出孤独的神情,说,“刀在心中。”
“嗬,深奥!”王跛子说,“你是他妈的哲学家。”
“老头儿有真功夫!教了几年,走了。”
“走了?你是说他死了?”
“不知道。”罗宾有些木然地说,“总之他不会回来就是。”
“他叫什么?我忘了。”
“我也忘了。”罗宾说,“反正他走了。他走了,我觉得孤独。”
两个人忽然沉默不语,车内便静得可怕。几乎每个人都把他们盯着,空气又闷热又紧张,罗宾和王跛子就感觉他们像是紧盯着两匹随时要咬人的狼。
只听见车轮碾在路面上,发出呜呜的响声。
车从北环下了高速公路,拐过新牌坊,驶进江北区最繁华的商务中心,在站上停下。罗宾和王跛子下了车,满眼都是高楼大厦,霓虹灯挂在半空,晃得他们直喊头晕。他们完全找不着东南西北。
两人互相望望,看着对方光丫丫的模样,忽然有些害羞。
“得遮一遮。”王跛子建议,“像城市人一样。”
“有道理。”罗宾说,“像城市人把自己裹起来,别让人看见。”
他们沿着车站围墙走,围墙外边的树木投下一片阴影。他们沿着阴影走。走到门口,侧面有一排大理石砌的阶梯,一个蓬头垢面的乞丐蜷缩在阶梯最下方,好像睡熟了。
罗宾和王跛子走过去,绕着圈看了会儿。王跛子蹲下身,开始剥乞丐的衣裤。乞丐被惊醒,大声嚷嚷,王跛子顺势给他一耳刮子,他立即哑了,顺从地让王跛子剥。王跛子先剥下破风衣,嗅了嗅,觉得太臭,就递给罗宾,罗宾把它穿上。接着他又脱下乞丐的裤子,那是留给自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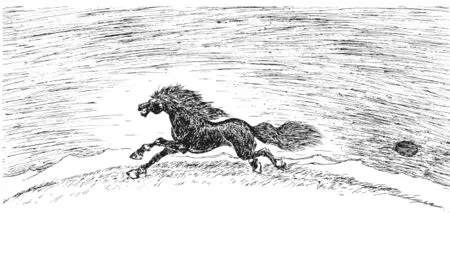
就这样,他们在街上大摇大摆地溜达,虽然夜深了,但行人并不少,很多商铺也还没有打烊。他们跟大多数人一样,没有目的,拖着幽灵般的影子游来荡去,像闯进富人区的乡巴佬,没有想过撞大运,只是想瞧瞧稀奇。
这时从黑暗的角落踅出来一个老女人。老女人涂着很厚的脂粉,瘦骨伶仃的,长相非常的不负责任,有点像鬼。
“嗨!”她冲着罗宾和王跛子招呼,“玩会儿,便宜得很。”
“玩什么?”罗宾和王跛子同声问。
“年轻人,装什么蒜!”老女人说,“不就那么回事吗?”
“嘿嘿,懂了。”王跛子笑道,“多少钱?”
“五十。呃……还可以讲。”
“只有二十,两个人。”王跛子从裤袋掏出皱巴巴的钱。
“开玩笑!”老女人撇了撇嘴,“一个才十块,简直不把人当人,什么社会!”
“社会就这样。”王跛子有点不耐烦,说,“要干就干,不干就滚!”
老女人犹豫不决。王跛子和罗宾看着她,等她决定,但她还想加价。
“滚!”罗宾突然吼道,“死瘟丧,快滚!”
老女人没好气地闪进暗影里,不见了。
罗宾和王跛子继续溜达,弯弯拐拐到了北滨路。他们趴在栏杆上欣赏河对岸的夜景。对岸就是重庆市区,摩天大楼鳞次栉比,亿万盏彩灯拉成无数条光网,把天空照耀得如同白昼。罗宾和王跛子感叹不已,接着他们为去不去对岸争论起来。最后,罗宾说不去,因为忽然不喜欢那些光。王跛子说,你不去我也不去,我一个人去兴许比你还孤独。
于是他们又说,本来说好今晚吃蛇肉的,蛇没打着,怎么糊里糊涂跑这儿瞧这些无聊的灯!王跛子问罗宾,你手里提的什么?罗宾说,是癞蛤蟆呀,这会儿好像已经死了,所以它又叫死蛤蟆。王跛子说,真有你的,提着个死蛤蟆想跑遍全城是不?干吗不找个馆子炒来吃了?罗宾说,好主意。
他们走进附近的小餐馆,店老板瞧他们那副行头打扮,不想热情都不行。他们把二十块钱扔给老板,说看着钱做几道菜,再就是把癞蛤蟆剐了,整一个汤什么的,反正要保证吃饱。店老板心想真是碰到两个胎神了,要吃饱还不容易?于是端了一甑子毛干饭,把癞蛤蟆宰了,混些杂七杂八的菜煮了一盆火锅。
罗宾和王跛子吃得直冒汗。这时候,门前那条滨江路上,忽然轰隆轰隆飙过来几十辆摩托,乱哄哄的。车手全是年轻人,蓄着稀奇古怪的发型,穿着比发型更稀奇古怪的服装。他们把摩托当成飞机开。
店老板看见他们,慌了神似的,赶紧跑去拉下卷闸门。
“他们做什么的?”罗宾不解地问,“老板,你好像怕他们。”
“嗯,怕!谁不怕?”店老板说。
“怕什么?怕他们开摩托撞你店铺?”
“那倒不会。怕他们白吃白喝,还白拿钱。”店老板摇头道。
“没有王法了?”罗宾说。
“王法?”店老板冷笑道,“他们就是王法。”
“你是说,王法也拿他们没办法?”王跛子搭上话。
“我可没这么说。”店老板道,“他们是著名的摩托帮。”
“死瘟,犯了法可以不坐牢?”王跛子愤愤道,“这么说,我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罗宾问。
“这十三年的牢,我算是白坐。”王跛子说。
“哈哈,你活该!”罗宾说,回头又问店老板,“刚才你说什么?你说摩托帮?”
“对呀,”店老板说,“滨江路这片,是他们的势力范围。”
“还分成片?”罗宾说,“听你的意思,有很多帮派?”
“听说有五六个。摩托帮排名老三。”
“都是哪些?”王跛子又插话。
“飞龙帮、斧头帮、98学社、肉摊帮……”
“肉摊帮?很有创意。”王跛子笑道,“吃肉的?”
“还真让你猜对了。”店老板说,“他们控制着好几家大农贸市场,肉摊菜摊都交保护费。上个月他们跟摩托帮火拼,吃了亏,老大重伤,成了植物人。现在老二当家。”
店老板刚说完,卷闸门“哗啦”一声被推上去,两个大汉猫着腰钻进来。头一个满脸横肉,穿皮裤;后面的剃了个朋克发型,怀里抱着头盔。他们朝四周扫了一眼,径直走到柜台边。
剃朋克发型的拉出抽屉,抓了一把钱塞进头盔,接着又去抓第二把。
店老板跟在后面,心痛得要死,但还得陪着笑。
“两位老大,少拿点。”店老板终于央求道,“这几天生意不顺。”
“生意不顺?”穿皮裤的说。
“不顺。”店老板说。
“这么晚,还有人照顾生意,还说不顺?”穿皮裤的指着罗宾和王跛子,突然吃吃地大笑,说,“看他们那副打扮,真酷!够时髦!像有钱人。”
他俩走到罗宾和王跛子面前。剃朋克发型的拿起筷子,伸进火锅盆里搅了几搅,什么也没捞着。突然他也跟着大笑,弯着腰笑,笑得泪花花儿滚进盆里。
“有钱人,有钱人!”他说,“就差汤没喝干了。”
“他们没有钱。这是赔本买卖。”店老板讪讪地说。
“哦?”穿皮裤的说,“听你的意思,他们是来吃混食的?”
罗宾和王跛子相顾一笑,心想这毛头不是分明在咱们头上找虱子吗?当着咱们的面打劫,还踏屑人,没王法就算了,王法也值不了几块钱一斤,眼里总不至于没我罗宾和王跛子吧?两人扔掉筷子,噌地站起身来。
两个摩托帮大佬立即露出鄙夷的神色。穿皮裤的大汉绕到罗宾背后,伸手拨弄琴弦。琴弦发出“咚咚咚”巨响。
“你们是艺术家?”穿皮裤的问,“服装设计得蛮不错。”
“抢的。”罗宾说。
“哦?这样就更有个性。”穿皮裤的说。
“是吗?”罗宾说,“我倒没发觉。”
“艺术家,你觉得我这皮裤怎样?”穿皮裤的问。
“像坨狗屎。”罗宾平静地说,“反正我不喜欢。”
“哎哟,这你就不对了。”穿皮裤的说。
“怎么讲?”罗宾问。
“我这皮裤三千块,每个月上四次油,知道不?”
“知道了。”罗宾说,“不过我觉得它只值一块钱。”
“怎么讲?”穿皮裤的不解地问道。
罗宾忽然大喝一声,身子腾地前躬,左脚撩空,右腿画弧,使了个漂亮的过桥摔。那穿皮裤的连哼都没来得及哼一声,就从罗宾背后飞起来,弯了一个圈儿,一屁股坐进滚烫的锅里,皮裤吱的一声烫得稀烂,痛得他哇哇怪叫。
“信了吧?我说它只值一块钱。”罗宾指着他烫烂的裤子,耸了耸肩。
剃朋克发型的见状,抖出一把刀子,向罗宾小腹捅去。罗宾闪过身,左手食、中二指夹住刀尖,一扭,刀子立即断为两截。
这两手干净利落,把摩托帮大佬给吓破了胆,他们一边发着狠话,一边抱头鼠窜。
店老板瞠目结舌,隔好一阵子,才醒豁过来,急得满屋乱转。
“停停停,你转个啥?”王跛子不耐烦地说。
“完啦,完啦。”店老板搓着手心,说,“死定了。”
“死定了?谁死?”罗宾问,“是你还是我?”
“两位大哥,求求你们离开这里。”
“为什么?”
“救命!”
“救谁的命?”
“救我们三个人的命。”
“我们没有命。”罗宾和王跛子笑道,“我们叫亡命。”
“那就算救我的命。”
“救你的命?”罗宾问,“你的命值多少钱?”
“钱?哦,对对对。”店老板说,“我给你们钱。”
店老板从皮夹摸出来三百块钱,双手递到罗宾手里。罗宾还给他一百,又把另一百递给王跛子。
“一人一百。”罗宾说,“这样谁也不欠谁。”
等他们走出卷闸门的时候,这才发现门口远远围了一大圈摩托,原来出口早就被摩托帮的人阻断。摩托帮的人见他们出来,一个个盯着他们看,谁也没有吱声。从他们表情判断,他们不相信眼前这两人有什么能耐。
罗宾和王跛子就着石坎坐下。摩托帮的人也不相逼,像在等人。王跛子的手心有点发汗。
“他们像在等人。”王跛子说。
“像是。”罗宾说。
“他们等谁?”王跛子又问。
“不知道。”罗宾说。
“我们先杀出去。”王跛子说,“他们的人会越来越多。”
“我们能杀到哪里去?”
“不知道,反正杀出去就行。”
“那样的话,我们反而杀不出去。”罗宾索性躺下来,望着天上的乌云,沉着嗓子说,“那样的话,我们反而会被围困一辈子。一辈子都抬不起头,知道不?”
“我不懂。”王跛子说,“你他妈玩什么深沉。”
“那个老头儿已经死了。”罗宾说,“你知道不?”
“哪个老头儿?”
“我们的师父。”
“哦,他死了!”王跛子有点失落,说,“怎么死的?”
“被刀杀死的。”
“谁杀死的?”
“我。”
“你怎么杀死他的?”
“因为速度!”罗宾眼眶里不知什么时候闪着泪花,补充说,“速度杀他!将来速度也会杀我!”
“他很痛苦吧?”王跛子叹口气。
“不!”罗宾说,“他笑着。”
“他为什么笑?”王跛子问。
“不知道。”罗宾说,“我猜他在这边很孤独。”
“所以他宁愿死?”王跛子说。
“也许是。”罗宾笑笑,歇一会儿,又说,“也许在那边他一样孤独。”
“他孤独,是因为没有对手?”王跛子说。
“也许是。”罗宾说,“也许相反。”
他们正说着话,突然听见摩托帮的人骚动起来。罗宾和王跛子站起身,放眼望过去。圈子打开一个缺口,驶进来一辆黑得锃亮的劳斯莱斯,停在罗宾和王跛子丈把远的地方。
先前剃朋克发型的从车上钻出来,后面跟着两个身材魁梧的人,都光着膀子。一个三十来岁,提两个簸箕大的拳头,右边手臂上纹着龙,龙头一直伸到胸口;一个四十来岁,抄两把斧头。摩托帮的人看见他们,便自觉向后散开,眼睛里流露出钦佩的神色。
“年轻人,你们好。”那个抄斧头的说,声音细,听上去斯斯文文,“我来介绍一下。我叫钟五,他们叫我钟老虎或者老钟,手下有一百二十号人,都是靠斧头吃饭……”
“哦,久仰。”罗宾扭头对王跛子说,“看来是砍材的。”
“不是。”钟老虎说,“我的斧头不砍材,砍人,它喝过十六个人的血。”
“挺吓人的。”罗宾说。
“他叫蟒蛇,飞龙帮的老大,连续四届的重庆散打冠军。”钟老虎向提着簸箕拳头的那位努了努嘴,说:“你们很幸运,碰上了好年代,居然让飞龙帮的老大亲自出马,这样你们就死得痛快些。”
“你的意思是说,要杀死我们,对不?”罗宾问。
“嗯。”钟老虎点头,“很快你们就会顺着嘉陵江,漂进长江,像高空漂移,很快!挺好玩的。”
“为什么要杀我们?”
“因为你们弄伤了摩托帮的老大。”
“是他先挑衅。”罗宾说。
“那不重要。”钟老虎说,“重要的是我们曾经欠他一个情,而现在他又找到了我们。”
“好像杀人对你们是一件挺简单的事。”
“不简单。”钟老虎说,“但该死的都得死,因为他们破坏了重庆市的统一。”
“统一?”罗宾不解地问,“难道重庆市还没有统一?”
“不错。”钟老虎说,“重庆六个帮派,要团结,要统一。”
“好像整得很正规,像警察。”
“当然。我们比警察更正规。白天是警察的,晚上是我们的;看得见的是警察的,看不见的是我们的。警察是我们的兄弟和竞争对手。”顿了顿,钟老虎望一眼身后五光十色的重庆市区,动情地说,“你们看,重庆多美!多好!秩序井然。但是它离不开我们这些为它工作的人,当然,还有警察。”
天空突然扯起一道闪电,把大地照耀得如同白纸,接着炸响一个焦雷。雨滴大颗大颗地砸下来。
“别废话。”飞龙帮老大不耐烦了,用比炸雷还响的声音说,“老子拳下不打无名鬼,报上名来。”
“我叫罗宾,他叫王跛子。”罗宾说,“王跛子叫我‘罗宾汉’,我叫王跛子‘跛子’。”
“好名字!”钟老虎斯斯文文地赞道,“小时候我想做佐罗,但是我不会用剑,也没有佐罗长得帅,所以只能做钟老虎。”
王跛子插了嘴,“小时候我也想做佐罗,可惜佐罗不瘸。”他说,“再说我没有生在法国,上帝安排我生在中国,上帝的意思不好违拗,所以我只能叫王跛子。”
“是吗?那倒挺有意思的。”钟老虎侧了侧头,睨一眼王跛子,嘴角挂着一丝轻蔑,不屑地说:“你也长得挺有意思的,有点惊世骇俗。”
“完全赞同。”罗宾忍住笑,说:“不过长相是父母给的,没有办法,对不对?”
“对极了。”钟老虎望了望天,雨越下越大,他呵了一口气,说:“同志,咱们不聊了。明天,白道上有几位朋友要谈笔生意,这事完了,我要回去睡个懒觉。”
“可以,同志。”罗宾说,“我也想快一点了事。”
雨劈劈啪啪地下,每一个人都淋得透湿。罗宾摘下背上的焦尾琴,轻轻一掀,琴的侧面掀开一条缝。他伸手摸出来一把短刀。
那刀有尺把长,宽宽的,没有刀尖,刀柄微微向上翘起,缠着黑布。在电光映衬下,寒光闪闪。
王跛子吃了一惊,他想凑上去瞧个仔细,但罗宾已经提着刀迈向前去了。王跛子本想冲上去阻止他,但是,忽然感觉脚根本就是挪不动,只好傻傻地站在原地,眼睁睁看着他靠近钟老虎和蟒蛇。
钟老虎和蟒蛇像两座铁塔,分立在离罗宾几步远的地方,一动也不动。在他们四周,腾腾地冒起一股杀气。

罗宾径直走去,终于走到他们两个人之间。这时候,“喀嚓”一声,头顶又滚动一个焦雷,同时,一条巨大的闪电仿佛撕裂了天幕,发出强烈刺眼的光芒。几乎所有的人,都下意识地用手遮住强光。
闪电过后,王跛子手搭凉棚,歪着头,吃力地瞧向前方。他看见钟老虎和蟒蛇仍然像铁塔一样挺立着,一动也不动。罗宾已经从他们之间走过去了,但他没有停,他仍然在走。
王跛子懵了。罗宾忽然站住,转过身,向王跛子招了招手。
“走啊!跛子。”罗宾说,“傻了你啦?”
“他们……”王跛子问。
“他们走完了人生旅途,见马克思去了。”罗宾说。
罗宾刚一说完,两座铁塔轰然倒下,溅起地上的雨水。顷刻间,雨水鲜红。王跛子怔怔地看着罗宾手中的刀,刀刃上淌着一丝血。他一下子明白了。
好一阵瓢泼大雨,将暑气驱得干干净净。罗宾感觉有点冷。摩托帮的人见出了命案,知道事情闹大了,发动马达,东奔西窜,逃得不见人影。连那个剃朋克发型的也跑掉了。现在只剩下雨打在地上,劈劈啪啪地响。
有命案当然就有警察,这时候,警笛声从四面八方传来,越来越近,无数警车把现场围得水泄不通。罗宾和王跛子举目望去,全是荷枪实弹的警察和晃得人睁不开眼的红光。
“你们被包围了,放下武器!”警察展开心理攻势,用喇叭高声喊话:“你们被包围了!你们被包围了!”
罗宾趴在栏杆上,一边弹响琴弦,一边望着对岸,对岸那些高楼大厦和扑朔迷离的灯光,令他的眼睛看上去很迷惑。
“怎么办?罗宾汉。”王跛子急了,问:“就这样等死?”
“你有办法?”罗宾问。
“我没有。”王跛子想了想,说:“你有。你有刀。”
“球戳!我也没办法。”罗宾说:“他们有子弹,子弹的速度好像比刀快。”
“我们总得杀出去。”王跛子说:“我们被包围了!”
“杀不出去!太强大了。”罗宾笑了一下,说:“其实,我们自从娘胎生出来,就已经被他们包围了。”
“我有点懂了。”王跛子点头。
“你很聪明,跛子。”罗宾说:“梦里不知身是客,其实我和你只是天地间的过客。”
高音喇叭还在喊话,那声音夹杂着滚雷,在空气中忽远忽近。
“你今后有什么打算?”罗宾忽然问王跛子。
“今后?”王跛子冷笑,“我们还有今后?”
“我是说以前。”罗宾更正道,歇了会儿,又补充说:“今后就是以前,死了就是活着,没有区别。”
“我的以前?这个,我想想——”王跛子想了好一阵,说:“我没有以前。我以前成天想着的就是越狱,逃出去。”
“逃到哪里?”罗宾问。
“施家墚!”王跛子说。
“嗯。”罗宾说,“你的理想比较远大,令人钦佩。”
“你呢?”
“我以前想当兵。”罗宾说:“想打仗。那时候,中国至少有两亿年轻人渴望战争。”
“可你最后,还是只有当农民的命。”王跛子说。
“对啊,后来我不想当兵了。当了兵也是逃兵。”罗宾说,“我只想专心做个农民。”
“为什么?”王跛子问。
“你还记得那个小姑娘不?”罗宾说:“她家离我们不远,住在施家墚坞口。”
“记得,当然记得。”王跛子说:“可惜十六岁那年被卖到静观镇去了。现在已经背上孩子了吧!反正没你的戏。样子嘛,长得不错。”
“长得是不错,挺考验人品的。”罗宾说。
“哦?你被她考验了?”王跛子笑嘻嘻地问。
“怎么可能。”罗宾说,“连手都没有摸到。”
“难怪,难怪。”王跛子煞有介事地点头,“忘了你是没有人品的。”
罗宾一巴掌拍在王跛子后脑勺上,说:“猪啊你,没人品我会连手都摸不到?”
“那是,那是。”王跛子忍住笑。
“以前我想娶她。我一直喜欢她。”罗宾认真地说,“这是我以前唯一的打算。”
“娶她?”王跛子终于忍不住,忽然大笑,止不住地笑。罗宾被他感染了,说,日你娘的笑什么?话还没说完,也仰头大笑。两个人肆无忌惮,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只蹲在地上,捂着肚子笑,嘎嘎的笑声远远地传播出去。
“这么说,我们是情敌?”王跛子站起身来,说。
“谁跟你是情敌?多没品味。”罗宾说。
“你知道我为什么坐牢?”王跛子问。
“关我什么事。”罗宾说:“那阵子我不在施家墚。”
“我杀的就是买她的人。”王跛子说:“只卸了他膀子,算是救了他一命,说起来,他还得叫我救命恩人。”
“那你也得叫我救命恩人。”罗宾说。
“为什么?”王跛子问。
“我们是情敌,但我没有杀你。”罗宾说。
于是两个人又大笑。他们笑着笑着,突然一声枪响,焦尾琴被打得粉碎。警察发动攻势了。
“警察最没有耐性。”罗宾指着扑在地上的两具尸体,说:“跟这两个死瘟一样,太粗鲁。”
“那我们就投降吧,大不了回去再坐大牢。”王跛子说。
“不是投降!”罗宾说:“如果我们杀上去,就等于死,知道不?死是一件太简单的事,死才是投降!”
罗宾掂掂手中的刀,凑近鼻子,用力嗅了嗅生铁的味道。刀还是那样寒气逼人。王跛子无意中瞥见上面镌刻着“民族英雄”四个字,又想笑。
忽然,罗宾手一扬,那刀飞速地旋转着,划出一道大弧线,向嘉陵江坠去。在电光下,它像一抹青烟。
“是师父的刀,还给师父。”罗宾说:“走吧,跛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