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她对于“痛苦”的敏感是持续而炽烈的《我们乘坐过山车飞向未来》大概是诗人马雁生前写的最后一首诗,诗后附注的写作日期为2010年12月2日。在这首诗中,“痛苦”一词一共重复出现了五次。实际上,如果通读马雁身后由友人整理、出版的两种作品集的话,不难发现,她对于“痛苦”的敏感是持续而炽烈的。在她的诗与散文中,有大量关于“痛苦”的描写,这个既具有名词又具有形容词性的双音节汉语词汇似乎被用来印证着马雁自身内部某种思想与精神的暗影。然而,在我看来,马雁诗中的“痛苦”不仅仅起到了描述其自身思想与精神的某种状态的作用,同时它还是一个超个人化的隐喻,涉及历史的悲剧性与宗教救赎的可能性问题。(实际上,如果读过马雁诸多散文篇章的话,我们会发现她的读书范围以及所思考问题的广度和深度是超出仅仅读她的诗后所得出的那种片面想象的。因此,在分析马雁诗歌的同时,试图忽略她的散文,在我看来,是不明智的,也是不严谨的。)马雁在她人生的最后一首诗中写道:
在波浪之下,在波浪的下面
一直匍匐着衰弱的故事人,
他曾经是伟大的创造者,
匍匐在最下面的飞得最高,
全是痛苦,全部都是痛苦。
那些与我耳语者,个个聪明无比,
他们说智慧来自痛苦,他们说:
来,给你智慧之路。
这首诗中,“痛苦”的高密度出现除了具有个人史层面上的描述性意义以外,还指向的是诗人生存背后的巨大现实和历史问题。在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所构建的碎片化与原子化的个人生活伦理中,个体的绝望实际上成为了整个历史的绝望。马雁在诗中运用的“过山车”这一意象颇能指明她对于现代社会所导向的一条历史方向的某种怀疑和批判态度。“过山车”是高速的、颠簸的、不确定的,它是一种历史的隐喻,在它之上的个体很容易就被它抛甩出去,飞入混沌的“空无”的空间,他们最后所拥有的将只有绝望与“全部都是痛苦”的宿命终结。马雁在诗中提到了“工人”,她说:“哦,每一个坐过山车的人/都是过山车建造厂的工人,/每一双手都充满智慧,是痛苦的/工艺匠。他们也制造不同的心灵,/这些心灵里孕育着奖励,/那些渴望奖励的人,那些最智慧的人,/他们总在沉默,不停地被从过山车上/推下去,在空中飘荡”。因此,在历史的“过山车”高强度的运转与前行中,个体只能不断地被外在力量的“隐形之手”推下去,在空中无尽地“飘荡”。这个时候,人的价值、尊严、荣耀等等将荡然无存,变得一文不值。在揭示与批判的过程中,马雁实际上也在寻求着一种超越的路径,即个人如何在历史的想象中突围,并且找到一个有效的通道来再次“优雅地”进入、理解并把握历史。
因而,在马雁诗的语境中,“痛苦”的精神状态(常态)并不是最终的归宿和终点,这其中还存在一种宗教性的超越的努力,即所谓“人间的互相拯救”所需要的真正的“智慧”。因而,“痛苦”在马雁那里似乎更近于一种灵魂的苦修行为,它的目的是为了使超越“痛苦”的更高“智慧”得以出现。这种“智慧”是优雅的、高贵的、质朴的,是人的最理想和最完美的一种存在状态,它似乎只能来自于造物主。马雁有一首诗的题目叫《痛苦不会摧毁痛苦的可能性》,她在诗中说:“他升起时,无花果树将开花,/贝壳将给出回环的路径,一切再次/降临,并反复以至于无穷。是这样;/他说:痛苦不会摧毁痛苦的可能性。”在此,“痛苦的可能性”无法被“痛苦”所摧毁,它是无限的,就像从“痛苦”中寻求超越的努力也是无限的一样,它不会停止,始终随生命的节奏而摆动。这种无限地“痛苦”,以及在它之中无限地寻求超越的过程,其实就是一种信仰不断渴望被抬升的过程,也是灵魂渴望无限地接近造物主、渴望拥有最高“智慧”的过程。“无花果树”这一意象出自于《古兰经》,它被视为一种圣树,无花果也被看作一种圣物,它是关于完美、纯洁、光亮、高贵的隐喻。在我看来,马雁其实在这首诗中描述了伊斯兰教“复生日”来临时的场景。这是一切人和事物“再次降临”并得到最终归宿的时刻,在造物主启示于先知的言词记载中它只能出现一次。但在马雁的诗中,这种“降临”的过程并非仅仅只有一次,而是“反复以至于无穷”。马雁对源自于造物主的最高“智慧”的渴望与她个体内部始终无法摆脱的虚无主义式的悲观是共存的。一面是“拯救”(轻盈),另一面是“堕落”(坠沉),(“拯救”与“堕落”均为马雁诗句中所提到的词汇,它们明显包含着宗教性的内容),这种矛盾、纠缠与互悖恰好促成了马雁诗歌中具有宗教性色彩的“痛苦的可能性”的一再出现。
马雁在写完《我们乘坐过山车飞向未来》一诗二十天后,又写了一篇题为《高贵一种,有诗为证》的读书随笔。在这篇随笔中,马雁讨论了林徽因的两首诗《莲灯》和《“谁爱这不息的变幻”》。她似乎十分钟爱林徽因的这两首诗,并以一种为林辩护的姿态显示出她对林的赞许和钦佩。马雁说:“在我个人心目里,《莲灯》算得上中国现代文学里最好的诗作之一。其中最可贵的是没有苦难,都是很优雅的。”“林女士的诗最后却没有以悲哀作结,她另有一种悲哀,是关于世间的无限和个人的有限,几乎可以上接陈子昂、李白。但又不同于男诗人的金戈铁马为出路,她的出路是爱,并且不满足地追索爱的道理,最后给出了绝望的勇气。”这种“追索爱的道理”恰恰也是马雁自身想要寻找到的一个出路。然而几乎令所有人扼腕叹息的是,在写完这篇随笔九天后,马雁便以不到三十二岁的年龄意外辞世,终止了她的思考与追索。然而,“死亡”对于马雁来说,既是结束,也是某种开端。在伊斯兰教信仰体系中,“死亡”有时被看作是趋向于个体本源的某种回归,进入“后世”,永居于那个真实的彼界。
这种诗歌写作过程中的“较劲”行动,带来的结果却并非“痛苦”,恰恰相反,在马雁那里,它更多转化成的是一种“感激”
马哈茂德·达尔维什说:“痛苦不是天赋,它是对天赋的考验:要么天赋征服痛苦,要么痛苦征服天赋。”因此,在它们互相考验、辩驳、角力、缠斗的共生关系中,诗成为了一种抵抗中具有必然属性的创造之物。在马雁的诗中,“痛苦”和“天赋”之间并不具有产生互相压倒与击败的结果的可能,而更是一种一直在体内互辩、共生的存在,它与其说是状态,毋宁说是属性,没有这个彼此肉搏苦斗的属性,诗的有效性就无法得到成立,诗的力量感也无法得到呈现。因此,马雁说:“我写诗似乎总是在较劲。”
然而,这种诗歌写作过程中的“较劲”行动,带来的结果却并非“痛苦”,恰恰相反,在马雁那里,它更多转化成的是一种“感激”。因为,在马雁看来,诗歌写作以及其它创造方式本身就是一种由“幸福的期许”所引致的生命的本能行为,携带着肉身的体感和温度。她由“痛苦”而进入诗,尽管诗并不能完全解决这种“痛苦”,但在诗的写作过程中,马雁实际上得到的却是一种情绪的冷静和心灵的喜悦。诗,在马雁那里,是协助她,并与她有着血肉关系的某种辅助器官。这或许就是雅克·朗西埃所谓的“诗的躯体”的概念所指向的一个意义层界:“无论是谁,只要他寻找打开文本的钥匙,通常就会发现一具躯体。”
文本层面上的诗是诗人的另一个“躯体”。所有的诗,都是基于诗人的身体感官所感觉、体验并进而思考、体悟而创造的。因此,诗人身体的感官也成为了诗的感官。真正的问题或差异在于,诗人如何促生“血肉之诗”的坚硬骨骼和诚实心灵,而不是轻而易举地落入肉体细描、器官隐喻、下半身书写的权力陷阱。身为一位女性诗人,她在“诗的躯体”层面上没有陷入俗套,却在不断思考和技艺精进的过程中,在自己的诗中呈现了轻盈、细腻、纯净、抒情、超越的个人化面貌。
马雁在2001年冬写的《十二街》一诗是她早期诗作中自己比较满意的一首,她在解读这首诗时说:“是非常简单的诗,只用几行构造出一个想象的世界,香味是可以攀缘取得的,蝉声给人的压迫感绵延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想象中的人可以有无限的身体,而人们在做着自己的事情。每一首诗都能够实现这样的功能,但好的诗歌能做到的显然比这更完美。”然而,仅仅过了一年之后,她所写的一首无韵十四行诗《看荷花的记事》就已经超越了之前的《十二街》,达到了一个她所说的“更完美”的层界:
我们在清晨五点醒来,听见外面的雨。
头一天,你在花坛等我的时候,已经开始了一些雨。现在,它们变大了,有动人的声音。
而我们已经不是昨天的那两个人。亲密让我们显得更年轻,更像一对恋人。所以,你不羞于亲吻我的脸颊。此刻,我想起一句曾让我深受感动的话,“这也许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一生中最幸福的,又再降临
在我身上。她仿佛从来没有中断过,仿佛一直
埋伏在那些没有痕迹的日期中间。我们穿过雨,
穿过了绿和透明。整个秋天,你的被打湿的头发
都在滴水。没有很多人看见了我们,那是一个清晨。
五点,我们穿过校园,经过我看了好几个春天的桃树,
到起着涟漪的勺海。一勺水也做了海,我们看荷花。
从这首诗中,读者大概可以感受到马雁对于世界充沛的爱意。“五点”上溯卞之琳《距离的组织》中“友人带来了雪意和五点钟”一句,只是将时间维度调换为“清晨”,更具清新色调。“雨”、“花坛”、“亲密”、“亲吻”、“幸福”、“校园”、“荷花”等词语所营造的气氛浪漫又平静,近于极致。这首诗充分调动了读者的全部感官机能,在有限的词句组织中,把场景的美与情感的爱意集中突显出来,显示出新诗对于书写人内心情感的细腻变化所独有的优势。尽管,这首诗语句不那么晦涩,通畅、自然,然而,它将这些平常字词重新组合起来的手法,却是独特又惊艳的,是独属于马雁的。马雁用了“荷花”这一古典诗中最常见的意象,但她却把“荷花”重新纳入到现代经验与审美的体系中来,并且呈现出唯美而不矫揉造作的诗歌效力。
二
北岛在评价马雁的诗时曾说:“初读马雁的诗令人感到惊喜。我一直琢磨这惊喜来自何处,后来终有答案:就总体而言,中国当下的诗歌太油腔滑调了,而马雁的诗中那纯净的力量恰好与此形成极大反差。她才华横溢,尚在摸索,若再有十年,必修成正果——让我深感上苍的残酷:一手赋予她柔情与才华,一手又把她轻轻捏碎。”其实,北岛的这段评语只说对了一半。马雁的诗的确为当下汉语新诗的场域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的途径,丰富了当下的诗歌生态,矫正了某种“油腔滑调”的风气。然而,她生前的写作并非还处于“尚在摸索”的阶段。实际上,马雁的诗歌创作从十多岁就开始了,她的诗歌起点是比较早的。等到2010年她离世之时,马雁的整个诗歌写作经历大概有二十多年的时间,这对于一位早慧、敏锐、勤奋的诗人来说,其实是一段比较长的诗歌历练与冒险的时期。因此,诗的“正果”之修成不一定完全是由年龄的标尺来测度的。另外,从作品层面上来看,马雁的诗歌写作从2002年前后开始就已经拥有了个人极为平稳和成熟的体式和技艺。并且马雁也还写有许多谈诗随笔,对于诗已有自身系统、自足、成熟的认识。只不过,她对于诗歌的严肃态度和谨慎气质使她的诗歌产量并不高,因此,留下来的诗相对就比较少。然而,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使得收入《马雁诗集》中的每首诗作,均显示了颇高的艺术水准,几乎每首诗都具有自身准确、圆熟、精当、超前的品质。马雁对于诗的认知是肉身化的,与她的生命感受和经验紧紧贴合在一起。在她那里,诗的问题与生活、信仰、爱情、时间、未来等问题是紧密相关的。她在《学着逢场作戏》一诗中写道:
马雁对于诗的认知是肉身化的,与她的生命感受和经验紧紧贴合在一起
发明词语者
发明未来。
这句诗可以说很好地概括了马雁对于诗与现实关系的理解。句末那个干脆利落的句号似乎显示了她对这一观念的确信与坚定。不过,与其说这是一句判断句的话,倒不如把它看成马雁对于这个世界留下的一连串疑问:究竟该“发明”什么样的“词语”和“未来”?以及如何“发明”等等。自从白话文运动的主将们创制了新诗这一文学形式以来,“词语”问题就一直是汉语新诗所要解决的基本性难题之一。与古典诗稳定、同一的意象体系相比,现代汉语新诗的“词语”明显变得游移、多义、含混与不确定。因此,诗人由此便有了一项“发明”的基本“天职”。于是,如何“发明”、“发明”什么“词语”成为了现代汉语新诗写作者们所要面对的头等要务。敬文东在研究了汉语诗歌“词语”的这种性质的根本转变之后认为:“细微的差别对于较为粗线条的视觉原则,对于较为粗放、粗犷的直观,对于古人面对农耕经验时的灵魂反应,基本上不值得计较。直观就是整体;农耕生活在整体上的趋同性,倾向于支持词语在语义上和语用上的同一性。词语的一次性原则与此刚好相反:同一个词语在不同的诗人或在同一个诗人的不同诗作当中,含义应当是不一样的;其分析能力、分析的层面,还有分析的深浅度,也必将是有差异的。微小的差异在新诗写作中必须被突出:这就是新诗现代性的本有语气和内在律令。”
因此,对于“词语”这个基本性元素的思考与发现必将是每一个现代汉语新诗写作者直面的问题。马雁在这一点上是十分自觉与清醒的。她在2009年的一篇获奖发言中说:“诗歌语言则基于日常语言,做出严格的定义和限制,坚持‘隐喻和日常平权’、‘本义与引申平权’,通过实验性的运作使这些平等的要素重新形成权力层次,形成使人惊讶的效果——有时候,我们就把这叫做诗意。”与此同时,她还认为:“诗人应当对自己的艺术语言怀着极大的热情。对基础的重新发现,通过实践这种重新发现予以了证实,这种艺术就获得了更新。”马雁本身就是一位对诗歌怀着极大热情的诗人,她的写作实践也证实了这种热情。2010年4月至9月期间,马雁在北京上苑艺术馆担任驻馆诗人。在这期间,她的诗歌写作出现了一个小的创作上的“高峰”。尤其是在9月18日,她在这一天之内连续写了八首诗作,分别为《爬山》、《骑车》、《上苑艺术馆》、《沙峪口村》、《桥梓镇》、《怀柔县》、《北京城》、《北中国》。这八首诗作均代表了马雁诗歌的最高水准,其中,部分诗句流传颇广,比如《北京城》中的“热衷于责任而毫无办法”、“让人痛苦的爱,绝望中一再重生”,《上苑艺术馆》中的“卑微的造物”等等。这些诗句之所以流传广泛,尤其是在更年轻的诗人群体中备受征引、传诵、解读与模仿(有些诗句或词组甚至还被他们借用为自己诗集的名字),一个很大的原因是马雁诗歌内部所具有的强烈又真诚的抒情引力和开放又包容的理想空间。在短暂的一天内,创作出闪烁着智慧、技艺与美的光芒的八首诗作,这在整个汉语新诗的历史上都是一个罕见的事件。因此,2010年9月18日,无论如何都可以说是属于马雁的“诗的黄金日”。


三
通过这种写作关系的建立,马雁最终的目的,或许是试图掌握某种她所说的“美与幸福的发明学”。马雁说:“每个人都在进行着创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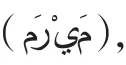


母亲的离世给马雁造成的精神冲击是强烈的,并使她重新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她一直处于一种挣扎的状态中,精神上是痛苦与紧张的。这在她2004年及之后的诗中有所呈现。在这一段时期,“死亡”、“裹尸布”、“尸体”、“堕落”等阴冷色系的词汇开始大量出现在她的诗中,比如:“我好像死过一回,/像在绝望的刀刃上爱”(《爱》,2004年夏)、“我缓慢吞食这蜜样的/嫣红尸体”(《樱桃》,2004年春)、“我只能死去,含着大块的冰”(《结婚》,2004年冬)、“死亡是解放”(《欢饮》,2004年夏)、“我堕落/如蚂蚁悬浮在尘土”(《死亡是最大的政治》,2004年3月10日)、“狂热是我的裹尸布,我等那送我上火刑柱的人”(《狂热是我的裹尸布》,2006年10月7日)等等。在这些诗中,最能充分体现马雁这一时段精神的危机感与空虚感的诗是《亲爱的,我正死去》,此诗还有一个副标题为“给小黄、我的爱和赎罪”:
亲爱的,在成都,雨雪开始于清晨,
我正死去。我在阴沉的下午死去,
你看,自从那时起,我就混乱至今。
他们一个个离开,我曾经跳舞,在
石板地上,这是一个快乐的节日。
我们都有节日,你穿过锋利的北京,
亲爱的,穿过高大的白杨树,他
一个声音就处死了你。谁也不能
处死我,你的尸体叫我快活。你我
曾经是英雄的小姐妹,但现在是
灰暗的中国大地上堕落的一对。
对,我无耻近于勇,请亲吻我吧,
我期待与你有关,潮湿、腐烂、冰凉,
与死亡有关,与一切的堕落有关。
2004年春



? 马雁:《我们乘坐过山车飞向未来》,《马雁诗集》,新星出版社,2012年,第135页。
? 马雁:《痛苦不会摧毁痛苦的可能性······》,《马雁诗集》,新星出版社,2012年,第112页。
? 马雁:《高贵一种,有诗为证》,《马雁散文集》,新星出版社,2012年,第45-46页。
? 马哈茂德·达尔维什:《诗眼》,《来自巴勒斯坦的情人》,薛庆国、唐珺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239页。
? 马雁:《无力的成就》,《马雁散文集》,新星出版社,2012年,第241页。
? 雅克·朗西埃:《词语的肉身》,朱康、朱羽、黄锐杰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67页。
? 马雁:《无力的成就》,《马雁散文集》,新星出版社,2012年,第242页。
? 见《马雁诗集》封底。
? 敬文东:《词语:百年新诗的基本问题——以欧阳江河为中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10期,第22-23页。
? 马雁:《自从我写诗》,《马雁诗集》,新星出版社,2012年,第202-20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