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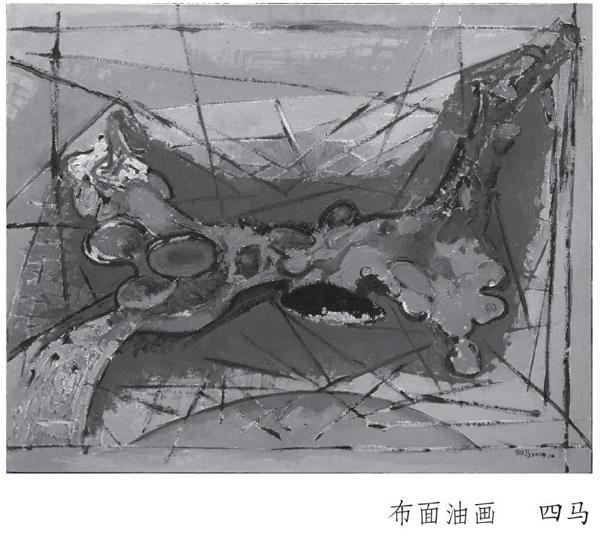
逆光走过繁花丛
咏华君:
平凡的一天,听见窗外唧唧的鸟叫,你心可安?
我不心安,所以一早起床就走个远路去吃胡辣汤了。在太原卷烟厂边的底楼,小小门店,河南逍遥镇人家的生意,不是老客的一般人都不太可能找得到。而我是去年冬天一个黑黢黢的下雪天的早晨打着手电找到的。
找到时,心里一瞬间明亮。
咏华君,如果你与我来吃,胡辣汤一定要大碗优质加肉的,草帽饼则可各自来四两,飞快地一气吃完,在被胡椒充分渲染过的唇齿与鼻息中,羞愧感便会迅速灌满全身,我们便可以有一点劲头去干活了。
我们活着,也许正需要一点点羞愧感随身,始知什么不该做,什么该赶紧去做。而时至今日,这一点可以鼓舞生活继续向前的羞愧感,我似乎只能从食物与日常之美中去寻找了。
譬如早晨的逍遥镇胡辣汤,譬如此刻逆着晨光穿越的繁花丛。
逆光走过花丛间弯弯曲曲的小道,繁花唤起万千体内的恍惚,一瞬间我想只要走出这道光之幕,一定就可以穿山过海一路走到往日的你身边。
繁花开得到处都是,繁花就是往日春天里的你与我。
那时的你与我都还是个小孩子,但我竟还没见过你,你来到你的泡桐下,泡桐就开紫,我来到我的杨树下,杨树就飞白,你我一起来到槭树下,槭树也开青青黄黄的小花。
但,你的故乡有槭树吗?我的故乡真的没有。
你有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悄悄跑到过一棵槭树下,问它究竟开不开花?
今天是第一次,我发现南沙河边移栽的槭树竟然也是开花的。而我前几日深夜月下所见的,其实正是这些花叶一并婆娑的槭树啊。
昨夜我从外面看开花的槭树回来,喝水时偶然就玩了一个测人性的微信小程序,才突然发现我原来是被谪仙人和转世佛包围的一头暗黑恶魔啊——兽性、妖性、魔性都爆表,而神性与佛性皆是零,至于人性,只一半稍多尔——我原来竟乃半人。
但这个结论很好——因为恶魔是不需要转世的,他充分疯魔过这一辈子就已足够,恰与我的心态暗合。尤其是,恣肆而活的魔是有朋友的,譬如美猴王,譬如牛魔王。而佛与仙则未必,谁敢说弥勒佛是太白金星的好朋友呢?而之于人,似乎已只有朋友圈了。
但是,在这只能充分活过的一辈子里,我想每一天都能发现、都能重温一点点日常的永恒。咏华君,永恒也许正在转瞬消逝的日常平凡里,在被树木沾惹的夕光中,在早晨被玻璃窗过滤后的鸟叫中,在此刻我吞吞吐吐写给你的书信中,在顶楼的马戏团乐队的手风琴声里,在窗外提着水管的园丁偶然看向我的一眼里。
我相信,这些毫不足道的日常正支撑着我们的生活,正开启着一种可以隐隐期待的远景,那里面,有开敞的秘密,有某种温柔的法则。而温柔,正是温柔,才让我与窗前的白脉椒草一起开口与生活说话。
这日常中平凡流逝的永恒与温柔,也许值得我们每一天都睁大双眼,看清眼前的事物,并盯紧摇晃着的地平线,并尽可能双脚站稳握紧双拳奋尽全力地活过每一分,每一秒。它太美了,我們要努力让它慢下来。
缓慢里才有灵魂。
咏华君,此刻的鸟在叫,鸟叫时,我看见你与别人在谈论着一部日记。我必须大胆说,这部日记让我看到了一部作品在它时代的具体命运,以及它在产生与传播过程中的全部社会细节。有趣的是,我们——就这部日记展开激烈谈论的你与我——作为参与者,其实正在丰富着一部作品的历史。事实上,如果偶尔扭回头去看一看,会发现历史中几乎所有产生过争议并流传至今的作品,无不是在其时代的万千困境中争取作为一部作品的自由,而那些伴随作品而生的细节,早已经被时间埋葬于尘灰之下,成为验证那部作品强大生命力的一点点微不足道的碎屑。所以,咏华君,无论那些反对那些赞美多么激烈,真的是不重要的,它和千年前百年前飞出城市窗口的一点点飞沫并无多少区别。
所以,作品自有作品为证,作品也只到作品为止,其余的都是喧嚣,不如且听窗外的鸟叫。
鸟叫时,我忽然就想停下手中的一切,为你勾勒一下这一刻我所在的城市,勾勒一下这一刻的我自己。因为鸟叫声只要一停,城市与我便都已不在这一刻的永恒中了。
鸟叫时,火车正贴着平原与山峦,从南向北穿越城市,像平凡而难以心安的每一天一样唤起羞愧;鸟叫时,火车贴着山峦与平原,从北向南,再次穿越这个城市,也像平凡而难以心安的每一天一样唤起羞愧。每一天,每一刻,这个城市在东面的火车声中都越过我窗前的一棵榆树向着西面多生长一点,又越过一条与铁路几乎平行的河流,继续向着西面再多生长一点,直到遇见南北延伸着的山峦,它才停下来,才把山朝更上面努力挤一挤。
它,这庞大的携带着我生活的城市,一直在长,向着四面八方,它的生长让我觉得自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的时候,我就想拼命地说话,就想拼命地把说话的空间再向上面的山峦努力撑上一撑。
那些山峦之下,曾经丰富的矿藏,一度支撑起这个城市生活的往昔。那些山峦之上,夕阳的余光似乎在想象中永恒。
咏华君,到了黄昏时,它会无辜而温柔地照耀面山而行的我,恰如难安而羞愧之昨日。
(庚子年,谷雨前,并州小石山房)
谷雨:草香、鸽翅与槐花饼
咏华君:
在长长的午觉后醒来,天阴。阳台窗口像个打印出来的二维码,扫一扫,就进入一个落雨的黄昏。水汽很饱足,窗口下方的白铁皮屋顶上雨水清澈,那一圈圈飞快涌现又消逝的涟漪,闪亮恰如近来心事。
但这雨又下得太过短促,以至于我不能有足够的酝酿去把这几日慢慢写给你看。
这几日风一样就吹过去了。这几日风一直在吹,楼群与树梢之间,风声呼啸,尖利而漫长,这是这个城市夏日将来的征兆之一。风也带来了四面八方的草香,窗外,广场,街道的绿化带,到处可以看到沉默的园丁。他们一个一个推着、举着修剪机在草坪与灌木身上劳作。那飞溅的青草碎屑,那扑面而来的好闻的植物气味,是城市夏日将临的另一个征兆。
我羡慕这些包围在草香之间的园丁。他们搁置了心事,他们在草香之间悬空般高大而静穆。
咏华君,我总是爱着新鲜的草香,就像爱早晨的日出与河畔饮水的马群。它们都冷静、温柔而热烈,都能将我推入瞬间的梦境,又使我倏然间清醒并长久感恩。我曾想,我可以不要一整夜的睡眠,甚至不要食物与篝火,只要带着昨夜浓郁的草香,就能一人一马静待对岸的日出了。
所以请不要奇怪为什么我总是喜欢停留在那些草坪或绿化带修剪机砰砰砰嗡嗡嗡的响声范围内,为什么总要闭上眼睛繁忙地翕动鼻翼。我只是想更多地吸收那些来自植物的新鲜赐予,只是想短暂地在青草的迷恋中做一小会儿白日的美梦。
而整个上午我做的正是这一件事,站在城市广场环绕的紫藤架下,闻绿化带修剪机送来的一份新鲜的金叶女贞香。我甚至走到那台修剪机的跟前,俯身在刚刚修剪过的女贞身上闻了一闻,那份浓郁的甜香,真是无可言喻。
无可言喻的还有鸽翅。城市的广场上总是聚着一群群的鸽子,正如乡村的树下总是聚着蚂蚁。稍稍不同的是蚂蚁总是精瘦,而鸽子又总胖乎乎,即使被一个戴口罩的学步小女孩驱赶,也是不慌不忙,飞上去又落下来。但它们扇动的翅膀却让我吃惊,它们扇动中的翅膀不仅仅带来视觉反复调整后的清晰与恍惚,更重要的是,它带来了时间缓慢耸动的流逝感。
像河水一样,鸽翅的振动让时间的流逝在眼前定格,并带着响声一点一点放大。静观者之心,会因此而缓缓加速。
是啊咏华君,鸽翅振动着从我身边带走了时间,我相信,它也带走了你的。虽然你更迷恋于春日的花朵而很少留意那些胖乎乎的鸽子究竟如何扇动翅膀。但时间又能饶过谁,像对待我一样,它也掠过你的窗前花圃,带着花朵消失于下一个季节。
作为时间隐秘的携带者,鸽子们咕噜噜转动的小眼睛里有我们流失的能量。所以,如果它恰好落到你窗前,请尽量不要与它长久地对视。这些天外的来客,礼送出境即好。其实,它们也会飞快地自行脱身——有更新鲜的时间在远处召唤着它们前去。
所以真是快啊,一个节令又一个节令都在鸽翅声中飞速消逝。而去年时令我忧愁万端的紫藤竟又开花了,远望巍巍然,如一座花朵堆起的云山。但我不爱这满架垂挂如流苏的紫藤,它们,其实是安静而鲜艳的带毒者。它们将携带这份鲜艳开过整个夏天,并安静地遗下带毒的种子。但有那么多的孩子爱它的花,爱它长豆角似的种子,嘴馋的人还食之津津而不怕肚子痛。但这又能怪谁呢,这世上偏偏有人就爱肚子痛,正如我之爱日常的忧闷以及你的——爱日常生气。
所以,我真同情那些爱吃紫藤的人,却又不以为怪。不以为怪的时候,我就可以空着一张肚子去大吃我母亲刚烙的槐花饼了。
咏华君,忘记对你讲啦,这几日的风也渐渐吹开了一树一树的槐花,而槐花开时正是我大快朵颐之时也。少年时在老家,清明后便时仰高树,看屋后的槐花到底开了没有。等到得谷雨,风吹几吹,雨润几润,院子中就可以闻到槐花香了。槐花下树,便可以焖饭、烙饼、拌馅包饺子。但我最爱吃的,我母亲也最爱做的,還是槐花饼——
白面以为浆,槐花洒拌之,调匀摊上鏊子,在滋啦滋啦的阵阵轻响中,一张薄而金黄的槐花饼就可以趁热吃了。
吃槐花饼时我爱反锅盖以盛之,一张热饼摊在锅盖上,手持盖柄,就可以转着圈儿吃而不觉丝毫口烫。此一节,乃儿时智慧,我还从未对人讲过的。
而进城后槐花饼不得常食有数年矣。其实这城市是号称唐槐之城的,谷雨后槐花也一树一树开得人心乱。但我撒不得野,使不得蛮,爬不得树,亦无登天之梯。有一年我实在没忍住,就袖着一根铁丝做的钩子,乘夜去了附近的一棵老槐下。等努力站到一块石头上,我就带着偌大志向,朝头上开得喷香的老槐使劲啪了一钩子。只是——老树几乎一动没动,我的钩子却脱翼而去不见了。
树下摸黑找了半晌,一抬头钩子却吊在树上。满树的槐花白白的,竟都不是我的。
而那一夜的槐花饼,我其实最终还是吃上了的。咏华君,你能想象一个深夜围炉骑马一般烙饼人的模样吗?他深爱着窗外的草香与清晨的日出。
(庚子年,谷雨,并州闻钟斋)
重瓣朱槿的第二朵
咏华君:
家里的重瓣朱槿开了,需要说于你知道,因为我记得自己曾经说过,要与你“木槿为号,相遇于烽烟旅次”的。如今这阳光无限推送的窗外虽不见烽烟,但远门是轻易出不得的,只好细说一朵木槿,遥为长思吧。
花开了一前一后两朵,仿佛约好的两个急匆匆的信使,第一朵几乎凋谢在晨光里的时刻,第二朵乘夜盛开了。虽然不是在同一天,但它二者在时间之中的距离,我差不多可在一次大醉之后一觉睡过,或者再睡上一觉。
虽然我其实并不常常大醉,尤其是即使真的大醉,我也是要昏昏然早起的。你问我这样昏昏然早起来做什么,那当然是能做什么就做什么了。真的什么也做不得时,还可以发呆、假寐,做一小半的昼寝之兽。
在我的观察中,重瓣朱槿的第二朵开得较有法相,兼藏并蓄又缓缓不言的样子,而第一朵有点像饮酒时的我,完全无城府,又是个自由散漫派,忽一下的就把该说不该说的话全说完了。
她也可能是受了暗伤,在虫豺暗布的来时旅途上。她需要争取时间,在苟延残喘之后。
但无论前后的哪一朵,重瓣朱槿这样的花在我看来,都携带着无尽的秘密,要与时间来一番隐隐的抗衡。就像衣带里藏着一封密信,或帽檐里夹着密码本的女人,她们想要藏在日常时间的烟尘里,释放能量,有所作为。但一切的密信和密码其实都是藏不住的,即使对携带秘密的人来说,秘密也从来不是一种成就,而是期待被解脱的一身重负。所以重瓣朱槿总是显得沉甸甸的,它似乎总是有心事,侧身低着头,又努力着想抬起来。以至于我脱离了常识,暗自思忖,它名字里的第一个字,究竟是读沉重的重,还是读重叠的重。但无论它读什么,重大概都是秘密的代言者,前者是暗自里的表征,沉甸甸的;后者,可以说是一种袖里乾坤吧,重叠了,就有秘密存身的偌大空间。
但这样粗糙的文字学解密又有什么意思呢?咏华君,当心领神会,什么都不说透,才是最好。
但秘密总是会被说透的。这有时候要带着朱槿一样暗红的血。当秘密一旦一瓣一瓣绽开在夜色里,当灰尘的颗粒在花盆后的阳光中清晰可见地升腾,花朵秘密的使命就结束了。携密者沉重的压力瞬时间解脱,像一下终于浮上水面的潜艇,可以被爱情的嘴唇迎接,也可以被炸弹铺天盖地间轰炸,但总之,天空是真的好美啊。
重瓣朱槿似乎也正是这样,它感叹着天空真的好美呀。所以我并不奇怪,为什么它的花朵在枯萎时反倒更加好看而自如,如一腔秘密都说尽,可与风月同此天地而无愧无憾的样子。尤其是你从背面悄悄看过去,她很娴雅,很安静,甚至很喜悦,虽然悄无声响,虽然颜色正渐渐褪尽,但恰因此可以长长久久,安安稳稳,肌理和畅,于绿叶中,像一个伟大的老妪缩身在孤儿院游戏的女孩群中。
我敢說,第二朵几天后一定也是这个样子的。她送来的是夏天即将来临,而她的姐姐,或者早殒的妹妹,送来的是春日已经结束。
咏华君,春日已尽夏日将临的时刻,我终于睡了数月以来的第一个长长的好觉,虽然昨夜也并未大醉,虽然昨夜也饮了酒。
酒醒时,下床穿衣,我发现我的衣竟还是四五年前的衣。穿上这四五年前的旧衣时,我忽然惊觉,四五年前热爱的、亲近的、相与饮酒的人,竟已寥寥无几了。
在旧日亲近者寥寥无几不如一件旧衣能得长久的寂寞的早晨,窗台上阳光下的重瓣朱槿的第二朵开放了。
我细细说于你知道,以为无可旅次的一份长思。
(庚子年,春尽时,并州闻钟斋)
崇善寺的雪糕与山口百惠
咏华君:
天热,一下子让人猝不及防。衣柜里的夏日衣物还没翻拣出来,夏天已迅速抢占并坐稳了它的位置。大街上的铸铁灯杆与不锈钢垃圾桶是发烫的,公交车上塑料座椅是发烫的,35度左右的温度啊,贴身的秋衣秋裤是发烫的。
弟弟说,今天我的太原热过了他的佛山。
尤其发烫的傍晚,下班过河时,我在忽然一下就变得空荡荡的公交车上,发现一本被遗忘在对面车座上的《知音》杂志。一瞬间,“知音”这两个字让我在恍惚中觉得久违了的亲切与熟悉,让我重新想起你来——在奔涌的汗水中,在从车窗里迅疾灌入的河上凉风里,我想起你来了,想起我需要重新专注,去认真描述这知音被遗忘时飞快进驻的夏天。
夏天开始的时候,我开始习惯在嘴里插上一根雪糕慢慢踱过崇善寺的黄昏,看一只猫逆着光从夕阳笼罩的月门洞上穿越今古。在夕阳中,在夜晚到来前,我爱上了紧贴舌头带来冰凉粗暴感的一种又一种雪糕。它们有许多种,满满当当塞在唐久便利店进门处的冰柜里,像彩色的药盒儿塞满在隔壁的药店里。我迅速依赖上它们,我无法不依赖它们,一种从口腔开始的夏日疗愈。但雪糕真的挺贵的,甚至比药片还贵,我前天买了三个醉花樱是十九块八,昨天买了两个橙子芝芝是十三块六。今天我就只买了一根冰棍,两块钱,也很好吃,它的名字是“粽子熟了”——冰块里封冻一块带红枣与豆沙的糯米,我很喜欢。
嘴里塞满一块凉凉的红枣豆沙糯米冰棍走过崇善寺的黄昏时,我觉得寺门前的两只铁狮子也是开心的。它们咧开的大嘴今天笑得自然,一点也不勉强,和开门捧着小米出来喂麻雀的老僧笑得一样。
老僧一次一次把黄灿灿的小米撒到寺门左右的两只大碾盘上,小麻雀就一群群就从槐树上跳下来。一起从树梢、檐头、墙头上下来进晚食的还有高深莫测的喜鹊,以及胖乎乎的鸽子们。它们落在碾盘上,不慌不忙吃起来,它们的小米是富裕的,而我叼着一根冰棍从一只碾盘走过另一只碾盘时,嘴里早已是空空荡荡的了。
咏华君,我还是怀念我们小时候的老冰棍啊,硬邦邦的,糖精甜得浓烈,被它硬邦邦地塞满嘴巴说不出话来的感觉是多么值得留恋呀,好像可以一直不说话从学校门口顺着断流的河床吃到家门前,还可一直接着吃下去,吃到今天。但那样的老冰棍和旧日子毕竟早已过去了,如今的冰棍只能从寺门前的一只碾盘吃到另一只碾盘,就没有了,而你走出去好远,一回头,小麻雀们竟然还在吃。
真让人生气。
红枣豆沙糯米冰棍吃完时,我一扬手偶然发现拇指宽的竹片上有印刷体的字迹,认真一看果然是有一行字,反过来一看也是一行字,正面是“升职加薪符”,背面是“有钱有颜符”,这真是美好的祝愿啊,无论正反,一瞬间都让我有点感动了。尤其是,联系到冰棍之外扑面而来使我脱不开身的近来现实,我真的是不能不感慨了。
我甚至都以为,这竹片正面与背面的符,是崇善寺门前摆摊卜卦的人趁我不注意偷偷印上去的。这些替人卜卦者,男的女的都有,都是衣装古旧,脸上装着世界奥秘的样子。他们生意很好,面前总坐着一些年轻的女孩子,伸着一只迷惘的手让卜卦的人握住,喃喃地说着些什么。
那些卜卦者以前也常常看着我,用下巴与眼神暗示着我上去坐下来,也伸出一只手给他们握一握。但他们后来似乎放弃了这样的想法,我于他们而言,已经是一个不言不语每日过路的熟人了吧。
但是明显带着心事,我想他们对我还并不死心。
咏华君,这夏天最开始的时候,我是心事沉沉的。面对一根冰棍之外的生活,我感到自己是如此慌乱,如此焦灼,如此觉得自己仍与十多岁时面对数学一样虚弱,一样被人反复摆弄着却无力反击。这种很糟糕的感觉就像前天深夜里的小腿抽筋,那么一小块腿肚子上抽搐着的疼让你全身发僵,让你感到平静再也难以坚持,让你想蹬着腿脚狠命挣扎,又想干脆放弃这种根本不解决问题的徒劳反抗。
而我已经不再是十多岁时了啊。夜晚包裹着我,带着一条抽筋的小腿,分分秒秒,踏进了中年。
我用抽筋的中年小腿使劲踢蹬的这个夜晚,窗台上放着的重瓣朱槿,前几日还开着的那一朵,忽一下就脱离它的枝头,掉到楼下人家的窗台护栏上。
这是我第二天早上才发现的。我想下楼敲门去索要,那凋谢的一朵失去颜色的花我还可以夹在一本新书里做成标本的,但最终我还是没有去。我怕那家的女主人问我每次浇水时为什么总会滴漏一些到她家窗台上的事。
咏华君,带着这种谋事而不成的无力感踏入中年后的夏天时,我爱上的另一件好东西,是山口百惠的歌声——那种我无法捕捉在手、无法准确定义的既飘渺又热烈而浓情的天籁真是恍如拯救。我彻底敞开自己,从早到晚让它们灌满我的耳朵,让它们久久回荡在我的心灵深处。它们让我感到不堪的生活仍然是足以留恋的,仍然是值得鼓起一份余勇去面对并克服的。
就像我前天深夜带着抽筋的一条腿在无法入眠时起身看的一集美剧里的话:你不能忽视你的痛苦与沉重,有人告诉你要忽视它,对它闭上眼睛,至少不要去直视,它的确可能因此而短暂消失,但这会使你的内心更加软弱。你得随时提着这沉重、这痛苦去行动,时时刻刻记得它,让它成为你内心的一个部分,直到你能够轻易挥舞,它会无限增强你的力量,所以来吧,拾起地上的这把重剑,我们再来一次。
这是在峻岭的教堂中,一個电闪雷鸣的深夜,一个老年修道院长对少年骑士图里说的话。我忽然就听到自己心里去了。咏华君,和那个要去为国王送一封信的图里一样,我们也许同样怀揣着一封关系重大的密信,需要带着沉重与痛苦,送到一个尚不可知的终点。
所以,我决定要越过这笼罩在头顶之上的迷雾,越过这夏日开始时心头的种种不堪与折磨,带着一条抽筋的左腿,重新鼓舞着走向清醒的早晨。
早晨我清醒着出门,一抬头,槐花仍在白,泡桐花仍在紫,空气一块一块的,供应着不同的香甜。很美好,只是我忽然感到,这些头顶上的花啊,真是要比我们这些人对生活来得更赤诚。
你看,它们一心一意从春天开到了现在,它们还要一心一意,从现在一直开到时间里的终点。
它们也有一封信要送,送给我,送给你,也送给无数迷惘的、丧气的、但一颗真心犹存的人。
它们正赤诚地跑在长路上,像骑着黑马蹚入了大河的那个少年。
(庚子年,立夏前,并州崇善寺)
寻找鱼腥草
咏华君:
翻《中草药彩色图谱》,寻鱼腥草。在第405页找到了,这是典籍中的第860条,一种腥臭的植物。
别名臭菜、臭根草、臭灵丹、侧耳根。
之所以找这味草药,是年来我常服鱼腥草复方口服液,用来防治上呼吸道感染,还将其热情荐于熟人,非常有效,所以就很想知道它究竟为何物。
对有效的东西,我常想求根问底,以求效用翻倍。这算是我的一个经验,也是一个功利主义者的毛病。
但这一查之下,就不想再服它了,只因名字太坏。由此看来,我不仅好貌相,还爱因名而加青白眼,这真是不太好,但也真是没办法。
但也可能,好东西都有一个坏名字吧,恰如时下的坏东西都有一个好名字。所以,鱼腥草日后怕还是要服的,因为人不能因为一个坏名字而不治自己的病。
病才是真的麻烦,恰如麻烦都是必须去解治的一种病。
但咏华君,我今日为寻鱼腥草而翻药谱,最强烈的感受,还是别一种。那就是几乎我们身边的每一株草、每一棵树、每一朵花,都是药。譬如你窗外种的腊梅,你天天跑去看的木槿,你好奇不解的旱金莲,以及我窗外的丁香、合欢、槐花,窗台上日日凝望的虎耳草、金钱草,连带窗外墙壁上的爬山虎,都是药呀!
这么多的草药罗列在大地上,我们的身体该是有多少的病痛啊,以至于上天如此垂怜,降下这许多止痛解苦的草木来,只留出一分半垄的空隙供我们驻足,并偶尔透过它们的枝叶眺望远方。这让我忽然觉得有点奇怪,仿佛梦里置身于庞大的药店之中无法找到出去的门扇。
难道真的是这样么——这些日常植物与药物之间,有着怎样的距离?又有着怎样的联系?而典籍煌煌,就在眼前。黑纸白字,图文并茂,中西对照,条分缕析,证明它们的确各具药性。而于我这个闲翻典籍的人而言,它们已是那些彩色图片中看起来十分陌生而怪异的药用植物。与我们日常经见的、熟悉的、喜欢的花草树木已经距离甚远。
也许无论什么东西,一论实用,距离便远了吧,也就显得陌生而冰凉。
就像这些归入药谱的草木,也许它们真的都是药,但,我们一旦真的病了,哪里靠得住这些身边触手可及的草木呢?又怎么敢把自己的性命托于草木呢?细细想来,我们对它们其实真的甚为陌生,真的还十分无知,以至于不能透过那层日常的可怜经验,抵达它们的根性深处,抽离它们作为药的化学部分为我所用。
这又使我想到,我们生活中有意无意之间积攒起来的熟人,亦如这些草木——也许的确各具所能,但我们还远远不足以接近他们的本性,只是在远观中模糊地窥见了一丝半缕可供赏玩的优点罢了。这样的熟人,无事尚可通有无,遣闲情,遇大事则几无一用矣。
你我怎能将身家性命寄于这般熟人呢?须知,我们还远在他们之外,如在一棵高高的合欢树下幻想与花心中飞舞的蜜蜂谈生意。
它嗡嗡嗡嗡的一阵,就飞走了。你再多说几句,它就要落下来,蜇你一下,毫不客气。
但咏华君,莫要悲观。今日闲翻药谱,也有一些暗自惊喜,因为发现了许多可爱可喜的名字。譬如:
野马追、鹿衔草、仙鹤草、鸭跖草:它们的志向都长着腿脚,它们唇吻亲切,表情憨厚。
飞龙掌血、虎掌南星、绵马贯众:你说,它们像不像金庸小说里的功夫煞星,手段狠辣但并非恶人。
救必应、独一味、十大功劳:前者说大话而不惭,却亦有几分功夫。而后二者真是敢于骄傲。
阿魏、青黛、陆英、昆布、马勃:都像我们朋友的笔名,善写小说。
望江南:我喜欢的最后一个名字,它让我无限地生出对前世与故人的纷纷想念。
(庚子年,立夏前,并州小石山房)
猫夜啼
咏华君:
隔壁猫叫。嘤咛凄清如小儿夜啼,让梦中惊醒者一阵阵心慌——直以为是梦境未断,而忽然转折掉进了下一层。
我本做着一场美食与泳池的好梦,但吃的什么在听见猫叫的一瞬间便全泡了汤。
这让我愤恨。
我起身走到门前,想摸黑找根棍棒,突然推门出去把楼道里的护栏使劲猛敲一通,但那猫叫声忽然间微弱了,它似乎不是在楼道里。我返身回到阳台上,想开窗把铁护栏使劲敲一敲,好把那藏在隔壁阳台上的猫吓一吓,让它停止这深夜凄苦的哀叫。
但我终于还是没有去与楼里夜哭的这只猫正面对抗。我深信,夜哭者肯定有自己认真的理由,即便它是一只猫。我更相信,惊吓深夜的一只有理有据的猫是种不祥。如果真的与它针锋相对,真的将它劈头盖脸地赶跑,它回头时哀怨的眼神会在一瞬间把我从立定处推远,远得回也回不来。
猫是有这样的力量的,咏华君,在深夜的剧集里,它们据传是巫的前身。所以就且由着它,让它继续为了饥饿、为了病痛、为了性爱的折磨而哭泣吧。
这真是受苦。
这只反复用深夜的哭声为我勾画自身哀苦形象的猫,或者这几只猫,我其实常常在楼道里碰见它们。它们的毛很长,个子也很大,有些形销骨立的瘦,站在洞开的窗口前,常常像一只落魄在夕阳里的病虎。
在楼道这样的人间角落,它们本该是享受到与它们作为一只猫相应的待遇的,比如充足的食物、温柔的床铺,以及恰如其分的爱人,但是,它们似乎并没有得到这些。它们难得安稳,需要四处流窜,需要扒开我门前的垃圾袋,需要在我早上一开门时喵呜一声窜进来,寻找片刻安慰。
这时候常常是冬天,楼里很冷。但我实在无法安慰它们,它们只是会让我感到慌乱。作为生命,它们没有得到该有的对待,在我这里也没有。这是一定的,所以它们哭,带着凄苦的诉求,从冬天一直到春天,再从春天一直到此刻的入夏。
它们几乎无一日不哭,无一夜不求,如同教徒在绝望时的喃喃祷告。
咏华君,我觉得这样的哭求是可以理解的,这并没有什么不可理解。即便这是一只让入睡者无法再入睡的貓。
实在无法入睡了,我就卧听山口百惠。耳机里的歌声,慢慢为我的烦乱套上了襁褓,令我渐渐安稳如婴孩,慢慢重新进入梦的围裹。
再醒来时,窗外风声很大,一场夏雨在重瓣朱槿飘摇的叶片上酝酿。我喜欢酝酿中的事物,比如几朵新生的花蕾,比如床上慢慢长大的孩子,比如风起云涌时的一次约会。
其实昨日午后就已经起风了,有个穿裙子的女人在院子的尽头扯着根绳子放风筝,我隔着窗子却看成了一片彩色塑料在天上飞。我站在窗前,看了那只飘飘摇摇的风筝很久,它一直都没有飞起来,一直像一块不甘心的彩色塑料,但忽然之间,我有点心痛——我觉着了一个人的努力拉扯,在另外的眼睛里,结果就是一块不安分的塑料呀。
这个事,挺有意思的。但究竟有些什么意思,我却也说不明白,只是想让那拉扯着风筝的女人,再多拉扯一会儿,为了她自己。
恰如晚来树下风好,我就站定在树下让它多吹上一会儿,再提着一瓶没喝完的老酒慢慢走着回家。路上遇到穿情侣装的一对妙人,又像是穿着附近酒店里的睡衣出来晚风中散步的样子。这让我开心。
我开心时眼前忽然就一个电闪,没错儿,那就是一个真的电闪,像远远在天边,又像是在我眼前的上方一点点。
我想大街上只有我一个人看到了,因为我一个人开心。
而此刻的清晨,昨夜电闪预告的雨在我身后终于下起来了,它们真够慢。我希望它们能多下上一会儿。这样,我就可以听着雨声写完给你的这封短短的信。
忽然又记起来,今日原来是青年节啊。这真是有点不好意思,如今——哪里找得到青年呢,哪里还有如利刃新发于硎的老牌子新青年啊。长着青年脸面的人,非老人,即婴孩。但他们一定从不这样认为,而我们无论怎样认为,在他们怕都是一声远远的驴叫。
而连我们自己其实也从未年轻便已过早衰老了——有人一定也是这样看我们的。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一声声的驴叫里,自觉年轻的人永远年轻着。管什么前浪后浪的献媚声。
不如隔窗且听风吹细雨,看过路的飞鸟呼啦一下跃上红色断墙,看墙上乌云分解,看闪亮的雨点如灵魂中突围的新物质,慢慢打湿榆树的腰身。
这真美。
这雨且要下呢,夏天更长,我们之间的话还可以慢慢来细说。
(庚子年,立夏前日,并州闻钟斋)
回梦树
咏华君:
一下雨,树的脸就露出来了。
它们站成一排,忽然一下子,就把表情不一的脸齐刷刷转向了我。好像它们站在雨里一整天,就是专为等我从一个地方慢慢走到这里来。
这真是令我吃惊的一件事。一群深藏不露的人集体在某个地方等着你出现,在你出现的一瞬间,他们把准备好的脸忽然间从雨幕中露了出来。
这应该是谍战片里常见的一个桥段。紧接着,大概就是枪声、围捕以及奔逃中的人仰马翻吧。但此刻在雨中,这些树木的脸又像是站立在梦的边缘,麻木而鲜活,冰凉而热情,久违的亲人一样以湿淋淋的饱含着意志力的忍耐,把一个刚刚走下公交车的过路人带进了他偶然参与过的一个迷梦。
那个梦他早已经忘记,忘记是因为他感到了恐惧。
咏华君,我是说,作为一个忽然被雨水中的树木导引着开始原地转圈的人,我忽然重新进入了我曾经参与过的一个梦。
这个梦,它带来的恐惧无法终止时,我只能拒绝再睡并反复拒绝。而梦中的那些人似乎直到今天还没有忘记我,他们呼唤出了一个连绵的雨天,并派遣出了一支搜索队,好押解我回到那个我该回到的地方去。
但我似乎又不该属于那个梦境。那个梦境的尽头,我独自一个丢弃了那些熟人,丢弃了我们共同承担的一个集体使命,我逃离了。
我逃离的全部原因,是因为我感到了恐惧。而恐惧的全部,是我不知道那后面究竟有些什么。
只记得——是我的一个熟人,一个充满魅力的女同学,忽然走进来找我借衣物。
她说,这些衣物要借去做一个大用处,我们参与这次集体行动的每一个人都要借,谁也不可以拒绝。
我说我不愿意,我的衣服都还是崭新的。
她就很不高兴,但也没有坚持,只是等我打哈欠时,她突然在我的床铺前弯了一下腰就走出去了。
那似乎是一个夜晚,人们都即将要睡去的时候。
我们每个人似乎都睡在一个单独而狭隘的地方,但似乎又睡在一个共同的屋顶下。一盏油灯,吐着长长的舌头,我们都可以一抬头就看见它。
那个女同学就坐在油灯下面,我们也都可以一睁眼就看见她。她手里似乎一直在忙着些什么,我却看不清楚,她和我们每一个人之间,似乎都隔着很遥远的距离。
而当我忽然从梦中的短暂睡眠里醒来时,我下意识地感觉到我的什么东西被拿走了。果然,我的一双崭新的安踏鞋不见了,我就光着脚下地走到了刚才找我借衣物的女同学跟前,质问她是不是刚才提走了我的新鞋。
她说,一双鞋,你本就该主动捐献出来的啊,不止鞋,还有你的那些衣服,我已经一并都拿过来了。这时我才发觉,我是光着身子站在黑暗中。她真的是偷偷连我的里外衣服都拿走了。
黑暗中唯一的那盞油灯,忽忽闪闪亮在女同学的头顶上。她的身后躺着一排排的人。
她说,你就委屈一下吧,我们这么大的一次行动,必须依赖于这次捐献。
我说,你赶紧把我的鞋还给我。她说,已经来不及了,你看——
我低头一看,在油灯光伸展下来的火苗中,我发现,我崭新的安踏鞋,已经蒙上了一层黑纱。那黑纱显然是刚刚用针线缝上去的,扯断的一小截线头还清晰可见。
我很生气,又感到害怕,说你这是干什么?
女同学似乎也很无奈。她说:“我必须这样,要不,我拿什么去给他们穿呢?”说着,她侧了一下身体,指了一下身后那一排排躺在白被单里的人。她说,我必须给他们找到新衣服,新鞋子,明天,我们这些人要把他们送到该去的地方。这就是我们这一次的使命。
我什么都没说,只是撕下了那一层黑纱,并把鞋子狠狠套到了自己的脚上。
而在第二天拂晓时分,在一阵骤然的枪声中,在女同学率领的运尸队被敌人伏击的一刹那,我逃脱了。不,应该说,是那些穷凶极恶的敌人旁若无人地从后面越过了我,直扑那些光着脚抬着担架行走的人——我的抬着一床床白被单艰难行走的队友们。
而我大声喊向他们的示警声,似乎那样无力,他们又似乎离我那么遥远,以至于一瞬间,他们便淹没在敌群中。
而我光着身体踩着一双崭新的安踏鞋,反复倒动着双腿,终于冲出了那一片枪声之外。
而咏华君,此刻,在黄昏的雨水中,从树木中忽然露出来的这一排排的脸,似乎是要重新带着我回去,回到那一阵枪声之中,回到那一盏忽忽闪闪的油灯下,回到那位既美丽又无奈的女同学跟前。
如今,她应该也躺在了一床白被单中,等着我主动送去一双新鞋。
咏华君,如果真是这样,那这次我一定会主动捐献给她。
因为,忽然之间,就在此刻,我想明白了那个梦的后面究竟藏着什么。
就在此刻,就在这对你的倾诉中,我忽然明白了那个梦究竟所从何来了。而这些雨水中忽然露出来的树的脸,其实是为了把我的那一份恐惧收回去,收进它们深沉的树的表情中。
它们,的确是从那个梦中来的,带着巨大的解脱的善意。
(庚子年,立夏后,并州闻钟斋)
责任编辑? 包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