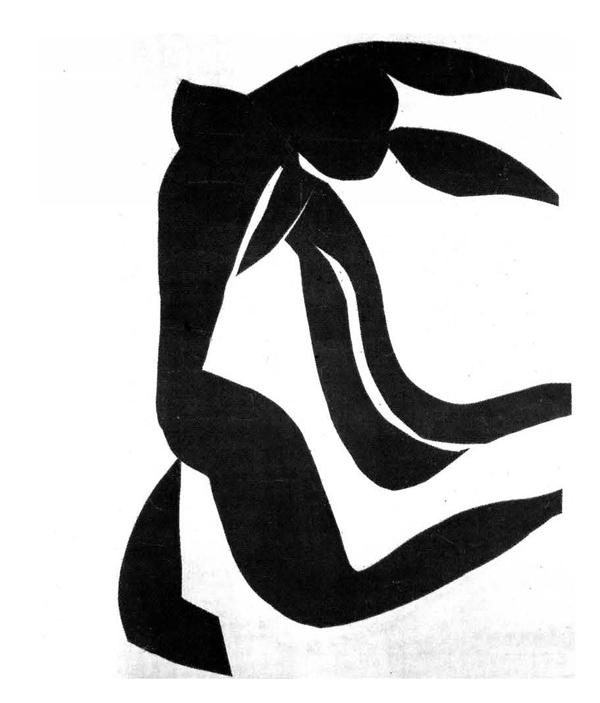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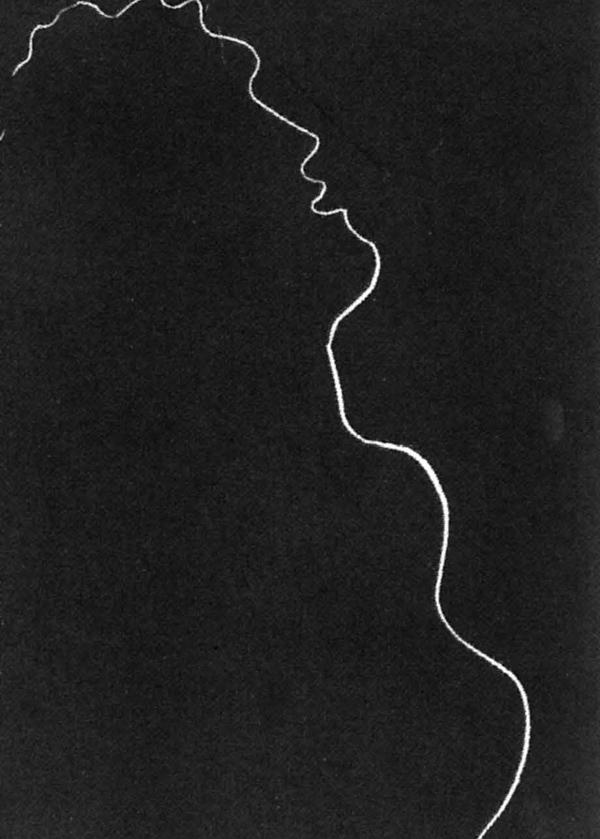
沙尘暴终于消停了,好像一群猛兽,在大地上撒欢和迁徙完毕,又躲在某一片人迹不至的地方,开始了它们的宁谧时光。日光随之凌厉起来,落在戈壁上,似乎一层水汪汪的油脂,傍晚时候被星光和夜幕扑灭。妻子打来电话说,你该休假了!我说,明天就去请。这是遥远的巴丹吉林沙漠,古书上所说的瀚海泽卤,赵破奴和路博德修筑的汉长城边缘。几近于荒芜的绝望之地,无论多么遥远和亲近的过往,都必将消失无踪,其中闪光的成为历史,琐碎的湮灭无声。人和万物莫不如此。
沙漠兀自浩荡,在无际的苍天之下辽阔而欣欣向荣。在时间之中,这一过程,万物的宿命一次次重蹈覆辙,又一次次卷土重来。当我在沙尘暴和酷烈的日光之下,踩着松软的沙子,走过青春期之后,迎来的是与其他人一般无二的婚姻生活。而生育,总是有一些肉身欢愉之外的突如其来的感觉。我还记得,那一个秋风横扫的傍晚,整个巴丹吉林沙漠都沉浸在了无限的怒吼与晃动之中。灯光如此昏黄,呛人的灰尘自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木质窗棂缝隙鱼贯而入,躺在已经发冷,但因为两个人的肉体拥抱而有些温暖的床上,妻子在我耳边说她怀孕了!
我僵了一下,继而脑袋空白,瞬间整个身心犹如薄纸,酥酥的、皱皱的、麻麻的。妻子嗔怒。我抱着她解释:不是我不欢迎我们的孩子,而是思想上还处在蒙昧状态。你这乍然一说,我觉得了一种雷击式的欣悦与不安。当然,还有一种生活即将为之改变的讶异甚至震惊。妻子眨了眨眼睛,微笑着告诉我说,她确认这一消息时,也有与我差不多的感觉。
生命的到来如此不期然,有着闪电的猝然与猛烈。当妻子的小腹越来越大,宛若沙漠里最美的那座沙丘的时候,我多次听到了一个新生命在她肚子里的各种声音和动作。到九个月,可以看到孩子伸胳膊、蹬腿的形状和速度。我欣喜,伸手摩挲,隔着妻子肚皮,与就要谋面的孩子肌肤相亲。直到这时候,我才真正地调整好了自己的心态,而且在内心和灵魂当中,让自己作为了一个父亲的模样和姿态,当然还有心情。
作为一个结婚两年不到的男人,我已经跳出了婚前的那种自由和婚后的各种混乱、不在意,跟随妻子肚皮胀大的速度,真正地把自己调整到了准备做父亲的状态。请假回家,十多天后的一个周末,妻子突然说肚子疼,赶紧去到单位医院。检查之后,医生说胎位不正,建议我们及早去513医院,并说,这里的医院相对简陋,要想顺产的话,必须校正胎位才可以。斯时,戈壁沙漠的天气空前暴热,毒烈的日光把稀少的杨树都晒得满身皱褶。513医院也是军队医院,隶属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我们虽然是空军的,但也可以凭本部队医疗单位开具的介绍信,来这里看病或住院。
医生和医院是生命的校正点与收容地。身处沙漠的军队医院,也拥挤不堪,但一切都按照既定的规矩来。确定剖腹产,要手术了,我推着妻子,眼泪不由流下,一滴一滴,打在她脸上。她伸手为我擦拭,说,没事的,一会就出来了。可我总是想起岳母那句话,女人生孩子,就像去了一趟阎王殿。我这个人天生有很强的恐怖感或者不祥的想法,总是怕身边最亲的人,有个什么不测。
两个多小时后。医生抱着我们的儿子出来了。岳母欣喜,跟上看。我仍旧在等妻子。妻子出来了,我赶紧从医生手中接过推车。妻子脸色苍白,但面色幸福问我说,为什么不跟妈一起去看儿子呢。我说,还是你重要。儿子刚才被护士抱出来了,我也看到了他。等你出来,你没事儿,我才真正放心。这些话,当然出自肺腑,直到现在,我仍旧认为,自己的做法是对的。因为,无论我们出生于谁的身体,勾连了多么深广的血脉,但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始终一起的,只有爱人。
儿子一生下来就好哭,妻子挣扎着要去看。我征求护士同意,把儿子抱过来给她看。妻子面色激动、浑身颤抖,抱住儿子,也顾不得剖腹产之后的刀口疼,亲了儿子小脸,随后就把他抱在怀里,撩开衣襟,把奶头送到了儿子嘴里。
孩子终究出自母亲的身体,尤其是男孩,他天然地与母亲亲近,而且永不背离。这种血浓于水、有些玄妙的情感,体现在生活中,奇妙且绵长。我一次次记起,自己从小到大,甚至在自己儿子出生前,无论何时,都紧紧围绕着母亲,母子之间的矛盾与小型战争,也仿佛和父亲没有关系。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如此忽略父亲,甚至有点决绝与冷漠。直到儿子出生,我才忽然想到,自己是严重地怠慢和轻视了父亲的。往常,在我眼里,父亲,作为一个男人,似乎只是家里的一个摆设,做农活、出去打工、给乡邻盖房子、做木工、编荆条篮子等等,这似乎是他的使命,无缘由地由他来做。他就应当风里来雨里去,每天和日月的头尾约定,用双手和体力,为一家人挣来活命的钱。
2004年春节,我和妻子带着儿子回老家过年。春节前一周,父亲还在邻县修公路的工地。大年二十三,铺天盖地的大雪,一夜之间,掩埋了大地。公路结冰,车辆不能行驶。我站在院子里,看着莽苍苍的群山,提议去邻县工地上找父亲,把他接回来。母亲则说,也不知道人家啥时候放工,去了不放工,就算不了工钱。
在母亲眼里,工钱是核心。细想起来,这才是残酷,钱超越了人,而人,却不容置疑地退居其次。听了母亲這句话,我怔了半晌,胸口发堵。起初,对母亲的话,有些生气,但很快觉得,这完全不能怪她。现实生活如此冰冷,步步都张着獠牙。
大雪继续洋洋洒洒,在穷困的南太行乡村,进行着布道式的宣扬。我依旧站在院子里张望。阴灰天空下,白雪也都是灰苍苍的。对面的马路上偶尔有行人往来。突然,有一个人站在马路边,喊弟弟名字。我浑身一惊,知道是父亲,一个纵身跳下门前的冬麦地,跑了几步,又跳下去,从斜坡上,趔趄着跑到对面山坡。此时,父亲挑着一根扁担,一身大雪,走到我面前。看着父亲胡子和头发上结冰的雪,我使劲地喊了一声爹,哽咽着接过他肩上的扁担。
我炖了刚买的羊肉,端给他,看着他吃。这时候,我才真正发现,这个被我轻视甚至忽略了三十年的男人,大半生的苦难已经浸漫了他全身,他的每一寸肌肤和骨头,都发出痛苦的摩擦声。
到春节,我和父亲喝了几杯酒。是当时比较流行的宁夏红。大致两小杯,父亲就说他头晕,胃也不舒服。我看着他,给他夹了几块妻子炖的鸡块,又给他舀了半碗鸡汤,看着他吃完一块,再把另一块递给他。儿子和侄女在炕上玩耍,学电视里的戏剧,舞着妻子和弟媳妇的红围巾,咿咿呀呀地。父亲照例用袖筒抹了嘴巴,坐在炕沿上,孩子们一看到爷爷,争相趴在他背上玩。父亲咧嘴笑,又伸出一只胳膊作挡住的样子,怕孩子们不小心摔倒在地上。
这一幕,是父亲和我儿子在一起为数不多的温馨场景之一。再就是夏天带儿子回老家,父亲总是背着儿子,为他摘苹果,抓知了;秋天则给儿子烧板栗、核桃吃,坐在冬天的院子里,披着暖洋洋的日光,为儿子吹口琴……现在,父亲作古十年,厚厚的泥土上面长满了蒿草,我和弟弟清理了多次;坟头不断地被摊平,我们一次次地用土垫高。
父亲去世时,儿子八岁。按照乡俗,儿子作为长孙,要回去给爷爷打灵幡的。可事发突然,我们就没带儿子回去。送走了父亲之后,岳母在电话中说,我和妻子回老家的那一天下午,儿子放学回来,要姥姥去楼下院子里挖了一瓷碗沙子,还拉着姥姥去很大的集市上买了一把柏香。回到家,把柏香点着,插在沙子碗里,在阳台上跪拜。姥姥很吃惊,问他为什么这样做,儿子说,爷爷死了!以前回家,爷爷给他吹口琴、背着他去田里、给他捉知了玩儿、烧核桃和板栗吃……爷爷对他很好,现在,爷爷死了,再也见不到了,他应当给爷爷烧一炷香。
柏香點燃,袅袅向上,从有到无,全身的事物,都来自大地,也归于大地。借用烟雾的方式,完成从肉身到灵魂的过程。这其实如人一般。现在,儿子都是大小伙子了,个子比我还高一头。他去了绵阳读书,虽说距离不远,可他不在身边,总是觉得命里少了一件最重要的东西。闲暇时候,常想起儿子小时候。从513医院回来,妻子刀口还没好,天气又热,我给儿子洗尿布屎布。新生儿第一次大便是黄色的,还有些白色,不臭,但黏度很高。一开始,我还觉得脏,可看到他那张懵懂的小脸蛋,马上就觉得他是那么干净,即使粪便,也来自妻子的身体,甚至来自冥冥之中的某一些神意。
因此,搓洗起来,我一点也不嫌脏,每一次都格外起劲儿,心里觉得好像是在履行一种神圣的使命。那些时日,搓洗尿布成了我唯一的“业余运动”。儿子拉了尿了,我首当其冲,洗得手掌脱皮不亦乐乎。可我也慢慢发现,儿子和父亲之间,有一种天然的敌意,古老、顽固甚至残酷。起初几天,我抱他,他就哭,有时候咧着小嘴,哇哇不停,小脸都哭得紫胀,有时候像把声带撕裂一样,把黑夜都哭成了黎明。有一次,他哭得没天没地的,我气急败坏,大声对他说,再哭,我从窗户把你扔下去。这句话不小心被老婆和岳母听到,挨了一顿好骂。几年后,儿子懂事了,听说了我当时说他的这句话,倒是没说什么。一个下午,我和他闹着玩,儿子生气。我哄他说,我是老爸,你不要和老爸闹别扭。儿子哼了一声,叉着腰看着我说,我小时候,你要把我从窗户扔出去!
儿子几个月的时候,正是秋天,他感冒了,发了高烧。本单位医院看不好,我和妻子打车去当地的县医院。在秋风之中,妻子紧紧抱着昏睡的儿子,我在一边焦急得一言不发。儿子从母腹出来,就有八斤重,而且妻子奶水足,一直到五岁,他都是胖嘟嘟的。那一次,我也才知道,还可以从头顶输液。小家伙被剃掉了一片毛发,他哭,还乱动。我束手无策。等他长到四五岁,打针输液就不用人哄骗了,自己把手伸出来,护士扎几次他都不吭一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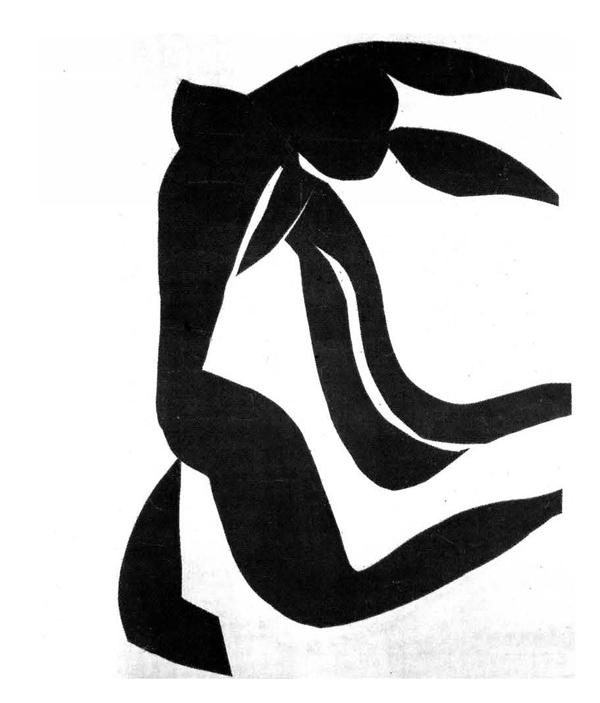
儿子的受疼、耐疼能力远胜于我,我有点疼,就龇牙咧嘴,哎呀娘啊乱叫。儿子继承了他母亲的基因。三岁时候,我给他买了一台赛车,骑得飞一样,真的是见沟飞沟,见石头故意压上去。有一次,小子脚踝破了,血都粘住了袜子,脱时,生生地把一片皮扯了下来,血赤拉乎的,儿子却眉头不皱一下,视若无物。我电话听说后,想起关云长刮骨疗毒,苦笑之余,觉得儿子真是了不起,能忍受我难以忍受的疼痛,至少这一点上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
儿子上小学二年级时,正逢父亲生病,我们商议着,要儿子也回去和侄女一起到村小学上学。儿子没怨言,跟着妻子就回南太行老家了。大冬天,早早起来,在奶奶那儿吃了饭,就和他堂姐一起背着书包到学校。那年冬天,我借公差回家数日,天天早上去送他们。到学校,儿子也和其他同学一样,抱着扫把扫地,和人一起抬水。乡村学校极其简陋,虽装着空调,但窗户都是破的。我送到校门口,儿子说老爸你回家吧。我要进去,他拦住我不让进。
其实我知道他不要我看到什么。
再后来,儿子和村里的一些孩子玩得很熟悉。有几个特别要好的,每天早上,专程来叫儿子和他们一起到学校,放学了,还把他送到家。弟弟的女儿性格看起来也开朗了许多。有一次,儿子要去小卖部买东西吃,我说不好,垃圾食品,他就和我闹。说着说着就哭了,然后自顾自地,迎着北风往学校走。我尾随其后,等他进了校门,又转进去,走到他面前,拉着他去小卖部。儿子却使劲挣脱,说不要了,不吃了,放开我!
那是2009年,在老家陪护父亲,又过了春节,我们决定带儿子回去上学。因为儿子在老单位子弟学校时,门门功课都认真,放学回家第一件事是做作业,字也写得非常工整。到老家小学后,字写得比我小时候还潦草,作业也是糊弄着过。我不是看不起乡村小学,而是觉得,乡村小学的师资力量还是很薄弱的,教小学的教师,大都是乡里村里干部的各种亲戚,有些干脆是女儿、儿媳妇,对学生是爱管不管,课堂上说了,下来再问就不耐烦。
离开老家的那一个早上,父亲躺在炕上哭了,看着儿子说,锐锐,再回来就看不到爷爷了。我们都哭。儿子走过去,抱了抱父亲的头,轻声说,爷爷不会的,我还会回来看你。可一个月后,父亲就不在了。我和妻子凌晨赶回家,父亲已经去世了,左眼一直没闭上,说是等我和妻子。
每一个人的最终,可能最想见到的,只有那么一个两个人。妻儿、孙辈、朋友、师长,以及诧然一面的陌生人……父亲左眼死了都没闭上,一直看着门口。
愧疚不仅仅是对逝者生前的各种亏欠,还有弥留之际的那种阴阳相隔。而后者,则是最痛苦的了。父亲逝后几个月,妻子专程回家把母亲接到西北和我们同住。有一次,母亲问我们儿子说:锐锐,以后你长大了有钱给奶奶花不?儿子说,当然给了。母亲说,那是为啥呢?儿子说:因为你是我老爸的妈妈,我的奶奶呗。岳母也问他同样的话,儿子也说,姥姥我小时候你带我多,我不能亏待你,等我长大了,我买一台大长车,把你和姥爷拉上,全世界旅游。有时候儿子也很吝啬,看到妻子或我给老人钱,岳母推辞的时候,儿子就说,姥姥可能不用,那就以后再给吧。惹得全家人哄堂大笑。岳父说,锐锐,把你老爸老妈的钱抢过来,我和你花行不行?儿子说,姥爷,也不是不行,可是呢,不能光咱俩花了,让他俩受苦,这样不公平。
2010年年底,我由西北调到成都,妻儿还在巴丹吉林沙漠。有一段时间,儿子接连来电话,要我给他做事情,甚至找他同学玩,都交给我办。我说我不知怎么联系。儿子就把他同学和同学父亲的名字告诉我,让我查,然后飞快地说,老爸我出去玩了,联系好了,你就给我发短信!还有一段时间,儿子对他妈说,老妈你说我爸这么长时间没给我电话,他是啥意思他?这事儿我俩得好好想想。妻子对我说,赶紧打电话给他。儿子说,老爸我现在正在游乐场玩,有啥事,咱以后再说。把我弄得心里七上八下,不知道小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距离远了,任何事情和事物都会起变化。在家庭中,人的自由确实有限,长期的分离导致的,不是情感上生疑,就是现实无常的逆变。2011年儿子生日之前,我想买礼物给他快递过去,妻子说没这个必要,马上就到一起了。还说,遵照儿子命令,她在饭店订了一个房间,邀请他要好的同学朋友一起来。
這种习惯,大致从他读幼儿园开始,就成了每年的一个规定节目。每一次,至少会有三十个同学带着各种礼物,如约而至。那时候,儿子就像一个王,在欢笑中接受那些同学的朝拜。一伙小孩子闹腾几个小时,就相约出去玩了。我负责给他照相。我想给他多留存一些生长的痕迹,将来,他看着,自然也会想起好多有趣的事情。
技术的进步,一方面让我们随时随地都能记取自己的一切活动;另一方面,科技仍旧解决不了人的疾病和终极问题。可以安慰的是,人也是有传承的,持续连绵,如这巍巍自然,亘古天地。父亲去世之前,我也给他拍了很多照片。存在电脑里,也洗印出来,挂在老家的墙壁上。每次回去,看着他那张瘦削悲苦的脸,看着他直视过往和现在的眼神,忍不住痛苦与哀伤,同时还有恐惧。
有些时候,无意中在电脑里翻开父亲的照片,盯看之间,仿佛父亲在说话,脸上浮起他活着时候的表情。我一阵惊喜,又一阵疑惧。道家理论说,人的灵魂不灭,所有逝去的人,都会在某个时候,借用另一张皮囊重新来到这个世上。父亲在世的时候,我对此一点不信,现在却越来越相信。
父亲和我,我和儿子之间,有一个惊人的相似点,那就是,我小时候不重视父亲,甚至把父亲视为摆设。现在,我和儿子之间的关系,也仿佛如此。在儿子面前,我是没有一星点权威的。妻子和岳母说我这人嘴碎心软。要教育孩子,他对的好的要鼓励,不对的要批评甚至打几下,不管什么事,说一句就行了,不要顺嘴流,时间久了,便在孩子面前没了威信。我知道这个道理,可做不到。比如,我刚训了儿子一句,马上就心软如泥,觉得不应当让他不开心;举起巴掌打他几下,就心如刀割。他做了错事,我也舍不得责怪他一句半句。懂事后,我和儿子,儿子和我,俨然不像父子,更像是兄弟。
儿子自小懂事,在老家,亲戚们都说,跟个小大人一样,从不说一句没道理和忤逆不孝的话。我对孩子过早成熟是有看法的,就像我总是喜欢和尊重大智若愚型的人一样。
在日常生活中,我也总是想到,自己小时候贫苦,吃块糖都如过年,奢侈而幸福,现在物质丰富了,不想要儿子也经受那种苦与卑微,别人家孩子有的东西,只要他要,我也会给他。物质有时候可以影响一个人的性格养成和处事方式,尤其是对待物质与享受的态度。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不想让儿子也成为一个十足的物欲者和自私的人。
记得儿子五六岁,存的零花钱比较多,有些年,不管是姥姥姥爷还是我们给的,他一毛钱都会攒起来,让他花也不花。先是一堆零钱扔在他房间的抽屉里,见到我们放的零钱也收进自己的小金库,开始满抽屉飘着,后来他自己用一只废弃的钱包装在一起,十块二十块五十块乃至毛钱钢镚,泾渭分明。有几次,送水的来,恰好没零钱,我便偷他几块钱。他开始自己不看,发现少了后就问,我的钱怎么剩这么点了?
姥姥、奶奶来了,他还拿出来说,你看奶奶、姥姥,这是我攒的钱。老人夸他,他很自豪。大概是他上小学二年级,儿子有段时间花钱厉害,有时候也不说,拿出来买乱七八糟的东西吃,怕我们看到,藏在被窝里。老婆认为这种行为不光明正大,男子汉,要吃就光明正大,理所当然,再说,爹妈也不是管不起他吃。妻子有一次教育他,打得厉害。我心疼,上去抱他,也被老婆呵斥了一顿。儿子在那儿哭,我在旁边干瞪眼,转圈,束手无策。
妻子是善于管儿子的,这一点,就像我母亲。小时候,都是母亲在管我,父亲则是对我爱护。我想这也可能是一个家族的传统。
读初一那年夏天,也不知怎么回事,同学都戴上了表。有的是好看的电子表,有的是金色、白色链子的石英表、机械表。我没有。有一天我发现,父亲手腕上有一块表,也不知道从哪来的。早上醒来,父亲要去干活。我尾随着他。父子俩,一前一后,在晨曦初染的马路上,甩着脚片子走。走了一公里多。父亲忽然转过身来,把手表从自己手腕上脱下,晃着对我说,来,给你!
对于那块表,父亲肯定也是很喜欢的。要不然,他不会等我尾随他一公里多,才脱下来给我。拿到表,我眉笑眼开。父亲一边走,一边说,好好戴着,不要搞丢了啊!又拿出两块钱,叮嘱我到学校外面,买点东西吃……在父亲离开的匆匆十年中,每一次回到老家,不论去田里,还是在村里,还有串亲戚,几乎每一处,每一个人,都能唤醒我对父亲的记忆。
妻子爱儿子,也舍得管教他。有时候很严厉,有时候还动手,打儿子屁股甚至脸蛋。我在面前,儿子就会转身往我这里跑,我一护他,就会一同遭到妻子喝骂。久而久之,儿子知道在我这里得不到任何庇护,再做错事被收拾的时候,也就不找我了,干挨着,或者自己躲在一边生闷气。有个别时候,儿子还会冲我发点火。我呢,鼻子一酸,就把他揽在怀里。
通常,按照妻子要求,她训斥孩子,过一会儿,我就去安抚儿子。儿子见我进来,一句话不说,哼一声,或躺在床上假寐,我再说他不理我。我说得多了,他一句话不说,转到另一个房间。但很快,他们母子之间和解了,又亲成一团。我看着,心里有一种酸酸的幸福感。七八岁的时候,儿子很调皮。有一次,妻子从娘家回来,儿子竟煞有介事地对他妈说,老妈,你不在家的时候,我听见一个女的给我爸打电话,叫他杨哥,说得还特别热烈。我说你小子简直是无中生有。他继续给他妈妈煽风点火,非要说有。还有一次,在外地笔会,与一个女同志合照了一张相,儿子看到了说,我老爸太不像话了……他似乎明白,在家里,强势的人是他老妈。他这样说,无非是站队,更好地保护自己。那么小,他已经懂得在父母之间作选择了,知道怎样才能使自己更有安全感,拥有强大的庇护者。
这些年,对儿子产生影响的不是我这个父亲,而是他的母亲。我甚至有些相信棍棒下面出孝子这句古话,有人觉得是陋习,但其中的道理也是千锤百炼的。妻子经常说,给他吃好的,穿好的,但不能娇惯他。每次一起出去,我或是妻子,见到沿街乞讨的残障者,都会给儿子几块钱,让他自己送过去。
2008年夏天,我们一起回到河北老家。一天中午,儿子上气不接下气跑回家,拉着我手急切地说,老爸老爸,一个奶奶被人欺负了,你赶紧去主持正义!说完,拉着我就跑。我问他,为什么要老爸去主持正义啊?儿子说,你是大男人,又是解放军,你不主持正义谁主持?我跑着,把儿子抱起来,而且很用力。
我也多次对母亲说,幸亏你小时候经常打我、骂我。要不然,我真可能就是一个不成器的人,到现在都不知父母恩,不知生活难。母亲说,也是的。然后又给我絮叨她如何打我的往事。
人的天性是自由的,生长路上,有很多道路可以走,就像一条开始宁静继而狂野的河流,方向不是唯一的。人为的教育或者引导绝对有必要,虽然很多时候家长乃至老师的教育,就人本性而言是扭曲和伤害。但人毕竟不是单独的,每个人都生活在人群之中,而人群是有许多规则和禁忌的,每个人都得学习着去适应。
这些年来,每到一处,儿子都会有很多朋友,没事时候几乎不着家。同学来找他玩的也非常多。我觉得很开心,一个孩子,不孤僻,有自己喜欢的愿意和同学们分享,这就是好的行为。但同学之间相互排斥的事情不是没有,但儿子从不记仇。即使吃亏了,以后在一起,还是好朋友。这一点非常像我。每次看到儿子和同学一起玩,甚至在上学放学路上护佑一个比他矮小的男同学,我就很欣慰,暗暗为他鼓掌。
有几次,儿子说,他们班的某某女同学太坏蛋,全班男生都跟那几个女生怎么不合拍。他说得头头是道,天花乱坠,甚至穷凶极恶,但事情都是小事。我知道孩子之间的事情,大人不可体会。到九岁那年,儿子也转到成都读书,男女同学之间,朦胧的情愫很生涩,也很美好。有几次,儿子说他们班里某个女生喜欢他,还说长大了要和他结婚。十三岁后,则极少再提那些事情。
多么美好的青春年少!我也常想,要是能和儿子换换就好了。这种天真的想法一直萦绕不去。人总说,时间会说明一切,但有一些说明也会在时间中无效甚至与之相悖。我性格散漫、自怜且充满疑问,自小很犟,有河北人的驴脾气。
儿子在这方面也像我,我愿意他是有血性和理智的人。尽管他有时候对人、对事过于热忱,不计一切代价,更不设防。我也着急,对他说,要理性客观地去看待任何的人和事情,他还是不听从。从本质上说,对人好,不耍心眼,不玩阴谋诡计,是真好的品质,可是,他正在成长的时代,是人心人性复杂深刻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我不想他过早遇到不应当的伤害,或者对某些人事产生过多的负面情绪。
内心和精神的健康,才是真正的所向无敌。相对于我的成长环境和青春期的经历,儿子是单纯的,也是优裕的。十一岁,儿子的个头就已经一米七了。人说,有苗不愁长,果真是这个道理,想想,也是喜悦之中有惶恐。儿子一天天长大,我却一天天变老。儿子十四岁,就在我面前顶天立地了,个子达到了一米七三以上,而我却越来越萎缩。我们父子的角色,从形体上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儿子对父亲的逆袭,是全方位的,那么天经地义,又猝不及防。很多时候,站在高个子的儿子面前,我总是想起,他刚来成都的时候,每次出门上街,都是我拉着他的手,生怕他丢了,或者被什么撞到了。即使冬天,父子俩的手心也都是汗。两个人,在成都宽大的街道上,那么不显眼,却又无比紧密,内心充盈着一种生命相依之感。而现在,我站直了,也才到他肩膀边上。有几次,在街上、地铁上,我想抱抱儿子,却够不到,只好抱住他的腰。
十二岁之前,他总是让我陪着他睡觉。他伸胳膊蹬腿,一会儿翘在我的肚子上,一会儿又滚过来把我压醒。尤其是冬天,他蹬了被子,我会把他抱在怀里,给他盖好。他肚子露出来了,我惺忪着把被子送过去。睡前,他要看会书。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不断地给儿子买书看。他也爱看,《意大利童话》《福尔摩斯探案集》《大唐狄公案》等等,他都读完了。他也会和我说很多的话,有关历史、家事、学校、未来……都很有想法。困了就抱着我,不一会儿,就呼呼睡着了。每天早上,醒来他会伸懒腰,再眯一会儿,我以为又睡着了,他忽然转过身,说老爸我忘了一件事,应当昨天说,不过现在说也不算太迟。说着说着,又说老爸我先去尿个尿啊。
儿子越来越大,抱着他睡,逐渐成为奢侈。这是我最直接的担心和不安。儿子是父母种植的树,毕竟要独立成长,虽是铁律,但我总希望这个铁律生效再慢些。每次,母亲都在电话叮嘱我说,好好看孩子啊!母亲话中,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她始终和家乡的那些乡亲一样,对人,特别是孩子,格外看重。也常说,有人不算贫,没人贫死人。意思是,一个家庭再怎么穷,只要有人,就还有希望。
儿子读初中的时候,我每天早上和他一起去学校,晚上去接他。父子二人,每天坐公交车来来回回。我知道他会饿,提前给他买巧克力、酸奶,还有其他吃的。那段时间,总是早上六点钟准时醒,自己先穿好衣服,再盛好吃的,叫儿子起床。可是,这样的时光并不长,似乎转眼间,儿子就去绵阳读高中了。
相守的儿子忽然不在身边,心里的那种空,无以复加,又万般无奈。闲暇时总是想起儿子,心里蓦然升起一股力量,很强大,直冲霄汉的样子。有时候翻看他的照片,各个年龄段的,尤其是在学校和老家的。儿子的一个好的品质是,从不嫌弃乡村,不嫌弃和他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一样的穷苦人,和弟弟几个孩子也玩得好。每次带他回家,夏天的时候身上长红斑点,很痒,有的抓破了、流水,他也没说过那地方不好,要赶紧离开之类的话。农忙时候,儿子还和奶奶一起下地,帮着奶奶干点小活儿,虽然是一时兴趣,玩够了就闪人,但他也从没有流露出对乡村乃至农事的任何鄙夷色彩。
我觉得,这就是最成功的。儿子是2002年生的。我自信在当下这样的孩子极少,我也很庆幸,我自己生在乡村,能够使得自己的孩子时常能够近距离地在泥土大地上与最真切的人事物发生联系。因为儿子,我觉得自己枯燥的人生有了滔滔不绝的波澜;因为儿子,我也觉得自己在大地上异常充实;因为儿子,我就是一个有传承的人。在他面前,我是父亲,他在我面前,却是另一种生命景观的渐次隆起与多种色彩的有序生成。
父子这种传承,是一个家族在时间中的自然延续,是人的生命之根在大地上的持续葳蕤。前不久,带儿子去饭店吃饭。儿子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以前,有一个外国男人,他女儿小时,他喜欢咬她的手指和胳膊。女儿慢慢长大,他老了,牙齿脱落。等到他更老的时候,只能吻吻女儿的手背。那个父亲就像你。小时候,你老是咬我的手,还有脚。还记得不,老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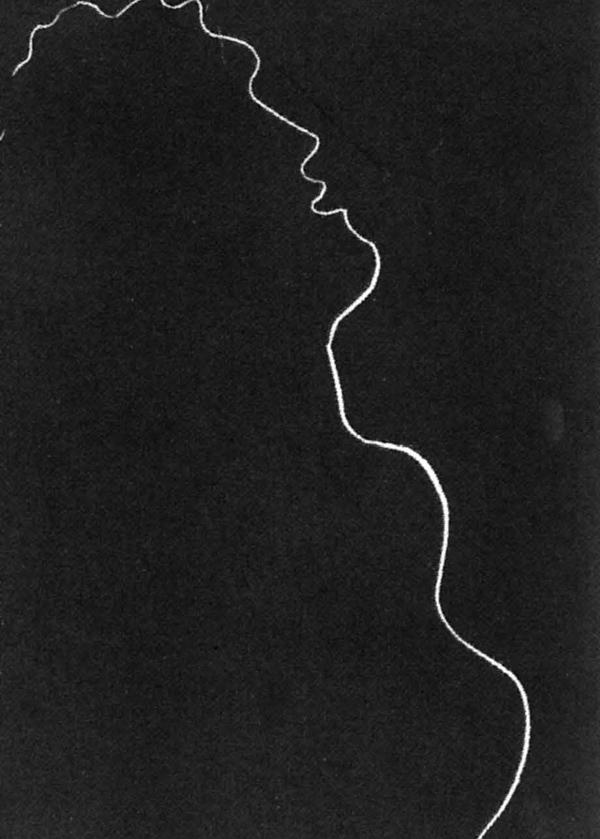
我不由潸然泪下。
同时,觉得这个故事充满意味,也觉得,咬——其实是爱和疼的感觉,是那种无法表明的心理以及一说就错的感情。咬——是表达爱与疼的恰当方式,比亲吻层次更高,或说,咬,在某种程度上还包含着自觉、自愿、爱怜、唯美、不舍与珍爱等因素。现在,我已经开始老了,再过几年,等他长大了,一个老男人再咬一个小男人的手指,那是怎样的情景和滋味?
我也适才相信,人和人,尤其是血缘之间,有些东西是非常微妙的,有着无可言说的丰富意味。这种意味有时候像一根针,隐隐作疼,且坚持不懈。就传统伦理而言,西方和东方的差距是巨大的,两种文化传统,使得一些故事,乃至人间伦理之间的简单仪式,也无可喻晓。
2018年清明节,我再次回到老家,和弟弟一起为父亲扫墓。跪在满是沙土的坟前,我想哭,可又哭不出来。那时候,北方还是一片荒寒,只有冬麦哆嗦着身子,在田里,像婴儿一样相互拍打取暖。其实,我想带儿子回来的,只是他课业太重,每一次放假,都尽量让他多休息。面对父亲的坟茔,我喃喃说,爹,俺娘很好,我也是,弟弟一家也过得不错,孙子孙女们上学都还可以。无论到啥时候,我都记得你,你是爹,是俺们的出处。包括我和弟弟,乃至孫子们的孩子。不管再怎么遥远,我们在一起,永生永世,不会分离。就像这世间的万物,各不相同,但都会枯荣不尽,生生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