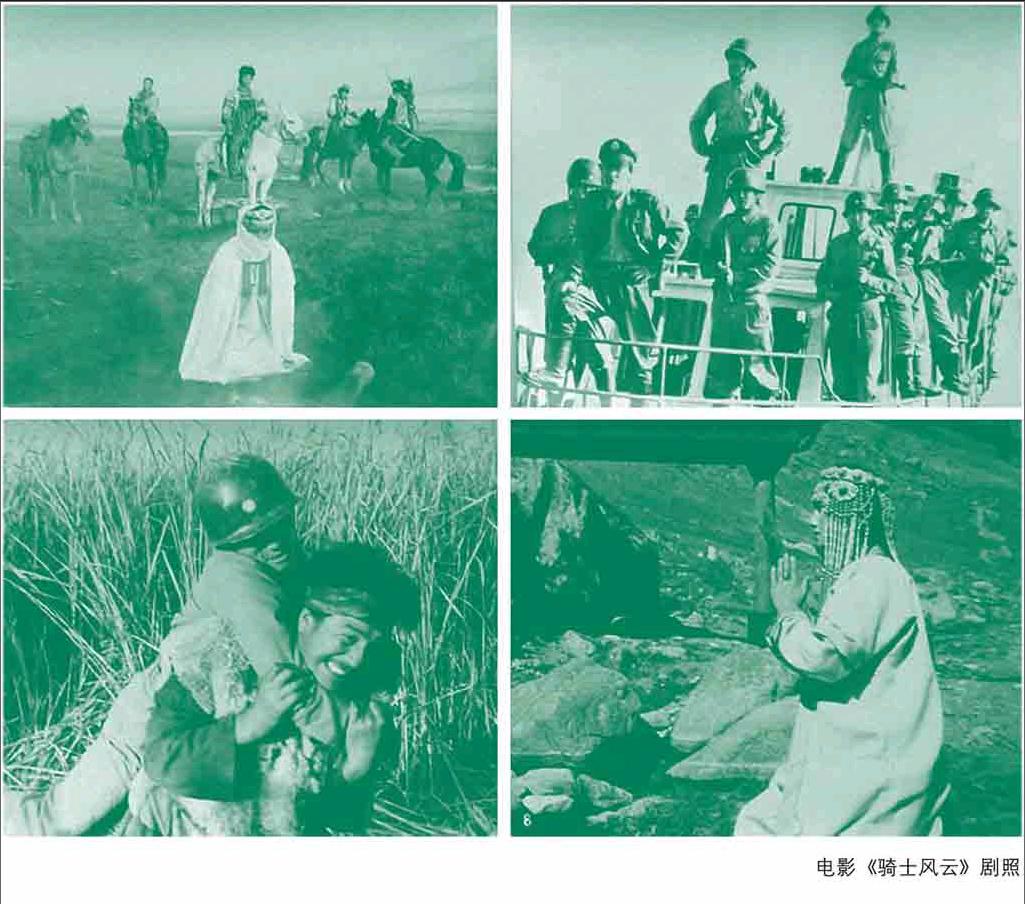
【摘要】 影视作品在形塑“内向性”少数民族文化,构建国族文化的过程中举足轻重。以塞夫、麦丽丝为代表的“新民族电影”,在主体构建过程中生成内向视角,以叙述者本民族的“自我”意识贯穿行动过程。从而,对本民族所谓“真实历史”“客观生活”的表征成为新民族电影作者的追求。与此同时,国家认同作为一种特殊的心理认知现象,具备情感皈依和心理依附的特征。由此,如何正确理解和阐释“新民族电影”所表征的族群记忆与民族文化,如何让其统摄于“国族认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
【关键词】 族群记忆;内外视角 ;文化认同;国族想象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置身现代性语境,新时期少数民族的身份认同与信息传播特别是族群集体记忆性质的信息传播紧密联系。这主要基于以下两点:首先,媒介信息的接受和传播是主体确认自我身份的重要标识。当作为主体的个人接受某种特定信息时,也意味着他暗示自己接受何种特定的“文化身份”。而在两个不同族群的文化相互融合与渗透的过程中,个人和团体获得了其他个体或群体的记忆、情感以及态度,并通过分享他们的经历与历史而与他们整合进入到一种共同的文化生活中。最终的结果是“种族背景和文化传统不同的人群(people)占据共同的地域,获得一种文化一致性(cultural solidarity),这种文化一致性可以维持一个民族的存在(a national existence)”[1]91。对此,社会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常用诸如“涵化”(acculturation)、“文化同化”(culture acculturation)、“同化”(assimilation)这样的术语来描述两个不同民族的文化“碰撞”的过程和结果。
再者,“共享记忆”的媒介信息并且“整合融入共同生活”,能帮助族群个体确定其文化身份。这类媒介信息在圈定人们精神思想疆域的同时也固化其特定的“记忆认同空间”。毋庸置疑,当代的集体记忆有相当部分是藉助电影提供的素材建立而成。依赖共有传统、集体记忆、历史遗产,个人文化身份认同受到催化,集体认同的凝聚性也得以巩固。“所以,电影传媒可以通过塑造记忆进而决定人的身份认同。如此,‘怀旧、传播和身份认同三个概念就此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现代都市文化的一道獨特景观。”[2]242电影传播带来的文化认同媒介效果既受到受众意愿的限制,又受到新来文化是否积极参与并且接受群体社会的意愿程度。
本文以塞夫、麦丽丝“新时期内蒙古少数民族电影”作为研究个案,选择“集体记忆——信息传播——身份认同”的路径,原因在于:其一,边疆地区游牧民族与主体民族相比,具有不同的文化生态、宗教信仰、生活方式以及社会结构。这使得边疆地区的文化身份认同危机频频出现,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亦成为研究“身份认同”的典型范例;其二,边疆地区文化多元混杂,少数民族个体在异域文化的冲击下,极易产生身份认同危机;其三,相较用强硬的意识形态手段规训形塑少数民族的公民身份,以电影为代表的大众传媒用逼真的影像让“身份认同”成为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文化自觉,并形成新的文化记忆组织形式。换而言之,媒介领域的革新(以影视媒介为代表)使集体的认同随之发生意义更为深远的革新;而集体认同的升级亦伴随一定的文化技术手段的变革而变革。
一、民族语言的静默书写
语言文字具有抽象性和穿透力,而电影主要以人物对白、独白、画外音以及特定的场面调度、镜头剪辑来表情达意,以此体现语言文字的魅力。“电影话语不同于小说或者戏剧,因为它通过影像(image)和声音(sound)来讲故事。电影话语也是再现生产和理解现实,以及把意义固定下来的过程。既然话语同时是现实的产物和建构者,它们既反映又加强意识形态,在这个意义上,它们反映了权力关系——也就是说,会存在主导话语和边缘话语。”[3]135新中国成立以来,共计出品了300多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故事片(还有大量少数民族题材新闻纪录片和科教片)。这些影片的编导多为汉族、对白也大多为汉语,在影片的生产消费体系中表征出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导向功能。“电影中的语言文字,是呈现文化差异并辨识其民族特征的符号,流露出特定民族极为丰富复杂的精神症候。21世纪前后中国的新民族电影,正是以静默书写与艰难发声的民族语文而在中国电影文化史上独树一帜。”[4]178
建国初期的内蒙古少数民族电影即表征出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1953年中央电影局和东北电影制片厂联合出品的影片《草原上的人们》为典型一例。该片取材自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的同名小说,由海默、玛拉沁夫编剧,汉族导演徐韬执导。片头处萨仁格娃与桑布畅想美好的社会主义新图景:“政府让我们定点游牧、生产互助,到时候好牛奶光喝也喝不完啊!我们种草、点电灯,驰骋在草原上,建设祖国的边疆。”(影片对白)1953年时值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的历史时代大背景,男主角桑布把反革命分子的破坏行径比喻为“狼跑到羊群里去了”,以争当打狼模范为荣。而在片中无处不在的宣传式标语、口号式对白、蒙古包中的领袖像,呈现出一个“符号过剩”的世界。
1963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推出李俊导演的藏族题材电影《农奴》。该片主流话语鲜明、富于政治意识形态导向功能。影片中的老奶奶在去寺庙为农奴强巴求护身符的路上跌入河中;活佛把叛乱用的枪支藏在佛像的肚子里;以及“卫教军”强奸尼姑、焚烧经书,直至最后活佛放火烧毁寺庙。影片《农奴》画面构图新颖,明暗对比强烈,造型独特。导演选用的全部是第一次走上银幕的藏族农奴演员,呈现出真挚饱满的本色气质。值得提醒的是,影片善于从西藏宗教文化和民俗自然风情中,选择富于特征性的情节与场面,隐晦、含蓄地揭示这一特定文化的矛盾与冲突。如强巴奶奶以虔诚之心,倾其所有,去寺庙为孙儿求得保平安的护身符,结果不仅未能护佑孙儿平安,她自己在半路倒在了河流中,一纸护身符亦随河水流逝……强巴受兰尕一颗纯洁之心的托付,在慈善的“白度母”面前多拜一拜时,因肚子饥饿,吃了一把酥油,被凶恶的铁棒喇嘛捉住,几乎要砍断手、割掉舌。“白度母”视而不见,闻而不问。再如,更顿老喇嘛一生辛苦,泥塑佛像,金涂佛面,功德无量。可是恰恰在大佛“开光”之日,老喇嘛双目失明了,连他亲手塑造的佛面也未看到。片头的空镜头从高山乌云摇到喇嘛寺庙的金顶,再摇到阴沉神秘的寺庙,伴以时断时续凝重的长号声,让人感到一种被原始、野蛮笼罩着的宗教氛围,令人沉重压抑,暗示出旧西藏的社会环境氛围。[5]206-2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