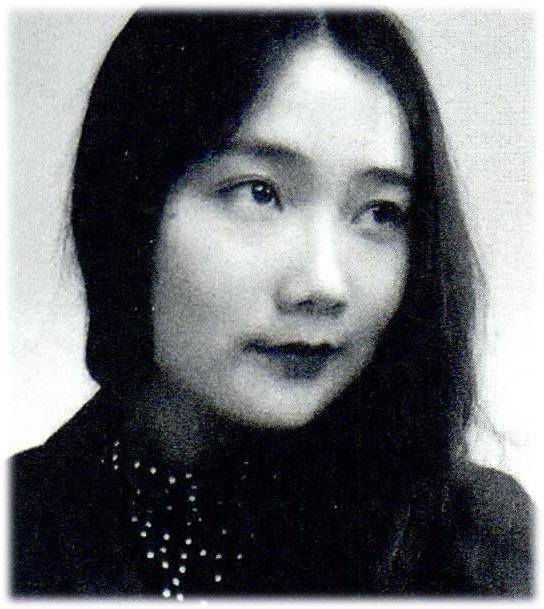
积雨云
多年前我被装裱进小镇,陷入一场突发的对弈
性格中的举棋不定和黑白分明悄然分娩
抬头瞥见始于远古的影像,母亲在林间怀抱我
花整个下午窥视猫的瞳仁,或者它窥视我
穿堂风带来老冰棍,一种形影不离的清凉井深
从咽喉浮起来。然后话语咽下去
大部分时候世界无声,唯有褪壳的鸡蛋在平底锅里
回归
——它死于打捞月之破碎
我们随时准备跳进这延伸至死的水域
种下一生的逃亡,误认为自由
像我始终分不清的麻将。在祖母手中整齐排列
它们漠然相对茶馆的沸水,遮盖所有人穿梭明灭的
面相
——也算是召唤满城风雨,以及
我往后所有的时光。从未离开过头顶上方那片薄云
兄弟姊妹
在拉萨市中心,每一个地方都可以望见布达拉官
再远一些就不行了,除非我祈祷光线弯曲
除非神当真能满足我的愿望
从灵芝、雅鲁藏布大峡谷、朗县至拉姆拉措
海拔成为致幻剂,男孩说他梦到蘑菇,而我遇见
绵羊
两种场景都被我拒之体外
这不能算作衰老的标志。“我不会爱上一个被过
滤的世界”
自羊卓雍措至纳木错。总有坚持不食鱼的司机
“水里的神灵,穿透污浊。”
我初次在固执前变得柔软
这两条姊妹一样的湖泊,诞育个性木讷的兄弟
像简易帐篷里藏族小女孩的清澈双眸
光线投入湖水时,我可以看见所有途经之地
坐在任何角落,重复翻开一本睡去又醒来的影子
深处
这条街随时会下雨
我又遗失了雨伞
如果这也算一种习性
是从何处而来?
每座城市都漂浮尘埃
穿堂风在嗅觉里
干燥或者磨砺
它不发光,不似夏夜萤火
更接近药粉
很多年都在咽喉深处
被反复捣碎
像开水一样翻滚
又迅速冷却
再走几步
我们可以变成完全一样的人
比如,只酿酒不喝酒
只行走不回头
不再弄丢任何事物
除了眼泪
草木如织
今年的暮春比去年轮廓清晰
我一直在墙壁深处
乔装成骨质疏松的旅者
如你所闻,我长年典当露水
从微弱的裂隙种下每一枚铜币
听说,它们会发芽
听说,每一枚都有一个故事
有人就这样一直听到死去
也还是婴孩的模样
但是我已经很老很老了啊
一想到你听故事的傍晚
庭有奇树,天色灰蓝
寄居地
她最近看了很多电影,每一部里
都有一个城市,像面对童年的旧墙根
上面有格言和海。有庄园和建筑
有晨醒时分的冥想:油漆喃喃自语
一边剥裂一边喊疼
她猜想她从出生以前就学习过
像傍晚火锅里的辣椒,深夜广场的麦克风
便利店的玉米,乍来之日冗长的车厢
在高温和雨水的胞衣里低头疾行
编织群居的假象
她希望自己变成,水
从天上落下来,怀揣新鲜的故事
要么是植物,从午夜的土壤里
长到云端。那些一大片
一大片的幻象
是死去的影子,还是心跳的衍生
或者是流动的,异度空间
她可以在梦里,热一杯牛奶
夏的密码
夏天,起始于记忆和树林的广场
风穿过玻璃、心口、木凳
一片叶子敲打下来,再没有其他声响
世界成为寂静的湖面
你我在镜子中央,翻过很多次的童话集
书页上布满水纹,被清晨的豆浆铺吆喝开
舒展的样子,让我想躺在晴天的云朵里
我并未想验证些什么
比如,旧钥匙上雕刻的词语
早就预言我会在哪个国度遇见你们
当然也是离开之后才爱上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我始终在汗水深处分辨、打捞
那些苍弱的语气,到底是盐晶还是花瓣
与乞丐对饮
香樟树又开始落叶了
我找不到一个可以对饮的人
迄今为止,我所有的词汇都来自于
父亲,包括眉眼中的内敛
有什么是属于我自己的呢
昨日我打了个电话问他:
“为什么小时候我在屋檐下唱歌,
就会挨打?”
他像往常一般沉默
我很想虚构一种锐利
假装它是属于我的
后来我站在人流之中
沉恸于这荒谬的矛盾
直至在街道尽头看见一个乞丐
像所有的乞丐一样
他卑微,讨好,低垂头颅
我与他同样贫瘠,可以对饮
清欢盏
藏家的火炉、合体的衣裳、抵足而眠的人
我将永远应和,从水里掩映的盛世光景。
你们独立出来,你们都是一座丰碑
只应短暂的微醺,梦外和梦里之物的颠倒
傍晚有只棕色的猫
在深山中
我无意瞥到晨昏边界
暗色里走出一只棕色的猫
当我觉得屋子很空
就喂它麻花
这不能被祖母的母亲发现
这是她走很多路唯一能买给我的零食
有时候她不穿上衣
露出耷拉的,和猫同样颜色的乳房
纵向褶皱如生硬的素描
更多时候她和光线一起消失
只剩下猫发亮的眼睛和我手里的麻花
它叫一声
我掰一块
后来她死了
猫也不见了
我看到所有的猫
都开始在傍晚长出皱纹
深夜过南门
没有马匹抵御冬夜的刺藤
我站在栅栏里
逃逸。从一种精神的颤动
到另一种精神的颤动
这本该是一种天赋。攀越铁门时
撕扯出来的秦叔宝
怒目像极了父亲
比呼吸和渴望疏远
女孩尚未学会拒绝之初
就懂欣赏陌生女人的妆面
她。皮肤上粉末的衰老快于
米粉店老板手起刀落
后者又快于白炽灯外雪花堆积的速度
这段距离在古老的城门遗存
我走在自己的肋骨上
每一步都下坠,每一步都压低哑语
铁笼在深夜破裂
只能算作一次虚拟的重生
水库行
1.
我曾深深惧怕过水,它们吞噬一切
像拖动一截面壁的枯枝
如同衰老没入眉心,尖锐的波纹
我必须与这些长远的意识熟稔起来
童年我被一只鹅追赶,中途卷入夕阳的纷争
它们在河里扭曲变形,互不相认
我们试图说服所爱之人,很多次了
我褪尽衣衫,归来,独自离开
一瓣沙砾让我拾回重返婴儿时期的父亲
面孔宁静,似乎从未发过脾气
有几日,我没有展示与众不同的热情
这难道是一种幻觉?当我欣赏破旧的建筑
翻开德松去拍摄肥胖无忧的鸡群
某个朝代某个院子,我也给它们喂过米
关于欲望,它们了解得并不算多
一个人经过
两个人经过
所有人经过
我认不出他们或者它们
我最终只剩一种表情
2.
我没有再往下看
路过铁桥对于胆怯者如同走钢丝
血管内奔涌的荫翳
像一只手,抓起此刻的
风向、影子、喘息、蠕动、咽喉
我站在求生之木上,底下摇摆
起源、嘶喊、死鱼、报纸、历史
我往后退了一步
巨大的波纹里有个黑衣男子
手握钓竿朝上,看
这时还未掀起一丁点浪花
面对广阔的水域我本该平静
影子小记
1.
凌晨影子逃离我,从单人床上坐起来
和对面的墙壁同时发出吞咽声
她已经很多年不曾提起对自由的兴趣了
冬夜里饮下一杯乌托邦
冷水的辩证法让饥饿更加清醒
哦,异乡人
所谓旅行不过是
换了一张床做相似的梦
2.
我总是忘记很多事情
比如我出生时的啼哭
是在一个护士的巴掌之下才存在
它来自母亲的言论
永远停在那一刻
我的影子永远停在她形成的时分
我看到过去式,又遗忘过去式
身陷老旧的囹圄,出于本能寻找
最新鲜的监狱
写给前年未至之地
此前,这个地名并不泛滥,我拥有陌生人的信任
说:大俗即大雅。每个溺水者都有过真诚
对待的艳遇,像影子从光的头顶垂下无声拆迁
这样的时代,你仍躺在老去的雕花大床上
搭乘火车,遗落一串咳嗽:小青呐,小青呐
请来吸干我的精元。此前,我曾读过一些故事
从梦里醒来时,还蒙着被子。听见沉闷的余韵
奥秘一开始就写好了,只是后来我慕名去了断桥
发现她不如长桥可爱。一切只在传说里
现世,是踩进云里涉水,这些年我去过很多城市
每一座都疲惫,我服下一种冗杂,里的迅疾
我终究没到达从前,如今
所有的孤独拥挤在同一趟电车
轨道空茫茫,人间空茫茫
此前,我期待我是在老死时写下
背叛
行走的人
睡眠是不知轻重的骨骼
弹奏易折之水
渐次拔出
枯荷
从手心的淤泥沉入持久
无限生长的丝蔓
说缓慢却也迅疾
只以坚硬示人的莲子
内里清苦
后来她同他们一样轻薄
只在梦里看见柔软的藕色
一场黄昏的苏醒
故事的生长是一次不存在
折断声持续浮动
脚踩柳枝的少女在荫翳下
死去。之后我更爱她
这样的傍晚充满交谈声
并非出于虚构
长久累积的车辙从鸟鸣流出
练习更为成熟
的对抗,如竹篮,打捞罅隙
打捞长久不间断的枪口
他们和我来自同一个空间
他们的表情浸泡经年的泡沫
披上精神胞衣
任意选择一只生灵来寄居目光
植物都孤独站立的世界里
人群在黄昏成为传说
冬日
所有的故事终将在冬日重复,像一层层抽屉
几代人呼啸抽动,只有影子可以溜进去
长久以来我坚信,万物凭借天赋相爱
四十年前,父亲与祖母初识
二十年前,母亲与我初识
十年前。我与檐下的燕子初识
我模仿它们走在细绳上,无限接近
天地之间的隧道,换一个方向跨过去
就是从《牡丹亭》走到《桃花扇》
纸上的生死关乎情爱,而长满厌倦的人间
只有天气能与这结界亲近
长幼有序
谦卑有礼
坟茔上的荒草别去拔它
等待它们与冥币一起挥发,与空气一起冷进骨头
或者扑面而来
而我下跪的姿势,多么像对千次万次遇见的膜拜
元素
多年来,引领我体内潮汐的暗渠
似乎又延伸到体外了
母亲说她始终做同一个梦
台阶长青苔,小船深红色
我的情绪躁动不安,不愿听她说完
我的河流急匆匆哗啦啦,终年落满大雪
母亲的棕色眼睛里积累湿气
最终成了柴屋灶台上烧开的水
我日复一日地练习静坐,冲茶,种花,等人
各种元素各种颜色。都造就我的寒性体质
河水坚持不发一言,在没有战争的清晨
像我一样面壁思过
而不计其数的尘埃在移动啊
像气泡浮出表面
我每戳破一个。都是戳破自己
雪落下
的声音。
某个瞬间,那些来自宇宙的白
断裂。我坐在门口,用整个下午观察
废墟中不断延续深入
扩大的喧哗,被寂静湮没
眼睛层层覆盖的弦。渴望一面镜子的墙
我尚未懂得怀念
我为何要怀念?
像失贞的少女不舍告别一个狂妄者?
假如造化想验证什么,也该先给我酒精
用围城腐蚀皮肤,手扶母辈的孱弱
可为何要用我的名字来借代我?
为何要把虚构的容颜摆在我脸上
我不说,爱
面对终将融化的浩瀚
也不愿接受。恨
她们的矜持,分娩成六瓣
疾速坠落
奥斯维辛
耳朵是不如眼睛自由的感官
没有新闻用于膨胀怀疑主义者的口腔
白杨树,波兰河,中世纪的铁笼长满寂静
想起天黑,就落下巨大的棺木
不要悲伤,把寒冷从胃里掏出来
延伸一种对微笑的饥渴,女孩
逃离死亡喋喋不休的演讲
不代表你不尊重权利
不要悲伤,另一扇门不属于白昼
自由诞生于安慰
空房间不期待脚步声
这乐趣类似于陌生人群
沉默或者打开,共同组成撤退的方式
不要悲伤,我们被这样无奈地呈现
约等于尺子,掷地有声,断裂无声
请正视,枪口是换了表情的镜子
白昼之诗
1.
长久以来嘶鸣的光,从天花板掉落
我穿插其中,听闻簌簌声响
清晨和黄昏,闺蜜都吹着口哨
我是损坏的音箱
巨大无垠的裂缝渗入寒气
整齐的老妪在咖啡馆前跳舞
2.
与一本书的封面熟识
隔天我经过酸枣树、野山杏、丁香
像画中的女子一样轻叩悬于头顶的掌心
我从未深入之处是一张白纸
平躺,顺从,洁净
依附于一场从未发生的大雪
依附于黑色的眼睛,藏家的火炉
起初,这些植物的枝干用力如碑刻
最后的细节融入鼓楼、屋檐、双塔
3.
有时很多扇门同时合上
像无语的口腔
但我一直张开,嘶喊
等待精神的纹路从云层跌落
人群是隐秘的森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