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071002)
小镇是中国社会结构中不可忽视的一环,在“乡土中国”与“城市中国”之间,还有一个“小镇中国”。位于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小镇,区别而又兼具二者的特点。小镇在地理及社会意义上的独特性也决定了其在文学世界中的特殊地位。作家们自然也格外关注小镇,可以说,小镇文学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改革开放之后,经济的迅速发展带来狂飙突进式的城镇化,在文学创作中以小镇视野观察这一进程,独具可观之处。小镇的发展是现代化、城镇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一定程度上小镇视野被遮蔽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通过改革开放的视角同样可以剖析与了解小镇,深入探究小镇生活的变迁、精神裂变和这个时代的深层关系。之所以选择“70 后”作家的小镇叙述作为切入点,是因为“70 后”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社会转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70 后”在外出求学、工作之时,又赶上了深化改革开放、大规模人口流动的90 年代,中国的社会、文化变迁是其深刻的生命体验。在“70 后”一代人身上,既有与生俱来的传统文化和理想主义的烙印,又在成长中浸染着商业文明和现实物欲。
位于乡村、城市之间的小镇,与处于“革命”和“改革”之间的“70 后”,在某种意义上同属于社会、历史的“中间物”。这也使得通过“70 后”作家的小镇叙述,回望改革开放40 年间的进程,有特殊的价值与意义。从小镇文学的视角观察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社会转型,至少有四个维度值得关注:第一是小镇的发展可看作时代的缩影。小镇作为城乡过渡带的独特性,使其成为传统与现代文明冲突与交汇的特殊空间,乡土中国与城市文明共同构成文学世界中丰富多彩而独具代表性的小镇。第二是城镇化进程中精神、文化的变迁。经济的发展使得商业文明、城市文明侵入乡土,挤压了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人们在对物欲的追求中,理想主义走向衰落,批判与反思也随之出现。第三是人与故乡的关系。改革开放带来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数以亿计的国人从乡村来到小镇,又从小镇奔向城市。对于同时怀揣乡土情怀和“到世界去”的梦想的“70 后”作家而言,逃离小镇与回望家乡,成为他们小镇文学创作的共同主题。第四是小镇的“中间物”与边界属性。在新旧交替的八九十年代,社会出现了短暂的动荡期。在公权力难以触及的城乡之间的边缘地带,“江湖”得以出现。一部分迷茫、叛逆的小镇青年选择了“混社会”。
一、小镇视野下的时代镜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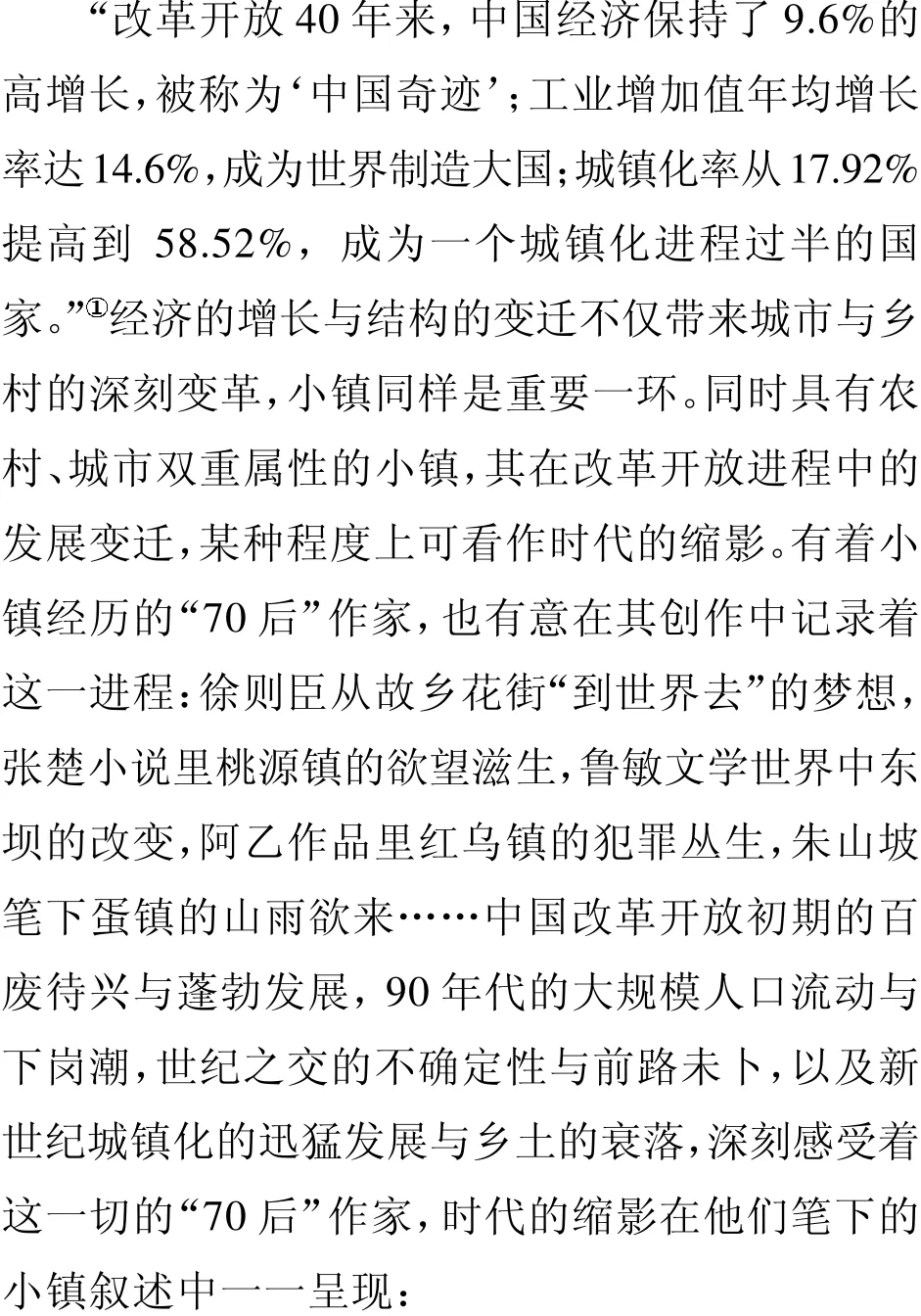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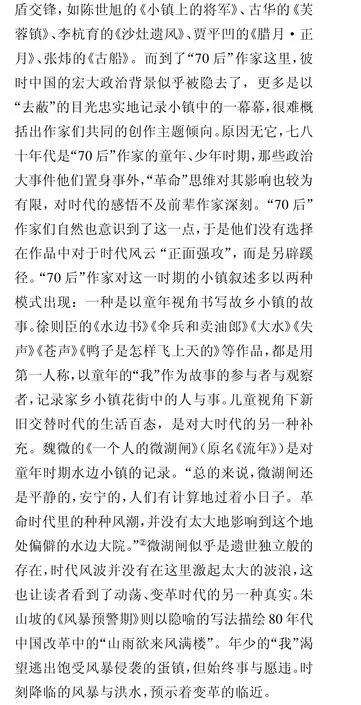
(一)对七八十年代中国小镇的书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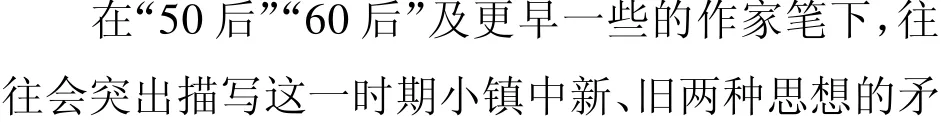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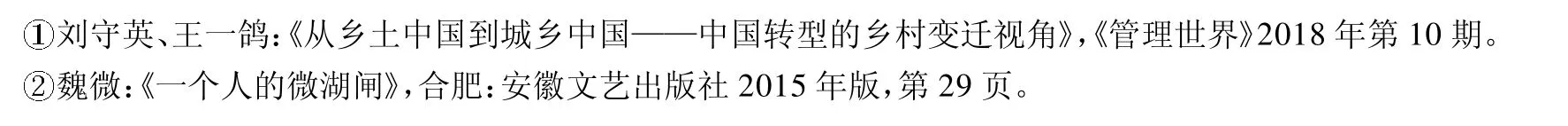
另一种对七八十年代小镇的书写,是以生活中的种种细节描述时代的变革。路内的《花街往事》由“文革”武斗写起,记叙至90 年代初,其中80 年代中国小镇中的暗流汹涌是小说的主体与最生动的内容。时代的破冰带来了身体的解放,路内以“跳舞时代”为80 年代命名。爸爸顾大宏靠着舞技,人到中年又在舞台中焕发出了光彩。跳舞与欲望,以隐秘的方式构成与时代的关联。薛舒的《隐声街》《那时花香》等作品,以回忆的方式记录了80年代的刘湾镇。《隐声街》中扫街的大毛毛和捡垃圾的阿宝,以及一些拾荒者,真实地记录了底层的生存状况。《那时花香》则通过派出所姚所长的视角,反映了小镇居民的生活群像。湖南作家艾玛的“涔水镇系列”小说,描写了改革开放给小镇社会、风俗、思想、生活等方面带来的种种变革。
(二)对90 年代及世纪之交中国小镇的描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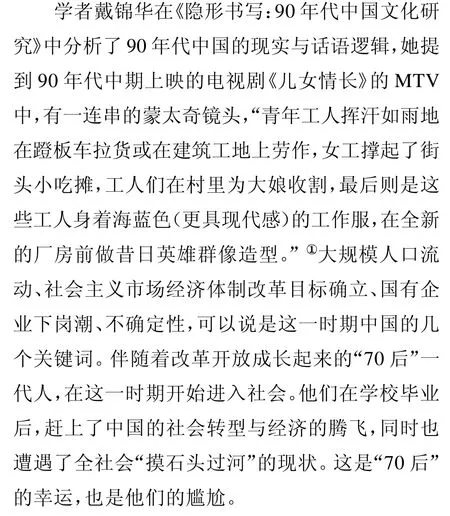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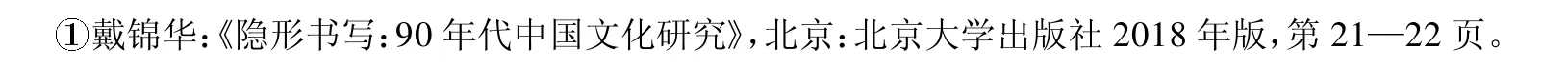
在90 年代与世纪之交,处于青春岁月的“70后”位于人生的十字路口,而小镇可以说是连接城乡的十字路口,这便是“70 后”作家对这一时期小镇空间书写的契合点与复杂所在。山西作家杨遥的《弟弟带刀出门》,描写到那个年代年轻人中汹涌的发财梦。小说标题中的“出门”可以理解为“出路”,作者追问的是小镇中的年轻人,他们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弟弟外出进了一批佛像和刀子,回小镇贩卖。镇民们为了发财不择手段,求神拜佛。弟弟爱上的女孩白牡丹,原来是镇中有名的妓女;常来弟弟店中的和尚和年轻人,原来是在暗中买卖毒品。小说最后,弟弟把白色的货品摆满货架,意指弟弟的纯洁与时代的不相容。“盲流”一词在1953年到1989 年间,特指摆脱户籍管理,自发迁往城市谋生的人群。到了90 年代,随着政策的改善,这个歧视性的词汇不再使用。很多“70 后”作家都不约而同地描写到90 年代大规模人口迁移中的小镇状况。路内《雾行者》的主要故事发生在90 年代末。新兴工业区铁井镇是小说里的重要空间,1995 年成立开发区之后,铁井镇便高楼平地起,数以万计的打工仔涌入这里。外来者人口很快超越了本地人口,混乱与治安问题也随之而来。有警察经历的阿乙关注到了这一时期小镇中的犯罪问题。他的中篇小说《意外杀人事件》写到2000 年红乌镇中的一起案件。小镇居民本以为火车的开通会给小镇带来发展的机遇,没想到却带来了罪犯。被迫下岗的工人李继锡,带着3000 元的辞退金坐火车回家乡。路上他总是疑心有人要偷自己的钱,便中途跳车,意外来到了红乌镇。当他发现自己真的弄丢了那3000 元钱时,失心疯一般连杀6 人。阿乙的另一篇小说《情人节爆炸案》的故事发生在1998 年。何大智和吴军都觉得自己是被世界抛弃的人,他们选择了用极端的方式报复社会,让整个世界偿还他们的委屈与愤怒。他们在情人节制造爆炸,是为了毁灭美好的东西。两位迷失的边缘人选择制造一场灾难,以终结个体与世界间不可调和的矛盾。“70后”作家对90 年代及世纪之交中国小镇的叙述,可以看作转型期的中国迅猛发展与不确定性共存的时代缩影。
(三)对21 世纪中国小镇的描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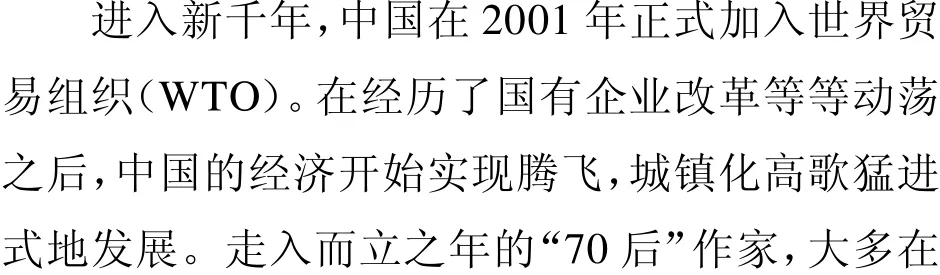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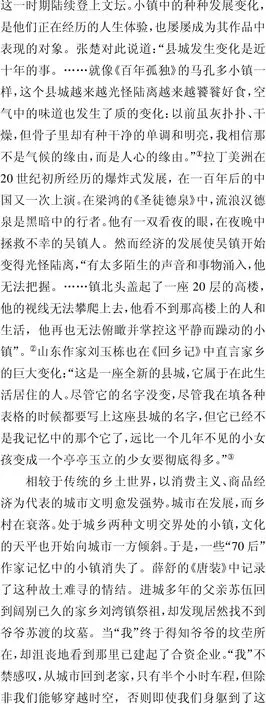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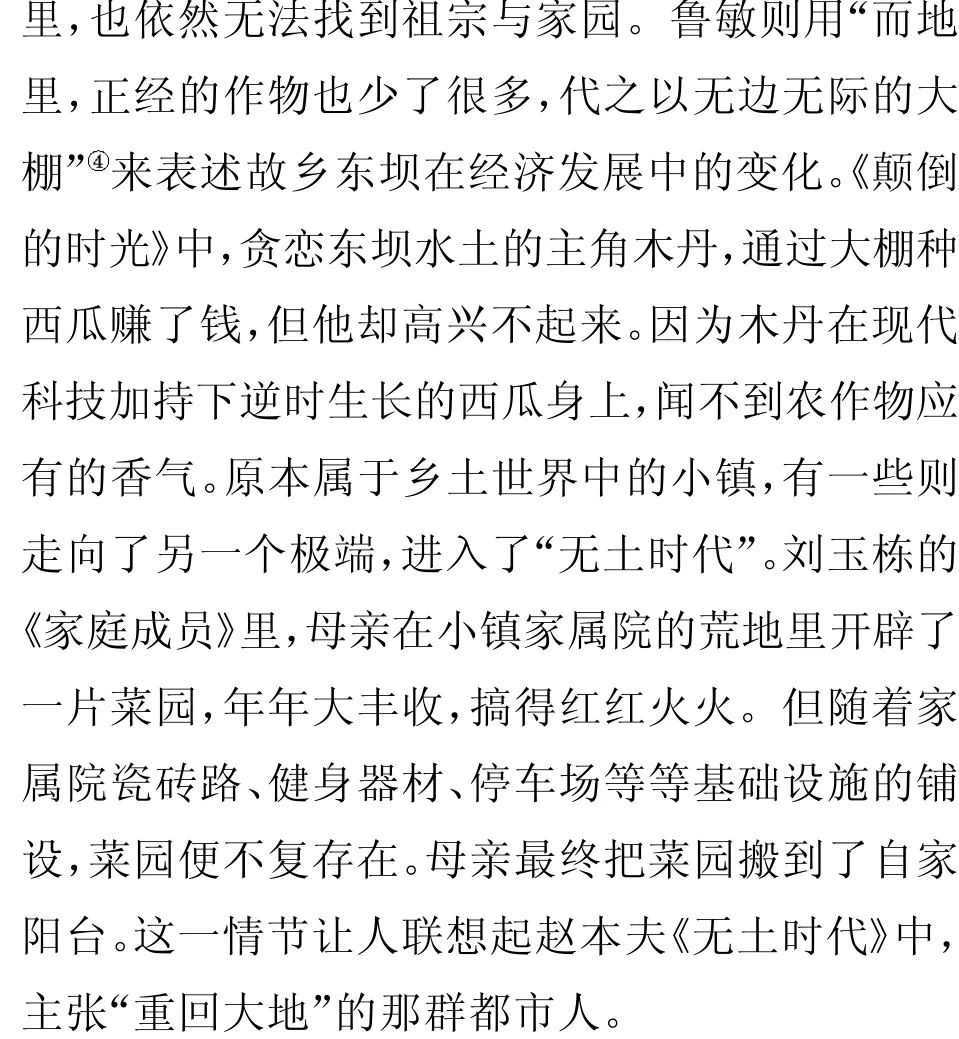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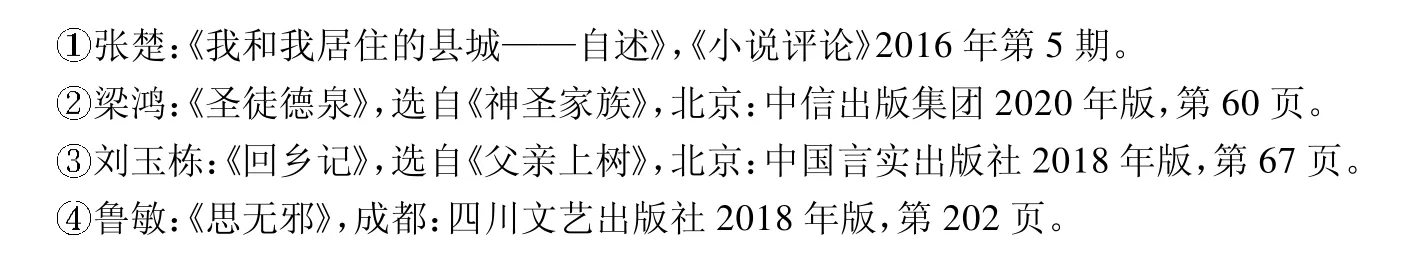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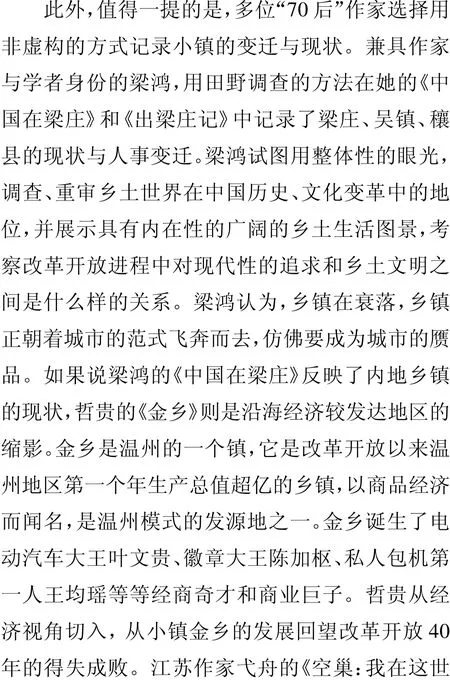

二、城镇化进程中的批判与反思
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乡村发展为小镇,县镇发展为城市。回望改革开放40 多年的历程,如何解释中国崛起的奇迹成为一个难题。中国经济这种“炸裂式”的增长,也屡屡成为作家们书写的主题。阎连科的《炸裂志》以深圳为原型,描写一个乡村在短短十数年间,由村升县,又由县变市,最终发展为超级大都市。余华的《兄弟》以荒诞与反讽的手法描绘了中国动荡的社会现实。流氓李光头靠着捡破烂发迹,后做跨国生意而一夜暴富。有钱后的李光头居然想花上两千万美金,搭乘俄罗斯的飞船上宇宙游览一番。贾平凹的《秦腔》通过清风街上白、夏两家大户的故事,折射中国社会大转型给乡镇带来的激烈冲击。小说里写到有村民死后,村里居然找不齐抬棺材的年轻人,意指乡土世界的衰败。在“50 后”“60 后”作家笔下,对高速城镇化进程中的批判与反思成为作品的主旋律。“70 后”作家继承了这种批判与反思,但不同的是,他们的作品中淡化了隐喻性与宏大性,取而代之的是形而下的、个体经验化的表述。总的来说,“70 后”作家的小镇叙述中,对城镇化进程的批判与反思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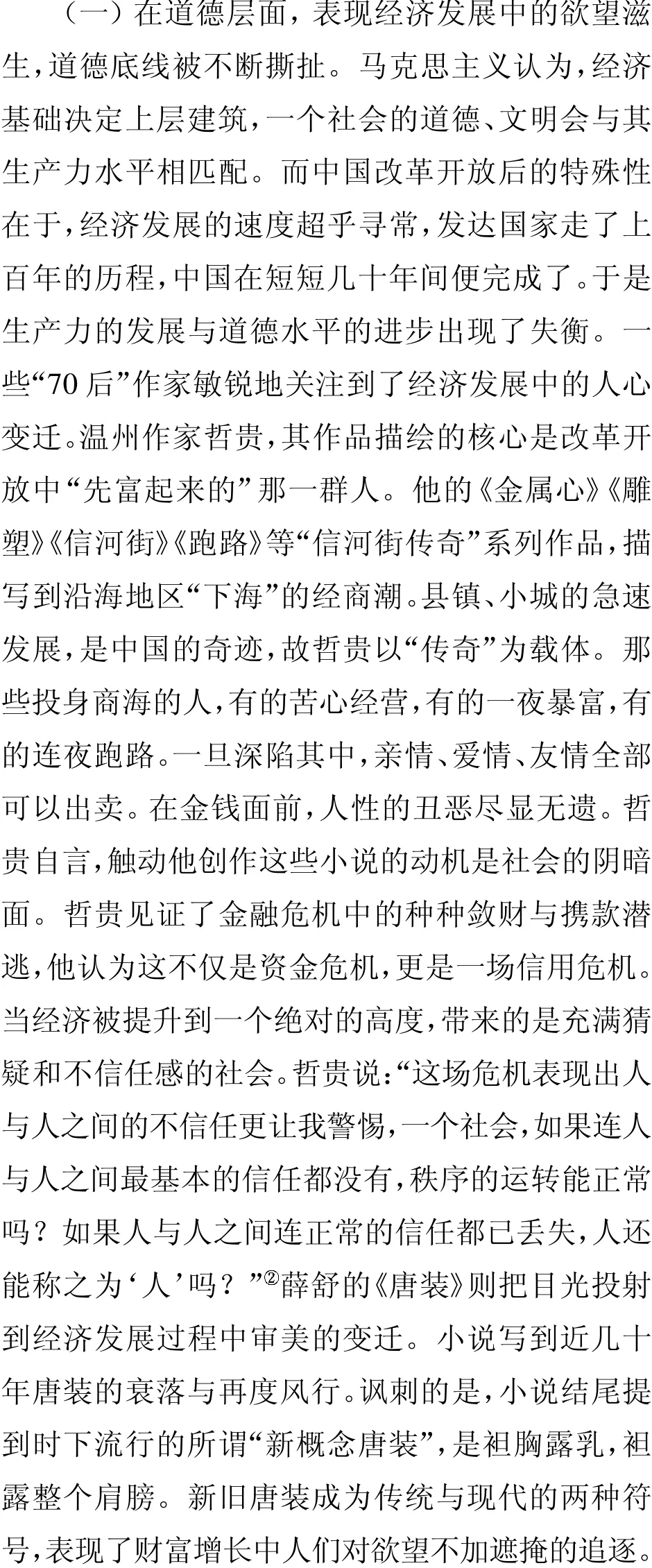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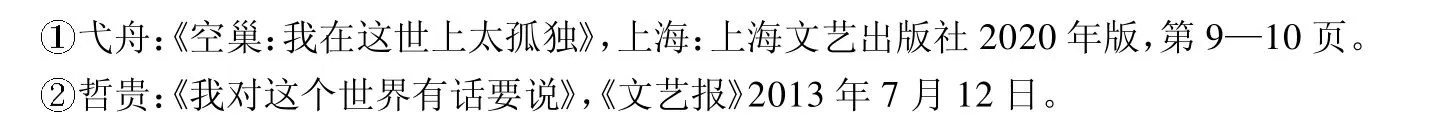
在另一些“70 后”作家的小镇文学里,则直接描写到社会伦理道德的滑坡。徐则臣的《花街》中,老默死后意外地把一生的积蓄留给邻居后辈良生。原来良生并非麻婆和麻爷爷的孩子,麻婆当年孤身流落到花街,当时便抱着良生,好心的花街人收留了这对母子。良生的亲生父亲可能是追随至此的老默,但如今良生为了面子却不愿给老默收尸和举办葬礼。新旧两代人的伦理道德在这里尽显无遗。畀愚《通往天堂的路》的故事由镇上火葬场的迁移开始。一开始乡民们不同意火葬场来到家门口,但随着他们发现其中的商业利益,便都干起了丧葬相关的买卖。孙一定是其中的领头羊,没想到的是他的儿子却死在了追逐财富的路上。孙一定想给没结婚的儿子配一门阴亲,他在医院发现了一位被父母遗弃的奄奄一息的女孩。孙一定竟觉得这是个好消息,因为女孩死后就可以给自己的儿子配阴亲了。由金钱、道德败坏构成的“通往天堂的路”,是作者的反讽。石一枫的《小李还乡》中,出走的小李衣锦还乡。他反复表达自己对家乡小镇的眷恋,说要在家乡投资办厂,回报家乡父老。结局却出人意料,事情的真相是小李非但没有外出赚到钱,还欠了一身债,这次回乡其实是为了骗取家乡廉价的土地套利。艾玛的“涔水镇系列”小说,通过对湖南小镇的描写,表现对大时代下小镇精神、文化现状的关注与反思。《米线店》中外出的镇民遭遇的种种欺骗与不幸,《人面桃花》里的谋杀案,《菊花枕》中的背叛,《小民还乡》中更是将世道比作涔水河,表面上风平浪静,人心却如河底的暗流般又险又恶。相较于沈从文笔下湘西世界的良善美好,艾玛作品中的湖南小镇则表现了都市文明冲击下,被金钱与欲望异化的人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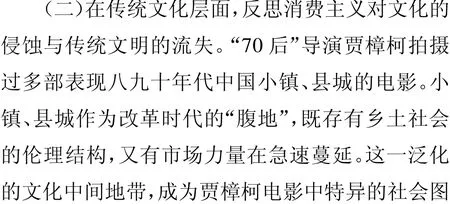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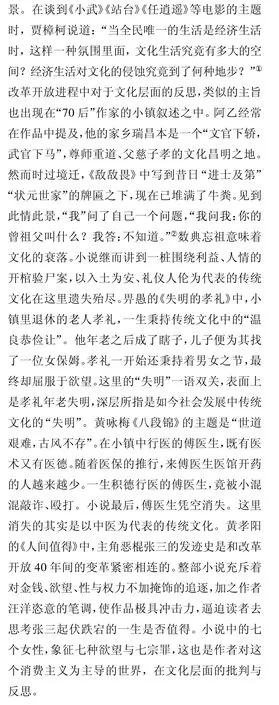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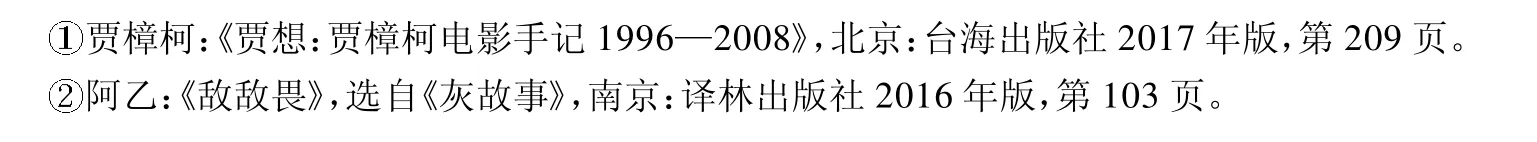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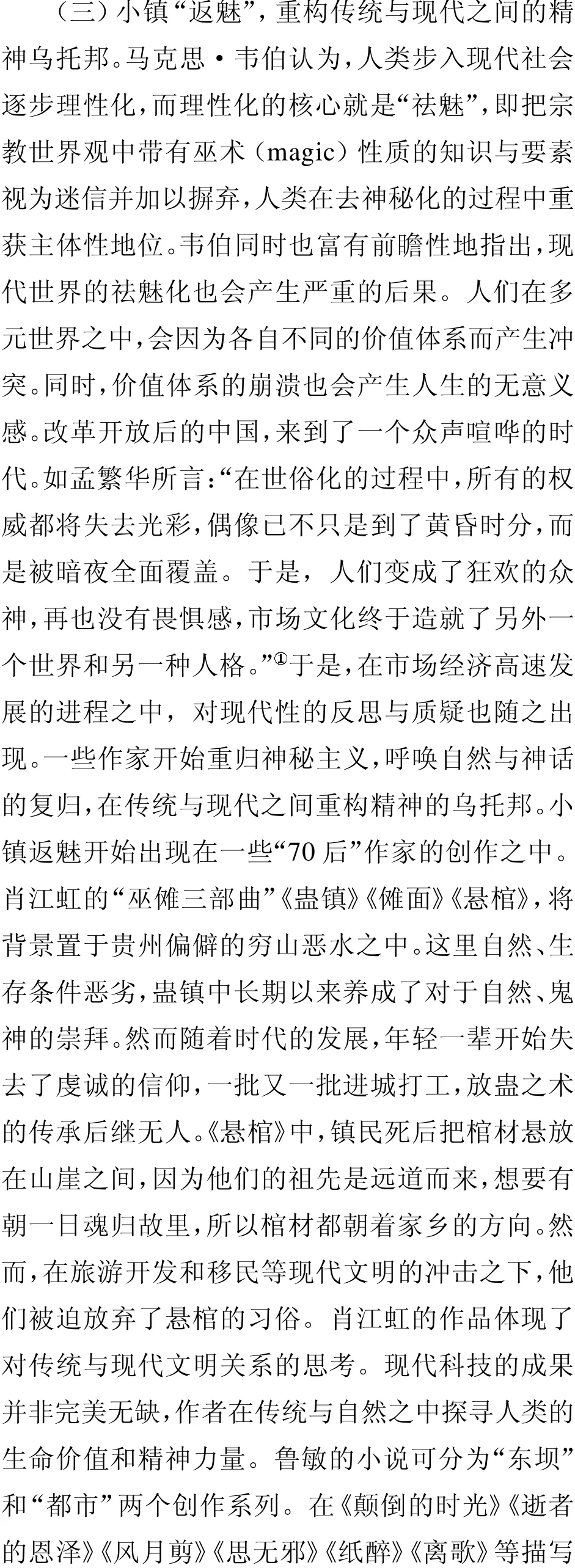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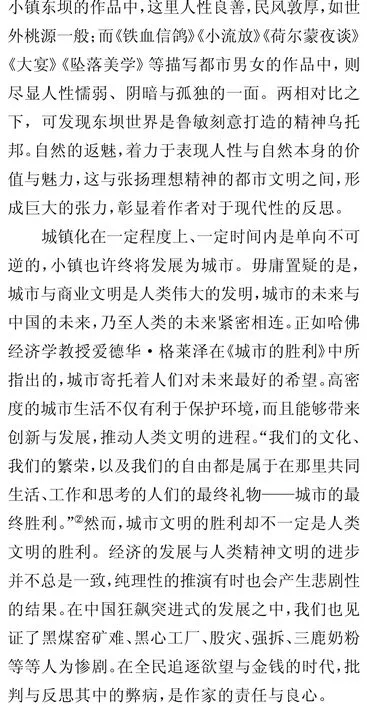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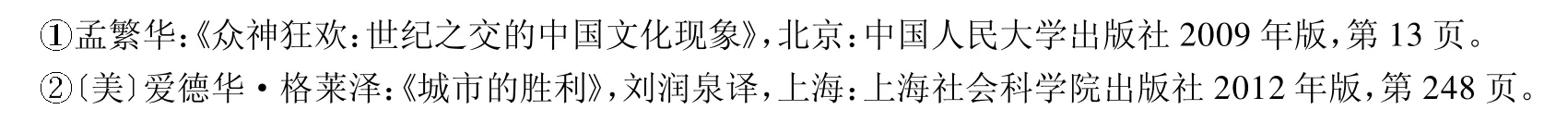
三、小镇“围城”:远方、逃离与进退失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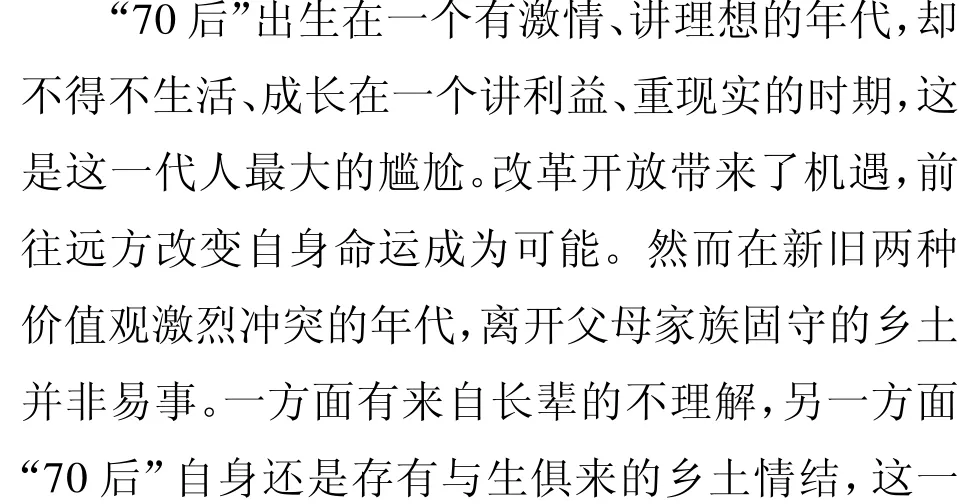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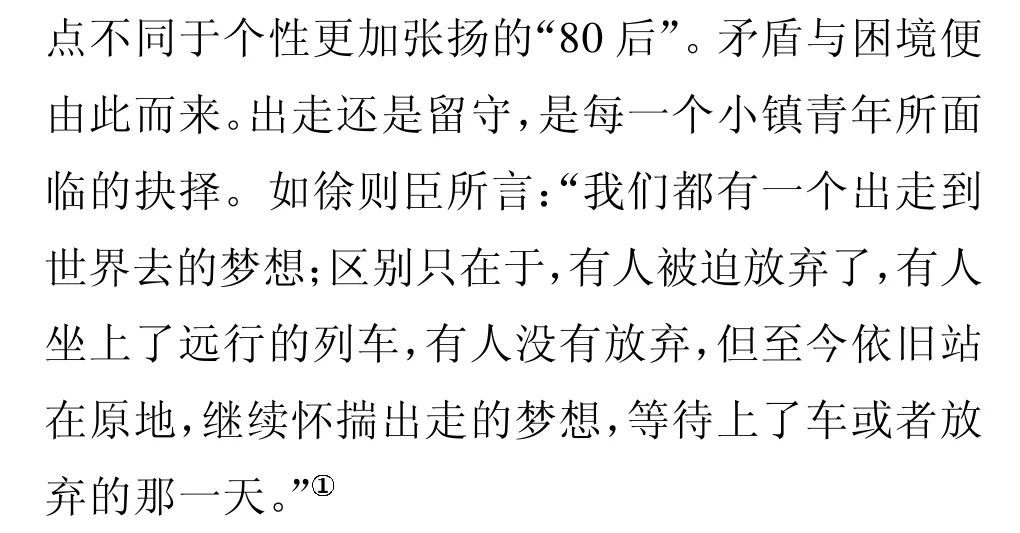
考察“70 后”作家的创作,可以发现“火车”这个意象屡屡出现。徐则臣的《夜火车》中,主角陈木年喜欢在晚上扒火车,随便去一个不知名的地方。他向往远方,他的梦想就是去见识那些陌生的人和事。绿皮火车也常常出现在路内的小说中,《追随她的旅程》结束于两场乘着火车的逃亡;《雾行者》的整体情节是坐着火车一路向西;《少年巴比伦》《云中人》《天使坠落在哪里》中,火车内的场景也都多次出现;鲁敏的《在地图上》,讲述了一个喜欢生活在火车上,在地上走反而会觉得不舒服的人;阿乙的《意外杀人事件》中,红乌镇火车站的建成,是全镇人翘首以盼的大事,他们前呼后拥,张灯结彩等着第一辆火车驶来。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火车是再平常不过的交通工具,但对于昔日小镇中的“70 后”少男少女而言,火车代表着远方的诱惑、未来的希望。出生在1970 年的贾樟柯曾回忆,自己上初一的时候学会骑自行车,头一件事就是偷偷骑去30 公里外的县城,找铁路看火车。对于火车与远方的畅想,是一代人共同的记忆。
火车承载着的是一代小镇青年离开家乡,通过奋斗改变自身命运的梦想。对城市生活的美好构想,构成了小镇青年们奋斗的原动力。徐则臣的《耶路撒冷》就是一个“到世界去”的故事。“耶路撒冷”这个遥远的地名在作品中象征未知、诱惑与憧憬,更是少年人的精神寄托。初平阳、杨杰、秦福小、易长安等人纷纷离开家乡花街,去北京闯荡。在徐则臣的另一部作品《水边书》中,沟通南北的河道勾连起少年陈千帆对于远方的想象。他向往着一人一剑走江湖,居然真的在某天离家出走,孤身前往河南少林寺学武;路内笔下的少年都渴望着远方的世界。《少年巴比伦》中的男女主角路小路和白蓝都厌倦工厂无聊的生活,想要见识外面的世界。二人之间轰轰烈烈的爱情也没有停下他们奔向远方的脚步。最终,白蓝去了上海,路小路也放弃了糖精厂的工作;李凤群《大野》的女主角名叫在桃,谐音“在逃”。在桃的一生都在和这个世界“死磕”,11 岁时便接受男孩子的搭讪,坐在她爱慕的男生的摩托车挎斗里,年纪轻轻便混迹在周边的小镇之中。在桃一路奔走,横行于世,为了成为舞台上的主角而奋斗着;朱山坡的《荀滑脱逃》讲述了一个颇具浪漫主义的故事。蛋镇里的荀滑是个小偷,他被人围追堵截在电影院中,眼看无处可逃,正赶上银幕中有火车驶来,荀滑居然跳进了电影银幕中的火车,还回过头来对所有人说,他要跟随火车离开蛋镇,到世界上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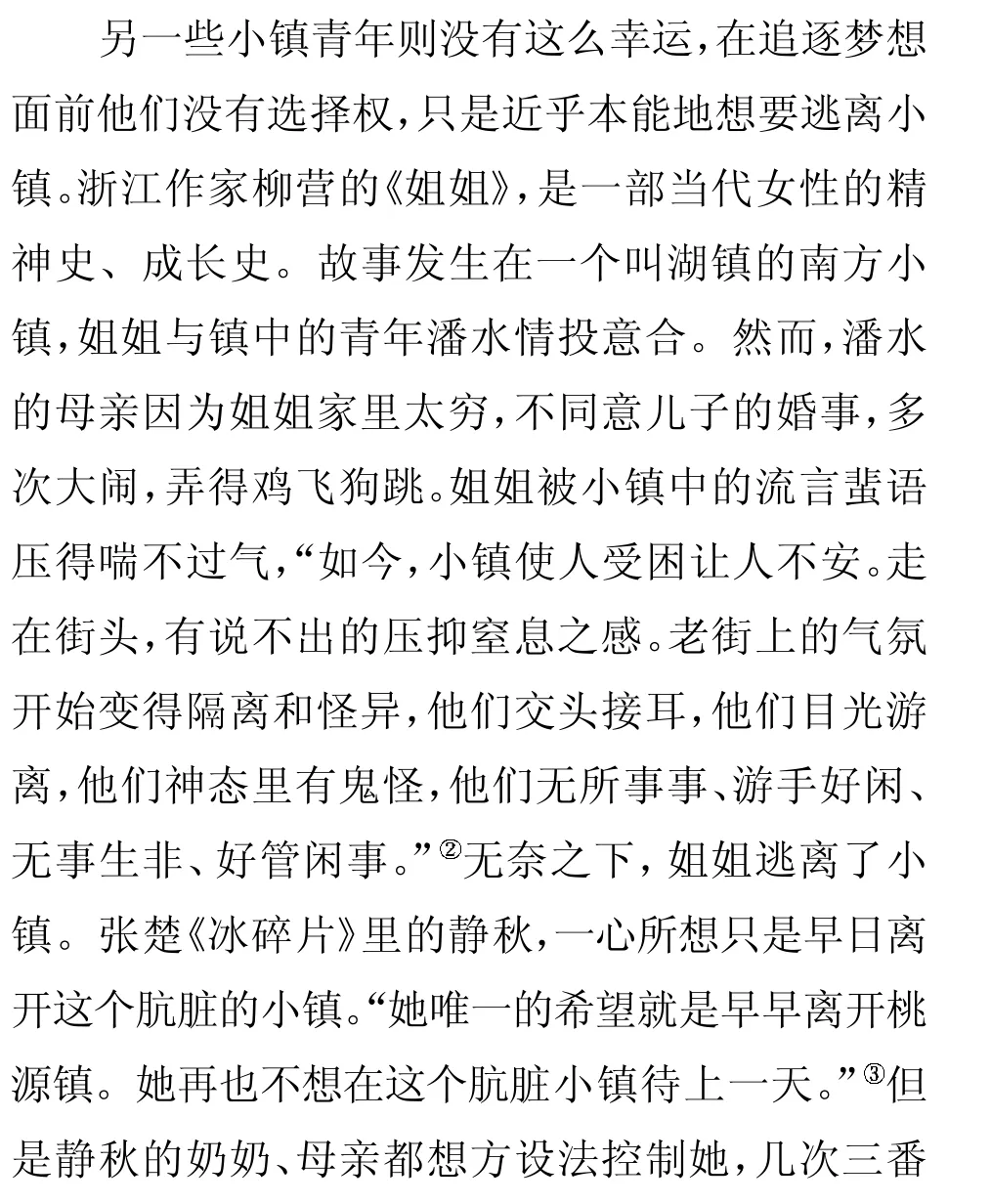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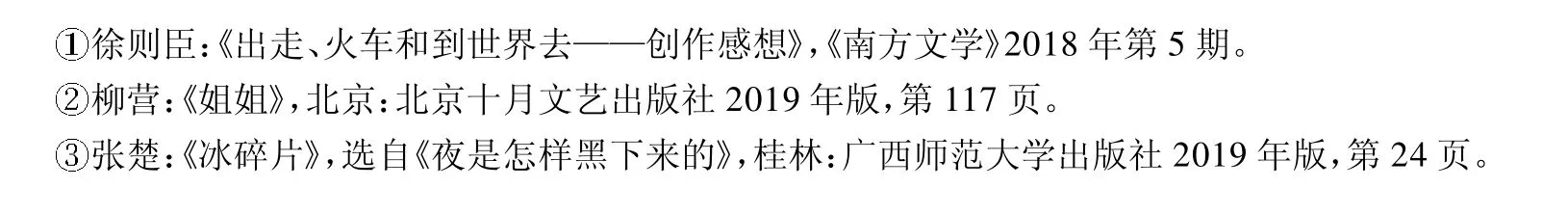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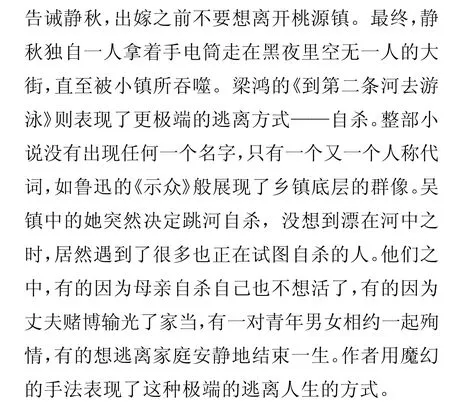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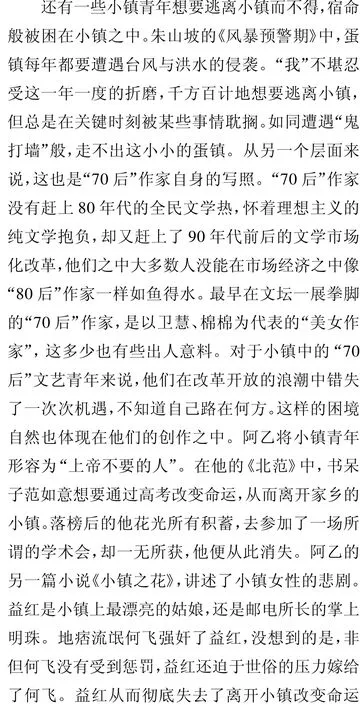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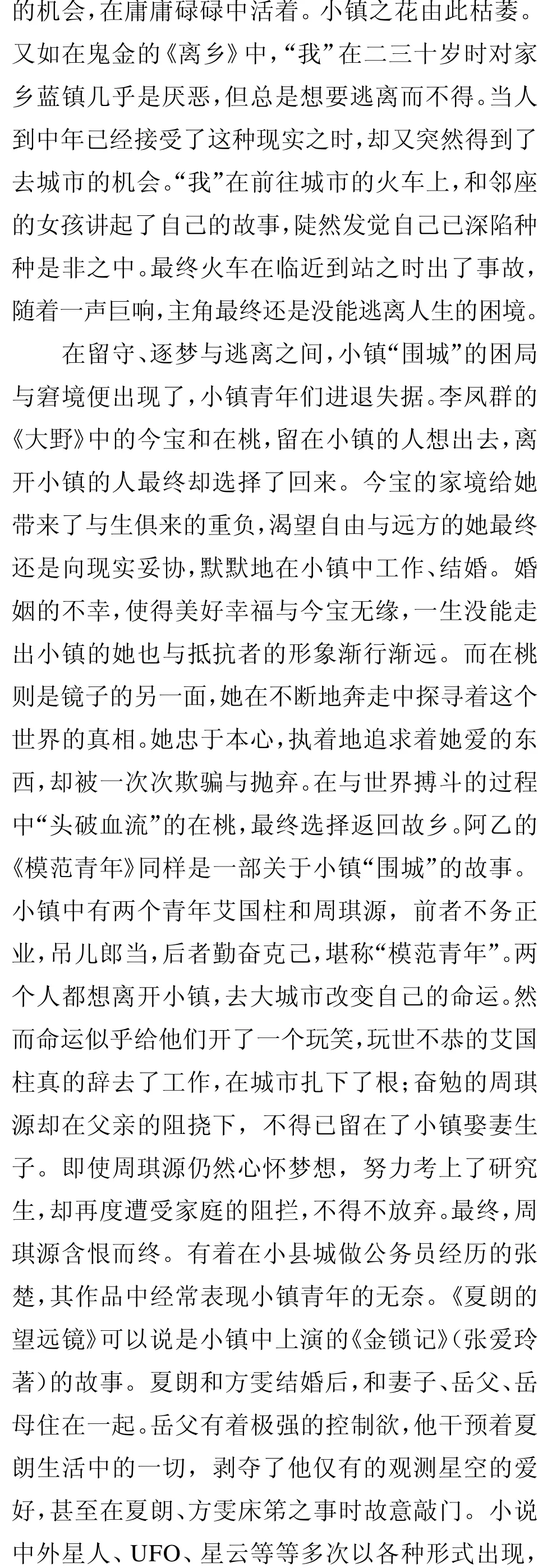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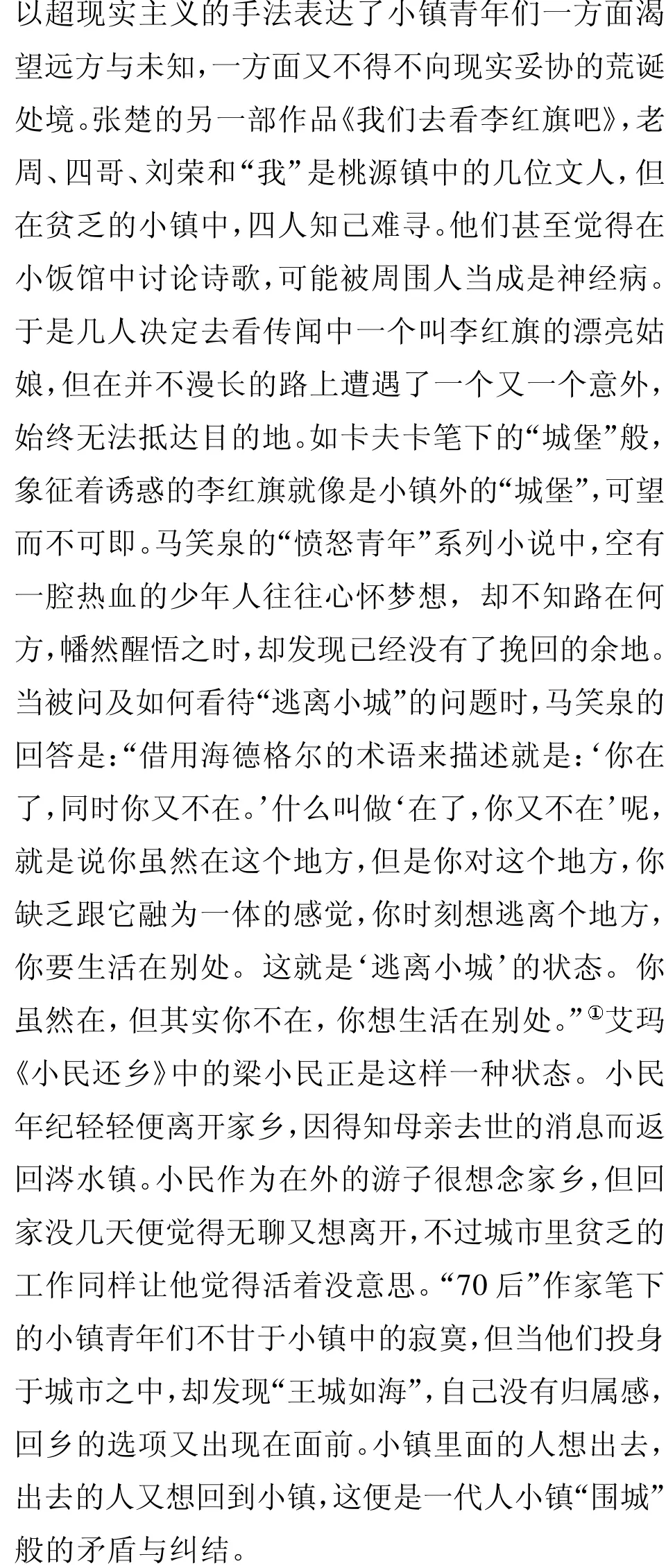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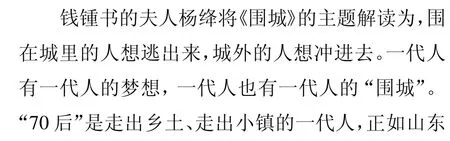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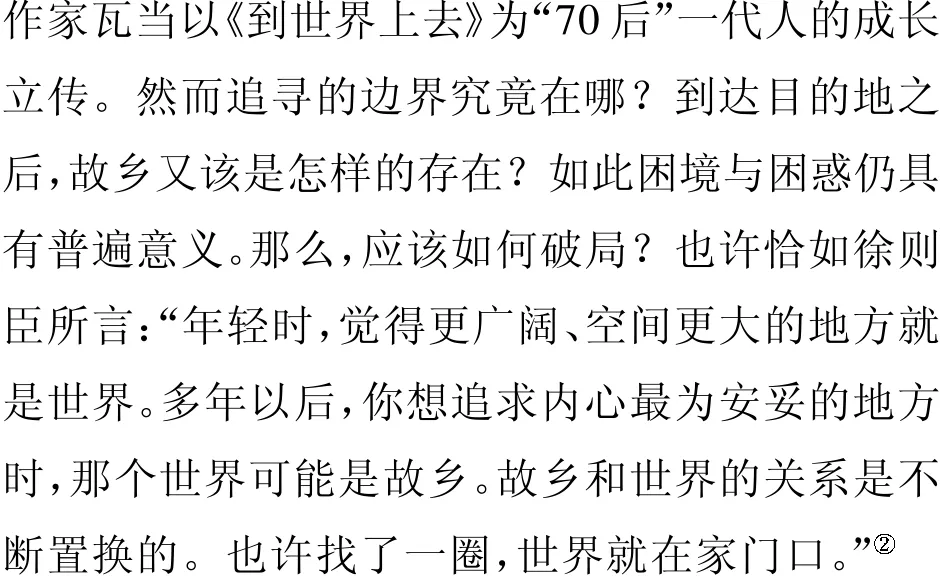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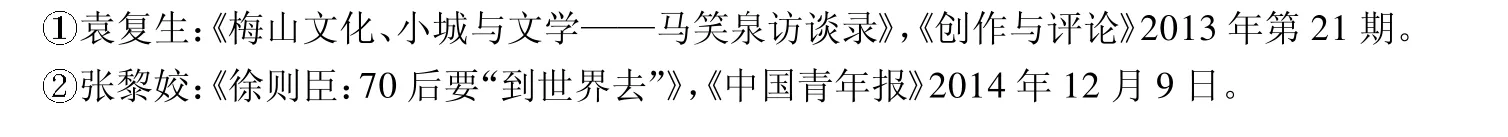
四、小镇“江湖”:改革时代的侠与义
“江湖”与其说是地理概念,不如说是权力概念。公权力真空的边缘地带,江湖才得以出现。因为“处江湖之远”,“庙堂之高”才不可触及。越是“三不管”的地域,“江湖人士”越有生存的空间。改革开放解放了生产力,带来了中国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激荡的变革中,一定时期内出现了短暂的社会失序。在这个时期的小镇之中,规则与秩序尚未完善,政府权力难以触及各个角落,这不同于城市;商品经济有了一定发展,不靠种地为生成为可能,人口构成也日益复杂,这不同于农村。所以,在城乡之间的边缘地带,小镇“江湖”随之出现。“江湖”从来不缺故事,小镇中的“江湖”也屡屡成为“70 后”作家表现的对象,出现了马笑泉的《愤怒青年》《江湖传说》、田耳的《一统江湖》《老大你好》、徐则臣的《忆秦娥》《最后一个猎人》、路内的《雾行者》、阿乙的《早上九点叫醒我》《小卖铺大侠》、黄咏梅的《达人》、黄孝阳的《人间值得》、李云雷的《纵横四海》等等作品。为何如此多的“70 后”作家涉及江湖叙事,这与他们是市场经济初起之时城乡之间混乱状态的亲历者有关。“70 后”作家大多有在底层打拼的经历,他们在迷惘的青春岁月体验了江湖中的身不由己,又在之后的成长中慢慢见证了江湖的消逝。如李云雷在谈到《纵横四海》的创作时说,1990 年代是他所在的小城发生剧烈变化的年代,他想从亲历者的角度写出那个时代底层青年的生活与命运,以及一个“江湖”的形成与消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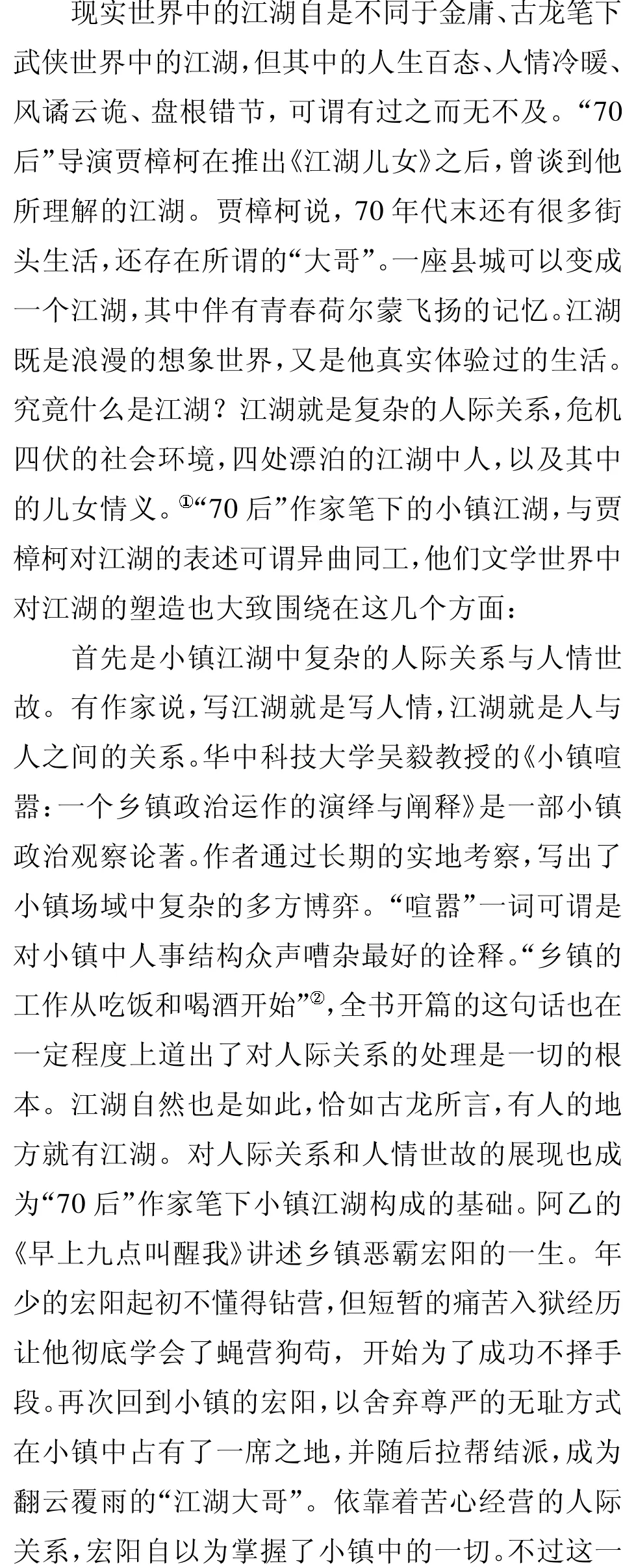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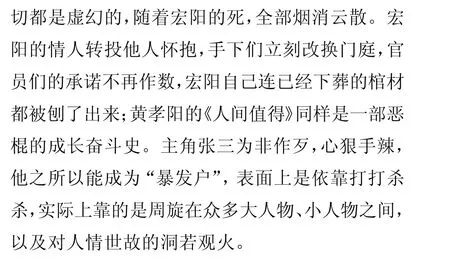
其次是小镇江湖中的秩序与权力。武侠与江湖之所以被称为成人的童话,是因为满足了饱受现实消磨之人,对于快意恩仇、鲜衣怒马、侠骨柔肠、一呼百应的畅想。现实世界当然没有这么美好,对江湖权力的争夺往往伴随着丑陋与罪恶。马笑泉的《江湖传说》,通过王一川的老师、手下、情妇,以及追捕过他的警察等人的叙述,勾勒出在县城中叱咤风云、为祸一方的帮派头目王一川的一生。王一川为人狠毒,有管理人的手段。他在成立了“大川帮”之后,靠着打架、收账等非法行径,事业越做越大。为了维系自己的权力,一个个兄弟被他抛弃。社会的失序终究只是一时的,随着一次严打,王一川便锒铛入狱;田耳的《一统江湖》讲述了权力所营造的幻象。佴城中的柯羊靠着律师生意发了家,摇身一变成为了柯老板。他依靠律师的身份,帮人解决纠纷,逐渐积累起了人脉,小城中的各种事情只要经他手都可以办成,柯老板就又成了江湖中的“柯老大”。随着名声越来越响,街上流氓和商家有了冲突,甚至更愿意找柯老大调解,而不是找警察。江湖中人对柯老大又开始以更尊敬的“柯老”相称。然而盛极而衰,众星捧月般的柯老真的以为自己做到了“一统江湖”,在一次酒席中大发感慨,大喊愿意认他做老大的人来和他喝一杯血酒。没想到却没有想象中的一呼百应,众人之中的柯老像演独角戏一般无人理睬。这一刻,柯老又变回了最初的柯羊。江湖只会出现在国家权力的边缘地带,随着社会秩序的逐步完善,江湖便会失去生存的空间。江湖中的秩序与规则只是临时填补空白,其中的权力也是脆弱不堪。

再次是四处漂泊的江湖儿女。庄子有言,“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相较于安稳,江湖儿女更向往自由。李凤群《大野》中的在桃,对小镇中的乏味感到厌烦,年纪轻轻便孤身出去闯荡;徐则臣《耶路撒冷》中花街的伙伴们,全部选择了远走他乡;阿乙《巴赫》的主角巴礼柯,为了脱离庸常的生活,选择了一次次失踪;田耳《夏天糖》里的火车司机江标,为了重温记忆中的美好,辗转在全国各地;路内的《雾行者》中的周邵、端木云以及“十兄弟”,则都是江湖中人的代表,颠沛流离与命若浮萍成为了小说的主旋律。另一些“70 后”作家的小镇江湖中,刻画了小镇中来来去去的江湖儿女群像。朱山坡的《蛋镇电影院》写到了蛋镇中的那些漂泊之人,贩卖白虎油的越南人阮囊羞、为了免费看场电影而自称有麻风病的西装革履的外来者、来到蛋镇中排演《哈姆雷特》的鹅镇“莎士比亚”、在工作室里闭门不出的神秘美工、每月都划船来看电影的来自深山的夫妇、跳进电影银幕的火车中离开蛋镇的小偷荀滑……形形色色的江湖儿女构成了蛋镇中的江湖。还有一些四处漂泊的小镇青年,自由、浪漫与美好通通与他们无关,他们的奔波流浪只是为了生存。张楚的《草莓冰山》写出了外出打工的小镇青年的艰辛,困苦的人生中,一个小小的草莓冰激凌都可以成为活下去的支柱;畀愚《寻夫记》的主角李龙香,为了寻找外出打工的丈夫,一路从北方农村辗转至南方小镇,举目无亲的她甚至被当成了疯子;盛可以《北妹》中的钱小红和李思江,历经种种骗局依然坚持在外打工,只为改变自己的命运;魏微的《大老郑的女人》中,大老郑领回家的女人其实是半良半娼,她本身有丈夫和孩子,靠着和外来打工者搭伙过日子赚些钱,以补贴自己本来的那个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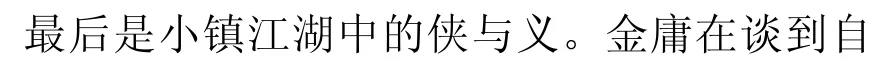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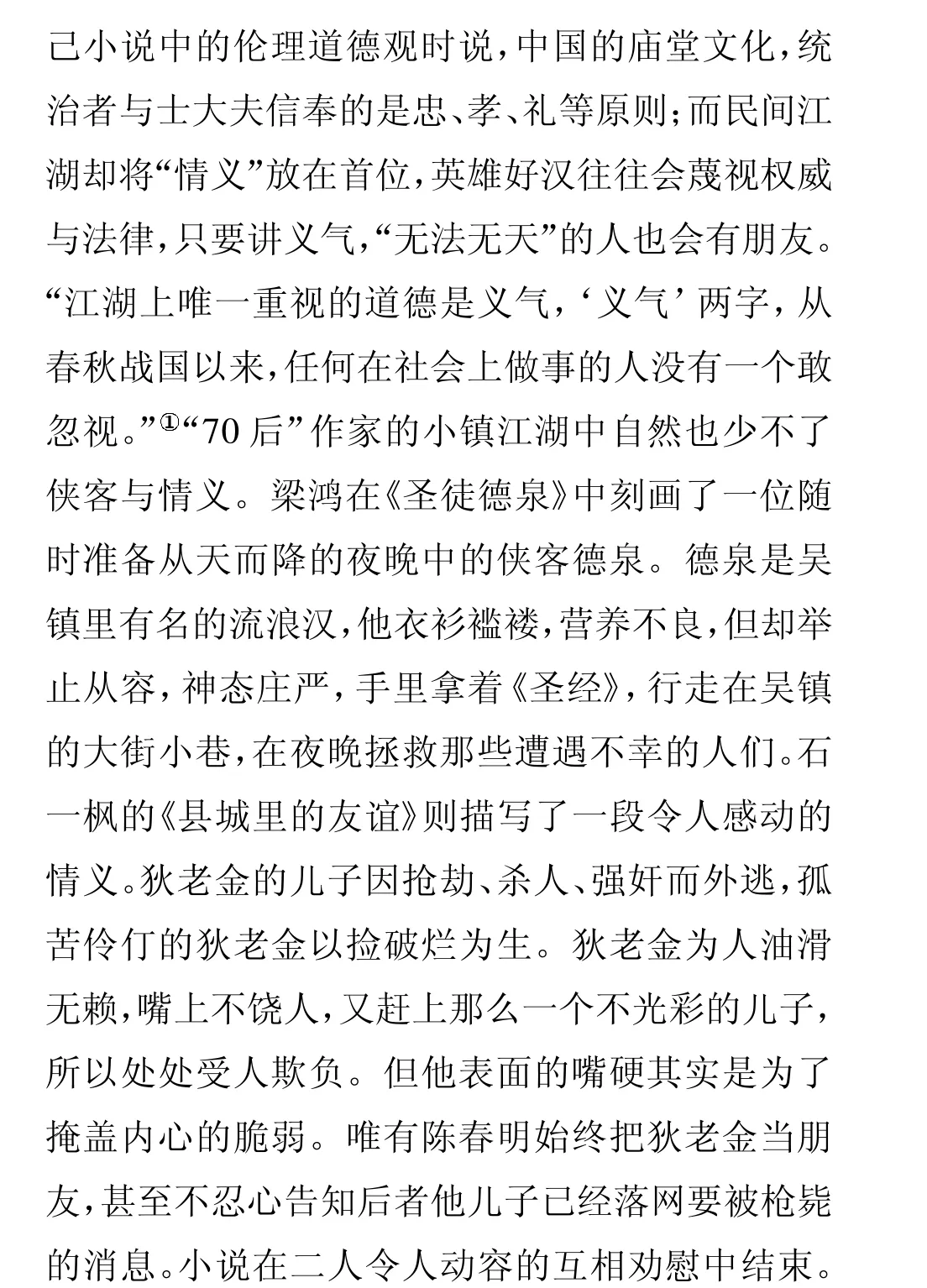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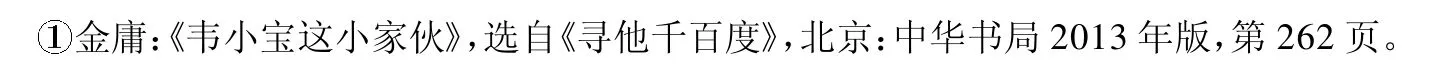
“70 后”作家笔下的侠与义,还表现了对于江湖世界的反讽,这也是当代小镇江湖的特殊性所在。黄咏梅的《达人》中,石井街的孙毅是一位精通武侠小说的“达人”,因为酷爱《射雕英雄传》,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了“丘处机”。这位小镇中的“丘处机”想要行侠仗义,却发现办什么事都要走关系,自己一介无业游民自是什么忙都帮不上。最终,“丘处机”为了生计学会了趋炎附势,在与世俗的同流合污中仍幻想着自己的侠客梦。阿乙的《小卖部大侠》则将侠义与疯癫相连。小卖铺中的张大侠是一位中年独腿的残疾人。他说自己自幼在少林寺习武,学得一身本事后孤身闯西域,大败西毒欧阳锋。如今开小卖部是为了退隐江湖。之所以还经常受人欺负,是自己故意忍着。事情的真相是,张大侠借出去4 万元钱要不回来,从此便疯了,活在自己臆想的江湖世界之中。黄咏梅和阿乙都在自己的作品里直接套用了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人名与故事,而传达出的意蕴却与“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以及除暴安良、急公好义等全然无关,甚至截然相反。当“丘处机”也“为五斗米而折腰”,小镇中的大侠其实是疯子,江湖只剩下了反讽的意味。
“侠以武犯禁”,韩非子这句话道明了一个道理:一个法制健全的社会,不会允许侠客与江湖的存在。在中国改革开放刚刚兴起的八九十年代,整个社会经历了短暂的动荡期。在城市边缘、城乡之间的灰色地带,弥补社会失序的江湖便出现了。那时叛逆的年轻人中,一部分人选择了“混社会”。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社会愈发稳定,法制愈加健全,在政府与老百姓之间,不再需要一个“江湖”的存在。“70 后”作家笔下昔日的小镇“江湖”,也许就是中国最后的“江湖”。
“70 后”网络作家十年砍柴在自传性质的《进城走了十八年》一书中写到,当他儿时以稚嫩的眼光看世界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正在目睹中国一百年间最大的变化。他为自己成长在一个生机勃勃、充满希望的大时代而感到幸运。作者靠奋斗改变命运的经历,是进城青年的缩影,也是一个国家一代人的共同记忆。在吐旧与革新间出生、成长的“70 后”一代人,时代的特征注定了他们是承前启后的一代。而承接乡村与城市的小镇,承载着他们跨越阶层的梦想,小镇经历也成为“70 后”作家深刻的人生体验。这便是“70 后”作家、小镇故事与改革开放进程之间的紧密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