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300071)
20 世纪20 至40 年代,在陈钟凡、郭绍虞、朱东润、罗根泽、方孝岳、傅庚生等一批著名学者的努力下,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得以建立和完善。自彼洎今的近一个世纪里,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包括基本文献的整理、校释,各类专题研究和通史、断代、分体的批评史撰写等,取得了极为丰富而辉煌的成就,“文学批评史”作为古代文论研究的经典路径得以稳固确立。
随着古代文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开始有学者主张拓展古代文论的研究视域。如王元化先生于1983 年提出,古代文论研究应当采取“三个结合”,即“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的方法。他特别看重文史哲结合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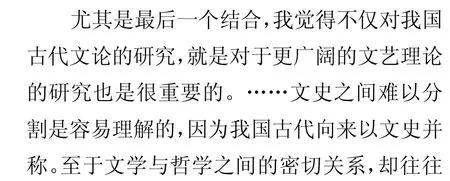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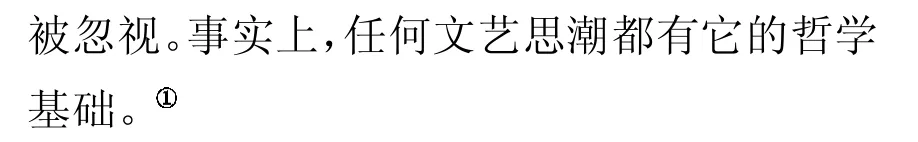

这在当时,是极富启发意义的学术思想。与此同时,罗宗强先生已经在做着实际的研究工作。他在打通文史哲壁垒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把文学理论批评与文学创作实际结合起来进行思考熔铸,切实开拓了一条研究古代文学思想行之有效的研究路径。1980 年,罗先生出版了《李杜论略》(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 年,他又出版了《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尤其后一著作的出版,在文史哲融通的背景下,切实把文学创作倾向和理论表述的文论结合起来,标志着“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范式的基本确立。此后,罗宗强先生不断探索、完善“文学思想史”的研究路径,于1991 年出版了《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浙江人民出版社)。这部著作论述了玄学思潮与士人心态变化之间的关系,进而说明了士人心态的变化怎样影响了他们对文学题材的选择,影响了他们的审美情趣,甚至影响了文体的演变。到1997 年,罗先生又出版了《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在《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原有研究思路之上,又加入了这个时期士人心态的研究,把社会政局、文化思潮、士人心态、文学创作倾向、文学理论批评逻辑严密地融会在一起,进行综合考察,对这一时期文学思想的发展演变作出了极为细密、准确且有深度的描述。这部著作完整系统地呈现了“文学思想史”研究的理念、路径和方法,标志着“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范式的成熟。
本文便是基于罗宗强先生所撰中国文学思想史的系列研究著作,简要阐述“中国文学思想史”的根本理念、思理逻辑和研究路径。
还原中国古代文论(文学思想)及其发展演进的本来面貌,寻求古代文学思想的真相和特质,是“中国文学思想史”的根本学术理念,也是文学思想史首要的研究目的。
中国文学思想史,无疑属于历史研究的范畴,这就自然产生一个根本问题:文学思想史的研究目的,是描述历史真相,还是古为今用?一般地说,此二者本来可以兼顾,并不存在势不两立的矛盾,但也确有如何去正确认识和把握的问题。在20 世纪20 至40 年代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建立之初,学者们自然而一致地认为,描述历史原貌本身就是文学批评史研究的目的——这在他们当时的著作中显然可见。但是自50 年代以后,我国学术更多地倡导和追求古为今用。在这种急功近利的思想导向下,古代文论研究事实上成为当代文论(其实主要是苏俄文论)的附庸或注脚,前者须依附于后者才能得到解释和理解。八九十年代,随着思想解放和西学东渐的潮流,古代文论研究受到西方多种学术思想的影响,不少的学者转而追求理论阐释——古为今用的渴望似乎淡弱了,借用西方某种思想方法以发挥宏论的热情却高涨起来。世纪之交,趋奉西学的思想热潮逐渐有所平静,学人重新思考古代文论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于是,又回到了问题的原点——古代文论研究的基本目的,究竟是追求当下实用,还是描述历史原貌?客观地说,学界同仁迄今还没有趋于一致的看法。默默地追究历史真相者、热衷于借助西学展开思想实验者、心心念念追求“现代转换”者并存,大家都在努力做着自己的研究工作。这是文化和学术思想多元时代十分正常的现象,学者都可以本着自己的理解和意愿去做学术探索。
只是,“中国文学思想史”作为一种古代文论研究的新路径,有着自己的学术理念和旨趣。“中国文学思想史”怎样看待古代文论(文学思想)的研究目的呢?罗宗强先生曾经多次反复强调:追求和描述历史真相,就是“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的根本目的。他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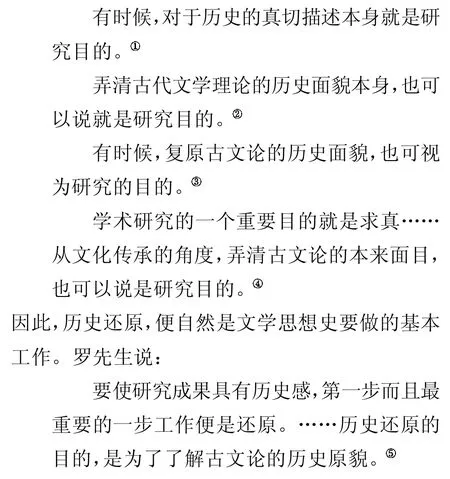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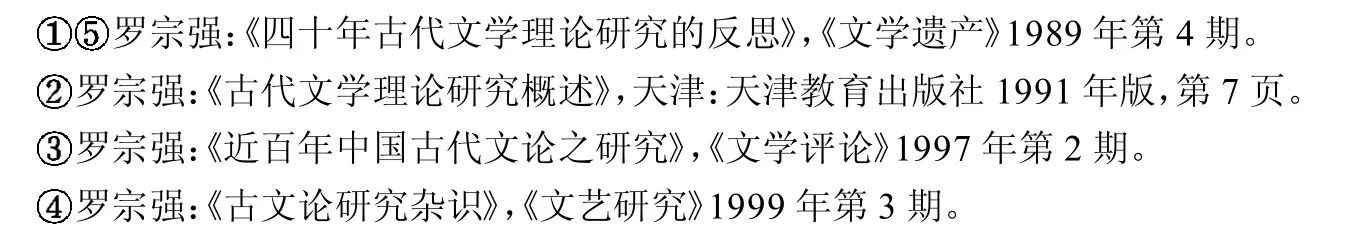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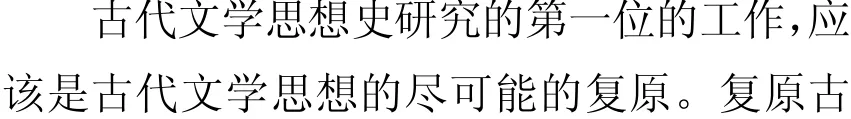
一、历史还原:中国文学思想史的学术理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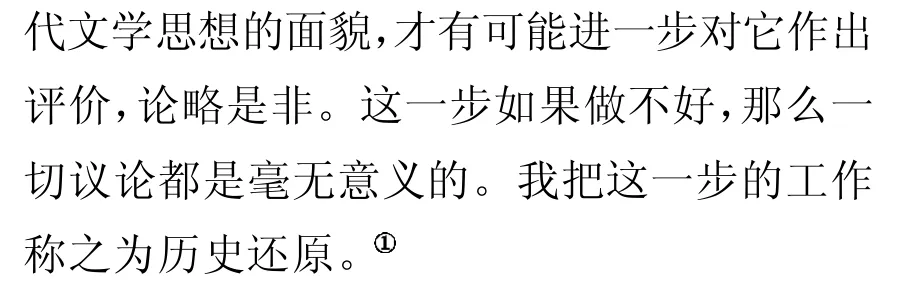
罗宗强先生先后出版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明代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2013),以及相关的专题研究著作如《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读〈文心雕龙〉手记》(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07)等,无不鲜明地体现着追求历史还原的求真求实的学术精神。
这里需要厘清与历史还原相关的两个思想问题:
第一,历史还原是否可能?“文学思想史”强调历史还原,当然不是没有看到研究者的当代意识和知识结构必然会影响历史书写这个实情,也不是不懂得史料文献不足够的客观制限;而是认为,正缘于此,就更有必要强调:研究者在尽可能多占有直接间接相关的史料文献的基础上,进行全面而客观的梳理分析,使历史描述尽可能地接近于历史原貌。罗先生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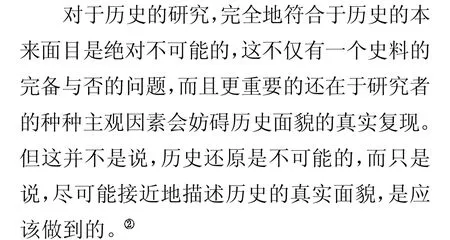
也就是说,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完全符合历史真相的历史还原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不能因此便放弃对历史真相的追求,更不能因此便根据研究者的意愿去任意地解读、讲述历史。把历史当作“小姑娘”随意打扮,那是小说家的操作,不应成为学者的做法。学者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基于现存所有相关史料,最大限度地接近和描述历史原貌。这是“中国文学思想史”追求历史还原的真义所在。
第二,历史还原与当代思想文化建设有无关联?强调追求历史真相,并非忽视古代文论研究对于当代文化建设的作用;而只是认为,像古代文论(文学思想)这类传统思想文化的基础研究,对当代社会、思想、文化的建设作用,不是立竿见影、即时可用的,而是潜移默化的。它的作用和功效,必将经历一个较长时期才能体现出来。罗宗强先生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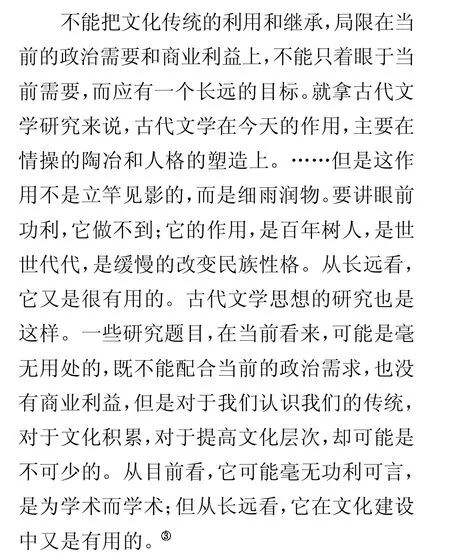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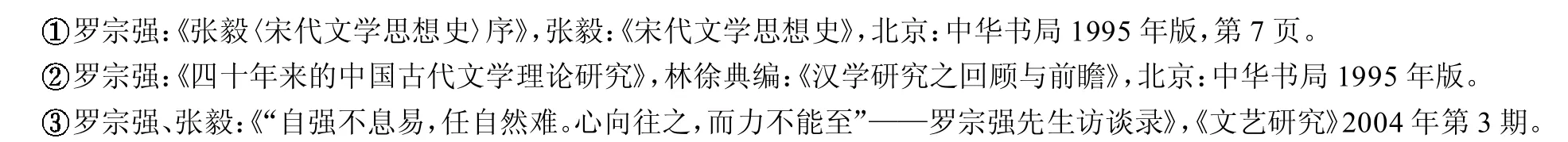
二、文学创作倾向:中国文学思想史所开拓的研究路径之一
中国文学思想史的研究目的,是要尽可能描述古代文学思想之内涵、特质及其发展演进的原貌。然则,如何实现这一研究目标?或者说,以怎样的方法、经由怎样的途径去实现历史还原?文学思想史在承续文学批评史的经典研究路径——解析理论表述形态的文论著作之外,又开拓了两条研究路径:其一,是把理论表述形态的文论著作与相应时期的文学创作实际结合起来,也就是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相结合,共同考察一个作家、一个流派、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学思想观念。其二,是把士人心态作为社会政局、文化思潮等外部影响因素与文学创作倾向、文学思想观念的中介,充分重视士人心态的折射作用。这里先看第一条路径。把理论批评与创作实际结合起来,相互参照,作出综合判断,这是“中国文学思想史”基本的学术思想,也是最基本的研究路径,它是实现历史还原的重要保证之一。同时,这也是文学思想史区别于文学批评史的关键所在。这个学术思想,罗宗强先生早在1980 年出版的《李杜论略》一书中就已经提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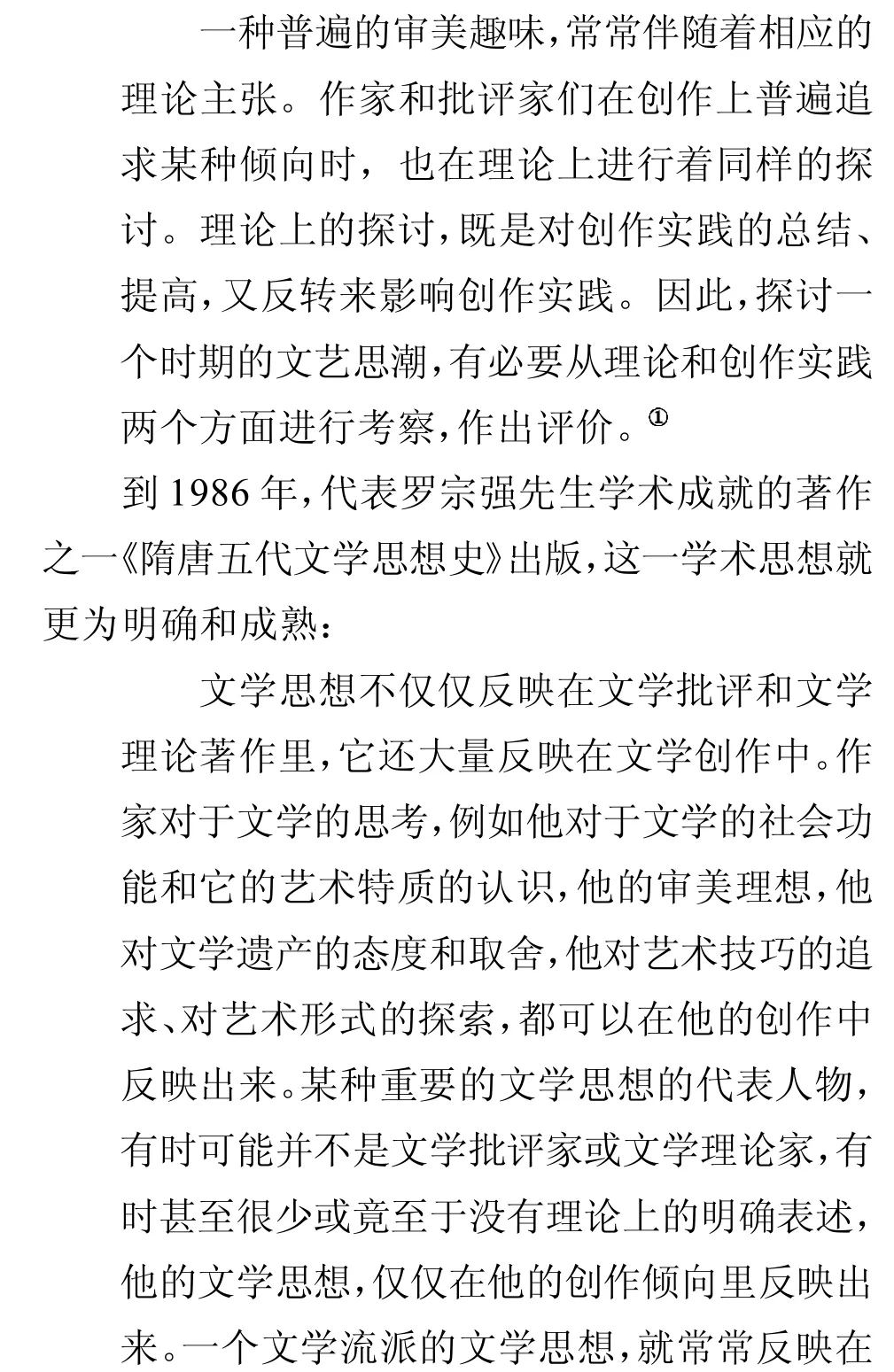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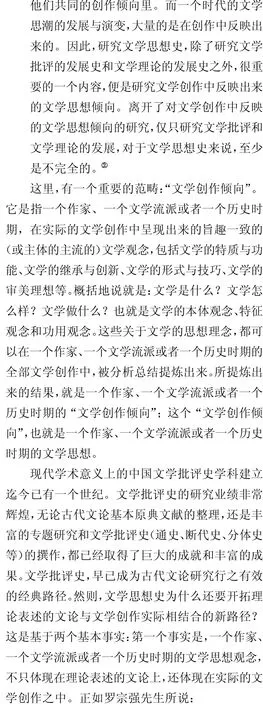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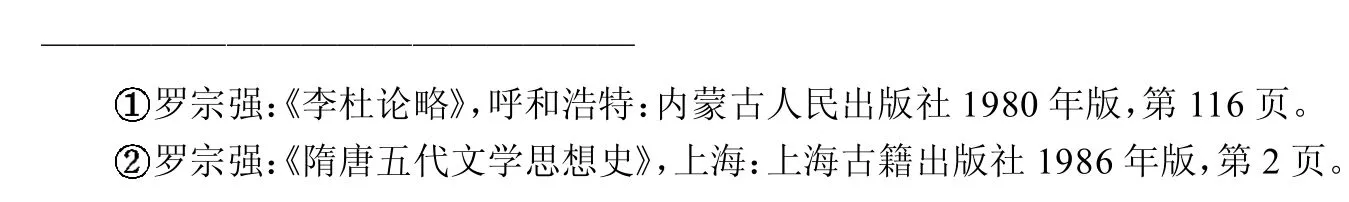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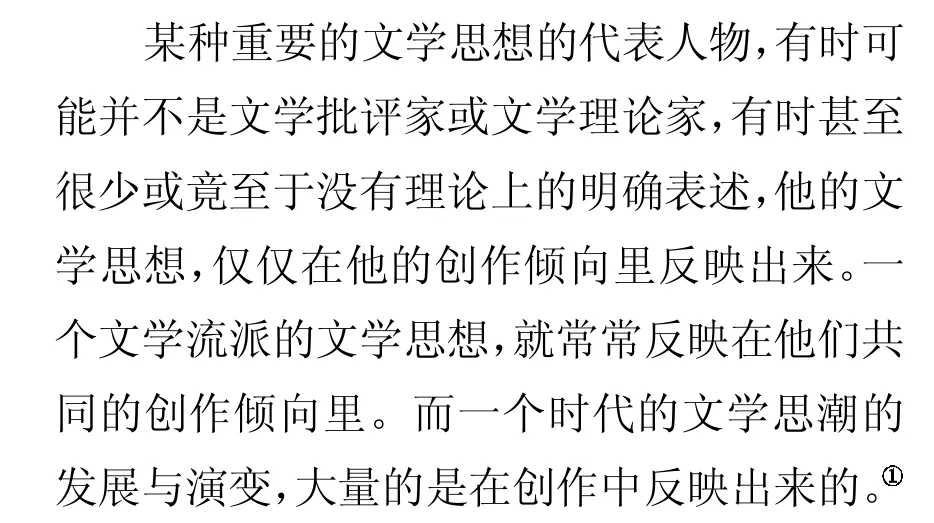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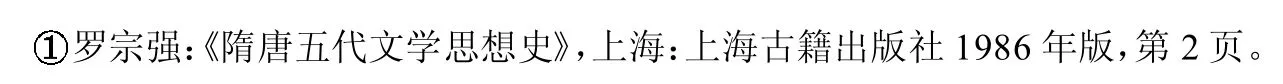
如果仅限于解析理论表述形态的文论,而不关注实际创作中呈现出来的文学思想,那么,对一个作家、一个文学流派或者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学观念的描述,可能就是不完整的。第二个事实是,往往有这样的情形:一个作家或一个历史时期理论表述形态的文论,与这个作家或历史时期实际的文学创作旨趣并不一致,甚或错位。如果仅限于解析理论表述形态的文论,而不关注实际创作的主流倾向,对某个作家或历史时期文学思想的描述,可能就不够全面不够准确。举两个例子来看:
一个例子是南朝时期。这个历史时期,理论表述的文论与实际的文学创作倾向之间,就存在错位的现象。南朝无疑是文学理论极为发达的时代,同时也是文学创作繁荣并且不断探索出新的时代。但是看一下这个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文论著作——《文心雕龙》和《诗品》,它们所表述的文学思想,整体来说是偏于正统和保守的:《文心雕龙》论“文之枢纽”,首列“原道”“征圣”“宗经”;论诗则以“诗言志”“持人情性”“义归无邪”(《明诗》)为准则;论骚则以为“诗人提耳,屈原婉顺。《离骚》之文,依经立义”(《辨骚》);论赋则以为“《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诠赋》);论文则以为“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序志》)。刘勰的文学思想总体上是正统的、经典的。《诗品》品第诗之高下,所奉行的原则或标尺,便是其《序》所主张之兴、比、赋“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吟咏情性,亦何贵乎用事?……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今既不被于管弦,亦何取于声律耶?……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也就是持守风雅比兴传统,无需用典,不必过分讲求声律。钟嵘的诗歌思想,也是中正的、保守的。而南朝实际的文学创作,则与刘勰、钟嵘阐述的文学思想大不相同:不那么关注重大社会政治而注重独抒一己的情志,开拓更多的文体形式和文学题材领域,深细地探索文学的多种艺术表现技巧,这才是这个时期文学创作实际的普遍情形。然则,南朝时期普遍的主流的文学思想观念该当如何描述?显然,如果仅仅依据《文心雕龙》《诗品》等理论著作来描述,那就与历史真相相距较远了。而把南朝文学创作的实际倾向结合进来,共同梳理、描述南朝时期普遍的文学思想观念,就会更为确切一些。
再一个例子是唐代。唐代各体文学创作的成就均可称巨大,但是众所周知,唐代理论表述的文论却显得零散不成体系,文学理论成就不足,这也是实情。那么,鉴于这种理论阐述远逊于创作实际的不同步、不一致的情形,可以判断为唐代的文学思想比较贫乏吗?一个文学创作十分繁荣、成就空前巨大的时代,却没有自己成熟的文学思想观念吗?显然,没有人会做这样的论断。然则,唐人的文学思想观念该怎样去总结描述呢?这就必须在唐人的文学创作实际中提炼他们的文学思想。如果不去关注唐代文学的实际创作,仅限于解析这个历史时期理论表述的文论,那么对唐代文学思想观念的描述,可能就会比较零散不成系统,也可能就不那么周全完善。
上述文学理论主张与创作实际不相吻合(或不同步、不一致)的状况,也体现在一些重要作家的身上。有的作家文学创作成就极大,却并没有理论阐述的文学思想。比如李白,基本找不到他的理论表述形态的诗歌思想,但是很难因此就论断说:像李白这样的一流大诗人,对“诗是什么”“诗有怎样的表现特征”“诗为何而作”等问题,没有自己的明确见解——任谁都不会这样去认知的。李白肯定有自己的诗歌思想,只是他并没有理论的表述和阐发;他的诗歌思想,需要从他所有传世的诗歌作品当中总结提炼出来。另有一些作家,他既有丰富的文学创作实绩,也有重要的文学观念阐述,但是他的实际创作和理论表述之间存在着悖离的情形。比如白居易,其《与元九书》历数中唐以前的诗史,拈出“六义”“风雅比兴”的创作纲领;他“常痛诗道崩坏,忽忽愤发,或食辍哺、夜辍寝,不量才力,欲扶起之”,大力倡导“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白居易诗歌创作的实际情形究竟如何呢?不妨引出他的自述:“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讫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谕诗。又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又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一百首,谓之感伤诗。又有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一百韵至两韵者四百余首,谓之杂律诗。凡为十五卷,约八百首。”(以上均见《与元九书》)白居易分类编辑自己创作的四类诗歌中,唯有“讽谕诗”150 首,是符合其“合为时”“合为事”的理论主张的;其他三类“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共600 余首,则大抵都是与现实社会政治并无直接关系的自抒一己感怀和情志意趣的诗作。那么,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美刺兴比”精神,究竟可不可以判定为白居易主要的或基本的诗歌思想呢?显然是不甚恰当的。因此,要想准确地归纳总结白居易的诗歌思想,需要把他的《与元九书》和他的800 首诗歌作品联系起来共同参酌,才能得到比较准确的切近实际的认识。
要之,“中国文学思想史”的基本思想理念和研究路径,就是要把实际的文学创作倾向提炼出来,并与同时期的文学理论(批评)相校互参,把二者综合起来,完成对一个理论家、一个文学流派或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学思想的描述。遵循这一思想路径所得出的结论、所描述的样貌,可能会更为准确切实一些,更加靠近历史真相一些。把理论主张与创作实际二者结合起来考量,也正是实现文学思想史追求历史真实面貌之研究目的的主要学术路径之一。
三、士人心态:中国文学思想史所开拓的研究路径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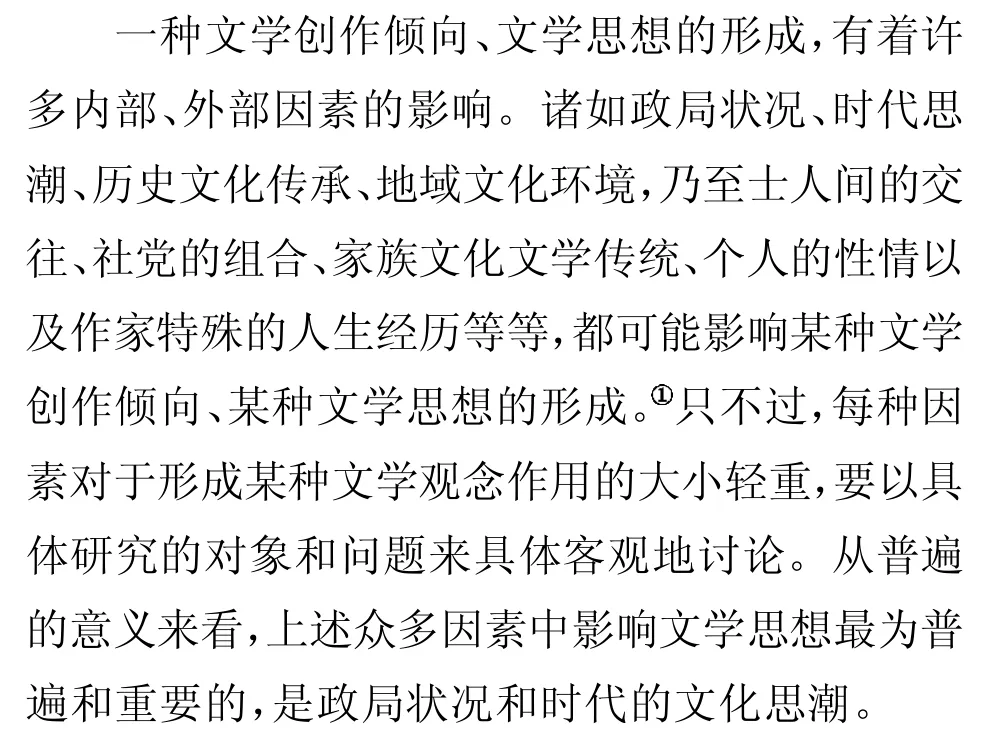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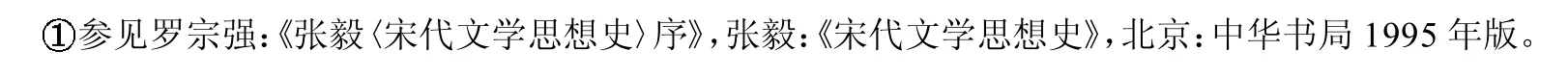
在这里,有必要强调一个不应忽略的思想逻辑,那就是:政局、思潮并不能直接对文学创作、文学思想发生作用,处在政局、思潮与文学创作、文学思想之间的,是士人,是士人心态——士人的生存状态和由此而形成的士人的处世态度。政局、思潮等外部因素对文学创作倾向、对文学观念的影响,必然是通过士人心态这一中介来实现的。因为文学毕竟是人学,它是描写人的生活、人的理想、人的心灵;社会时代的、历史文化的、生活处境的一切影响,终究要通过士人心灵的反应和折射,才能流向文学作品,影响文学观念。
“中国文学思想史”确立这一学术理念和思想路径,还有一个更加切合实际的理由,那就是:中国古代的士人与政治生活关系极为密切,一个时代的政治状况,往往决定着其时士人的出处进退,影响着他们对社会人生的看法,也就是对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生活理想有着直接的影响,这种影响自然会在他们的文学创作、文学理论批评中表现出来。与此同时,一种强大的时代思潮,也往往同时左右着士人的生活理想、生活方式和生活情趣,进而对文学之本体及其功能的认识、审美追求、题材倾向诸方面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士人心态的中介和折射作用,在一种文学思想的生成和演变中具有关键或枢纽的意义。只有弄清楚政局、思潮等外部因素如何影响士人心态以及士人心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才可以理解他们的处世态度、人生旨趣何以发生了这样那样的变化,才可以理解他们的文学创作倾向、审美情趣、文学观念发生了这样那样的变化。也就是说,只有弄清了士人心态的性状样态,才可能具体真切地描述某个时期某种文学创作倾向、某种文学思想观念的形成及其演进的面貌。
这个学术思想路径,是罗宗强先生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时所开拓的。他于1991 年出版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就是标志和代表。这部著作,以及出版于2006 年的《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都明晰切实地呈现了士人心态的研究与文学思想的研究之间密不可分的思理逻辑关联。
应该说明的是,“中国文学思想史”的士人心态研究,学术目的十分明确。它主要研究一个历史时期士人群体的处世心态,及其与当时文学思想发展动向的因缘关联,而不是单纯的心理学或社会心理学意义上的心态研究。因此,它与单纯心理学或社会心理学家的研究方法也有很大不同。罗宗强先生对士人心态的考察,主要是从三个方面进行的,即:政局状况、时代文化思潮和社会历史环境提供给士人的生活出路的情况,研究这三种因素对士人心态的影响。至于影响个人处世心态的种种特殊因素,诸如地域文化、家族文化传统、社党组织、人际交往、婚姻状况、个性特征以至人生经历中的某种特殊际遇等等,对于个案研究固然十分重要,但对一个时期的士人群体而言则往往不具有普遍的意义。这就表明,罗先生的士人心态研究,是紧紧围绕着他的最终目的——文学思想史而进行的。所以他的研究对象,主要侧重在士人群体的心态倾向和处世态度,其目的在于更准确深入地说明一个时期文学思潮的状貌及其演变情状。当然,主要进行士人群体心态的研究,是从文学思想“史”的论域来说的;这并不是说不能研究士人个体的处世心态——有的时候,研究个体士人的心态,对于体认这个士人甚至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学思想而言,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要依据具体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来确定。
经典的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研究,也注重政局社会、文化思潮等外部因素对文学创作、文学观念的影响作用。不过,它们往往会默认:政局社会、文化思潮等外部因素与文学作品创作、文学思想观念之关联,乃是一种直接的因果关系。这一思想理路,在任何一种文学史、文学批评史著作中都有呈现。这样的认识,大格局大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它的思想逻辑还不够精确不够严密。比如,它很难解释处于同一时代、同一社会政局、同一文化环境甚至同一生活圈儿当中的作家,他们的文学创作特质、文学思想旨趣却并不相同的现象——而这一文学现象,是文学史上最为普遍的情状。因此,只有补足士人心态这个关键和枢纽环节,充分体认士人心态的中介和折射作用,才能更加准确地认知某种文学创作倾向、某种文学思想的形成及其特质,才能更趋近于历史真相。
士人心态对于“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的重大意义,一言以蔽之,就是补足了一个重要的思想逻辑环节,使文学思想研究的思理逻辑更加周密谨严了。揭示并充分考量士人心态的中介作用,是“中国文学思想史”追求历史真相的又一条必由之路。
综上所述,“中国文学思想史”的研究路径,在对象范围、思想理念、路径方法几个方面,对古代文论研究都做出了系统周密的新的规划,从而与传统的文学批评史研究区别开来,事实上形成了一个新的学科。它的基本模型是:把政局社会、文化思潮、士人心态、文学创作倾向、文学理论批评逻辑严密地融会在一起,作综合考察,以描述文学思想的特质和演进。其中,士人心态是政局社会、文化思潮等外部影响因素与文学创作倾向、文学理论批评之间不可或缺的中介;文学创作倾向是文学思想不可忽视的重要呈现,要把它与理论表述的文论结合起来,共同论定文学思想的内涵。
最后,还必须申明一个学术理念:“中国文学思想史”的思理途径,强调打通文史哲的界域,全面了解相关的文史哲史料,作为研究文学思想的背景和参照。而融通文史哲、作多学科交叉研究的目的,乃是为了弄清楚某种文学思想的历史内涵、形成原因及其演进的因缘,是为了理解文学思想研究中的种种问题。罗宗强先生强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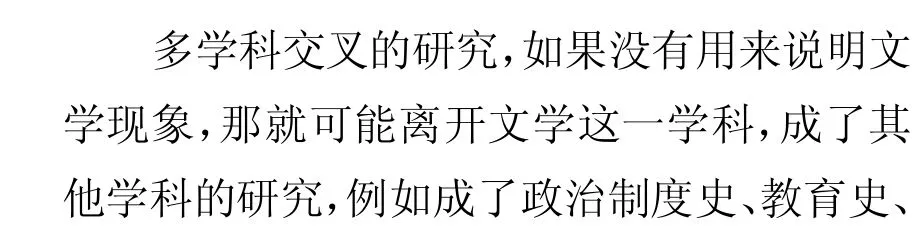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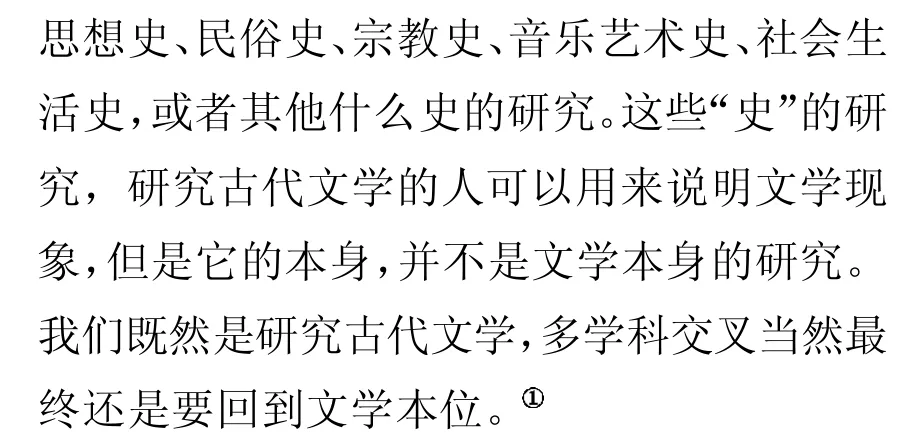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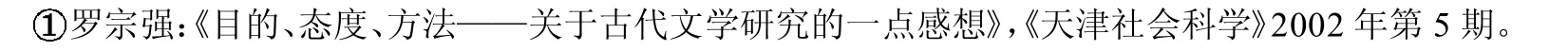
回到文学本位的实质,是回到文学审美上来。文史哲综合考量的目的,是寻找多学科因素与文学审美的关联,以便更加准确深入地描述文学思想的形成及其演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