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潭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 湘潭411105)
被誉为“外部思想家”“实验哲学家”的法国著名思想家德勒兹是20 世纪后马克思主义美学领域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具有重要诗学意义的“机器”与“装配”概念表达了非同凡响的文学旨趣,突破了传统文学阐释的思维定式,为我们审视经典作家带来了新的感悟与阐释路径。在德勒兹的“文学机器装配”视域中,狄更斯是文学机器装配的大师,他的每一部小说都体现了块茎图式的机器装配,这一艺术手法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超文本作家及其作品。
一、“文学机器装配”界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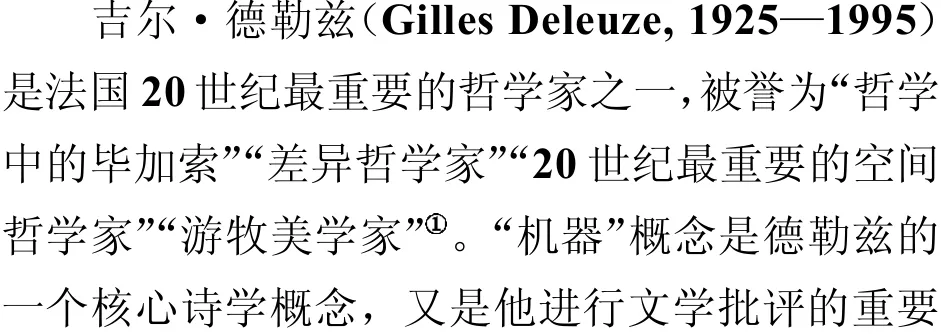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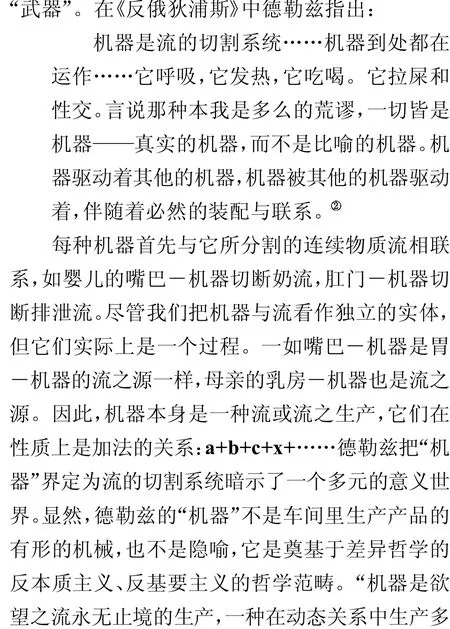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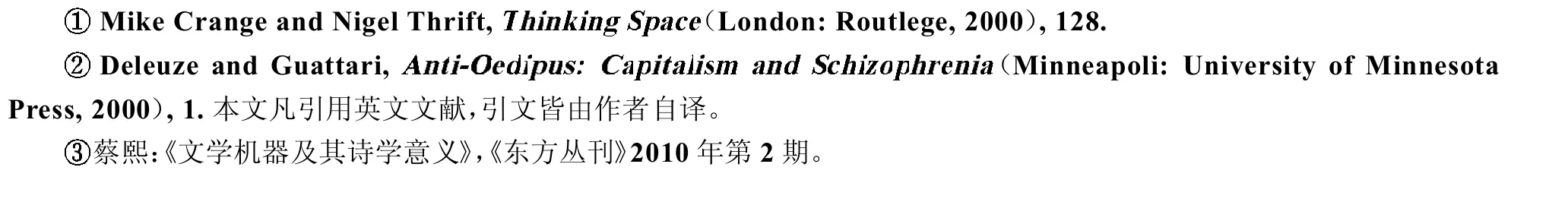

德勒兹的“机器”与块茎、装配、解域、逃逸线皆为一致性平面上的一系列概念图式,具有内在的有机关联。因为机器的运转不是各部件的单独运行,而是各部件的共同作用。德勒兹在《千高原》的序言中列出了一系列等式,块茎学=精神分裂分析学=地层分析学=语用学=微观政治学。
德勒兹的“解辖域化”概念是对拉康的“辖域化”的反拨。在拉康那里,辖域化指一种将欲望和某种器官与对象的关系加以固化的过程,它意指既定的、现存的固化的疆域,疆域之间有明确的边界。在人类的物质实践与精神实践中,辖域化的表现以西方文化模式为甚。西方思想文化的一种主要模式是将事物划分为条条块块以便于掌握。德勒兹的“解辖域化”概念在心理学领域颠覆了拉康式的辖域化,将欲望从已经建构而成的器官与对象的关系中解放出来;在社会领域,解辖域化用来将劳动力从特定的生产工具或方式中解放出来;在德勒兹后结构主义的诗学意义上,解辖域化指从所栖居的或强制性的社会和思想结构内逃逸而出的过程。在德勒兹看来,精神分裂症是解辖域化的完美存在方式。逃逸线与解辖域化密切相关,它强调摆脱既定辖域,通往自由的境界,旨在创造新的流变与生成的可能性。逃逸线是抽象的生命之线,创造之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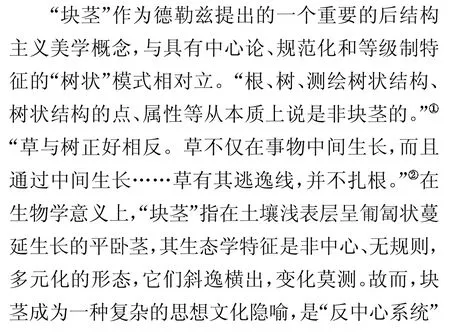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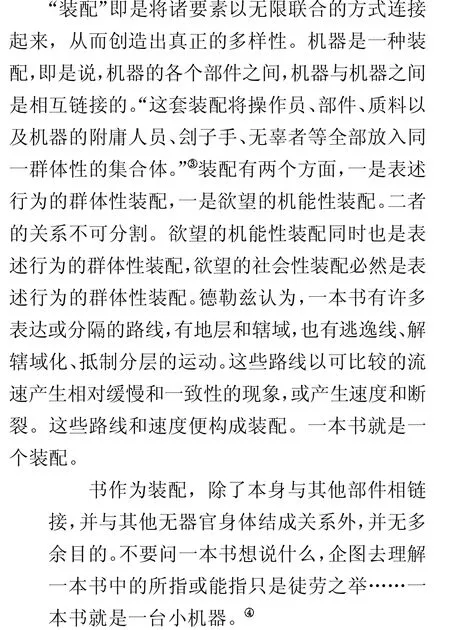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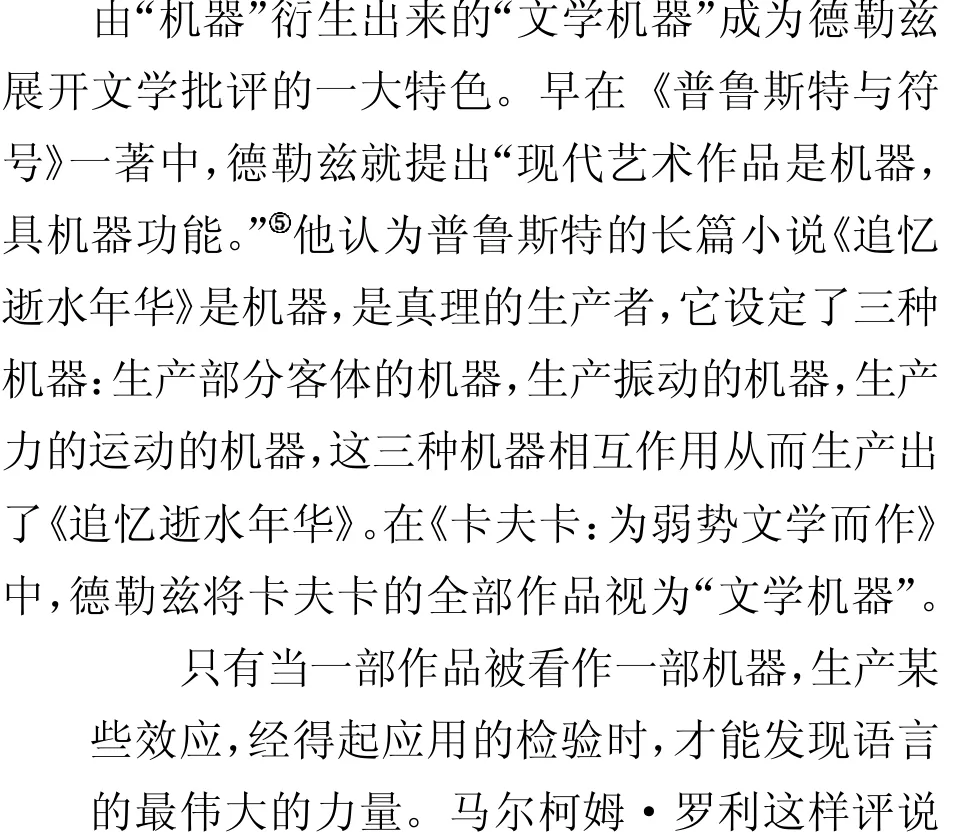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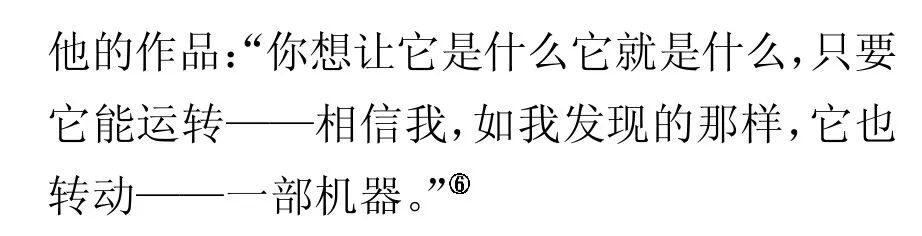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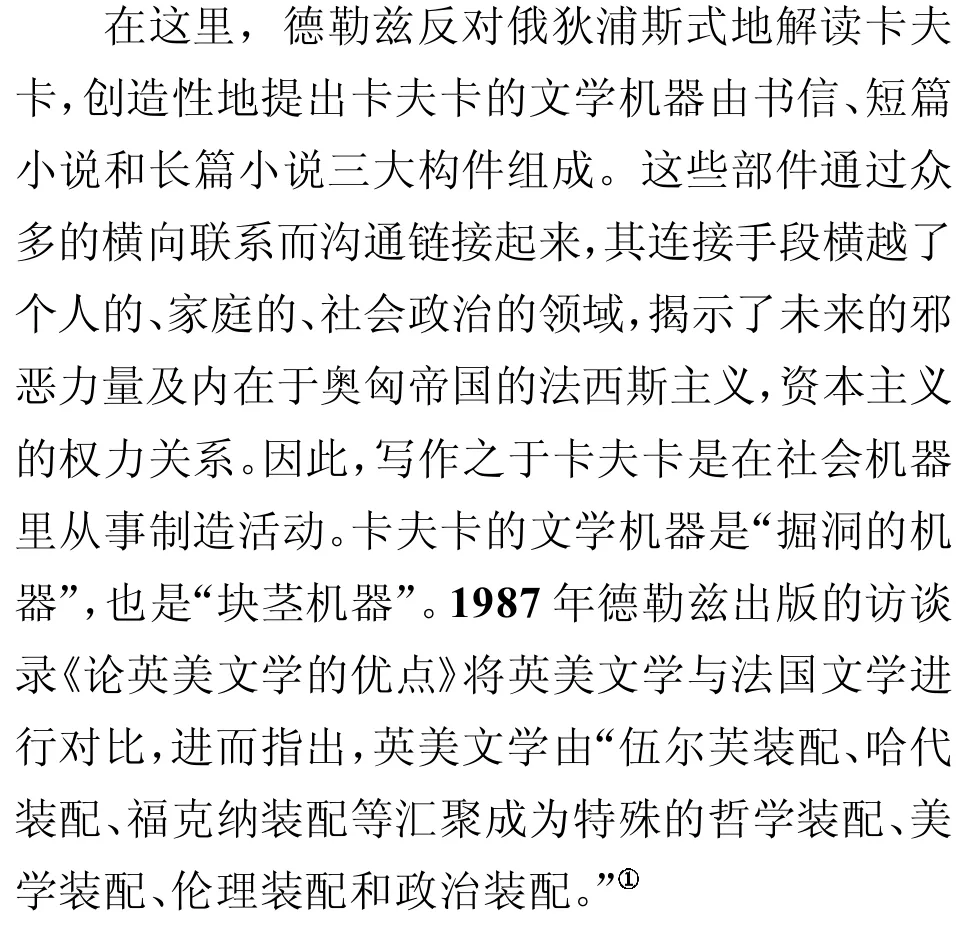

德勒兹的文学机器装配观念,消解了符号/意义,能指/所指,内容/形式,内在/外在,欲望/客体之间的二元对立范式,颠覆等级制,主张差异对话精神,反对孤立自足的封闭性,强调变动不居的开放性及块茎图式的间性关联。块茎图式强调事物是由诸多不同要素构成的组合关系生成的,这一观念突破了传统文学阐释的思维定式,具有非同凡响的穿透力,引发对文学经典的新感悟与新理解。下面我们运用这一概念来探讨狄更斯的文学机器装配。
二、狄更斯的文学机器装配
在德勒兹的文学机器装配视域中,狄更斯是文学机器装配的大师。他的每一部小说都体现了块茎图式的文学机器装配,下面以三部小说《荒凉山庄》《远大前程》和《我们共同的朋友》为例展开分析。《荒凉山庄》中的人物散居于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被囚禁于各自的独特性中,但他们相互联系的方式却多种多样。在小说的开头,到处都是雾,河的上游、河的下游,伦敦的每一个地方都是雾茫茫的,最后在大法官庭把画面放大,这里的雾最为浓稠。《荒凉山庄》中的雾成了人物联系的纽带,正如贾迪斯控贾迪斯案将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联系起来一样。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不同程度地牵涉到埃斯塔·萨姆逊的故事或者牵涉到大法官庭的庄迪斯诉讼案。精明的律师塔尔金霍恩和贾格斯在狄更斯的小说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二者是连接庄园世界与城市世界之间的中介。他们的力量来自其手中掌握的信息,并利用这些信息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这些信息包括埃斯塔·萨姆逊的私生女身份,这关涉到她母亲德洛克夫人的命运,而德洛克夫人有着隐秘的历史,但这并不妨碍她嫁入英国最有权势的家庭。埃斯塔的故事还涉及到她的父亲——命运不济的霍顿队长。霍顿队长落魄之后,进入伦敦的鸦片馆,处于社会的边缘,生活潦倒,仅靠誊写法律文件勉强度日。这个四分五裂的家庭包括社会最上层的人(德洛克夫人)和最底层的人(霍顿队长),夹在中间的是埃斯塔。埃斯塔一边跟着约翰·庄迪斯旅行,一边带着深深的同情观察穷人和流浪汉的生活。律师塔尔金霍恩在这两个有着天壤之别的世界中起着纽带作用。他怀疑德洛克夫人的过去,开展了深入的调查,这一调查将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如斯纳斯比、肯吉、戈匹、斯墨尔维德、朗斯威尔、乔等串联起来。
那么,骄傲的德洛克夫人和扫地的亡命之徒乔之间存在什么联系?把德洛克夫人和乔从鸿沟的两岸带到一起的是公众对乔犯下的罪过和德洛克夫人对女儿犯下的罪过,二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两种罪过是一种父母不负责任的模式:否认亲生孩子的女人和由社会充当养父的流浪儿。他们在同一个教堂墓地并排摆在一起,供同一种蛆虫吞食,这时两种模式又相互联系起来。这种蛛网式的内在联系,在19 世纪的小说中发展为一种强烈的意象。在《荒凉山庄》中,伦敦警察局的侦探把质疑他的女主人象征着英国中心的所在——伦敦贫民窟里一座漆黑的墓地,天花传染病和一张封死了的、由法律和色情结成的大网向四周延展开去,就像泛着泡沫的臭水坑,把整个英国社会陷入其中。斯蒂芬·马库斯指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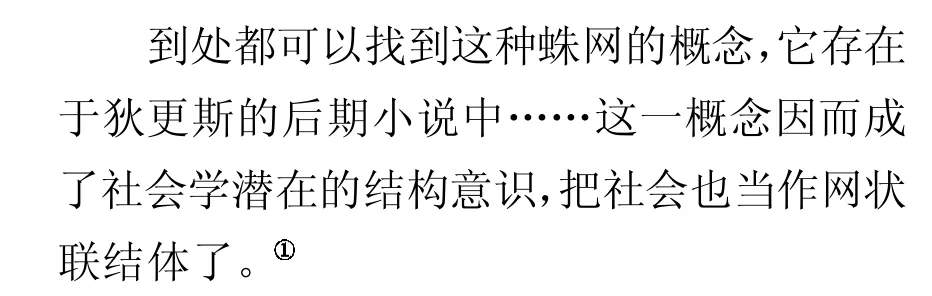

在《远大前程》中,让囚犯马格韦契跨越“鸿沟”来到男孩皮普身边的同样是充满负罪感的契约。这种契约如同脚镣一样具有约束力,脚镣是反复出现的象征,这依然是父母不负责任的模式。虽然条款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但是,受虐待的孩子恰恰是充当养父的囚犯马格韦契,而皮普这个被宠坏的孩子反而得承担社会对马格韦契犯下的罪过。马格韦契从海外回来后,他再次出现的那个夜晚预示他接近神秘的警告,无一不是道德的投影,就像窗外的风雨和阴暗的楼梯上恶毒的奥利克一样真实。在这部小说中,把双方联系到一起的事物是合乎情理的。私人或公众行为所经历的总体变化,对外在物质原子的影响与对心灵的影响一样具体,结果连自然物质也来合作,参与报复行动。这一主题联系将《荒凉山庄》和《远大前程》装配成一台“文学机器”。
从德勒兹的机器诗学视域来看,《我们共同的朋友》可以说是文学机器装配的范本。这部小说有几个贯穿始终的主题,如友谊的主题、溺水的主题、浓雾的主题、酷似的主题等,而这些主题成了人物之间相互联系的纽带。
先看友谊的主题。这从小说的标题就可以管窥一二。“我们共同的朋友”本来是一种错误的习惯用法,但是因为习以为常,以至惯用法专家现在也允许这样使用。“Mutual”的意思是“共享的”“共同拥有的”,如“共同的情感”表示两人之间的相互爱慕。只有在违背社会常规的权限内延伸其字面意义,“Mutual”才可以用来表示“我们共同的朋友”,如某人是我的朋友,他或她也是你的朋友。虽然我们相互之间根本不了解,也没有共同的友谊,但我们共享对同一个人的友谊,对于将我们联系起来的第三个人的友谊是“共同的”。以第三个人为纽带,我们相互关联起来,也有着共同的感情。在小说中,“我们共同的朋友”一词是由目不识丁的鲍芬之口说出来的,鲍芬用这一短语来给约翰·罗克史密斯(又名约翰·哈蒙)命名。罗克史密斯是鲍芬先生的秘书,也是维尔弗家的房客,因此,鲍芬先生对维尔弗太太说:“我可以称他为共同的朋友。”用这一短语作为整部小说的标题暗示了范围更广泛的联系。这一联系甚至超越了约翰·哈蒙的中心地位,延伸到了小说的情节构思之中。在小说中,约翰·哈蒙是所有人物的“共同的朋友”。
再看酷似的人。这部小说涉及很多地理空间,一方与另一方的关联不是直接的,作者往往通过二者都了解的第三方来构成联系纽带。“共同的友谊”这一主题与酷似的人这一主题紧密相关。这部小说有一系列酷似的人,即一个人与另一个人酷似,但还有一个人与另一个人酷似。乔治·拉德福特与约翰·哈蒙外貌极端相似,约翰·哈蒙后来化名为朱丽叶斯·汉福德和约翰·罗克史密斯,两次成为与自己酷似的人。赖皮·赖德胡德无论在外表还是职业上都是与赫克萨姆老头酷似的人,但后来布莱特赖·海德斯东在谋杀尤金·瑞伯恩时穿上赖德胡德的衣服,成为与赖皮·赖德胡德酷似的人,其目的是将谋杀尤金·瑞伯恩的责任归咎于赖德胡德。海德斯东与赖皮·赖德胡德在泰晤士河中箍成一个铁箍,二者都被淹死。尤金·瑞伯恩与海德斯东在竞争丽齐·赫克萨姆的爱情时成了酷似的人。莫蒂默·莱特伍德仿效他的偶像尤金·瑞伯恩,他们的言行举止一模一样,也成了酷似的人。当鲍芬假装成为吝啬鬼时,成了与他自己对立的酷似的人。
第三,溺水的主题。在这部小说中,溺水是贯穿始终的主题。约翰·哈蒙被谋财者扔进泰晤士河,爬到岸上后,先化名为朱丽叶斯·汉福德,后来又改名为约翰·罗克史密斯。约翰·哈蒙重复了小说中前后发生的多次溺水:与他酷似的人乔治·拉德福特跟约翰·哈蒙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被人扔进泰晤士河。赫克萨姆老头的溺水,赖皮·赖德胡德两次溺水(一次复活,一次被淹死),尤金·瑞伯恩与布莱特赖·海德斯东的溺水。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小说中还有隐喻意义上的溺水,如赛.拉斯·魏格被斯洛皮扔进一辆垃圾运货马车,“发出一声扑通巨响”。迷人的弗莱吉贝遭到拉姆尔的一顿毒打之后,珍妮小姐在每张膏药上撒满胡椒粉,并将膏药贴在弗莱吉贝的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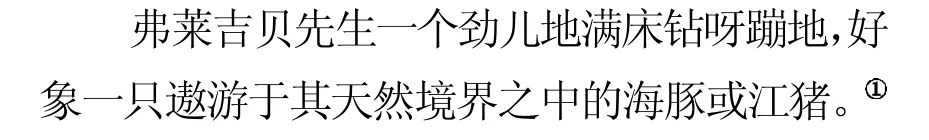
第四,浓雾的主题。在《我们共同的朋友》中,雾是一个茫茫无边的大海,它将万物和所有的人都淹没于其中。叙述者从伦敦之外的高地这一视角来告诉读者。浓雾将每一个人与其邻居隔离开来,同时又将他们联系起来。因为所有的人都为浓雾所包围,并因一场规模庞大的感冒症而咳嗽,甚至被窒息。虽然伦敦人是相互隔绝的,但浓雾和感冒症却是共同的朋友,将人物隔离开来的东西恰恰又将他们联系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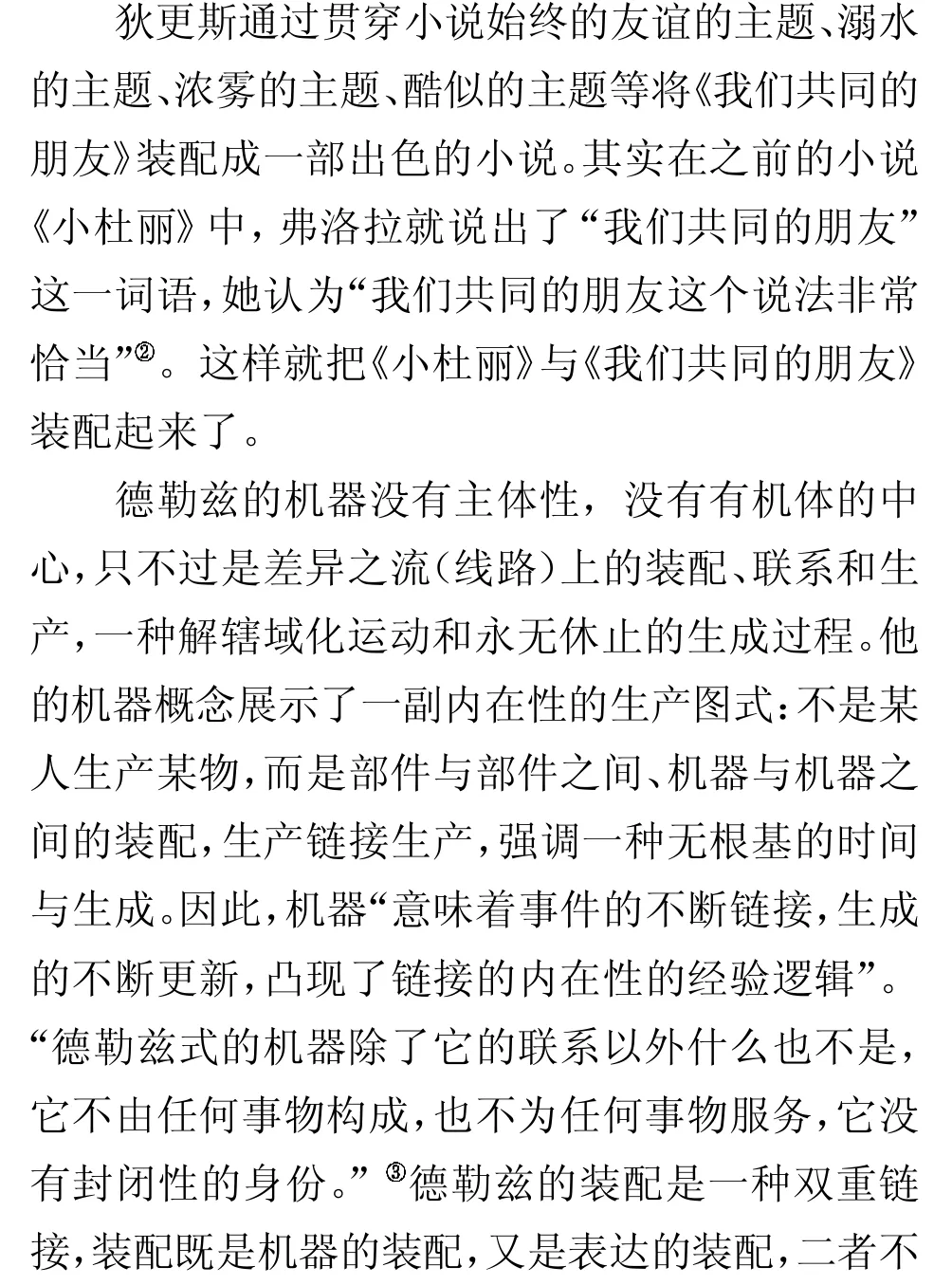
三、狄更斯文学机器装配的意义及其文学影响
19 世纪的伦敦,是一个色彩斑斓的碎片化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思想本身与外部处于一种蛛网般的关联之中。狄更斯以无限多样的方式把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生活现象装配成“文学伦敦”,组成一台生机盎然的“文学机器”。狄更斯的文学机器暗合了装配和块茎原则,体现了一种动态的块茎图式的间性关联。著名的狄更斯研究专家史蒂芬·马库斯指出: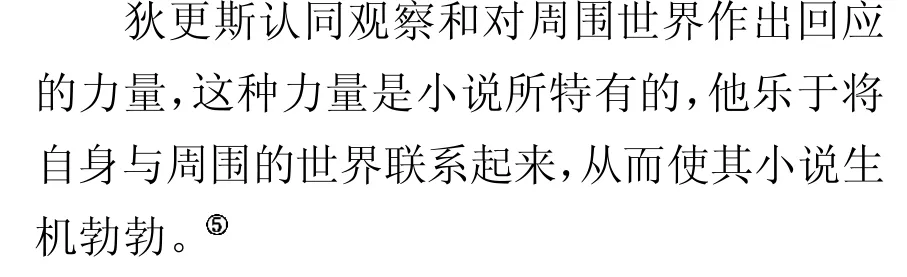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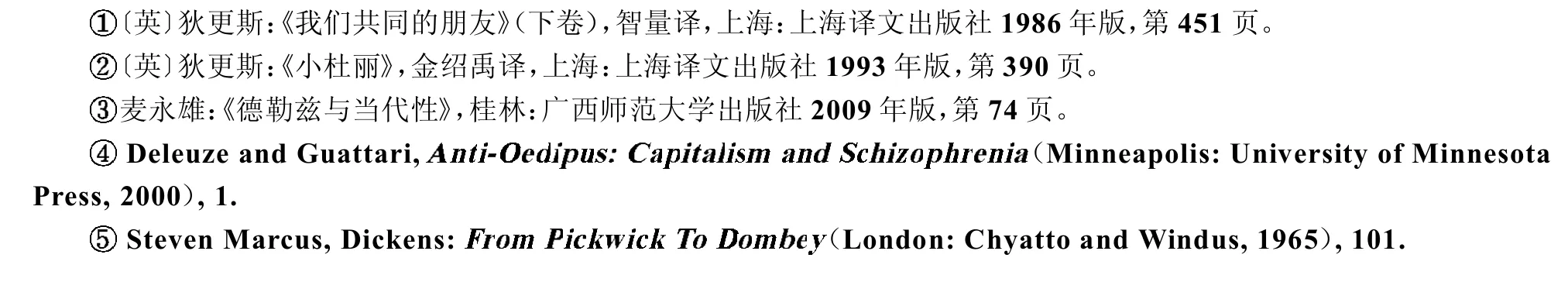
在狄更斯的艺术世界,不仅小说内部的各元素之间,而且每一件艺术作品皆是相互链接的,或者具有相互链接的潜质。同时,他还以机器装配的方式将自己的作品与其他人的作品或者自然系统相互沟通,从而构成一个不断拓展的开放式的光滑空间。从更宽泛的精神文化现象来看,“狄更斯装配”强调块茎图式的间性关联和变动不居的开放性,不断创造出新的现实,构建新的机器和装配,彰显了文学永恒创新的本质。
狄更斯的文学机器装配影响了后来的超文本作家及其作品。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 1882—1941)的《芬尼根的守灵夜》给读者以超文本链接的印象。这部作品提及了上万种书籍,仿佛是一张硕大无朋的网络,其中不乏大量的自指涉、典故、二次文献、双关语词汇、新词和外来词等等,并且它们之间常常相互指涉,具体呈现了超文本的结构形态,包含一大堆暗示和重现的主题,堪称非线性和联想式文体的极品。俄裔美国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1899—1977)的《微暗的火》由前言、诗歌“微暗的火”以及对这首诗的大量评论与索引组成,读者可以在多种选择中整合和解释这四个部分,从而产生与“真正的故事”不同的结果。《微暗的火》与“块茎”十分接近,它从不同的方面预示了数字化的大门已向文学敞开,被称为“原型超文本”(protohypertex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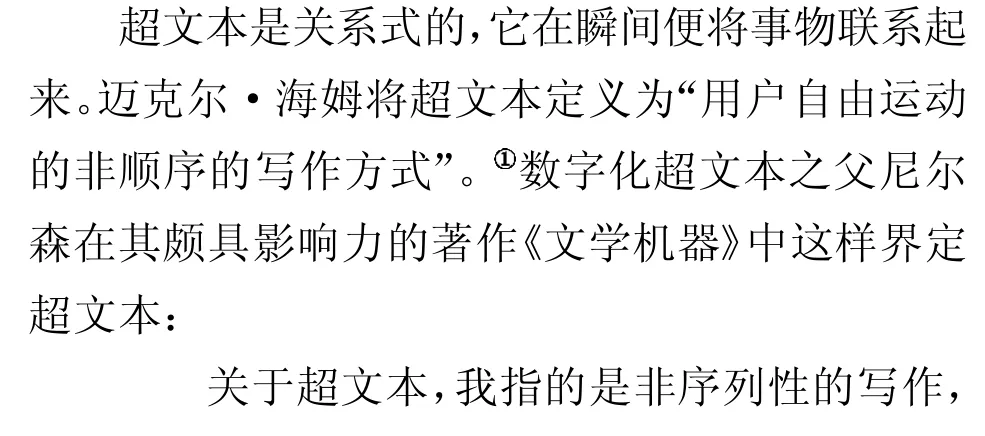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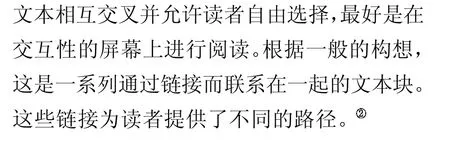
在尼尔森那里,超文本与文学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文学被理解为一个庞大的网状结构。可见,超文本小说是一种超级链接,超级链接把这些片断整合为一体,创造一种多线程的网络。超文本系统是一部文学机器,是文学机器装配的进一步发展。
纳博科夫谙熟狄更斯的作品,称道狄更斯“善于运用强烈诉诸官能感觉的比喻,有唤起逼真感觉的艺术功力”。他认为,大作家总归是魔法师,只有从这点出发,才能领悟天才之作的魅力。狄更斯写得最好的时候,作为魔法师、艺术家的一面也体现得最为充分。由此,他称“狄更斯是一个出色的魔法师”。他的“原型超文本”小说受到了狄更斯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被誉为高度原创性的乔伊斯并不是脱离文学传统在真空中的独创,其独创性在于,谙熟狄更斯作品的乔伊斯常常从狄更斯的作品中吸收营养,并仿效它们来开展文学实验,进而拓展出一片新的文学天空。评论家米歇尔·霍灵顿(Michael Hollington)在其主编的四卷本论文集《狄更斯批评评价》的序言中指出:
只有阅读乔伊斯、普鲁斯特、福克纳、卡夫卡之后,我们才能理解狄更斯。⑤Michael Hollington,(Robertsbridge:Helm Information Ltd,1995),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