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甘肃 兰州73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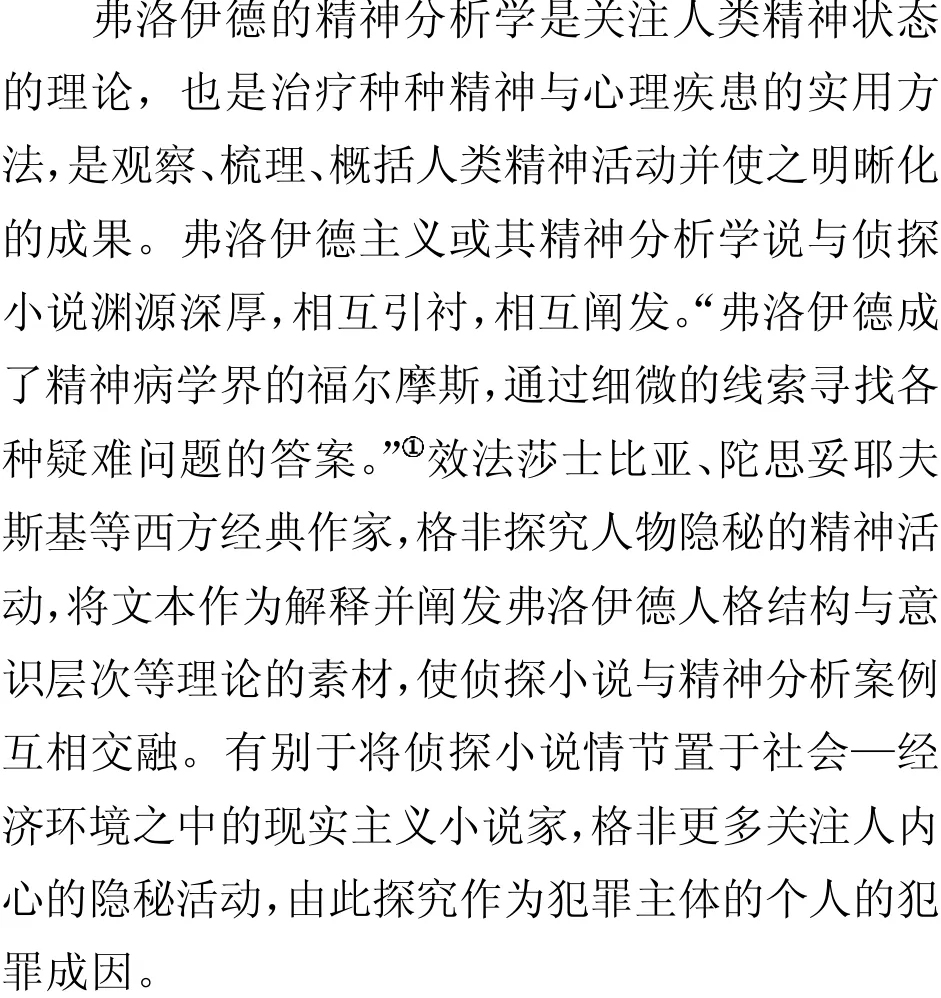
窥探人心的悬疑式侦探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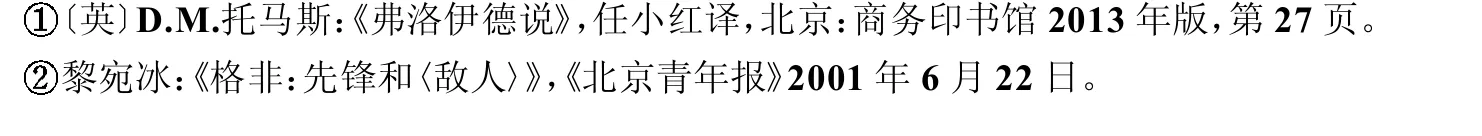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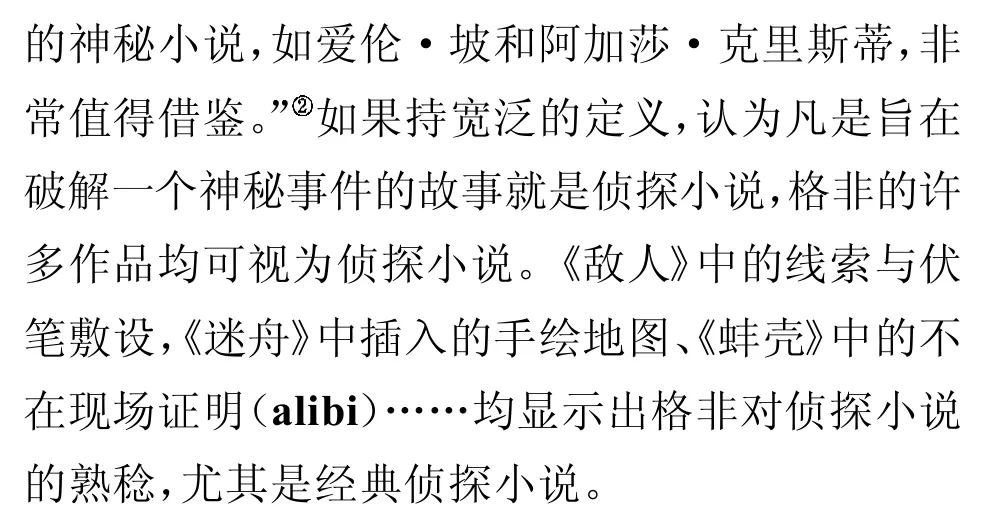
不仅具有侦探小说的形式,令人毛骨悚然的《敌人》的情节确是一部长篇侦探小说的情节。作者不以揭露真相为目的,但是这并不能消解它的侦探小说性质,只是表明它是另类的侦探小说。神秘的氛围,一连串血腥的神秘犯罪事件,罪犯与侦探的对垒……这些均是侦探小说的情节要素。最耐人寻味的是,读者不知不觉地“入局”,他接受侦探的身份,并在无意间与赵家家长赵少忠一起调查扑朔迷离的连环杀人案,将作品变为“可写性文本”。唯一缺失的只是程式化侦探小说结局,即除赵少忠之外的罪犯始终未被揭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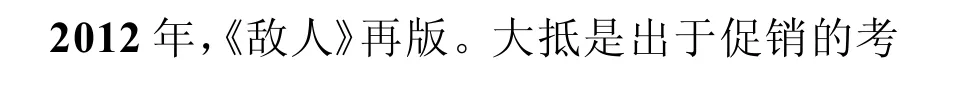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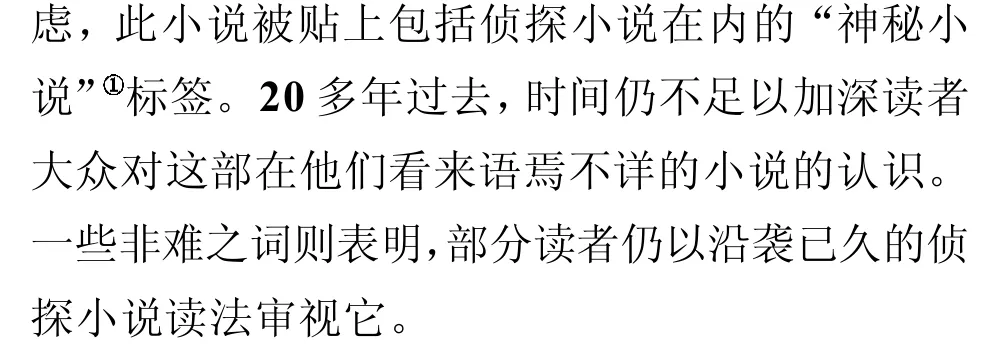
遗憾的是,这本小说虽然名曰《敌人》,从开始到结尾,除了景物描写和心理描写,没有见到“敌人”的一个衣角一个背影。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却不在小说深处,类似于吃了半碗米饭,混了半个肚饱,怎一个“可恼”了得?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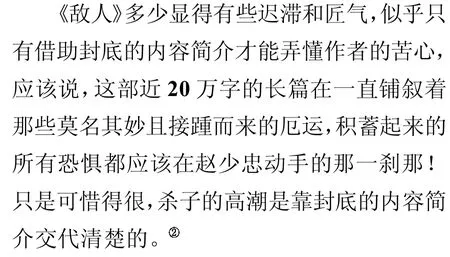
几桩谋杀案源于长期积累,高度激化的人际矛盾与冲突,赵少忠等以自己的诡秘方式对谋杀案的侦破使《敌人》涉及秘密的暴露,即知识以及知识的获取过程,成为一部侦探小说。因此我们也可以将迪潘、福尔摩斯等侦探视为意欲达到特定认知目标的人物,对真相的探索也即对知识的追求,这不仅是使命,似乎也是孤寂生活中的乐趣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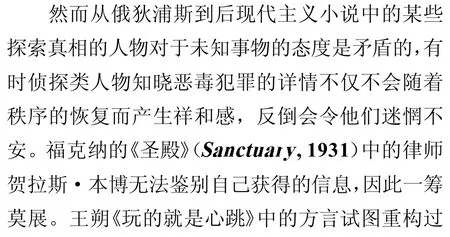

《敌人》始终无解的悬念似乎暗示侦探在调查过程中试图重构赵家不确定、永远无法证实的过去,意味着自身面临隐性的危险、灾难甚至毁灭。《敌人》又是反常规的侦探小说,作者无意遵循经典侦探小说的游戏规则,似乎希冀读者在侦探徒劳无功的探索中得到启示,在探究外部世界的秘密时审视自己的内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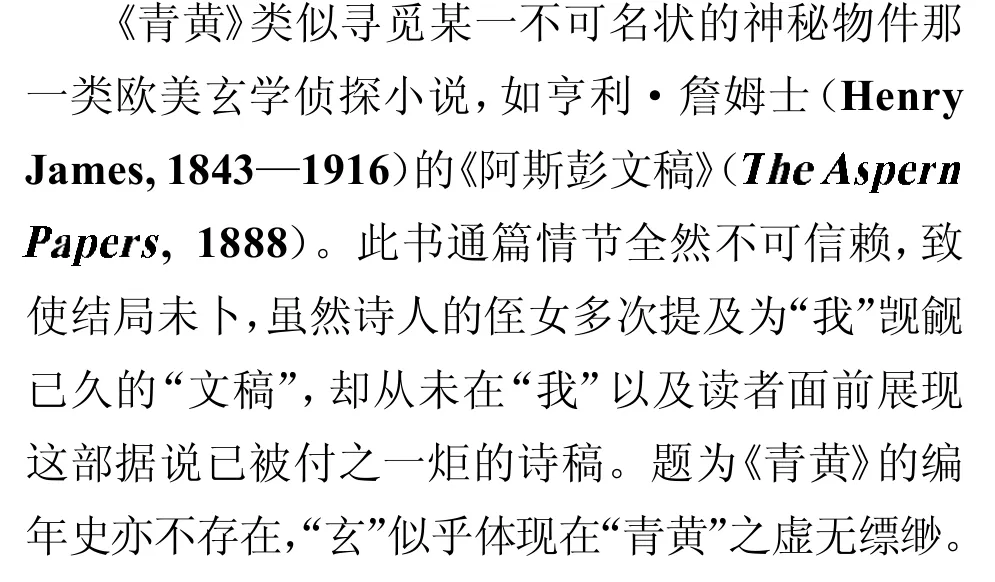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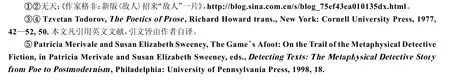
作者借“我”对谭教授的最新专著《中国娼妓史》第426 页上一个颇有争议的名词“青黄”的调查,表达对“此在”可信性的思索,是现实与虚构世界的对立。谭教授认为“青黄”是一部记载九姓渔户妓女生活的编年史,扮演侦探角色的“我”的初衷就是找到这部散落在民间的史籍,为此甚至不厌其烦地探问死去的外乡人的棺材中是否有一本书。假想中的能指“书”在调查过程中滑向青春年少的或人老珠黄的妓女、良种狗、草本植物……但是观念中最初的所指始终缺席,它可以是某种具体或抽象事物的名称,也可以是现世不存在的东西。对“青黄”的意蕴的寻觅在虚与实、动与静、生与死的交替中转换,寓示人生的无奈、世事的无常和不可捉摸的虚幻。侦探的失败象征着理性在瞬息万变的人世间的无助,情节的空缺则是对书写成文的种种高深理论建构的嘲讽,质疑。成功的认知使人获得自信,失败的认知则使人沮丧,继而领悟到存在之荒诞不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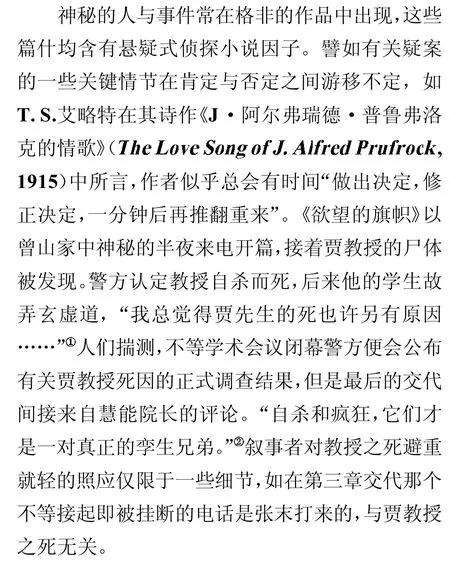
除《敌人》之外,格非的其他一些小说亦或多或少采用悬疑式侦探小说的结构、题材,其主要人物是形形色色案件中的嫌犯和业余侦探。《迷舟》描写大战前孙传芳部队的一个旅长萧的“失踪”,这位军官身陷阴谋与爱情、谍战与性爱旋涡之中而不自知,像迷失在浩渺湖海中的一叶孤舟,随风飘荡,听凭命运摆布。在主人公怀旧的思绪中展开的神秘事件不难破解,但仍是一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曲折心理故事。虽有叙事空白有待读者填补,但与《褐色鸟群》一类的作品相比,《迷舟》难度较小。悬念迭起,萧的生死系于一线。这个游戏的关键是榆关,一个由萧的哥哥统领的北伐军部队攻陷的小镇。萧的卫士是受命监视萧的侦探兼杀手,他得到的指令是,如果萧去榆关便有通敌嫌疑,就必须杀死他。但是萧赴榆关的目的不是向北伐军传递情报,而是去看望被丈夫割去输卵管的情人杏。阴差阳错,或者命运,使决心回前线赴死的萧得到情敌三顺的理解与宽宥,最后却死在自己卫士手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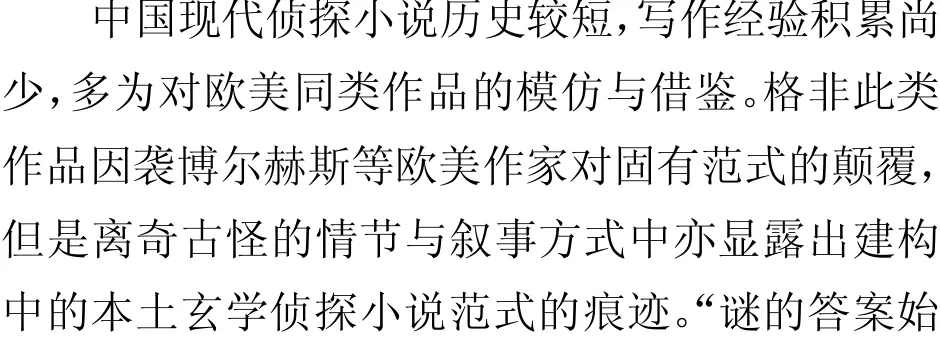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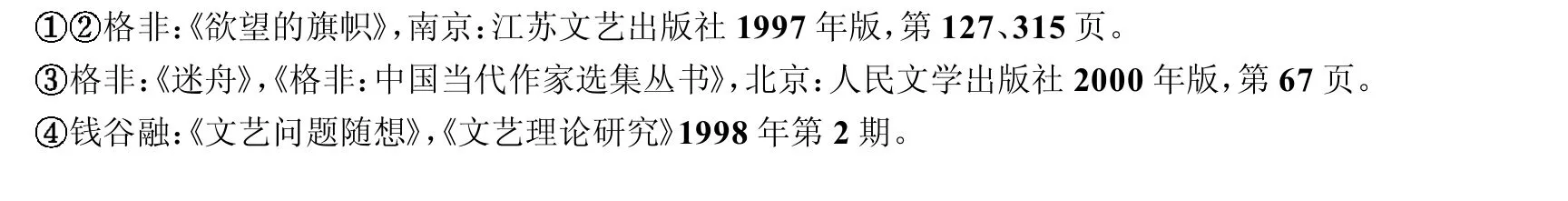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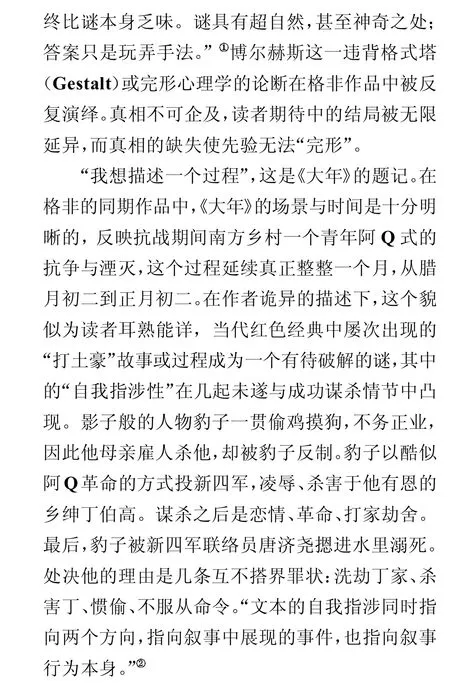
20 世纪80 年代,西方文学思潮纷纷涌进中国,格非等作家注意汲取西方文学的表现方法。他们的作品表现的内容与技巧令人耳目一新,因此理所当然地被贴上“先锋”的标签。格非在情节建构上中断叙事的连续性,在人物塑造方面实验由外向内的转向,以静态的白描式手法揭示人物心理活动,采取多种视角反映生活的悖论,通常是以隐形的二元对立模式出现,诸如掩盖在欲望之下的生存本能与死亡本能的抗衡(《敌人》《迷舟》《蚌壳》)、混沌世事中存在与虚无的纠葛(《欲望的旗帜》《大年》《褐色鸟群》)……他在犯罪文学的基本建构中以多种视角探究欲望、友谊、性爱、生死……以激动人心的情节诱惑读者,引导他们由追捧情节转而思考主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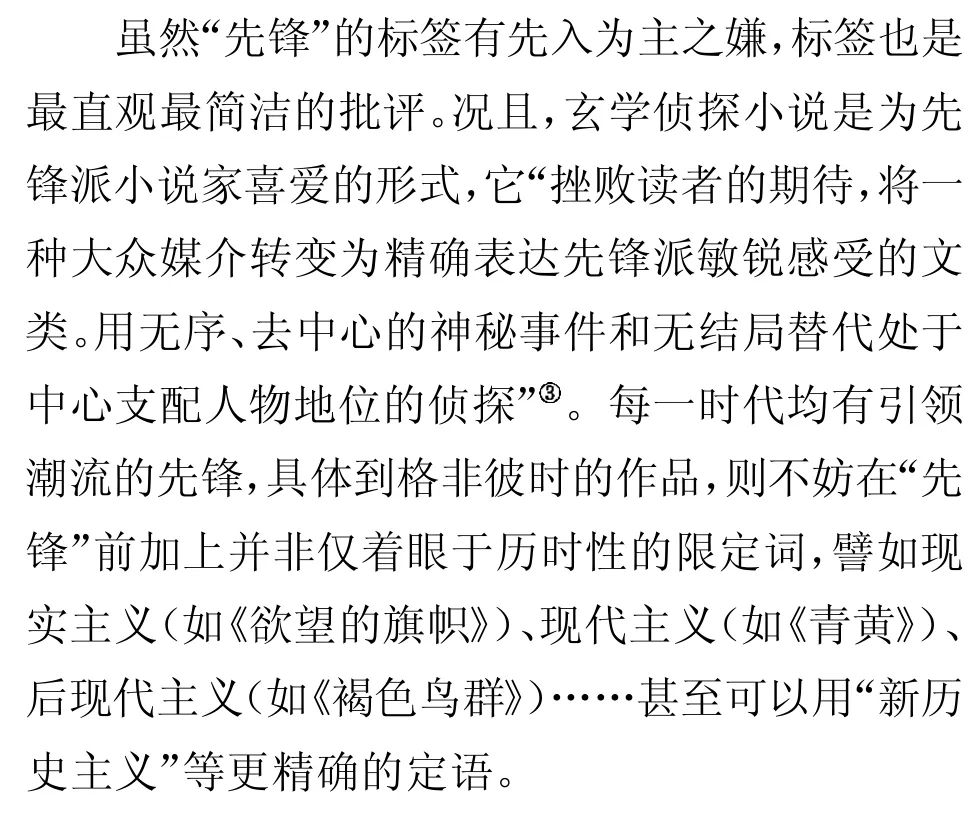
在技巧上,格非在戏仿侦探小说程式的前提下娴熟运用适切不同文学思潮的欧美文本策略与技巧,诸如反讽(irony)、影射(allusion)、拼贴(collage)、破碎(fragmentation)、混杂(pastiche)。“故事中的故事”皆是常用小说技法,在不同风格的作品中显露独到之处。在《蚌壳》中,“故事中的故事”是“我”父亲与长辫子女人的性事。在《大年》中,“故事中的故事”于玫与唐济尧的暧昧情事降级为隐晦的副情节,在豹子的故事中若隐若现。在《褐色鸟群》中,“故事中的故事”是“自我指涉式”的嵌入。“我”的多重亲身经历与“我”的故事相互衬托、否定,带领被挫败的读者在叙事的迷宫中艰难穿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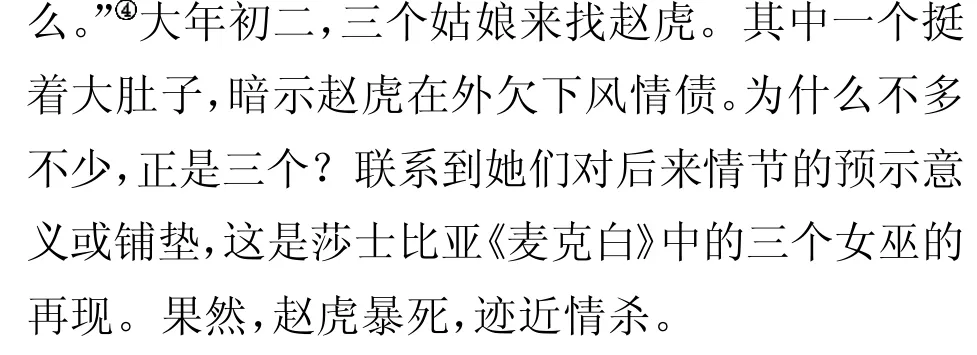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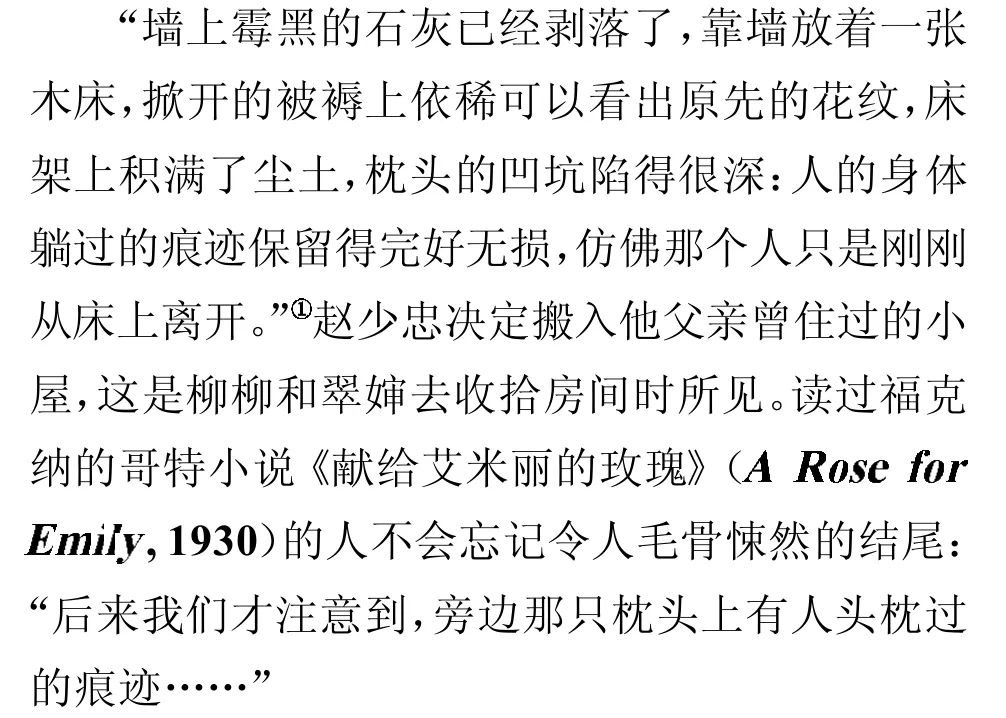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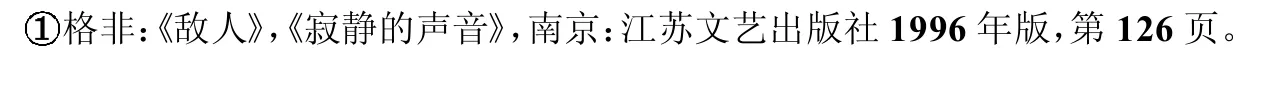
作品中种种没有做出交代或不符合逻辑的情节似乎暗示格非无意象经典侦探小说家那样探究现实中的秘密,他更留意窥探人心,企图发掘其中难以言表的阴暗。臆想中的“现实”更宜于用玄学侦探小说的形式,以类似精神分析的方法表达,这是格非此类作品不易解读的原因之一。
犯罪起因与弗洛伊德主义的“欲望”
以往主流话语强调精神可以变物质,20 世纪80 年代格非在文坛出道之时适值知识界“思想解放”之际,这种类似唯意志论的观念受到质疑。“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老子认为有身体便对外部世界有敏锐的感觉,便不免为欲望所羁绊。欲望令人生有所追求,也是痛苦之源。经历多年物质匮乏的磨砺之后,人们受到压抑的欲望再度勃发。他们渴望得到以往被剥夺的一切,在短期内满足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所有各级,从日常吃穿用度、性爱,再到自我实现。除此之外,中国彼时的国情使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在长期奉行集体主义,被迫压抑自己情感的国人心中激烈迸发,在与人交往中刻意追求无拘无束的感觉,即自由。较之物欲,情欲更不容易满足。格非以侦探小说范式与精神分析原理为经纬,定位难分善恶的人物的欲望。这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平凡人物饱受欲望煎熬,大多欲望是基于补偿心理的对“酒色财气”的觊觎,如《敌人》中的翠婶“体内炽烈的情火”,哑巴对梅梅的父爱转化为对她的花布衫的恋物癖,象征其主人移情别恋的手镯均在暗示这个大家庭匪夷所思的秘事。源于社会与自身的压抑使人心躁动,革命则使原来的社会等级制度瓦解,于是与生俱来的补偿心理极度膨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平民版本便是对在某一方面比自己优越的他人的嫉妒与敌意,这种心理引发激烈的,甚至你死我活的冲突,这正是格非某些作品中的隐性主题。
然而我们还必须将目光投注到人类相同或相通的补偿心理。此处,弗洛伊德人格理论关于文明与个人之间根本冲突的解释十分切题。文明是人类打造的一把双刃剑,它保护人们免遭不幸,同时也是人们最大不幸之源泉。像其他生物一样,人竭尽所能追求欲望的满足,但是社会逼迫他不得不压抑个性,屈从于现实的群体生活。弗洛伊德认为人的精神活动的能量来源于本能(力比多,原欲),这种能量积聚到一定程度就会使肌体紧张,寻求释放能量的途径。本能是人一切心理活动的内在动力,其中生的本能与死亡(攻击)本能是最基本的本能。生的本能包括保持个体生存与种族繁衍的性本能,在泛性论者弗洛伊德的观念中,性本能冲动自然专指性欲,但是也泛指人追求快乐的所有欲望,比饮食男女更为宽泛,并非仅仅是交媾与交媾后的杀戮。埋葬赵龙,送走哑巴后,在《敌人》结尾呈现的正是这一幕:
赵少忠将那副鸡血色的手镯套在她的手腕上,皮肤上残留的那种凉飕飕的感觉立刻爬遍了她的全身。
翠婶躺在卧房阴湿的地上,窗洞中洒进来的一缕阳光刺得她睁不开眼,她的耳边灌满了他沉重的喘息声,许多天来一直缠绕着她的晦暗的阴云伴随着屋外远去的风声消失得无影无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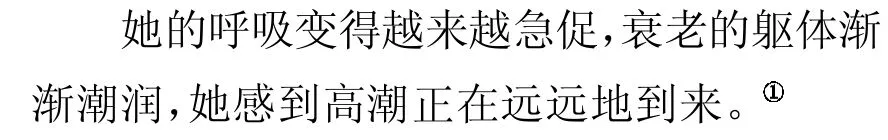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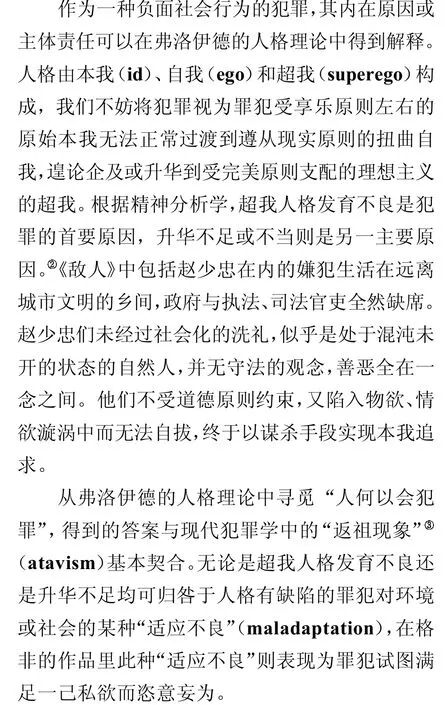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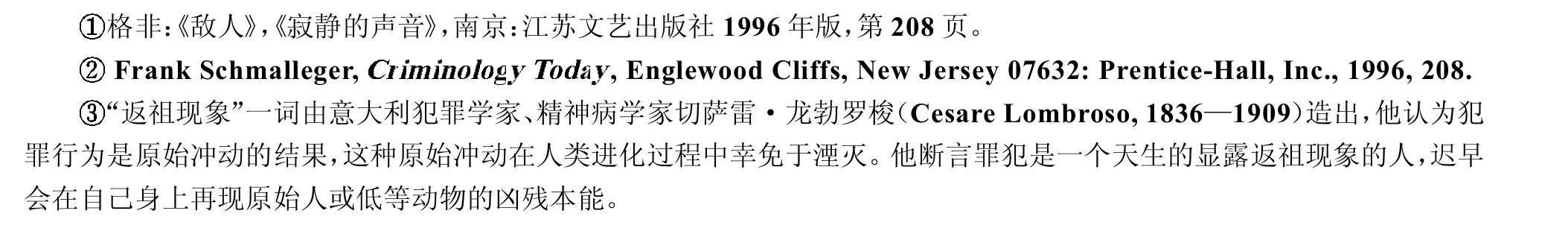
中篇小说《蚌壳》是描写犯罪的杰作,也是一个挑战读者推理能力的可写性文本。马那在童年时代目睹父亲与女人私通,身心受到刺激,成年后性能力不济,与妻子性生活不和谐,最终被与医生私通的妻子用毒蛇谋杀。充斥整部作品的是几个人物放纵洪水般奔泻的情欲以及为满足情欲而实施的种种阴谋诡计,故事在马那的父亲与长辫子女人、“我”(即马那)与小羊姑娘、马那的妻子与医生这几对男女的性事中展开,淋漓尽致地表现受情欲折磨、驱使的人物的众生态。《蚌壳》由“我”(即马那)与基本采用外视角的叙述者交替叙事,外视角易于设置悬念,像中国写意画似的“留白”,因此常为侦探小说家采用。情节是任意铺陈的,不起眼的故事或本事敷设其中,欲参与破案的读者必须首先厘清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
经过读者重置后的叙事或许是:
1(原2):童年时代,父亲带他去河边摸河蚌,他无意间目睹父亲与那个高大健壮的女人像两条水蛇一般缠绕在一起,震惊不已。
2(原1):“我”去蝙蝠大街7 号一家私人诊所看病。从诊所出来,“我”发现自己钥匙丢在那里。“我”回去取钥匙,再度走出诊所时遇到一个来自G省,自称“小羊”的乡下女人,与她首次做爱。
3(原6):“我”再度去蝙蝠大街7 号的私人诊所看病。告诉医生“我”梦见妻子要杀掉“我”……医生建议“我”戴墨镜。
4(原3):一个女人在诊所做妇科检查时与她的医生勾搭成奸,事后医生建议她吃毒蛇胆治病。
5(原5):马那与许多天之前在街上相遇的那个来自G 省的女人已成为情人,预备这天晚上去与她幽会。傍晚六点零五分,马那对妻子编谎说要出门看望朋友。出门前,马那先去卫生间洗澡,躺在浴盆里时背上被毒蛇咬了一口。
6(原4):一个男人在夜里猝死,虽然背部有伤口出血,警方有悖常理地判断他死于自杀,原因是他从来自G 省的那个女人那儿染上梅毒,遂产生轻生之念。
这六节亦是可以独立成篇的小故事,依照时间顺序与情节发展重置后又以一个需要读者参与的完整悬疑故事呈现。格非的情节合情合理,节奏舒缓有致,前后呼应,情节发展毫无突兀感。他善于细致刻画人物心理,使矛盾冲突显得可信。
马那在对性事懵懂无知的童年时代看到父亲与女人冒雨在芦苇丛中私通,心灵受到极大刺激。待他回到家里——
母亲朝他笑了笑。她俯下身咬断被角上的那根长长的白线。阳光从土墙上窗骨的缝隙中照到她身边的地上。

作品无疑受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启发,甚至试图解释弗洛伊德的童年创伤理论基本思想。通过对梦的解析,弗洛伊德认识到人的不幸童年经历必定使他受到精神创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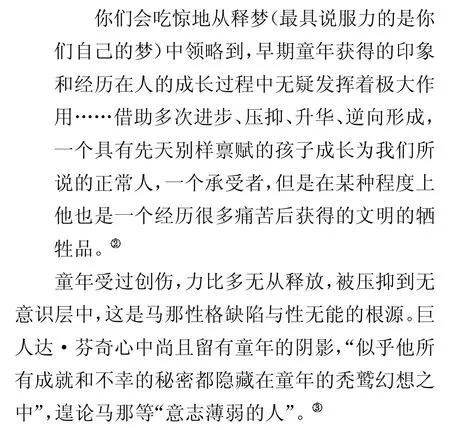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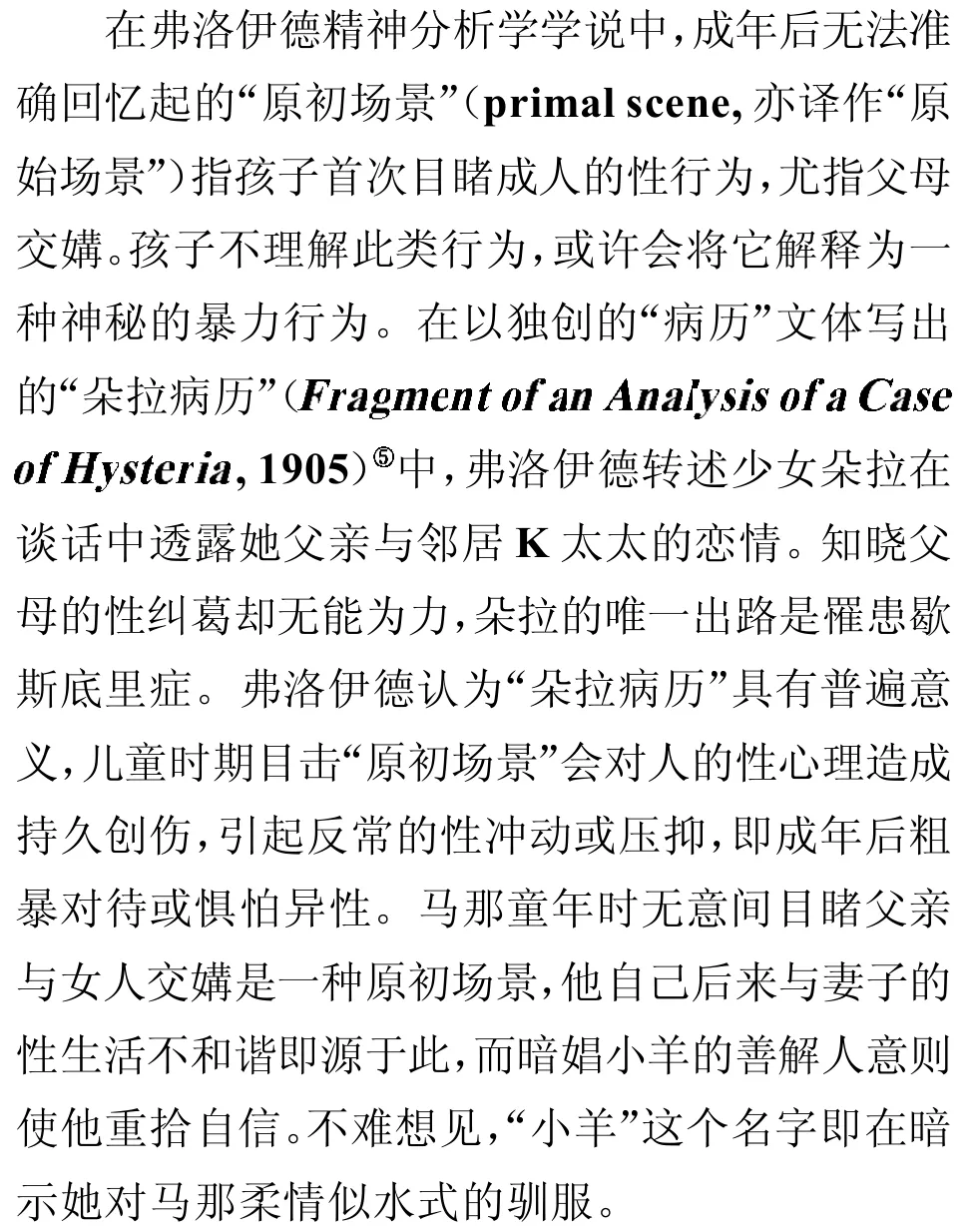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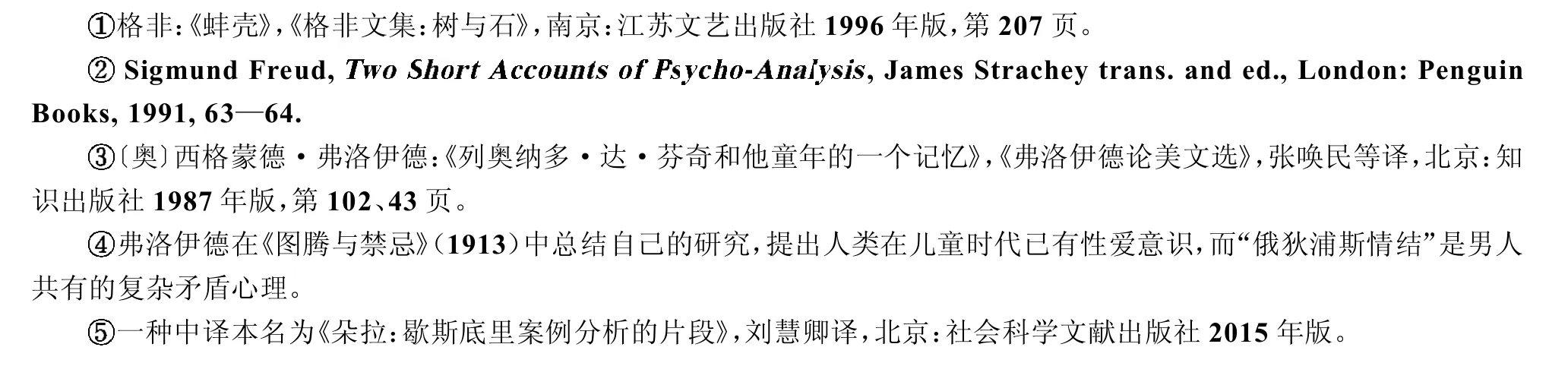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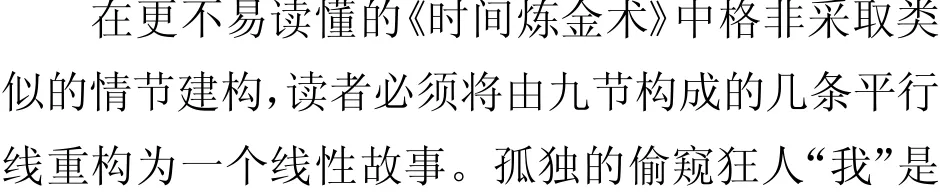
《蚌壳》中的马那、《时间炼金术》中的“我”等主人公均在童年有过不平凡的经历,因此这类作品亦是对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的叛逆。成长小说描写主人公出身卑微,几经磨难,阅尽人世沧桑后终于苦尽甘来,同时也领略到生活的真谛。在格非“一反常规的成长小说”(anti-Bildungsroman)中主人公却不如《人性的枷锁》中的菲利普幸运,童年时代有意的偷窥或无意的窥见使马那们为卑下却又难以满足的欲望萦绕,深陷于童年创伤中不能自拔,受辱蒙羞、失败、早夭成为他们的宿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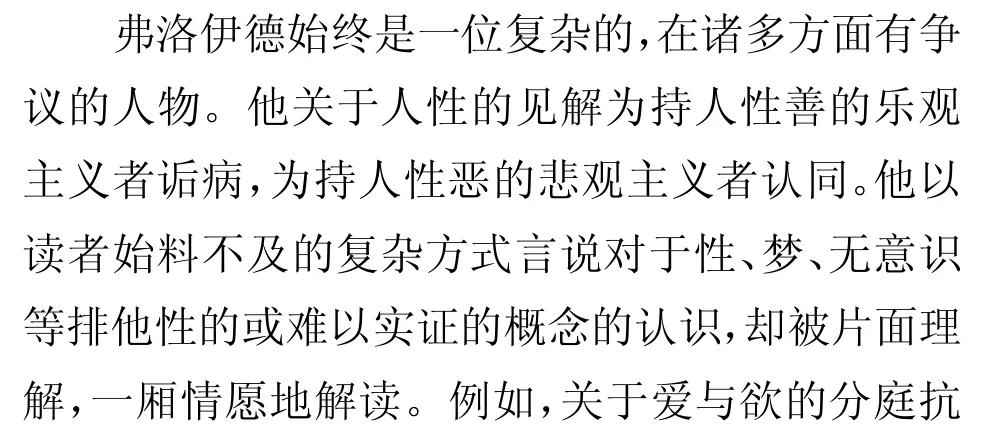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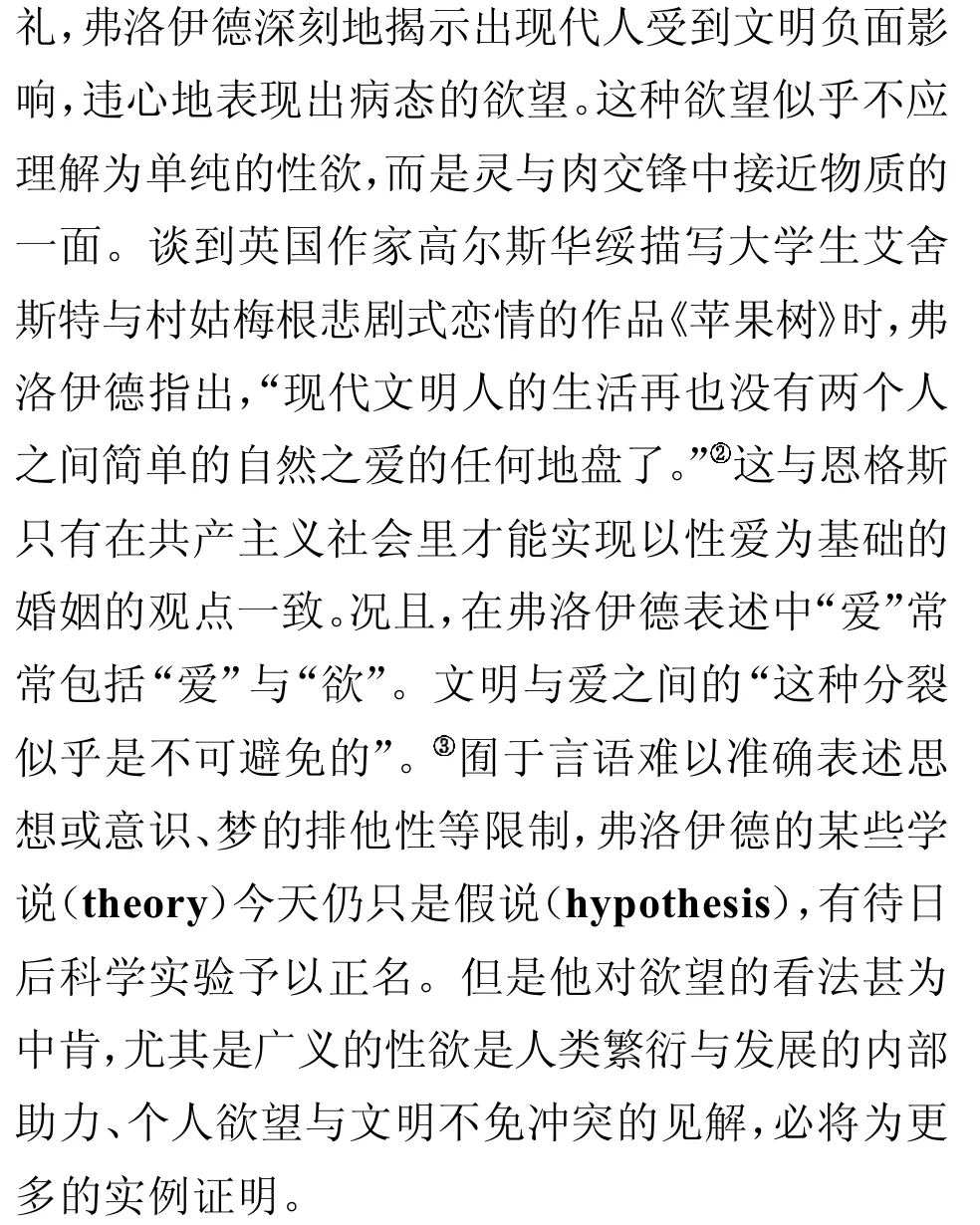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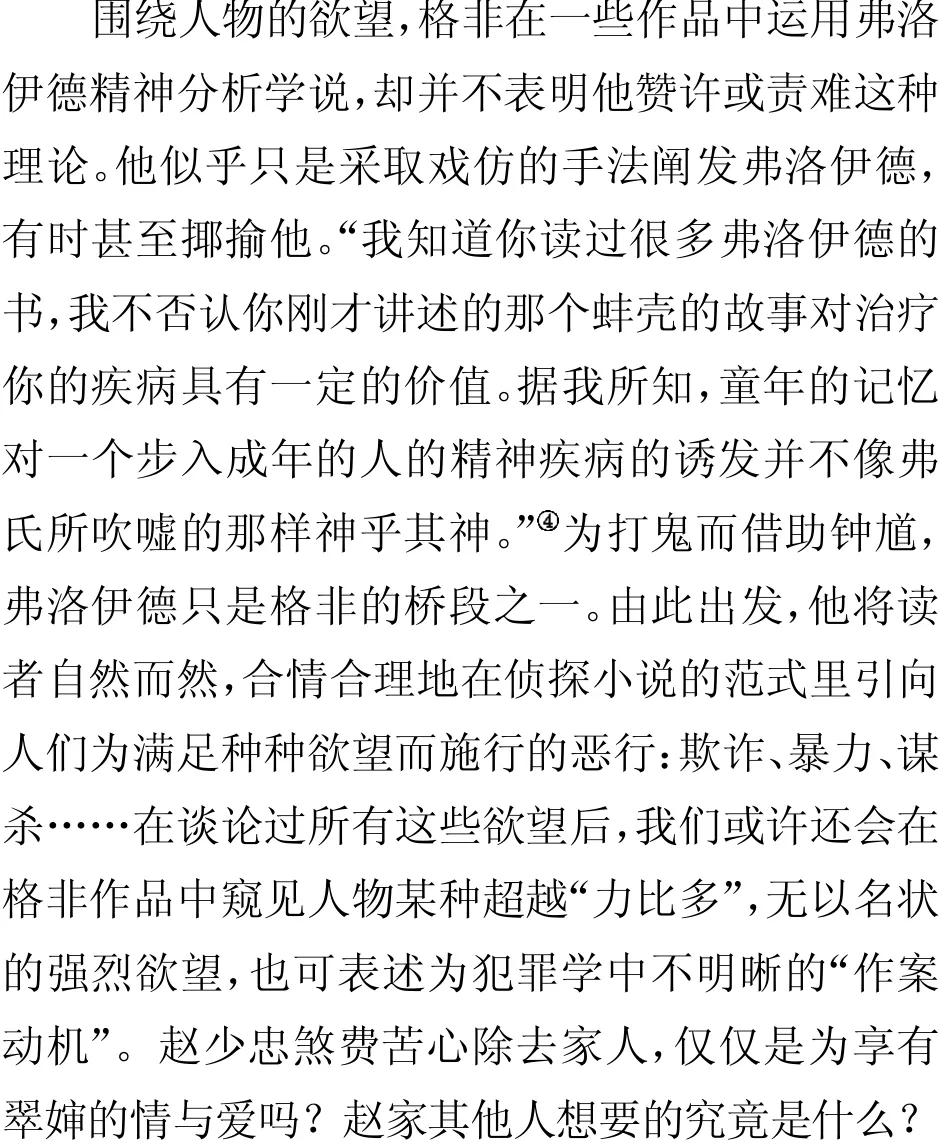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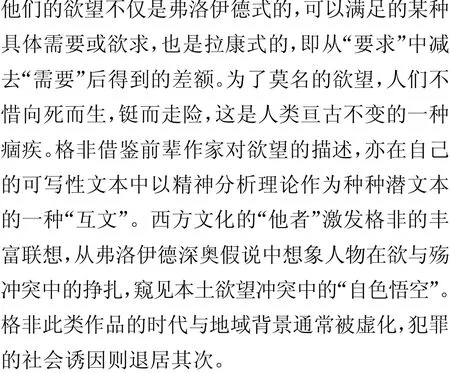
吸引读者参与的可写性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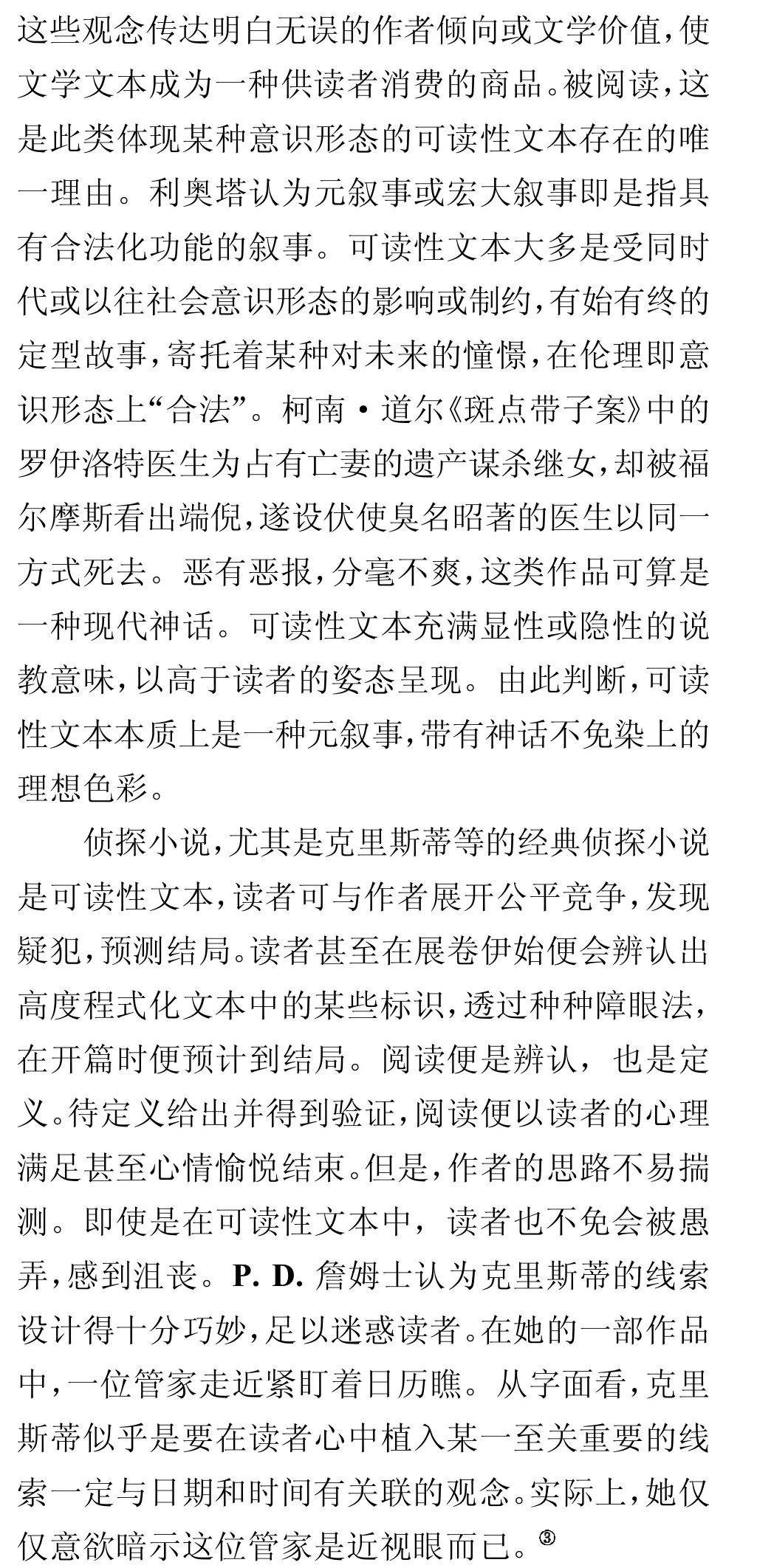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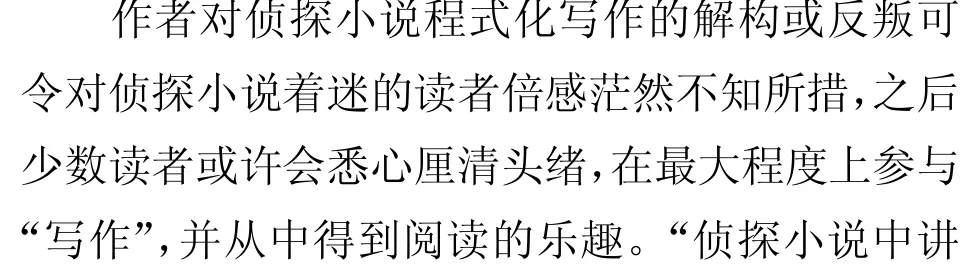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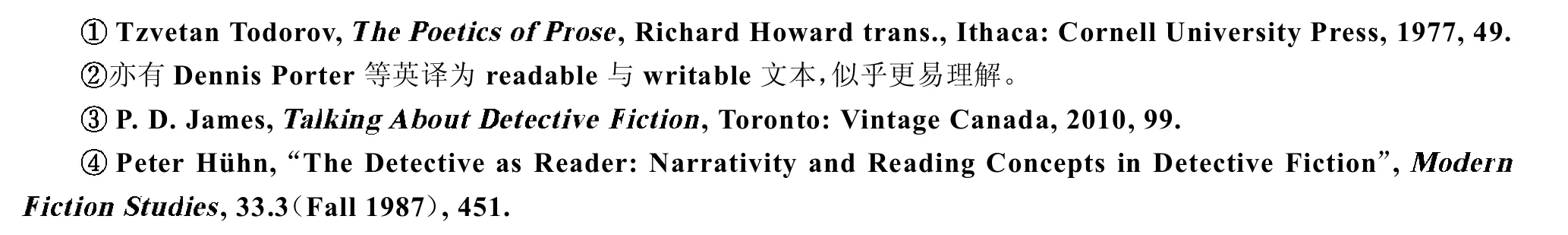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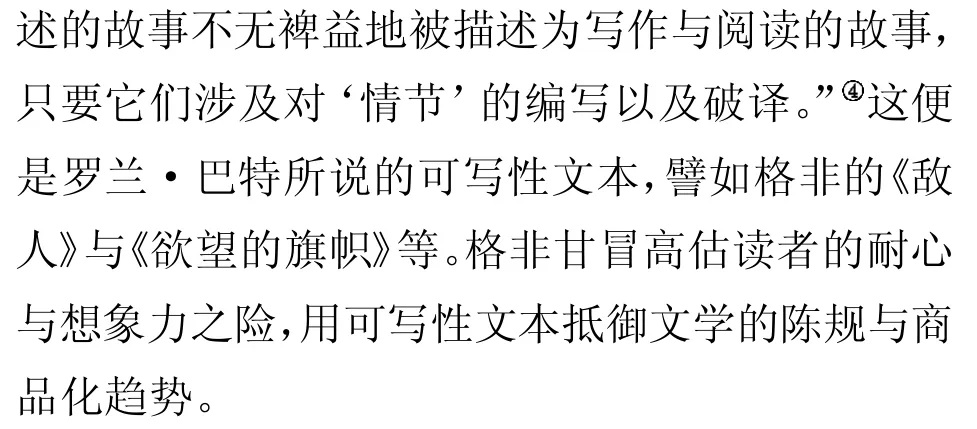
与可读性文本相对的可写性文本实为可以由读者“再度摹写的文本”。可写性文本往往隐含可读性文本予以遮蔽的内容,但是需要由读者自己努力发掘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读者不再被动接受,亦不仅仅满足于与作者展开公平竞争,发现疑犯,预测结局。他应在阅读过程中审视、估价、批判作者的文本,建构自己无形的文本,即“再度摹写”。原作者之外,理论上每一读者均是另一作者。在再度摹写中叙事结构被解构,固化的意义则被多重衍生意义取代。面对多重含义,读者成为在语词筑起的迷宫中寻觅出口的探险者。可写性文本无情地使读者解码努力受挫,直至读到卷终处的期待全然落空。
认为侦探小说是一种可写性文本的依据只是文本依赖读者的阅读生成,理论上N 种文本的生成可表述为能指的无限延异。在《敌人》一类解构型文本中,读者在苦苦寻觅线索,根据蛛丝马迹得出林林总总、见仁见智的无结局式结局。《敌人》的故事时间跨度为几十年,以子午镇为空间背景,描写殷实的赵家如何在“敌人”暗中攻击下破败。细究之下,读者发现作者并未交待故事发生的具体时间,子午镇位于何省何县亦不得而知,虽然他可以根据人物和环境描写大致揣测故事发生在民国时期的江南。
《敌人》从回顾几十年前赵少忠的爷爷赵伯衡时代一场神秘大火开始,这个以倒叙开篇的犯罪故事是侦探小说的传统叙事方法,貌似可信。但是,读者只得自己确定究竟是火灾还是有人纵火。此后的几十年内,赵伯衡、赵景轩、赵少忠祖孙三代均是业余侦探,前赴后继地致力于发现纵火者。赵伯衡临终留下的嫌疑者名单上的人被逐个排除,到赵少忠的父亲赵景轩这一辈时只剩三人。赵少忠在父亲葬礼当天烧毁名单,放弃调查。几十年后,灾难在赵少忠60 大寿前后再度降临。情节发展的走向完全不可预测,产生张力,“前理解”的难度增加,召唤读者再度摹写文本。
一年内赵家死去五人,出走两人。赵少忠的孙子突然溺死在水缸里,赵太太病死,小儿子赵虎和小女儿柳柳被杀,大女儿梅梅(作者晦涩地暗示她或许是哑巴的女儿)离开夫家出走,最后是赵家的继承人大儿子赵龙之死与哑巴的离去。谋杀的阴影笼罩下,赵家人死去散尽,陷入灭顶之灾,也令人联想起那场神秘大火,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大火与一系列暴死有关联。至此,读者相信一度鼎盛的赵家注定会随着赵少忠的死而覆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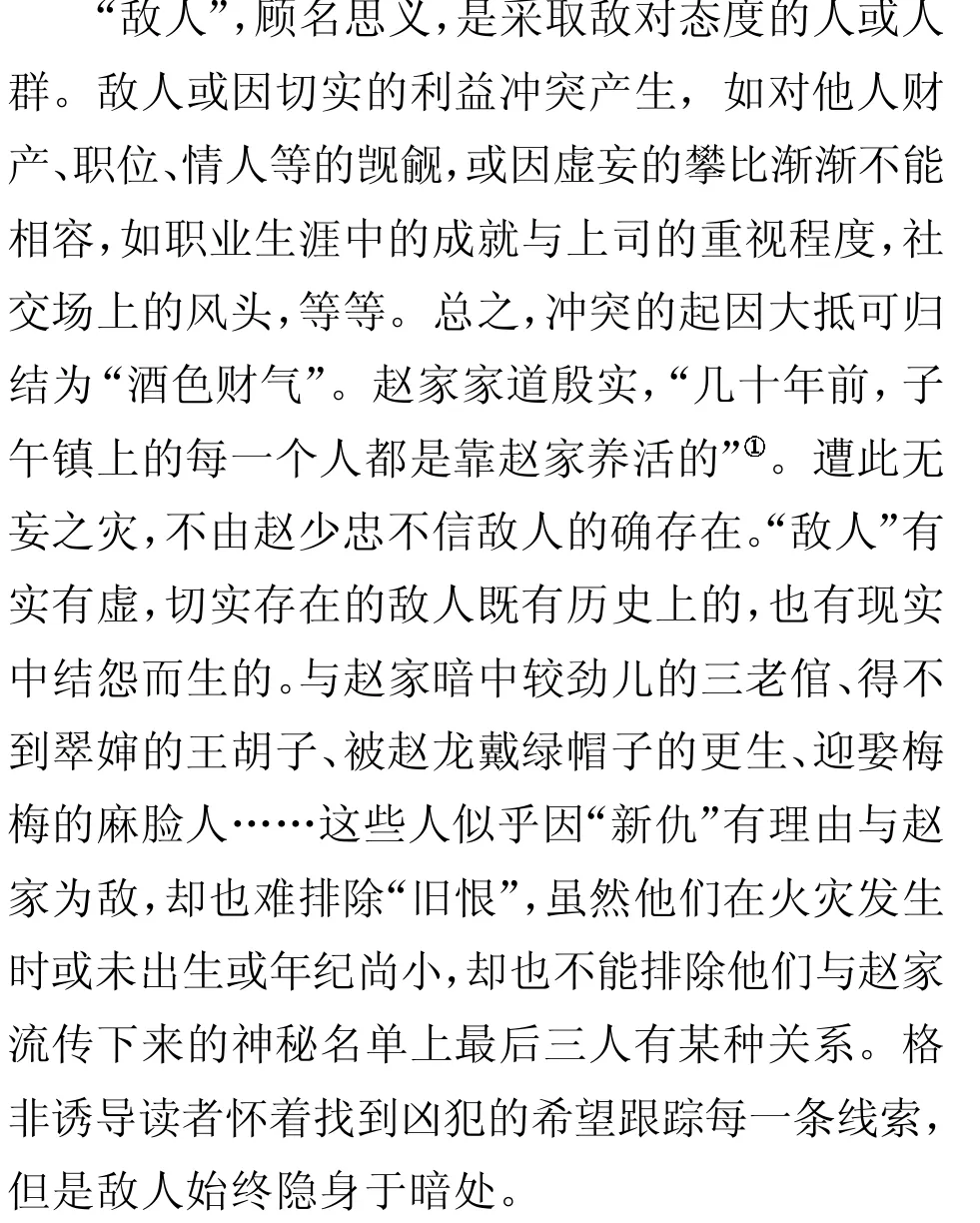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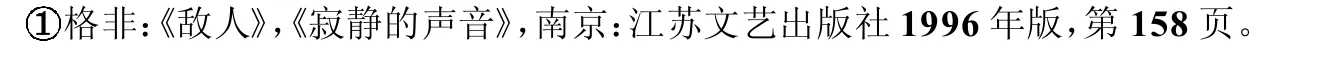
赵少忠的孙子猴子溺死在水缸里,貌似被谋杀,使故事开篇便笼罩在经典侦探小说氛围之中。表面上看,猴子的死与在酒席上闹事,摔坏好几只酒盅的麻脸人有关。但是作者暗示,疑凶可能另有他人。赵龙的妻子与人私通,被他撞见后跟情人私奔,一去不返,因此他或许早已悟到孩子并非己出。
院子里赵龙和猴子不知为什么事扭打在一起,他们在地上翻滚着,身上沾满了草茎和泥土。翠婶端着一盆衣服笑呵呵地走到廊下,“你看, 你们哪里像一对父子,简直就是兄弟俩。”(第29 页)
十年前,在赵龙的婚礼上赵少忠在众人的起哄中“用含混不清的声音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使他浑身躁动的那两个字:扒灰扒灰扒灰……”(第34 页)
似乎这是在暗示赵少忠亦有可能是猴子的父亲,然而诸如此类的多处描述均是旨在调动读者参与的障眼法,既无从证实也无法证伪。积极参与的读者或会因失败而感到沮丧,因为作者可以随时放弃循序渐进式(the progressive)的情节,转而设置多重、多种偏离正途的情节(the digressive)或转移注意力的话题以迷惑甚至愚弄读者。读者无法跟上作者的思路,不可避免地会大失所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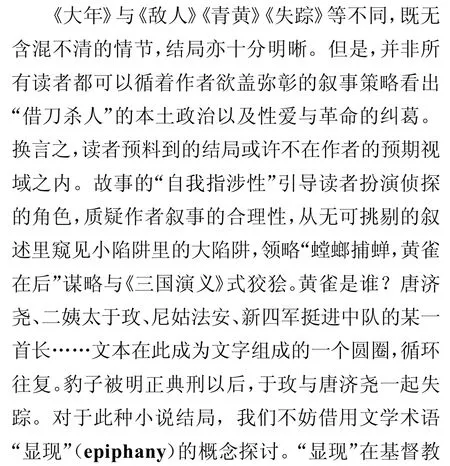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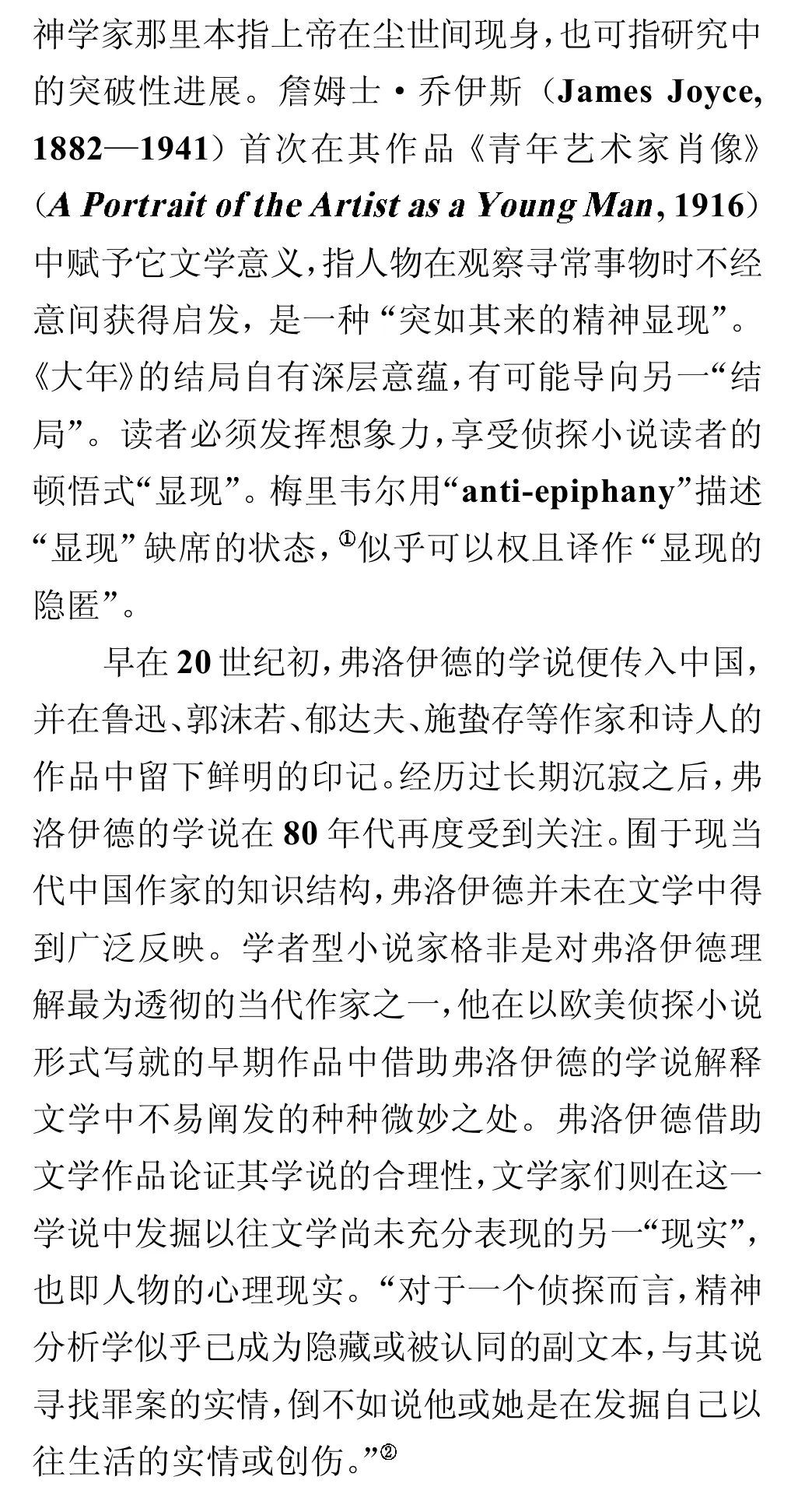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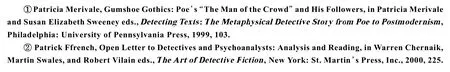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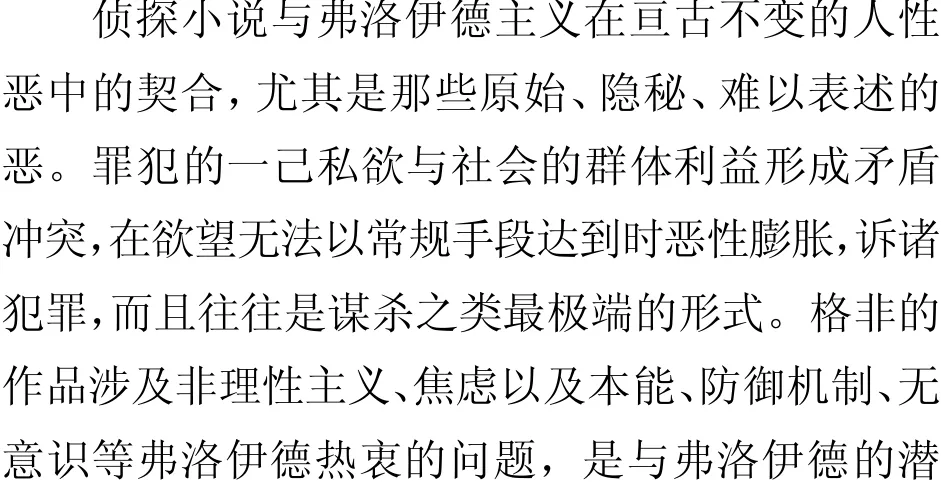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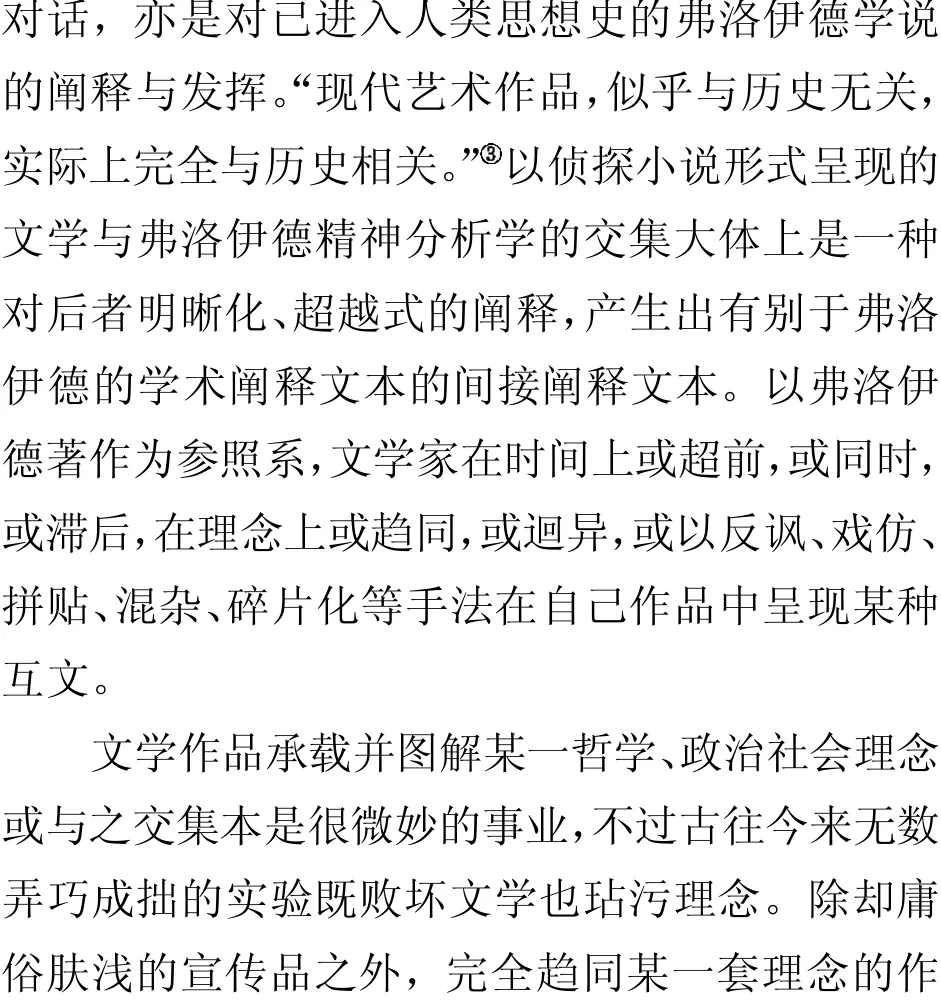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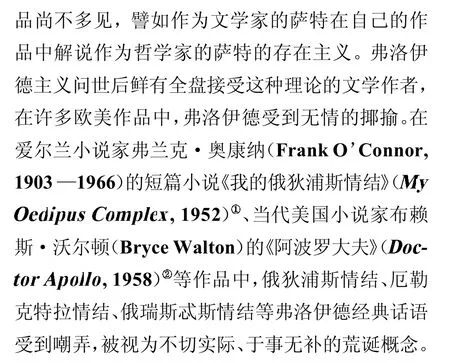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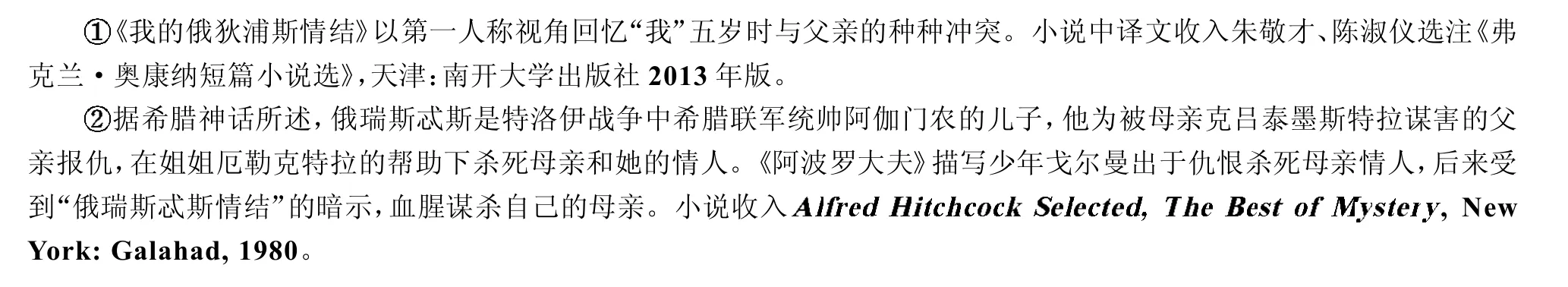
在格非的早期“解谜”小说中,作者对弗洛伊德理论的解释仍有待读者发掘,探索。但是,为揭开掩盖在可以想象却又无法窥见的生存本能与死亡本能的抗衡中的这一与生俱来的冲突,弗洛伊德的理论或假说是无法回避的。世道人心,始终是生活不可割裂的两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