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 中国文学系,台湾 高雄 80424)
论邵雍思想之结构、来历与其数理论、观物说对于理学之影响(三之二)
〔台〕戴景贤
(中山大学 中国文学系,台湾 高雄 80424)
邵雍思想之受理学家重视,因于二程,而为朱子所承。然其事迹流传虽广,真知其思想之内涵、来历与其学术之性质者实尠。故对于理学之发展,康节是否具有影响?其影响为何?历来学者,能论之者亦寡。唯以今日学界所建立之“学术史”与“思想史”之研究方法论之,则颇有可分析者。
大体而言,康节思想之来历,最可据者,为二程之说。依其说,康节之学最要者有四:一为数,一为理,一为术,一为道。此四者皆中国学术思想所讨论,而康节之为取择,非纯然属儒家。本篇之主旨,在于论叙康节思想之由论“数”及“理”,以与儒义相契之主要思想关键,乃至其“观物说”建构之理论结构;并进而分析其对于“理学”所造成之影响。至于其与道、释思想之异同,亦依议题之伸展,随文加以比论。
本文共分三篇五节,即:一、康节“数论”之历史渊源及其“推数及理”之思想结构(上);二、康节“数论”之历史渊源及其“推数及理”之思想结构(下);三、康节观物说之认识论基础,及其设论所建构之“与理学之关连”;四、康节持养工夫之精微,与其“数学”于学术方法上之限制,乃至其“数理论”所以未能真正融入“理学”之原因;五、康节所传图、数于《易》学之意义。此为三篇中之第二篇。
邵雍 理学 易学 术数 中国思想史 中国哲学史
二、康节“数论”之历史渊源及其“推数及理”之思想结构(下)
延续前说,进而考论所谓“数”之概念之于中古三国、两晋以下,则明显可见彼所受另一种属于“气论新趋”之影响。此一新趋之起因,来自战国末以至汉代,道家之一有关“气”之新观点,即是:于“气”之生化,提出“分阶”之概念;从而有所谓“元气”之说。而此论之所以成说之哲学起因为何?则可由《淮南子》之所论,予以追溯。《淮南子·俶真训》云:
有始者,有未始有有始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有有者,有无者,有未始有有无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无者。
所谓有始者,繁愤未发,萌兆牙蘖,未有形埒垠堮,无无蝡蝡,将欲生兴而未成物类。
有未始有有始者,天气始下,地气始上,阴阳错合,相与优游,竞畅于宇宙之间,被德含和,缤纷茏苁,欲与物接而未成兆朕。
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天含和而未降,地怀气而未扬,虚无寂寞,萧条霄雿,无有仿佛,气遂而大通冥冥者也。
有有者,言万物掺落,根茎枝叶,青葱苓茏,雚蔰炫煌,蠉飞蝡动,蚑行哙息,可切循把握而有数量。
有无者,视之不见其形,听之不闻其声,扪之不可得也,望之不可极也,储与扈冶,浩浩瀚瀚,不可隐仪揆度而通光耀者。
有未始有有无者,包裹天地,陶冶万物,大通混冥,深闳广大,不可为外,析豪剖芒,不可为内,无环堵之宇而生有无之根。
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无者,天地未剖,阴阳未判,四时未分,万物未生,汪然平静,寂然清澄,莫见其形,若光耀之间于无有,退而自失也,曰:“予能有无而未能无无也。及其为无无,至妙何从及此哉!”
论中所谓“有始者”,“有未始有有始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三者之论,皆以“始”为题;“有有者,有无者”,“有未始有有无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无者”,三者之论,皆以“有”、“无”为题;而二项议题,彼此相关。凡此,并是庄子〈齐物论〉中所陈之说。
而由此一讨论之方式观察,则可见出:道家之于战国以降,对于《老子》书中所提“有生于无”之说法,随“气”之概念之明确化、深层化,开始因“宇宙起源论”(cosmogony)方面议题之追索,出现崭新之进展,故胪列多种歧向之意见。而《淮南子》此篇,亦即以此种探论之方式为说。
唯以淮南(刘安,前179—前122)宾客所为、或所集之论说观之,其书无论〈原道训〉所云“泰古二皇,得道之柄,立于中央。神与化游,以抚四方”,或〈精神训〉所云“二神混生,经天营地,孔乎莫知其所终极,滔乎莫知其所止息。于是乃别为阴阳,离为八极,刚柔相成,万物乃形”,皆已是将道家原本之论,结合之于阴阳家所言之“阴阳”、“五行”,而将“道”、“道柄”与“运使”三层分释;并由此阐明“神”之所托,与其所以能“以德致和”之原因。其中〈原道训〉之论,尤为重要;其文云:
泰古二皇,得道之柄,立于中央,神与化游,以抚四方。是故能天运地滞,轮转而无废,水流而不止,与万物终始。风兴云蒸,事无不应;雷声雨降,并应无穷;鬼出电入,龙兴鸾集;钧旋毂转,周而复匝;已雕已琢,还反于朴。无为为之而合于道,无为言之而通乎德,恬愉无矜而得于和,有万不同而便于性,神托于秋毫之末,而大与宇宙之总。其德优天地而和阴阳,节四时而调五行。呴谕覆育,万物群生,润于草木,浸于金石,禽兽硕大,毫毛润泽,羽翼奋也,角觡生也,兽胎不贕,鸟卵不毈,父无丧子之忧,兄无哭弟之哀,童子不孤,妇人不孀,虹蜺不出,贼星不行,含德之所致也。
此种论述之逻辑,显示有关“气”之“构成”概念,一旦加入于“道论”,所必然引起之有关“宇宙构成论”(cosmology)之议题;《庄子》外、杂,与《淮南子》所集录,皆可见出此项发展之痕迹。
而若以此处所引〈原道训〉、〈俶真训〉二文合论,则见“始”与“有”之议题,虽由《庄》书提出,其所本原之“有”、“无”之论,已非《老子》书中以之作为“存有学”(ontology)与“宇宙构成论”相接合之观念,而系以之处理特定范围内之“气化”问题。
于其区分“道”、“道柄”、“运使”之推衍中,事实乃预设一“阴阳未判”之“原始之气”之状态。此一关涉“神”与“气”之“既分而又合”之观点,可系之于《淮南子》书中之“精”、“神”论。其〈精神训〉云:
古未有天地之时,惟像无形,窈窈冥冥,芒芠漠闵,澒蒙鸿洞,莫知其门。有二神混生,经天营地,孔乎莫知其所终极,滔乎莫知其所止息。于是乃别为阴阳,离为八极,刚柔相成,万物乃形,烦气为虫,精气为人。
是故精神者,天之有也;而骨骸者,地之有也。精神入其门,而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是故圣人法天顺情,不拘于俗,不诱于人,以天为父,以地为母,阴阳为纲,四时为纪。天静以清,地定以宁,万物失之者死,法之者生。
夫静漠者,神明之宅也;虚无者,道之所居也。是故或求之于外者,失之于内;有守之于内者,失之于外。譬犹本与末也,从本引之,千枝万叶,莫得不随也。

故头之圆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时、五行、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支、五藏、九窍、三百六十六节。天有风、雨、寒、暑,人亦有取、与、喜、怒。故胆为云,肺为气,肝为风,肾为雨,脾为雷,以与天地相参也,而心为之主。是故耳目者,日月也;血气者,风雨也。日中有踆乌,而月中有蟾蜍。日月失其行,薄蚀无光;风雨非其时,毁折生灾;五星失其行,州国受殃。夫天地之道,至纮以大,尚犹节其章光,爱其神明,人之耳目曷能久熏劳而不息乎?精神何能久驰骋而不既乎?


唯《淮南子》论中所谓“二皇”、“二神”,其本质究竟为何?则其论未周。以是此种接合“阴阳家”与“道家”之思惟,亦可产生不同发展趋向:一种结合社会中所尚遗存之古代“萨满教”(shamanism)之思想成分,正式向新形态之“泛神论”(pantheism)方向发展;甚或企图同时建构具有哲学义涵之“清净”本质之“至上神”之概念。一种则是将道家“精”、“神”之论中,所藉以融合“精神性存在”与“物质性存在”之“精”、“粗”概念,更往上提升;于是而有关于“真人”之具体论述。后者之铺陈,即《淮南子》书中它篇所提出之“反本”之说。

此类丹道之所以具有“数、气并论”之特质,关键在于:彼所释之法,牵涉“内养”与“炉火”,而皆有所以“相应”之理。汉末魏伯阳(翱,号云牙子)《周易参同契》云:
乾、坤者,易之门户,众卦之父母。坎离匡廓,运毂正轴。牝牡四卦,以为槖钥。覆冒阴阳之道,犹工御者执衔辔,准绳墨,随轨辙,处中以制外。数在律历纪。月节有五六,经纬奉日使。兼并为六十,刚柔有表里。朔旦屯直事,至暮蒙当受。昼夜各一卦,用之如次序。既、未至晦爽,终则复更始。日辰为期度,动静有早晚。春夏据内体,从子到辰巳。秋冬当外用,自午讫戌亥。赏罚应春秋,昏明顺寒暑。爻辞有仁义,随时发喜怒,如是应四时,五行得其序。
又曰:

又曰:

又曰:
子午数合三,戊己号称五。二五既和谐,八石正纲纪。嘑吸相贪欲,伫思为夫妇。黄土金之父,流珠水之母。水以土为鬼,土填水不起。朱雀为火精,执平调胜负。水胜火消灭,俱死归厚土。三性既合会,本性共宗祖。巨胜尚延年,还丹可入口。金性不败朽,故为万物宝。术士服食之,寿命得长久。土游于四季,守界定规矩。金砂入五内,雾散若风雨。熏蒸达四肢,颜色悦泽好。发白更生黑,齿落出旧所。老翁复丁壮,耆妪成姹女。改形免世厄,号之曰真人。
《参同契》以《周易》之象数说明丹道,其说虽仅立梗概,然其言“运毂正轴”以成丹之理,已具规模。而其所以合黄老、炉火于《大易》,于观念中,“气”、“数”之相应,即是关键。理学之兴,濂溪得〈太极图〉、康节得〈先天图〉,其传授皆云曾假手穆修伯长,而伯长之得〈先天图〉,则出于陈抟希夷;后人由此上溯南朝以前,谓二图尚可追溯之于魏伯阳此书。此一笼统之说,于今细究,其间固不无可疑与可议,然明道〈邵尧夫先生墓志铭〉,谓康节之学“推其源流,远有端绪”,亦是北宋当时流传之说,于《易》数之学,本即有一概括之见,与此相类。朱子之为《参同契》考异,亦系认为此间必有牵涉“气论”之重要关系,故虽涉方外之论而不避。此一线索,不应轻看。
穆伯长、李挺之之说《易》,以今而言,已无可得而详,然彼二人所涉之传授,既皆云出希夷,则此一与丹道相关之“观念形态”与理路,应可由希夷及其师友关系,略见梗概。于今而可追寻之重要线索之一,即为与希夷同时之谭景升(峭,860/873—968/976)。景升之著论云:
道之委也,虚化神,神化气,气化形,形生而万物所以塞也。道之用也,形化气,气化神,神化虚,虚明而万物所以通也。是以古圣人穷通塞之端,得造化之源,忘形以养气,忘气以养神,忘神以养虚。虚实相通,是谓大同。故藏之为元精,用之为万灵,含之为太一,放之为太清。是以坎离消长于一身,风云发泄于七窍,真气熏蒸而时无寒暑,纯阳流注而民无死生,是谓神化之道者也。
文中之言“虚化神,神化气,气化形”,其等级之不同于汉代之论,在于以“神”与“气”同出于“虚”,而不复使用气之“分阶”概念;而彼之以所谓“虚、实相通”,作为“丹法”理论之基础,则是沿《周易参同契》而有。唯此种以“道之体”为未可论,凡有可说,必于其“委而后生神”论之,乃是将“存有学”所应涉及之“道体”之论,暂时排除于“宇宙构成论”之外,使“气化论”得以单独成说。
而究论此一论述模式,所以得以成说,其须有之设论,则是以“道用”之“目的性”(finality)之缺乏,上推于“道体”,而以“自然”义之“虚无”释之,从而将道之起用,说之为“委”;以此作为“炼气化神”者得以“反本”之依据。
唯因此所谓“委”之缺乏“目的性”,仅是说明其“成化”之非由“目的因”(final cause)所主导,无“积极性”,并非无“数理性”;故“虚”之于“实”,具有一种“无障碍”之“神”之“胜用”。此种“无障碍”之神之“胜用”,与“有所障碍”之形质之“偏用”间,相互协应;“虚”、“实”之相通,盖以是而成为可能。
景升此一仅言“太一”不言“道体”之说法,显示“气”之得以“虚”、“实”相通,以彼所明之“数”“理”论之,其分、合,应自有丹家一套哲学,作为画分“气之本体之第一义”(即“精”),与“气之流行之第二义”(即“气”)之基础。而此种理论之必需,应亦是希夷所以有取于《易》图之象、数,以发明所谓“先天之学”之原因。
希夷之论云:
易者,大易也。大易,未见气也,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故曰易。易者,希微玄虚凝寂之称也。及易变而为一,一变而为七,七变而为九,九复变而为一也。一者,形变之始也,清轻者上为天,重浊者下为地,冲和气者中为人。谓之易者,知阴阳之根本有在于是也。
希夷此一诠说,略本于前引《列子》“太易”之论,而删除其下“太初”、“太始”、“太素”各阶,其意盖欲以彼所信解之《老子》,合之于《易》,而以所谓“先天之卦位”释之。彼论中,以“一”为道之子,即两仪未判之“太极”,乃气“能变”之本,而非变合之数。若然,则不唯“道”有体、用,“气”亦有体、用;所谓“先天”之学,即由气“形变”自然之生序,以推知其当有“未变合而已备”之数。然此所谓“数”,仅可心通,而非可智推,故非炼气化神以反乎其本者不知;心通则道成矣,可以变幻而莫测。
凡康节之以“气、神不离”之观点,总绾其论,即由类此之思惟所构成。康节之论云:
气一而已,主之者乾也。神亦一而已,乘气而变化,出入于有无死生之间,无方而不测者也。即是其说。
然对于道体之体,与道用中于“气”所见“数”、“理”之分、合,康节亦有不同于希夷之理论建构;企图将当时丹鼎家所主之自然观,由“消极”改为“积极”。其说云:
阳尊而神,尊故役物,神故藏用,是以道生天地万物而不自见也。天地万物亦取法乎道矣。
阳者道之用,阴者道之体。阳用阴,阴用阳,以阳为用则尊阴,以阴为用则尊阳也。
阴几于道,故以况道也。六变而成三十六矣,八变而成六十四矣,十二变而成三百八十四矣。六六而变之,八八六十四变而成三百八十四矣。八八而变之,七七四十九变而成三百八十四矣。


心为太极。
又曰:
道为太极。
又曰:
形可分,神不可分。
又曰:
性非体不成,体非性不生,阳以阴为体,阴以阳为体。动者性也,静者体也。在天则阳动而阴静,在地则阳静而阴动。性得体而静,体随性而动,是以阳舒而阴疾也。
阳不能独立,必得阴而后立,故阳以阴为基;阴不能自见,必待阳而后见,故阴以阳为唱。阳知其始而享其成,阴效其法而终其劳。
阳能知而阴不能知,阳能见而阴不能见也。能知能见者为有,故阳性有而阴性无也。阳有所不徧,而阴无所不徧也。阳有去(校云:《道藏》本作“知”),而阴常居也。无不徧而常居者为实,故阳体虚而阴体实也。
又曰:
天地之本其起于中乎?是以乾坤屡变而不离乎中。
人居天地之中,心居人之中,日中则盛,月中则盈,故君子贵中也。
本一气也,生则为阳,消则为阴,故二者一而已矣,四者二而已矣,六者三而已矣,八者四而已矣,是以言天不言地,言君不言臣,言父不言子,言夫不言妇也。然天得地而万物生,君得臣而万化行,父得子、夫得妇而家道成,故有一则有二,有二则有四,有三则有六,有四则有八。
文中所谓“阳性有而阴性无”,即是物之可观常在“动”,其所显即“象”;若阴静之体,则非可观,特可缘“形”、“名”以推,“质”以是而有“数”。“数”之不虚,与“性”、“命”相符,则证“道之用”中有“理”。至于心之所以能知,则是因“形可分,神不可分”,道体于人之得“数之中”以生者,显其能;以是而有可以表乎“象”、“数”之“言”、“意”。故又曰:
道生天,天生地。及其功成而身退,故子继父禅,是以乾退一位也。
象起于形,数起于质,名起于言,意起于用。天下之数出于理,违乎理则入于术。世人以数而入于术,故失于理也。
其论中所云“功成而身退,故子继父禅,是以乾退一位”,事实上,即是主张:道之体虽虚而无有“目的”,其变化之中,则可因神化之推衍而有“理”;于此之时,子继父禅,以是而有“形”、“质”、“言”、“用”,以是而有“象”、“数”、“名”、“意”。凡尽性者之可于彼所值之“后天”,善养所谓全乎天地之“先天”而无所偏离,皆准焉。康节之以精于数而归本于儒,而非“以数入术”,其关键在此。以下续论之。
三、康节观物说之认识论基础,及其设论所建构之“与理学之关连”
前论引丹家之说,谓彼所指“虚、实相通”,其验在于“坎”、“离”之能消长于一身,“风”、“云”之能发泄于七窍,与真气熏蒸之能时无寒暑;以是而得纯阳流注于体,而无死生。此说与儒者所云“率性”、“致和”,自是整体之发展方向不同。而康节之由论“数”及“理”,则是可与儒义相契。其关键在于:康节以“理”为尽性者所不可失,以是“观物而知理”,成为必须。康节云:《易》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所以谓之理者,物之理也。所以谓之性者,天之性也。所以谓之命者,处理性者也。所以能处理性者,非道而何?是知道为天地之本,天地为万物之本。以天地观万物,则万物为万物,以道观天地,则天地亦为万物。

正因如此,故若以前引康节说所云“功成而身退,故子继父禅,是以乾退一位”论之,则“道”、“天地”与“万物”三者作为可认识之“对象”,皆可因观者所选择之立场、角度不同,亦使其所获得之“诠释意义”随之差异。
因若以万物所以产生之“过程”观万物,则由天地之渐生万物,乾退一位,所得者即万殊之理数,而乾之位仍在;此“后天”必得乎“先天”而始全之义,故云“以天地观万物,则万物为万物”。然若更由天地而上溯,则见所以为天地之乾,与所以为万物之乾,皆是同一乾道推去,因此依“道”之施用言,“天地亦为万物”。
康节此说,依理路言之,即是“一为数本,万数不离于一”之数法。数理具有贯通始末之一致性。唯于康节而言,见有数而不见有理,必流于术。人之明理,倘就“天地”观万物,万物同为物而物物不同,虽物物不同,而莫非此天地,此即是“理”;若就“道”而观万物,则万物之性皆源于天,乃出于一,此一乃道之一,而非气之一,以是而有“天性”。故就“人”而言,于人亦存在“以所受命,而可以处物之道”。此即是儒家所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为“穷理之学”与“为人之道”之完成。
然如依此说,于同一对象,观者可有不同之观法,且于理论,此一“观法”,虽不离于“主观之体”,却又具有一种“客观性”(objectiveness);则作为此种主张之“认识论”,其基础为何?亦不能不进一步论之。康节于此,则有“心得而知之为‘知’;心不得而知之为‘不知’”之说。康节云:
人或告我曰:“天地之外,别有天地万物,异乎此天地万物。”则吾不得而知之也。非惟吾不得而知之也,圣人亦不得而知之也。凡言知者,谓其心得而知之也。言言者,谓其口得而言之也。既心尚不得而知之,口又恶得而言之乎?以心不可得知而知之,是谓妄知也。以口不可得言而言之,是谓妄言也。吾又安能从妄人而行妄知妄言者乎!
此所云“人或告我曰:天地之外别有天地万物,异乎此天地万物”,以当时之思想环境言,当即指佛说,而康节于此不论;以佛家言说无从得而确认。此即“不知为不知”。至于心之所以尽物性,则在康节所指言之“意”,故曰:
夫意也者尽物之性也,言也者尽物之情也,象也者尽物之形也,数也者尽物之体也。仁也者尽人之圣也,礼也者尽人之贤也,义也者尽人之才也,智也者尽人之术也。
尽物之性者谓之道,尽物之情者谓之德,尽物之形者谓之功,尽物之体者谓之力。尽人之圣者谓之化,尽人之贤者谓之教,尽人之才者谓之劝,尽人之术者谓之率。
道德功力者,存乎体者也。化教劝率者,存乎用者也。体用之间有变存焉者,圣人之业也。
夫变也者,昊天生万物之谓也。权也者,圣人生万民之谓也。非生物非生民,而得谓之权变乎?
文中康节“意”、“言”、“象”、“数”并举,盖亦是依《易》学为论。所谓“意”,虽云乃所以“尽物之性”,其关键,则须兼得“物之形”与“物之体”;故不离于象、数。由此而有“象”、“数”之“知”,由此而有达“象”、“数”之“言”,由此而得以知“道”、“德”、“功”、“力”之有可为,由此而得以知“化”、“教”、“劝”、“率”之必能尽之。此种非物之自身所能然,而得以因“道”与“圣”以全其能然者,康节谓之“权变”。
然依其说,心有知,而不能尽知,其所能得于“象”、“数”与“体”、“用”之知者,又有可凭依;则“心”与“物”之间,“心”与“天”、“地”之间,其感应之关连处何在?是否亦同于丹家“虚、实相通”之说?亦须一辨。康节云:
天地之本其起于中乎?是以乾坤屡变而不离乎中。
又云:
人居天地之中,心居人之中,日中则盛,月中则盈,故君子贵中也。
又云:
元有二:有生天地之始者,太极也;有万物之中各有始者,生之本也。“天地之心”者,生万物之本也。“天地之情”者,情状也,与“鬼神之情状”同也。
又云:
太极一也,不动;生二,二则神也。神生数,数生象,象生器。
太极不动,性也,发则神,神则数,数则象,象则器。器之变复归于神也。
康节此处所谓“中”,乃“处位”之“中”;然此位,非方位,而系消长变化之本位。以“数”言,即《河图》之五,为天数之和;以“卦”言,即内、外二卦之中爻。其以“中五”为天地生数,而为太极本位,其理则见于康节“先天《易》数”之说;盖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也。故凡所谓“人居天地之中,心居人之中”,俱是以“天地之本起于中”为本因7。以是而言,人心之为“中”之“中”,即等同太极所能显性之极致,以是而备天地万物之理;为阳中之阳。凡所以为“先天之学”者,皆自中起。
既以人之心为天地之心,从而亦谓“人心中自具一天地”,则人心之于“能知”见有所谓“意”,非臆之也,必有其可合于“理”者;但须于心中见有所谓“天地万物”。此即为“观物”。
故康节云:
天所以谓之观物者,非以目观之也。非观之以目而观之以心也,非观之以心而观之以理也。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焉,莫不有性焉,莫不有命焉。所以谓之理者,穷之而后可知也。所以谓之性者,尽之而后可知也。所以谓之命者,至之而后可知也。此三知者,天下之真知也。……圣人之所以能一万物之情者,谓其圣人之能反观也。所以谓之反观者,不以我观物也。不以我观物者,以物观物之谓也。既能以物观物,又安有我于其间哉!
夫所谓“以物观物,不以我观物”,依此而言,约有三层,即:知其理、知其性、知其命。知其理者,达其变;知其性者,明其本;知其命者,通晓其所以“与万为一”之义。而所以知之,皆须于“己心”尽之;而此心乃“无我”。无我而能尽万物之情,则能使天下皆归于中焉;此即是圣人之“建中作极”。
今若取以上所释,与丹家之论相较,则其相关而同者在于:如无道家自魏晋以来“深化”后之气论,从而将“虚、实相通”之理落实于修为,则无以见“心气”与“质气”间之关连。此种藉由丹道而增益之说法,超越战国以至于汉一般道家论者对于所谓“精”、“神”之说之理解。
唯丹家虽云“道合自然”,其“尽性”之义,无“建中作极”之义,故为“道”不为“儒”。康节则是由“心”、“气”之实然相通,以探知“数”、“理”之所本,并由此而深明“理”、“性”、“命”三者之关连,从而有“化成万物”之志;此为二者之异。
然康节之由“道家之论”转向儒学,论之者以之归于《易》学中之一种发展而即可;何以后之诠释者,仍每企图于“理学”之脉络中辨之?又是否真可于“理学”之脉络中辨之?凡此,亦应深究。
依余之见,康节之论于北宋理学之发展,应有其意义,且此意义不应忽略之原因在于:透过其论,可彰显“气化”之过程中,“气”所以能分别展现“精神面相”与“物质面相”之起因,及其关连;而不须别为一种“唯心之论”,如释氏之学。此点于理学之初起,建构其完整之“宇宙构成论”至为重要。至于康节影响之于其身后实质发生,则系藉朱子之《易》论,与其“理”、“气”之说而达成。
关于《易》论部分,朱子之答袁机仲(枢,1131—1205)云:
来教疑《河图》、《洛书》是后人伪作。
熹窃谓生于今世而读古人之书,所以能别其真伪者,一则以其义理之所当否而知之,二则以其左验之异同而质之,未有舍此两涂而能直以臆度悬断之者也。熹于世传《河图》、《洛书》之旧所以不敢不信者,正以其义理不悖而证验不差尔。来教必以为伪,则未见有以指其义理之缪、证验之差也。而直欲以臆度悬断之,此熹之所以未敢曲从而不得不辨也。……
来教疑先天、后天之说。
据邵氏说,先天者,伏羲所画之易也;后天者,文王所演之易也。伏羲之易初无文字,只有一图以寓其象数,而天地万物之理、阴阳始终之变具焉。文王之易即今之《周易》,而孔子所为作传者是也。孔子既因文王之易以作传,则其所论固当专以文王之易为主。然不推本伏羲作易画卦之所由,则学者必将误认文王所演之易便为伏羲始画之易,只从中半说起,不识向上根原矣。
朱子此一阐论,谓“先天”象数之理,先于“后天”万物阴阳始终之变之理,若以康节之说明之,即其诗中所云“体在天地后,用起天地先”。此一发明《易》理之途径,最主要之特点,在于不取二氏于“变”之上,或云“之前”,另说“恒常之体”,而系以“数理”之方式,说明“能”与“所”间之关系之为一种“化”之展衍;以是成“象”。凡此皆乃“自然”,而无“使之然”者。故以“存在”义言,凡云“实存之体”皆属后,而“成化之用”则在先;特所谓“象”“数”于“已成者”推之之法,与“未形者”推之之法差异。

朱子它处释康节之说云:
“性者,道之形体;心者,性之郛郭。”康节这数句极好。盖道即理也,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是也。然非性,何以见理之所在?故曰:“性者,道之形体。”仁义礼智,性也,理也;而具此性者,心也,故曰:“心者,性之郛郭。”

关于第一项所谓“‘道’为‘能变’之整体,‘道’预涵一切‘形式’之可能”。

关于第二项所谓“理、数为‘气化’实现其潜能之途径与规律”。
此一观点之意义,在于先天之理数,于一切存有物“存在”之前,即以“非‘实在’之可能性”预涵于道体之中,并成为“气化”实现其潜能之途径。然由于“道体”本身“动态”之动力性,使因实现而产生之变化,于连续中,具有立基于“先”“后”而产生之差异,以是“形体”与“性情”交相感应后出现之“形式”,日趋于复杂;所谓变化中之“规律”,即是由此展现。
关于第三项所谓“‘精神性存有’与‘物质性存有’,同属气化之可能”。
康节云:
人之所以能灵于万物者,谓其目能收万物之色,耳能收万物之声,鼻能收万物之气,口能收万物之味。声色气味者,万物之体也。目耳鼻口者,万人之用也。……
然则人亦物也,圣亦人也。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万物之物,有亿物之物,有兆物之物。为兆物之物岂非人乎!
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万人之人,有亿人之人,有兆人之人。为兆人之人,岂非圣乎!
是知人也者,物之至者也。圣也者,人之至者也。物之至者始得谓之物之物也。人之至者始得谓之人之人也。夫物之物者,至物之谓也。人之人者,至人之谓也。以一至物而当一至人,则非圣人而何?人谓之不圣,则吾不信也。何哉?谓其能以一心观万心,一身观万身,一物观万物,一世观万世者焉。又谓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功,身代天事者焉。又谓其能以上识天时,下尽地理,中尽物情,通照人事者焉。又谓其能以弥纶天地,出入造化,进退古今,表里人物者焉。
噫!圣人者,非世世而效圣焉。吾不得而目见之也。虽然吾不得而目见之,察其心,观其迹,探其体,潜其用,虽亿千万年亦可以理知之也。
所谓“为兆物之物者为人”,在人能通知“万物之体”,“得物之物”;所谓“为兆人之人为圣”,在于其能“以一心观万心,一身观万身,一物观万物,一世观万世”。凡此,皆系以物之相“感应”、人之有“知”而言,其立论之基础,在于前所叙道家论“气”时所主之“虚、实相通”。然康节所指之“能观”与“所观”,则是丹家之义所未及。此“观”字之用,若溯其源,当出于释氏“止”、“观”之说。

关于第四项所谓“人心之成为一种特殊之‘存在样态’,来自‘道体’内在核心动力之驱使;而其所具有‘创造价值’之可能,则来自‘道体’本身所蕴涵之丰满性与完整性”。
此所谓“道之体”具内在之核心动力,约有数义:
以“动力”义而言,即是“道”之“生化”之能;以“核心”义而言,即是“道”于“生化”中,数、理之归极,其表现于“数”,即“中数”,其表现于“极”,即“中极”。故就人之于万物之生化中出现论,虽非来自“化”之积极目的,却属“道”之整体性所能然,而其展现为“人性”,则包有一种数理之丰满性;此丰满性,乃数“所可有之必然”。此即所谓“天地之本起于中,人居天地之中,心居人之中”一语,可深掘之概括义。
综以上四项论述,而为之析理,则见以“数”、“理”之方式,建构一种融合“理”、“气”,乃至“心”、“性”之论,于“宇宙构成论”之部分,有其可以发展之理路;朱子之将《易》义区分阶层,而不废象、数,即是受康节之影响而然。特就“存有学”之议题而言,朱子以“理体”当“道体”,则有其特殊之立义主张;非皆遵康节。二者亦当分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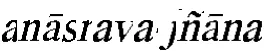
唯就哲学方法言,朱子之有取于《图》、《书》,仅是主张“理”之为有,就“生成”之层次言,“象数之理”实先于“事物之理”;并未如康节不仅总括一切历学,尽归之于《易》,亦在总括一切“生成”之理,尽归之于数。故若因朱子之有取于康节,遂谓朱子乃“杂于道家之学”,或“实是道家之学”,自属过当而不实。
责任编辑:于亭
The Philosophical System of Shao Yong and Its Impact on Neo-Confucianism:Part Two(second of three parts)
〔TW〕Ching-hsien Tai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Sun Yat-sen University,Kaohsiung 80424,Taiwan)
Historically,Shao Yong(1011—1077)was praised so highly that his life has become a legend.Yet,as a philosopher,he has neither been fully understood nor have his works been accurately interpreted.The reason for this paradoxical phenomenon lies in Shao Yong’s complicated philosophical treatment with Yin-yang School,Daoism and Confucianism.This article aims to re-discover the philosophical system of Shao Yong,as well as his impact on the Neo-Confucianism,through a careful examination of his writings,and hopefully give a new look at the question.
Shao Yong;Yin-yang School;Daoism;Neo-Confucianism;Song Studies;History of Chinese Thought
戴景贤,字嘉佑,祖籍安徽合肥,1951年出生于台北市。自高中时代起,即师事国学大师、著名史学家钱穆,前后逾二十载。1982年毕业于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班,获文学博士学位。自同年起,任教于高雄中山大学中国文学系迄今,并曾担任该系教授兼主任。耶鲁大学东亚语文系、“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学者。现任台湾高雄中山大学特聘教授。研究领域涵括学术史、思想史、美学、文学批评与中西思想比较。曾获中山大学研究杰出奖、杰出教学奖,并经遴选为该校传授教师(mentor)。此外亦获颁“教育部师铎奖”、“国家科学委员会杰出研究奖”,及多次“特殊优秀人才”奖励。众多著作,编辑为《程学阁著作集》,将陆续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目前已刊行《明清学术思想史论集》上下编、《王船山学术思想总纲与其道器论之发展》上下编、《钱宾四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论集》,共六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