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文化各自有其源远流长的传承,有其相对独立演变的时间段,有其信仰的不同,有其人间处境与人世关怀的差异。文人与艺术家生活在相对独立的文化环境,他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因其独特的艺术感知,会探索自己熟知的人类处境,而凝聚出璀璨的艺术结晶。
一
一般而言,在特定的历史环节上,不同文化传统会诱使心灵敏感的艺术家,专注生于斯、长于斯的独特文化面向,发展出别开生面的艺术形式,思考他们关心的人类处境;通过思想意识的艺术虚构,凸显人生的悲欢离合,叩问生命的实存意义;进而追求与创作出理想的升华或幻灭,在精神领域上为自己的文化传统提出突破心灵困境的艺术方案。然而,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人所面临的处境也有相似的悲欢离合,沉浸于爱情的甜蜜与死亡的悲怆,也同样会发出今古沧桑的感怀。历史文化的发展是缤纷复杂的,也充满了偶然性的变数,因此,不同文化传统的独特展现,在特定的历史节点有时居然若合符节,甚至因为类似的外铄因素,而产生“历史错位”,使得本来是南辕北辙的藝术心灵,在同一个时间平台上,关怀相似的人生处境,让我们在回顾历史时,产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感觉,从而加深普遍人性的艺术幻觉。汤显祖(1550-1616)与莎士比亚(1564-1616),就是一项探讨文化艺术产生历史错位的议题。
比较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我们到底想要比较什么?一般学者首先会想到,比较他们的文学作品,比较已经成为文学经典的“文本”,特别是可以在舞台上演出的剧本,设置一个客观的标准,比较他们的文学成就,甚至比出孰优孰劣。有人认为,他们的剧本是客观存在的艺术文本,已经独立存在,不再受到写作者的控制,可以由我们从文学批评的标准来做出评价。其实,这样的想法问题很多。什么是文学批评的标准,是作者的写作意图,是解构主义的批判观点,是历史主义探讨作者与时代风气的关系,是涉及女性观、种族观、阶级观、宗教观的认知盲点,还是只注意文字结构与意象修辞的排列组合?何况,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的剧本是要在舞台上演出的,其艺术成就不能排除表演艺术的因素,不能忽视历代演出的艺术传承。特别是汤显祖的戏曲作品,涉及音乐唱腔以及载歌载舞的表演身段,与莎剧舞台呈演的方式相距甚远。怎么比?
比来比去,不啻在比较橘子与苹果的优劣,在众声喧哗中比谁的声音大。若说不清比较的立足点,是比不出什么名堂的。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十六世纪末到十七世纪初,死在同一年,这是历史错位的偶然性。他们生活的中国与英国,在文化艺术传统上大体是隔绝的,虽非“萧条异代不同时”,却是“萧条同代在异地”。对我们做比较研究而言,探讨他们的艺术成就,“怅望千秋一洒泪”,最轻易的方式,是超越时空的形而上感怀,抽离具体的人生体验,侈言文学艺术无国界、无时空隔绝,一切都以人类普世化艺术追求的标准来定位,来评判高下优劣。这种充满优越感的普世化标准,基本上排斥了不同地域文明发展演化的意义。普世化标准的绝对化,不顾及人类文明的时空性,其实是无限夸大了研究者与评论家的当前性与在地性,昧于自身认知的局限,以主观能动替代客观存在,可以把新石器时代文明肇始与二十一世纪全球化文明认知混作一谈,放在同一杆秤上衡量,完全不管各地文明发展的相对独立性,摒弃了文明认知与艺术审美的多元标准。
比较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我们想要知道什么?我们又是在怎样的历史框架下做这个比较?假如主观化了的普世框架不灵,采取多元文化标准,我们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会不会众说纷纭,“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出现“鸡同鸭讲”的现象?我想,只要能够清楚分辨鸡是鸡、鸭是鸭,橘子是橘子、苹果是苹果,各溯其源,各识其流,各安其位,比较不同文化的艺术产品,是能提升我们的审美认知的。假如我们都肯定汤显祖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白眉,是伟大的文学家与戏剧家,而莎士比亚则是英国文化传统的中流砥柱,他的剧作代表了西方文学与演艺的顶峰,为什么要以单一标准比出优劣高下,而不是在对比之中,展示东西文化艺术探索的不同面向?
二○一六年是汤显祖、莎士比亚、塞万提斯逝世四百年,值得全世界爱好文学艺术的人顶礼膜拜,纪念他们为人类文明做出的贡献。他们在同一年逝世,当然只是个巧合,不可能是上帝为了展示文学艺术的普世意义,召回三个萧条异地的文曲星。那么,这个巧合,是否也有特殊的历史意义?这个四百年,对我们的文明认知有什么影响,如何塑造了我们对他们艺术成就的理解,又如何让我们逐渐认识他们的伟大贡献?
 最早的莎士比亚铜板蚀刻像
最早的莎士比亚铜板蚀刻像我们暂且撇开塞万提斯,只就今天的主题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来谈他们的艺术成就与文化贡献,也同时审视我们在四百年间,是如何逐渐认识他们的伟大成就,把他们推上了顶礼膜拜的神坛的。我们不要忘了,在四百年前,汤显祖与莎士比亚还在世的时候,虽然人们赞扬他们的作品,欣赏他们剧本的演出,但却不认为他们有什么伟大之处,当时的人们不会想到四百年后他们居然成了享誉全世界的文化巨人。他们逝世一个世纪之后,虽然官方正史《明史》上汤显祖名列其中,却只提到他曾参与政治斗争,关于文学艺术的成就只有这么几个字:“少善属文,有时名。”连他写的《牡丹亭》剧本、创作“临川四梦”都不提。而莎士比亚,更是不配与英国的贵族名流并列,整个十七世纪,他连一篇正儿八经的传记都没有,以致到了今天还会有些莫名其妙的学者,质疑莎士比亚到底是谁。
二
要了解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的伟大,首先要回到他们生活的时代,了解那个时代的历史意义。他们所处的时代,分别是中国的晚明时期与英国的伊丽莎白时代,都是历史大转折时期,政治环境波动反复,经济发展活跃繁荣,社会出现地域性的阶级冲突,在文化艺术方面则发展出独特的审美追求与境界。他们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就像游泳健儿在时代洪流的急湍险滩之间展现出美妙的泳姿,超越了时代潮流翻腾灭顶的危险,抵达艺术世界的江渚。回顾巨浪滔天,多少人挟泥沙以俱下。汤公与莎翁都是文学巨匠,文学创作的想象能力超乎当时的一般作者,以文字追求艺境,构架出想象的世界,以超强的感性、飞翔的想象、无所羁绊的艺术触角,探索人性的幽微,摸索人生的复杂意义和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处境。他们的作品,展现了时代的前瞻性,在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大变动的环境下,思考人生在世的意义。假如每个人的存在都面临生老病死,“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世事到头皆成虚幻,生命的意义何在?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的伟大之处,就在于通过戏剧这种艺术形式,以具体的人生角色,虚构出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俗世实情,表达“人生大舞台,剧场小世界”,提供了超越他们时代的思想内容与审美观照。
先说他们所处的历史背景。从四百年后的今天回顾,我们无法不从全球史的视角来思考。汤公与莎翁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充满了变数、肇始新时代的世界。从历史学时代分类的角度而言,当时属于早近代(Early Modern),我称之为“早期全球化雏形时代”。欧洲人发现新大陆、新航路,前往美洲拓展,打开了欧亚的海上直接通路。那个时候,欧洲与中国有了直接的联系。葡萄牙人从印度洋一路来到东方,西班牙人由新大陆来到菲律宾马尼拉,将太平洋和大西洋贯穿了起来,全球一体的世界格局出现。中国盛产的丝绸、瓷、茶连接起早期的“一带一路”,颠覆了整个世界经济、文化的秩序。美洲本身其实也很重要。弗兰克的《白银资本》(1998年出版,中文版2008年出版)中指出,其实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西方经济史家就已经开始研究美洲白银对欧洲金融和经济的冲击。威廉·莱特尔·苏尔兹(William Lytle Schurz)在一九三九年出版的The Manila Galleon,明确陈述了西班牙大帆船跨越太平洋,通过控制马尼拉,对东亚经济造成了白银冲击。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休格特(Huguette)和皮埃尔·乔努(Pierre Chaunu)出版的九卷本Séville et l'Atlantique (1504-1650),更是事无巨细地记录了美洲白银,如何通过西班牙的塞维尔,影响了整个欧洲的经济生活。这些过去的重大学术著作,只是没有放到全球史这样的一个框架里,在宏观历史的视野中,详细讨论美洲白银的出现,是如何冲击了整个欧洲旧大陆的经济结构,又是如何波及亚洲,开启了环球地缘经济的新局面。到了二十世纪末,大家才清楚地认识到,原来美洲白银的影响是全球性的。中国一直是一个产银很少的国家,早期从日本进口,后来美洲白银大量经马尼拉流入中国,造就了晚明东南沿海一带商品经济的发达,刺激了社会生活的繁荣,构成了大运河和长江流域的消费意识与精致文化网络,出现草根型的商品经济变化,滋生思想文化探索的环境与氛围。
在十五世纪的文化意识领域,中国出现了阳明学派的内向探索,在追求圣贤之道的过程中,摆脱官方程朱理学的意识限制,解放个人思想的藩篱,引发缤纷多样的思想潮流。阳明学派中的泰州学派及民间盛行的三教合一风气,培育了李贽与汤显祖这类不同流俗的知识人,他们肯定主体认知,探索超越性的文化与艺术。就欧洲而言,文艺复兴的影响是铺天盖地的,不但逐步脱离宗教的桎梏,从封闭性的单一信仰走向多元的客观世界,也在挑战上帝权威、质疑教会思想霸权之后,使得人们掌握自我解释知识的权利,形成多元认知的现象。
发展到十六世纪中期以后,中国农业国家的权力结构基本未变,可是欧洲变了,欧洲开始了商业革命与工业革命,展开了掠夺性的经济与殖民扩张。因此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是整个东西方实力易位的开始。中国出现的情况是,清军入关,坚定维持农耕大帝国的架构,而欧洲的现代化进程正在起步。到了十九世纪,整个世界都改变了。我们回顾这四百年来的历史,会发现晚明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是一个文化、思想开放探索的时代,却因清朝专制严控而早夭。然而,回到当时,就必须认识,晚明中国与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有类似之处。晚明时期的中国商品经济发达、社会生活繁荣(以江南为中心,沿长江及大运河十字轴线辐射扩散),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商品经济发达、社会生活繁荣(以伦敦为中心,向周边扩散);晚明时的阳明学派强调个人良知,肯定主体(多元认知),欧洲的文艺复兴强调客观认知,宗教改革强调主体信仰的选择(多元)。两个国家都为文化人与艺术家提供了开放的想象空间。
当时中国的戏曲发展迅速,内容呈现人生的多样化,形式雅俗共赏。南戏自明代中期,因社会经济的繁荣,在各地广为流传,得到充分发展,各种声腔兴盛纷纭,有弋阳腔、余姚腔、海盐腔、昆腔,以及各种配合地方腔调的演艺,而最有艺术探索价值的是海盐腔和昆腔。嘉靖万历年间,海盐腔盛行,此后是昆腔。各种唱腔,加之各种角色,就能表达不同人的不同思想脉络和情感,因此,戏曲内容呈现人生处境,表演形式多样化,反映了社会繁荣与思想控制的松动。文人作家大量涌现,明传奇剧本不下两三千种,汤显祖就是最出色的作者。
西欧的演剧情况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原来流行的宗教教化剧或奇迹剧、道德剧,纷纷让位于世俗的人文剧。莎士比亚那个时代,伦敦建起了许多公共剧场,不同社会阶层的人都可以观赏戏剧作为娱乐,同时涌现了一大批写作剧本的高手,比如极负盛名的马洛,以及一批出身牛津、剑桥的文人,最重要的是投身演艺事业的莎士比亚。当时的英国社会有基督教的新旧之争,又赶上殖民热潮的经济拓展,文化艺术受到国势的崛起与新旧观念的纷争,出现思想意识开放的刺激,爆发文化艺术的探新能量,开始讨论起了人生际遇与生命意义。当时历史剧云涌,其实这些舞台上演出的历史剧都是“戏说”,即使不是意在讽喻,也是对当下社会的历史阐释,探讨人性在具体历史环境中的困境与解脱。这种充满新思维的历史剧,展示了历史人物的多重复杂性格,更通过不同阶层的角色,颠覆了宗教剧的一元教化思维,让不同性格、不同阶级利益的角色展现纷繁复杂的人生态度与追求。在这个意义上,莎士比亚的剧作为多元思想提供了最精彩的呈现,舞台上有血有肉的人物,展示了丰满的人文精神,为文艺复兴的理念做出了无可磨灭的伟大贡献。
三
历代讨论汤显祖“临川四梦”,经常纠缠在“案头之书和筵上之曲”的议题上。有些批评指出,汤显祖的剧作是戏剧文学,与舞台戏曲演出(特别是昆曲演出)有龃龉之处。其实,这不是真正的问题,问题出在“崇词派”与“尚律派”文人无聊的意气之争。从剧本到演出,一定要经过调整,才能在舞台上大放光芒。没有好剧本,怎么调整发挥也难臻艺术的境界。四百年下来,我们可以看到,沈璟的剧作,所谓“尚律派”的标兵,已没有太多人关注了。不过,这场争论也显示了汤显祖最注重的是剧本的“意趣神色”,是传统文人对文学性的尊崇。他是剧作家,更是传统的诗文大家,虽然着眼于演剧的技艺,但与大多数写作传奇的文人学士一样,本身不是演员,不是从事具体舞台演出的工作者。汤显祖成为大剧作家,与他处的时代有关。那时正值中国南戏出现雅化的倾向,文人雅士竞写配合雅调(海盐腔与昆腔)的戏曲,向典雅的诗词歌赋传统靠拢,造成昆曲风靡全国、雅调独领风骚的景象。由俗入雅的倾向,使得文人剧作家得以探索人生際遇与生命意义。在这个方面,汤显祖是最杰出的。
欧洲的戏剧,一直到伊丽莎白时代,主流剧本写作还是按照“三一律”的时空限制,形式的规矩束缚了广阔的跳跃式时空场景变化。莎士比亚的不羁想象,打破了“三一律”的牢笼。在欧洲文艺复兴的氛围中,莎士比亚与明清的文人剧作家完全不同,他的身份是个演员与舞台工作者,具有编导演三位一体的性格。斯坦利·韦尔斯(Stanley Wells)在Shakespeare: For All Time书中说道:“他首先是个剧界中人,写戏是为了演出,而非供人阅读。”《牛津版莎士比亚全集》(1988)编者按语也指出,“莎士比亚写下的是台词,那是写给观众听的,而不是供人阅读的”。当然,过去也有不同的意见,如赛缪尔·泰勒·科尔里奇(Samuel Taylor Coleridge)、威廉·黑兹利特(William Hazlitt)、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这些文学大家的看法就不同,认为莎士比亚剧作是文学经典,许多戏词需要沉下心来阅读,才能体会其中蕴意。演出只是看热闹,不是看门道。
约翰生博士在《莎士比亚戏剧集序言》(1765)中说:
莎士比亚的戏剧,从严格的和文学批评的意义上说,既非悲剧,又非喜剧,而是某种自成一格的作品,展示了人间的真实状况,其中有善也有恶,有欢乐也有悲辛,就其比例以及糅合的无数种形式而论,真是变化无穷。他的剧本还表现了世事的轨迹:一个人之所失乃是另一人之所得;寻欢作乐的人迫不及待酗酒去的同时,吊丧客却正在埋葬亡友;某甲的恶毒诡计有时会被某乙闹着玩的把戏所挫败;多少祸福得失都会在偶然之中得以实现或防止。(陆谷孙译)
汤显祖与莎士比亚出身不同,人生追求不同,对文章不朽的看法不同:莎士比亚是职业艺人,在剧团演戏并写戏,他在生前从未安排出版自己的剧作,只是将自己的作品视为演剧的底本,写作的动机是为了谋生。汤显祖不同,他对自己的作品视若珍璧,“一字不能易”。从汤显祖与沈璟的冲突可以看出,他强调文章的“意趣神色”,强调文学作品的境界。
将这两个人的生平对比起来看其实挺有趣的。汤显祖是书香门第,家里世代都很有钱,虽有功名,但不太高,只出过秀才。到了汤显祖,他二十一岁中举,承袭了士大夫家庭的君子传统,师从阳明学派分支泰州学派罗汝芳大师,深受其“修齊治平”思想的影响,但最后厌倦仕途而归隐写作,留下不朽的“临川四梦”。而莎士比亚出身于中下层,家里是做皮毛生意的,父亲靠给贵族做手套发家。莎士比亚在伦敦参加剧团演戏编剧,事业有成,还花钱给父亲买了一个族徽头衔,努力攀升到“乡绅阶层”,成为职业剧作家,一生写了三十九部戏,是全世界公认的大文豪。尽管有着不同的文学艺术传统,不同的历史文化体验,但是两人却具有相似的文学艺术想象和人生处境关怀。换句话说,他们两个人的社会身份很不同,汤显祖属于上层精英阶层,想要延续的是传统的士大夫精神;莎士比亚属于新兴的中下阶层,靠写作和演艺谋生。
 汤显祖画像。陈作霖摹,1838 年
汤显祖画像。陈作霖摹,1838 年他们两位都著作等身。我们往往说莎士比亚的著作要比汤显祖多,这是对的,汤显祖只有四部剧本。但汤显祖其实不只是剧作家,他还是大诗人,是以诗、文、赋在精英阶层的文学传统中成名的。汤显祖的赋写得特别好,研究汤显祖的话,可以研究一下他写的赋。
四
我强调“历史错位”,主要是说,他们生活在地球上的同一个历史时代,却继承着不同的文学与演艺传统。中国文学源远流长,有着清晰的脉络。英国文学也有其独特的脉络,主要是从希腊罗马这一路下来,当然还包括《圣经》的传统。经过文艺复兴的重新省思,西方文化传统挣脱了教会的钳制,全部打散后重新组合,于是英国开始了现代的白话文学。汤显祖与莎士比亚都生活在体制松绑的时代,虽然文化传统不同,影响作家在遣词用字、思维脉络上的想象空间。但是,他们都有超凡的文字想象能力,在思维方式、文字意象、对人生处境的体会上非常接近,描写爱情,刻画生命面临的选择,都栩栩如生,这是成就伟大作品的关键。过去通行的剧作套用传统程式,千篇一律,对人生处境没有深刻的关怀与思考。其实每个时代的人,在一生中都会面临很多重大选择而不自觉,有人感恩天赐,有人悔恨终身,这些在两位文豪的笔下都探索得鞭辟入里。他们身后的世界,因经济社会的转型,产生了现代殖民扩张与工业化的进程,也造成东西方经济政治势力的易位。回顾四百年前创作的环境,由于文化传统不同,思想脉络不同,两人的作品也展现出不同的内容关注。但是,他们却有相同的人类文化求索,这一点,是需要强调的。历史错位让我们看到西方文化霸权的兴起,展示了莎士比亚在全世界的长远影响,一直到当前的二十一世纪,远远超过汤显祖。再过四百年呢?这我们就不知道了,因为涉及以后的文化兴衰,很难说。
莎剧的演出传统,基本上变动不大,但也经过各类删减改编,到了二十世纪初,特别是经过哈利·格兰维尔-巴克(Harley Granville-Barker)的研究与演绎,才基本定型,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建立起莎剧演出的模式。T. S.艾略特曾经指出,哈利·格兰维尔-巴克的四大册Prefaces to Shakespeare,开创了莎剧演艺的崭新局面,厥功至伟。有了电影以后,莎剧也一直是保留剧目,改头换面后演出,持续莎士比亚的影响。有声电影开始,莎剧就一部一部地接连着演,不但助长了西方的文化优越感,也在东方造成类似的影响。著名莎剧演员劳伦斯·奥利弗(Lawrence Olivier)在一九四八年主演的《王子复仇记》(Hamlet),过了七十年,依然在中国脍炙人口,其后还有各种演出版本,不断制造与巩固莎剧独占鳌头的文化地位。一九九八年好莱坞推出影片《莎翁情史》(Shakespeare in Love),糅杂了伊丽莎白时代的演剧情况与莎士比亚的生平,基本上是“戏说”《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创作背景,属于杜撰的历史剧,但是有莎剧专家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参与制作,让热闹情节呈现的生活细节基本上符合历史实况。剧中饰演伊丽莎白女王的朱迪·丹奇(Judi Dench),是大家熟悉的演员,在后期007系列电影中饰演英国女情报头子,但是她主要是位著名的莎剧演员,而且因为塑造莎剧角色出众,获颁英国爵位。她在一九六○年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影片中,饰演朱丽叶,深获好评。
说到戏剧的思想性问题,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的剧作,历经四百年而不过时,还受到现代读者与观众的讴歌,证明其中有不可磨灭的前瞻意义。汤显祖在《牡丹亭》“标目”中写道“世间只有情难诉”,“但是相思莫相负,牡丹亭上三生路”,就是他对“至情”的阐释。《牡丹亭》整出剧的故事展现,赞扬了生生死死的至情追求,其“题词”中就说:“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杜丽娘的梦中出现了她理想的情人、理想的伴侣、理想的婚姻,所以她为自己的幸福而追求,生生死死,不改其志。其思想性一如阳明学派讲的“致良知”,追求主体认知的美好境界与世间至情。追求的是理想、光辉的未来,带有强调个人自我的叛逆性,与当时一般的才子佳人剧极为不同。在程朱理学盛行的时代,这出剧的哲学性、思想性很强,甚至还有文化意识的颠覆性。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中也有类似的情节,世家无法解脱的世代冤仇,因为恋人追求至爱的殉情,而捐弃前嫌,改变了历来墨守的传统。配合莎士比亚在其他剧作中展现的理性宽恕与多元心态,我总觉得这出殉情戏带有强烈的思想性,颠覆了家族钳制个人情感倾向的专制,反映了文艺复兴以来肯定自我本体的宽容多样。
再来看看文字修辞的巧妙,这方面汤显祖和莎士比亚可谓旗鼓相当。他们都会借鉴别人的故事与文字,但不是随便抄袭,而是点铁成金,进行修改与提升。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所有剧情,大都能找到传说或历史小说的原型。汤显祖的《牡丹亭》借鉴了《杜丽娘慕色还魂》话本,《紫钗记》则借鉴的是《霍小玉传》。但是由于汤公与莎翁表达人情关怀的广度和探索人性的立足点深刻,高瞻远瞩,他们写出的东西确实比原作更好,达到的意境也有所超越。即使是袭自前人的只字片词,但凡涉及情景需要表现得更为深刻,一定都做出极其巧妙的变动。比如沉鱼落雁、闭月羞花、良辰美景、赏心乐事这样的成语,汤显祖在《牡丹亭·惊梦》中就用了“不堤防沉鱼落雁鸟惊喧,则怕的羞花闭月花愁颤”,“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这些改動之后的文辞,充满了杳渺婉转的情思,再也不是浮滥的老生常谈,勾起了读者与观众的文学想象及参与感。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也是这样,在阳台会情节中,罗密欧展露他内心的爱恋,一见钟情,他形容朱丽叶有一双明媚的眼睛:“Two of the fairest stars in all the heaven,/Having some business, do entreat her eyes/To twinkle in their spheres till they return.”(朱生豪中译:天上两颗最灿烂的星,因为有事他去,请求她的眼睛替代它们在空中闪耀。)又比如,他在《威尼斯商人》写犹太人夏洛克的邪恶,通过契约的法律约束,要割下威尼斯商人的一磅肉,残忍而血腥。第三幕中有一段细节铺垫,让夏洛克迸发出他积怨已久的愤恨:“I am a Jew. Hath not a Jew eyes? Hath not a Jew hands, organs, dimensions, senses, affections, passions? Fed with the same food, hurt with the same weapons, subject to the same diseases, healed by the same means, warmed and cooled by the same winter and summer as a Christian is? …If you poison us, do we not die? And if you wrong us, shall we not revenge?”(朱生豪中译:我是一个犹太人。难道犹太人没有眼睛吗?难道犹太人没有五官四肢、没有知觉、没有感情、没有血气吗?他不是吃着同样的食物,同样的武器可以伤害他,同样的医药可以疗治他,冬天同样会冷,夏天同样会热,就像一个基督徒一样吗?……你们要是用毒药谋害我们,我们不是也会死的吗?那么要是你们欺侮了我们,我们难道不会复仇吗?)对比阅读,我们可以发现原文雷霆万钧,而译文是多么拖泥带水。莎士比亚写夏洛克,本来是刻画刻薄的犹太人,但同时也通过文字细节,描述了犹太人受尽欺侮的痛苦。十九世纪犹太裔的德国诗人海涅看《威尼斯商人》一剧,当夏洛克说到我们犹太人也是人,也有眼睛也有手脚,有血有肉,却遭受压迫与侮辱,不禁泪如雨下。这就是艺术的力量。

五
除了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莎翁作品,我还想提一部谈论爱情的喜剧《爱的徒劳》,一个简单的爱情小故事。声称不近女色的国王和他的臣子去清修院静修,见到漂亮的法国公主和其侍女后陷入爱河,把之前定下的清规戒律全都忘记了。
初看这部剧,你可能觉得它是一部单纯的宫廷喜剧,讽刺这些王公贵族心口不一,但你若细细揣摩整个情节,其实这出戏探讨的是关于爱情的理论与实际。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皇亲国戚,从下到上,没有人不被爱笼罩,为爱烦恼,因爱困扰,神魂颠倒。一个人即便位高权重,想抗拒爱的魔力,也是徒劳。在剧情的时代背景下,明确表达对爱情的向往,也是对禁欲主义的讽刺。剧中有一个角色叫俾隆,本来是剧中最玩世不恭的人,世间感情在他看来不屑一顾,但他遇到真爱以后,却用情最深。他陷入爱河之后,茶不思饭不想,寝食难安,却也感受着迷离失落的刺激快感,“恋爱是充满了各种失态的怪癖的,因此它才使我们表现出荒谬的举止,像孩子一般无赖、淘气而自大;它是产生在眼睛里的,因此它像眼睛一般充满了无数迷离惆怅变幻多端的形象,正像眼珠的转动反映着它关照的事事物物一样”(朱生豪译)。
两位大师笔下的小人物,也描绘得活灵活现。比如《爱的徒劳》里的学究亚马多,呈现得十分巧妙,主要是通过他说话的遣词用字,时不时地显摆自己似通非通的拉丁文,就像《牡丹亭》里的陈最良,总是引经据典说些无关紧要的日常话。亚马多坠入爱河,奋力抵挡爱情的引诱,说“爱情是一个魔鬼”,接着却说,“可所罗门也曾被它迷惑,他是个聪明无比的人”。这展示了他心里涌现了无限波澜,抬出智慧之王所罗门,其实就是说:这些聪明的人都没办法逃脱爱的牢笼,我若不幸陷入爱河,似乎也情有可原。
正是这些丑角的登场,展示社会的三教九流,反映了纷杂繁复的人生实况,使得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的戏剧更生动、更跌宕,也更可爱。我们虽然莫名其妙接受了西方戏剧的分类,武断划分这是喜剧,那是悲剧,但不能忘了,戏剧终究如约翰生博士所说,是生活的再现、反思和升华。一出戏有了丑角的插科打诨,不管是喜剧还是悲剧,或是专家也说不清楚的悲喜剧、寓言剧、象征剧、超越剧,就切切实实接上了地气,以反讽的手法,呈现了真实生活中荒诞的形形色色,不仅观众的心情有了调节的余地,整个情节也更生动。类似的小人物,如《李尔王》中的弄人、《暴风雨》中的卡利班(Caliban)。《牡丹亭》里则有学究陈最良、石道姑、癞头鼋,《邯郸记》里面有崖州司户,不一而足。《牡丹亭》里的石道姑,颠倒了《千字文》的字序,以此叙述自己生平遭遇,把枯燥无聊的识字课本,解构成低俗色情的胡闹,调笑讽刺传统蒙学教育,让人啼笑皆非。令人失笑之余,还可以想象当时观剧的卫道人士的反应,是当成滑稽的乡语村言,还是大逆不道的污蔑谰言,挑战了道德底线呢?
汤公和莎翁对人世的观察,有一种超越时代的特殊眼光,充满了穿透世俗迷雾的智慧。他们描绘人类生老病死,一定会经过几个阶段,说得天经地义、日用平常。莎翁在《皆大欢喜》里指出,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舞台,我们每个人都在表演。人的一生,总要经过七个人生阶段:从清晨般朝气蓬勃的婴儿、怨天尤人的小学生慢慢长大成为社会人,成为叹息连连的情人、鲁莽但满怀激情的士兵。再长大一些,身材发福,身份也变成法官,还不时说出一些至理名言。最后,我们变成了消瘦的傻老头,渐渐地,没了牙齿眼力,没了口味,尘世万物逐渐远去。汤显祖的《紫箫记》里,有一段借四空禅师之口,谈论人生的片段:人生十岁童稚时期,终日戏耍。二十岁衣着光鲜,三十岁一心奔波慕功名,四十岁终于功成名就。等到了五六十岁,开始享受身份地位带来的锦衣玉食。七八十岁,容颜渐衰、心智渐微。直至最后老来混沌糊涂,死灭归于大化。
这种戏词的巧合反映出两大文豪的敏锐心灵,他们对人生的观察有着惊人的相似。但说到底,人生的真谛是一致的,有其物理的普遍性,不受时间空间的阻隔,生命的内核和意义是相通的,只是外在的文化传统不同,风俗习惯的包装不一样。
除了对人生的观察,两人对思维想象的飞跃翱翔有着特殊的感受,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说的:“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也因此,人们对于神思想象的飞跃,对梦境超越现实的恍惚迷离,有着无限的依恋。汤显祖的“临川四梦”,都探讨了人生如梦的现实与空幻。《紫钗记》还有个别称是《鞋儿梦》,“本传开宗”中有“黄衣客强合鞋儿梦”;《牡丹亭》也叫《还魂梦》;《南柯记》与《邯郸记》,都是梦。除此之外,他还写过长诗《梦觉篇》,叙述了达观和尚来书,唤醒他的春梦,点化了生命真幻。莎士比亚有《仲夏夜之梦》《暴风雨》,都专门写了梦。其中《暴风雨》的收场诗也是莎士比亚的收笔之诗:“高兴起来吧,我儿;我们的狂欢已经终止了。我们的这一些演员们,我曾经告诉过你,原是一群精灵……都将同样消散,就像这一场幻景,连一点烟云的影子都不曾留下。构成我们的料子也就是那梦幻的料子;我们的短暂的一生,前后都环绕在酣睡之中。”(朱生豪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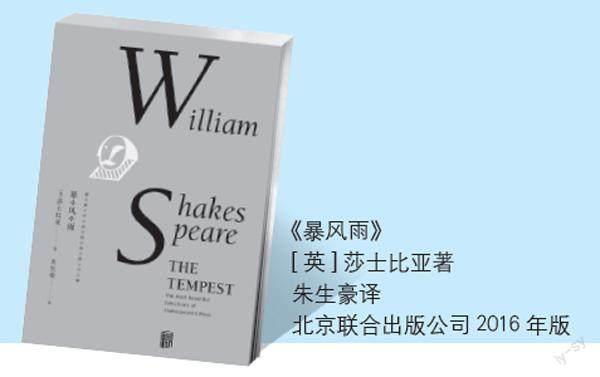
我们拿汤公与莎翁比较,必须提醒自己,是在比较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洋文化传统,可以对比,但不要陷入文学艺术无国界的陷阱。所谓“理一分殊”,是上升到哲学思维的普遍人性探讨,经常脱离人生实际的缤纷多彩。文化傳统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有相通,也有分歧,剧场展示的人生尤其如此。中国的剧场是雅俗共赏的,是精英与市井交汇之处,但汤显祖是偏向精英的阳春白雪,直祧古典文学的血脉;莎翁出自新兴的中下层阶级,文字游走在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之间,作品主要面向市井阶层。欧洲的文艺复兴,促使文学从拉丁文变成现代英文,莎士比亚的文字是现代英文的滥觞;汤显祖继承中国诗文传统,曲文文字集古典文学的大成,宾白则是口语白话。通俗白话文的出现,成为主导的文字表述,跟文化发展的关系很重要。西方白话文出现是四五百年连续性的发展,从乔叟到莎士比亚,奠定了现代英文写作的基础。中国的白话文发展则是断裂性的,从晚清到五四这二十年间才突然爆发,随政治革命成为文化主流,这就造成一系列文化传统的继承问题,现代中国人面临古典诗文与戏曲经常茫然不知所措。汤显祖文字虽美,奈何怎么也读不通;以白话翻译的莎士比亚则文从字顺,开卷即懂。
六
汤显祖出身书香门第,祖上虽然没有功名,却广有田产,藏书富赡,从小就出类拔萃,傲视群伦。他诗词歌赋都写得好,而且才名远播,连当朝内阁首辅张居正都对他青眼有加。他三十七岁的时候,写了生日诗,回顾了前半生,意气风发,有澄清天下之志,却拒绝了权相的拉拢,不愿意参与政治上的勾结。从此他远离官场的蝇营狗苟,置身政海波涛之外,后来还因批评朝廷而遭贬岭南,成了政坛的局外人,把一腔心血化作文学追求的理想世界。莎士比亚的境况完全不同,因为当时的社会动荡与宗教冲突,莎士比亚家道突然中落,他不得已辍学,几番折腾后终于背井离乡,到伦敦参加剧团,开始演戏、写戏,甚至参与编导和剧团业务。他由此而富裕置产,回家买地盖房,又在伦敦置业,还为父亲捐了乡绅的资格,俨然靠演剧事业兴家。两人的社会背景不同,追求的方式也不同,却都因生花妙笔而流芳百世。
汤显祖的诗文明确展示生命理念的追求,在剧中也偶尔会透露自身的人生理想。他写《紫钗记》,在第一出“本传开宗”就说:“点缀红泉旧本,标题玉茗新词。人间何处说相思?我辈钟情似此。”要探索“情”的生命意义。他罢官回乡,写了首诗,表达自己脱离官场的心境:“彭泽孤舟一赋归,高云无尽恰低飞。烧丹纵辱金还是,抵鹊徒夸玉已非。便觉风尘随老大,那堪烟景入清微?春深小院啼莺午,残梦香销半掩扉。”(《初归》)头两句用的是陶渊明归田园的典故,罢官回乡,不受官场的气了。接着的两句非常有意思,是说闭门炼丹虽然也会失败受辱,但到头来黄金还在;拿一块玉石去掷赶鸦鹊,玉石则会碎裂而浪掷。在官场上虚度光阴,哪能进入清风吹拂的文学美景?还不如回到鸟啭莺啼的春天小院,在香销的残梦中续写文学想象的世界。汤显祖这时回到自己的家乡临川,续完了他的《牡丹亭》,诗中意境写出了他撰述《牡丹亭》的写作氛围与追求。
 莎士比亚家乡的圣三一教堂在他去世后给他立的塑像
莎士比亚家乡的圣三一教堂在他去世后给他立的塑像莎士比亚剧作纷繁,他一般借着剧中人表达自己的人生观察,并展示了不同角色多元的思想与见解,因此难以锁定剧作者本人一贯的思想。但他的《十四行诗》第十八首,倒是明确表露了他对文学不朽的态度。诗一开头是赞扬献诗的对象,最后几句说的是:
But thy eternal summer shall not fade(你的夏天永不消逝),Nor lose possession of that fair thou ow?st(你的美貌永不消失),Nor shall death brag thou wander?st in his shade(死亡不能夸耀说你进入他的阴影),When in eternal lines to time thou grow?st(你在不朽的诗句中成长),So long as men can breathe, or eyes can see, So long lives this, and this gives life to thee.(只要有人呼吸,有眼睛能看,我诗长存,让你得永生。)
莎士比亚明确表示了文字的力量,只要人类长存,文学不朽,写入诗中的人物就会得到永生。
莎士比亚在《暴风雨》的结尾也讲世代繁衍,人生不朽,同时在剧中联系了新大陆的发现,出现了剧中的名言“美丽新世界”:“O, wonder! How many goodly creatures are there here! How beauteous mankind is! O brave new world. That has such people in?t!”《暴风雨》写魔法岛,是发现美洲新大陆给他的灵感,虽然想象是想象,想象世界不能钉死在历史现实的柱上,但是与历史有所关联却是无可隐晦的事实。《暴风雨》结尾出现了对新世界的憧憬,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在Marvelous Possessions: The Wonder of the New World(1992)一书中指出,《暴风雨》是受了当时哥伦布等人发现新大陆的影响,寓意着新兴的资本主义世界即将到来。拉丁美洲的莎士比亚研究者特别指出这一点,显示欧洲殖民者奴役美洲原住民的情况潜藏在英国人的下意识中,让现代学者读得触目惊心。有一本很重要的著作,专写魔法岛的原住民卡利班人,写卡利班人如何被白人奴役(見Roberto Fernández Retamar,Caliban and Other Essay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9),显示新世界中有蛮荒,蛮荒之中有暴力,而暴力又被掩盖成美丽的风景。
文学反映时代的角度是曲折的,伟大的作品经常超越时代局限,在下意识的细节描写中,透露了普遍人性的复杂与善恶交织。时代的变化与重大事件对作者的创意会有影响,不同文化传统也在艺术创新之中出现新的转折。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汤公与莎翁生活的时代很特别,全球发生重大而长远的动荡与变化,真正有才华的人在这个时候特别能够趁势而创新。斯蒂芬·格林布拉特说,这是释放特殊能量的时代,全世界都在变,能量迸发,特殊有智慧的人能够得到感召,掌握时代的脉动,感知冥漠中勃发的生气,在创作中进行特殊的个人艺术调适,从中产生不世出的伟大杰作。天才就是天才,天才不必解释。可是我们必须知道,汤公与莎翁所处的时代出现了巨大的历史变化,之后的四百年,又出现了东西文化的历史错位。我不知道未来会如何,但是全球化的发展到了二十一世纪,历史文化错位的现象,是所有中国学者必须重视的,也是中华文化复兴的契机:我们对莎士比亚了解很多,对汤显祖了解得太少,只研究了《牡丹亭》。我觉得纪念汤公和莎翁逝世四百周年,对我们也是个提示、重新思考和诠释的机会。
本文系作者在新华·知本读书会第四十二期所做演讲,二○二二年九月经作者修订





